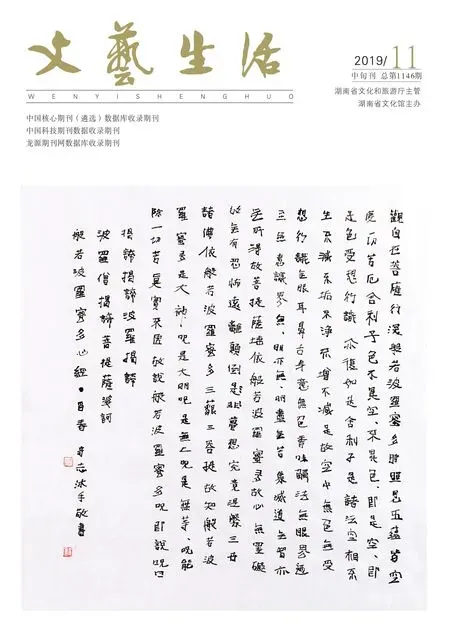大时代下的小人物
——浅析电影《芳华》及其人物建构
张旭婷
(青岛大学,山东 青岛 266071)
一、引言
电影《芳华》对人物角色的塑造别具匠心,生动的展现了在历史洪流作用下,小人物所拥有的充满着变数的人生命运以及特殊时代环境影响下所形成的人性的善与恶。本文将借助拉康的镜像理论和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分别对《芳华》中何小萍、刘峰两个角色进行人物分析,通过探讨人物自我意识的构建过程来还原中国特殊时代的社会样貌。
二、“他者”认同下的自我确立
拉康的镜像理论被诸多电影运用到人物角色的构建上,指的是所有混淆了现实与想象的情景意识称其为镜像体验的理论。《芳华》中的何小萍,身世悲惨,从小缺失了亲情,造成了何小萍性格的边缘化,长期受到战友的排挤使她的心里特别能理解刘峰的遭遇,何小萍在刘峰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完成了镜像认同。何小萍也由此对刘峰产生了自恋性的“镜像之爱”,因此她恨林丁丁,讨厌文工团,宁可去前线也不愿留在舞台上跳舞。
拉康认为自我的认同是具有“他性”的,而“他者”可分为“小他者”和“大他者”。“小他者”即镜子中最初“我”的影像,以及周围包括父母和社会关系对“我”所实施的语言与行为。小他者是形象、感性的,而“大他者”的概念则更抽象和宏观,它可以是某种社会需求、文化影响、社会制度。改嫁的母亲、没有平反的父亲、嘲笑她的队友、被人诬陷的刘峰,这些都是影响何小萍的“小他者”。而影片中出现的像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对越自卫反击战等特殊时代环境下的各种符号则都是“大他者”化身。演出时装病的何小萍,却被政委利用这件事来宣传“轻伤不下火线”等口号;医院受到轰炸,何小萍用身体护住伤员,她意外的变为英雄,结果却是因为反差太大精神崩溃;战争结束后同是英雄的刘峰和何小萍依然贫穷落魄,与其他人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看似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选择就是时代大他者的影响,也是电影对社会符号秩序的讽剌。
三、“本我”对“超我”的反抗
弗洛伊德在心理动力论中将人的精神分为三个部分,即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基础,是潜意识中所有的最原始的本能和欲望。“自我”则是由“本我”分化出来,处于人格结构的中间层,调节着“本我”与“超我”两者间的矛盾。超我,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内化社会及文化环境的价值观念而形成的。
影片开头的刘峰是队伍里的“活雷锋”,是众人的榜样。此时的刘峰具有一种“超我”的人格,在周围人都是掺杂着“本能”的“自我”中,他变得格外的突出。他被众人异化成为没有人性中藏污纳垢、七情六欲的圣人。而那首邓丽君的歌曲的出现则打破了刘峰“超我”对“本我”原本的控制,人类最原始的荷尔蒙冲动让“本我”开始释放。“本我”与“超我”的对抗最后以“本我”的胜利告终,刘峰没有控制住拥抱林丁丁的欲望,他也因此从神坛跌落下来。众人通过排挤抑制刘峰的“本我”来释放自己的“本我”,人性有时就是这样让人又爱又恨。片中刘峰将之前所得的奖品证书全部处理掉,这也是他挣脱荣誉的束缚与“超我”人格的告别。他被驱逐出文工团、在战场上失去手臂、退伍后的生活更是贫穷落魄,但他并没有自我堕落,他依然会关心战友,帮助他人,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这样的状态则对应着一种“自我”的回归。
四、特殊时代下人性的光泽与幽暗
《芳华》这部电影在展现小人物残酷曲折的人生命运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讨人性与时代的切口。影片所讲述的特殊时代是动荡的、割裂的,在它影响下的人性的光辉格外显眼,只有在那个时代才能塑造出刘峰那样崇高的品格,也同样是那个时代亲手摧毁了它。片中众人对何小萍的嘲笑排挤,对刘峰善行的漠视以及后来对他的唾弃,无不将人性中固有的弱点与幽暗面表现的淋漓尽致。在那个特殊的集体主义时代,人性的弱点被放大,为了自保而不得不向更为强势的集体靠拢,一旦有个体产生了与集体相悖的立场,便会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口诛笔伐。影片中刘峰便是那个被集体所抛弃的个体,人们通过一起唾弃驱逐刘峰来找寻自己的集体归属感和安全感。人性的弱点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消失,只是在那个集体主义的大时代下,人性的光泽与幽暗都被无限放大,让观众感受到了超时代的共鸣,使观众触动的同时不禁对时代及人性进行反思。
在目前较为功利的电影创作环境下,《芳华》的出现是值得鼓励的,尽管这部影片存在叙事视点稍显混乱、个别情节的设计有待考究等瑕疵,但总体上来说瑕不掩瑜。影片在人物形象自我意识的塑造方面别具匠心,将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曲折命运刻画的淋漓尽致。作为一个反应特定时代的影片,缅怀青春、回忆见证一代人的芳华仅仅是它的表层含义,其对时代历史的反思、人性的探讨则更值得人们深思。
——
——拉康对《孟子》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