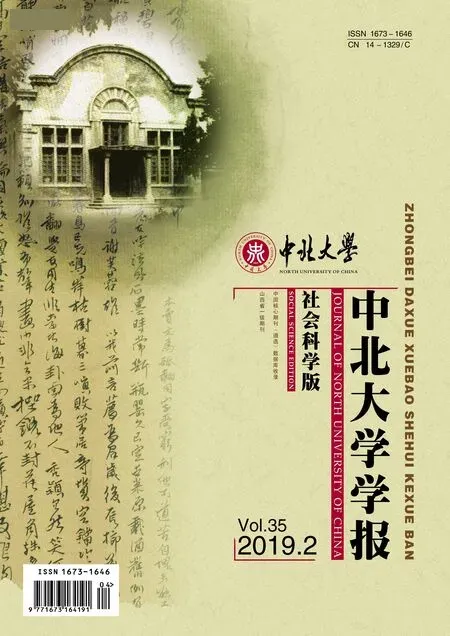《白驹》主旨考证
颜 敏
(广西大学 文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作为《诗经》中的名篇, 《小雅·白驹》共四章, 每章共六句:
皎皎白驹, 食我场苗。 絷之维之, 以永今朝。 所谓伊人, 于焉逍遥。
皎皎白驹, 食我场藿。 絷之维之, 以永今夕。 所谓伊人, 于焉嘉客。
皎皎白驹, 贲然来思。 尔公尔侯, 逸豫无期。 慎尔优游, 勉尔遁思。
皎皎白驹, 在彼空谷。 生刍一束, 其人如玉。 毋金玉尔音, 而有遐心。[1]378-379
1 《白驹》主旨众说梳理
《诗经·小雅·白驹》的主旨, 迄今主要有五类观点。
1.1 饯别友人类
这类观点按申说重点不同可分为两类。
申培的《鲁故》“《白驹》者, 失朋友之所作”,《韩诗》言“彼朋友之离别, 犹求思乎《白驹》”[2]600, 均认为此诗主旨是表达对友人的惜别之情。 龚橙《诗本谊》“伊人乘白驹过其隐退之友, 其友留之, 劝以勿忘隐遁”[3]293, 提出此诗乃留友隐遁之作。
1.2 讽刺时事类
这类观点按申说重点不同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刺宣王说出自《毛诗序》:言“《白驹》, 大夫刺宣王也”。 由此引申出二说:郑《笺》“刺其不能留贤也”“宣王之末, 不能用贤, 贤者有乘白驹而去者……愿此去者, 乘其白驹而来, 使食我场中之苗。 我则绊之系之, 以永今朝”[1]378-379, 以“伊人”为乘白驹而去的贤人, 认为此乃讽刺宣王不能留贤之作。 朱谋《诗故》言:“《白驹》, 大夫刺宣王也。 何刺乎?《鹤鸣》之应也。 王不纳诲, 贤者惧祸及身, 故去之”[4]587, 承《毛诗序》刺宣王之说, 但以之为刺宣王不纳诲之作。
第二类观点始出自杨名时《诗经札记》, 杨名时言“……《白驹》则贤人远遁……此六篇并西周畿内夷厉以降之风謡也”[5]39, 以此诗为泛言讽谏之诗, 没有具体的讽刺对象。
第三类观点出自牟庭《诗切》, 其言“《白驹》, 刺隐士入朝也”[6]2877。
1.3 思慕贤人类
这类观点按申说重点不同有招贤、 燕贤、 饯贤、 颂贤之别, 但都将作诗对象视作贤人, 都表达了作者的好贤之心, 均归为“思慕贤人类”。
戴溪以为此诗大旨在“诗人惜贤者之去, 而冀其复至也”[7]838。 贺贻孙《诗触》“宣王之时, 贤者不用而去, 故大夫代为招隐之辞”[8]590。 牟应震《诗问》言“《白驹》, 勉用世也, 犹云圣天子在上, 可以岀而仕矣”[9]108。 以上诸家所言虽有留贤、 惜贤、 招隐、 劝贤入世之别, 但均意在招贤。
认为《白驹》乃燕贤诗者, 如何楷《经世本古义》言“此诗所以燕贤也”[10]261。 认为此诗乃饯贤之作者, 如邹忠胤以之为饯箕子之作[11]661-662, 方玉润“此王者欲留贤士不得, 因放归山林而赐以诗也”[12]378。 认为此诗旨在歌颂贤人者, 如祝敏彻等《诗经译注》认为“这首诗歌颂一位其洁如玉的隐遁的贤人”[13]396。
1.4 恋歌类
郭沫若根据盠器铭所记王参加执驹礼之事, 推断《白驹》“分明是‘中春通淫’——行‘执驹’之礼时的恋诗, 决不是《诗序》所说‘大夫刺宣王’。 对白驹而‘絷之维之’即此尊铭所谓‘执驹’或‘拘驹’。 诗中言‘尔公尔侯’正表明公侯也参预典礼”[14]。
1.5 挽留客人类
余冠英先生认为“这是留客惜别的诗。 前三章是客未去而挽留, 后一章是客已去而相忆”[15]196, 以《白驹》为留客之作。 古代学者解读《白驹》多以“絷之维之”为留友、 留贤之意, 主旨在表达惜别之情或思慕贤才, 与留客不同, 故不归入此类。
2 《白驹》主旨众说分析
从主旨梳理可知, 古代学者多将《白驹》解读为饯别友人之作、 讽刺时事之作或思慕贤人之作, 其中又以从后两说者为多。
四家诗中, 对《白驹》的解读现存三家。 东汉以来, 《毛诗》大行, 鲁韩两家式微, 故刺宣王说渐盛。 但《毛诗序》所言刺宣王事实于史无征, 诗歌文本也未透露与具体时代相关的信息, 故虽然从之者众, 亦有学者提出不同见解, 如杨名时等提出了泛言讽谏说, 不限定此诗的具体讽谏对象为宣王。
申培、 韩婴以《白驹》为惜别友人之作, 毛公、 申公皆以作诗对象为贤能之人, 毛公又言“贤者乘白驹而去”, 三家的解读实有重合之处, 即贤才、 离别。 《白驹》第四章言“皎皎白驹, 在彼空谷。 生刍一束, 其人如玉。 毋金玉尔音, 而有遐心”, 于文本上看, 确似赠礼惜别之语, “其人如玉”也确有赞美人品行高尚之意。 而《毛诗序》及《毛诗笺》均认为《白驹》有“刺不用贤”“刺不能留贤”意, 实际加强了此诗表达渴求贤才的主旨倾向, 故衍生了慕贤说。
《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具有极高的学习价值, 因此, “白驹”“空谷”不断在文学、 史学作品中以较固定的内涵出现, 逐渐演变成代表离别、 贤能、 隐居的意象群。 如《嵇康集》录郭遐周赠嵇康诗“离别自古有, 人非比目鱼……岩穴隐傅说, 寒谷纳白驹”[16]57, 陆云《逸民赋》赞咏隐逸之士, 曰“乘白驹兮皎皎, 游穹谷兮蔼蔼。 寻峻路兮峥嵘, 临芳水兮悠裔”[17]392, 均以白驹游于空谷比喻贤才离去, 隐居世外。 意象群具有极强的历史文化继承性, 故历代研究《诗经》的学者受其影响, 无意识中继承了对“白驹”“空谷”的解读, 如蔡卞《毛诗名物解》以白驹为德行高尚而不能得用之人, 或如戴溪认为此诗以白驹在谷比喻贤者隐岩穴之间, 与郭遐周及陆云在文学创作中对《白驹》的解读相似。
古代学者对《白驹》主要意象的解读较一致, 对《雅》诗的认识也较固定, 故对《白驹》主旨的探讨多不出讽谏说或慕贤说。 但因时代风潮、 作者人生经历及对《诗经》认识的不同, 对《白驹》主旨的理解还是略有差别的。 例如:钱澄之乃明末爱国志士, 曾于孔庙大斥阉党, 嫉恶如仇, 故将《白驹》解读为“王室政衰, 贤者争思洁身以去, 亦有不能去者。 ……既羡其去, 又望其去后之尔音。 则诗人欲去不能, 去之情言外隐然, 所以讽朝廷者深矣”[18]574, 实际隐含了自己在国家危难之时的复杂心理。 钟惺曾在南京礼部任职, 亲涉礼制, 因此而解《白驹》为燕贤之作。 方玉润二十二岁入县学, 应试十五次均不第, 其父方凌瀚应试十三次不第, 故怀才不遇的方氏, 有心企望君主招贤之事。
虽然讽谏说及慕贤说占据了对《白驹》主旨解读的主流, 但从上述梳理探究来看, 其生成源头乃《毛诗序》刺宣王说。 而刺宣王说乃时代风潮下比附政教的结果, 实难服人。 因此, 由刺宣王说生发而来的讽刺说及慕贤说的准确性亦值得怀疑。 在无新的史料发现的情况下, 《白驹》宜暂定为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
“五四运动”时期, 胡适在《谈谈诗经》一文中提出“大胆地推翻二千年来积下来的附会的见解; 完全用社会学的、 历史的、 文学的眼光重新给每一首诗下个解释”[19]580, 揭开了《诗经》研究的新篇章。 郭沫若将金石学研究成果用于《诗经》考释, 别为新说, 但其仅以“执驹”一词就断定此乃恋情诗, 未对诗文本进行深入考证, 亦难服人。 余冠英跳出经学窠臼, 将《白驹》视作一首生活诗, 又是一种新思路, 但失于未结合周代礼乐文化背景考察此诗。
3 《白驹》主旨辩证
关于《白驹》的主旨, 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必有其可取之处, 但今细究字意, 梳理文句上下逻辑关系, 结合文献, 认为这是一首诸侯朝觐天子时, 周王室臣子作的燕飨诗。 下文试作辨析。
诗中言“尔公尔侯”, “尔”即“汝”, 直译作“你公你侯”, 可知是指作诗对象, 即乘白驹之人、 诗中的“伊人”“嘉客”“其人”。 郑玄认为作诗对象是乘白驹而去的贤者, 将“尔公尔侯”释作“尔公尔侯邪, 何为逸乐无期以反也”? 孔颖达进一步解释郑玄之意, 言“公侯之尊, 可得逸豫。 若非公侯, 无逸豫之理。 尔岂是公也?尔岂是侯也?何为亦逸豫无期以反乎”。 公侯虽属统治阶级, 掌一方土地, 但若沉迷逸乐, 定受讽谏批驳。 郑玄、 孔颖达以《白驹》为讽谏诗, 在释诗过程中显露出“公侯可逸豫”这样的观点, 实与《雅》诗颂扬讽谏之用相悖。 又有如龚橙言“虽至公侯, 无可逸豫”, 以“公侯可逸豫无期”作为招贤之资者, 亦悖于《雅》之用。 戴溪言贤者已至, “为公卿者, 不以贤才为念, 逸豫无度, 贤者不肯留”, 似可通, 却未释“尔”字, 似把“尔”作语辞用。 但“尔”处句首, 不可作语辞, 在《白驹》诗中“尔”字只能作第二人称代词。 若依戴溪说, 此诗叙招贤之事, 诗中的第二人称指向也定是贤人, 而此处却言“你们公你们侯”, 叙公侯之短并冠以第二人称, 则与《白驹》整首诗的写作视角不相符合。
《周礼正义》称“诸侯朝称宾, 卿大夫来聘称客”[20]162, 但亦言“此宾客相对则别, 散文则通。 是以《大司徒》云‘大宾客, 则令野修道委积’, 宾亦名客。 《小司徒》云‘小宾客, 令野修道委’, 则客亦名宾, 是宾客通也”[20]560。 可见虽有明言“宾”为诸侯, “客”为卿大夫, 但在实际操作中, 两者可混用。
春秋时, 对各阶层使用的马有亦明确规定。 何休注:“天子马曰龙, 高七尺以上; 诸侯曰马, 高六尺以上; 卿大夫、 士曰驹, 高五尺以上。”[21]14此诗作诗对象为诸侯却用“驹”不用“马”的原因大抵是作诗时并不局限此规定。 《诗经》中出现“驹”字的诗有五首:《周南·汉广》《陈风·株林》《小雅·皇皇者华》《小雅·角弓》《小雅·白驹》。 《皇皇者华》“我马维驹, 六辔如濡”“我马维骐, 六辔如丝”“我马维骆, 六辔沃若”“我马维骃, 六辔既均”[1]319, 记录了四种马:初生两年的驹、 青黑色的马、 白毛黑鬛的马、 夹杂着白毛的马。 《汉广》“之子于归, 言秣其马”[1]42“之子于归, 言秣其驹”[1]43, 《株林》“驾我乘马, 说于株野。 乘我乘驹, 朝食于株”[1]256。 上述各诗均言“马”为“驹”, 但作诗对象仅一人, 可见《诗经》并不拘于马的等级规定。 故此诗虽以“客”称作诗对象, 且作诗对象所乘乃“驹”, 但并不影响从“尔公尔侯”得出作诗对象乃是“公侯”的结论。
邹忠胤云“殷人尚白, 至周犹仍其色, 乘彼白驹, 非殷士而何受之”[11]661, 从驹色白推论《白驹》乃饯箕子之作。 《礼记·明堂位》记“是以季夏六月, (鲁)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 牲用白牡”[22]577, 此鲁国之祭祀, 鲁非殷后, 亦强调用白牲。 《灵台》“麀鹿濯濯, 白鸟翯翯”[1]580, 《閟宫》“白牡骍刚, 牺尊将将”[1]778, 前者叙文王建灵台之事, 后者是赞扬鲁僖公的诗。 可见用白色者非定是殷人也, 骑白马者, 不一定是箕子。 故以“白”来断定作诗对象的身份, 是不妥当的。
毛注“藿犹苗也”, 严粲以“藿”与“苗”皆菜茹之类, 马瑞辰释“场苗卽豆苗”[23]574, 牟应震认为“苗藿”喻食禄。 菜茹、 豆苗皆可供人食用, 当不会用作饲马, 牟应震所说乃附会之言。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艹部》:“苗, 古或假借为茅。 如《士相见礼》古文‘艹茅’作‘艹苗’, 《洛阳伽蓝记》所云魏时‘苗茨之碑’实即‘茅茨’。”[24]40此处“苗”当取“茅”意。 《采菽》篇, 郑玄注“藿, 豆叶也”[1]500。 茅草与豆叶都是可作草料的作物, 盖因产自周室场圃, 故此士大夫言“食我场苗” “食我场藿”。
“絷”“维”二字, 毛注“絷, 绊。 维, 系也”。 郑《笺》“原此去者, 乘其白驹而来, 使食我场中之苗。 我则绊之系之, 以永今朝”[1]378-379, 孔言“絷之谓绊其足, 维之谓系靷也”。 历代解读多以之象征留客、 留友、 留贤, 如《毛诗正义》“谓绊絷其马, 留其人”, 朱熹认为“絷之维之”与“后人留客而投其辖于井中也”[25]578意同。

《周礼·遗人》言:“郊里之委积, 以待宾客; 野鄙之委积, 以待羁旅”, 贾公彦曰“旅, 客也。 谓客有羁絷在此未得去者, 则于此惠之。”[20]204-205郑玄注:“委积, 谓牢米薪刍给宾客道用也。”周王朝在郊里与野鄙设类于驿站的官舍, 准备粮食与草料以供宾客旅人使用, 客之羁絷者即系马足停留在此的旅客。 《山东莒县东莞出土汉画像石》中1号石正面(见图 1)及2号石背面, 均有绑住马脚之图。 其中1号石“第三层中间刻一圆坑……左侧站一人, 正在洗刷树下之马”(见图 2)[27], 图中之人手中执一器具, 人与马之间立一桶状物, 当是洗马无疑。 汉代亦有絷马进食和仆侍清理马粪的画像石。 “絷马”乃古时为方便照料马匹之举。

图 1 《山东莒县东莞出土汉画像石》一号

图 2 《山东莒县东莞出土汉画像石》二号
盠驹尊记王所行执驹礼即是缚住马足以保护、 控制幼马。 郭沫若以为“皎皎白驹”“絷之维之”描述的是行执驹礼时的礼节, 过牵强了。 此诗“絷之维之”实际是体现了周王朝对诸侯的礼待, 以显示天子的恩德。 马乃是王朝战力的体现, 能够养护大量马匹, 也能展示周王朝国力的强盛及权威, 此举有恩威并施之用, 并非是留客。 “以永今朝”“以永今夕”表层意似祝酒词, 对诸侯国表示欢迎之情, 望其在周王朝的招待下能朝夕逸乐。 但“今朝”“今夕”实际是指代朝觐燕飨时主客双方的和谐关系, “以永今朝”“以永今夕”表达了周王朝对诸侯长久拥护中央王权的要求与希望。
故《白驹》第一、 二章描述的是诸侯到朝, 周朝官员照料其马匹, 诸侯在朝燕飨的场景。
《毛诗李黄集解》收录了各家对“贲”的解释:《毛传》以为装饰之意, 郑玄以之表黄白色, 王安石以之为“奔”, 程颐以为乃贲然光彩貌。[28]436《白驹》第一、 二章言周室照料诸侯之马, 亦写周天子招待诸侯的场面。 三章言“贲然来思”, 当从毛说为是:洁白的驹马被尽心照料, 装饰一新。 可见来朝的诸侯即将启程归国。 孔颖达言“此来思、 遁思, 二思皆语助, 不为义也”, 是也。
历代学者多将“无期”译作“没有期限”。 实“期”当作语辞, 不表意。 《小雅·頍弁》“有頍者弁, 实维伊何?”“有頍者弁, 实维何期?”“何期”即“伊何”, 郑玄言“期, 辞也”[1]483。 “逸豫无期”之“期”作语辞, 此章首句与末句句末“思”字亦是语辞, “期”与“思”都为之部字, 为此章韵脚, 如此则于音韵、 文法上皆相称。 “无”表否定, “逸豫无期”即“不要逸豫啊”, 否定词后置, 当也是为了句式工整之故。
孔颖达将“勉尔遁思”释作“汝遁思之志, 勿使不终也”, 即劝“汝”停止隐遁的想法, 于意可行, 但未能明确训出“勉”的字意。 此“勉”当作否定意。 现多将《诗经》的产生时代定为商至春秋中期或晚期。 笔者目力可及的出土文物中, “勉”字仅出现于战国晚期的秦虎形辖一器上。 同期《吕氏春秋·辩土》“免耕杀匿, 使农事得”, 王念孙言“免, 读为勉”[29]695。 《古今韵会举要·铣韵》亦言“勉”可通作“免”[30]615。 “勉”字, 从力, 免声。 《诗经》产生的时代, 并无“勉”字, 《白驹》写作时此字或作“免”。 后人作“勉”, 或是秦火战乱, 文献散佚, 口耳相传后写定之故。 龚橙将此句释作“无可逸豫”, 郭沫若将此句译作“不要到处溜”, 亦为“勉”乃“免”之借用。
朝聘盟会制度是周代用以维系天子与诸侯关系的主要活动方式, 灌输君臣、 上下、 亲疏、 尊卑的等级观念, 达到尊天子、 卑诸侯的目的, 以维持和巩固周代统治。 《礼记·经解》“朝觐之礼, 所以明君臣之义也”[31]847, 据《仪礼·觐礼》记载, 诸侯朝觐时, “乃入门右, 北面立, 告听事……天子辞于侯氏, 曰:‘伯父无事, 归宁乃邦’”, 郑玄注“告听事者, 告王以国所用为罪之事也”[32]326。 可见诸侯需向周天子汇报封地相关事宜, 以示臣服于周王室, 表达对天子的忠诚, 而天子做出的回应中定有警醒劝勉之语, 以明君臣之义。
“遁”有隐匿、 隐居之意, 在《白驹》中意为不要澹于游乐而远离国事。 “逸豫无期, 勉尔遁思”即是天子劝谏诸侯“不要沉迷逸豫安乐啊, 对于游乐一事要慎重以待, 不要沉迷于此而荒废国事”。 末句“毋金玉尔音, 而有遐心”, 意为“不要吝惜你的声音, 而有远离我的心”, 亦是嘱咐诸侯之语, 是望其常与周王朝联络, 接受周室的统治政令, 不要有背弃天子之心。 前句赞“其人如玉”, 后句有保持联系之意, 是周天子的驭下敛贤之策。
《周礼·宰夫》记载:“凡朝觐、 会同、 宾客, 以牢礼之法掌其牢礼、 委积、 膳献、 饮食、 宾赐之飧牵, 与其陈数。”[26]48“委积”是给宾客准备的牢米薪刍。 “刍”字, 《说文》“刈艹也。 象包束艹之形”, 谓可饲牛马者。[32]44《礼记·聘义》记载:“主国待客, 出入三积, 饩客于舍, 五牢之具陈于内, 米三十车, 禾三十车, 刍薪倍禾, 皆陈于外, 乘禽日五双, 群介皆有饩牢, 壹食再飨, 燕与时赐无数, 所以厚重礼也。”[30]1029《左传·僖公二十九年》亦有记载:“介葛卢来朝, 舍于昌衍之上。 公在会, 馈之刍米, 礼也。”[16]283从上述文献记载可知, 周时, 主国招待宾客, 以刍为礼。 诗中赠送的“生刍”或是新鲜的未晒干的草, 以示植物的成色好, 又因在宴会上无法展示全部数量, 故以“一束”聊表所赐之物。
《白驹》第三、 四章, 言白驹已被装饰一新, 在郊外空旷处等待, 周室按制赠送来朝的诸侯米禾刍薪等, 并赞美诸侯的德行如玉, 勉励其毋沉迷游乐, 要忠于天子。
《白驹》或是作于诸侯即将归国的宴会上, 周王朝的卿大夫在庭献诗, 记录天子对诸侯的恩德, 并通过在庭献诗的方式代天子委婉地向诸侯提出治理国家与尊重中央的要求。 此诗作诗之意是燕飨时警醒诸侯, 春秋时《诗》无达诂, 后世曲解此诗, 造成白驹、 空谷这样的意象群, 不能不说是一种美好的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