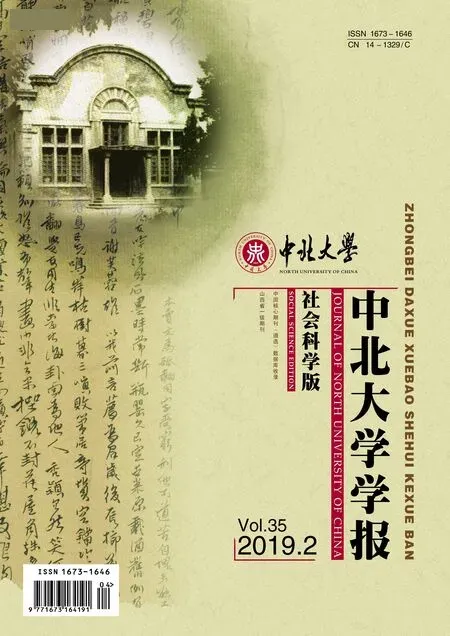精英认知视角下的早期土耳其土地改革
王 辉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
0 引 言
国内外学术界对土耳其土地改革的研究文献较多, 其中可分为专著和学术论文两大类。 研究土耳其农业的专著有许多, 其中以《奥斯曼帝国与现代土耳其史》(青海出版社, 2006年)为大家熟悉, 该专著在论述各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时, 涉及农业发展, 主要对坦齐马特时期政府的土地改革论述较多, 并论述了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土地改革。 该著作论只是从宏观上对农业发展进行论述, 细节上描述不多。 其次《奥斯曼帝国经济和社会史, 1300~191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在“国家, 土地和农民”一节中, 论述了奥斯曼帝国的土地国有制度, 国有土地之外的土地所有权主体、 土地调查、 奥斯曼帝国农村社会中的组织团体和西夫特-房屋系统等, 该著作主要从土地制度角度, 论述奥斯曼农村社会的基本状况。 国内对奥斯曼土耳其农业发展论述比较多的是: 《土耳其通史》(上海科学社会院出版社, 2014年), 《奥斯曼帝国》(三秦出版社, 2000年)和《晚期奥斯曼帝国研究(1792~191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年)。 其中《土耳其通史》与《奥斯曼帝国》各自首先论述论了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农业与农民, 涉及土地税的包税制, 其次论述了凯末尔时期的农业发展与土地改革的初步举措, 并论述了二战后农业的进步与乡村社会的变革。 最后, 论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农村发展状况。 《晚期奥斯曼帝国研究(1792~1918)》主要论述了坦齐马特时期的土地改革。
论述土耳其土地改革的论文也有许多。 如《20世纪中叶中东国家的土地改革》[1]一文主要论述了土耳其、 伊朗、 叙利亚、 伊拉克和埃及等国家的地权变迁, 土地兼并, 土地改革和土地改革后的乡村社会。 其次, 《土耳其农业发展政策的沿革及其特点》[2]《土耳其土地关系的演变和农业生产的演变》[3]和《权力的局限: 穆罕默德二世土地改革再探》[4]也是论述土耳其和奥斯曼帝国农业与土地关系的佳作。
综上所述, 上述专著和论文主要论述了土耳其土地改革有关的制度、 农业政策和农业经济等, 但并没有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分析早期的土地改革。 所以本文从土耳其精英认知视角观察土地改革,并分析影响统治精英对土改看法转变的因素, 最后解释1945年土地改革法出台的原因。
1 土耳其土地改革的历史背景

1934年6月, 土耳其政府通过了一项更完善的定居法, 并为那些在国家东西部之间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了土地。 这次土地分配的尝试是为了解决库尔德问题, 削弱库尔德部落领导人的政治权力, 因为他们的权力来自对库尔德农民的经济支配。 从此之后, 政府土地改革计划的范围扩大到全国范围。 这项定居法是重要的, 因为它是国家消除阻止其征用私人土地的障碍的第一步, 在 1936年的最后几个月, 政府更加关注类似的土地安排。
1936年11月, 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宣称:“每个土耳其农民家庭绝对有必要拥有足够的土地去培育和谋生。 国家的基础和进步被建立在这项原则之上。” 他还补充道, 政府希望“鼓励大农场合理经营, 并提高农作物剩余产量”。 同年12月, 伊努诺表示, 该国的农业处于严重萧条状态, 政府从 1937年开始, “提供大量的现金为农业和农民造福”。 在1937年春, 大国民议会讨论的构成方式发生改变, 土地问题慢慢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 有人指出, 为了使农民成为“社会的积极分子”, 并使社会从他们的劳动中受益, 他们必须从其他人耕作的土地中获得救助, 并获得自己的土地。 或许最重要的信号来自阿塔图尔克于1937年11月的演讲, 他认为“应该给无地的农民分配土地, 而且重要的是农户耕作的土地在任何情况下, 都是可以被分割的”。 这次演讲似乎给土耳其土地问题的讨论增添了动力。[6]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对土地问题感兴趣的精英消失了, 战争成为他们的关注点。 战争结束后, 政府开始着手推进实施“土地分配法”和“建立农民宅基地法”, 并删除了与农民宅基地相关的条款, 因为政府面临大国民议会激烈的反对, 所以最终以“提供土地给农民法”(LPLF)的名义获得大国民议会批准, 这是一党制政权历史上第一次遭到议会相当多成员的反对。
虽然“建立农民宅基地”的相关条款被删除了, 但重要的是对该条款的理解, 因为它反映了1930年到1940年执政精英关于土地分配争论的动机。 政府建立农民宅基地的目标是维护“农民家庭的独立”, 并确保“农民土地的不可分割性”, 而且每户家庭可获得的土地面积的大小为3~50公顷。 农田只能由一个人拥有, 而且这个人必须是农民家庭的户主, 并且只许一个人继承家庭的耕地。 在25年之内, 这些农田不能出售。 继承农田者对其他家庭成员必须进行金钱补偿, 但不能让继承农田者自身陷入收入困境。 此外, 分配给农民当宅基地的土地,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扣押或抵押, 这是一项保护农民的预防措施。 如果继承者不耕种农田, 国家将回收这些农田, 并转让给其他家庭成员。 最后严禁对农民宅基地采取分成制。
总而言之, 首先, 提及农民宅基地的潜在意图是, 确保家庭农田面积的不可分割; 其次, 阻止农田被抵押和扣押, 进而保护他们的土地。 这样做是为了拆开与商业和市场关系密切的经济部门。 最后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项措施体现了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目标是, 维持农民家庭的“根”, 因为农民只能依靠他们自身的劳动和财产而生存。
删除的“向农民提供土地的法律”原则上通过了给无地和少地农民提供土地, 给农民提供信贷和农具, 对私人土地的面积设定上限和下限, 并确保所有土地都持续耕作。 该法明确规定: 首先, 不得重新分配私人土地, 但是国有和其它有生产潜力的土地, 例如: 那些通过排干湖泊和沼泽后重新开垦的土地, 根据该法, 如果没有可分配的土地, 私人土地也可以被挪用和重新分配。 私人持有土地面积超过500公顷, 就会被重新分配, 但在土地稀缺的地区, 这个上限可能会降至200公顷。 然而也可以灵活地解释法律, 因为大地产主高效且合理的耕作, 就可以免除挪用其土地。 最后, 法律中最有争议的部分是著名的第17条, 即促使农业工人和佃农有权索取他们当前耕作的土地。 在土耳其, 佃农是普遍存在的, 他们可以租种大量的私人土地。
该法引起了大国民议会强烈的政治抗议, 如著名的部长阿德南·曼德列斯(Adnan Menderes), 埃敏·萨扎克(Emin Sazak)和卡维特·奥拉尔(Cavit Oral), 他们本身是大资本主义地产主, 所以强烈地反对该法。 曼德列斯(Menderes)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土耳其总理, 并成为反对派的主要发言人。 按照他的说法, 土耳其没有土地稀缺问题, 因为潜在可耕种的土地面积比已耕种的土地高出三倍。 他认为, 真正的问题是农业与工业的贸易逆差。 此外, 根据曼德列斯的观点, 农民真正需要的是获得必要的生产资料, 增加信贷机会以及在农业中引入科学生产方式。
曼德列斯还对法律条款作出了妄言, 如“农民宅基地”条款, 简单地抄袭自希特勒1933年的“限定继承不动产法”。 我们会在下文对曼德列斯的观点进行解释。
2 土地改革的原因
2.1 无地农民问题
土耳其一党执政时代的土地改革尝试的首要动机是远比经济更为重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7]虽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政权会优先考虑超越经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 这并不意味着改革没有受到经济的影响。 经济文献指出, 改革目标, 即通过向农民提供土地来提高农作物生产率, 并增加他们对工业品的需求, 从而推动土耳其的整体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 有的学者认为土地改革可能阻止劳动力的流动并增加他们的自给自足性,而不是促进农业商业化。 尽管这种解释强调土地改革背后的经济动机, 但事实上在土耳其, 经济原因起着次要作用。 其原因可能是当时的精英相信土地改革的经济理性并不强烈, 而且他们确实怀疑土改对解决土耳其农村经济问题的有利性。[8]153因此, 经济因素既没有成为土耳其土地改革的背后动机, 也没有对土改起多大作用。
在我们看来, 促使土耳其政治精英头脑中形成土地改革倡议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精英们的认知。 从30年代早期开始, 无地和贫困人口呈现越来越增加的态势。 而许多学者和政界人士一直认为, 无地和贫困人口的数量并不大。[9]96例如, 上述曼德列斯认为土耳其土地并不稀少, 并不会发生严重的无土地问题。
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资料, 所以我们很难确定该时期的农业结构问题。 为了讨论土地改革背后的经济动机, 以及土改对农业结构的潜在影响, 我们需要知道土地的分布、 无地农民数量、 家畜的分布等等。 鉴于资料的缺乏, 统治精英对农业和农民结构的认知变得尤为重要。 在这个时期, 制定政策的人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来准确地解释土耳其农村的客观状况, 即便如此, 他们也没想到土耳其乡村的客观状况是指导其行动的关键。
对于30年代的大部分土耳其统治精英来说, 无地和农村贫穷被认为是国家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内政部长卡亚 (Kaya)于1934年6月发表的演讲中, 宣称“国家今天有人口500万耕种着他人的土地, 所以国家首要的责任就是将土地分配给无地者, 从而那时候著名的口号‘农民是国家的主人’变为现实”。 三年后, 在制定宪法修正案并使其成为分配土地的法律依据的过程中, 重复了同样的关注——1 800万土耳其人中有1 500万是农民。 但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可耕种的土地。 为了让大多数土耳其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 就必须促使他们成为掌握自身经济命运的主人。 所以, 政府必须让他们生活富裕, 并成为社会的积极分子。 1934年, 伊斯梅尔·希斯雷夫·东金(Ismail Hiisrev Tökin)预测到, 如果目前的局势持续下去, 在不久的将来, 失地农民的数量将急剧增加。 巴坎坚持认为土耳其没有土地问题是一个错觉。 即使在1950年, 全国的部分土地被重新分配后, 37.9%的家庭占所有耕地面积的81.4%, 0.8% 以上的700个德卡尔控制着所有肥沃土地的19.6%。
尽管上述一切都表明土地是30年代土耳其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但我们不知道这些发现所代表的真实状况。 我们知道不断增长的大地产主, 并不为无地问题负唯一责任。 其他因素, 如人口增长, 巨大的国有和公共土地的存在, 以及生产资本和农具的稀缺等都导致了农村问题的产生。
明确了土耳其统治精英对土地问题的认知, 我们还需要仔细分析他们关注失地的性质、 失地与土地改革倡议的关系。 失地被视为社会和政治问题, 而不是经济问题, 最重要的是, 失地农民是社会动荡和动乱的潜在根源。 历史经验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在东欧和东南欧的许多国家, 失地和贫困农民通过革命, 从而获得土地, 巴尔干国家并没有强迫实施独立于客观条件并令人绝望的土地改革, 而是乐意将已成事实合法化。 正如巴坎(Barkan)指出的那样, 20世纪的大多数革命运动发生在反抗地主所有制的农业社会中。 饥饿的农民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中的作用, 在许多土耳其精英头脑中仍然记忆尤新。[10]21农民可能引发破坏性社会革命的认知, 深深地扎根于土耳其统治精英的脑海之中。 为此, 他们重复明确了土改的必要性, 以维护“社会的和平与稳定”。
2.2 意识形态背景
虽然统治精英与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背景, 有利于我们理解土地改革及其相关问题。 但是一方面, 共和国早期没有出现推动土地改革的农民运动。 另一方面, 传统共和党精英的意识形态背景及其对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承诺, 也无助于我们深层次地了解统治精英对土地改革的态度。[11]22因此, 我们需要考虑农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土地改革中的作用。
自20世纪20年代起, 农民主义就开始出现了。 特别是1932年以后, 农民主义出现在各地的书籍和期刊中。[12]虽然当时的精英分子既没有把他们自身描述为农民主义者, 也没有形成许多农民主义者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特点, 更没有关注农民主义者。 然而, 他们保守的头脑和心态都受到农民主义的影响, 而且农民主义也混杂在他们的思想之中。[13]88
农民主义有许多特征, 最重要的特征是, 对走向城市和城市化以及“城市文明”的敌视态度, 而且城市化是造成当前所有“社会传染病”的根本原因。[14]例如, 大萧条开始是一种纯粹的城市现象, 但全世界的农民实际上都支付了成本。 城市体现了世界主义, 阶级斗争, 失业, 经济萧条, 工人罢工, 各种不安全感, 社会控制力减弱以及各种退化因素。 据农民主义者说, “城市文明”依靠剥削农民而存在, 所以城市和城市居民要为当时农村地区的社会、 文化和经济不发达状况负责。
农民主义者还顽固地反对土耳其工人阶级的出现。 他们认为工人阶级有社会动荡和革命的内在倾向, 并不愿意接受新国家的民族主义, 还会引起令人不安的“国际主义”。 另一方面, 农民指的是小业主和小生产者, 他们被视为所有社会问题的解毒剂, 而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美国和苏联大型工业产生的。 尽管农民主义者同意需要一个民族工业, 但是他们想要一个有利于农民幸福的工业。 有趣的是, 他们赞成工业而反对工业化。 这些知识分子设想国家应该控制工业的发展,工业应位于城市之外, 保证工业不会造成农村人口脱节。 同时, 政府要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 保护传统的权威关系不会被颠覆。[15]
最后, 精英人物对城市化和工人阶级的恐惧是农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两个焦点。 将土地分给农民会阻止他们向城市迁移。 农民主义者希望土耳其的城市不存在政治和社会动荡, 就像欧洲和美国的城市情况一样。 土地改革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后, 土地充当农民的“社会保险”, 从而解决农民主义者担忧的城市化问题。
统治精英对工人阶级的恐惧是土地改革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高级共和人民党领导人和农民主义者的拥护者把佃农制与无产阶级化联系起来。 在他们的头脑中,佃农制很可能会导致失地农民的无家可归, 最后无产阶级化。 换句话说, 他们对佃农制持批判态度, 希望通过土地改革取消该制度。
统治精英的土地改革也是为了阻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内出现。 土地改革导致了中小业主的形成, 他们的保守主义将是解决共产主义的“良药”[16]454。 这点与农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特点相符。 农民的保守主义是当前各种或潜在的社会苦难和灾难的“社会保险”。 农民将会成为一党制保守主义社会的群众基础。[17]这种支持言论可以在许多共和人民党领导人的演讲和著作中找到。例如党的秘书长雷杰普·佩克尔(Recep Peker )的作品。 据一位前副部长兼历史学家M.古罗鲁说:“在大国民议会讨论中, 佩克尔是最能够准确理解土地改革真实背景的人。” 在1945年关于土地分配的争论中, 佩克尔表示:“如果农民没有得到土地, 那么战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将可能恶化整个社会的肌肤, 并破坏社会结构和国家统一。”
统治精英将预防土地改革与危险的意识形态联系, 并不令人惊讶。 正如许多共和人民党领导人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所倡导的那样。 雷沙特·阿克坦是一位研究与土地改革有问题关的院士, 他支持一个观点, 即由独立的农民社区组成一个社会将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 而且这个社会可以抵制有害和危险的意识形态, 土地改革是共产主义的最佳“药方”。 甚至在1980年的军事政变后, 精英分子还认同这样的观点。
总之, 农民主义形态是统治精英土改的激励, 而预防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土改的目标。
2.3 政府巩固政权的尝试
土地改革的另一个动机是,获得农民对政治体制的支持。 在土耳其, 农民主义者认定农民不仅仅是人口的大多数, 而且是土耳其民族最纯粹和最好的典范。[18]虽然农民被誉为“国家的主人”, 但是通常农民被公认为是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漠不关心的阶级。[19]23出于这个原因, 农民主义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复兴”众多农民的民族主义认同感, 而且当时的政府也通过这种方法招募农民。 这项任务不容易被完成, 因为艾代米尔和其他人认为农民是“最后, 也是最不愿意接受革命性变革”的阶级。 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跟随者之一A.H.巴沙尔在全国巡回评估1930年的国家状况时, 指出“在农村看到的第一件事是革命根本没有走进这里”。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政府可能希望土改可以把中小农民的命运与凯末尔主义的命运联系起来。 开展土地改革也被看作是扩大政权统治基础的尝试。
土耳其政府30年代的土改, 就是取得当地库尔德农民对政权的支持, 从而解决库尔德问题。 土地改革与库尔德问题之间的关系, 被当时最着名的期刊之一《卡德罗》(Kadro), 有说服力地提出。[20]尽管《卡德罗》和统治精英之间总体上存在意见分歧, 但后者认为《卡德罗》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公正的。
根据《卡德罗》和其他期刊的观点, 即它们认为库尔德问题是“一党制时代最难以解决的问题”, 艾米代尔(Aydemir)认为这是一个阶级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 其根源在于该地区普遍存在的封建生产关系。 占领封建地主的土地并分配土地给农民, 会解决这些封建的生产关系, 从而削弱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基础。[21]
虽然解决库尔德问题仍是土地改革最关键的目标之一, 但是这个话题并不值得历史学家们充分的讨论。 原因之一也许是与库尔德人相关的问题一直是政治禁忌。 另一个原因是土地改革的经济原理吸引了学者的大部分注意力, 而不是土改的社会和政治动机。
在一党制时期, 库尔德问题无疑对土地改革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事实上, 无论何时土耳其政府打算围绕“东部和东南部做些事情, 于是土地改革问题走到了前台, 1997年和1937年的土改关注点都一样”[22]111-112。 即使在1997年夏天, 与库尔德问题有关的土地改革的讨论出现在土耳其媒体上, 而且政治家和政府官员, 如时任总理比伦特·埃杰维特(Bülent Ecevit) 认为这个“特别地区”, 即土耳其东南部的问题可能会通过土改解决。
土改在多大程度是否会成为解决该地区问题的灵丹妙药, 有待公众的观察, 但这个问题超出本文的研究范围。 我们的目标是揭开土地改革与库尔德问题的关系, 而库尔德问题在当时统治精英的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3 结 语
由于土耳其土地改革的倡议和实践来自上层, 主要存在于国家必需品的限制之内, 并且未能完成其有限的目标,农民享受的好处有限。 部分原因是因为土耳其没有组织农民运动, 农民无法获得利益而积极投身于到农民运动之中。 土耳其自上而下的情况与二战后东欧巴尔干地区, 特别是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捷克斯洛伐克、 波兰和南斯拉夫的经验形成鲜明对比, 那里的“群众起义”有他们自己的政党领导, 并对土地改革产生了压力。 与土耳其不同的是, 这些国家的土地改革标志着它们的历史出现了激进民主的转折点, 因为土地问题是群众进入国家机构的工具。 此外, 在很大程度上, 他们不可避免地与大地产主发生对抗, 从而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被除去了。 尽管土耳其分配了一些国有土地, 但是1945年的土地改革没有驱除落后的农地关系和减轻不平等, 所以没有像上述国家那样产生过重大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