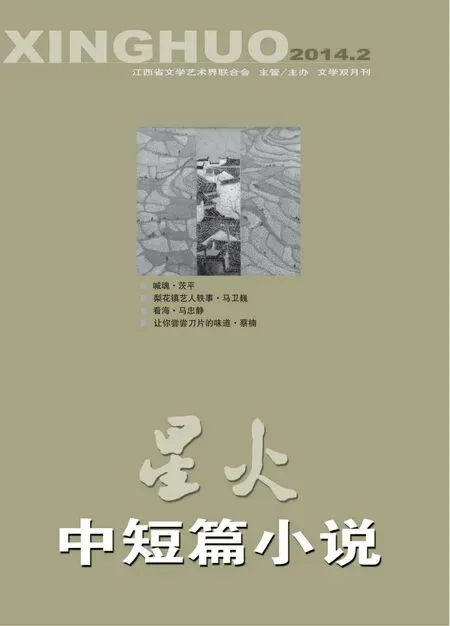写作者之间的相互敬重
○刘秀娟
2018年初冬到盐城,参加李有干先生长篇小说《蔷薇河》新书发布会。看着眼前板正高大、相貌清隽的李有干先生,实在无法相信这是一位88岁的老人。他的气息,是一种“中年感”。
到盐城,是作家曹文轩教授专门邀请,诚挚而恳切。对与会的外地评论家,曹文轩老师安排自己在老家工作的妹妹、作家曹文芳接送、陪同,是我所从未见过的周到、细致。有位评论家曾说过,只有一个人的研讨会能让曹文轩教授忙前忙后、亲力亲为,那就是李有干先生。多年前如此,多年之后,捧回国际安徒生奖,依旧如此。
曹文轩教授一直说“李有干先生是我的老师”。我以为,这是曹教授的谦虚和客气,以及中国尊师重教传统的延续。我也一直以为,李有干先生是盐城当地中学或者小学教师。读到曹教授为《李有干文集》作的序,才知道,曹教授是以李有干先生为文学道路上的老师、做人为文的老师。
李有干当时在县文化馆工作,创作上已经有不俗的成绩。但是他却经年累月走在乡间的小道上,把全副精力用于辅导当地的业余作者。“寒冷的冬天,手冻得无法提笔,而那些业余作者又急切地想早一点看到被他改过的稿子,他就全靠不停地喝开水来取暖。他一天能喝掉三四暖壶开水。至今我的记忆里仍然保存着一个形象——他双手抱住茶杯的形象。炎热的夏天,乡下的蚊子多得用手几乎推不开,到处蚊声如雷,他就钻在蚊帐里为那些将文学之路几乎看成生死之路的业余作者看稿、改稿。后来,我到北京大学读书了,他仍然一年四季往乡下跑。”
写作的“技术”之外,更深刻地影响着曹文轩的,是李有干先生的赤诚与干净,“文学给他带来了那个地方上的人所没有的心境,给他带来了年轻的相貌(别人对他年龄的估计,一般情况下都要少估十五岁左右),给单调无味的小城生活带来了一种不可穷尽的丰富。他是那个地方上最富有、最有情调的人之一”。
见到李有干先生,才知道曹教授所言不虚。会上,师生二人,一身清雅,默契相投,那种言语不多而深厚温煦的气息,让我不只是触动,而是心生羡慕。人与人,尤其是文人与文人,这样一份敬重何其珍贵。包括曹文轩的小妹妹曹文芳,那样出挑的相貌和气质,对自己的哥哥和李有干先生温软的、亲昵的爱戴,让人生出一份特别的感慨——他们和文学,是多么美好的存在。
李有干先生最后发言,在那样一种场合,他完全可以称呼“文轩”,以示亲切,但他特别庄重地称呼“曹文轩教授”。我当时心里一动,从中体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谦和与郑重。敬重与感念是相互的。虽然曹文轩说自己作品的基本元素来自盐城,来自李有干,但是,在李有干先生心里,他或许也是以曹文轩为师的。
这是一段意味深长的文学佳话。从80年代以来,那么多曹文轩作品的研究文章,可有谁论到盐城的文学生活、盐城的李有干对曹文轩的影响?在新中国文学中,业余写作者、赤诚的文学青年、文化馆的辅导员,构成了一种多么独特的文学场域?在今天,我们还能否感受到写作者之间的这种相互信任、贴近与扶持?
编辑的无奈
2018年,我们网站对原创投稿系统进行了升级,极大改善了用户体验,吸引了很多写作者。做了多年报纸编辑,我深知对很多写作者而言,尤其是业余作者和基层作者(虽然我认为这是极不恰当的称谓,但约定俗成,姑且用之),能发表或者出版自己的作品,是多么深切的渴望。我们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编辑力量去做这件事,带着不计成本的决心。和传统报刊不一样的是,连接我们的编辑和作者的,是计算机系统。彼此之间是“陌生人”,却也让编辑和作者退回到一种特别简单而纯粹的关系。
很多写作者不愿意相信,做编辑的(除非特别混差事的),都愿意发现好文章,发掘好作者,没有哪个编辑是靠“关系稿”度日的。就像很多编辑也不愿意去思考,这些热爱文学的人,哪怕他写不出理想的作品,但他们对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对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仍旧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所以,当我们决定从海量的投稿中遴选优秀作品,出版作品集时,很多对编辑抱有成见,习惯了作品在网络上自生自灭、悄无声息的作者,根本不相信这会是真的。
我们的编辑联系作者授权的时候,有的作者喜极而泣。不是夸张,是真的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有的作者,再三确认,以为碰到了骗子。山东的一位作者,我们编辑询问他银行卡号等信息时,死活不肯给,问东问西,直到年轻的编辑失去耐心。过了半天,他又打来电话,恰好我接。从当地略有名气的作家,到谁谁谁的新作,从自己激动的心情,到对网站的表扬,说了足足有半个小时。虽然当时特别忙,但我理解这种激动的心情,一一应着,心里却火烧火燎。当晚加班,没想到又接到这位作者的电话,问我,他们县作协没有办公的地方,在私人家里办公不太好吧?能不能给解决一下?他要加入省作家协会,应该怎么做?我一一解释。但他就是不肯放下电话。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惊觉,他是在试探我们!他觉得这是一个骗局!我突然间哭笑不得,他认为我们只需要一个账号就可以把钱转走。同时,我又有些难过,你看,这就是我们的作者,哪怕他心里很疑惑,甚至八成认定我们是骗子,但是他又特别珍惜自己作品出版的机会,不敢“直言”得罪编辑,把自己绕得如此辛苦!
假如不跟广大的业余作家或者基层作家接触,你可能无法感受那种心情。达不到发表水准的文章,赤诚恳切的眼神,小心翼翼的态度,这是我们这座报刊社聚集的大楼里时常会遇到的情景。虽然做了十多年编辑,但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依旧煎熬,甚至心疼。既不想糊弄,又怕打击甚至浇灭他心头的那一苗火。
当90后与70后面对面,他们会谈些什么?
2018年7月,我们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研讨,邀请10位90后作家与10位70后作家面对面座谈。在作家王十月的建议下,我们打破平时研讨活动围绕某个主题各自发言的方式,采取了互相提问的方式,开放、自由而充满不确定性。
特别有意思的是,当一个90后作家和一个70后作家面对面,看到二人之间的差异,我们会认为这是人和人、作家和作家之间非常自然的差异,这种差异同样存在于同代作家之间。但是当20位颇有代表性的作家面对面时,从表情、话语方式、性格,你会非常直接地感觉到,哦,这真的是两代人。而且你会坚信,这些看似“表面”的差异,一定会影响到作品的“内在”。
70后作家乔叶表示,女作家很容易陷入自我,很容易依赖于自我经验,她想知道90后的女性作家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回答这个问题的是90后作家庞羽。她认为,很多作家喜欢写自己,其实多数是因为怀念过去。为什么会怀念过去?据她的观察,是因为人们是无知的,容易沉溺于过去,“我们相爱相亲,物质的岁月可能不会再更改,我们是在怀念相亲相爱的时光。”而且,庞羽直言,自己从来不看父亲庞余亮的作品。大约心底里,她是要避免一种亲近的影响?女孩的回答特别坦率,又带着小孩子的忐忑,引得众人大笑。
70后作家张楚很想知道,90后作家是否还会阅读文学刊物?90后作家王占黑说,她很少阅读文学期刊,因为如今刊物也不是很容易买到,她一般只会阅读寄给她的刊物,但是,她仍然可以时常在刊物中发现惊喜之作。同时,她也不太看纸质书,其中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书太多了搬家时很困扰。所以从方便的角度,她基本只会阅读电子书。王占黑还提到,她读文学作品少,读社科类著作更多,而且她更看重社会实践,称自己是个“行动者”。
王占黑毕业于复旦大学,刚刚参加工作,白白净净的一副学生模样。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在国际学校执教的女孩子,在写作和生活中都是典型的“爷叔”爱好者,而丝毫不见矫情的“国际范儿”和“都市病”。她的都市,是有着小人物卑微生活的都市,是有着纵横交叉的晾衣架、洗刷不掉的小广告、缠绕不清的电线网的都市。后来看她在“一席”的演讲,我又想起那个下午的王占黑,她带给在场的人那么大的触动。有多少像她一样的年轻人,活动在社区,活动在各种义工组织,他们的行动和价值观,我们的作家、我们的文学是否了解?
70后作家石一枫和90后作家索耳当时是同事。“话痨”的石一枫,关心国家大事、国际形势的石一枫,每每在办公室和同事聊得热火朝天、海阔天空的时候,他总感觉索耳对这些话题是没有兴趣的,起码是没有兴趣参与讨论的。对石一枫,或者说对70后往前的作家而言,他们会深切地感受到一些看似远在天边的国际事件,和自己、和每个人的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因此,他们的写作中,个人经验与时代经验无法分离。当石一枫提问90后作家,是否有同样的感受时,确实没有得到共鸣性的回答。
在现场,你会强烈感受到70后作家比90后作家反倒带着对彼此更强烈的好奇心,70后作家的表达愿望更强烈,阐述问题的逻辑性更强。而90后作家显得更加言简意赅,言行举止有一种淡淡的、安静的感觉。他们的安静又不是古典的安静,而是后现代的安静,或者说寂静。有点淡漠,又有一种自在安然。是初入文坛的拘谨,还是一代人的性格?
或许正像王十月说的,90后作家普遍没有想要做“大师”的念头,而是出于本心地在写作;而70后作家或许怀着更大的写作野心,更鲜明地表现出对父辈的叛逆与批判,甚至不惜做出“张牙舞爪”的姿态。
在研讨会的上半场,《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也做出了类似的观察。他认为,90后作家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从自我经验出发,而不是从前辈经验、也不是从反叛前辈经验出发,他们的写作源自天真,又能正视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多的“妄念”和姿态性的宣言,显示出这一代人不同的思维方式。
这两年来,90后作家越来越受到关注,甚至变得“抢手”起来。他们作品的特质正在显现,这到底是一代怎样的作家,我们还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