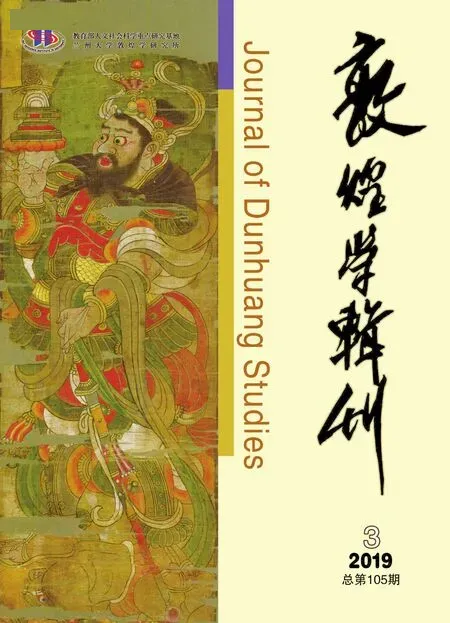青藏高原发现的古代黄金面具及其文化意义
霍 巍 霍 川
(四川大学 1. 藏学研究所、 2. 考古学系, 四川 成都 610064)
青藏高原是吐蕃王朝主要的统治地域, 在吐蕃版图上曾经有过不同的古代族群在此生存、 活动, 并且遗留下来众多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墓葬, 成为吐蕃先民们的最终归宿之地。 对于死者遗体的处理方式, 体现出极其丰富的文化史意义, 从来就是研究不同地区、 不同民族在丧葬习俗、 丧葬观念和具体的营葬方式等诸多领域的“题中要义”。 著名的英国人类学家J.G. 弗雷泽关于人类的死亡, 曾经讲过一段意义深刻的话: “死亡在所有时代一直是使人们感到困扰的问题, 与许多仅为少数思想家感兴趣的问题不同,因为圣贤与傻瓜都难免一死, 甚至最无心的人和最愚蠢人有时也不免问自己死后如何。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关注中成为一种确实存在的困惑。 在漫长的人类思考的历史中, 最有智慧的人总在沉思着这个问题, 寻求此谜的解答。”①[英] J.G. 弗雷泽著, 李新萍等译《永生的信仰和对死者的崇拜》,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2 年,第1 页。由于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 从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墓葬中, 提供了有关高原先民对死者遗体进行过处理的若干考古痕迹和现象, 其中, 对于死者面部进行覆盖和遮掩的黄金面具, 十分引人注目, 曾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随着资料的不断增加, 对于这一考古现象深入进行综合研究是有所必要的。
一、 青藏高原考古发现的黄金面具
近年来, 在青藏高原的不同地区发现了一批不同时期的古代墓葬, 从中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随葬器物, 其中包括大量的金银器。 而在金银器中, 又以作为死者葬具之一的金银面具十分引人注目。 从考古形态上划分, 这类黄金面具可以划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类型, 是用金箔制成剪切、 捶拓成模仿人脸形状的椭圆形或正方形, 然后在这个扁平的金箔上面捶拓出凸起的眼、 鼻、 口等五官的轮廓线, 或者在模仿人脸形的金箔上用不同的色彩描绘出五官。 由于这种类型的黄金面具所表现出的人脸总体而言是一个整体, 我们可以称其为“整体型” 面具。 迄今为止, 属于这种类型的黄金面具一共出土有3 件, 分别出土于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和札达县曲踏墓地。
其中, 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一件系用金箔压制而成, 呈正方形, 长4.5cm、 宽4.3cm、 厚0.1cm。 正面用红、 黑、 白三色绘出人面部的眼、 鼻、 口等五官, 面部的轮廓线条用红色勾出。 在面具的周边均匀地分布着8 个小圆孔, 应该是缝缀在质地较软的材料上, 很大的可能性是缝缀在丝织物上, 从而整体形成和人脸大小相当的“金箔加织物面具” (图1)。
另一件出土于曲踏墓地2 区, 呈椭圆形, 长5.5cm、 宽4.1cm、 厚0.01cm。 也是用金箔捶拓而成, 凸出面部的轮廓线和眉毛、 眼、 口、 鼻等五官, 五官的刻痕处都遗留下来使用红色颜料描绘的痕迹(图2)。 从其大小情况来看, 也不大可能单独使用, 推测也是与某种织物合体形成面具。
还有一件出土于曲踏墓地1 区的黄金面具则形态较为复杂, 在迄今为止西藏西部发现的黄金面具中形体也最大。 这件面具与真人的面部大小相仿, 长14.2cm、 宽14cm、 厚0.01cm。 它是由上下两个部分组成, 上部是一个长方形的冠状金箔板, 上面錾刻出阶梯形的雉堞、 立鸟、 植物、 羊等组合成的图案; 下部是人脸形的椭圆形金箔, 面部捶拓出眉毛、 眼、 鼻、 口等五官, 冠部和面部的轮廓线都用红色颜料勾勒。 整个面部的周边, 有成组的数个圆孔, 用丝线将面具与多层丝织物连缀在一起, 冠部背面的丝织物还用薄木片加固(图3)。
第二种类型, 是用金片与宝石镶嵌而成的单独的眉毛、 眼、 鼻、 口等形态, 可以拼合成为面部的五官。 由于这类黄金面具的特点是由各自独立的五官拼合而成一套人脸面具, 我们可以称其为“拼合型”面具。 最早公诸于世的这类黄金面具, 是2013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公开展出的“梦蝶轩藏中国古代金饰” 中所见的三套黄金面具(展品说明中将其命名为“金覆面” ), 每套均分别由双眉、 两眼、 鼻子、 口唇共计六件组合而成, 制作方式是用黄金箔片为底, 上面用金片制成不同的分格, 在格内镶嵌以绿松石等宝石。 由于在各个部件的背面, 均有小钉, 表明其很有可能是固定在某种材质(如金属、 木质、 皮革、 纺织品) 之上组成整体的人脸面具。 此种类型的黄金面具也存在着一些细微差别, 展出图录说明中将其分为三型:
A 型: 眉毛形如卧蚕, 头部下垂, 尾部上扬, 当中以方格相间, 在方格中镶嵌绿松石。 两眼边缘以细点金珠为饰, 当中镶嵌有一颗淡红色的宝石作为眼珠, 上下眼睑和左右眼角上也以绿松石镶嵌。 鼻梁笔直, 从上向下逐渐扩大形成鼻翼, 在两侧鼻翼上各镶嵌一颗较大的绿松石。 鼻子的其余各处均划分为小方格, 以大小不等的绿松石块镶嵌其中。 此型的嘴部呈树叶状, 上下嘴唇线也以细点金珠围绕一周, 在嘴唇上镶嵌绿松石(图4)。①苏方淑主编《金曜风华·赤猊青骢: 梦蝶轩藏中国古代金饰》,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第115 页, 图24-A。
B 型: 造型风格和镶嵌绿松石、 宝石的装饰手法均与A 型相同, 但眼、 嘴的形状、大小与A 型有所不同, 此型的眼眶较圆, 眼睑线较短, 嘴部呈直条形(图5)。②苏方淑主编《金曜风华·赤猊青骢: 梦蝶轩藏中国古代金饰》, 第116 页, 图24-B。
C 型: 较为接近B 型, 但眼眶更为短小, 鼻梁稍狭, 五官上镶嵌的绿松石保存情况较好(图6)。③苏方淑主编《金曜风华·赤猊青骢: 梦蝶轩藏中国古代金饰》, 第117 页, 图24-C。
上述三型黄金面具的五官具体尺寸为: 眉毛长10.2-10.8cm、 宽0.8cm; 眼长4.1-6.6cm、 宽2-2.6cm; 鼻长11.1-11.4cm、 宽3.4-3.5cm; 口长6.4-8.4cm、 宽0.6-2.1cm。 可见其制作工艺和规格大体相同, 尺寸大小略有差异, 当系手工制作时形成的细微区别, 应无表现等级差异的意图, 属于同一阶层使用的葬具。
由于香港梦蝶轩收藏和展出的黄金面具均无明确的考古出土地点, 尽管当时已有学者正确地判断出这批藏品可能系“吐蕃金银器”①霍巍《梦蝶轩藏吐蕃金银器概述》, 收入苏方淑主编《金曜风华·赤猊青骢: 梦蝶轩藏中国古代金饰》,第2-14 页。, 但对其年代、 性质、 功能等诸多问题尚无法加以深入认识。 2019 年, 首都博物馆展出了青海出土文物特展“山宗水源路之冲”, 展品中有与上述香港梦蝶轩出土的黄金面具形态几乎完全相同的一套黄金面具上的五官构件, 分别由两眉、 鼻子、 嘴巴和双眼组合而成, 只是这套黄金葬具中缺少了一只眼晴。 从制作工艺和造型特点上观察, 这套黄金面具五官的形制与梦蝶轩所藏的A型面具较为接近, 也是在五官的表面通体镶嵌绿松石和宝石(但出土时已经不存), 眼眶的形态略有不同, 两个眼角向上扬起(图7)。
而实际上, 青海出土的这批黄金制品中, 还有多件同类的遗物, 如同种类型的眉毛共有三对, 由此推知理论上可以组合出三套以上的面具(图8)。①有关照片资料系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冉万里教授提供, 特此致谢!只是因为各种原因,目前仅组合出一套残缺不齐的面具公开展出。 青海这批金银器的出土点十分明确, 在展器说明牌上均注明系“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热水吐蕃墓群” 出土, 这就佐证了香港梦蝶轩同类藏品的来源, 应当也是出自青海都兰热水吐蕃墓地。
二、 年代、 类型与用法的考古学观察
上述考古发现充分表明, 为死者制作黄金面具的习俗曾在青藏高原各古代部族中流行,但在年代、 类型和具体的用法上, 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有必要从考古学的观察入手弄清其基本情况, 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考察其文化来源及其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十分必要。
第一种类型即“整体型” 的黄金面具, 目前仅发现于西藏西部及其周边地区。 如前所述, 在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境内的故如甲木墓地和札达县境内的曲踏墓地共发现三件, 年代为公元1-2 世纪。②仝涛、 李林辉《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 《考古》 2015 年第2 期,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另据考古资料表明, 1986-1987 年由印度学者在印度北方邦加瓦地区(喜马拉雅山地) 的马拉里墓地中曾发现同一类型的遗物, 黄金面具呈倒梯形, 长8、 最宽7cm, 系在厚度仅有0.009cm 的金箔上采用拓捶的方式敲打出五官,面具两侧的边缘处各有10 个小孔, 可供穿系附着于其他载体之上(图9)。 所属墓葬的年代为公元前1 世纪前后。①仝涛、 李林辉《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 图五。2011 年, 美国考古学家在尼泊尔穆斯塘地区萨木宗墓地第五号墓中, 也发现了一具用黄金箔片制成的面具, 其形态略呈倒梯形, 尺寸与真人面部大小相当, 长51.1cm、 最宽12.8cm、 厚约0.01cm。 面具表面用红色颜料勾勒出眼眶、鼻子和牙齿以及多条胡须和双条眼角纹, 用黑色颜料描画出眉毛和眼珠(图10)。 该墓的年代为公元4-5 世纪。②仝涛、 李林辉《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 图六。由上可见, 这批黄金面具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出土年代最早的遗物, 年代上下限约为公元前1 世纪至公元5 世纪。
第二种类型即“拼合型” 的黄金面具, 目前仅发现于青海境内的都兰热水吐蕃墓地。都兰热水吐蕃墓地的情况较为复杂, 从现已发掘出土的墓葬情况来看, 可能延续的时间从南北朝直到唐代, 死者的族属情况也并非单一民族。 不过, 其中一些墓葬规格较高、 出土遗物较为丰富的大墓当中, 不排除其墓主人属于吐蕃贵族大臣或者高级将领, 也包括吐蕃统治下已经“吐蕃化” 的旧吐谷浑王公贵族。 结合历史文献分析, 都兰热水墓地中出土金银器的这批吐蕃大墓的年代, 应当属于吐蕃王朝兴盛时期, 即8-9 世纪左右。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年, 第127-128 页。
两相比较, 可以比较明确的看出, 虽然这两种类型的黄金面具总体上来看都具有一个用此种丧葬仪礼来遮掩死者面部的共性存在, 但从流行的地域、 年代和族属等方面考察, 却又有所不同。 第一种类型的黄金面具在青藏高原主要考古出土在西藏西部及其周边地区, 流行的年代约从公元前1 世纪至公元5 世纪左右。 这个时期, 根据藏、 汉文献的记载, 西藏西部地区主要活动的古代族属应为“象雄” 部族, 亦即唐代以来汉文史书中所记载的大、 小“羊同”。 第二种类型的黄金面具则主要发现在青藏高原的青海地区, 流行的年代约在公元8-9 世纪左右, 时代明显要晚于第一种类型。 根据文献史料的记载, 这个时期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 前期主要活动着吐谷浑人, 公元7世纪以后, 吐蕃不断向东扩张, 在吞并吐谷浑诸部之后, 这个地区主要活动的古代族属即有吐蕃人, 也有吐谷浑人, 还有党项羌、 原属西域胡人的康国人、 何国人, 甚至部分汉人。④周伟洲《吐谷浑史》,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第186-187 页。在如此广阔的时、 空框架之内来观察这一考古文化现象, 我们很难简单地将其归入一个考古学文化体系当中来加以看待, 还有必要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加以梳理和比较。
与上述西藏和青海地区出土的黄金具面可以进行比较的, 是我国新疆地区和相邻的南亚、 中亚地区发现的黄金面具。 第一种类型的“整体型” 黄金面具, 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地中海文明时代, 后来在波斯地区公元前后也开始流行。 如在帕提亚尼尼微出土的黄金面具, 就是在一件用黄金箔片制成的呈倒三角形的人脸上, 采用捶拓的方式凸显出人脸的眉毛、 眼晴、 鼻子和口部(图11), 其出现的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后。⑤仝涛、 李林辉《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 图七。
公元4-5 世纪, 中亚地区也发现了这类黄金面具, 最具代表性的遗物可举吉尔吉斯坦萨石(Shamsy) 墓地中出土的一件黄金面具, 它也是在整块的捶拓成人脸形的黄金面具表面, 再捶拓出眼晴、 鼻子、 口部。 但不同的变化在于, 它在人脸的双眉、 脸颊、 鼻梁等显要之处, 镂刻出连续的细点纹, 并在双眼部开孔, 镶嵌进红宝石。 (图12) 这种镶嵌宝石的做法, 很可能是中亚游牧民族新的创造。
公元5 世纪前后, 大约与中亚地区大体相当, 在西藏西部及其周边地区也发现了这类整体型的黄金面具。 其共同特点均是采用黄金箔片拓捶的方式, 加工出黄金面具的轮廓, 再在其上描绘出五官。 如前所述, 西藏西部的故如甲木墓地、 曲踏墓地、 与我国西藏地区相邻的印度北方邦马拉里墓地、 尼泊尔穆斯塘地区的萨木宗墓地中, 都出土过在金箔表面采用绘彩的方式描述出人脸五官的黄金面具, 很可能是受到西藏西部地区古代文化的直接影响。 而西藏西部这类黄金面具的来源, 究竟是直接来源于中亚地区? 还是另有它途? 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细加分析, 可以观察到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在西藏阿里札达县曲踏墓地1 区出土的这件黄金面具的周边, 有一周小圆孔, 每两个为一组, 在面具的背后, 残存有多层丝织物, 还残留着打结的系带, 面具冠部背面的丝织物还用薄木片加固, 通过系带与丝织物缝制在一起。 这个现象说明, 丝绸在这个时期已经传入到西藏西部, 并且使用在丧葬仪轨当中。 在同一座墓葬中出土有“王侯” 字样的丝绸, 用以包裹死者的头部, 棺内还发现大量丝织物, 也都证明了这一点。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藏自治区广的保护研究所、 阿里地区文物局、 札达县文物局《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 《考古》 2015 年第7 期, 第29-50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2012 年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2014 年第4期, 第563-587 页。 据考古报告称: “人骨发现于木棺内, 双手作束缚状置于胸前, 人骨发黑, 具体葬式不明, 头骨包裹有‘王侯’ 文鸟兽纹锦, 棺内发现大量丝织物。”所以, 西藏阿里出土的此类黄金面具和丝绸合体并用的情况, 并不见于最早出现此类面具的西亚、 中亚地区, 而有可能受到流行以丝绸制作丧葬用具的“丝绸之路” 东段丧葬文化的影响。 发掘者曾经观察分析, “从具体的发现情况来看, 基本上都是固定在纺织物上, 其中三件器物有较多的丝织物残余。”同时, 还正确的指出: “较小型的面具可以通过衬底的纺织品来扩大其面部覆盖面积,这种面具基本是象征性的。”①仝涛、 李林辉《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 第92-102 页。由此推测, 与西藏阿里地区地理位置最为接近的、 同时处在“丝绸之路” 东段的我国新疆地区, 有可能是西藏西部及其周边地区这类“整体型” 的黄金面具辅之以丝绸等织物衬底、 用作“覆面” 习俗的源头之一。
主要发现在青海都兰热水吐蕃墓葬当中的第二类“拼合型” 的黄金面具, 其来源目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这是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黄金面具, 结合现有资料来看, 其特点十分突出: 首先是做出单独的眉毛、 眼晴、 鼻子、 口唇等器官, 然后加以组合。 我们可以推测, 附在这些五官后面的, 应当是一个与人脸或者与人脸大小、 形状相接近的衬底, 然后将这些黄金制作的五官钉在这个衬底之上, 最后形成一件完整的面具。
新疆昭苏波马墓地中曾发现过一件年代下限在公元6-7 世纪前后的黄金面具,②安英新《新疆伊犁昭苏县古墓葬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 《文物》 1999 年第9 期, 第4-15 页。很值得加以关注。 它是用一件人脸形的黄金面具作为衬底子, 虽然从总体上看, 可以归纳到笔者所划分的第一类“整体型” 黄金面具之中, 但是它却采用了多种综合性的加工手法: 先是捶拓出鼻、 眼、 口的大体轮廓, 然后在双眼开出眼框, 在眼框内镶嵌以珠宝。最令人感兴趣的是, 它的眉毛和胡子却是采用了焊接镶嵌的方式, 即事先“预制” 好眉毛和胡子饰件, 最后用焊接的方式连辍在面具的表面。 这种将单独预制而成的黄金五官和某种特定材质的托底相互结合, 最后形成为一套完整面具的做法, 似乎又带有第二类“拼合型” 黄金面具的特点, 堪称为一种具有复合型特点的黄金面具, 我们是否又可将其划分为第三类“复合型” 的黄金面具, 很值得思考。 (图13)
这种“复合型” 的黄金面具同时也提示我们注意, 青海都兰热水墓地中出土的这类“拼合型” 的黄金面具的五官, 有可能也采用了类似的衬底。 不过, 从一般常识而论, 如果其衬底也如同新疆昭苏波马墓地一样是用黄金制作, 则很难继续保存在墓中而不被发现, 如果是采用丝织物和纺织物作为衬底, 在衬底腐朽之后, 将其金质的五官盗掘出土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当然, 这个推测是否成立, 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考古工作方能确证。 新疆昭苏波马墓地这件黄金面具的发现, 很可能将成为解开青海都兰热水墓地出土的这类“拼合型” 黄金面具源头的一个重要线索。
综上可见, 近年来在我国西藏、 青海等地考古出土的这些黄金面具, 与欧亚地区和南亚、 中亚一带的黄金面具有着某些相似的文化因素, 从总的背景而言, 都反映出通过“丝绸之路” 文化带沿线不同古代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联系。 不过, 十分显然, 不同类型的黄金面具和丧葬习俗密切相关, 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也会出现不同的类型和制作工艺, 在具体的使用方法上也有不同的特点。 西藏西部地区出土的“整体型” 面具主要与公元5 世纪以前活跃在这一地区的“羊同” (藏语中称为“象雄” )古部族有关, 从采用丝绸和黄金面具合体制作为葬具的方式来看, 既受到西亚、 中亚一带黄金面具习俗的影响, 但同时也接受了丝绸之路东段我国新疆地区“覆面” 习俗的影响, 具有东西方文化交互影响的痕迹。 而青海都兰热水墓地中出土的“拼合型” 黄金面具, 流行年代可能下限为唐代公元8-9 世纪左右, 而其上限或可上溯到公元5 世纪前后的南北朝时期, 使用这类葬具的死者主要的族属, 则可能为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旧部、 吐蕃高级官员及贵族, 至于这种“拼合型” 面具的源头, 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三、 黄金面具所隐含的文化意义
我们注意到, 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 对于青藏高原古代部族当中黄金面具的制作与使用, 也曾留下来十分重要的历史线索, 成为我们理解这一丧葬习俗所反映的文化意义的参照。 如唐人杜佑所撰《通典·边防典六》 “大羊同” 条下记载:
大羊同, 东接吐蕃, 西接小羊同, 北直于阗。 东西千余里, 胜兵八九万人。 其人辫发毡裘, 畜牧为业。 地多风雪, 冰厚丈余。 所出物产, 颇同蕃俗。 无文字, 但刻木结绳而已。 刑法严峻。 其酋豪死, 抉去其脑, 实以珠玉, 剖其五脏, 易以黄金, 假造金鼻银齿, 以人为殉, 卜以吉辰, 藏诸岩穴, 他人莫知其所, 多杀牸牛羊马, 以充祭祀, 葬毕服除。其王姓姜葛, 有四大臣分掌国事。 自古未通, 大唐贞观十五年, 遣使来朝。①[唐] 杜佑撰, 王文锦等点校《通典》 卷190 《边防典六·大羊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年, 第5177-5178 页。 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文中所记载的大、 小羊同等地, 和今天的西藏西部、 北部的羌塘高原密切相关, 而这个地区的“酋豪” ——也就是部落首领之类的人物, 在死后有着特殊的葬俗, 其中“假造金鼻银齿” 的做法, 或许就是考古发现中制作黄金面具的一个泛指。 长期以来, 由于没有考古发现的佐证, 这些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不能得到确认。 而新的考古资料则提供给我们重新认识青藏高原古代文明中黄金面具的流行及其历史背景, 有着重要的价值。
为何要在死者的面部覆盖以黄金面具? 考古学者和人类学者都有过不同的解释, 有的认为是代表着死者的地位与身份, 也有的认为可能和企图保护死者遗容有关, 还有意见认为可能是为了避免死者生前的某些禁忌(如面容残损等) 所为。 如果从上面所引的唐人杜佑所著《通典》 的记载来看, 在西藏西部的大、 小羊同(藏语称为象雄) 地区, 这种丧葬习俗具有某种“外科手术式” 的遗体处理特点, 类似古代埃及制作死去法老的“木乃伊” 的做法。 即首先要“抉去其脑”, 清除颅内物体, 尔后“实以珠宝”, 再“剖其五脏”、 “易以黄金”, 对腹腔内的器官也要全部摘除, 用黄金加以装饰。在这个过程当中, 死者的头部、 面部容貌可能会有所改变, 所以, 必须用“金鼻银齿”制作而成的黄金面具加以覆盖和遮掩。 不排除这个习俗与这个地区某种古老的祭祀传统有关, 即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保存部落首领的遗体得以不朽长存, 或者至少保存其遗容具有尊严性, 从而达到佑护族人昌盛之目的。
青海都兰热水吐蕃墓地出土的“拼合型” 黄金面具上, 尤其突出了死者的五官,可以想见, 这些用黄金制成的镶嵌着珠宝、 绿松石的眉毛、 鼻子、 双眼和嘴唇, 恰如文献中所记载的“金鼻银齿”, 会让死者的面容得以重新塑造, 不仅金碧辉煌, 而且庄严可敬, 既维护了死者最后的尊严, 也体现出如同黄金和宝石一般永生不朽的深长意义。
西藏西部的象雄(羊同) 地区从来被认为是西藏原始宗教本教的发源地, 后来又接受了来自伊朗高原波斯古文明中的所谓“雍仲本教” 的影响。 其中本教师中的“辛”, 就是丧葬仪轨中专门负责对遗体进行解剖、 处理的专门“祭司”, 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涉及到丧葬仪轨的部份很多与他们有关, 曾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系统的研究。①褚俊杰《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一) 》, 《中国藏学》 1989 年第3 期, 第118-134、 49 页; 褚俊杰《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续) 》, 《中国藏学》 1989 年第4 期, 第15-34 页。目前在出土黄金面具的西藏阿里噶尔县古如甲木墓地、 曲踏墓地当中, 由于遗体并未能完整保存, 无法观察到是否有过特殊处理后留下的痕迹。 但是在与西藏西部地区相邻近的尼泊尔穆斯塘地区萨木宗墓地当中, 发掘者观察到墓地遗体“76%带有确定无疑的刀痕,并且这些痕迹很明显是在死后产生的”②仝涛、 李林辉《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 第92-102 页。这是否就是在对死者遗体进行某种特殊处理的遗迹? 值得留意。 西藏阿里曲踏墓地出土黄金面具的一号墓(M1) 死者头颅用带有汉字“王侯” 字样的丝绸包裹, 面部覆盖有与真人面孔大小相仿的黄金面具, 可以肯定死者的身份等级正是唐人杜佑《通典》 中所记载的地方“酋豪” 一类人物。 联系到文献中关于遗体处理和制作“金鼻银齿” 的记载, 应当考虑其在丧葬过程中也可能采用了本教丧葬仪轨, 成为这个区域古老文明的标志性特征之一。
青海都兰热水吐蕃墓地多件、 套“拼合型” 黄金面具的出土, 表明这一习俗流行程度很高, 甚至可能在一座墓葬当中便有多套黄金面具的存在。③2019 年青海省举办的“山宗水源路之冲” 特展上虽然只展出了都兰热水吐蕃墓地出土的其中一套黄金面具, 但据悉在该墓中一共出土了6 根金制的眉毛, 表明下葬时墓内至少应有3 套黄金面具存在。这一方面表明, 吐蕃时期仍然继承了青藏高原远古时代来自西方的本教丧葬仪轨的某些遗绪, 但另一方面和西藏西部地区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黄金面具相比较, 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具体而言:
首先, 是黄金面具已经趋于大型化、 制度化。 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数据来看, 金面具的五官当中, 眉毛、 鼻子的长度均超过了10cm, 以此类推, 整个面具拼合后的长、 宽、高度, 都应与真人面容大小相当。 早期西藏西部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整体型” 小型黄金面具在这个地区没有发现。 从出土的黄金面具五官大小基本一致、 形态基本相同这一点来看, 很可能当时对于制作和使用这类黄金面具已经形成某种制度, 有一定的规制。
其次, 黄金面具的制作工艺这时更为精美, 在黄金面具五官的表面大量采用宝石、绿松石加以镶嵌, 更显金碧辉煌、 五彩斑烂。 这种在黄金面具上镶嵌珠宝的做法, 其源头至少可以上溯到中亚吉尔吉斯萨石墓地, 但在这个时期镶嵌的面积几乎达到全覆盖,使用的手法也更加丰富多样。
其三, 香港梦蝶轩公开展出的金银器当中, 和上述三套“拼合型” 的黄金面具五官同时展出的, 还有一组也是用黄金箔片拓捶而成的下颔托, 共计四件, 包括额带、 项圈、 指环和下颔托(图14),①苏方淑主编《金曜风华·赤猊青骢: 梦蝶轩藏中国古代金饰》, 第121 页, 图26。这暗示着和这些黄金面具同时使用在墓葬当中的, 可能还有此类黄金制作的下颔托。 为死者制作和使用下颔托这种葬俗,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 在西亚和中亚都曾流行, 北朝至隋唐在我国西北和中原地区也有发现, 如大同南郊北魏墓群②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大同市博物馆编著《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年, 第233 页。、 宁夏固原九龙山③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九龙山汉唐墓葬》,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年, 第129 页。、 宁夏固原史道德墓④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唐史道德墓清理简报》, 《文物》 1985 年第11 期, 第21-30、 20 页。等都有出土。 其中出土在宁夏固原史道德墓中的一套下颔托, 有金额带与下颌托共同组成, 下颔托托部有开口, 额带上有日月等图案(图15), 形制和宁夏固原九龙山唐墓所出者相似。 死者史道德生前任唐给事郎兰池正监, 是昭武九姓之后, 其先祖曾居西域, 后迁至固原。①宁夏固原博物馆《固原文物精品图集》,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下册, 第20 页。在史道德墓中出土的这组下颔托的额带上方, 有新月和日轮的图案, 也带有浓重的域外色彩, 在波斯萨珊和粟特人的装饰图案中十分流行。 这些迹象均表明, 青海都兰唐代热水墓地出土黄金面具和黄金下颔托的这些墓葬, 和同样处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宁夏地区一样, 已经受到更多的来自“丝绸之路” 上多种文明的影响。
青海都兰热水墓地所在的柴达木盆地, 既是吐谷浑故地, 也被唐代吐蕃统治长达170 多年。 从公元5 世纪到9 世纪, 这一地区事实上已经成为中西交通的中心区域和“陆上丝绸之路” 的主要干线之一, “从青海向北、 向东、 向西、 向西南, 都有着畅通的交通路线, 联系着中国与漠北、 西域、 西藏高原、 印度等地的交往, 其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②周伟洲《吐谷浑史》, 第144 页。而无论是吐谷浑人还是吐蕃人, 都不仅不曾中断过这些对外交流的通道,而且还积极参与了丝绸之路上的各种政治、 经济、 文化、 商贸、 宗教活动, 维护了这些通道的畅通, 这在文献和考古两个方面都留下来大量丰富的证据。 从这个意义上去透视青海都兰热水墓地中出土的这些黄金面具, 它们很显然都被打上了“高原丝绸之路”与外界交流、 交通、 交往的历史印迹, 是东西方文明交汇于此的珍贵考古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