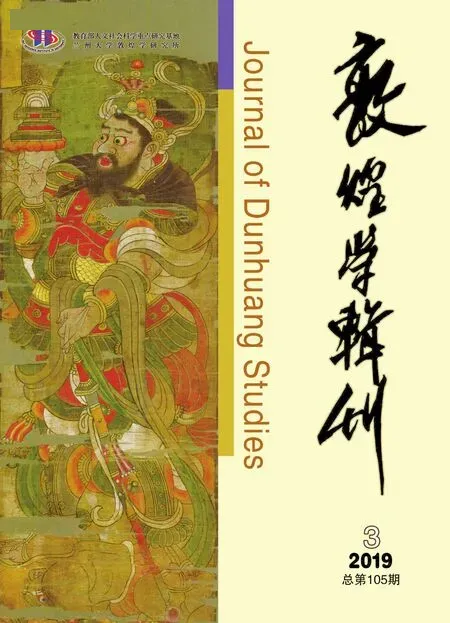敦煌莫高窟409 窟、 237 窟男供养人像考
任怀晟
(南通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 江苏 南通 266019)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古代4 至14 世纪佛教文化艺术最高成就的代表, 是享誉世界的佛教艺术宝库, 它也是多国、 多民族文化交流、 碰撞的印记。
西夏统辖敦煌近两个世纪, 其皇室笃信佛教, 作为佛教艺术荟萃之地的敦煌集中了为数不少的西夏石窟壁画, 包括佛像画、 经变画、 供养人画像等艺术作品。 莫高窟409窟男供养人画像保存完好, 是供养人画像中的精品。
409 窟东壁南侧男供养人像(图1, 1)①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 卷5,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年, 第135 页。主尊头戴尖顶高帽, 高帽有明显涂改痕迹。帽子底层有红色底纹, 近似新疆回鹘可汗的帽饰, 但是在帽子的底层之上涂有一层细腻的白色, 帽座两侧的帽带于颈下系结。 主尊身穿圆领窄袖团龙纹袍, 袍长及脚面, 袍上可见十一处团龙纹图案, 龙首居中, 龙有四足, 靠近头部有两足, 靠近尾部有两足。 团龙纹样较大, 且对称分布, 龙首均朝一个方向。 长袍左右各一条高度及腰的开衩(图上可见左侧开衩), 从开衩处可见外袍的里布为浅绿色, 里袍为白色。 腰间束浅色蹀躞带, 带头下垂, 图中可见蹀躞七事。 脚穿白色毡靴, 左手持一长柄香炉, 右手做礼佛状。 该男供养人细眼高鼻小嘴, 眉毛不清晰, 面圆颈短。 画像左侧绘一比例较小的人物, 服饰款型同男供养人, 但长袍为单一颜色, 没有装饰纹样, 双手捧一个瓶状物。 两人均站在一长方形藤蔓纹地毯上。
主尊身后侍从八身, 上第二排右侧一身只余头像、 手和剑, 其他部分无法辨识。 其余七身皆着圆领窄袖袍, 袍长及膝。 此七人中, 三人着浅绿底碎花纹袍, 分别持伞、 龙纹扇、 弓; 两人穿蓝底碎花纹袍, 持金瓜、 背负盾状物(以两带系于前胸); 另两人穿红底花袍, 持龙纹扇、 剑。 八人均头戴扇形帽, 帽带系于颈下。 腰间束蹀躞带, 脚穿白色毡靴, 眉不清晰。
东壁北侧女供养人像两身, 面部颜色已变黑, 但服饰清晰可辨。 两人头戴桃形大凤冠, 冠后垂红结绶, 宽发双鬓抱面, 戴圆形耳环, 身着大翻领窄袖长袍。
供养人题记因年代原因均已漫漶不清, 目视无法辨别。
莫高窟237 窟南壁男供养人像上半部分保存较好(图1, 2)①段文杰编《中国敦煌壁画全集》 卷10 《敦煌西夏元》, 天津: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6 年, 第24 页。。 可见供养人穿着圆领窄袖团龙纹长袍, 头戴尖顶高帽, 帽带系于颈下。 供养人面圆颈短, 双目细长, 手持供奉物, 身后可见龙纹扇、 伞。 其余部分不易辨认。 题记不存。 该窟北壁两身女供养人像, 均已模糊。 该男供养人的面部特征、 服饰、 仪仗与409 窟男供养人像十分相似, 显示出风格上的内在关联性, 故此本文将两供养人视为一组进行研究。
一、 “回鹘可汗” 说的主要依据及其疑点
409 窟男供养人像的族属是敦煌回鹘窟与西夏窟划分争论的焦点问题, 并沿及风格类似的237 窟男供养人像。 有些学者认为这些男供养人的服饰属回鹘服饰, 穿着团龙纹长袍的则是回鹘可汗。①段文杰《莫高窟晚期艺术》, 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 卷五,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7年, 第172 页。 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 《1987 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石窟考古编), 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 1990 年, 第9 页。 刘玉权《敦煌西夏石窟研究琐言》, 《敦煌研究》2009 年第4 期, 第8-11 页, 改“西夏王” 为“回鹘王”。 杨富学《沙州回鹘及其政权组织》, 《1990 年敦煌国际研讨会文集》 (石窟史地编), 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 1995 年, 第184-185 页。这是因为其圆领窄袖长袍与新疆伯孜克里克45 窟、 9 窟回鹘供养人的服装款式相同。 (图2, 1②A.Von Le Coq,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Vol. 3 Die Wandmalereien, Verlag Dietrich Reimer Ernst Vohsen / Berlin, pp 97, Tafel 18, “Bruchstück einer wandmalerei: stieterbilder uigurischer forsten” .、 图2, 2③Uyghur Princes wearing Chinese-styled robes and headgear. Bezeklik, Cave 9, 9-12th century CE, wall painting,62.4 × 59.5 cm. Located at the 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 Berlin-Dahlem. From Wikimedia Commons, the free media repository. File: 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 Dahlem Berlin Mai 2006 063.jpg, Photographed by Gryffindor,May 2006.) 其尖顶高帽, 以及身后侍从的扇形冠与伯孜克里克十六回鹘男子像(图2, 3)④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Vol. 3 Die Wandmalereien,pp 89,Tafel 14, “Bruchstück einer wandmalerei: stieterbilder uigurischer forsten” . 该画像现存于德国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 Dahlem Berlin, 编号为Bäzäklik Turfan Oase Ⅲ14。的冠廓形相似。 所以他们得出结论“两地回鹘可汗、 贵族的服饰是基本相同的。 而且回鹘可汗的服饰与回鹘王室贵族男子的衣冠服饰形制基本一致。 区别只在服装的质地和图案上, 回鹘可汗多穿有团龙图案的锦袍, 王室贵族男子多穿团花锦袍。”①谢静、 谢生保《敦煌石窟壁画中回鹘与西夏供养人服饰辨析》, 《敦煌研究》 2007 年第4 期, 第82 页。然而, 对此问题笔者认为有以下疑点:首先, 迄今为止, 新疆地区的回鹘供养人像中并未发现团龙纹长袍,也未发现相关文献记载; 其次, 409 窟男供养人长袍样式是否专属回鹘本民族仍需考证; 第三, 经对比研究, 409 窟男供养人高冠与新疆地区回鹘可汗的冠存在显著差别。 本文第二部分将对此展开详细论述。
那是否可以通过409 窟两身女供养人所着回鹘装, 判定女供养人为回鹘人, 进而推断对面的男供养人像为回鹘可汗呢? 笔者认为,虽然供养人采用写真画法, 但服饰不足以作为供养人族属的最终依据。 例如, 花蕊夫人《宫词》 “回鹘衣装回鹘马, 就中偏称小腰身”②都江堰市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都江堰市文史资料(第十辑) 》, 都江堰市政协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出版, 1994 年, 第21 页。描述的是后蜀内宫的仕女风尚, 但她们穿回鹘装却非回鹘人。又如, 元人马祖常《河西歌》 曰: “贺兰山下河西地, 女郎十八梳高髻。”③马祖常《河西歌效长吉体》, [清] 顾嗣立《元诗选(初集)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年, 第716 页。诗中所言西夏妇女常梳回鹘高髻,④杨富学《论回鹘文化对西夏的影响》, 《宋史研究论丛》 第5 辑,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第179-194 页。但她们也非回鹘人。所以, 不能以服饰作为判定族属的唯一证据。 如此以来, 也就不可能在女供养人族属的基础上推知男供养人族属。
近年松井太对409 窟回鹘文榜题的解读似为解开主尊男供养人族属之谜提供了依据。 松井先生将以技术手段从409 窟男供养人像北侧提取的榜题左列回鹘文字el alsran xan 意译为“国之狮王”。⑤[日] 松井太《敦煌石窟ウイグル语·モンゴル语题记名文集成》 “莫高窟第409 窟” 条: “所在: 主室东壁南侧。 在前面的蒙古王供养人像北侧(左侧) 的榜题上。 语注: ……关于el arslan xan ‘国之狮王’,(维吾尔语) 指称西维吾尔王的说法请参照松井2014.29 的版本。” [日] 松井太、 荒川慎太郎编《敦煌石窟多语言资料集成》, 东京外国语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语文化研究所, 2017 年, 第54 页。 杨富学《莫高窟第61 窟甬道为元代西夏窟说》, 节引此成果, “回鹘、 西夏、 元敦煌石窟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2017 年10 月14 日大会主题报告。有学者以此断定409 窟男供养人是回鹘可汗。⑥杨富学《裕固族与晚期敦煌石窟》, 《敦煌研究》 2017 年第6 期, 第46-57 页。实际上松井先生原意并非如此。 笔者将松井太对此榜题(图3)⑦[日] 松井太《敦煌诸石窟のウイグル语题记铭文に关する劄记》 (二), 《人文社會論叢·人文科学篇》第32 号, 2014 年, 第28 页, 图版。的研究结果概括如下:
榜题左侧竖列文字字符顺序错误。 如果对原字符顺序进行调整, 那么左列文字变为el arslan xan, 音译为“阿斯兰汗”。 右列文字män sävg (i), 后半部不清晰。 右列文字译意存在两种可能, 一是“沙州” (sacu) (这是指榜题题字者的出生地、 籍贯), 另一是题字者的名字“sävgi”。 文字位置布局疑点较多, 字体像蒙文正草体。
最终, 松井认为这个榜题是元代一个叫sävgi 的旧西(州) 回鹘后人题写的,①因为10-11 世纪以后回鹘文行款为字序从上向下、 竖列从左向右排布, 所以如按松井太解读, 只能从左向右翻译为“阿斯兰汗, 沙州(或者sävigi) ”。 (回鹘文行款方式参见张铁山《回鹘文献语言的结构与特点》,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第341 页。)且sävgi 不能肯定409 窟男供养人像是回鹘王像。 松井猜测409 窟男供养人像是西(州)回鹘王像, 但是他本人坦诚这个猜测没有十分可靠的依据。②[日] 松井太《敦煌诸石窟のウイグル语题记铭文に关する箚记》 (二), 第29 页。 [日] 松井太《敦煌石窟ウイグル语·モンゴル语题记铭文集成》 “莫高窟第409 窟” 条: “3. (注释) 1: ‘arslan 狮子lion’实际上被写作LSR'N =alsran 是因为L 的位置被添错了。 对于用这个elarsan xan ‘国之狮王’ (维吾尔语)指称西维吾尔王的说法请参照松井2014、 29 的版本。” 第54 页。 笔者在松井太研究基础上认为409 窟榜题“阿斯兰汗” 字符顺序错误暗示题写者对回鹘文比较生疏, 据此推论题写者的生年可能在回鹘文消亡的时期, 这个时期应在元末或晚于元代, 所以题写者对回鹘文的拼写不太熟悉。
笔者同意松井太认为该榜题是后人题写的推测。
首先, 在唐宋时期敦煌壁画中题字和绘画分别由专门的写手和画师承担, 分工明确。 题写者由文化程度较高的专人组成, 壁画创作完成, 由专人对工程进行审核验收。③Sarah E. Fraser, Performing the Visual: the Practice of Buddhist Wall Painting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618-96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89-192.若存在这样一个拼写错误的回鹘文榜题, 一定会发现, 并责令改正, 不会任其留存。 所以, 不可能出现把如此重要的信息, 即可汗称号写错并存留多年的情况。 其次,在墨色方面, 409 窟壁画中供养人手持熏香的烟雾也为墨线绘制, 色彩清晰, 而相邻的榜题墨字颜色却几近于无。 如果两者是同时绘制的, 则很难解释榜题无法辨认的原因。409 窟男供养人像中还存在侍从上身颜色被涂改的情况, 不排除这是后人涂改壁画造成的, 当然也就不能排除榜题为后人补写的可能。
即便409 窟存在与供养人像同时期题写的回鹘文榜题, 且拼写准确, 也不一定说明男供养人为回鹘可汗。 因为以“狮子” 为称号是中亚到欧洲许多民族崇拜狮子习俗的反映。 巴比伦国王称突厥皇帝为“野兽国王”④[法] 伯希和著, 冯承钧译《四天子说》, 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 第3 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 年, 第105、 106、 113 页; 原文见“ 《通报》 第22 期, 1923 年, 第97-125 页, La théorie des quatre du ciel”。 王永平《 “五王” 与“四天子” 说: 一种“世界观念” 在亚欧大陆的流动》, 《世界历史》 2015年第3 期, 第30-39 页。; 佛尊被称为“狮子王”; “狮子王” 也曾作为吐蕃对中原皇帝的尊称, 吐蕃称唐太宗为“成格赞普”, 意为“狮子王”。⑤布顿大师著, 郭和卿译《佛教史大宝藏论》 “甲二分说西藏佛教如何而来的情况”, 北京: 民族出版社,1986 年, 第170 页。《新红史》 也记载唐太宗是唐朝皇帝狮子赞普⑥娘·尼玛韦色《娘氏宗教源流》, 拉萨: 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第194 页。 “rgy nag gi rgy lpo seng ge btsn po”。 中原王朝统辖下的族群有以本族传统尊称称呼中原皇帝的习惯。 例如突厥称唐太宗为“天可汗”⑦朱振宏《唐代“皇帝·天可汗” 释义》, 《汉学研究》 第21 卷第1 期, 2003 年, 第413 页。。 故“国之狮王” 并非回鹘皇帝的专属称谓。 此外, 西夏是多民族构成的政权, 西夏皇室对一些民族采取“羁縻”政策①[元] 脱脱等撰《宋史》 卷485 《夏国传上》: “太宗尝宴群臣苑中, 谓继捧曰: ‘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诸部?’ 对曰: ‘羌人鸷悍, 但羁縻而已, 非能制也。’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年, 第13984 页。, 所以在该政权内使用其他文字也属正常。 在此情况下, 不排除西夏统治下回鹘人称党项皇帝“国之狮王” 的可能。
因此, 一方面由于同窟女供养人服饰不是判定其族属的根据, 故无法通过女供养人族属推断男供养人族属。 另一方面, 男供养人的榜题也不能作为判定族属的根据。 鉴于此, 本文以写真的供养人面部细节为主要依据, 结合服饰样式与文献记载对409 窟、237 窟男供养人像的族属进行探讨, 尝试对此问题提出新的见解, 从而推进敦煌其他同类风格供养人像的研究。
二、 莫高窟409 窟、 237 窟男供养人服饰与妆容
作为壁画中的供养人画像, 409 窟、 237 窟基本上遵循世俗人物画的写实性原则。自唐代以来中国肖像画已经很注意人物写实性。 初唐人物画代表画家阎立本以“象人”、 “肖形” 为准则, 如《步辇图》 《历代帝王图》 《萧翼赚兰亭图》 等都是“状物描形” 的名品。 敦煌壁画与新疆等地的石窟壁画也多受到唐代人物画影响②邢煦寰《中华艺术通史·隋唐卷》 (下),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第105 页。。 实际上, 有宋一代写实肖像绘画在中原和周边地区已经非常普遍, 如宋朝各代帝后像、 刘松年《中兴四将图》、 赵佶《听琴图》、 辽代《东丹王出行图》 等都是写实的佳作。 当时的墓室壁画, 如白沙宋墓、 宣化下八里辽墓等壁画中也存在丰富的写实人物像。 同时,409、 237 窟男供养人像也符合敦煌供养人画像为写真像的三个特征, 即画像精美, 只有一身且身份特殊, 同时又有明确的人物题名。③沙武田《敦煌写真邈真画稿研究——兼论敦煌画之写真肖像艺术》, 《敦煌学辑刊》 2006 年第1 期, 第20-26 页。虽然409、 237 窟男供养人像没有题名留存, 但是书写榜题的位置是预留的, 说明这些人像原本是有明确提名的。 因而,409、 237 窟男供养人像与高昌地区回鹘供养人像同样是“一张尽可能像的图像, 也就是一个肖像画”④Annemarie v. Gabain 认为: “要画一张关于他的非常系统的图片, 在旁边一个指定的书写区域内标明了名字和称谓。 如同在一份官方的文件上所标明的‘这是关于……的照片’ 为了能够确定, 会画一张尽可能像的图像, 也是就一个肖像画。” Annemarie v. Gabain, Das Uigurische Koenigreich von Chotscho 850-1250,Berlin: Akademie-Verlag, 1961, pp 55., 而非程式化的写意作品。 因为人物写真的写实与传神体现在人物面目表情之描画,⑤沙武田《敦煌写真邈真画稿研究——兼论敦煌画之写真肖像艺术》, 《敦煌学辑刊》 2006 年第1 期, 第20-26 页。族属特征也是按照供养人期冀的样式描绘。⑥沙武田《敦煌石窟归义军曹氏供养人画像与其族属之判别》, 《西部考古》 第6 辑, 西安: 三秦出版社,2012 年, 第207、 225、 226 页。 文中指出归义军曹氏画像采用汉人面貌特征刻画, 已达到掩盖粟特胡人移民身份的愿望。 所以, 面貌族属特征是敦煌供养人非常注重的细节, 也是后世判断供养人族属的依据。所以, 供养人像可以作为族属判定的依据。
当然这些人物画在写实的基础上也会进行细节的修饰美化, 从而符合当时的审美标准。 比如, 为了体现身份地位的差异, 画家会调整画中人物尺寸大小。 但每个人物的比例、 基本特征都会忠实于人物原貌。①衷心感谢田孟秋女士对“供养人像为写实肖像画” 观点的论述!
(一) 冠
新疆地区的回鹘贵族供养人常头戴仰莲饰花金冠。 此冠上尖下圆, 形似贝壳, 无顶, 底座窄而冠身宽, 冠尖略向后倾斜, 冠有前后两层, 前低后高, 外沿均为曲线状,冠带系于颈下。 伯孜克里克9 窟、 45 窟的冠边缘饰有花纹, 前中有一拳头状结构。 考虑到当时的条件, 这种冠应该是由金属制成, 工艺上则采用敲铜工艺。 沿帽缘的花纹是绘制上去的。 (图4, 1-3)
莫高窟409 窟男供养人的帽子情况则较为复杂。 经辨认, 该帽有底层和表层之分。首先, 底层显示出的帽子轮廓, 是一种与新疆伯孜克里克回鹘可汗帽型基本一致的帽子。 其次, 经色彩分层分析发现, 表层的白色应该是画师对底层帽子的覆盖, 只是因为年代久远其表层的白色逐步脱落, 所以露出了底层帽子的红色纹样。 第三, 画面底层的红色纹样浮现均匀, 所以可知当时画家涂白色时非常仔细, 注意用色的均匀, 由此造成现存白色粉粒自然脱落后, 底色呈现出色彩均匀的效果。 同时可观察到, 此高帽沿外轮廓勾线的线条粗细色彩均匀, 显示出画师勾画准确、 运笔稳健。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底层轮廓与新疆地区回鹘可汗帽型相同的情况, 笔者推测有可能是画师一开始使用了外来粉本, 即新疆传入的粉本绘制帽子, 经(出资人、 僧侣) 发现不适用于该窟供养人, 从而做了刻意的修改。
综上所述, 409 窟男供养人帽子的终稿是一个封闭、 尖顶、 橄榄型、 白色高帽。(图4, 4-5) 当时能用于体现该帽通体白色、 质地均一、 无接缝效果的材料只能是金属或者毛毡。 由于金属太重, 戴上后因具有一定高度会导致重心不稳, 且没有金属能呈现出该帽特有的白色质感效果。 而西夏统治过的地区生产优质白驼毡、 且名气很大,①[意] 马可波罗著,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 第164 页。所以采用毛毡和擀毡工艺制作比较符合历史情况。 (图5, 1) 这与新疆伯孜克里克回鹘贵族男子像的冠存在明显区别。 (图5, 2)②衷心感谢孙建华、 袁海军先生的复原工作和田孟秋女士对冠型结构的研究!
就409 窟侍从所戴的扇形冠而言, 在伯孜克里克壁画十六回鹘男子像中, 下排的后四人头上似乎也出现了廓形类似的冠。 但不同的是, 新疆的冠是竖立于头顶中央, 没有罩住头发; 此外, 这些“帽” 也没有下颌带。 而409 窟的扇形冠下口宽大, 更像是法式贝雷帽。 最显著的区别是这些随从帽子的底座上缠绕有一条彩色的条带, 而十六回鹘男子像中的帽子则没有此带。 因此,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冠。
(二) 团龙纹袍
伯孜克里克9 窟、 45 窟回鹘供养人像也出现了与409 窟款式相同的圆领窄袖侧开衩长袍, 但它们不是回鹘专属服装。 高昌地区回鹘男供养人像主要出现过两种服装款式: 一种是以伯孜克里克十六回鹘男子像为代表的右衽饰带长袍。 长袍有四处镶边饰带: 一条从颈右侧一直延伸到脚面, 一条沿下摆水平延伸, 另两条分别在上臂中部。 这种饰带或许是对面料毛边、 拼缝的包边处理。 冯·佳班发现“宽饰带总是黄色的, 并且上面有红色的线条状纹样”,③Annemarie v. Gabain , Das Uigurische Koenigreich von Chotscho 850-1250, pp 39.可见宽饰带具有较强的装饰性和统一性。 另一种款式则为装饰单独纹样的圆领窄袖长袍, 如伯孜克里克9、 17、 45 窟供养人袍采用的单独纹样。
两种款式, 前者是回鹘自身的民族服装, 后者是源于自北朝隋唐衍生而来的中原公服。①圆领窄袖袍来源于北朝时期, 当时鲜卑政权入主中原, 建立服饰制度, 就将胡风国俗相糅合。 圆领窄袖袍作为官员的常服出现在朝堂之上。 到了唐代, 这种常服也称为公服。 到了宋代, 圆领窄袖公服的等级差异是根据颜色、 纹样和材质来区分的。宋临阎立本《唐太宗画像》 (图6, 1) 的团龙纹长袍就是这种款式。 后者出现在高昌回鹘贵族供养人画像上, 是因为高昌曾深受中原文化影响。 贞观十四年(640),唐进军高昌, 设安西都护府, 并以将士戍边, 将中原汉文化传播到高昌。
而西夏也深受中原服饰文化的影响。 首先, 在款式上。 409、 237 窟男供养人的圆领窄袖袍也源于北朝隋唐以来的中原公服。 史籍记载了西夏接受宋朝赏赐和倾慕中原衣冠的情况。 如,
保忠辞日, (太宗) 宴于长春殿, 赐袭衣、 玉带、 银鞍马、 锦彩三千匹、 银器三千两, 又赐锦袍、 银帶五百、 副马百匹。
(德明) 吾族三十年衣锦绮, 此宋恩也, 不可负。 嘉祐六年, (谅祚) 上书自言慕中国衣冠, 明年当以此迎使者。 诏许之。②[元] 脱脱等撰《宋史》 卷485 《夏国传上》, 第13984 页。
再者, 409、 237 窟男供养人袍服与同时期汉、 回鹘、 契丹等民族所穿着的同款长袍同源(图6, 2-4)。
其次, 在服装纹样上, 409、 237 窟供养人袍服团龙纹(图7, 1) 与内蒙古赤峰市庆州白塔寺出土的辽代团龙纹刺绣十分相似(图7, 2)。 西夏初期的统治者多采取向辽称臣、 与辽联姻的“联辽” 政策,①[元] 脱脱等撰《宋史》 卷485 《夏国传上》: “辽以义成公主嫁继迁…… (元昊) 凡五娶, 一曰大辽兴平公主。” 第13986 页。夏辽贡赐密切。 而历史上辽和西夏都积极接受包括龙纹在内的中原服饰文化, 因而西夏和辽服装上出现中原地区崇尚、 且样式基本相同的龙纹也是符合史实的。②感谢田孟秋女士提供该部分团龙纹对比研究成果!
另外, 迄今为止, 两窟主尊男供养人像外袍上的团龙纹, 在新疆地区回鹘服饰图像中还没被发现过。 而西夏对团龙纹的使用规范却有明确的记载。 《天盛律令》 “敕禁门”规定:
节亲主、 诸大小官员、 僧人、 道士等一律敕禁男女穿戴鸟足黄(汉语石黄)、鸟足赤(汉语石红)、 杏黄、 绣花、 饰金、 有日月, 及原已纺织中有一色花身, 有日月, 及杂色等上有一团身龙(汉语团身龙), 官民女人冠子上插以真金之凤凰龙样一齐使用。 倘若违律时, 徒二年。④史金波、 聂鸿音、 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9 年, 第282 页。
西夏法律规定亲王(节亲主) 在内的官员禁服团身龙纹, 这种纹饰只有西夏皇帝才可服用。 史金波先生指出“假若409 窟是沙州回鹘王的供养人, 在后来西夏管理沙州漫长的岁月中, 西夏的统治者对这种明显僭越的壁画, 也不会容许它存在。”⑤史金波《西夏皇室和敦煌莫高窟刍议》, 第167 页。
所以, 409 窟、 237 窟供养人团龙纹袍样式应属西夏时期。
(三) 须眉及五官
回鹘人的须眉、 五官特点突出。 在高昌回鹘供养人画像上, 可以看到回鹘成年男子皆蓄须。 胡须造型可归纳为两种: 一种是上唇有髭, 两鬓连下巴留有络腮胡; 另一种是上唇有髭, 同时下巴处留有一绺或两绺山羊胡。 伯孜克里克9 窟供养人就刻意将山羊胡分成两绺, (图2, 2) 画师精细刻画了这一特点。 另外, 高昌壁画也很好的刻画了浓眉深目的回鹘人五官特征。
甘、 凉、 瓜、 沙回鹘人也同样具备这些人种特点。 史载:
回鹘自唐末浸微, 本朝盛时, 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 女真破陕, 悉徙之燕山、甘、 凉、 瓜、 沙。 旧皆有族帐, 后悉羁縻于西夏, 唯居四郡外地者, 颇自为国, 有君长。 其人卷发深目, 眉修而浓, 自眼睫而下多虬髯。 […] 今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虬者, 盖与汉儿通而生也。①[宋] 洪皓《松漠纪闻》, 李澍田《长白丛书(初集)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6 年, 第15 页。
这是1125-1143 年洪皓羁留金朝时所见, 也就是金朝早期的回鹘情况。 可知, 直到金代, 沙州回鹘人仍然保留着本族群鲜明的人种特征。 这种特征的文献记载与高昌地区壁画中的回鹘人面貌特征是一致的。 这也印证了高昌壁画对回鹘人面貌的刻画是写实的。
而莫高窟409 窟、 237 窟, 榆林窟29 窟男供养人像都有无须的特点。 (图8)②敦煌研究院主编《敦煌石窟全集》 卷24 《服饰画卷》, 香港: 香港商务印书馆, 2005 年, 第214 页。西夏谚语中有“没有胡子拿镊子, 肚子未大松腰带”③陈炳应译《西夏谚语》,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第12 页。 该书为乾佑丁未十八年西夏御史承旨番大学士梁德养著《新集锦成对谚语》。的记载, 可见西夏党项人有用镊子拔除胡须的习惯。 当今大凉山彝族祖先来自古羌人, 他们至今仍保留拔除胡须的习俗。 彝族“尔比” 有记载: “跟着汉族留胡须, 跟着彝族拔胡须。说是汉族没胡须, 说是彝族没英雄结。”④陈国光《彝族“尔比” 对彝、 汉族群差异性的认知》,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年第1 期, 第60-63 页。 是文“尔比” 均引自沈伍已《彝族尔比词典》 (彝文版),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 年。这两句谚语既说明了彝汉外貌的特征, 也说明了彝族以无须为美的风俗特点。 这与西夏党项羌人拔须的风俗完全相同。
西夏王朝是由党项羌人建立的多民族政权,西夏人包括党项羌人、 汉人、 回鹘人、 吐蕃等多个民族, 除须仅是党项人的风俗习惯。 因为,没有资料证实西夏强制其他民族除须, 因而西夏世俗供养人像中蓄须人物应不是党项羌人。
如将409、 237 窟两供养人像与新疆地区回鹘男子供养像的脸型和五官进行对比,发现区别显著: 前者面圆颈短, 细眉细眼, 显示出蒙古人种特征; 后者浓眉深目, 眉峰清晰, 毛发重, 显示出欧罗巴人种特征。 故409、 237 窟男供养人应非回鹘民族。
(四) 发式
高昌等地的回鹘供养人画像上, 均能看到明显的披发, 画师特意刻画了这一特点。以伯孜克里克十六回鹘男子像为例, “回鹘男子的头发在中间分向两侧, 长长的一缕垂在后背上。 偶尔在前额上会有流海, 同样从中间分向两边。 绘画中从未出现男性辫发的形象, 女性辫发形象则少见。”①Annemarie v. Gabain, Das Uigurische Koenigreich von Chotscho 850-1250, pp 38.有些回鹘贵族成年男子喜欢将额角修剪成接近直角的折线(图2, 2)。 此外, 画像中的世俗成年男子和男童也采用披发样式。 沙州相邻的甘州回鹘, 也保留了这一民族习俗。 文献记载, 甘州回鹘以“披发” 为礼。 史载:
(甘州回鹘) 其可汗常楼居, 妻号天公主, 其国相号媚禄都督。 见可汗, 则去帽被发而入以为礼。②[宋]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 卷74 《四夷附录第三》,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年, 第916 页。
然而409 窟男供养人和侍从既没有披发, 也没有流海这类高昌回鹘男子的发式, 这一特点同样清晰地反映在237 窟供养人像上。 闽宁村墓地和银川西夏陵6 号陵出土的俑头都证实了西夏戴冠权贵采用束发的形式。③任怀晟、 田孟秋《从帽式看西夏朝服》,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2017.02, 学术报告; 任怀晟、 田孟秋《西夏朝服的冠饰研究》, 《西夏学》 2018 年第2 期, 第86-93 页。(图9, 1-2)④史金波、 李进増《西夏文物·宁夏卷》,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年, 第4885 页。这种情况在文献中也有反映:
元昊结发用兵, 凡二十年, 无能折其强者。⑤[元] 脱脱等撰《宋史》 卷485 《夏国上》, 第14030 页。这句话记载了元昊从天圣六年(26 岁) 攻打甘州开始, 一直到他去世前二十年间英勇善战的情况。 同时, 这里的“结发” 也反映了元昊发式的特点。
另外《天盛律令》 “许举不许举门” 中规定“诸人不许服丧服, 披发, 头中有白,冬冠凉笠入于内宫, 及相互礼拜等”。①史金波、 聂鸿音、 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卷12 “内宫待命等头门”, 第435 页。说明西夏有臣僚入宫、 礼拜时不许披发的规定。
是否存在以下情况: 这些窟中供养人无须无发是因为年代久远、 颜色衰退或剥落造成他们面容不清晰、 须发难辨。 从绘画的技术层面看, 即使绘制这种浓密披发、 虬髯的颜料脱落, 也应该在绘制原处留下一个比较明显的轮廓。 而在409 窟、 237 窟男供养人和侍从像上, 这种色彩剥落的痕迹没有出现, 说明原画没有绘制浓密的须髯和长披发。
除以上几个方面外, 两窟两男供养人像的仪仗形制也与西夏史籍记载相符。 史金波先生发现《天盛律令》 中规定只有西夏皇帝才可使用“伞”, 即华盖。②史金波《西夏皇室和敦煌莫高窟刍议》, 《西夏学》 第4 辑, 2009 年, 第165-171 页。 类似观点的论文有:白滨、 史金波《莫高窟、 榆林窟西夏资料概述》, 《敦煌学辑刊》 1980 年第3 期, 第63-68 页。 陈炳应《莫高窟、 榆林窟西夏专题考察述论》, 《丝绸之路》 2011 年第18 期, 第91-94 页。 汤晓芳《西夏艺术的遗存、 分类与价值》 (上),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3 年第2 期, 第93-99 页。《宋史》 中对于西夏皇帝元昊出行时的仪仗也有记载:
(元昊) 少时好衣长袖绯衣, 冠黑冠, 佩弓矢, 从卫步卒张青盖。③[元] 脱脱等撰《宋史》 卷485 《夏国传上》, 第13993 页。
这里的“青盖” 与“弓矢” 与409 窟男供养人像中的伞、 弓箭, 以及237 窟的伞相符。
综上所述, 敦煌莫高窟409 窟、 237 窟男供养人的帽与新疆地区回鹘贵族的冠存在差异, 窄袖长袍款式为多民族共有; 其团龙纹近似于同样受中原文化影响的辽代服饰纹样; 且团龙纹与两供养人像中的“伞” 均符合西夏律令和《宋史》 记载; 无须、 束发也符合历史文献对党项族妆容的描述。 因而, 可以确认这两窟男供养人均为西夏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