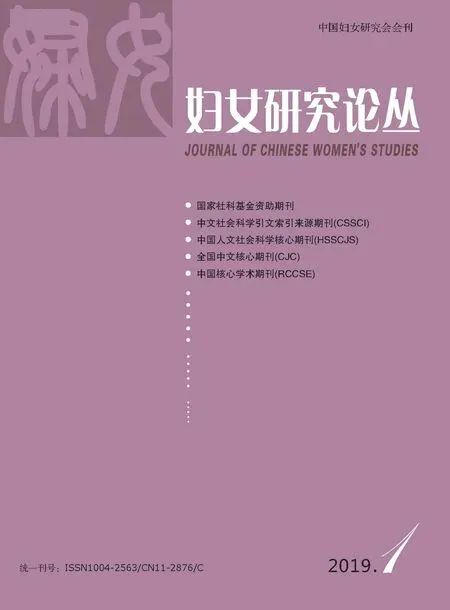性别:作为文学分析的方法
——评《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及相关系列丛书
董丽敏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作为当代性别研究的开端,女性文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兴起,既与“拨乱反正”的特定社会历史语境息息相关,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域外女性主义理论跨国旅行的需要,甚至暗合了国际学界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转向”潮流,因而它并不是一个局限在文学研究领域内部的孤立事件,而更应被视为当代中国知识生产嬗变的一个缩影。基于这样的前提,女性文学研究的应运而生,就不只是指向文学学科内部新的研究空间的探索,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当代中国学术版图尤其是妇女/性别研究领域的拓展甚至重构,并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在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伴随着与国际接轨的“社会性别”研究范式的进入,女性文学研究逐渐演变为以社会性别视角展开的文学研究,“从性别角度构建新型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事”[1]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然而,范式的转型似乎并没有带来更多的社会认同,相反,却常常因为被指斥为与社会性别状况相“断裂”而出现了普遍的“危机感”:“一边是女性文学研究的规范化和学科化,一边是大众文化和社会常识系统中女性形象想象的刻板化和定型化”[2]。如何在勾勒三十多年来的女性/性别文学研究发展轨迹的基础上,进一步明晰“女性/性别”与“文学”在中国语境中结合所产生的特殊学术品格与价值指向,进而为女性/性别文学研究勾勒出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成为亟需重视和突破的瓶颈问题。
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最终成果,南开大学乔以钢教授等著的《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以及由10本著作构成的“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丛书”[注]这些著作具体包括:乔以钢等著的《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乔以钢主编的“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丛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2016年出版,共10本著作),包括:陈洪、乔以钢等著的《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的性别审视》(2009),刘思谦、屈雅君等著的《性别研究:理论背景与文学文化阐释》(2010),张莉著的《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2010),乔以钢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现象与性别》(2012),陈惠芬等著的《现代性的姿容:性别视角下的上海都市文化》(2013),陈千里著的《因性而别:中国现代文学家庭书写新论》(2013),陈宁著的《女性身体观念与当代文学批评》(2014),刘堃著的《晚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传统再构》(2015),马勤勤著的《隐蔽的风景: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创作研究》(2016),[韩]李贞玉著的《清末民初的“善女子”想象》(2016)。,正可以被搁置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加以讨论。这一系列著作立足于“性别”,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与文化现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其问题意识、理论资源乃至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近年来女性/性别文学研究的一些新特点、新变化、新趋势,值得进一步关注。
一
作为研究的基础和起点,如何来理解“性别”这一聚讼纷纭的核心概念,无疑是该系列著作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乔以钢认为,“性别”“反映了一种不无策略性而又关乎根本的学术意识”,具体表现为,“首先,它包括妇女,但并非特指妇女”;“其次,‘性别’肯定和强调了不同性别之间密切关联、互为参照的关系”;“最后,‘性别’暗示着主体认同的社会根源,提示着社会文化建构性别、造就不同的角色分工的事实”[3](P 2)。这一颇为辩证的“性别”概念界定显然涵盖了作者一系列的思考:辨析“性别”与“妇女”之间的差异,不只是为了概念外延的扩大,更为重要的是立场的调整——从单一的“女性主义”立场调整为对两性的共同关注,意味着一种结构化的性别观照视野的生成;强调两性之间互为依存,使得“性别”概念的重心不再落在“性/别”的差异性层面,而指向两性共同发展的整体性因素;将“性别”与源远流长的社会分工状况勾连在一起,则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出“性别”不只是一种文化政治,而更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因而性别问题归根结底仍需要回到具体社会根源中去加以处理。
可以说,这样的“性别”概念界定,在理论脉络上呼应了从“女性”到“性别”的研究范式的转换。一般说来,“性别”概念主要来源于“西方女权主义在对她们的文化、历史、社会的剖析过程中发展”的“社会性别”[4]理论。作为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以及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积累”[5]的特定产物,“社会性别”理论建立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框架以及特定的社会文化所形成的两性差异基础上,因而由此产生的“性别”概念就会以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男性/女性乃至公领域/私领域之间的区隔作为内涵建构的起点。而在乔以钢的视野中,“性别”概念则被定位在“策略”与“根本”之间,性别分析被理解为“以‘人’为对象并为宗旨的综合—分析方法模式”[6](P 2)。显然,这样的“性别”及性别分析模式的理解并不能被完全纳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语境中的“社会性别”理论框架中,它更强调性别和解而不是性别对抗,瞩目于作为“有性的人”的完整性而非单一性别维度,注重在传统经验中而非在抽象的话语层面理解性别问题的复杂性。可以说,上述“性别”概念建构,其实是以男性/女性为基本范畴,通过引入文化/实践、历史/当下等多重维度,试图在内涵构成上推动其进一步本土化和语境化,进而拓展出更为复杂而有弹性的“性别”讨论空间。
在这样的梳理中,才更能理解以《性别研究:理论背景与文学文化阐释》(刘思谦、屈雅君等著)一书为代表的系列著作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性别”与“文学”如何有效结合所做出的种种理论探索。与从“女性”到“性别”的研究范式的转换相一致,该书所收录的论文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从“女性文学”到“性别文学”的嬗变轨迹及其内在逻辑的建构过程。尽管“女性文学”概念一直存在争议,但该书所选入的有关论文仍体现了独到的思考。如刘思谦在《女性文学这个概念》一文中认为,对“女性文学”的理解不能就事论事,而需要将其放置在作为根本的历史观中去理解:“如何认识女性文学的诞生和如何界定女性文学这一概念,关系到我们对历史的根本看法。”她进一步指出,“只有在人类文明由母系制到父权制再到近现代由传统的封建父权社会向现代化自由民主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才可能出现属于女性自己的文学。这是女性文学诞生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也是她的必要前提和历史条件”[7](P 55)。这一认识,规避了仅仅从抽象的概念层面来定义“女性文学”的内涵,通过还原“女性文学”得以诞生的历史语境,将其重新嵌入社会文化结构中,从而揭示其作为“现代性”事件的性质。由此,她将“女性文学”定义为是与“五四”精神相一致的具有“女性主体性”的文学:“女性文学是诞生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的、以女性为言说主体、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的文学。”[7](P 57)或许这一定义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但这种内外打通的“在地化”论证思路本身,无疑是“女性文学”可以在中国落地生根并获得合法性的基石。
之所以会有从“女性文学”到“性别文学”的研究范式转变,系列著作也提供了一系列的论证。刘思谦指出,“‘性别’这个概念所涵盖的既包括女性也包括男性,既包括女性文学文本也包括男性文学文本,将二者作为互为参照比较的互文本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将会发现文学作品中一些习焉不察、视而不见的被遮蔽的问题和意义”,在此基础上,“由于‘性别’无法割断与政治、权力、经济、文化的联系”,“种种有性别而又超越性别的人性的、政治的、心理的、审美的意义将会进入我们的视野”[7](P 31)。这种“有性别而又超越性别”的性别批评原则,显然已经不止于从女权立场进入文学研究,而更关注在性别维度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维度有机结合的基础上,打开文学研究的新空间,特别是不同性别文本之间复杂的勾连及其藉由“性别”所指向的特定的社会文化。在这里,“性别”作为文学研究方法,其指向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显然都得到了尊重,从而使得“性别”与“文学”的结合不再如“女性文学”那样是局限的、边缘的、孤立的,而是具有与主流研究相贯通的可能性。
屈雅君认为,“性别”与“文学”的有效结合需要建立在“去本质主义”的“女性”基础上:“自觉的性别批评不是认同某种经过框范的女性‘本质’,或者重复体验一种被给予的女性经验,而是根据她自身被某种思想点亮的经验和这些经验与阅读对象之间的遇合、离间、撞击去生成新的经验。”[7](P 215)对整齐划一的“女性”本质的警惕,使她更注重文学作品中女性经验的流动性、多元性与生成性。这种具有解构主义色彩的“性别文学”理解方式,既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后殖民女性主义资源的汲取,潜藏着对后发现代性国家女性主体位置的探寻和建构,同时,也涵盖了对中国本土语境中女性文学经验的重返乃至激活。乔以钢进一步将性别批评与社会文化构成联系在一起,强调了后者之于前者的决定性意义,以及性别批评对于女性主义批评的超越性所在:“性别批评,作为广义的性别文化研究,立足于社会文化构成,以社会分析范畴取代生理决定论,超越传统性别内涵,打破传统女性主义批评的二元对立思维,重绘了人类深层性别结构的文化图景。”[7](P 67)
对于陈惠芬来说,“性别”分析不仅指向实然意义上的性别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其甚至可以在抽象的层面上被扩大为对所有权力等级关系中所谓“次等”位置的质疑:“在权力的谱系中,所谓‘女性’指称的其实并不是生理意义上的女性,而是权力的等级,它可以是女性人物,也可以是男性人物或其他事物,只要它们占据的是‘次等’的女性化的处境和位置。”[8](P 23)如果依据这一逻辑,那么“女性”乃至“性别”其实就更多转化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受压迫的符号,在文化隐喻的意义上,性别分析将会与更为多样化的压迫/反抗形式勾连在一起,并为此提供可以分享的经验和形式,从而打开更为广阔的学术疆域。
可以说,在“性别”与“文学”的关系理解上,上述研究者的观点尽管存在一定差异,但表现出了某种值得关注的相通性,即“性别”并没有被简单地定位成一种先验的立场,而更多是一种具有开放意味的视野和方法,一种既与性别问题直接相关却又不限于性别领域而可能有利于观照社会领域内其他权力压迫问题的视野和方法;“性别”并不优先于也不外在于“文学”而存在,需要与文学特有的分析手段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应有作用。立足于这一格局,系列著作由此形成基本研究方案:“从性别视角出发,审视中国古代文学及文化传统”,“考察文学现代性生成过程中性别因素的多样表现,对文学文化现象进行性别分析”;“对中国妇女/女性文学史书写进行反思”;“在性别视野中对文学语言进行深入研究,探察文学文本呈现的特定语言形态与性别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考察性别研究的理论背景,剖析性别理论与其他当代理论思潮之间的复杂纠葛”[9](PP 4-5)。对系列著作而言,以“性别”为原点,从视角、叙事、知识、语言、思潮等方面与文学/文学史有机结合,成为可以推动“性别文学”研究走向可能的方法论预设。
二
尽管如此,“性别文学”研究要想成为一种令人信服的研究范式,仍需要在实践层面上提供具有拓展性和生产性的具体阐释。这不仅意味着,“性别文学”研究需要在文学内部开疆拓土,形成不只对于女性文学领域而且对于整个文学传统都具有开创意义的成果。而且作为“性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还需要以文学为方法,为处理好实践层面的性别问题提供必要的经验/理论支撑。很大程度上,上述问题意识正可以被视为系列著作运用“性别文学”研究范式开展具体研究时的基本出发点。
可以发现,该系列著作形成了两大研究重点:其一,从纵向的历时性角度描绘中国“性别文学”的基本图景,归纳“性别文学”演进的一般规律,尤其注重在古今演变的大格局中来呈现女性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内在复杂性。应该说,在近年来的文学研究界引入“性别”维度已渐成风潮,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现当代文学还是古代文学对“性别文学”研究范式的运用,大多限于学科领域归属而存在着将其人为切割为断代史研究的问题,如何打破学科壁垒并在更大的格局中勾勒“性别文学”的发展轨迹,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推进。“丛书”的突破显然正在于此——通过收入《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的性别审视》(陈洪、乔以钢等著)、《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现象与性别》(乔以钢等著)等不同时段“性别文学”研究著作,“丛书”表现出了试图整合不同时段的“性别文学”的意图。值得注意的是,该套“丛书”并不满足于仅仅做物理意义上的断代文学史的叠加,而更着眼于探索长时段的“性别文学史”建构的可能性,因而,以“性别”为中轴来讨论历史/文学史的“断裂”/“接续”的关系问题,就成为势之必然。
在这一格局中,《晚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传统再构》(刘堃著)、《清末民初的“善女子”想象》(李贞玉著)、《隐蔽的风景: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创作研究》(马勤勤著)、《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张莉著)等一系列著作所做出的进展,需要好好分析。这些著作或以文学为主要场域聚焦于传统中国女德/女教在清末民初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及转型的艰难,或从“闺情”“启蒙”“市场”“学校”等多重维度着力挖掘被转型时期主流历史所湮没的女性创作的特殊贡献,或从新的文学/文化生产机制入手探讨“现代”女性文学得以诞生的根源……无论是致力于内部研究还是外部研究,上述研究对于性别文学/文化转型现场的清理,都体现出了企图在对“转型”的复杂研究中打通“断裂”/“接续”这样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努力。
刘堃立足于晚清中西文化互动乃至互渗的背景,梳理了这一时期性别文学资源构成的流动性、多样性与复杂性。一方面,她敏锐地看到了现代性的要求如何进入并改造了传统的性别符码,如“‘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与其说是出自儒家女性/女教观的固有传统,不如说是亚洲近代化要求的产物”,因为“儒家传统女性观的思想基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观念,而‘贤妻良母’的妇女观则出于以近代西方人权思想为基础的平等观”[10](P P90-91)。另一方面,她考察了传统性别文化资源在新的观念体系中被认知、转化并生成新的意义的复杂过程,如通过对类似于《浮生六记》这样的文本在现代中国被“发明”的过程,她梳理了俞平伯、林语堂、潘光旦三位“新文化人”所分别代表的“启蒙主义、文化调和主义和唯科学主义这三种认识路径”,指出“芸娘这一‘理想/非理想妻子’的形象,是作为某种喻体、某种象征而镶嵌并内在于沈复所代表的民间文人文化或者中国式人生哲学之中的,因而不具备单独被讨论的可能和意义”[10](P P274-275)。李贞玉则通过对“善女子”这一晚清女性人物类型的概念史式的梳理指出,其“曲折投射了‘女侠’‘女英雄’‘英雌女杰’等晚清话语对女国民/政治新成员的想象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谱系的暗合与统一”[11](P 1),因此“善女子”并不能放在普泛意义上的女德层面来讨论,而更应被视作“孝女”“侠女”“烈女”等传统性别资源之于特定社会文化危机的一种应对形式:“‘善女子’形象涉及民族意识与文化认同的博弈,以及知识分子对女性角色的重估、对社会责任感的强调等关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问题。”[11](P 233)可以说,就性别文化传统内部而言,建立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前提下,“断裂”与“接续”因而更多构成了类似于“一体两面”的关系。
与这样的梳理形成某种呼应,“女性文学”在近代中国的诞生,同样具有被复杂化讨论的空间。马勤勤认为,“近代”不能仅仅被看作方法或策略,而更应关注到其独立性的一面:“我们该如何避免‘近代’继续沦为‘现代’的注脚,彰显‘近代’作为‘近代’的独一无二?”[12](P 5)。由这样的质疑出发,她强调了对原点的研究需要从“历时性”话语中解放出来而关注“共时性”维度的重要性,指出“女性小说”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同处于文化边缘的‘女性’与‘小说’,共同参与了当时文学权利与性别权利的争夺”[12](PP 7-8),在这个意义上,她认为“清末民初才是中国女性小说创作的起点”[12](P 7)。张莉则试图通过“梳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女作家的教育史、生活史及写作史”,来回溯“女学生与现代女性文学发生的渊源”[13](P 1)。此外,她还在论著中讨论了“现代女性写作风格”,其中不仅包含对女学生形象的讨论,还涉及“女性知识分子视角”“女性第一人称”“日记体、书信体”等女性叙事形式特点的分析。藉此,她不仅描绘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发生的基本轨迹及其基本风貌,而且尝试以此为切入口,意在“使重新理解现代文学发生史成为可能”[13](P 310)。
可以看到,研究者运用“性别文学”范式进入清末民初这一特殊的社会文化转型期文学领域时,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本土现代性”研究思路,同时,还试图在“历史化”与“化历史”之间寻找某种研究需要的平衡,从而在“断裂”与“接续”之间建构出具有某种整合性的诠释框架,为长时段的性别文学史书写探寻可能的路径。正是有了这样的研究准备,《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这样的熔古今于一炉的性别文学史书写尝试才得以在理论层面获得了支撑。尽管该著作仍以“古代”“现代”“当代”等学界约定俗成的文学史分段作为书写的基本依据,但无论是理论阐释还是个案分析,大多关注到性别文化传统在古/今、中/西、新/旧等看似对峙的格局中实际上发生的传承性、流动性及变异性,这种对历史肌理深处“变”与“不变”的自觉把握意识,使得其中短时段的性别文学分析因获得了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研究视野,而能够超越差异性和封闭性,由此而汇聚起的长时段性别文学史才初步具有在历史维度和性别维度都经得起考验的内在逻辑性。
其二,从“性别文学”出发,从横向讨论其与主体、阶级以及空间的关系,尤其是通过这样的联结来分析现代中国性别文化的价值指向,进而从一个侧面把握20世纪中国独特的现代性进程,也产出了一系列颇引人深思的成果,有《女性身体观念与当代文学批评》(陈宁著)、《因性而别:中国现代文学家庭书写新论》(陈千里著)、《现代性的姿容:性别视角下的上海都市文化》(陈惠芬等著)等。
如果说长时段的性别文学史架构试图解决的是“性别文学”的“历史化”问题,那么,发现甚至发明“性别文学”与同时代重要事件/概念的关联,其实要处理的是“性别文学”的“在地化”问题。作为“性别文学”研究的重要术语,“身体”概念及其话语的域外色彩是显而易见的。陈宁强调了从特定意识形态角度进入身体研究的重要性,指出“身体”样貌是在“多重话语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这里既混合着经由媒体表达的国家话语和文化精英话语,同时民间日常生活自身的发展逻辑又对前两者不断地进行利用和改造”[14](P 40),提出“建构中国女性身体书写的历史”,“考察其不同样态与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14](P 194),重点讨论身体与疾病、服饰、饮食等日常生活构成之间的关系问题[14](PP 198-199)。在这一格局中,“身体”显然成为一种指向文化政治的“有意味的形式”,有关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演变的梳理,落在了对于女性之为女性的文化构造机制的追寻上,同时,这样的处理也隐含了以女性身体为符码进入20世纪中国日常生活分析的意图。
较之于“身体”概念,对“家庭”话语的分析显然更容易触摸到本土社会文化特性。陈千里以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自古至今小说中的家庭书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着重讨论了近代以来家庭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息息相关性,指出家庭观念的变革包含了对纲常伦理、传统大家庭以及性别关系的反思和批判[15](PP 55-64)。另一方面,她注意到不同性别的作家之于家庭观念变革的不同立场和态度,选择了“‘神圣’与‘世俗’”“‘淑女’与‘荡妇’”“‘支配’与‘平等’”等几组关系,来讨论性别差异之于文学书写的影响。在上述讨论中,“家庭”作为关涉情感、伦理、代际的基本社会单位,其功能的、价值的乃至美学的种种维度得到了一定的观照。
陈惠芬等人则将“性别”放置在现代都市文化的演进过程中加以研究,旨在说明“现代性是‘有性’的,其‘姿容’很多时候是由性别/女性所表现的”[8](P 3)。如通过对现代中国“摩登女郎”形象的分析,指出“现代意义上的消费不仅仅是对物质的享用,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或重建,摩登女郎恰是以此实现了她们在都市的占位”[8](PP 15-16);而藉由对《神女》的解读,则发现其中“阶级意识和性别关系互为‘勾连’”,“神女”身体“被任意地‘污名化’,这是父权社会特别‘赋予’女性的惩罚,其对女性的伤害并不比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轻”[8](PP 350-357)。应该说,在陈惠芬等人的视野中,“性别”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不只是用来呈现文学/文化领域内的性别宰制/抗争关系,建筑在其与大众媒介、消费文化、民族国家建构等更为复杂多样的关联基础上,很大程度上“性别文学”又成为分析“现代中国”方法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了。当“性别文学”范式在这样内外打通的层面上被使用时,其边界和内涵显然被大大地拓展了,“性别”如何在边缘又不局限于边缘并能对主流世界发出声音,也因此大致找到了可以操作的基本路径。
作为“性别文学”研究范式进入中国文学传统的一次集中尝试,该系列著作在理论、视野、方法、资源等诸多方面做出了积极而有意义的探索,同时也留下了一些可以进一步思考的论题:有关性别文学理论资源的梳理,仍然存在着性别本质主义以及建筑于其上的男/女二元对立思维的痕迹,如何在激活本土性别理论资源的基础上,通过与域外性别研究话语体系的互动与对话,更为自觉地形成具有中国性别文学特点的问题意识、概念范畴与分析工具,这方面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关于性别文学史的研究,除了在“清末民初”这样的历史关键点用力之外,如何进一步抓住其他关键环节特别是对诸如“革命—社会主义”等中国独特的历史实践经验开展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在“通史”的意义上更为系统而完整地展现“性别文学”演进的历史脉络,甚至打开讨论中国文学史/社会史的更大空间,仍然是一个有待于推进的艰难任务;对于“性别文学”研究范式的运用,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立场大于方法的倾向,如何在“性别作为立场”与“性别作为方法”之间找到更有分寸感的平衡,进一步推动“性别文学”研究进入主流研究视野,仍需要继续探索。
正如乔以钢所指出的,“追求原创性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它不仅与知识背景、思维方式、文化底蕴、研究传统、学术环境等因素有关,同时也需要研究者具有智慧、信念、自觉的批判意识和创造的激情”[3](P 407),在这个高度上来展望“性别文学”研究的前景,应该说,仍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