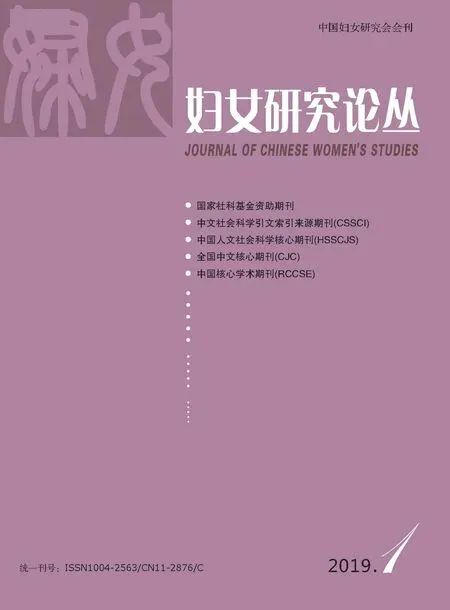社区大学与乡村妇女的生命变革
孙庆忠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 社会学系,北京 100083)
20世纪6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H.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在出版《农民的终结》时,曾令法国学术界震惊。法国是欧洲传统的农业大国,孟德拉斯提出的命题不能不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冲击。然而到了80年代,当他为该书增写20年后的变化时,展现的却是乡村社会惊人的复兴——“我们的社会对于农民和乡村的态度突然地转变了:曾经成为过时的遗迹的农民,在年轻人眼里成了智慧和学问的典范。生活在农村和小城市是3/4法国人的期望”[1](P 273)。而今,中国社会虽尚未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诸多种类的公共服务还难以满足乡村发展的内在需求,但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无不彰显着乡村存在的意义和乡土文化的特殊价值。
一、教育离土:乡土社会的困局与前路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与此同步,中国社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镇常住人口8134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58.52%。在城乡漂移的社会里,农民工总量已升至28652万人。在国民经济收入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7.90%[2]。这些数字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标识,也是乡土社会血缘和地缘关系松动、家族和村落文化衰微的真实写照。农业劳动力离乡的直接后果是土地撂荒、村庄的社会生活缺乏活力,也使“留守”成为中国乡土社会的突出特点,“别样童年”“阡陌独舞”“静寞夕阳”形象地勾勒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的生存状态[3]=[4]=[5]。曾经,那些有形的农具与无形的农业技术,是农民靠土地生活的象征;如今,农民不再倾注心力于农田,而是把城市的繁华视为向往的生活目标。对乡村而言,在农民如潮般向城市流动的同时,电视、手机、网络等信息媒体也在引领着乡村生活的走向。也就是说,城市文化正在影响着农民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重新想象和设计。
这种历史性的变革,改写了乡土中国的发展轨迹。在城市中心主义的驱动下,数以百万计的村落已经消失。在繁华都市的映照下,乡村更像是“废弃的生命”。在这里,累世传承的乡土知识备受冷落,被视为乡村生活灵魂的仪式活动渐行渐远,以养生和送死为核心的礼俗传统被置于漠然无视的境地。农民对家乡的情感爱恨交织,城市对乡村的依赖若即若离,寂寞村落里的农耕智慧无人问津。其结局是使乡村少年失去家乡情感,使乡村青年无心在农村寻求发展,使乡村老人丧失文化自信。“土地的黄昏”因此成为乡村的共相和乡土社会的缩影。
乡村凋敝落寞,教育离土是直接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大规模撤点并校和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导致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农村平均每天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一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6](PP 27-34)。为了追逐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父母陪孩子进城读书已成为乡村普遍的事实。这种教育改革政策在强调教育公平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割断了孩子与乡土的联系。2011-2013年,我们在河北、河南、北京、内蒙古等7个省、市和自治区进行了乡村教育和村落状况调查。期间,我们追问过留守儿童孤单无望的感受,调查过流动儿童的辛酸经历,深为他们忘却家乡的名字而感到悲伤。大部分学校从乡村抽离,仅有的乡村学校也因高墙大院和紧锁的大门而隔断了与乡村的联系,没有成为传播乡村文明的中心。在这样的情景下,乡村学校难以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令人感受最深的是乡村少年的四种失忆状态:第一,寄宿制使孩子与家庭生活游离,父母带给他们的呵护与日常生活的影响甚为缺失。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早期成长不只在于耳提面命式的教育,还在于父母在举手投足间对他们生活习惯的养成。第二,与自然环境相对疏远。他们可能还生活在乡间,但山上的动植物与他们无缘,触目可及的河水因封闭的校园而无法亲近,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他们来说是“无感”的。第三,对于家乡的历史处于无知的状态。我们在走访和问卷调查中发现,孩子们对家乡的历史名人、地方风物几乎都不知晓,细致追问他们的父母,同样一片茫然,他们共同的心念是要逃离乡村。第四,对村落礼俗漠然无视,那些被视为乡村生活灵魂的活动渐已远离了孩子们的生活[7]。这样看来,农村教育已背离了乡村,乡村也因此身处集体失忆的边缘。
乡村学校日益萎缩,农村教育与农村生活严重脱节。这种困境难以化解,因为城市化的教育已深入人心,业已成为乡村父母改变儿女命运的心理动力和行动上的必然选择。面对这样的现实,乡村文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还能传承,那些祖辈相承的生活叙事是否还能发挥延续文化根脉的作用?当作为实体村落的故乡渐行渐远,作为精神的故乡也不复存在之时,是否还能在历史与现实的追问中拥有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当没有了学校的乡村和没有了乡村的学校变成普遍存在的现实,当数以千万计的流动儿童遭遇“城市留不下,乡村回不去”的窘境,文化记忆能否成为链接过往与当下、城市与乡村的精神纽带?
法国人类学家玛丽·鲁埃(Marie Roue)通过对加拿大詹姆斯湾世代聚居的克里印第安人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富说服力的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拿大政府把印第安孩子送进寄宿制学校接受现代教育,目的是使其成为普通的加拿大公民。然而,结果并未如愿,学校教育使年轻人远离了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父母的价值观,却没有使他们获得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手段。他们无法在城市中生活,也失去了祖辈在山林中生存的本领,双重的失败把他们推向了绝望的深渊。正是在这样的困顿之下,某些在狩猎营地继续其传统活动的长辈,将歧途中的年轻人送到克里人祖辈的狩猎营地,引导他们“重归土地”开始新生,让他们在狩猎和捕鱼中学习自己的母语,习得生存的技能,从而重建了他们与生活世界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活出了自信,建立了自身与祖居地之间精神上的联系[8](PP 17-26)。老一辈克里人依靠回归土地的方法,医治了教育的创伤,拯救了迷失的一代。这个案例说明了“回归土地”的特殊意义,也为人们在现代魔性造就的不安中寻求生活的本质,开启了一条情感归属的道路。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作为文化、情感和意义体系的乡村聚落,既是记忆的风景,又是乡愁的栖居之地。在由血缘和地缘构成的乡土社会里,祖先与后辈共同传续的是生生不息的村落民俗文化。这也是我们刻意存留乡土、复育乡村文化的重要依据。然而,乡土的意义不止于此,村落的价值更在于它可以安顿心灵、拯救落魄的灵魂。基于这样的认识,接下来必须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进行乡土重建以应对乡村凋敝的处境?如何让乡村教育回归乡土以传续记忆的根脉?
教育可以拯救乡村,文化是乡村自身携带的力量。如果没有了文化之魂,乡村就会彻底崩解。那么,如何促发乡村的改变?如何让农民重新发现乡村之美,进而激发他们对家乡的归属与认同?最为根本的前提就是乡村文化的复育。我们以社区大学的方式,尝试着探寻乡村教育的出路,努力让终身学习的观念深入村民的内心,让那些没有自信的村民感受到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让他们拥有守望乡土的热情和希望。作为乡土社会存续与发展的路径,河南省辉县的川中社区大学自开办以来,四年间受到了学校周边十几个村庄村民的喜爱,特别是为数众多的年轻妇女,她们向幼儿园的老师学唱歌、学舞蹈、练书法、练表达。更为关键的是,社区大学的课堂从学校延伸到了家庭,很多学员在社区大学读书期间,解决了家庭纠纷,化解了夫妻、婆媳之间的矛盾,使学校在乡村社会的教育功能得到了精彩的诠释。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学校是乡村的希望,其独有的功能无法替代。这种对学校的“信仰”就是人们对于教育和文化的迷恋。这样看来,社区大学并非给农民上几节课那么简单,教育要走入人的心灵,要培育农民热爱生活的能力。这项乡村教育实验意在衍生教育链条,使其成为连接学校、村落的精神纽带,进而成为培育乡村自信的精神场域,这是我们开办乡村社区大学的愿景。事实证明,教育可以为乡村“招魂”,这文化之“魂”正是乡村振兴的根基。
二、社区大学:终身学习的启蒙与成效
2014年5月30日,川中幼儿园举行了以“社区大学伴乡村走进生态文明新时代暨侯兆川第一届乡土文化艺术节”为主题的文艺表演,辉县教育局局长刘向民和我共同为川中社区大学揭牌,河南师范大学刘晓红教授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首批学员展示了她们的绘画作品和烹饪手艺。是日下午,我为社区大学学员讲授了第一堂课“川中社大与乡村生活”。让我震惊且感动的是,有近300人听了这次主题报告。学校的会议室是闷热的,两小时间,除了小孩子的偶尔哭泣,课堂十分安静。对于学校周边的百姓而言,社区大学是一件新鲜事儿;对于我们的幼教团队而言,对从幼儿教师转变成为社区大学义工也心存不解,目标在哪里,前路怎样走,好像都在等着我讲清楚、说明白。也就是在这次课堂上,我明确地提出一种认识:我们这所依托幼儿园的乡村社区大学,尽管目前学员都是家长,农技课程也不可或缺,但它不是家长学校,不是农业技术学校,而是成人终身学习的公民学校。6月6日,《教育时报》以《川中社区大学:平民教育与乡土重建》[9]为题,报道了川中幼教人在山区创办社区大学的新闻。这所服务乡村的成人教育学校,从此正式拉开了序幕。
这种不为多见的乡村教育实验,从学前教育的角度来看,它通过“上游干预”为孩子创置和谐的家庭环境;从成人学习的角度视之,其宗旨是“系统干预”。一方面,作为义工团队的幼儿园教师,在这种特殊的乡土教育中可以开掘自身潜能,重新发现和定位自我存在的价值和乡村教育的功能;另一方面,作为学员的农民,可以在自身发展中重获乡民社会中的团结互助意识。教学实践说明,教师教育意识的觉醒,唤起了他们的职业神圣感和在乡村工作的成就感;农民社群意识的萌生,激发了他们改变自我继而改变周遭的愿望[7]。
社区大学从2014年3月试办到2018年6月,先后共有252位学员加入学习行列,其中绝大部分是留守妇女和老人,男性学员仅有3位。2018年9月新学期开学,增加了34位新学员,与以往不同的是,出现了父母与儿子儿媳一起参加学习的新情况。至此,社区大学已辐射学校周边西沙岗、东沙岗、司东村、司北村、中坪村、西平罗村、南平罗村、柏树湾村、张庄村、莲花村、赵村、郎山村、河北村、北东坡村、疙垱坡村等15个村落。
社区大学的课程是丰富多彩的,四年间开设了“侯兆川自然风物与人文景观”“辉县历史文化”“生活叙事与口语表达”“《乡土文学》选读”“经典童话”“手工艺术创作”“书画欣赏与创作”“民事纠纷与民法”“育儿知识”“卫生常识与养生保健”“烹饪与家乡美食”“瑜伽与形体艺术”“心灵环保与幸福人生”等课程。此外,还有为年轻妇女设计的“肚皮舞”和老年人喜爱的“太极剑与木兰扇”等专项训练课程。这是当地幼儿教师团队的杰作,他们对新知的渴望以及创造生活的能力在这个成人教育的课堂上得到了尽情的发挥。社区大学的课程填充了乡村妇女的生活内容,特别是改变了“80后”和“90后”年轻妈妈的生活节奏。她们有对外出生活的向往,却因孩子小而被迫留守;她们想活出自我,但又无力摆脱带宝宝、做饭和下地干活的单调状态。而对于那些身为祖父母的老人而言,除了为儿孙忙碌,几乎不曾设想过自己也能过有滋有味的生活。社区大学课程的设计不仅拉近了学校与乡民之间的关系,重拾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关切,也让艺术走进了他们乏味的生活。在这美好感受的相互影响中,他们对家庭生活的理解,对自我生命的重新认识与定位,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革。
我把社区大学课堂称为“幸福课”,希望义工团队以此作为提升自我能力的阶梯,更渴望乡民能在学习中激发自己的潜能。因此,幸福先挂在嘴上没关系,慢慢地就会融入心里。每年社区大学在课程之外有三项核心工作:其一是庆典晚会,这是一年学习成果的综合展演,是幼儿园孩子、义工团队和社区大学学员尽显才艺的巅峰时刻;其二是座谈分享,这是总结过往、倾诉情感、传递能量的工作坊;其三是年刊编撰,这是对一年教与学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的记录。
2015年6月2日,为了纪念川中社区大学揭牌一周年,幼教团队筹办了一台盛大的晚会。所有的节目均由幼儿园孩子、幼教义工团队和社区大学学员联袂出演。他们精彩的表演,惊艳全场。远方的客人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因为它们早已跨越了人们对乡村的想象。两个小时的演出转瞬即逝,但谢幕后依依不舍的情绪却在全场蔓延。这个月朗星稀的夜晚是侯兆川的不眠之夜。精彩的表演凝聚着团队每一位成员的付出,社大学员的表现让人看到了教育的力量。社区大学依托幼儿园的在地资源,老师们为社区大学所做的一切没有分文的回报;作为社区大学学员的家长则义务为幼儿园60亩种植园付出过太多的辛苦,他们甚至放下自家待耕的土地来援助幼儿园。所有人的付出都是如此的自然而纯粹,这就是爱的传递,就是生命的改观!6月3日,我与《教育时报》张红梅副总编、安阳师范学院刘军奎教授、新乡学院汪德辉老师一同参加了社区大学一周年庆典之后20位学员到场的座谈会。这次座谈可谓欢笑与哭泣同在、幸福与泪水共存,每一位学员的感受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西沙岗村的LXY有这样一段深情告白:
我一提到社区大学,除了感动还是感动。我们这些人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伸开手每个人都有老茧。我们除了种地就是在家里围着锅台转。可是因为社区大学,能有那么多人关注我们这些山里人,我特别感动!我刚生孩子那时候,家里生活压力大,我就像得了产后抑郁症一样,几乎要崩溃了,对孩子的教育简直太欠缺了。社区大学真的把我改变了,以前心情不好时就到麻将桌前发泄,每天打麻将、种地、做饭,就是没有智慧。然而社区大学却正好弥补了这一欠缺,一个普通人也能和艺术挂钩了。社区大学把家长一个个变好了,家里变好了,教育孩子的态度也跟着转变了。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生活链接啊!
在这次座谈会上,平素讷于言辞的RMX站起来便开始哭泣,好像那一刻只有止不住的泪水才能表达她对社区大学老师的感激。她曾默默地为幼儿园做了许多事情。在老师们为生态园忙碌的时候,她会在早晨五点多带着婆婆和孩子一起在生态园犁地。学员们的这些感动瞬间和那些发自肺腑的感言令我沉醉,只因那里珍藏着我们团队每一位成员的汗水和泪水,那里有着我们共同期待的“改变”!
而今,翻阅3卷本百余万字的《川中社区大学年刊》,总会被那质朴的文字和真挚的情感所打动,感慨幼教团队的学习能力和奉献精神,感慨学员们寻求改变的勇气和力量,更感慨社区大学带给他们精神世界的变化。
2015年入学的WSF说:自从参加了社区大学,我以前枯燥乏味的生活变得有意义而健康。我不再是那个只会一天三顿饭围着锅台转的家庭妇女。川中社区大学教会了我许许多多,比如要学会知足、感恩、欣赏,而不是一味地斤斤计较。在我的心中,川中社区大学是幸福的港湾,是心灵的殿堂。在这里我有了很大的改变:因为心里有苦有烦恼没有地方发泄,使我与身边的亲人发生摩擦,少不了夫妻吵架,教育孩子也没有耐心。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很失败,感觉很自卑,不敢往人群里去。是社区大学的老师们,让我找回自信,让不爱说话、脾气暴躁的我又一次获得了重生。谢谢社大的群体,让我可以在平凡的世界里,不管是否有阳光照耀依然美丽[10](P 166)。
2016年入学的WYL写道:结婚后开始抚育孩子,终日是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可想而知这种画面并不美好,像流水线工作一样,毫无趣味性和成就感。生活中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不顺心的事情,久而久之变得颓废懈怠、心情浮躁烦闷、整宿整宿地睡不着,真是要崩溃了,孩子每每看到我都是战战兢兢的,哪怕是做错一丁点儿都能让我体内的洪荒之力爆发。本事不大,脾气不小,就是我那时的写照。入川中社区大学也有一年了,回想走过的时光是多么的美好,和蔼可亲的川中幼儿园的老师,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笑容的红梅姐,是他们让我猛然觉醒,生活其实很简单,就是给孩子微笑,给自己微笑,给身边人温暖。在社区大学,大家不分年龄、不分层次、不分彼此,不管谁有困惑,只要说出来大家都会想办法解决。这样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里少不了我们强有力的师资团队的功劳,感恩、感谢有这样一群教师和知心姐妹,还有我们的孙教授,就在这平凡的课堂上扭转了我自己的状态,我不再总是郁郁寡欢、患得患失,而是以积极向上的心态去面对一切,每一节课慢慢地清扫我内心的阴霾,在这里我的心情异常的平静,也只有在平静的时候才能权衡自己的过失缺点[11](P 155)。
2015年庆典晚会之后,我提议编辑《川中社区大学年刊》,希望以此记录川中幼儿教育链接成人教育的足迹。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本年刊竟然激发了老师们的写作欲望和学员们动笔书写的热情。三年来,教师团队在编辑校对中提高了驾驭文字的能力,学员们在看到自己的作品时激动得彻夜难眠。无论是那些滚烫的文字,还是那些书画作品,都呈现了他们改变生活的进程,都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与美同在”的幸福,并感恩有年刊这一平台,“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村妇有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
东沙岗村的JHY这样写道:“让我悄悄告诉你,我们川中社区大学出年刊了,上面有我的两篇文章和衍纸画,给你发的有图片,一定要看哟!”这几天除了工作就是做这些,想装低调但又控制不住那份喜悦,心里别提有多爽了。这种心情岂能用一般词语来形容,对于一个自卑渺小的村妇来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堪比久旱逢甘露。这是社区大学老师为我们创造的奇迹。此时,零点的钟声已经敲响,一个女人在外地奔波真的很不容易,一天班下来特累,回来的路上就剩下孤单一人,有些害怕,有些忧伤,鼻子酸酸的想哭。但回到住所,看到床头平放的《川中社区大学年刊》,就迫不及待地翻开第199页,它是我的骄傲。年刊上还有孙教授和老师们的文章,他们炙热的文字温暖着我,幽默的话语依然响在耳畔——“你听,幸福在敲门”,对呀,我就是幸福的人儿。这里还有我社区大学的同学,一个个的名字清晰可见。她们在说不同的话,却又表达同一个意思——只要我们够努力,明天的我们就会闪亮。有她们的陪伴,我很踏实,不再害怕,不再孤单
2018年6月2日,在社区大学四周年的座谈会上,我们分享了每一位学员的学习感受。尽管每一次所听的内容都可预期,但这些乡村妇女丰富的精神世界,试图寻求改变的内在冲动,却总能令在场的每一位泪眼模糊。“80后”妈妈CCM说:“我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嫁到西沙岗村11年,和左邻右舍没有打过交道。我养两个孩子,每天就是搂着孩子抱着手机。但是社区大学改变了我,让我一下子意识到我的生活可以变得如此明朗,我不仅可以和本村的姑娘们联系,还可以和外村的人相识……”“90后”妈妈JHX说:“我过的是无悲无喜、无欲无求的生活,别人一年有365天,而我一天有365遍,我在单调重复着,我的生活里没有自我,我不知道我自己活着的价值在哪里。我养了两个孩子,可是我初中都没有毕业,我不知道怎么教育他们,我就像拿锄头在雕琢一块璞玉一样,这就是我的生活……”在她们的倾诉中,有对生活的无奈,更有对自己年轻生命的梦想,这是社区大学带给她们的精神启蒙。
在社区大学,除了这些年轻的妇女,还有十几位老年学员。他们自从踏入学堂,就爱上了幼儿园里的这道“夕阳晚景”。65岁的QYY说:“通过上社区大学,让我的一些旧思想、旧观念得到改变,学员们之间也非常友爱,大家都结伴一起去上课,感觉自己真成了大学生。在社大我非常快乐!”与她同龄的WHY,虽不识字,却不愿落下一节课。我教她写字,她说:“我记性不好,从东屋到西屋就忘了去干什么了。我赶过牛,劈过柴,就是没拿过笔。”当我握住她拿笔的手写下川中社区大学×××时,她脸上划过的那丝微笑,可能是这辈子都不曾体验过的快乐感受的表达。
2016年入学的LBH说:自从我上了社区大学,我特别开心,我的快乐就是想着社区大学的点点滴滴。社区大学幸福课,让我的梦想成真,我感到人生更加美好,家庭和睦太平了。我的内心感觉自己有两个家,一个是日常生活的家,另一个幸福的家就是社区大学。老师们用优美的语言,教我们唱歌、做手工、画画,还教我们练太极。自从我上了社区大学,我感觉找到了一条开心的路,那就是社大幸福课[13](P 153)。
东沙岗村的NSM写道:在我漫长的人生中,有多少烦心事压在我身上,就像许多小小的子弹落到了我的身上,不知从哪里飞来,击中我的心灵,于是给我留下了许多弹伤。自从我走进社区大学的校门,这些数不尽的伤口开始愈合了。在课堂上,我的烦恼都跑到九霄云外去了,觉得自己的烦心事都没有了,心里感到甜甜的,好美呀
社区大学的课堂让这些乡村老人感受到了一份关怀、一丝温暖,他们也因此觉得自己拥有了一种不曾预期的生活。尤为可贵的是,他们又把在这里获得的力量传递给家庭,传递给自己所在的村落。社区大学学员中婆婆与儿媳共同学习、年长者人数逐年增多的事实就是有力的证明。
社区大学课程以及师者的才艺、耐心与宽容,为乡村妇女打开了心锁,让她们在平淡的生活中品尝着艺术的滋味。幼教团队从课程设计入手,将乡村的自然资源转变成为课程资源:河滩里的卵石成为学员们作画描摹的艺术品;玉米皮在手工制作中华丽转身为小拖鞋、小靠垫和令人不忍触摸的盛开的花朵;废弃的竹帘变成了风筝的龙骨;丢落的纸箱幻化为墙壁上悠然的舞者。几年来,幼儿园的走廊里增添了好多社区大学学员的作品——线描画、油画棒画、扣贴花、布贴画、吹画、伞绘,可谓异彩纷呈。每次看到YHY画的竹子《高风亮节》、JXL画的牡丹《花开富贵》,我们都不敢相信这样的作品出自乡村妇女之手。更令我们惊叹的是,经过朗诵课程训练,学员不仅可以用标准的普通话交流,而且可以登台诵读岳飞的《满江红》。这些乡村妇女的变化,让我们看到生命的变革其实并不遥远。
从2014年社大揭牌仪式到2018年四周年庆典,每一次晚会都吸引着十里八村的乡亲们,他们有的站在三轮车上,有的扛着孩子站在摩托车的小座上,那份专注的深情与台上遥相呼应。还有一些老人,一直蹲在舞台的近旁,等着看儿媳妇的表演。社区大学为乡村带来了生机,在音乐声响的背后,是乡民对文化的渴望和对教育的尊重。这一年一次的侯兆川不眠之夜,让我们目睹了幼教团队和社大学员由内及外的精神变革。
三、乡村复育:幼儿教师的躬行与力耕
促发乡村妇女精神变革最不容忽视的力量,是以女性为主体的川中幼教团队的付出。作为社区大学的义工,他们秉持教育家陈鹤琴的教育理念,将“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鲜活地呈现在幼儿教育和成人教育之中。为了让学员每一堂课都有所获,他们利用下班休息时间,或集体操演或个人苦练。超越预期的结果是,他们个人的才能获得了极大拓展,在利他的奉献中获得了莫大的幸福。在我看来,这20余位幼教老师是乡村教育和文化传承的“种子”,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力量。
回首走过的路,川中幼教团队开辟了一项非常有益于乡村的工作,在这之中他们自己的心灵世界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13年6月我们在河南山区调研时发现,住校的教师普遍觉得晚上的时间不知道怎么打发。他们的生活好像只有两种基本状态:年纪大的,等待着退休;年纪轻的,等待着回城。在此期间,与川中幼儿教师的交流激发了我为乡村教育做事的冲动,似乎看到了教育重新启动乡村的希望。我曾在田间地头分享过他们苦中作乐的欢悦,也曾与他们在舞蹈室座谈。我当时想的是,这些年轻教师如果觉得生活在乡村是有意义、有价值的,那么他们的工作状态就会改变,乡村教育无力的状态就会缓解。他们自己描述的生活是这样的——“我们像生活在笼子里一样,终日在幼儿园这个楼里转,在孩子们的嘈杂声背后,虽然能体会到一份乡村旷野的宁静,但是也决定了我们生活的半径。我们在乡村的生活可能一天也不出方圆一里地,即便走出去也不过几里地。”在我看来,他们的生活空间实在有限,但社区大学的开启却使他们在方寸之间链接了中国乡村的大事,生活世界不再是自己的小群体,还有侯兆川的老百姓。
川中幼儿园是辉县侯兆川教育文化中心的一部分。在这个乡村教育园区里有幼儿园、有小学、有初中,教学环境、硬件设施相当完备。幼教团队在已故园长张青娥的带领下,在校园里的建筑空地上开辟出60亩生态园,希望以此让孩子们亲近土地,更多地享受优质的乡村教育。提及生态园,老师们喜忧参半,在几乎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他们开荒耕种所付出的时间和体力是可想而知的。当老师还是当农民,他们有时候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们不知道有多少次想放弃,但是每年到播种和收获的时候,看着孩子们观察葫芦和红薯出苗,看着他们能够听闻大自然的声响,20位姑娘和4位小伙子就好像把劳累统统忘了一样。我曾经在那里和老师们一起掰玉米,也和孩子们一起拔花生,真切体会到学校一定要以培养完整的人性和人格为目标,也一定要发挥传承乡土礼俗和传播乡村文明的功能。
从2014年第一次在川中授课到四年半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景象是社区大学让年轻的妈妈们与艺术为伴,让麻将桌前的留守妇女拥有了服务家庭的尽职生活,让留守老人体验了老有所乐的美好时光。幼教团队在让孩子们享受优质乡村教育的同时,也让学校成为凝聚周边村落的中心。从2013年与川中幼教人的初相识,到现在走进义工团队的工作与生活,我不知道是我温暖了他们,还是他们温暖了我。我一直觉得,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年轻人,才让我始终能看到乡村的希望。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家在城里,每周回家一次,他们的孩子也在川中读书。他们忍受了乡村生活的寂寞,一直在寻找活着的意义。我理解他们的困惑与迷茫,理解他们无力改变生活时的沮丧,这可能正是我当时走进这所学校,也希望尽自己一个大学老师之力做一件事的最初念头吧。
川中社区大学最初试办的时候,幼教团队的老师们都很忧虑。他们说:“我们都是中师生,没有念过大学,怎么教大学我们不知道呀!”“我们平时面对的是孩子,现在却要给成年人上课,真是太紧张了。”“我们幼儿园办社区大学真的可以吗?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农民会来上课吗?幼儿园的工作会不会受到影响啊?”这样的疑惑在我给社区大学学员的第一次课中得到了部分解答,并在当晚与幼教团队的座谈之后达成了共识。老师们纷纷表达了听课后的心情,讲述了他们对社区大学的理解。
GWY:“讲座给了我勇往直前的动力,我知道我们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HH:“讲座改变了我们的思想,让我们觉得做这件事情特别值得。这是件非常有意义也快乐的事情。我觉得以前所做的任何事情,再苦再累都值得,我释然了。通过这两天的交流,我的心情一下子放下了,对于社区大学、生态园,我没有半点犹豫、彷徨和挣扎!”
CJF:“原来前方的路在哪、目标在哪,我不是很清楚,但现在轮廓清晰,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一定主动且尽力干好!”
社区大学自开办以来,除了日常的教学实践之外,幼教团队的工作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社区大学庆典和年刊的编辑。截至目前,连同揭牌仪式,社区大学已经举办了5次庆典。姑娘们在台上简直就是仙女下凡,可是等回到她们的宿舍,累得全都立马倒下。半夜12点的时候,她们又都兴奋地爬起来,为自己的成功庆贺。我从心里往外敬佩团队的姑娘们和小伙子们,他们靠自己的力量一次次超越能力的极限。这台看似简单的演出,却是他们创造生活的过程展现,没有什么力量比这更鼓舞年轻人成长了。对于社区大学的学员和周边的村民而言,社区大学的庆典是乡村生活里令人惊艳的一幕,老师们到新乡去租服装,与学员们一起精心排练,目的是要展演一个学年的学习成果,要满足学校周边十几个村老百姓一年一度的期盼。华美的表演展示了他们在乡村的行动,但是我知道每一个节目背后的故事和辛苦。每年观看庆典,看到姑娘们和小伙子们以饱满的姿态将节目呈现在面前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身处何地,不敢相信他们带着那些年轻妈妈和年老长者,经过了怎样的努力,才排出了如此令人惊艳的节目。那一刻我总是感叹不已,觉得他们的创造力超乎想象。每一个幼儿园老师都有才艺,真可谓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吹拉弹唱、书画舞蹈,真的了不起。排节目对他们来说曾经是难事,但是做来做去就轻松自如了。每年编一卷30余万字的《川中社区大学年刊》,也曾让他们不知所措,但三年走下来,他们已经在平时积累、集中学习、团队合作中,不断地看到自身能量的长进。在他们的观念中,幼儿教师可以为乡村做的事情多了,要读的书多了。我曾和他们说:“在我的眼里,你们就像在山区布道的修女和牧师,在以自己的方式传递着温暖和爱。”《教育时报》记者张红梅一直追踪报道川中幼儿园,她称川中幼教团队是“喝西北风的精神贵族”。这些年轻人每月的工资只有一两千元。他们为社区大学上课都是义务的,我也从未有过赚钱的想法。我们的教育实验也因此遭受着不绝于耳的质疑声音,第一年很多人认为可笑,第二年有人认为是天方夜谭,第三年还有人认为不可持续,但是当第四年走过来的时候,这样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弱了,我们的幼儿教师团队也在这个创造性工作的过程中获得了自信。他们因为社区大学心胸变得一天天开阔,他们也在行动中看到了一个自己未曾想象的世界,做了自己都觉得不可能的事情。而今,我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五步培养法”(撰写观察日志—记录教学过程—积累教学心得—提炼教育叙事—形成教育理念)正在一步一步推进,这些奉献乡村的教师在实践中赋予生活以意义,向游走于学前教育与成人教育之间的全能型教育专家迈进。
川中教育实验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2018年6月13日,我在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学术年会上做了题为“乡村社区大学与悄悄的生命变革”的主题报告,其后数月间,一系列的追问令我无力解答。这之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其一,无名无利的奉献,这里的幼教老师是如何做到的?其二,这样的运作机制,社区大学能否持续?一位学前教育的专家说:“我不知道怎样解读川中教育现象,发自本心,我不舍得让幼儿教师承担那么沉重的社会问题与政府职责,他们是以撕裂自己家庭的方式奉献救助孤寡的心灵。甚至,我觉得歌颂他们是有风险的,让本就羸弱的幼教群体增加更多的社会期待。”对此,我回应说:“如果社区大学带给年轻团队的只是沉重的负担,那我可谓是罪孽深重!事实上,在助人的过程中,我看到的是他们通往心灵解放之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点上,他们的生活,或者说是‘活法’,多了一种可能性。无论站在哪一角度想,尽微薄之力,改善我们的生存状态,都是一种积极应对问题症结的策略。……对川中幼教团队我的心情很复杂,他们若是懈怠,我会极度失落,事实上是他们加油干,舍去了太多的自我,我又莫名地悲伤。从这种心情来说,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在伙伴们四年半间创造的生活中,我看到更多的是希望,是乡村教师自我救赎的希望,是乡土中国的希望。这样的教育实验能走多远我不知道,就让我对他们、对生活始终抱有积极的想象吧!”当我把我和这位专家的对话分享给幼教团队后,他们做出了如下的应答。
GWY:不愿意把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当作是奉献,这个词太大,实在是不敢当,我更想说所谓的付出它不是消耗,更不是牺牲,而是一种能量的转化,当你在付出的时候其实你得到了比付出要多得多的东西,从另一层面上讲你一定是在汲取能量,而川中社区大学带给我们乡村教师的首先就是个人的成长和能力的提高……我们的人生会因为这些所谓的付出而变得丰富、丰满,并具有意义和价值。年轻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经历是难能可贵的,除了珍惜就是要努力做好。
FYP:总在想一个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了什么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用什么证明我们还在活着。其实想来想去这就和我们一直在苦苦追寻的幸福一样,并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是为了得到什么,也并不是所有的付出都能得到什么,做自己应该做的、自己能做的事情,从中获得的是满满的能量与无以言表的幸福!
LSM:我们只是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现在已成为一种习惯,甚至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这种习惯使我们的生命有了不一样的诠释,我想这更应该是我们互相感谢的地方。
ZL:温暖是相互的,幸福是相互的,与其说我们引领学员改变观念,体味生活的快乐,过一种幸福有尊严的生活,不如说我们自身在创办社大的过程中更深刻地感悟到了生活的真谛,体味到了教育的价值,活出了生命中的精彩!
川中教育实验,让我目睹了个人、家庭和村落因为教育的回归而带来的一线生机。这所以幼儿园为依托、以幼教团队为义工主体的乡村学堂,已经使286位学员从中受益,这也意味着有大致相同数目的家庭受到了社区大学的影响。幼教团队以他们的身体力行让乡村妇女有了精彩活过一次的感觉,也让乡土社会里日渐冷漠的人情在他们学习的过程中温暖起来。当他们一次又一次讲述社区大学带给他们心灵冲击的时候,当看到幼教团队在能量提升中展现其创造力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四年是多么值得,因为这里发生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变化,而是一个生命发生变化以后带给整个乡土社会变革的讯息[15](PP 127-136)。
四、行动研究:自立与立人的身体实践
川中幼教团队和乡村妇女的故事,被教育界的同仁广泛关注。作为一名从事人类学教学与研究的大学教师,这里的田野叙事以及与之相伴的复杂心情,也会被学生经常追问。“老师,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从南美洲回法国的时候,一路想着肖邦的E大调练习曲《离别》,你从乡村回来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想点什么?”我说:“我想的是一首歌,一首我们(20世纪)90年代初听过的歌,叫《野百合也有春天》。”为什么会想到这首歌?因为这些生活在农村的妇女、这些工作在乡村的女教师,我目睹了她们生命的灿然绽放,就像山沟沟里的野百合,每逢春天都会静静地开放,她们的生命需要得到尊重。因此回到城里,当我看到自己的生活、看到周边人生活的时候,一种莫名的悲伤就会涌上心头,就会在不经意间念起那些生活在乡村的“野百合”。当我把社区大学的故事细细讲过之后,学生们的感动无以言表。在他们的心中,“这所乡村社区大学不仅是学校,更是以艺术为阶梯的心灵宗教。年轻的幼儿老师以自己的方式寻找到了生命的价值,同时也为别人建构了生命的意义”。就在我们交流的那一刻,我的眼前再度模糊,因为他们对幼教团队所做工作的心领神会,也读懂了我在乡村进行教育实验的初心与远念。
当然,除了这份情感思绪,更有对乡村未来、对自我生命的理性思考。社区大学的创办一方面是为了提升农民热爱生活的能力,协助他们成为自觉的乡村建设者;另一方面是培育乡村教师成为自觉的行动研究者,在寂寞的乡村重新发现自我存在的意义,重新认识活着的价值。简言之,促发改变是乡村教育实验所追逐的目标。我们以幼儿园的教育资源为依托,期待通过拓展学校的教育空间与功能,实现个人、群体与社会的变革。事实证明,川中教育实验实现了三个层面的变革:我个人的生命变革是源头,继而启发年轻教师在奉献中践行教育的理念,其直接后果就是社区大学学员观念的转变。这种接续性的变革带来的必然是乡土社会的改变。
作为行动者,我的变革是让我在感动中更换了自己的心灵密码。之所以说在感动中,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需要一种情感纽带。每当我面对这些年轻的乡村教师,看到他们为寻求改变所做出的努力,都会心存感动和敬意,都会愿意为他们去做尽我所能的事情。这种付出会进入一种良性的循环之中,总能让我们在人性的光辉中看到现实生活的理想样态,于是就笃信生活的美好和变革的力量。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一个文弱书生,不仅可以给别人带去温暖,也可以成为乡村建设的助力者和引领者。川中的教育实验让我对钱理群的话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他说:“作为一个践行者也许我们是孤独的,但不要希望去影响太多的人,就从改变我们自己开始,继而改变周遭、改变社会,实现悄悄的生命变革。”[16]尽管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大学老师,但却可以把自己的学术研究转换成身体实践,为乡村妇女和乡村教师传递美和智慧。在这看似奉献实则获取的自我成长中,感触最深的是,生命的质感有了一次次宝贵的回归。
对于幼教团队而言,首要突破是去除倦怠心理的魔咒,在单调循复的工作中寻求改变,成为具有反观能力的行动研究者。可以肯定的是,社会需要变革,每个人的生命需要变革。如果行动者自身的生命不能从根本上有所改变,就期望去改变别人、改变社会,那是不可能的。然而,自身观念的改变和生命的变革需要有一种信念。这之中最为核心的则是关乎一辈子的人生修养问题。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高悬的理想,尤其是年轻人。怎么让这份激情对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精神品质的提升发生影响,这是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然而,“众多身处复杂人类与社会现场的工作者,在追寻知识与探索方法的过程中,陷入僵窄的胡同,久而久之,实践工作者失去了对生命细微变化辨识的能力,对场域脉络间交织牵动的力量亦视而不见”[17]=(P 4)。这种失能状态正是乡村教师这一群体普遍遭遇的事实。那么,如何让“改变”深入人心,进而成为一种自我拯救的力量?答案只有一个:做一个理想主义者,赋予生活以意义。这是足以应对各种处境的生存之道。只有这样,乏味枯燥的日子才能过得有滋有味,才能如余光中所说即便在寒冷的冬日里也能闻到玫瑰的芳香。这是一种生存的智慧,是一种爱生活、爱生命的能力。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心理素质,所有的工作都难以走入内心,更不会持久。就此而言,人生就是一场修炼,让我们始终以纯净和美好的心地滋养心灵,而后用一个生命影响另一个生命,用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在自己精神生活蜕变的同时,实现社会生活的变革。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乡村建设中,卢作孚在他的乡村建设思想中提出,“训练人是一切问题的中心问题”,而训练人最核心的目的,就是“人人都能自立,人人都能立人”[18](PP 17-31)。自立才能立人,这也是我们今天乡村教育实验的思想基础。把人立住了,教育事业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才有可能性。因此,行动者不可忘记,立人必须先自立。如果想做助人的工作,而自身不够强大,底气不够,那就仅能停留在幻想。这样看来,社区大学的深层价值和使命是要完成由“私”向“公”的转变,要实现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这正是我们终日奔波所积极推动的改变。如果这样的观念没有植根于心,我们所做的工作可能更多的是“发展的幻象”,也便无法理解行动研究的基本诉求——自立、立人与促发改变的真义。
在与川中幼儿园、社区大学共同走过的日子里,我的心里的确有了太多的牵挂。我不知道这样的乡村教育能走多远,但这种带有实验性质的个案,总会点燃我们通过教育重建乡土的希望。这里是全国唯一一所依托幼儿园创办的社区大学,是多种机缘聚合的结果。川中幼儿园的特色不仅为乡村提供了优质的学前教育,更重要的是它把学校周边的村落与成人的终身学习连接在了一起。在参与式的教学活动中,每一位家长或者潜在的学员都能够以一种自我存在的方式,去拓展学习的能力,去思考琐碎的家庭生活和自己的未来。与学员成长并行的是幼教团队精神素养和内在品质的提升。曾经闲散的乡村生活变得紧张而忙碌,昔日只负责学前教育的老师如今已成为社区大学的义工,在这样的奉献中,他们对自己的人生也有了新的设计与定位。由此可见,乡村教育实验客观上揭示了乡村教育的应然状态——乡村教师的职业生命需要持续性的滋养,乡民社会更需要学校教育来满足其终身学习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川中社区大学不仅是教师发展和教育境界提升的阶梯,更是为乡村传递温暖、促进生命变革的重要场域。作为行动者和研究者,川中的教育实验也让我更加坚定——必须将学术研究的判断转换成学者自身的身体实践。这是让学术研究更有力量的依据,也是我们服务乡村、积极倡导乡村变革的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