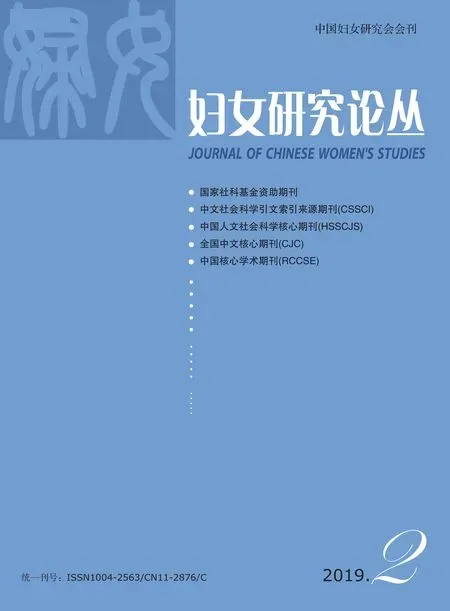重访马克思主义经典*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相关理论误读的反思
杜珉璐
(哈尔滨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Marxist Feminism)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是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三足鼎立的重要思想流派[1](P 92)。一般而言,学术界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粗略分为三个相对各具特质的理论阶段: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致力于在当代西方社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由于各种局限,其在不同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误读。分析这些误读,可以为我们在新时期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启示和参考,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妇女问题理论的中国化提供借鉴。
一、家务与资本批判: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联姻与误读
马克思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是对“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即“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2](P 158)的唯物主义分析与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逐步认识到,要使人类生命得以延续,必须不断地从事两类性质不同的生产活动,即自身生命的生产和他人生命的生产,于是在男女之间便“自然地”发生了性别化的劳动分工。这种被称为“自然分工论”的理论在传至20世纪60年代时因其视域似乎仅限于生物学意义而遭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质疑。
20世纪60年代登上女权运动舞台并被统称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主要有艾丽·泽拉塔斯基(Eli Zaretsky)、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玛格丽特·本斯顿(Margaret Berston)、盖尔·卢宾(Gayle Rubin)等。他们虽然质疑这种带有生物学色彩的“自然分工论”,但是却毫无例外地接受了隐含于其间的分析框架:生产性劳动(自身生命的生产等)与非生产性劳动(他人生命的生产等)、家庭与社会、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相区隔,并进一步将其作为分析性别压迫的理论抓手。比如,艾丽·泽拉塔斯基曾言:“随着工业的兴盛,资本主义使社会化的物质生产(即商品的生产范畴)和主要由家庭妇女完成的私人劳动‘相分离’。”[3](P 108)不难看出,其思维逻辑并未脱出上述二元论窠臼。
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最大的理论亮点在于,尽管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发展,由市场主导的有偿生产性劳动与由伦理维持的无偿非生产性劳动愈发分离,但妇女并没有因此逃脱被资本主义无情剥削的悲惨命运。因为,无论分离与否,主要由妇女承担的家务劳动事实上一直在发挥着无偿再生产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功能,客观上服务于资本家追逐最大剩余价值的剥削活动。正如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所指出的:“女性工人从事家务劳动‘解放’了男性工人,使其为资本家工作更长的时间,并且因此增加了剩余价值的比率。”[4](P 103)对此,盖尔·卢宾总结道:“正是通过劳动力的再生产,妇女才被连接到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剩余价值关系中。”[5](P 27)可见,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通过打通由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剩余价值再生产之间的内在逻辑通道,试图通过批判资本逻辑揭示妇女遭受性别压迫的资本主义经济根源,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将性别压迫等同于阶级压迫,或者说,将性别压迫融入了阶级压迫。于是,便产生了某种理论误读。
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腰斩”了马克思的“自然分工论”思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诚然认可“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但是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分工并不足以构成妇女受压迫的真正根源,因为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分工始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2](P 162),而与性别无涉。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自然分工论”应包含两重维度:自然维度与社会历史维度。在马克思看来,这两种维度是须臾不可分的,因为两种性质不同的“生命的生产”一旦开始“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2](P 160)。显然,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只关注了带有生物学意义的自然维度,而忽视了更为根本的社会历史维度。其二,更为致命的误读在于,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把全部批判的锋芒都聚焦于经济领域,以经济领域的阶级压迫取代或者涵盖家庭生活中的男权压迫,完全没有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谈及的:“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servitus),而且包含着农奴制”,使其“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6](P 67)。因此,必然在客观上钝化了其性别理论批判的锋芒。
二、父权制与性别异化: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联姻与误读
也许正是由于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在分析性别压迫结构时过分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压迫作用而忽视父权制的做法,不能有效指导当时女权运动的火热实践,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出现了主要以批判资本主义父权制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新形态,通常称之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这一术语一般认为是由成立于1969年的芝加哥妇女解放联盟最早使用的[7](P 138)。被公认为该流派的主要学者有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海迪·哈特曼(Heidi Hartmann)、阿莉森·贾格尔(Alison Jaggar)、艾瑞斯·杨(Irish Young)等。他们虽然批评早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某些做法,却与后者达成了如下共识:“妇女受压迫并不是个人蓄意行动的结果,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物。”[8](P 141)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开始了富有特色的性别压迫研究。不过遗憾的是,由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主持的这段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的“联姻”一开始便是“不幸的”。在其看来,马克思主义不仅存在着“性别盲区”,而且成了服务于男性统治的“另一种意识形态”,它“通过对性别的隐藏”,使其“理论迷惑了社会现实并且使得女性继续受压迫合法化了”[4](P 116),所以以性别不平等为特征的父权制成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批驳的首要论题,但在具体论证上略有分歧,主要集中于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社会在造成妇女受压迫的性别结构中所占的关系。比如,海迪·哈特曼认为应当是二元压迫结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经济力量二者相对独立地共同起作用,使妇女遭受双重压迫,主张应两线作战,同时反对二者;艾里斯·杨则反对这种二元制理论,主张“把资本主义家长制(父权制——引者注)理解为一种制度”[9](P 77)才能更透彻地揭示妇女受压迫的现实结构。在这一问题上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知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阿莉森·贾格尔在资本主义父权制条件下对妇女所作的性别异化分析。
阿莉森·贾格尔在其名著《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中比较全面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的“联姻”并对性别异化做了精彩分析。
首先,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贾格尔高度评价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认为其“是对女性问题的经典阐释”[4](P 74),不过这丝毫不妨碍其又站在女权主义的立场质疑有关这部著作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不能因为资本主义条件下女性遭受的性别压迫现象有了新的历史特点,就将恩格斯的有关理论人为地截为两段:前资本主义性别压迫理论和资本主义性别压迫理论,尽管二者有很大区别——并明确提出其富有特色的具体方法论原则,即在性别研究中,应将“女性从属地位的起源”问题与“这种从属地位如何持续至今”[4](P 92)问题剥离开来。
其次,在轻松摆脱妇女背负千年的父权压迫重负之后,贾格尔聚焦资本主义父权制之于妇女性别异化的研究。在贾格尔看来,马克思早年提出的“劳动异化”概念并不能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受压迫女性实现全覆盖,存在着某种先验的理论局限,因为如果“家庭主妇没有参与资本主义的生产”,且异化又是“资本主义关系的特征和结构所特有的,所以家庭主妇就不能被描述为异化的存在”[4](PP 317-318),而这样的家庭主妇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少见。基于此,贾格尔在借鉴马克思“异化劳动”论证路径的基础上分析了异化的“特殊的、独特的性别形式”。这种新形式的性别异化是指“女性在社会中被异化成了三种形象:性伴侣、母亲和妻子”,甚至“女性气质本身就是一种异化”。贾格尔着重分析了前三种形象,这里以“性伴侣”异化为例进行阐述。在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下,“大多数女性都将自己置于通过性来取悦男人的处境”之中,这必然使女性:(一)同性行为本身相异化,使得“很多女性在性行为中都无法获得高潮”;(二)同女性自身相异化,使得“女人们不但将自己的思想同身体割裂……而且她们与自己的思维也产生了分裂”;(三)同其他女性相异化,使得女性成了“为博得男人的性关注而相互竞争的许多个体”[4](PP 453-457)。毋庸讳言,贾格尔的分析入木三分,其间马克思“异化劳动”的分析架构也显而易见。
再次,贾格尔在深刻分析性别异化后指出,“当代社会女性的异化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具体的、历史的产物”[4](PP 470-471),而要更深刻阐明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父权制,“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必须采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4](P 183)。不过,在此便有误读存在。其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否真如一些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所言的那般在性别压迫与妇女解放问题上保持了意味深长的“沉默”,在对苦难的人类史展开几乎全景式扫描时遗漏了“妇女园地”?实事求是地讲,一些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如此言说并非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妇女问题没有丝毫的理性认知(比如朱丽叶·米切尔就曾在其文章中援引过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摘录傅立叶的那段名言——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9](P 11)),而是质疑于其理论分析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当然,在如此言说之时并非是从实证科学与合理发展角度立论的)。对此,可以提出以下两方面驳证。一方面,不妨进行一番比较,恩格斯在系统研究了母权制向父权制演变、家庭的历史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受压迫的真实现状之后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6](P 85)作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代表人物的贾格尔则指出:“女性的彻底解放需要一种社会生产的全新组织模式和女性柔弱特质的最终消灭。”[4](P 471)两相比较,其间确有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非完全不可对话、通约,因为二者均寄希望于经济领域的某种变革,所以性别盲区言过其实。另一方面,同为美国女权主义者,拉·杜娜耶夫斯卡娅曾著文评价道:“马克思无论在组织关系中还是在私人关系中都认为妇女既是革命的力量,又是革命的原因。”[10](P 205)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遗漏“妇女园地”的说法恐难成立。
其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一方面在哲学方法论上承认要彻底阐明资本主义父权制舍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而不能,另一方面却在具体理论实践分析中采取了机械的形而上学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南辕北辙。以贾格尔为例,其性别异化的逻辑起点是将女性漫长的受压迫史一刀两断,径直取资本主义父权制的一段深入挖掘,尽管有所理论创获,但毕竟在性别压迫分析中缺失了历史视野的深邃投射。其误读在于仅仅透过资本主义父权制这一单一化视角展开分析,竟置并非可有可无的女性受压迫的漫长前史于不顾,这就完全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而言,“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11](P 47),深刻洞察资本主义父权制对女性造成的性别异化之后还应反观历史,以此烛照最为幽暗的历史死角,才能在历史与现实复杂的立体化视域中洞穿妇女千百年来受压迫的历史死结,从而向真正消除性别压迫之路奋进。
三、自戕与后学困境: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联姻与误读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后工业化特征日益明显,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便是各种后学新潮层出不穷,这股时代涌动的大潮也以裹挟一切的气魄时刻提醒着人们置身解构的时代,无物常存。在这种无法抗拒的时代风潮下,许多女权主义者纷纷断言“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蜜月已经结束了”[12](P 364);一些不愿彻底割断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理论脐带的女权主义者在充分吸收以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各种后学之后也在理论特征上大踏步地迈入了“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自戕时代。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传统流派一样,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一个内部极其复杂多元的思想群落。根据英国学者朱利斯·汤申德(Jules Townshend)的研究,甚至在这些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之间还有“强”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与“弱”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之分[12](P 362),其标准无非是理论家所持立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距离之远近。不过,总体而言,这种差距相当微弱。换言之,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联姻”较之以前更显稀薄,所以下面统而论之。
西蒙·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的名著《第二性》一直被誉为女权主义运动的“圣经”,几乎改变了整个女权主义理论大厦的形态,自此,女权主义者在性与性别之间苦心孤诣,无往不前。这种影响之于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结果便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频遭质疑,他们纷纷指责马克思主义以一种自然主义的眼光观照女性。比如,凯瑟琳·麦金侬(Catharine MacKinnon)指出:“马克思对妇女是从自然而不是从社会来定义的。”[13](P 3)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由于受到阿尔都塞、福柯等思想家的影响,使其在这一问题上的论证逻辑较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大异其趣,后学气息十足。比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性别不是一个人类本性或生物学特征的问题,而是既定文化规范所强加的一种表现。”[14](P 68)这种既定的文化规范所含内容复杂而广泛,不同的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侧重点也彼此互异。比如,米歇尔·巴雷特(Michel Barret)侧重于性别意识形态如何经由教育等途径“归化”、建构女性的主体身份;南希·哈索克(Nancy Hartsock)侧重于主流话语、知识生产、文本语境等对女性性别意识的影响,提出创建女性立场理论的设想。加之用语晦涩难懂,因而学院化倾向不断加强,也因此日益淡化着其大众化的女权政治运动初衷,在客观上走向了一种自戕。
此外,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在另一路径上不断自我消解。由于拥抱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理论,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开始质疑启蒙时代以来理性之光所照耀着的诸如“主体”“女性”“女权”等一切话语体系,认为抽象提纯之后的概念术语抹杀了其外延所及的一切个体的差异,应当反对这种本质化的做法,因为它构成了男权社会最为稳固的话语堤坝,而话语即权力[15]。所以,女权主义运动本身也横遭质疑。这种强调差异化的批判路径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很容易得到非欧美裔女权主义者的赞成与响应。差异性不仅时间性历史化地存在着,更以空间性的理化质态实存着:“归化”女性气质的意识形态等话语体系在不同的国家、民族、阶层之间千差万别,这些地区对“主体”“女性”“压迫”等的理解与西方差异极大,因而真正实现女性的自由解放必须拒斥“女性沙文主义”和批判“欧洲、北美女权主义中心地位”[16](P 2)。不过,在批判女权沙文主义的过程中,女权运动很容易为民族主义、反霸权主义等非女权主义的异质化思想所裹挟而失去自主的独立形态,势必消融于其他主义与运动而不自知,这是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需要面对的后学困境:女权运动由反对男权压迫始,经反对男性/女性主体而走向反对女性自身,批判者成了被批判者,自身消解着妇女解放理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四、结语:重访马克思主义经典,超越女权主义的理论局限
德里达指出,对于我们的时代而言,“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17](P 15)马克思主义是寻求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体系,而女权主义是追求女性自由发展的思想潮流。一个反抗阶级压迫,一个反抗性别压迫,两者之间本来就存在天然的亲缘关系。然而长期以来,西方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甚至走向自我消解的困境。
新时代需要我们立足现实,重访马克思主义经典,发展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走出因为误读而垒造的理论困境。在此过程中,一方面要批判性地借鉴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探索,另一方面要结合新时代中国妇女发展与男女平等的重点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