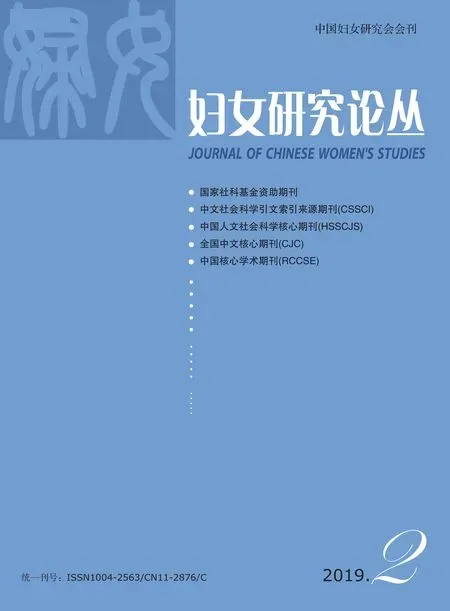何震的女子非军备主义论及其论述语境*
刘人鹏
(台湾清华大学 中国文学系,台湾 新竹 30013)
一、前言
何震(1886-1920?)[1](PP 491-539)是20世纪初中国一位重要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女子解放运动理论家[2](PP 22-35)。1907年6月,何震在东京与周怒涛、陆恢权等共同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并与刘师培(1884-1919)等共同创刊《天义报》,该刊“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3](P 580)。意即,《天义》的男女平等或女界革命、女子解放,并不满足于从文化中将性别范畴独立出来以追求平权为目标,而是从特定的历史时刻和人类社会整体性着眼,面对当时革命界与知识界支配性的政治视野局限,将性别革命的视野放在整体环境各种向度以及无政府主义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迈向世界平等幸福的愿景中,提出女界革命与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同时并进的路线。何震曾说,“亚洲妇女”的解放,绝不在于“步欧美女子之后尘”去获得“伪自由、伪平等”[3](P 136)。
何震的女性主义并非中国女性主义的权舆或代表。实际情况是,当时中国知识女性中对于妇女议题已有不同的运动路线,而《天义》走的是非主流甚至逆主流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道路。举例来说,1907年,在东京的《中国新女界杂志》与《天义》就分别走了“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路线。柳亚子(1887-1958)曾说:“抑记者旷观女界之机关,以东京为盛,若《天义》,则创无政府主义;若《中国新女界杂志》,则创国家主义。二者宗旨颇不尽合,而《天义》尤翩然高举不可一世。”[4](P 90)柳亚子在此固然高度评价了无政府主义的《天义》,实则当时知识妇女中“国家主义”的路线仍是较具支配性的,《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发行数量也远高于《天义》[5](PP 679-680)。何震是少数对于国家主义的妇女运动路线不以为然且提出异议者。面对强权与帝国主义,柳亚子曾作《花木兰传》以召唤尚武精神[注]花木兰等在晚清渐成女性典范,参见夏晓虹:《晚清女性典范的多元景观:从中外女杰到女报传记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6](PP 34-36),女界亦多有应和,何震则批判了女子参与强兵主义的主张,反对以花木兰、梁红玉自我期许的女子参战爱国路线。今日阅读《天义》何震的反军备主义及相关立论,还需要看见她如何与当时其他妇女运动路线争论。例如,早在《天义》第二期的《女子复仇论》长文中,何震即批评当时中国女子中“从男子之后,以拾种族革命之唾余”[3](P 49)者。对何震来说,种族革命不能止于“革满洲之命代以汉人”,因为汉人之君对女界来说仍是专制;她同时也批评,若是女子附和男子“攘夷”,不过是“汉人助满洲人排外”[3](P 50)罢了。她的女子革命主张不仅针对男子的压迫,而且包括了对于妇女运动本身支配性论述的批判,而在反军备主义论中,她批判了当时知识妇女对于“强兵”论的附和。
事实上,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日甚至欧美妇女运动的主要方向是以西方现代性为基础及目标的“平权”路线,《天义》的女子“革命”则是当时极少数质疑西方现代性且受政治压迫的路线。该路线及立场的差异在《天义》表达最明显的是署名“志达”(当代学者疑其即为何震)[注]由于有两篇文章“志达“与”震述“在正文及目录页的署名互见,夏晓虹和宋少鹏皆疑”志达“即何震。参见宋少鹏:《何殷震的“女界革命”——无政府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第1期。[7](P 73)的《女子教育问题》一文。该文批评当时亚东、欧美方兴未艾的女子教育,只求形式解放,却未见“思想上之解放”,指出亚东各国女校的伦理教育“在日本者,固以养成贤妻良母为目的,而饰以忠君爱国之观念;在中国者,则大抵采集前人格言,以训女子”[3](P 193)。该文章也批评了当时女界较受重视的“家政学”及军国主义教育,认为历史学科可以启发思想,应是重要的教育内容,但“关于国家主义者,宜在屏遗之列”[3](P 196);同时提到女子习医固深合博爱之旨,但欧美、日本各国女子习医多是作为看护妇服务于军旅:“女子肄习此科者,多给役军旅之中,以为看护妇,此则深可嫉视者也。”[3](P 196)当时政治、陆军、警察各学科均专属男子,但《天义》主张女子要的平等不在于“争习此科”,而在于“非军备之运动”[3](P 196)。该文在按语中直指当时学界舆论主流是“家庭教育乃一切教育之基。欲兴家庭教育,必自兴女学始”,然《天义》所提出的则是自言想必令主流舆论“恐怖”的革命主张:“家庭革命为一切革命之基。欲兴家庭革命,必自兴女学始。”[3](P 197)
何震在《天义》发表的诸多文章中,1907年11月刊出的《女子非军备主义论》[注]夏晓虹曾推论此文非何震所作。学界也颇有些说法对于何震的书写能力有所保留,或疑其文为刘师培代笔。本文则认为,在未有明确证据证实该文非何震所作之前,倾向于相信何震本人的书写论述能力。从当时各种活动记录看,何震是有见解的积极参与者,如与中日革命志士和日人幸德秋水见面或书面讨论不同意见、社会主义讲习会中何震本人发表演说见于记录、亚洲和亲会的发起何震亦在其中亲身参与。《天义》创刊后,幸德秋水在《大阪新闻》刊登的赞词说:“中国妇女何震等,近日发刊《天义报》,其主张男女同权,且鼓吹政治革命及社会革命之处,与单纯地从事排斥满清的革命党青年的选择颇不相同,中国妇女之前途绝不可轻视也。”(幸德秋水:《7月5日于东大大久保村》,《大阪新闻》明治40年7月15日第4号,转引自[日]富田升著,张哲译:《社会主义讲习会与亚洲和亲会──明治末期日中知识界人士的交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33-234页)幸德秋水又说:“《天义报》首册读毕,拍案呼快。就中《女子宣布书》,议论雄大,如名将行兵,旗鼓堂堂不可当。若《帝王与娼妓》,骂得痛绝,如利刃刺骨,何等刺心文字也!敬服之至。男女同权者,人生之精理,而方今之急务。贵娘今开阐此真理,以冀实行此急务,以着女子先鞭,感激无已。即为社会之女子思之,固不容不谢此劳也。”幸德秋水在这封信中,对《女子宣布书》中“初婚之女,必嫁初婚之男;再婚之妇,必嫁再婚之夫”表示不同意,因自己在病中,希望何震来访,并邀当时同样关切妇女议题的堺利彦一起讨论“女权问题”。 《天义》在信后附了何震的按语:“震得书后,即往访幸德君。时,堺君亦在座。”(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47页)《天义》亦附了何震对幸德秋水意见的回应。这些材料虽然无法证明署名何震的文章如何写成,但至少显示了何震并非只是挂名的人物。 《天义》此期刘师培的《亚洲现势论》在前,何震的《女子非军备主义论》在后,看似何呼应刘,但《天义》中也有何文在前而刘在后呼应者,如第2期何震《女子复仇论》的男女不平等的历史由来,在第4期后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中“男女不平等之原因”其说相同,我们似无理由预先排除何震启发刘师培的可能,虽然在19世纪甄克思(E.Jenks)、恩格斯等人的著作中都有类似说法。此外,《天义》中有些文章单署名何震,有些文章则是何震、申叔共同署名,显然有分别。也有些文章是申叔所作,但文后附何震按语,如《人类均力说》(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3页)。[8](P 313)一文别具特色,在当时中、日各种妇女或女权论述中,甚至在当时世界女权主义者中,其批判论点与论证都是别开生面且具开创意义的[注]并非所有女子皆反战,反战者为少数。日本1901年成立的“爱国妇人会”,“以后方军事支持为目的的国家主义妇女团体,是日本第一个体制内的官方妇女团体”。“草创时期的爱国妇人会的主要活动之一是在各地举办演讲会,呼吁妇女为战争服务。日俄战争期间,爱国妇人会会员们在全日本开展了送迎出发或归国部队,劳军、慰问军人家属和伤病士兵以及战死者遗族的活动。”(蒋立峰、汤重南:《日本军国主义论》(上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69页)后见之明看,反战或反军备主义是极其困难的运动,大部分妇女是以不同的方式响应战争。因现代军备主义透过人力物力脑力的全面动员、爱国主义的连动以及国家将“反战”视为“叛乱”而施以严厉法律惩处,几乎所有人都自愿或被迫卷入战争机器中,或“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参与了战争体制”(西川子:《总体战与女性:向战争的倾斜与翼赞“妇女”们》,载秋山洋子、加纳实纪代编:《战争与性别:日本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44页,引文在第1页)。顾德琳亦曾提及何震论述的独特性:“尤其是她那激进的无政府女性主义,在日本甚至都无人提出。”(顾德琳:《知易行难: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妇女性别论述及其落实限制》,载《共和时代的中国妇女》,台北:左岸文化,2007年,第63页)。[9](P 63)。事实上,“反军备主义”是《天义》的核心议题之一。 《天义》第1期即刊登了译自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1871-1911)《平民主义》的《呜呼劳动者》:“劳动者铸造大炮,何已转为大炮射杀乎?”[3](P 383)以及《〈击火石〉节译》:“作炮者,劳动之人也;使用炮者,劳动之人也;而死于炮者,亦劳动之人。”[3](P 383)[注]《天义》也有反战的图画诗。第八、九、十卷合刊“图画”栏有“从军苦”图,注文:“从军苦,从军苦。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页)。这是以“劳动者”为立场的反战主张,不同于诉诸普遍性的人类和平反战,也不同于当时日本的基督教和平反战主义,而是呼应幸德秋水等人在甲午战后渐渐提出的反帝国主义论,特别是日俄战争即将爆发之际提出的强烈非战论,同时也是当时国际无产阶级非军国主义运动的一环。 《天义报》曾刊载“社会主义讲习会”记录:“第三次讲习会上应邀主讲的,记得是大杉荣,他讲的是关于非军备主义的问题,主要讲了法国爱尔威的非军国主义运动,并联系到宗教方面的非军备主义运动等。”[3](P 342)[10](PP 340-360)就《天义》本身而言,采取的是“反宗教”的立场,因此并没有具体述介宗教方面的非军备主义运动,援为论述资源的主要是幸德秋水等的无政府共产主义非战论以及欧洲以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为主调的反军备主义运动,其所留意的不仅是思想内容,更是具体的国际活动。例如记载英国社会党领袖哈叠(James Keir Hardie,1856-1915)访日本社会党,《天义》受邀前往,会中述及“社会主义不以国界为限”[3](P 307)。《万国无政府党大会记略》记载,1907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无政府大会,其中言及“无政府主义政策中之非军备主义”[3](P 311);1907年德国斯图加特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中“提议非军备问题。其讨议大旨,在于凡持社会主义者,均当反对海陆军扩张预算案”[3](P 320)。《万国革命记》亦记载德国无政府党人一女五男,因鼓吹反对军国主义“并劝工民,遇战争之际,勿击外人而击本国之资本家。又劝军人与工民,协力罢战”[3](P 338)而受审遭监禁。
何震的《女子非军备主义论》置诸上述语境中,其独树一帜之处在于:以战斗的精神,坚持主张“女子”的运动路线不应该是加入国家战争、去追求通过战争而获得特权的男、富、强等尊位平权,而是以同样战斗的精神,看见大多数女子的地位如同平民,彻底与劳动平民站在同一阵线,揭露当时帝国主义军备主义的阶级与性别剥削性质,鲜明提出女子反对军备主义的主张。何震在文章最后呼吁的对象因此不是国族的妇女,而是“世界妇女”实行非军备主义运动:“吾深愿世界妇女共明此义,实行非军备运动,则济民救世之功,伟然与日月争光矣。”[3](P 188)
基于女子与战争的关系,就如同“平民”与战争的关系,何震指出,战争“无论胜败,影响所及,均为妇女之不利”[3](P 185)。其论述理路大略如下:非军备主义是有益于“人民”的,现今世界多数妇女居于“平民”的地位,而军备对女子有害而无利。野蛮时代固然是行军时奸淫掳杀“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到了现代文明时代,号称有现代的军队纪律,但以刚发生不久的甲午之战、日俄之战为例,战争中“妇女,婴儿莫不罹惨死及逃亡之祸”;再以不久前的时事为例,八国联军之役妇女多死、台湾割让后妇女成为日人玩物、被殖民的越南妇女为法人虐待等等,皆见证了现代文明国家扩张军备同样造成妇女受辱。进一步论,战败之国妇女固是遭殃,国家尚武强兵而进入战胜之国行列是否于妇女有益?何震以日本为例进行了分析,日本在中日、日俄战争皆为战胜国,然日本全国壮丁多战死于外,战后从国家获得的恤抚费微薄,妻丧其夫,女丧其父,无数妇女不得不靠卖淫维持生计。因此,只要用兵,不论胜败,都对妇女不利。此外,在历史男尊女卑的性别制度下,可参战的只有男子,妇女的战争经验表现为经历生离之苦、久别之苦以及战死闻耗之苦;即使自己的国家战胜而奏凯生还,但战争此胜则彼败,战败国伤亡必多,“死者既为他国之平民,则困苦者亦为他国平民之家室”[3](P 187)。何震以世界主义的精神指出,我们“以救济同胞”为目的,并非只着眼于自己国家的虚荣,“岂忍寡他国人民之妻,孤他国人民之子女,以逞国家虚伪之光荣哉”[3](P 187)?因此唯有反对战争本身,主张“战争一事,与妇女均有直接之不利,乃女子所首当反对者也”[3](P 187)。
这篇文章论点其实涉及当时国际反军国主义运动中的反爱国主义,亚洲反帝、反殖语境下女子与现代国家战争相关之阶级斗争问题,以及平民与女子“幸福生活”的生命要求,甚至在理论上提出战争为男女不平等之根源。文中引证当时具体的现代战争与殖民情境以及战争中社会民生付出的代价,背景与当时日本社会主义刊物中所呈现的日本甲午、日俄战后的平民社会现实景况相呼应,同时述及中国当时各省军备日增,以及世界女子生计困难沦为工女之现象与军备的关系,在理论视野上则与《天义》对于反帝反殖而提出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共产主义现代性相呼应。这是东亚历史中以女子立场参与无产阶级国际反战论述/运动的先声。以下就该文要义一一阐释。
二、国际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反战运动的思想资源
在《女子非军备主义论》一文开题后,何震即将“反军备主义”放在国际反军备主义运动视野中,例举法国、瑞士、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地皆“盛行此说”,并指出其具体运动策略包括刊行反战小册子、演说、发布宣言以及“提出战时总同盟罢工”、拒绝兵役、破坏军舰、军人脱伍等发生于荷兰、美洲、日本等地的“世界非军备主义之运动”[3](P 184)。何震在文中提到了四位著名的反战运动者:法国的爱尔威(Gustave Hervé,1871-1944)、德国的李伯彻巫瑞第(Karl Liebknecht,1871-1919,即李卜克内西)、荷兰的尼酷翁比酷依斯(Ferdinand Domela Nieuwenhuis,1846-1919,即尼万希尔斯)、挪威的利氏(Einar Li,1880-1955,即爱尔纳·李),以下对此略加说明。
挪威的利氏为《社会民主党人》编辑,曾因拒绝入伍而受刑事起诉[11](P 149)。尼万希尔斯主张战时总罢工,并曾领导成立国际反军国主义者协会。爱尔威与尼万希尔斯的无政府主义反军国主义,在理论及策略上都为李卜克内西所批判[注][德]卡尔·李卜克内西著,易廷镇译:《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特别就国际青年工人运动加以考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171-180页。又按:爱尔威以罢工和起义回应战争,这个主张亦为列宁所严厉批判(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63-65页),本文不处理议题本身的争论,仅就《天义》引用爱尔威之处加以阐释。,但在此何震并没有特别选择无政府主义的反战论。何震关注的是这些反战运动者所遭致的国家法律惩处。例如法国无政府主义反战志士爱尔威“与同志二十五人,受禁锢及罚金”,这是指1905年爱尔威于年度征兵时,因联署张贴反战宣言海报而以叛国罪名被捕[12](P II)。德、法、意、奥、丹麦等地革命者也曾因“非祖国主义”或“非军备主义”或“鼓吹总同盟罢工”而遭禁锢、罚金或放逐等事[3](P 330),《天义》在《万国革命运动记》中亦有简要记载。
爱尔威的论点在《天义》刘师培的《亚洲现势论》一文中多有引用。爱尔威被捕后在陪审团前曾发表一篇题为《反爱国主义》的演说,指出:法国大革命后,应许了普遍的集会、言论、出版等自由,然实际上因国家具有布尔乔亚阶级性质,普罗阶级立场的反战、反爱国主义言论与出版向受禁锢,从未享有革命所应许的言论、集会与出版等自由[12](P 15)。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卡尔·李卜克内西与爱尔威等人在《天义》其他篇章亦屡见提及,应是在日本透过社会主义讲习会及日本社会主义刊物研习所得。李卜克内西是德国工人阶级领袖,是国际工人运动最重要的活动家之一,1907年2月出版《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特别就国际青年工人运动加以考察》一书,对于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国主义论述实践逻辑以及各国反军国主义的理论与现实状况,都有概要性的阐述。书中指出,军备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关乎国族、阶级与文化自我保存之本能的表现;就其历史而言,不仅是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社会与经济上的紧张关系史(外部战争),而且是个别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史(内部战争)。李卜克内西也将反军备主义的理论基础推到《共产主义宣言》,他认为,《共产主义宣言》虽然并未直接处理军国主义问题,但确实指出了资本主义拓展所带来的国际性殖民与扩张政策及其所引发的国与国间的矛盾冲突。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显然与无产阶级争自由的斗争是相互对立的,书中曾引1894年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第12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对军国主义之决议结论:
在和平时期,常备军充当警察部队与射击机器。他们用流血方式镇压矿工和工厂工人为自己权利进行的斗争。无产阶级士兵们在愚蠢的狂怒中冲击自己的罢工的兄弟[11](P 124)。
亦即,对外战争时,无产的士兵须为布尔乔亚阶级的国家效忠,为之射杀敌国的无产阶级兄弟;在和平时期,亦因须效忠有产阶级的国家而为之镇压国内无产工人兄弟的罢工。
《天义》对于军国主义战争基本上即持以上看法。刘师培谓:“军国主义无非用多数人民之性命,以保卫有权力之人,复戕害境外无数之同胞,以增少数有权力者之光宠。”[3](P 178)敌国的人民,其实是“同胞”,然而国家发动对外战争却使得“平民自残同类”[3](P 178)。爱尔威曾主张“士兵们不要用武器对付无产阶级,如果接到这样的命令,就宁可将枪口转向指挥官们而不对准自己的阶级同志”[3](P 129),并呼吁士兵拒绝执行镇压罢工工人的命令。此反战的理论视野在于:战争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是“按照有产者的命令进行的无产者和无产者的互相残杀”,其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军队是为阻止工人阶级获得解放而服务的[11](P 138)。劳动者为战争遭到流血牺牲与财产损失,事后得到的却是“为数可怜的残废人员年金,退伍军人补助金,沿街卖唱和到处受人欺侮”[11](P 29)。
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力扩张、殖民战争不断的19世纪晚期,像这样通过教育或组织劳工,唤起无产阶级劳工意识,以劳工立场反对国家建立常备军、反对军国主义的运动,在欧洲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及之间方兴未艾。平民或劳工反军备主义也就意味着反剥削,当时期待的目标也包括避免世界大战的灾难以及终止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而何震的反军备论文正积极呼应了欧洲国际反军备主义运动。更重要的是,在亚洲当时情境下,将被侵略的弱种、被剥削的平民与被压迫的女子联结战线,认为非军备主义对于弱种、平民、女子皆有利,可共同致力于世界和平安乐:“非军备主义行,则弱种泯强种之侵凌,平民脱国家之压制,为女子者亦可脱男子之羁绊,以博自由之幸福。此实世界和平安乐之先声也。”[3](P 188)
三、“富国强兵”论批判与“反爱国主义”
立足于亚洲,何震反军备主义除了呼应欧洲的无产阶级反战观点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亚洲现实中,以过往中国历史与近日世界时事的材料所再现的具体经验为论证,回应当时亚洲国家政策及精英中支配性的“富国强兵”论。
“富国强兵”来自日本明治时期面对欧美现代文明而提出的回应之道,是一种国家政策立场以及国家精英对西力入侵的反应。而《天义》所跟随的社会主义批判“富国强兵”立场则是认清了一个事实:当帝国殖民的现代性成为世界文明进步唯一标准时,对落后者及平民造成了没有底限的压迫剥削,解决之道不是跟随强者追求富强,而是取消对于富强的崇拜,同时也是取消对于压迫的复制。
《女子反军备主义论》首先将反军备主义的主张放在对于“强兵主义”的批判视野中,开宗明义指出,女子不应因欧美、日本国势强大就提倡强兵主义、以军国民或花木兰等自我期许[注]夏晓虹的研究可见,1904年《女子世界》以来,表彰中国女性典范者,便强调花木兰、梁夫人、秦良玉等武勇楷模,丁初我《女子世界颂词》已将“养成‘军人之体格’、铸造‘军人世界’,为‘女子世界’诞生的首要指标”(《女子世界》第1期,第7页,参见夏晓虹:《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7页)。,反而应该提倡反军备主义,因为这些黩武穷兵的现代文明强国的“人民”其实是困苦的[注]《天义》甚至认为,欧美、日本等文明国的平民之苦,“有远甚中国者”(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8页)。这个认识,一方面来自日本社会主义或其他新兴刊物,如《女学世界》、《光》、田添铁二的《经济进化论》、《平民新闻》等,另一方面也来自东京实地见闻:“欧美之况,固闻而后知者也。欲穷文明国之实际,则曷向日本东京本所区,一观日本贫民之况乎?”见《论新政为病民之根》按语与相关篇章引用,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9页。,真正的解决之道应是女子反军备主义:
今中国愚昧之流,不察欧美、日本人民之困苦,徒震于彼国国势之强,由是倡强兵主义,以尚武之说相提倡,人人以军国民自诩。此实至荒谬之说也。而一二为女子者,亦侈然以木兰、梁红玉自期许。此尤无意识之尤。吾今特故反其词,论明女子非军备主义[3](P 184)。
事实上,《天义》中有多篇文章批评现代帝国主义殖民战争是“兵”与“财”的结合,如刘师培《废兵废财论》《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亚洲现势论》等文,因而坚持革命不能崇拜强权而走富国强兵之路。其中何震与刘师培合著的《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述义最详。该文批评“今日主张革命者,多醉心欧美、日本之文明……崇拜强权之心遂以日盛”[3](P 127),并指陈当时中国欲效法欧美、日本政治者主要有四端:“一曰以法治国,二曰建立议院,三曰振兴实业,四曰广设陆军。”[3](P 127)何震与刘师培认为,历史现实显示四者皆非“为人民计”,而是“保卫政府、官吏、资本家之安宁耳”[3](P 128),直接批判了现代文明帝国主义战争的野蛮性。 《天义》也通过“反军备主义”议题来表达其不以国族国家为界的世界主义路线,与当时国际社会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运动相呼应。
对于“战争”,何震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现代战争和军队的特殊性质进行了批判分析。她指出,现代国家军队的性质已不同于过去。过去人民革命可以靠“筑塞而守”的暴动,如今一方面现代都市“街衢广阔,据守甚艰”[3](P 184),另一方面,现代文明国家军队与政府日益整顿,更加文明体制化地保护“政府、资本家”[3](P 184),人民已无法如过去般以暴动抵抗,只能以消极为积极,“解散军队”[3](P 184)。对于战争的物质条件分析,也许可以用恩格斯的观点来注解:
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要求促使意志行为实现的非常现实的前提,特别是工具。 ……暴力还是由经济情况来决定,经济情况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但是还不仅如此。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13](P 206)。
何震从人类的“身命”与平民的自由立论:军人亦平民,却为“政府、资本家所利用”[3](P 184),如同奴隶,“日与国内外平民为敌而趋之于死”[3](P 184),这是人类令人悲悯的不幸,因此,通过非军备主义运动产生自觉,可以“助平民攫取自由,而因以保人类之身命者也”[3](P 184)。世界多数女子都居于“平民”的地位,也都是“人类”之一,何震问:女子难道甘罹祸难?抑或是盼望获取自由之幸福?既知妇女深恶奴隶之境遇,深恶非命之惨死,那么,“非军备主义当为女子所欢迎”[3](P 184)。
这里蕴含了一个关于“平民”与国家关系的假设,即《天义》主要的(反)国家观:国家军队与政府、资本家的利益一致,而与平民的利益矛盾。何震在《天义》创刊号《公论三则:帝王与娼妓,大盗与政府,道德与权力》一文即已使用较激烈的语言表达了国家与平民对立的观点,将政府与资本家视为一体,而将政府及资本家之合体与平民的关系比拟为“盗”与“被盗”的关系,并批判了国家法律与道德作为权力之压制的黑暗面[3](P 48)。事实上,这也是当时革命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共享的理论。例如,恩格斯将“国家”的构成视为与经济利益冲突的阶级对立有关,且在历史上产生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为有产阶级防御无产者阶级的组织[14](P 168);“工人没有祖国”“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等语,亦见于《共产党宣言》[15](P 291,P 274);爱尔威的《反爱国主义》演讲亦指出所有国家皆由少数的统治阶级与多数被统治的平民组成[12](PP 11-12)。何震对于国家与平民的对立关系正是基于此一理论框架。
虽然批判欧美、日本现代文明,但《天义》强调要与欧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相联合,目标在于使“世界之中,其有强权所加、人治所束者,均可同时颠覆,以图人类之自由”[3](P 180)。强调现代文明国家之“民党”本身已对其自身的侵略性提出批判。此即刘师培在《亚洲现势论》中所说:“近日欧美、日本民党之中,其抱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所持之点有二:一曰世界主义,一曰非军备主义,均反对本国政府持侵略主义者也。”[3](P 177)亦即欧美、日本中的社会主义者认为,祖国若通过战争“损他人以益己”[3](P 178),则不惜反对。
四、世界主义的“亚洲”视线
何震文中批评现代文明战争,具体事例是“中日之战、日俄之战、辽东之地”的炮火所造成的妇女、婴儿惨死及逃亡之祸,以及中日战后台湾因被“掠取”而使得“台湾女子,多为日人之玩物”[3](P 185)。当然,何震并未基于国族主义只论中国女子,她援引《越南亡国史》[注]《越南亡国史》载:“今日罚银未清,明日罚银又至,其最可哭不能哭,可笑不能笑者,为逼劫民家良妇女入娼之一事。法人于各都会城厢处,皆设娼楼,征妓女税钱……给予黄纸一片,有法文印记,这纸随身,方得卖艺……法人律,每夜令巡警兵侦探娼楼,有实无黄纸牌,私引男子行嫖者,押赴刑曹重罚其女,即没入其本银,若得娼楼税日增,巡警兵有重赏。巡警兵乘风生事,寻祸邀功,但见人家有零丁寡妇,流落孤娘,无父母兄弟可依,无要势力可援,即黑夜闯入其家(法律禁夜入人家,惟巡警兵得入)诬以窃窝嫖男,彼孤穷惧祸,怯见法官,恐喝雷霆,无所控诉,便唏忍泪,乞领黄纸了事,明明白白的良人,从此向贱妓场中生活,娼楼税日重,巡警声势愈大起来。嗟呼!黄纸一贴肤,终身落地狱,零丁弱妇,何辜于天,真是古今绝奇惨事,此政体,欧洲文明国,固当为之也。呵呵呵!”(潘佩珠:《越南亡国史》,1905年,载《梁启超全集》(第3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561-1575页,引文在1571页。)将受到法国殖民的越南女子与台湾女子的受辱相提并论,认为“劫夺人国,由于军备。是则台湾、越南妇女之受辱,均受强国扩张军备之影响者也”[3](P 185)。这里论述脉络涉及日本明治开始的中日、日俄现代战争随之而来的社会转变以及日本社会主义批判论述的兴起,而将台湾、越南妇女相提并论,则与《天义》提议的亚洲如何回应帝国主义战争与殖民有关。
日本早期社会主义的非战论及其所针对的日本现代战争脉络,始于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开战即以“文明”为名义,福泽谕吉曾指“甲午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我辈之目的惟有战胜而已,只要透过战胜,伸张吾国之国家主权,让吾人同胞从此享有对世界挺起胸膛的愉快感,无论内部有多少不义不平之事,均再也无暇顾及”[16](P 155)。此战日本一举获胜,作为战胜国,得到了赔偿金以及殖民地,也顺利进入了亚洲追赶欧美文明的先进国,并展开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行动。“在‘中国和朝鲜是野蛮国家、日本是文明国家’这样的优越感高涨的同时,即使是贫穷的佃农的儿子,战死之后全村也会举行盛大的葬礼,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参军、战死是一件很光荣的事。”[17](P 65)与此同时,日本内部因扩张军备而增税造成的社会问题、因现代工商业发展造成的城乡工农问题等,在战争之后也逐渐浮现。“甲午战争一落幕,社会运动的舞台揭幕。曰企业热潮、曰工业建设、曰受薪阶级激增,然而,曰扩张军备、曰扩增租税、曰物价腾贵、曰底层劳工穷困。劳动问题喧腾一时,识者无不关注社会问题。”[16](P 156)19世纪末,日本陆续有了现代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如“社会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协会”“社会民主党”等[注]“1898年10月,片山潜和安部、村井、高木、幸德、河上等十几个人共同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见肖立辉、芦钰雯著:《片山潜》,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年,第37页。。幸德秋水在1901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中,即已对爱国主义、军国主义提出批判[18](PP 142-185)。数年后的日俄战争规模远大于甲午战争。战事耗费及卷入的军人也数倍于前。俄国战败导致1905年的俄国革命,日本胜利则形塑了国家认同以及跻身全球列强的信心。即使耗损无数,但战争却得到“大众”支持,1903年日本舆论几乎都支持对俄战争,并幻想可以从战争得到好处。此时出现了少数却坚强的反战声音,呼应当时国际社会主义反战运动[18](P 96)。日俄战争前,幸德秋水与堺利彦退出了支持开战的《万朝报》,而创办《平民新闻》,批评爱国主义、军国主义,并提出反军备主义。《平民新闻》有反战言论专栏,几乎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俄战争作为活动重心。痛斥日俄战争乃“帝国主义的、为资产阶级和地主利益而进行的、损害人民利益的战争,而人民只是战争的牺牲品”[19](407)。《平民新闻》对于日本劳动人民因战争而陷于贫困的状况亦多所报导,经常刊登日本无产阶级罢工斗争的消息。幸德秋水曾说:
社会主义不但不承认今日国家的权力,而且坚决反对军备和战争。军备和战争是今日“国家”用来保卫资本主义制度的“铜墙铁壁”,多数人类为此遭受了重大的牺牲。今日世界列强为了军备竟然负了二百七十亿美元的国债,仅仅为偿付利息一项,就需要三百万人以上经常的劳动!而且,不得不经常使几十万壮丁服兵役,学习杀人技术,尝受着无谓的辛苦。据说在德国,多数壮丁被征入伍,以致从事耕种的,只有头发斑白的老人和妇女。唉,这是多么悲惨呀!况且战争一旦爆发,就要耗费多少亿国币,牺牲千万人命,国家社会的疮痍永远不得平复,只“赢得”少数军人的功名和投机商人的利益而已。人类的灾难祸害,难道还有比这更甚的吗?如果世界各国没有地主和资本家阶级,没有贸易市场的竞争,物产丰富,分配公平,人人各自安居乐业,还要为谁扩充军备,为谁发动战争呢?这些悲惨的灾难祸害将为之一扫而空,天下一家的理想也将得以实现。社会主义一方面是民主主义,同时又意味着伟大的世界和平主义[20](P 39)。
反对战争的论点,包含了对于战争具有阶级斗争性质,战争付出的代价以及谁付出代价,反战的目标在于社会主义、世界主义的理想等判断,《天义》的反军备主义论与之大致同调。然而,从被侵略的“弱种”出发,《天义》曾特别辨明“排强权”不同于“排外”[3](P 327),呼吁“亚洲弱种”与强国之民党相联,同时达到“排斥强权”与“共产、无政府”的目的[3](P 181)。
事实上,何震说欧美、日本“人民困苦”的论点,也呼应了欧美、日本社会主义者对其自身社会的观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当帝国主义向外为扩张殖民而耀武扬威时,掩盖的是国内失业、贫富不均等社会矛盾,这些现象通常见于欧洲、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批判视线。例如,爱尔威的演说中曾描述法国普罗大众的生活,指法国“现今这个国家,不过就是畸形地社会不公,畸形地人剥削人”[12](P 12)。
何震女子反战的立场有很大一部分是以民生为考虑的。在《女子非军备主义论》一文中,她提及当时世界军备扩张造成国防预算大增,以致租税日增,物价踊贵,人民生计困难对女子的影响则是世界女子沦为工女阶级[3](P 187)。中国“工女”渐增的现象从19世纪末以来已见于报刊如《女学报》[21](P 184),但是对何震来说,“沦为工女”意不在于劳动女子工作低贱,“女子之劳动,本女子应责之天职”[3](P 120),她在意的是“不可以劳动之事责之一部之贫女”这种“役使于人”之劳动[3](P 120),亦即如“志达”在《女子教育问题》一文所言,若没有经济革命,则女子走出家庭去劳动,也只不过是由服务于家庭中之男子,转而为服务于资产阶级[3](P 195)。何震提及当时英国海陆军费大增,中国也因用兵而税额日增,横征暴敛之政接踵行于世界。军人增加造成的影响是日常“生利”的人民成为“分利”的军人,且日常生产为军需生产所取代,生产额供不应求造成物值踊贵,兵备造成人民的贫穷,女子因家计困难而成为工女或仆婢娼妓,“给事富民,博取衣食”[3](P 188)。一般富国强兵论着眼点通常在于船坚炮利的军备造成的国家进入现代行列的展望,但何震采取了民生批判的眼光,强调的是船坚炮利背后付出的平民生计代价以及大部分平民女子在现代化过程中因军备而造成的生存状况改变。
该文在《天义》中呼应着刘师培同一期刊登的《亚洲现势论》。刘师培等因其无政府主义立场在过去的研究中负面评价较多,其理论也就常被忽略。事实上刘师培在《天义》中的《亚洲现势论》对于亚洲弱种联结的理论与现实基础提出了较为全面的看法,对于以下诸问题都提出了讨论:亚洲被殖民的“弱种”目前面临处境以及弱种相联以排斥强权的基础;亚洲中的日本,既是亚洲弱种,又逞帝国主义强权,如何排斥又如何联结?刘师培的主张是,欧美及日本强权中也有抱持社会主义者,均反对其本国政府之强权帝国主义侵略主义,应为联结的对象;他同时论及帝国主义的扩张仰赖军备,军备主义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关系密切,最后指出,弱种联合以排斥强权帝国主义的侵略,目标不是富国强兵变成强国,而是以大同社会主义为愿景的未来。 1907年4月,章太炎、何震、刘师培、张继等“为研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22](P 232),访问了幸德秋水先生。这期间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曾发表如下意见:“社会党运动是国际运动,无人种与国境区别。我认为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与德国和俄国的关系也很相似。因此,中国革命主义与日本社会运动者携手合作之日,为期不远。”[22](P 233)“正像欧洲各地的社会党几乎已经联成一体、展开共同活动那样,亚洲各国的社会党也必须结成一体,进而向全世界推进革命运动。”[23](P 190)在此论述语境中,何震的《女子非军备主义论》少见的以女子立场参与了这个亚洲社会主义的被殖民弱种连结,从而使得世界主义落实于亚洲的实践。
前文曾指出,何震的《天义》主张性别革命要与种族、政治、经济革命同时并进。其种族革命的要义在于反抗强族霸权而非种族分离,并且已具亚洲反帝反殖的第三世界[注]当然,此时尚未有“第三世界”一语,此乃回溯性叙述。革命视野:“吾人所言民族主义,在于排异族之特权,不在禁异族之混合。惟异族之特权应排,故不独汉人应排满,即印度之于英、安南之于法、菲律宾之于美、中亚之于俄,亦当脱其羁绊。则民族之革命,即弱种对于强种之抗力耳。”[3](P 125)“政治革命”是指欧美与日本资本主义现代性已通过帝国主义殖民或发动战争的强势,限缩了亚洲精英对革命后未来新政治形态的想象,仅醉心于欧美、日本的现代议会政治,面对当时知识界支配性的政治视野局限,以“无政府”革命作为批判性的视野及未来远景。“经济革命”则指资本主义通过帝国主义扩张,造成全球现代化的剥削苦难以及不平等,应以“共产主义”作为批判性的回应。当何震在分析性别、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时,处于当时具体的政经局势中,“战争”和“军备主义”都是核心议题。何震甚至认为,“战争”是女子受压迫的起源。
五、论战争为性别压迫之起源及女子在战争中之经验
何震认为,自古以来男女不平等就来自战争,战争造成了男女以及主奴阶级[3](P 188)。《天义》对于历史社会发展,大致模型如摩根《古代社会》以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注]《天义》曾载署名“志达”的《女子问题研究:因格尔斯学说》摘译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及国家之起源》,文后按语则呼应何震《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的主张。、甄克思(Edward Jenks,1861-1939)《社会通诠》[注]严复于1903年译出《社会通诠》,见引于何震《女子复仇论》,载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0-51页。等说,由古至今社会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天义》在多篇文章中预设了一个理论,即性别的压迫来自战争。这个观点,在《天义》创刊号的《女子宣布书》一文中即已露出端倪:
上古之民,战胜他族,则系累其女,械系其身,以为妃妾。由是,男为主而女为奴,是为剽掠妇女之时代[3](P 41)。
何震在《女子复仇论》中说:上古图腾社会公夫公妻,“为男子者视女子为公有,为女子者亦视男子为公有”[3](P 51),其后两部族相争,战胜之族对战败之民施行虐政,男则尽遭屠戮,女则身为累囚,为劫掠妇女之始,也是女子私有之始,“是为女子受制于男之始,亦女子属身于男之始也”[3](P 52)。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亦提及,上古之初行共夫共妻之制,未尝“女下于男”,亦未尝以女子为私有,后因“两部相争,战胜之民对于战败之族,系累女子,定为己身之私有”[3](P 99),亦即,战争带来的是男主女从以及女子私有的制度。何震在《女子非军备主义论》中则明白主张,“用兵”是男女不平等原因,同时也是男女不平等之制度产生的原因[3](P 188)。“制度”在此包括男有兵役权而女子则无,何震批评,通过“制度”而产生“观念”,亦即,制度不准许女子服役,而后再以男子能保卫国家而女子却不服役为口实,而论证女子不应享有与男子同等之权利,树立男尊女卑之观念。此一论证亦见于她的《女子复仇论》,该文指出,古代之国家均以女子从军为大戒,女子无从军之资格,制度上使女子无政权、学权、兵权,以至于偶有少数女子获政权、学权者“不复视为分为应然,而挟之以为奇。论者不察,遂以为女子无一善类”[3](P 71)。
观念上的男尊女卑以及贬抑女子来自制度的不平,而制度的不平又来自物质上的用兵──这是何震讨论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倾向于唯物主义而非唯心主义之处,于是解决之道也不会是以主张女子个人经济独立为已足,而是分析战争与经济体制。事实上,马克思也曾说过:“父权制的部落首领,他们管辖的部落成员,最后是奴隶。潜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随着战争和交易这种外部交往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24](P 69)
何震女子反战论值得注意的另一特色是,虽然呼应的是国际社会主义已有的论述,但当她面对在地脉络时,引述的却是古典文学诗歌,从性别及阶级的面向,通过传统诗歌来分析在地脉络中带着性别与阶级性的情感与生存状况。对她来说,这些诗歌重要的不在于作者个人的情志或文学造诣,而是通过这种较易承载情感表达的形式,看到战争与性别的关系及妇女在战争中的生存处境。而所谓“情感”,非指唯心主义的个人情感,而是如马克思所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是实践活动[25](P 60)。
何震从传统诗文分析女性战争经验,其实也是针对当时军国主义女学教材的批判。“志达”的《女子教育问题》一文批评“其尤上者,则又杂伺以军国主义,以《小戎》、《无衣》之风,提倡于女界。夫因此主义,以激发女子革命之心,此固至良之教法。若仅勉女子以爱国,则是导女子于国家奴隶耳”[3](P 194)。军国主义教育选择了《小戎》《无衣》等战争诗,何震则通过《诗经·豳风·东山》、蔡琰的《悲愤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曹植的《杂诗》、梁元帝的《荡妇秋思赋》、淮南王安的《谏伐南越书》、王粲的《从军诗》《七哀诗》、王微的《杂诗》、江淹的《别赋》、杜甫的《兵车行》《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别》、李华的《吊古战场文》等文学作品,从传统文学中与征战相关的诗文,读出了用兵对于女子安乐平和之“幸福”的破坏与亲密关系的断裂:“国家用兵之际,死别生离之惨,毕集于女子之一身。非唯为爱情之公敌也,且将陷女子于贫困死亡之一境。”[3](P 187)将妇女在战争中的经验总结为:在战争中成为囚虏、惨死或逃亡流离等身体经验,违背生民对于安乐平和要求的生离之苦、久别之苦以及战死闻耗之苦。
过去在诗评诗话或选集中提及军旅诗,或战争诗、征戍诗、军戎诗、边塞诗等,主要进行诗歌的内容或类别等零星的讨论,作家的艺术造诣是主要关注对象。何震则将历代战争或征戍诗歌作为材料,讨论其中所再现的女子在战争中的各种遭遇或情感表现,应是中国最早以文学作品做文化研究者。在何震的讨论中,主要不在于通过文学诗歌探讨作者本身的情志或艺术造诣,而是将其作为文化再现的素材,用于主题研究。何震应当也是最早在传统诗文中以反战的立场讨论战争文学者。
与此同时,文学艺术与战争的关系也在日本文坛明确浮现。幸德秋水以文学感性著称,他在写给出征去参加日俄战争的士兵的论说文《为士兵送行》(1904年2月14日)中写道:“呜呼,从军的士兵,诸君的田亩将荒芜,诸君的业务将废弛,诸君年迈的老亲正独自倚门长叹,诸君的妻儿正无奈地饥啼,而诸君之生还则原本即无可期待也。而诸君又不得不行,行矣!诸君且恪守自己的职份,如一架机器般的开动,然而俄国的士兵亦是人子,亦是人夫,亦是人父,亦是诸君同胞之人类也。思此,下手且谨慎,莫对其施行残暴之行为也。”[26](P 247)带着古典气息的文笔,将战争的负面经验穿越了古今的界限,以及国家的界限,难怪胡秋原说他“笔峰带感情”,“就说是日本最初最大的革命文学家也不为过”[27](P 5)。原田敬一在写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现代战争的蹂躏场景中也指出:“日本近代最早的‘战后文学’,是从战场的前线和城市贫民窟的黑暗中产生的。”[26](P 231)
六、结语
何震在《女子非军备主义论》的最后明确指出,自古以来女子不能当兵固是男尊女卑不平等,但迈向平等之道并不在于女子也一样要当兵,加入军备主义的行列,反而是女子要反对军备主义,使男子也解除“服兵之役”,才能有“济民救世之功”,才能“与日月争光”。其原因在于,战争涉及强种对弱种的侵略、国家对人民百姓的横征暴敛以及男对女的尊卑不平等,因此,对于被殖民的弱种、被具有阶级性质的现代国家所治理的平民、被不平等的性别体制所压迫的女子来说,唯有“非军备主义”,也就是停止侵略压迫本身,才能使得弱种、平民与女子共同获得解放进而得到自由幸福[3](P 188)。这是一种政治性的反军备主义,具有阶级意识以及政治选择与纲领视野,而不是道德性的、人道主义式的反对战争。何震政治性地解释了战争的原因、危险、利益与压迫及其意义所在,不论是国内或国外的战争,也不论是战胜或战败。在后来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成为女性主义理论主流后,性别议题与劳工、殖民、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批判作情感与政治目标上的连结,这一条迈向公有与世界主义的路线几乎被遗忘了。
《女子反军备主义论》全文论点相当程度上呼应着当时国际社会主义反战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以幸德秋水为中心的日本无政府共产主义非战论,并与《天义》整体基于亚洲现势而强调的反战与世界主义同调,其亮点在于提出性别议题并召唤女子自我解放加入反帝反殖反战争压迫的行列。何震论证了战争对妇女的影响,以中国传统诗歌呈现妇女在战争中的各种处境,使传统诗歌与现实议题产生了新的关系。《天义》通过反军备主义论,凝聚了亚洲被侵略“弱种”从根本反抗并停止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以达到世界主义大同理想之既是乌托邦也是现实斗争的理论。而何震立足于妇女作为“平民”的“幸福”生活而提出的“女子反军备主义论”则是向妇女呼吁:成为世界主义运动的战士,而非军国主义的爱国护士。对何震来说,当天下都能共产而平等时,也就是女子完成“复仇”心愿之时:“惟土地、财产均为公有,使男女无贫富之差,则男子不至饱暖而思淫,女子不至辱身而求食,此亦均平天下之道也。依此法而行,在众生固复其平等之权,在女子亦遂其复仇之愿。”[3](P 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