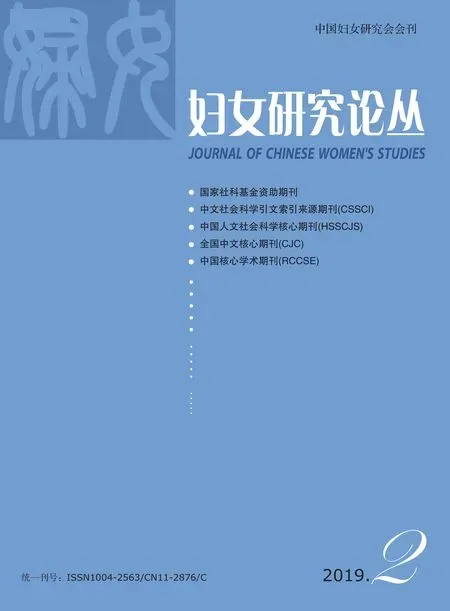悖离·妥协·成长:“她者”视阈下《少女的告密》中的女性关系书写*
凌 昊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6)
一、赤染晶子与《少女的告密》
1974年出生于日本京都府舞鹤市的赤染晶子,是日本当代文学史上女性作家群体的领军人物之一。赤染晶子本名濑野晶子,本科毕业于京都外国语大学外国语学部德语学科,后到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进修德语文学博士课程,期间退学。在她笔下诞生的《初子さん》(刊于《文学界》2004年12月号)、《恋もみじ》(刊于《文学界》2006年12月号)、《少女煙草》(刊于《文学界》2009年4月号)、《乙女の密告》(刊于《新潮》2010年6月号)等文学作品都以“‘她们’的世界”为创作出发点,无一例外都是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情感书写的产物。其中,赤染晶子凭借《初子さん》于2004年斩获第99届文学界新人奖,而《乙女の密告》(《少女的告密》)更是大受好评,于2010年获得第143届日本“新人登龙门”的芥川奖,这让赤染晶子作为新锐作家在日本当代文坛上大放异彩。
作为一名纯粹的文学创作者,赤染晶子勇敢地正面书写或实或虚的女性世界,以其作品映射日本社会当下的女性问题。她的创作关注女性的成长与生存境地,更对引导日本当代社会内部对女性的生存意义和价值进行自我剖析有着重要的影响。备受芥川奖评委青睐的《少女的告密》就是这样一部有着独特叙事角度的意义深远的文学作品。它以赤染晶子的母校京都外国语大学为创作舞台,讲述了女大学生通过校园里历经的种种——流言、友谊、蜕变、觉醒、成长——进而一步步脱离虚拟的假象世界、艰难重返现实世界的故事。作品以德国籍犹太人安妮·弗兰克写的《安妮日记》为创作线索贯穿始终,少女们的“告密”也正是在此基础上被架构起来的。外国语大学的姑娘们背诵的作品《安妮日记》是一本由安妮·弗兰克创作的真实存在的日记。这个曾经是她13岁生日礼物的红白格子本上记录了一个遭受种族屠杀的花季少女被拘捕之前在密室里度过的隐秘而又艰难的25个月。日记里书写了对自由和理想的向往、对纳粹统治的深恶痛恨以及对人性的肯定和质疑。芥川奖评审黑井千次在《乙女の試み》一文中提到作品中的女孩们背诵《安妮日记》时这样说,“她对少女们逐渐歪曲并向痛苦转变的过程进行了戏剧化的描写”[注]原文出自黒井千次「乙女の試み」『文藝春秋』2010年第9号「乙女達(女子学生)の動きが少しずつ歪んで苦しげなものへと変っていく過程が戯画化されつつ描かれる。」,暗示了在暗黑压抑的教室里学习德语的女孩们与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安妮所遭遇的困境是相似的;芥川奖评审高树信子也在《重層小説二編》一文中认为这两种困境的本质是一样的:“相比于安妮关乎生死的世界,学园中发生的事件则更像是带有趣味性的游戏,无法消除其违和感。虽然是嵌入脑海中的两个世界,但其差别对待的本质却是一样的。”[注]原文出自高樹のぶ子「重層小説二編」『文藝春秋』2010年第9号「生死のかかったアンネの世界に比べて、女の園の出来事が趣味的遊戯的で、違和感がぬぐえなかった。頭で考えられ、嵌め込まれた二つの世界だが、差別が発生する本質は同じだ。」那么,在赤染笔下的“密室”中生存的形形色色的“她”有着怎样各异的举动和心理,“她”如何在同性秩序下确立“自我”,如何在集团内的混乱中面对可怕的派系之争,成为剖析这部文学作品时不能被忽略的问题。
二、“她者”世界里的包容与侵犯
“他者”一词首见于西方后殖民理论。在西方后殖民主义的范畴中,“the other”即“他者”,是一个与主体性的“自我”(the self)相对的概念,具有客体和从属的性质。而广义上的“他者”泛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亦是与“自我”截然对立的概念。英语中的“the other”和汉语中的“他者”对性别的指向较为模糊,但由于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处在两性和同性秩序下女性的“他者”和“自我”,阐析“她”对“她”以外世界或顺从或反抗的态度,以及“她”对“她”本我的解构、重构和性别身份认同,因此,结合后女性主义时期中“他者”性在女性主义范畴内的新内涵,笔者选择使用“她者”一词,使之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他者”。
赤染笔下的女性关系十分微妙且细腻。她更关注发掘女性内心深层次的、隐秘而又不可告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理感受。在赤染看来,女性是可以结成同盟的。这种女性同盟的本质其实是女性对自我的一层保护,是女性情感里本能的需求,是借助某种外在形式解放“自我”和树立“自我”的途径。这种女性之间的情谊区别于男女两性之间的交流,她们可以暂时抛开对情欲的追求,转而在息息相通的精神层面上汇合,结合成为各自同盟里团结一致的情感。在《少女的告密》中,忙碌的女孩们被拘囿于外国语大学这座象牙塔,与外界鲜有联系,想要得到理解、关注、温暖,抑或是缓解和摆脱枯燥的生活带来的负面情绪和艰难困境,她们唯有通过对同性的亲近来表达情感和心灵层面的依赖,通过相互倾诉和倾听寻找彼此间的共性,从而借助女性之间的情谊构建起一个看似坚不可摧的小同盟,以此抵抗外敌达到自我防御的目的。
比如被巴赫曼教授随意划分出来的“紫罗兰组”和“黑玫瑰组”,其实只是课堂上简单的一个分组,却把原本就复杂的女孩之间的关系搞得愈发复杂——因为这种派系被女孩们固定了下来,成为她们识别与自己不同的存在的依据。小川洋子说:“虽然以‘喜欢草莓大福还是威士忌’为理由进行的分组毫无意义,但少女们对各自派系中另类的存在逐渐变得敏感起来。”[注]原文出自小川洋子「人形とストップウォッチ」『文藝春秋』2010年第9号「いちご大福とウィスキーではどちらが好きか、という質問によって成された無意味な分類にもかかわらず、乙女たちは自分の派閥に隠れている異質な存在に、どんどん敏感になってゆく。」这种女孩之间无关乎喜欢草莓大福还是威士忌的“敏感”逐渐发酵,最终将丽子学姐推上了风口浪尖。对于黑玫瑰组组长丽子学姐“不是女孩了”[注]全文引用的译文部分均出自姚东敏译《少女的告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的传言,起初只是敌对组紫罗兰组组长百合子学姐对此嗤笑不已,渐渐地,追随百合子的女孩们也开始参与到谣言的扩散中,乐此不疲。这个谣言不但成为女孩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且把她们划分成了不同世界的人,同一个世界的女孩更是在秘密交换信息的过程中加深了彼此间的情谊。她们为了捍卫各自团体的尊严与敌对方展开无休止的舌战,以表对自己团体组织的忠贞。黑玫瑰组的贵代在谣言甚嚣尘上之际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她第一个不再去丽子学姐的自主训练,并对谣言表达了赞同之意。这一举动得到了以百合子学姐为首的紫罗兰组一众人的赞许,她们认为贵代虽然是敌方阵营的,这种行为却是值得称赞的。于是贵代理所当然地取代了丽子学姐的地位,成为黑玫瑰组的新任领袖。此时的美佳子虽然内心深处依然以丽子学姐为信仰,但面对自己的新组长却也不得不说出“贵代你最棒了,比丽子学姐还棒”这样的话。不管这种同性同盟里相互依赖和慰藉的情感有几分真实几分虚伪,它们都是女孩们共同抵御外敌之下为自己处境寻求到的庇护和屏障,我们可以暂且称女孩身上的这种同一性为女性世界里的包容性。这种“她者”世界里所谓的包容,其实不过是女性们不约而同采取的以进为退的战术罢了,她们不在乎真相是什么,只追求与同性之间带有共性的交流,以此明哲保身。一旦这种共性偏离了当初的预期不复存在,那原本脆弱的包容性也就分化瓦解了。
赤染借助这部作品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女性关系相互作用的“她者”世界:同一性里有个性,包容性里有悖离。这种复杂的矛盾旨在说明,没有男性参与的女性同性关系并非充满和谐与宁静,它的阴暗面也是不能被忽视的。从某种层面上说,人际关系是导致女性之间发生明争暗斗的一个重要因素。李鹏程在《女性之间的暴力:一种被忽视的性别暴力》一文中提及了女性同性之间存在的攻击侵犯问题。他认为,女性暴力行为是一个很普遍的社会现象,残酷且惊心动魄。施暴的女性通常会通过语言攻击和间接攻击方式打压亲密关系中的弱势同性,如散播恶性谣言、断交、与敌对方建立友谊,等等。当她们以团体和组织的形式来进行暴力行为的时候,参与者可能是迫于施暴者的人际压力而被迫加入的[14](P 15)。黄育馥在《向“姐妹情谊”挑战——菲莉丝·切斯勒和她的<女性之相煎>》里总结了西方著名妇女活动家菲莉丝的“间接侵犯”与“同性性别歧视”观点,认为菲莉丝提出的这种种频发于女性之间的问题隐匿于心理、社交、经济等各个方面,不容忽视[8](P 65)。赤染塑造的百合子学姐就是这样一个在小团体中借用她人的刀杀人于无形的存在。她从未正面参与讨伐丽子学姐的行动,却在不知不觉中引导着她的追随者渐渐远离丽子学姐和事实的真相。百合子是一个面对任何情况都能淡然处之的人,再加上被低年级学生带着敬意地尊称一声学姐,她理所应当成为女孩们中的佼佼者。但随着她的风头接二连三地被丽子抢走,连续几年都在演讲比赛中输给丽子屈居第二,两人便成了水火不容的死对头。女孩们当然知道两位学姐的敌对关系,所以早已默默地站好了队,连成群结队上厕所期间都不忘与对方组的“敌人”大战一番。同样是面对与自己势均力敌的同性竞争者,丽子只是专注于对演讲的练习,力求优雅地记住每个词汇,而百合子的出击方式则显得更为主动且隐蔽,不论是暗地里较量还是通过操控舆论间接侵犯对方,百合子的目的最终是达到了——她的死对头被谣言击溃了,在比赛当天如百合子预期没能出现在赛场——甚至从今以后她可能再也不能站在话筒前了。百合子“呵呵”的一笑,已经说明她在这场弥漫了嫉妒、怨恨、畏惧等硝烟的战争里成为了赢家。对于女孩们之间隐秘、拖沓、紧张的争斗,虽然有人认为这与作品线索之一的“安妮的告密”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差异,但就像小川洋子所说的“赤染精心地将两种不同级别的恐怖串联起来,将故事细节向前推动”[注]原文出自小川洋子「人形とストップウォッチ」『文藝春秋』2010年第9号「赤染さんはレベルの違う恐怖の間をつなぐ、細い糸を丹念にたどっている。」一样,赤染将错时空的两种纷争串联起来,抨击了无意义的集团划分带来的恶果。
三、“她者”与“自我”的博弈
《少女的告密》的故事是以京都某外国语大学里一名普通女大学生美佳子的视角展开叙述的。对于美佳子来说,她所处的象牙塔有些许的与众不同——这里的女孩们相对于其他学校的女孩们而言是不一样的,因为她们“从不在课堂上偷偷化个妆玩个手机什么的,没有那闲工夫,她们都忙着预习其他功课”。象牙塔里的“她们”之于美佳子,是自由奔放没有礼貌的德国归日人士子女贵代,是对演讲永远保持热情却不得不直面流言蜚语的丽子学姐,是与丽子学姐势均力敌水火不容的百合子学姐,是被看似随意的草莓大福和威士忌划分成的紫罗兰组和黑玫瑰组两个派系。而这个充满着迷雾的女孩们的世界,是美佳子想要融入却又害怕融入的——她未曾想过背信弃义,也未可知平凡的自己会身处八卦的漩涡之中。“她们”的世界是扑朔迷离的,是美佳子想逃却逃离不得的,于是她沉迷在《安妮日记》中不能自拔,她认为自己就是安妮,是个可爱又浪漫的少女般的存在。
女孩们之间的明争暗斗打破了美佳子的幻想。因为“女孩团体本身就是嫉妒和八卦的发源地”,是“有洁癖的生物”,是“一方面感觉惊讶、难以置信,另一方面又比谁都深信不疑的生物”,是有心机的,是“在秘密交换信息中不断加深信仰”的一个存在。女孩们沉浸在丽子学姐不纯洁了的传言中一发不可收拾。紫罗兰组和黑玫瑰组剑拔弩张的纷争蔓延到了被称为八卦圣地的厕所,八卦持续发酵,终于导致了丽子学姐被驱逐出黑玫瑰组的结局。这种毫无根据的流言于美佳子来说是恐怖的,作为丽子学姐的隐性粉丝,一方面是相信丽子学姐的,另一方面害怕被卷到流言纷争中、成为众矢之的被女孩们攻击。所以,她只敢悄悄跟在丽子学姐身后窥探,试图找到真相。但无论告密者是谁,孤立无援的丽子学姐在美佳子的眼中都已经从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变成了可怜的替罪羊,美佳子甚至为女孩们的流言找到了出口——“丽子学姐也并未保证自己还是女孩”——此时在美佳子看来,好像告密者的身份也没那么重要了。与美佳子交好的贵代在听到美佳子不相信谣言的想法后甚至发出了“美佳子,你不是女孩吗”的质疑,这让美佳子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如贵代所说不能触碰真相的禁果。某天,在无意之中闯进巴赫曼教授的研究室,发现了巴赫曼教授与安杰利卡娃娃的真相之后,丽子学姐在美佳子心中的形象终于又回来了。可是,自己是女孩们之中唯一发现真相的人,她“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很恐怖,很想逃离这里,回到女孩们充斥的八卦世界”,因为“不信八卦,在女孩中间就无法立足”。
在美佳子充满矛盾和纠结的心理历程中,《安妮日记》有着很强的引导力。自始至终都坚信安妮可爱又浪漫的美佳子突然在巴赫曼教授的话语里醒悟过来:安妮害怕被“他”发现,安妮害怕自我会被“他”侵蚀掉,安妮害怕被“他”告密。然而最终,安妮还是誓死维护了她身为安妮·弗兰克的权利。被美佳子背诵了几十遍几百遍的《安妮日记》好像突然有了一种全新的解读——这时的安妮已经不是美佳子心里那个柔弱的存在了,而美佳子自己也终于愿意面对真相相信真相:因为犹豫不决的皮特,就是《安妮日记》最大的悲剧——她不愿像皮特一样戴上他人的假面违背自己的内心。当一度陷入流言漩涡的丽子学姐终于被证实了自己的清白,教授恳请美佳子参加演讲比赛的时候,美佳子又一次犹豫了,她害怕自己像可怜的丽子学姐那样成为女孩们中间坚持自我的另类,害怕成为被排除在女孩团体之外的“她”。但巴赫曼教授告诉美佳子,即使忘词,安妮的名字也一定要被讲出来——大屠杀带走了人的生命和财产,也妄图带走人的名字。大屠杀不允许自我的存在,与众不同的自我在“他”的笼罩之下,会被全世界排斥——但《安妮日记》让安妮有了自己的名字,也让后世的人了解了所有人都是有名字的,那些人不是“他”,而是无可替代的“自我”。在一直被美佳子视作精神信仰的“安妮”的鼓励下,美佳子终于鼓足勇气走上演讲台,屡屡被忘记的词汇也再度与她相遇。美佳子终于迈出了这一步——再也不掩饰自己对真相的渴求,勇敢地承认告密者本尊就是“我”,即使成为女孩们眼中另类的“她者”,也要找回“自我”,让自己成为安妮般永远不将自己名字遗忘的人。这时美佳子所成为的“她者”,对美佳子来说就是“自我”,是外部“她者”世界观照下被异化剥离出来的全新的本我。
赤染晶子这部作品以“告密”为贯穿全文的重要线索,勾勒出了一个从迷茫到清醒的女孩形象,在寻找真相和告密者的过程中,她从一个随波逐流的平凡女孩蜕变成一个自我觉醒的女性。对美佳子而言,与其说是少女的告密,倒不如说是一部少女的成长日记。芥川奖评审池泽夏树在评论这部中篇小说时提道:“演讲比赛中如女王一般的丽子学姐,身为归国子女且能讲一口流利德语的贵代,这些充满实力的人都是美佳子超越的对象。换言之,我们在这部作品里也能读到‘成长小说’的一面。作者的创作意图是改变安妮·弗兰克一直以来给人的纳粹牺牲品的印象,让她找回原本自立自强的年轻女性形象。”[注]原文出自池澤夏樹「ロマンチックではなく尊厳の問題」『文藝春秋』2010年第9号「スピーチコンテストの女王のような麗子様や、帰国子女でドイツ語完璧の貴代など、仰ぎ見る実力者たちを結果において彼女は追い越す。つまりこの作品には成長小説としての側面もあるということだ。作者の意図は、アンネ?フランクをたまたまナチスの犠牲になった不運な少女という従来のイメージから、自立した若い女性という本来の身分に引き上げることにある。」
在这部作品里,赤染晶子为少女美佳子造了一面镜子,镜面里映出了时空交错下逐渐建立起独立人格的安妮·弗兰克像。随着美佳子幻想中的传统的安妮被自己的成长打破,美佳子终于也从虚拟的世界中回归到了现实,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成长路上必经的自我“分离”与“撕裂”,从具有同一性和整体性的“她者”世界中解脱出来,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我”。镜子里的安妮引导着美佳子对自我的认同,让她成为具有“我”性质的“她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佳子和安妮共享着“成长中的少女”这一主体身份,美佳子就是镜子里的安妮,安妮就是镜子前的美佳子。美佳子从本我自身分离与撕裂成功而异化出来的“她者”,是一个自我主体由剥离到重新建构的过程,亦是美佳子撕下角色扮演的面具追求自我同一性的过程。而这样的成长,无疑也是少女美佳子塑造者的赤染晶子本人对于现代女性自我存在意义及价值的思考和追寻。
四、女性关系与父权制
《少女的告密》是一部主要着墨于女性角色的文学作品,在该作品中男性仿佛始终处于边缘性人物的队列。书中描绘的现实世界里,德国籍犹太人巴赫曼教授是赤染正面塑造的唯一一个男性角色。他的出场是王熙凤式的“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行事唐突的他总是毫无征兆地随意闯入日本教授的课堂,这让日本教授和德语系的女孩们苦不堪言。不过,我们不难发现的是,几乎每次女孩们之间掀起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风波,都会与巴赫曼教授有着细微的剪不断的关联。比如,巴赫曼教授起初只是为了方便研习而把女孩们分成两个组,却未曾想因为一个简单的分组就让女孩们之间的关系剑拔弩张愈显繁杂;又比如,优秀的丽子学姐被女孩们孤立、中伤,最后不得不放弃她所钟爱的演讲,是因女孩们中间流传着的关于丽子学姐和巴赫曼教授关系不纯洁的负面传言而导致的;再比如,始终畏惧被女孩们排除在外的一向谨小慎微的美佳子突然被误解与巴赫曼教授有染,一个“赎金7.5荷兰盾”的告密让她陷入了不得不怀疑身边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告密者的巨大恐惧之中;抑或是行为乖张的丽子学姐“拐走”了巴赫曼教授的安杰丽卡娃娃,只是因为她爱慕着巴赫曼教授,嫉妒每天被教授抱在怀里、睡前还要伴着莫扎特音乐入睡的玩偶,甚至最后她把娃娃小心翼翼地托付给美佳子,也是因为无法承受教授因为娃娃不见了而伤心过度的罪过。
笔者在前文提到过导致女性之间发生明争暗斗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际关系,而在赤染笔下牵引着女孩们之间人际关系微妙变动的恰恰是整部作品里唯一的一个男性人物巴赫曼教授。假如巴赫曼教授代表了这部作品里看似被边缘化了的父权世界,那他在一定程度上就拥有了两性世界里的话语主动权——这种权力有时会被女性推崇为至高无上的、可以借此参与到男性世界并受到男性尊重的一种方式。父权制应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的实质是一种社会权力等级体系。在这种体系下,男性和女性、上级和下级、长辈和晚辈由上至下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与《安妮日记》里因纳粹势力的追捕和囚禁不得不处在隐蔽密室空间里生活窘困的安妮一样,少女们在封闭的象牙塔里也很难实现真正的自由——因为巴赫曼教授坐在权力等级的顶端,是最拥有话语权的“家长”。巴赫曼教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左右着女孩们间的关系:有人渴求得到教授的赞许而拼命练习演讲;有人因为怨恨教授的苛刻而散布不利于教授的流言;有人因为暗恋教授而做出匪夷所思的行为。这是否可以说明,女孩们实际上视巴赫曼教授为两性世界里毋庸置疑的权威,她们渴望在这种权威之下被认可或得到存在感?而在这种导向下变化着的女孩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很大程度上被父权制意识形态所改写了的、不纯粹的关系——虽然女孩们的成长历程中有对“自我”的探索,有对两性情感的自主选择,也有对心灵精神丰富性的追求,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来自“权威”的把控、压制甚至是扭曲,因此呈现出来的女性同性世界是矛盾的、紧张的、阶级分化严重的、带有差异性的,而并非像我们预想的那样温柔善意且充满同性间的惺惺相惜。
巴赫曼教授在女孩们眼中是个怪异的存在,他的行为举止经常超乎人想象。他以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自豪,同时也钟爱日本式的努力和根性,赞许日本最炽烈的情怀。他在研习课上对女孩们异常苛刻,却唯独对安杰利卡娃娃温柔如水。面对这样一个喜怒无常又无时无刻不在她们身边徘徊的教授,女孩们从不敢正面与他辩驳,连深受欧美文化影响的德国归日人士女儿的贵代也只得对着他的背影暗骂一句“这老头真蠢”。女孩们在高高筑起的象牙塔里闭塞、压抑地度过大学漫长的时光,终日陪伴她们的只有枯燥的外文课、无趣的老教授,还有彼此之间可以结伴上厕所的情谊。当她们试图为情绪宣泄寻找出口时,女孩们之间泛起的一点点波澜都会成为清汤里的调味料,令她们欣喜,并期待这种波澜持续得久一些,让她们在仅有的厕所情谊之外获得更多的情感共鸣。所以,当小集团的首领势同水火,女孩们亦纷纷站队迅速结成同盟——当她们迫于压力不敢直接向权威发起质疑的时候,攻击亲密关系中的同性便成了她们间接宣泄不满的途径。在女性同性秩序下,金字塔依旧存在,金字塔顶端的人也依旧被赋予了父权制等级社会中的支配权。女性同性世界里不可避免地被划分等级、阶层甚至是明确隶属关系,其根本也是源于影响已久的父权制在潜移默化地左右着女性的思维方式。当她们无法向权势直接正面地发起挑战的时候,只有借助于在同性集团里占据一席之地的方式来找寻未能从男性那里得到的尊重、认可和存在感,其表现方式也许是拉拢亲近同性,孤立排挤同性,或者是攻击侵犯同性。这些行为可能是女性无意识的性别偏见带来的,却在一定程度上默认和支持了父权制在两性世界里的掌控权,并引导女性把这种权力代入了女性同性世界里,造成了女性内部相互作用、阶级分化严重的现状。“这种在女性同性秩序下对权力高峰服从的实质,并非是对女性个人的服从,而是对‘父权’的服从。”[11](P 249)这也就是为何少女们的象牙塔里多的是明争暗斗,从未有过绝对的相安无事。若想要在这样一部看似男性人物游离在外的女性文学作品里深刻剖析女性,恰恰最不能忽略的就是“缺席”的父权制对“她者”无形的驾驭。“她者”在这种悄无声息的掌控之下默认了自身作为第二性别阶级的从属地位,不自觉地认可了把父权本位思想中专制专权的一面应用到女性同性世界秩序当中来的行为,因此,我们所看到的现实世界里的“少女的告密”,其实也是某些“她者”试图在父权制社会下参与“权威”、支配“权威”或是向“权威”妥协的外在表现。
五、结语
《少女的告密》无疑是一部时空交错的少女成长日记。赤染晶子仅仅借助一篇研习教材、一个小玩偶和一只秒表就能把“告密”的安妮和“告密”的美佳子精心串联起来。“告密”仿佛成了这部作品唯一的主线,暗示了一个女大学生从女孩到女性的蜕变历程。但我们同样不能忽略小说里盘根错节的女性关系为“告密”这条主线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女孩们在“她者”世界里架构了一种包容与侵犯、亲和与悖离并存的同性关系,而这种复杂的关系里有阶级层面的差异性,也有人格层面的不平等,还有看似被边缘化的父权制对女性同性秩序无形的掌控。因此,我们不能抛开这种种因素空泛孤立地剖析被“告密”的女主角从迷失“自我”到找寻“自我”再到确立“自我”的艰难过程。在赤染笔下诞生的斑驳陆离的“她者”的世界里,始终贯穿着女性关系对于女性主体性成长意义的思索,这应该也是我们在女性主义文学作品里所能解读到的独有且多重的况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