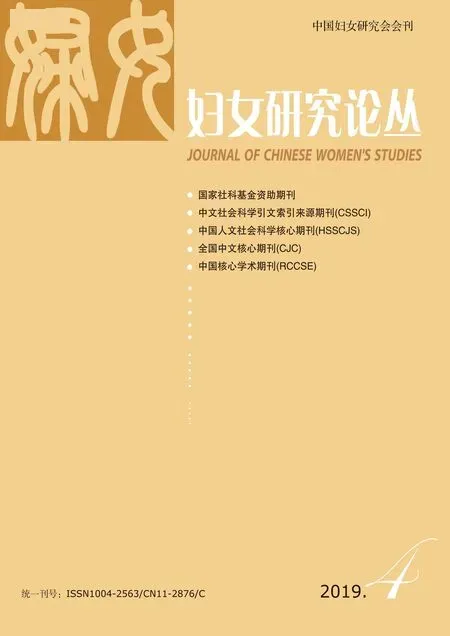从人的自由到女性的自由:反乌托邦小说的跨时空对话*
王 苇 杨莉馨
(1.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2.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近年来,反乌托邦文学(anti-utopian literature)备受瞩目,尤其是苏联作家尤金·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的《我们》(1924)、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1932)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1949),更是被并称为“反乌托邦小说”三部曲,以对极权恐怖和科技滥用的未来想象闻名于世。反乌托邦文学与欧洲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乌托邦文学可谓一体两面。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鸟》,到文艺复兴后期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1627)和19世纪英国小说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乌有乡消息》(1891),均蕴含着批判现实、遥想美好未来的乌托邦理想;进入启蒙时代之后,面对科技理性与“进步”话语压制人性的新现实,作家们开始反向推演世界发展的黯淡图景,反乌托邦文学开始崛起。20世纪以来,在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危机,唯科学主义泛滥、生态环境恶化与极权主义猖獗的新形势下,反乌托邦文学更是涂抹出一幅幅阴森可怖的地狱前景,戳破海市蜃楼的美妙幻象,成为乌托邦文学的“黑暗底片”。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1818)、H.G.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的《莫洛博士岛》(1896)以及“反乌托邦小说”三部曲,都是反乌托邦文学的代表作。
然而,大部分反乌托邦作品由于出自男性作家之手而有意无意地体现出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和对女性意识的遮蔽,以抽象的“人”的境遇掩盖了两性不同的生存处境,甚至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倾向,典型者如《一九八四》。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女性小说家的介入,反乌托邦文学中女性失语的局面开始得到扭转,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的《幸存者回忆录》(1974)、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的《新夏娃的激情》(1977)以及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的《使女的故事》(1985)等,均体现出对西方反乌托邦文学传统中女性意识缺失的强力矫正。尤其是《使女的故事》,一方面在揭露极权恐怖的主题上深受《一九八四》影响,另一方面又体现出身为女性作家与女性主义批评家的阿特伍德自觉的性别立场。故本文以《一九八四》与《使女的故事》为中心,通过分析这两部反乌托邦小说代表作的跨时空对话,探讨性别立场的引入为反乌托邦文学这一文类带来的新变化。
一、从《一九八四》到《使女的故事》:一脉相承的反乌托邦传统
作为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和社会批评家,乔治·奥威尔(1903-1950)的《动物农场》(AnimalFarm,1944)和《一九八四》(NineteenEighty-Four)对20世纪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奥威尔也由此被誉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一九八四》以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世界的政治格局为基础,遥想了极权国家大洋国无所不在的高压统治,描写了孤独者温斯顿·史密斯的抗争与失败。《使女的故事》(TheHandmaid’sTale)则是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重要作品,甫一问世即斩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洛杉矶时报最佳小说奖”“阿瑟·C.克拉克最佳科幻小说奖”和“英国布克奖”提名等,在国际文坛享有崇高声誉。2017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更是包揽了美国电视剧最高奖艾美奖的五项大奖。小说假想20世纪末的美国在一次政变后变成了由男性统治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极权国家——基列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Gilead)。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通过口述自己成为基列国的生育工具使女之后在统治者大主教家的苦难经历,披露了该国阴森恐怖的社会氛围。
《使女的故事》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对反乌托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阿特伍德曾在科幻小说评论集《在另类世界:科幻小说与人类想象》中回忆了奥威尔的著作伴随自己成长的历程。她9岁读《动物农场》,高中时代开始读《一九八四》:“我一遍遍地读,它和《呼啸山庄》已成为我的最爱。”[1](P98)《我们》、《美丽新世界》和亚瑟·库斯勒的《正午的黑暗》(1940)等反乌托邦杰作也都让她爱不释手。《一九八四》中大洋国“用宣扬仇恨而又混淆人心的口号将民众牢牢栓在一起,蓄意歪曲言语的意义,销毁一切真实的历史而用所谓的记录填充历史记录的空洞”[1](P101)的统治策略,给她留下了惊心动魄的印象。她终于在1984年开始创作《使女的故事》,向前辈大师表达了敬意。
两部小说的互文特征,更重要的是表现了极权国家等级森严、敌视人性、惩戒肉体、规训灵魂的共性:大洋国有老大哥、核心党、外围党及无产者4个阶层,其中占人口总数2%的核心党员掌控着国家;基列国则由大主教构成最高统治集团,女性被分为不同的等级:夫人(大主教妻子)、嬷嬷(使女的训导者)、使女(为大主教繁衍子嗣的工具)、马大(大主教家的女仆)、经济太太(平民妻子)、荡妇(在秘密俱乐部中为大主教提供性服务的年轻女性)和坏女人(上了年纪失去生育能力的女性,或未能怀孕生子的使女等)。大洋国成为18世纪英国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所预言的“全景式监狱”(panopticon)和当代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cault)所分析的监控者无处不在、被监控者无处遁形的现代规训与惩戒机制的精确呈现:到处有电幕监视着人的行动,监听着每一种声音。巡逻队的直升机在屋外盘旋,潜伏在身边的思想警察随时会逮捕异端分子。夫妻之情、亲子之爱没有容身之地,唯一的感情是对“老大哥”画像的膜拜和对他人的告发。在《使女的故事》中,政权由少数男性大主教掌控,他们刻板搬用《圣经》词句,通过散布各处的秘密警察即“眼目”和所谓的“天使军”镇压反叛者。戴着墨镜的“眼目”和他们“黑色的有篷车”令人不寒而栗:“车身上戴着白色翼眼标志。它没有拉警报,但其他车辆还是避之不及。它沿着街道缓慢巡行,似乎在寻找什么目标,就像潜行觅食、伺机而扑的鲨鱼。”[4](P195)两国统治者还动用各种方式如“秘密处决”、在围墙上将人吊死的公开“挽救仪式”和送“隔离营”等迫害异端,煽动群氓同仇敌忾的恐怖气氛。
再者,大洋国和基列国的统治者都高度重视话语对人民的思想钳制和精神愚弄。大洋国的口号是:“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5](P40)温斯顿所在的“真理部”的日常工作就是篡改历史、捏造谎言:“每个季度在纸面上都生产了天文数字的鞋子,但是大洋国里却有近一半的人口打赤脚。”[5](P48)统治者还通过减少词汇量、强制使用“新话”(newspeak)以达到控制思想的目的:“我们是在消灭老词儿——几十个,几百个地消灭,每天在消灭。我们把语言削减到只剩下骨架。十一版中没有一个词儿在二〇五〇年以前会陈旧过时的。”[5](P59)而“新话”的全部目的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没有词汇可以表达。凡是有必要使用的概念,都只有一个词来表达,意义受到严格限制,一切附带含义都被消除忘掉……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5](PP60-61)同样,在《使女的故事》中,电视连篇累牍地播放“天使军”打败叛军的胜利消息,“从来没有打败仗的报道”[4](P95)。而“事实上,根本无所谓什么前方:故事似乎在几个地方同时进行”[4](P95)。屏幕上还会出现胡子拉碴、肮脏不堪的俘虏的特写镜头。亲切慈祥的播音员,恰如《一九八四》中那位无所不在的“老大哥”:“他从屏幕上向外平视着我们,健康的肤色,花白的头发,坦诚的双眼,眼睛周围布满智慧的皱纹。这一切使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大众心目中的理想祖父。”[5](P95)在语言控制的力度上,基列国甚至超越了大洋国,因为统治者意欲彻底清除语言和思想带来的麻烦,所以剥夺了绝大多数女性甚至部分男性读书写字的权利,使女们更是成为沉默的群体,难得见面时的交流只能限制为以下两句固定对答:一个说“祈神保佑生养”,另一个说“愿主开恩赐予”。俄罗斯文论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指出,语言并非思想的被动载体,而与思想存在着互动关系,是具有主体性与生命力的。福柯更是提出了著名的权力-话语理论,揭示了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共谋关系。所以,无论《一九八四》还是《使女的故事》中,极权政治的统治策略之一就是通过控制语言操纵思想,达到清除异端、规训国民的目的。其结果正如美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所指出的:“极权主义运动将目标定在组织群众,并且获得了成功。”[6](P403)
除了在以上诸方面继承了《一九八四》的传统,对极权统治的反人性本质进行了出色的刻画之外,《使女的故事》还进一步发展与深化了反乌托邦小说的政治讽喻主题,以鲜明的当下性显示出阿特伍德密切关注时代热点问题的人文情怀。如果说《一九八四》以奥威尔于20世纪30年代亲历的西班牙内战以及在左翼党派斗争中梦魇般的经历为基础,呼唤民众警惕未来极权暴政出现的可能性的话,《使女的故事》则想象了21世纪初由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实施神权统治的世界,表现了当今国际社会对宗教极右翼势力猖獗的隐忧,以及作家对美国社会从自由主义价值观向右翼保守主义倾向转变的犀利观察。关于作品的创作动因,纳萨莉·库克(Nathalie Cooke)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传》中写道:“1981年的某一天,阿特伍德和夏娃·萨伦巴一起吃饭,席间谈到了原教旨主义过于极端的观点。萨伦巴说:‘谁也想象不出来,要真成那样的话将会怎样。’阿特伍德心中顿时出现了一个故事框架。她说:‘我想我能把它写出来。’萨伦巴说:‘那就写出来吧。’”[3](P81)而在接受采访被问及为何以美国而不是母国加拿大为小说背景时,阿特伍德的回答是:“比起加拿大,美国在很多事情上更为极端化。加拿大则与之不同,并不会在左右两翼之间摇摆不定,更为真实的是,现在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在关注美国正在做什么,或者十年、五十年后会做些什么。”[7](P96)美国左右翼政治与宗教势力的博弈,成为阿特伍德考察人类未来政治走向的一个集中入口。
这个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故事,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另一部同样以马萨诸塞的波士顿为背景、时间设定在17世纪北美清教时代的殖民社会的著名小说《红字》。在思想矛盾的清教作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me)的笔下,海丝特·白兰与丁梅斯代尔牧师在严酷惩戒中的绝望爱情,曾引无数读者扼腕叹息。当年为了逃离宗教迫害,乘坐“五月花号”漂洋过海、投奔新大陆的清教徒移民以及他们的后代子孙,体现出对天主教统治力量的专横堕落的不屈抗争和坚忍不拔地开疆拓土、以实现上帝托付的执着精神。然而他们在站稳脚跟后,也走向了排斥异己、实施宗教迫害的极端,并用森严的戒律压抑人性,从而在北美的清教社会中形成了虚伪、冷酷、苛刻、严厉的道德风气。到了阿特伍德笔下,基列国同样退化为一个加尔文式的政教合一的宗教极右翼极权社会,其中,《圣经》取代了宪法,色情场所被取缔,同性恋被宣布为非法,妇女被剥夺了工作和拥有财产的权力,男性同样生活在禁欲与异化之中。故有学者将基列社会统治称为“超级圣经清教主义”(super-biblical Puritanism)[8](PP74-75)。王韵秋在《非左即右——〈使女的故事〉中美国极权主义未来的意识形态溯源》一文中,亦准确地回溯了17世纪以来的美国清教主义文化传统与小说中的基督教右翼保守主义之间的精神联系,指出“小说的政治隐喻正是美国右翼保守主义”[9](P70)。虽然阿特伍德本人否认了小说的预言性,但在2017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这部有关美国极权主义未来的小说突然销量大增的结果却是耐人寻味的。“三十年后的今天,再读《使女的故事》之时,我们已经身处文本中的‘二十一世纪’。当下的我们虽然并没有遭遇小说中的极权主义,但是当看到‘9·11’事件后世界格局的风云变幻,近期伊斯兰国恐怖袭击的愈演愈烈,以及特朗普政府不顾后果的军事行动,我们也似乎看到了《使女的故事》中极权主义临近的步伐。”[9](P76)由此,阿特伍德通过文学的强大力量,喻示了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乃至世界各国的宗教狂热分子所隐含的危险,为人类的未来敲响了警钟,成为当代反乌托邦文学中的一部力作。
与此同时,阿特伍德又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重点揭示了极权主义对女性的压迫,将反乌托邦文学的主题从人性的自由进一步拓展为女性的自由。
二、从人的自由到女性的自由
20世纪30-40年代,在法西斯主义盛行、西班牙内战爆发、冷战开始的时代背景下,奥威尔预感到种种乱象的可怕前景,通过政治讽喻小说揭露了极权主义对人类的摧残。传记作家杰弗里·迈耶斯(Jeffrey Meyers)称赞奥威尔“在一个人心浮动、信仰不再的时代写作,为社会正义斗争过,并且相信最根本的是要拥有个人及政治上的正直品质”[10](P452)。然而,奥威尔笔下人的自由似乎并不包含女性的自由,相反体现出男权中心的意识形态。2018年恰逢奥威尔诞辰115周年。在新的文化语境下检视这位伟大作家的创作,我们却发现在他讽刺等级森严的乌托邦世界的小说及其他非虚构作品中,性别压迫并未进入他的视野。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学者达芙妮·帕泰(Daphne Patai)在《奥威尔神话:对男性意识形态的研究》(TheOrwellMystique:AStudyofMaleIdeology,1984)中通过对奥威尔作品的系统解读,认为男性中心论贯穿于他所有的创作之中。譬如,奥威尔对女性智力明显持否定态度,认为她们不能欣赏真正的艺术,无法与之进行深度的思想交流。他说“康拉德才华的最好证明就是女人们都不喜欢他”[11](P100);而萧伯纳后期作品越写越差的标志是“它们只配用来安慰那些渴望拥有高雅品位的胖女人们”[12](P143)。具体到《一九八四》中,思想者温斯顿与茱莉亚之间几乎没有过严肃交谈,他们走到一起也并非出于志同道合。裘莉亚首度出现时,奥威尔即通过温斯顿之口评论说:“总是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是党的最盲目的拥护者,生吞活剥口号的人义务的密探,非正统思想的检查员。”[5](P12)小说中女性浅薄、无知与盲从的突出实例,是温斯顿名义上的妻子凯瑟琳:“她毫无例外地是他所遇到过的人中头脑最愚蠢、庸俗、空虚的人。她的头脑里没有一个思想不是口号,只要是党告诉她的蠢话,她没有、绝对没有不盲目相信的。”[5](P76)在尚未接近裘莉亚之前,温斯顿痛恨她“青年反性同盟”成员的身份,在幻觉中“想象自己用橡皮棍把她揍死,又把她赤身裸体地绑在一根木桩上,像圣塞巴斯蒂安一样乱箭穿身。在最后高潮中,他污辱了她,割断了她的喉管。”[5](P18)而在两人成为情人之后,裘莉亚也只是温斯顿或奥威尔心目中的欲望对象,以搜集旧时代残存的脂粉、口红、丝袜、香水和高跟鞋取悦于男人,是温斯顿口中“腰部以下的叛逆”[5](P181)。无产者阶层的女性在奥威尔笔下更是愚昧、低俗与丑陋的。他在街上行走,听到愤怒与绝望的喊声,原以为无产者起来反抗,结果发现只是一群坡头散发的妇女在抢夺一只锅。他还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嫖妓时对妓女的观感:“她一头倒在床上,一点也没有什么预备动作,就马上撩起了裙子,这种粗野、可怕的样子是你所想象不到的。”[5](P77)这里,叙述者的性别优越感和对女性的蔑视暴露无遗。由此,奥威尔虽然笔锋直指独裁统治,但真正关心的实际上是性格懦弱、欠缺男性气质的温斯顿即男性在一个高度极权的等级社会中被阉割的弱势地位,女性似乎并非是他真正关注与尊重的群体。
颈椎管狭窄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患者脊髓和神经的空间不足,血供不足,造成各种临床症状。前路手术能够改善颈椎的稳定性,为后路手术提供一定的条件。颈椎前路和后路关节手术对脊髓损伤患者比较轻,与单纯的前路或后路减压手术相比,前路手术患者可以使颈椎稳定性恢复,采取仰卧位避免手术治疗和处理时导致患者的脊髓损伤加重[2]。然后采取仰卧位进行后路手术有利于颈椎病患者的长期稳定。
进入20世纪70年代,人类亲历了一系列由有毒气体、核废弃物所导致的环境公害事件。仅发生在美国的,就有1978年曝光的美国拉夫运河工业废弃物污染事件,197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三里岛核电站放射性物质泄漏事件,1982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华伦县肖科镇黑人居民抗议在阿夫顿社区附近建造有毒废弃物填埋场的游行示威事件等。而就在阿特伍德完成《使女的故事》的第二年,在苏联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造成了全球范围内最严重的一次核污染。得益于当代女性主义文化思潮的滋养,面对环境恶化、人类生育能力不断下降的危机,身为生物学家女儿的阿特伍德不仅揭示了极权专制与男权统治之间的共谋关系,还呈现了女性成为首当其冲的环境受害者的现实,体现了鲜明的生态女性主义立场。她曾这样回忆自己的创作动机:
假如女人的位置是在家里,那么为什么她们不在那儿?该怎样让她们重返家庭?如果你掌握了美国的政权,那么你的施政纲领将是什么?……我的小说是从处死叛党者的场景(后来我把它移到了小说的结尾)和我的主人公吃鸡蛋开始写的,那时,我还没给主人公和整部小说起名字。当时我在一张纸上写满了男人的名字,在每一个名字前面加上Of,最后我选择了Offred(奥芙弗雷德)这个名字,这样做有三个理由。第一,这个名字很古怪,大多数人很难立即看出它是什么意思——只是一个简单的男性名字前加上一个简单的表示归属的词of[13](PP18-19)。
作家从女主人公被剥夺了姓名与自我,仅以男性占有物而存在的命名方式起笔,不仅象征性地揭示了基列国的男权压迫本质,也鲜明地表达了为女性代言的立场,通过对作为“国有资源”,在人口凋零、畸胎甚多的基列国为大主教们繁衍子嗣的使女的生活回忆,表现了女性的悲惨命运。
小说的核心情节隐喻的是《圣经·创世纪》中不能生子的拉结让使女比拉代替她与其夫雅各同房从而得子的故事。未来世界的使女们“全身上下,除了包裹着脸的带翅膀的双翼头巾外,全是红色,如同鲜血一般的红色,那是区别我们的标志”[4](P8)。她们先是被迫在拉结-利亚(以拉结和她的姐姐利亚命名)感化中心接受嬷嬷们的训导,随后被分配到老迈的大主教家充当生育机器:“充其量我们只是长着两条腿的子宫:圣洁的容器,能行走的圣餐杯。”[4](P156)小说令人毛骨悚然地描写了大主教家例行的授精仪式:先是诵读《圣经》,随即由大主教、无法生育的夫人和使女共同完成整个过程。这其中不要说“爱”,连“欲”都不可能存在,唯有赤裸裸的功利目标——受孕:“我不说做爱,因为那不是他正在做的。说性交也不合适,因为这个词意味着两人参与,而现在却只是一个人的事。”[4](P109)不堪忍受的奥芙弗雷德只能紧闭双眼,努力“将自己与自己分离”[4](P110);使女的分娩场景同样具有非人的仪式意味:社区的所有夫人与使女均须参加,见证家有喜事的夫人和分娩使女同坐一张产凳,煞有介事地模拟分娩的过程。除了使女,大主教夫人身为统治阶层的一分子,同样是男权统治的牺牲品,年老色衰的她们不得不忍受丈夫的冷漠,以及在授精与分娩仪式上的尴尬与嫉妒;老年女性更因在男权社会中的失效而被强行带往隔离营清扫核废料,全身皮肤剥落,痛苦死去;奥芙弗雷德最好的大学同学,曾经意气风发、桀骜不驯的莫伊拉,虽然成功绑架了嬷嬷,逃离了感化中心,令“她们至高无上的权力出现了破绽”[4](P153),最终还是在被捕后成为专供大主教们淫乐的妓女。
在呈现了女性被压迫的普遍性后,阿特伍德还特别揭露了基列国实施性别迫害的内在机制,即除了严酷的肉体侵害与精神麻痹之外,统治者还动用国家机器和舆论力量,通过剥夺女性的工作权和冻结电子银行卡,剥夺女性的经济独立权和反抗的可能性。由此,女性只能对男性产生人身依附,从社会退居家庭。奥芙弗雷德本来是一位职业女性,和丈夫因爱建立了家庭。然而,政变发生后,她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和存款,也由此失去了在丈夫面前的自信心与安全感:“我觉得整个人在缩小,当他搂住我,拥我入怀时,我缩成了玩具娃娃那么大。我觉得爱正抛弃我独自远行”,“我们不再彼此相属。如今我属于他”[4](P210)。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阿特伍德改写了《一九八四》中的一个数学公式,使之生发出新的意义。温斯顿在秘密日记中写道:“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5](P93)作为自由的表征,二加二等于四象征了客观规律和知识理性,背后是对人性的珍视和自由意志的高扬。这也就是在可怖的刑讯室中,审讯者奥勃良通过酷刑逼迫温斯顿放弃对之的坚持的原因:“有时候是四,温斯顿。但有时候是五。有时候是三。有时候三、四、五全是。”[5](P288)到了《使女的故事》中,这一公式首先体现为大主教代表的男权意志对女性智力的蔑视:“女人不会加法,他曾经开玩笑地说。当我问他是什么意思时,他说,对女人来说,一加一加一再加一不等于四。那等于几?我问,以为他会说等于五或者三。还是一加一加一再加一,他回答。”[4](P214)但“我”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大主教的阐释重新解读与发挥为女性个体独特性的标志:“大主教说得对。一加一加一再加一不等于四。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无法将它们相加。不能相互交换,不能以此换彼。无法相互代替。”[4](P222)这里,经由对一个数学公式的意义的跨时空改写,阿特伍德表达了对女性不屈意志和独立存在的执着追求,深化了女性自由的主题,并预示了小说充满希望的结局。
三、《使女的故事》:《一九八四》的女性主义改写
除了对一个数学公式的具体改写,《使女的故事》从整体上看同样可以被视为对《一九八四》的女性主义改写,这也是不少评论者将《使女的故事》称为“女性主义的《一九八四》”的原因所在。这一改写不仅体现在作家对女性苦难的关切、对女性自由主题的拓展上,更表现为对女性抗争及其光明前景的呈现。在此方面,作家首先通过对女性声音的传达凸显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内在关联,其次也表达了与奥威尔不同的乐观主义倾向。
福柯认为,所有的权力都会带来反抗,以反面话语的形式生产出新的知识和真理,并形成新的权力。在基列国中,统治者压迫女性群体的制度性策略之一是剥夺其话语权。那么,女性要确认自身的存在,首先要从话语权的夺回开始。如果说《一九八四》主要呈现的是男性作者的叙述权威,《使女的故事》则采用了和温斯顿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不同的第一人称叙述,集中表达了女性强烈的个体意识,以及与女性群体交流的欲望。奥芙弗雷德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女英雄”,她没有闺蜜莫伊拉和具有女权倾向的母亲那么张扬和自信,相反有些怯懦,但却更具真实性和代表性。她在被迫成为使女期间心怀与母亲、丈夫和女儿重逢的一线希望而隐忍偷生,但还是在孤独中尝试通过各种形式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会哼唱过去时代的“禁歌”,以对美好过往的回忆支撑自己坚持下去;“我”清晰地意识到“名字对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4](P97)“我一遍遍叨念着自己原来的名字,让自己不要忘了从前曾经可以随心所欲去做的种种事情,以及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模样。”[4](P113)“我把那个名字珍藏起来,像宝贝一般,只待有朝一日有机会将其挖出,使之重见天日。”[4](P97)奥芙弗雷德努力在与遗忘作斗争,因为她深知只有保持记忆与清醒,才不会被统治者完全征服。“我”还利用在书房陪大主教取乐的机会,通过阅读被禁毁的“流行杂志”,用过去时代“无畏、从容、自信”的女性形象来激励自己,因为“她们没有恐惧,也不依附某人”[4](P181)。
除了孤军奋战之外,基列国的女性还暗暗通过各种渠道谋求团结与互助。即便没有并肩的战友,也要将信念作为宝贵的遗产传递给后来者。小说中多次出现奥芙弗雷德在自己那间牢狱般的小房间的衣橱深处发现的一行神秘的“拉丁文”,那是前一任使女在上吊自杀前用指甲刻出来的:“别让那些杂种骑在你头上。”[4](P216)对奥芙弗雷德来说,这不仅是女性间彼此激励的纽带,更是“一声命令”[4](P169)。正是这一“命令”激励着奥芙弗雷德在逃出魔爪后以录音的方式,为后代留下了基列国的女性受难史:
是讲,而不是写,因为在我身边没有可以书写的工具,即使有也受到严格禁止。但是,只要是故事,就算是在我脑海中,我也是在讲给某个人听。故事不可能只讲给自己听,总会有别的一些听众。
即便眼前没有任何人。
讲故事犹如写信。亲爱的你,我会这样称呼。只提你,不加名不带姓。加上一个名字,就等于把你和现实世界连在一起,便平添了莫大风险和危害:谁知道你活下来的机会能有多少。因此,我只说你,你,犹如一支古老的情歌。你可以是不止一人。
你可以是千万个人。
我眼下尚无危险,我会对你说。
我会当作你听到了我的声音[4](P44)。
阿特伍德曾在其剑桥大学演讲集《与死者协商》中写道:“小说中进行书写的虚构人物,鲜有不为任何人而写的。通常就算是写虚构日记的虚构作家,也希望预设读者的存在。”[14](P91)奥芙弗雷德的声音,就是为了传递给后来者的。小说的口述构思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爱尔兰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剧作《克拉普的最后一卷录音带》(Krapp’sLastTape,1958)的启发。剧中,克拉普用录音带写日记的方式,年复一年,倾听自己过往的生活。19世纪美国的“自白派”女诗人艾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亦曾秘密地给世界写信,她相信未来会有读者认真阅读她的作品,就像使女奥芙弗雷德希望后人可以认真倾听她的故事一样。因此,小说文本中以斜体书写的“你”,既是和奥芙弗雷德从未谋面的其他使女,向她透露“五月天”的求救暗号而自己不幸罹难的奥芙格伦,也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两部小说都通过对梦魇般的极权社会的控诉,呼唤人性的自由。只不过《一九八四》中,唯有温斯顿才是秘密日记的拥有者与书写者,而《使女的故事》中,则是被压迫的女性群体在通过各种形式打破缄默,发出自己不屈的声音。
或许奥威尔一方面将希望寄托在无产者身上,另一方面由于自身思想的矛盾又将无产者表现为愚昧与盲从的一群,也或许奥威尔由于自身意识的局限而无法解决反抗独裁暴政与崇尚男性权威之间的内在矛盾,所以,他眼中的人类前景是悲观的,《一九八四》的结局因而是灰暗的。温斯顿在极刑折磨下从肉体到灵魂均全线崩溃,最终以屈服与麻木结束了与强权之间的不平等对话,真心相信二加二等于五,过起了行尸走肉般的生活,直到“等待已久的子弹穿进了他的脑袋”[5](P344)。J.R.哈蒙德由此认为《一九八四》已经“悲观到了无法宽慰的地步”[15](P177)。但差不多与奥威尔生活于同一时期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却早在1938年出版的《三个基尼》中,已经揭示出了性别压迫与政治专制、战争及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共谋关系,认为战争正是男权中心机制的产物,来自于男性对权势的渴望、对财富的贪婪和对厮杀的病态热情。因此,她号召女性成为战争暴力的“局外人”。伍尔夫对性别压迫与政治压迫机制的内在关联的剖析,深刻影响了后代众多的思想者与艺术家,阿特伍德便是其中之一。
得益于前辈精神滋养与当代女性文化新成果的阿特伍德因而与奥威尔不同,始终怀抱对人类未来的乐观信念,并坚信女性的解放和男性的解放一样,是一个与社会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紧密相连的系统工程,因而不仅塑造了女性抗争者的群像,亦塑造了一批男性同盟者,如大主教家的司机兼“五月天”秘密成员的尼克。尤其是奥芙弗雷德,较之裘莉亚,她头脑冷静、行事缜密、意志坚强、为人隐忍。漫漫长夜中,她依靠不断唤起往日生活的温馨记忆来保持理性,不断重复自己的真实姓名而提醒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通过与母亲、莫伊拉、前一任使女以及奥芙格伦等的精神维系,以及与尼克的彼此取暖而怀抱对未来的希望;与温斯顿相比,她在反抗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个人意识,没有放纵个体的欲望,没有出卖他人,没有自暴自弃,最后也没有被极权统治所吞噬。她甚至还不惜撕开血淋淋的创口,在黑暗中通过完整的口述留下了基列国的滔天罪证,保存了人类历史上一段惨痛的历史。与奥威尔的悲观主义相连,大洋国的暴政似乎坚不可摧,人类的未来似乎是无望的;而《使女的故事》中的国家机器从一开始就显示出裂痕和脆弱的特性,暴露出统治基础受到撼动的可能性。基列国的不少人仍然保留着对历史与幸福的记忆,地下抵抗组织活跃着,女性与受压迫的底层男性依然不时有着思想与行为上的僭越。小说虽留下女主人公去向不明的开放式结尾,但还是通过录音带的存在,有力地暗示了人类光明的前景。
综上,作为一部女性主义的反乌托邦小说杰作,《使女的故事》既以对极权乌托邦的深刻揭露,有力继承了奥威尔《一九八四》所代表的政治讽喻传统,又以跨越时空的对话性表达了阿特伍德对女性生存的特别关注,并在生态环境恶化的时代语境下揭示了人类生存面临的共同危机,深化与拓展了反乌托邦文学高扬全人类的自由的普遍主题。如阿特伍德所说,她尝试的是从女性角度来重写反乌托邦小说,即裘莉亚眼中看到的世界。而让裘莉亚、奥芙弗雷德们打破缄默,不仅使读者看到了极权世界的另一种黑暗,亦使我们多了观察与反思现实与未来世界的一重新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