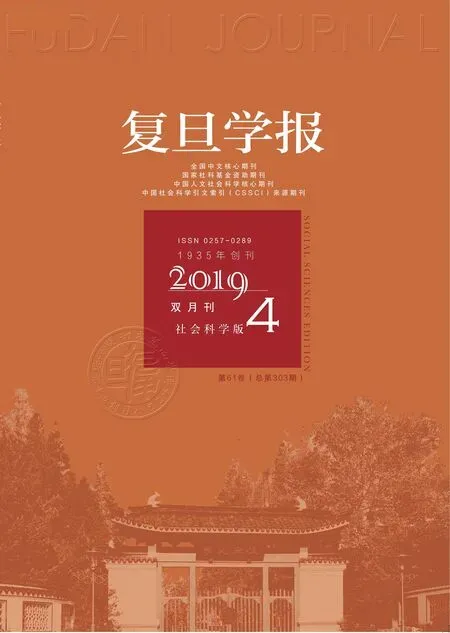《左传》繇词与早期韵体形式的产生
王汝虎
(曲阜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日照 276826)
一、 《左传》繇词的界定与意义
《左氏春秋传》中言及筮占活动且称引其为“繇”者有六次,古人多以此“繇”为“卜兆之辞”①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893、3852页。。孔颖达疏“庄公二十二年”中“懿氏卜妻敬仲占之”条言:
颂谓繇也,每体十繇。然则卜人所占之语,古人谓之繇,其辞视兆而作出于临时之占,或是旧辞,或是新造。犹如筮者引周易,或别造辞。卜之繇辞,未必皆在其颂,千有二百之中也。②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893、3852页。
现代学者多遵从古人将之视为卦爻辞或筮辞之别称,如余永梁在《易卦爻辞的时代及作者》(1928年)一文中提出:
卦爻辞本称繇词。《左传襄》二十五年,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妻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是以爻辞为繇辞。《昭》七年《左传》,“周成子以《周易》筮之,遇《屯》之《比》,其繇曰:‘利建侯’”,是以卦辞为繇辞。故卦爻等于龟卜的颂,六十四卦等于龟卜的兆象,颂就是繇词。③见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三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第96、97页。
由此余永梁言:“卦爻辞是繇词,卜辞是命龟之辞。”④见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三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第96、97页。进而他还系统比较了二者在句法上的异同,指出作为卦爻辞的繇词仿自卜辞的渊源关系。而高亨亦认为,“《周易》……卦辞和爻辞共四百五十条,四千九百多个字。先秦时代称作‘繇’,现在也叫做筮辞”。[注]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页。李镜池亦认为,“《左传》《国语》中所占之繇,跟《周易》之卦,爻辞大多相同”。[注]李镜池:《左国中之易筮研究》,见《古史辨》第三册,第117页。值得注意的是李镜池的研究范式,在《周易筮辞考》(1930年)和《周易筮辞续考》(1962年)两文中,他从文学形式上,特别是韵、散特征上,系统地比较了卜辞和筮辞之间的差异,并详细推演了《周易》筮辞的构成及演变过程,从而描述出了从散文式的卜辞到韵语式的筮辞的历史渐进过程。从用字、句式和辞例等文体和文法的比较而确立文本的时代特征,此种语言学和修辞学的视角在20世纪周易哲学美学研究史中显得尤为特殊而重要。在《周易筮辞续考》一文中,李镜池总结道:
从文学形式方面看,由卜辞的散文,到春秋时代卜筮用整齐韵语,这一长时间的演变,不特应用散文受美化韵文的影响,而且卜筮本身,也有采用韵文来写作的必要。这不光是关系于写作技巧的问题,也是文学形式的使用问题,卜辞的契刻,是记录事实,帮助记忆而写作的。《周易》的编纂,是供占筮者参考与研究用的,它的写作,最好是有系统而便于记诵的。[注]李镜池:《周易探源》,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43、149页。
今人潘雨廷先生亦对《左传》中的卜筮辞有着系统的分析与总结,在其《论〈左传〉与易学研究》一文中曾详细分析《左传》中涉及卜筮的三十四节文献,他创建性地指出:“筮书《周易》的形成与流传,与《左传》作者的巧妙安排有密切关系。《周易》能从筮中脱颖而出,亦未可忽视《左传》的若干记录。”[注]见潘雨廷:《易学史发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74页。潘雨廷先生结合汲冢书的发现,特别说明魏晋时人已经发现《周易》卦爻辞与繇辞本有不同,且后者更多地与《周易》之前的卜筮传统密切相关。
这些卜辞和筮辞作为富有口头文学意味的韵语单元,嵌入到《左传》、《国语》、《周礼》等先秦典籍中,特别是以简短韵语写成的筮辞,其雕饰和俪对的语体特征表征着早期韵语的兴起及早期语体审美观念的发生,对于探讨中国早期语言骈俪观念及形式审美的发生及其背后的历史和生活背景均极具重要意义。虽然各家对于《周易》的编著年代有着不同的认识,如顾颉刚认为其著作年代应在西周的初叶[注]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3页。,李镜池认为其写成时代在西周晚期[注]李镜池:《周易探源》,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43、149页。,陈梦家则直接以为《周易》为殷代遗民的作品,成书年代可定位“西周”[注]陈梦家:《郭沫若〈周易的构成时代〉书后》,见《陈梦家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25页。,但显然在周代,特别是在三家《春秋》的著述过程中,卜辞和卦爻辞逐渐脱离了其卜筮环境,从宗教文本逐渐变为富审美意味的文学文本。在为记诵方便的整理过程中,卦爻辞愈来愈具形式化和语言程式美感。故在卦爻辞这种逐渐“被文本化和经典化”[注]陈来认为,在春秋时期“《周易》卦爻辞脱离筮占行为而被文本化和经典化”。见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9页。,特别是被艺术化的历史过程中,关涉文类辞例和语言骈俪的形式审美因素,逐渐成为《左传》中繇辞的时代特征和文类特征。实际上,在《左传》中提到的几处繇辞,明显地更加骈俪和富雕饰意,暗涵着作者在整理和应用这些卦爻辞时文体审美意识的确证和语言形式美感的逐步程式化。
除上述余永梁文中所引用的“襄公二十五年”和“昭公七年”两条繇辞外,《春秋左氏传》中称“繇”的卦爻辞尚有下述四条[注]“《左传》《国语》中与《周易》和其他筮书有关的记载,共有二十二条。”引自刘大均:《周易概论》(增订修订本),成都:巴蜀书社,2016年,第68页。,迻录如下:
1. “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且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必不可。”(《左传·僖公四年》)
3. “孙文子卜追之,献兆于定姜。姜氏问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丧其雄。’姜氏曰:‘征者丧雄,御寇之利也。大夫图之!’”(《左传·襄公十年》)
4. “卫侯贞卜,其繇曰:‘如鱼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国,灭之,将亡。阖门塞窦,乃自后逾。’”(《左传·哀公十七年 》)[注]句读依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下同。
基于上述六条繇词的书写形式和参照其他先秦文本中所存卜筮辞,我们可以渐次讨论三个问题。
二、 “繇词皆韵”——作为早期韵体繇辞的形式价值
第一个问题即“繇词皆韵”,实涉及卦爻辞流传历史中韵散形式的逐渐区分和诗体型式的最初形成。
上引几条称“繇”的卜兆之筮辞,古人多以韵对看待,称“占辞谓之繇其法当韵”(宋魏了翁撰《春秋左传要义》第二十五),为在散文体中的《春秋左传》书写中嵌入的韵文单元。孔颖达在疏“襄公十年”条时,提出“繇词皆韵”[注]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238、3852、4734页。的观点,以“陵”、“雄”为韵;在“庄公二十二年”疏中,又言繇词“其辞也韵,则繇辞法当韵也”[注]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238、3852、4734页。,并举郭璞自称其所卜事为“辞林”,且其辞皆韵的例子,来说明郭璞习古之所在。杨伯峻亦以为“僖公四年”条中,“渝”、“羭”为韵,“莸”、“臭”为韵,且四字合韵,[注]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3页。故此条繇词亦是韵文体式。而“哀公十七年”条中的卫侯贞卜之繇词,历来争论颇多,除字义和繇词的喻象诸家有不同理解外,最关键的是对文句的句读,实关涉如何确定繇词的韵体特征。杜预注此条繇词,不同意刘炫将此繇词句读为“如鱼赬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国”,而是释读为“如鱼赬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国灭之”。孔颖达在疏此条时,则从杜预之说,其疏中认为杜预句读的合理性,实亦是基于对繇词韵文体式的把握:
刘炫以为卜繇之辞,文句相韵,以“裔焉”二字宜向下读之。知不然者,诗之为体,文皆韵句,其语助之辞皆在韵句之下。即《齐诗》云:“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王诗》云:“君子阳阳,左执簧,其乐只且”之类是也。此之“方羊”与下句“将亡”自相为韵,“裔焉”二字为助句之辞。且繇辞之例未必皆韵。此云:“阖门塞窦,乃自后踰”,不与“将亡”为韵。是或韵或不韵理无定准。[注]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238、3852、4734页。
此段疏文中“繇词之例未必皆韵”,显然与之前孔颖达所多次引用前人所言及“繇词皆韵”的观点相矛盾。顾炎武、钱大昕等人均不同意杜预和孔颖达之说,而多认同刘炫之句读。今人杨树达认为,杜预和孔颖达的注疏,其错误之处在于,“阖门塞窦,乃自后踰”中“窦”、“踰”二字为韵,这是此繇词之中的变韵,而不能说与前一句“将亡”不相为韵。杨树达在其《古书句读释例》中,直将此条疏的错误,归为“因不识古韵而误读”[注]杨树达:《马氏文通刊误·古书句读释例·古书疑义举例续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94页。的具体案例。
上述皆是从训诂学和音韵学的角度,通过分析词类和确立词位的文法学方式来确证繇词的句读和语义。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而言,在对繇词字句的训诂中,实又涉及对文体的审美本质或文类的形式特质的确证和发见。实际上,特别是在对“哀公十七年”条繇词的训诂中,无论是杜预和孔颖达,还是刘炫和顾炎武等人,虽然句读不同,但他们均承认繇词作为韵体的意义,其句读恰恰是通过文体的整体类型特征来得以确定的,而这正与西方20世纪以德国学者赫曼·衮克尔(Hermann Gunkel, 1862-1932年)为代表的圣经形式批评学派的研究思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对旧约特别是《创世纪》和《诗篇》的细读中,衮克尔认为在这些古老文本的口述和著述流传历史中,实际上融合了基于社会场景形成的不同文本单元和语言风格,并由此而逐步凝聚成不同的文类或类型。[注]参见田海华:《古克尔形式批判及其对圣经诠释的贡献》,《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4期。亦即繇辞的句读须通过卜筮辞的整体类型特征来得以确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散落的文本片段往往携带着不同时代的文化基因和生活场景,且往往隐含在神秘的卜筮传统中,为后人所忽略。
孔颖达在疏证此条时,又举两首诗歌为例。虽然其对具体字词的词性和韵部确定不同,然此处依诗歌文例而确定文本意义的思路,确可成为一种前述形式批评的重要立场。但最为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为何在《左传》中上述几条卦爻辞称“繇”,而其他二十几处所引卜筮辞则不称“繇”?如《僖公十五年》中有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条:
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注]杜预以为“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为“卜筮书杂辞”,顾炎武以为其是夏、商之占辞,杨伯峻以为“此盖其繇词”。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86页。
该条即附有卦辞而不言“繇”。朱熹亦意识到此命名问题而以为其关涉着古代易法断辞之源流,不同于前引孔颖达将繇视为颂词,朱子引孔子语以之为“彖辞”,《朱子语类》卷六十七载:
问:“卦下之辞为《彖辞》,《左传》以为 ‘繇辞’,何也?”
曰:“此只是彖辞,故孔子曰:‘智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如‘元亨利贞’,乃文王所系卦下之辞,以断一卦之吉凶,此名‘彖辞’。彖,断也。陆氏音中语所谓‘彖之经’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释经之辞,亦谓之‘彖’,所谓‘彖之传’也。爻下之辞,如‘潜龙勿用’,乃周公所系之辞,以断一爻之吉凶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谓‘大象之传’;‘潜龙勿用,阳在下也’,所谓‘小象之传’,皆孔子所作也。‘天尊地卑’以下,孔子所述《系辞》之传,通论一经之大体、凡例,无经可附,而自分《上系》《下系》也。左氏所谓‘繇’,字从 ‘系’,疑亦是言‘系辞’。系辞者,于卦下系之以辞也。”[注](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64、1647页。
显然,朱熹亦是臆测推断以“繇词”为卦爻辞,系于卦下以为观象之断辞,但其论断显然很难说服人,没有明确说明为何《左传》卜筮活动中的断辞有时言“繇”,有时不言“繇”。其实朱熹已经意识到《左传》中的繇词与普通的卦爻辞的不同,已经明确提出了卦爻辞的历史传承性与层累性问题,只不过他把这种卦爻辞的传承性归结为三圣之易,以为依次是伏羲、文王、周公三家累积而成,至于孔子而成“系辞”。朱熹以为“所以是书夏商周皆用之”:
其所言虽不同,其辞虽不可尽见,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为占筮之用。有所谓“繇辞”者,左氏所载,尤可见古人用《易》处。盖其所谓“象”者,皆是假此众人共晓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注](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64、1647页。
朱熹明确指出《左传》中所言“繇词”,是以物象来占筮吉凶,但其与普通卦爻辞不同在于其“尤可见古人用《易》处”,亦即此繇词为大众熟悉和熟知的物象与词语。当然,从现代易学研究角度而言,《左传》所载卦爻辞,不仅出自《周易》,而且出自《周易》形成之前的复杂的占卜传统。尚秉和、高亨、李镜池等人,均曾论及《左传》《国语》所引卜筮之辞,来自于包括《连山》、《归藏》在内,《周易》前史阶段中的卜筮传统。[注]见尚秉和先生《左传国语易象释》、李镜池先生《左国中易筮之研究》与高亨先生《〈左传〉〈国语〉的〈周易〉说通解》等文,参见刑文《〈左传〉、〈国语〉筮例再认识》(《国际儒学研究》第四辑,1998年)。由此我们一方面可以说“繇词”具有便于韵读的审美性和普及性,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推测这些繇词本来即是具有民间歌谣性质而逐渐经典化的历史过程。
而从文体特征上,我们其实更可清晰看到“繇词”的命名意义,如顾炎武在《易音卷》中曾断言:“古者卜筮之辞,多用音和,以便人之玩诵。虽夏商之《易》不传于世,然意其不始于文王也。”[注]顾炎武:《易音卷》,见《顾炎武全集》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56页。他直接地说明了卜筮之辞所具有的文体传承性,并且特别指出卜筮之辞“多用音和”的声律特征,而《左传》中所保存的繇词,应即是这种文体传统的最直接证据。或如尚秉和所言:“说《易》之书,莫古于《左传》、《国语》。其所取象,当然无讹。乃清儒信汉儒,而遗《左》、《国》。”[注]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第14页。顾颉刚则说得更明确,“《易》卦辞爻辞是与商人的甲骨卜辞的文句相近,而筮法也是从卜法蜕变出来的。”[注]顾颉刚:《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见《古史辨》第三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第97页。也就是说,《左传》、《国语》中较真实地保存了古代卜筮之法和文辞传统。我们以为《左传》中凡称“繇”的卦爻辞,实际是“旧辞”,是卜筮者或大众所熟悉的文词或歌谣,早已具有文学程式化意味,故语句骈俪而合韵,因而《左传》“闵公二年”中言“成风闻成季之繇”,即已“繇”、“谣”(或“颂”体)通用。明人谢肇淛早已怀疑此种繇词的来源,因时代局限且其笃信卜筮之法,故不明其为民间歌谣,如其言:“筮用《易》占,其繇不可得而闻也,不知故卜筮繇词皆何所本,如‘凤凰于飞’、‘大横庚庚’之类,似非当时杜撰也。”[注](明)谢肇淛:《五杂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5页。陆侃如、冯沅君则在其《中国古代文学简史》(1956年)一书中谨慎地推断,卜辞和金文“虽然多是散文,可以当做原始的散文作品看,可也有些很像最早的歌谣”[注]《陆侃如冯沅君合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42页。。亦有学者直言,“如果抛掉象数的包袱,删去占断词,径直从字句来揣测推敲,也许会发现某些卦爻辞可能是古谣谚。”[注]罗忼烈:《〈周易〉里的古谣谚》,见《罗忼烈杂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09页。通过前引《春秋》中的繇词,显然可以看出从散文到韵文的历史过程,从商周卦爻辞到进入周代典籍中的繇词歌谣,代表着中国诗学形体的逐步确立和形式审美意识逐渐定型。
三、 从民间口头歌谣到书面繇辞——隐在的文体传统
第二个问题即作为韵语文体的繇词与歌谣,实际关涉文学发生的本源性问题。
从文体发生学意义来说,此种极具审美意味的繇词,实际是属于包括夏商以来民间歌谣的文体传统,是中国诗歌早期文体确立过程中的韵文体式的一部分。故清人孙诒让言:“卜繇之文皆为韵语,与诗相类,故亦谓之颂”[注](清)孙诒让撰,汪少华整理:《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318页。;毛奇龄亦言:“假使得周太史者将此断文,出以韵語,即是春秋繇词矣”[注](清)毛奇龄:《仲氏易》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3页。。清人周亮工的推断更为合理,其言“或曰:《春秋左氏传》所载繇词,与《周易》不同者,盖夏、商之易,则以为有繇词也。然今莫可考证。”[注](清)周亮工:《书影》卷六,见《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3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341页。他们实际上都指出了繇词作为诗体韵语的形式本质和文体特征。明人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二中曾将“繇”与“谣”、“歌”、“操”、“铭”、“辞”、“谚”等并列[注](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见陈广宏、侯荣川编校:《明人诗话要籍汇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45页。,以为是古逸诗传统中的一部分。清人劳孝舆亦是在此发生学意义上,将繇词作为早期诗体之一种,在其《春秋诗话》中,其概括的早期十一种诗体为:“盖天籁之发,触而成声,凡有韵可歌者,皆诗也。其体凡十有一,因传所名而区之,曰赋、曰诵、曰讴、曰歌、曰谣、曰箴、曰投壶词、曰繇词、曰谚、曰隐语。”[注](清)劳孝舆:《春秋诗话》,见《清诗话三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05页。实际上,在清代之前,学者多依说文定义,将“繇”训为“籀”,音直救反或直又反[注]《说文解字》:“籀,读书也。从竹,声。《春秋传》曰‘卜籀’。”服虔曰:繇,抽也,抽出吉凶也。。而孙诒让和劳孝舆等清代学者,则显然充分认识到繇词与歌谣在文体上的相似性和同源性,故言“以繇借为谣”[注]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7页。。章学诚曾批评宋人李石《易十例略》“《诗》补遗”中所载逸诗,“与卜筮繇词并列,则不知繇词当为《易》补遗也。”[注](清)章学诚:《乙卯劄记 丙辰劄记 知非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页。繇词当然是《易》之补遗,但宋人李石的分类或并非不知繇词为卜筮之辞,他更多的是从诗体相似性上将繇词和逸诗并列。从此意义上,刘师培亦认为谣谚之作先于诗歌,其言“上古之时,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有声音,然后有点画、有谣谚,然后有诗歌。谣谚二体皆为韵语。”[注]刘师培:《论文杂记》,见《刘师培全集》第二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第83页。由此,我们亦可理解《左传》僖公五年中,当晋侯问卜于卜偃,卜偃对童谣(“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注]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39~340、1623页。)而非繇词,即在卜偃那里繇词和童谣本来即是同一体式,不过童谣重在对历史故事的演绎。此处卜筮者以童谣为卜筮之辞特喻当时政事,正说明繇词与歌谣在民间传播层次上的互通之处。
总之,从文体起源来说,繇和谣实是同源而异流的文体。当民间歌谣为卜筮者占卜时所用,往往变为具神秘色彩的繇词;而当占卜者之临时口占之韵语经记录和传播,又可流而为民间讴歌。正如陈梦家所总结的:“《易》为殷亡之后,殷学之遗留民间者,因求简易,故以筮代卜,仍沿用卜辞成语及殷代故事。当殷亡之后……卜史流为人民占卜,各有口诀相传,经后人汇集成为《周易 》。”[注]陈梦家:《郭沫若〈周易的构成时代〉书后》,见《陈梦家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25页。同样,当我们检《春秋左传》中所言之“谣”,实际上亦是为卜师占卜之时所常引用。作为韵文文体,其与繇词均可视为一种嵌入散文体式中的独立诗体单元。除上引如“僖公五年”中卜偃以童谣对晋侯条外,“昭公二十五年”中鲁大夫师己亦引用童谣,云:“鸲之鹆之,公出辱之。鸲鹆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鸲鹆跦跦,公在乾侯,征褰与襦。鸲鹆之巢,远哉遥遥,裯父丧劳,宋父以骄。鸲鹆鸲鹆,往歌来哭。”[注]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39~340、1623页。此亦是历史故事化为民间歌谣传唱,而在其后为卜师或大夫所引用为谣谶,使作为诗体的民谣带上神秘应验色彩的案例。当然汉代还保存着此种占卜之繇文体式,《汉书·文帝纪》记载,“大王报太后,计犹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李奇注曰:“庚庚,其繇文也。占谓其繇也。”颜师古则注曰:“繇,音丈救反,本作籕。籕,书也,谓读卜词。”[注]见(汉)班固撰,(清)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7页。此处汉文帝时卜筮之辞,附会夏启之事,且句式整齐,应是《左传》所记述之卜筮传统的延续。当然汉代对繇词韵文体承继和发挥最为典型的即是汉代《焦氏易林》一书,其以四言诗体形式阐发卦象,实际是一种“观象玩辞,非言灾变者也”[注](清)牟庭:《校正崔氏易林序》,见《续修四库全书总目·1055·子部·术数类》,第145页。牟庭以《焦氏易林》为王莽时崔延寿所作,顾炎武以为《焦氏易林》为东汉人所伪托,丁宴在其所撰《易林释文》中则系统驳斥二说,以为是西汉焦延寿所作无疑。。显然在这里韵文诗体成为一种独立自觉的形式意识,将《左传》中繇词体式直接视为四言诗体而加以理解和发扬。
当然,在汉代谶纬之说盛行的时代,所谓谣、谚、谶语、歌、颂等诸杂体盛行,亦往往被后世经学家视为或奇谲诡异或诙谐荒诞。[注]有人统计,汉代约有420余首谣谚,其中谣谶49首、神仙信仰类13首、志怪类10首,或可见当时谣谚与卜筮宗教的密切关系。见王轶:《两汉谣谚兴盛探源》,《古籍研究》2015年第2期。在古代经学视野里,《左传》所保存的古代歌谣因与占卜密切相关,亦经常被批评为“《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注](晋)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自序》,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127页。降及清代王夫之,在其《周易内传》卷五“系辞上传”第一章中,详叙了从上古到《左传》再到《焦氏易林》及《火珠林》以来的繇词传统,不过他对后世繇词与谶纬相结合的传统是持批判态度的,其言:
顾自《连山》以后,卜筮之官各异所授受之师说而增益之,为之繇词者不一,如《春秋传》所记,附会支离,或偶验于一时,而要不当于天人性命之理。流及后世,如焦赣、关朗之书,其私智窥测象数而为之辞,以待占者,类有吉凶而无得失。下逮《火珠林》之小技,贪夫、淫女、讼魁、盗帅,皆得以煨鄙悖逆之谋,取决于《易》,则唯辞不系于理数甚深之藏,而又旁引支干、五行、鬼神、妖妄(如朱雀、青龙之类,妖妄也)以相乱。[注]见《船山全书》第一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505~506页。
这里,王夫之亦以繇词为卜筮所系之辞,批评了后世以汉代焦延寿(焦赣)的《焦氏易林》和唐宋之际麻衣道者的《火珠林》为代表的技术占卜之书,往往以繇词待占者而逐于占象且与五行阴阳相混合而成谶纬传统,进而遮掩了帝王经世、君子穷理尽性之道。王夫之从反面指出了一种语辞传统[注]王夫之言:“盖所谓之卦者,一出于筮人,而极于焦赣四千九十六之繇辞。若以易简而知险阻言之,则三百八十四之爻辞通合于六十四彖之中,已足尽天人之变。如以为少而益之,则天化物理事变之日新,又岂但四千九十六而已哉!故赣之《易林》,诡于吉凶,而无得失之理以为枢机,率与流俗所传《灵棋经》、《一撮金》,同为小人细事之所取用,亵天悖理,君子不屑过而过问焉。”(见《船山全书》第一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678页)亦批评《焦氏易林》过于繁复、“诡于吉凶”之繇词写作形式。,即后世民间占筮者之于《左传》繇词四言体和韵语形式的继承和发挥,此可谓早期(周代之前)韵文体式的隐蔽保存渠道。当然王夫之不仅认识到《左传》中所引之卦爻辞与《周易》之不同,而且指出了《左传》中所引“爻辞”与《周易》所系之爻辞在详略、位次上亦不相同。[注]王夫之:“唯《春秋传》晋文、穆姜之占,以之卦为说,乃皆曰八,则疑问《连山》、《归藏》之法,而非《周易》之所取。其他《传》之所载,虽曰某卦之某,所占者抑唯本卦动爻之辞,且概取本卦一爻以为占,未必其筮者皆一爻动而五爻不动。意古之占法,动爻虽不一,但因事之所取象、位之与相当者,一爻以为主而略其余。” (见《船山全书》第一册,第678~679页)我们以为,如果把卦爻辞与历史故事相联系,或把一部分“繇词”看作流传于《左传》之前的民间歌谣,即把卦爻辞看作独立流传于世的韵语单元,或可解开朱熹、王夫之等人之于繇词的疑惑。
而如我们打破后世所做的通俗与神秘、民间与庙堂的人为区隔,祛除从卦爻辞以来的神秘宗教色彩,繇词与歌谣在韵文体式的发生及发展上实与后世作为经学文本《诗经》为同源文体。特别是在对谶纬之书有禁令的南北朝,此类文体逐渐被忽视而不入士大夫之视野,如《文心雕龙·杂文》中就以当时流行的“文”、“笔”观念,将“吟”“讽”“谣”“咏”等体归入“杂文之区”。所谓“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心雕龙·时序》),歌谣更多是以其政治和民俗价值得以存录。至此,繇词与歌谣一起被并入杂体之类,其意义和价值逐渐被边缘化,成为一种并无多少形式美感的文体。又如宋人郭茂倩在其《乐府诗集》中,将谣谶辑入“杂歌谣辞”类,并言“历世已来,歌讴杂出。令并采录,且以谣谶系其末云”[注](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6页。,亦不过将谣谶系于杂歌之后,不以为重。当然他受《尔雅》“徒歌谓之谣”的影响,将“杂歌谣辞”分为“歌辞”和“谣辞”两部分,又显示了其对此类文体声韵形式的认识。即使如唐代重视乐府诗歌的元稹,亦不过将此类边缘文体视为“六义之余”,其言:“诗讫于周,离骚讫于楚。是后,诗之流为二十四名:赋、颂、铭、赞、文、诔、箴、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操、引、谣、讴、歌、曲、词、调,皆诗人六义之余,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于郊祭、军宾、吉凶、苦乐之际。”[注](唐)元稹:《元稹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91页。元稹所言起于郊祭、吉凶之际的体式,即“操”、“引”、“谣”、“讴”、“歌”、“曲”、“词”、“调”八体,实际上暗含了由繇词到谣谶、诗谶一脉而来的卜筮背景和文体基因。元稹的贡献在于,他指明了这类文体的文学价值在于其声韵意义:“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别其在琴瑟者为操引,采民甿者为讴谣,备曲度者,总得谓之歌曲词调,皆斯由乐以定词,非选调以配乐也。”[注](唐)元稹:《元稹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91页。从声韵角度而言,这正是《左传》中作为韵语的繇词形式特征,由此韵语特征出发,清人冯班直接否定了南北朝以有韵无韵来区分文笔的价值观和文体分类传统,其言:
南北朝人以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亦通谓之文。唐自中叶以后,多以诗与文对言。愚按:有韵无韵皆可曰文;缘情之作则曰诗。诗者,思也,情动于中形乎言;言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咏歌之;有美焉,有刺焉:所谓诗也。不如此则非诗,其有韵之文耳。《礼》有汤之盘铭、孔子诔,《春秋左氏传》有卜筮繇词,皆有韵;三百篇中无此等文字,知古人自有阡陌,不以为诗也。[注](清)冯班:《纯吟杂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5页。(《钝吟杂录》卷四)
从文体发生学上而言,冯班抓住了“有韵”这一形式特征,实际上是以审美形式来确立文学的本质,而从南北朝时代以来把繇词看作有杂体的观念,实际上否定了繇词的诗体审美特征。当然,冯班并不能正确认识到,铭、诔、卜筮繇词等所谓“杂体”,实与后世凸显声韵的诗体同孕育于一个韵体传统和修辞形式渊源。后世能够认识到繇词此种韵语形式的,往往能够创作出与上述《左传》繇词相类似的体式,如前述郭璞所作“辞林”,又如杨维桢所撰《黄华先生传(菊)》中亦载有此种“得筮之繇”,或可说明在民间卜筮过程中,繇词四字韵语形式的传承:
先生姓黄,字华,其先日精者(《本草》菊一名日精),初生得筮之繇曰:炜炜煌煌,绿衣黄裳。德与坤恊,数用九彰。九九相仍,俾尔寿昌。佐用炎皇,起于兑之方,世爲中黄。(繇词颇有逸气)[注]载于(明)詹景凤辑:《古今寓言》第十二卷,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二五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189页。(括号内文字,为詹景凤所注——本文作者注)
再如明末清初的方以智,在其《易余引》中以繇词形式来隐晦署名,即是言“筮余之繇”,显然即是以繇词为韵体形式,且附以谜语式的宗教偈语意味。[注]方以智《易余引》:“爰有一人,合观乌兔。在旁之中,不圜何住?无人相似,矢口有自。因树无别,与天无二。章统十千,重光大渊。皇览以降,过不惑年。”庞朴先生以为前三句分别影射“大明”、“方”、“以智”,见(清)方以智撰,庞朴注释:《东西均注释:外一种》,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序言”第6页。
同样,大量的谣谶或诗谶,除历代史书和历代乐府诗集中得以记载外,宋《册府元龟》中“牧守部·谣颂感瑞”与“总录部谣言”、元人马瑞临所撰《文献通考》、明人所辑《古谣谚谶语歌诵》[注]全称为《我侬纂削七卷附古谣谚谶语歌诵五卷》,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八辑·第十五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18页。、清人杜文澜所辑《古谣谚》等中亦保持着其原初面貌,均可见这些民谣与卦爻辞和《左传》繇辞的传承关系,尤其在韵语体式、文法形态上的传承。特别是在《文献通考·卷三百九·物异考十五》“诗异”部分,其实即是汇辑从《春秋左传》开始的大量繇词、诗谶和民谣,从语言形态和体式制度上,可以看出所谓“诗异”、“诗妖”之说实际暗含着筮辞与诗歌相混同的源头形态。正如有学者所认识到的,“从诗学形态来看,谣谶与诗谶多属于‘杂体诗’,它们往往是人们利用古汉语的文字、音韵、词法、语法和修辞的特殊性而创制的”[注]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9页。。从形式批评角度而言,我们认为这一繇谣传统实际较好地保存和传承了先秦语辞体例和文体审美意识,尤为值得研究。又如逯钦立先生所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六朝前之诗歌谣谚杂辞等于一书,文献整理价值巨大,特别是对含韵文体式的诸多谣谶杂辞的著录,显示对诗体发展的精深体认。在其先秦部分分列歌、谣(附吟诵)、杂辞、诗、逸诗、古谚语六部分,即将先秦古诗分为歌、谣、杂辞、诗、谚语五大类。在“谣”体部分,虽将前论及《左传》僖公五年条和昭公二十年条分列为“晋童谣”、“鸲鹆谣”[注]见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7、38页。,惜其亦未明晰其来自卜筮繇词传统,亦未单列“繇”体条。
四、 历史中的文体样式——作为“偶辞之端”的繇词
第三个问题,由繇、谣辞的发生和发展,即可充分探究早期文体与历史文化的内在关联。
上述繇词在《春秋》中的呈现方式,实际上亦说明周易卦爻辞一方面来源于民间歌谣,有着漫长的口头历史,在历史传承过程中故事背景与历史事件逐渐模糊。王国维、顾颉刚等人均在此方面做出了奠基性的研究,如顾颉刚所著《〈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1926年)、《〈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1930年)等文,均对20世纪先秦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自不必赘述。另一方面,这些民间歌谣所具有的神秘意味,又因其承殷商卜辞,代表着早期文体的文法与修辞方式的定型化和通俗化过程。正如清人吴育为李兆洛所辑《骈体文钞》所作序中,把骈俪之文的体式和意识追溯到上古时代,其言“尧启四言之始,孔子赞《易》兆偶辞之端”[注]见(清)李兆洛选辑:《骈体文钞》“吴育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页。,虽然只是附会古人,但其将骈体文体的发展放在整个四言体式发展历史中,确实是具重要“体格有迁变”[注]见(清)李兆洛选辑:《骈体文钞》,第19页。(李兆洛语)的文体历史观。更为重要的是,吴育暗示出了与《易经》相关的卦爻辞历史与古代骈体文发展源头上的密切关系。
元人陈绎曾《文说》中曾以为彖辞、爻辞多实语而少助语:
《尚书》及《易》彖辞、爻辞,用助语极少。《春秋》、《仪礼》皆然。此实语也,凡碑碣传记等文不可多用助语字,序论辨说等文,须用助语字。[注]见《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45页。
实际上《左传》所载之繇词多有虚词助词,显出一种历史特殊性,亦可称是韵文与散文区分之开始。从现代语言学研究角度,王力先生在其《汉语诗律学》的导言部分就早已指出,在诗歌起源上,普通人所以为的先散文后韵文的观念是最靠不住的:
因为人类创造了文字之后,文化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当韵文和散文可以同时产生。韵文以韵语为基础,而韵语的产生远在文字的产生之前,这是毫无疑义的。[注]王力:《汉语诗律学》,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页。
《左传》中的繇辞在一定意义上保存着上古时期诗歌韵语的一种传统,亦可说明上古韵语发达的程度。
此一方面作为先秦文学史所要关注的问题,从前述形式批评角度而言,透过文体形式的凝固和历史的积淀,早期文体的形成与宗教、政治、文化、民俗等诸多方面有着复杂而又深刻的关系,值得深究。其研究思路及展开方式,与文化批评和历史批评等理论视角之区分,即在于承认文体形式的凝固性和稳定性,以为形式的审美最终落实为一种公共惯例与大众习俗。正如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曾提出的:判定不具卜人的卜辞的年代要依据字体、词汇和文例(包括行款、卜辞形式和文法等)来判定[注]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37页。。裘锡圭先生亦认为,“考释古文字的根据主要是字形和文例”[注]裘锡圭:《以郭店〈老子〉简为例谈谈古文字的考释》,见《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二卷·简牍帛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5页。。如果说字形是古文字研究的基础,体现着中国文字的构造和书写特性的话,那么文例和辞例就要依据于对语法习惯、语言风格和形式稳定性等诸方面来确立。在此种文本整体性的语辞体例和文体型式的确认和参证的过程中,上述形式批评或语辞批评则是一种包含于其中的文学批评视角。从文学审美的角度而言,先秦典籍中语辞和文例的考查不仅是考释古文字的工具,更应是确立早期文体和文类的形式审美和语词风格的基础,亦关涉如何理解中国文学的审美本质和韵文传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虽然形式、文类具有超时代的稳定性,然终究有着内在的发展逻辑,特殊的文类样式往往内含着丰富历史的意味与生活场景,值得后世研究者细细追绎,这亦是20世纪以古史辨派诸学者为代表的现代学术范式研究重点之所在。更进一步来说,通过上述关于《左传》繇辞的分析,我们可见出音节、韵律、结构和文体之类的形式因素,不只是文学审美得以形成的基础,更是历史与当下的连接点,历史批评和文化批评不应忽视此种形式审美的历史性,更不应脱离具体文本语句而去探寻文本之外的意识形态或历史因素。从人类学的意义而言,嵌入到《左传》中具韵文体式的繇词,实际可称得上是借卜筮仪式而得以激活的远古记忆。在特殊宗教和政治情境中展开的此种具节奏性记忆的文化片段复活着古代特殊的生活情境,因而具有特殊的文化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