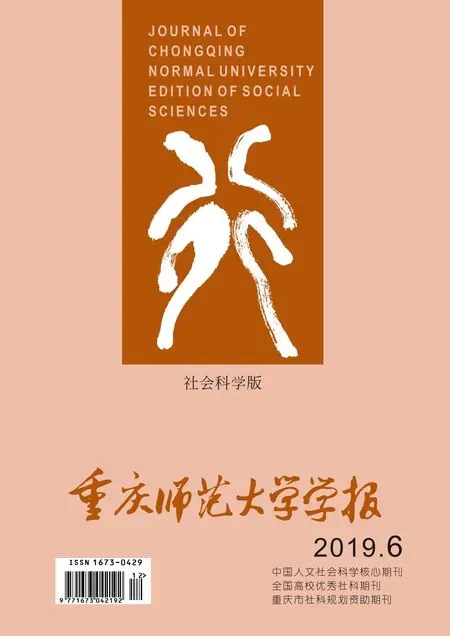“以孝治天下” :晋汉承继损益研究
赵 昆 生 肖 潇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汉“以孝治天下”,使得以“孝”为主旨的儒家伦理作为政权稳定的基础和礼之秩序重建的核心一次次被强化。此后,“以孝治天下”的礼之秩序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的表征。司马氏父子建晋代魏,对汉的“以孝治天下”因袭损益,演绎出其时特有的世风和伦理规范。
一
汉代在京城设立太学,“五经”则成为太学中的主要学习内容。其中,《孝经》也成为“经”,“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1]1719自汉代始,立冬以后,乡里“命幼童读《孝经》《论语》”[2]104。汉代官吏选拔制度以察举制为主,由郡守及中央主要官员定期向朝廷推荐候选人。“孝”与“廉”是对被推荐对象应具备的素质要求。汉武帝时与大臣议不举孝廉者罪,“复孝敬,选豪俊。……兴廉举孝,庶几成风。……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1]166-167儒家强调的维系家庭、家族人际秩序的伦理道德规范不仅仅是入仕者的基本素质,也是从政者必须具备的条件。自此,家庭、家族的伦理道德规范与政府官员的行为素质要求相一致,家庭、家族中的老幼贵贱秩序与政治统治中的尊卑等级之礼遵循特征相似。
对“孝”的道德认知也是汉代司法判断的主要内容。“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3]28东汉末,曾经的太山太守应劭“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4] 1612。汉代将儒家倡导的存在于农耕社会家庭、家族里的伦理秩序演变为维系整个统治政权巩固和运行的礼,“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5]6处在不同的社会关系节点,受制于不同的伦理规范制约,“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6] 363于是,政治伦理、社会伦理、家庭家族伦理融合为一体,指导着统治者有效地实现社会控制。其中,以孝为主的家庭、家族伦理秩序是支撑礼体系的核心要素,且得到全社会的响应。
西晋统治者在对汉代建构的社会秩序之礼深入认识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其极具时代特色的秩序观。司马懿“聪朗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7] 1,其在辅佐魏帝时就强调 :“礼,乡闾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间一相承习,卒不能改。”[8] 298重视源于乡里社会家庭家族生活之中的礼秩序。继承者司马师称 :“闻人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礼,大宗无嗣,则择支子之贤者;为人后者,为之子也。”[8] 131对家庭、家族中的长者尊者极尽尊崇。至司马昭时,“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以仁孝著称的司隶校尉何曾也在坐,遂建议司马昭 :“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9] 390司马昭时期,司马氏已经从夺取政权、控制政权过渡到改造政权的阶段,对以孝为本的礼乐制度已有自己的认知方式。
西晋初建,“共掌谏职”的傅玄总结了秦朝灭亡的原因以及曹魏历代帝王执政的利弊,上书建言 :“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7] 1319武帝采纳其建议。武帝欲诏征犍为武阳人李密为太子洗马,李密自幼父亲早亡,由祖母抚养成人,此时,李密“以祖母年高,无人奉养,遂不应命”。上书称 :“圣朝以孝治天下……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私情区区不敢弃远。”武帝允许李密奉养祖母终身,然后再出山仕官。当晋“以孝治天下”出现了家庭尽孝义务和为国尽忠矛盾时,大臣李密将二者合理地结合在一起,“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而报养刘之日短也。”[7] 2275忠孝一体,构成其时臣民道德实践的一生。即是说,在尽孝的礼秩序中,不论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甚至君主权臣都必须遵循属于自己等级、阶层的规范要求,顺从礼秩序的行为要求。
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家庭、家族为单位聚居的农耕社会,家族中的老幼尊卑关系也就是基层社会的基本人际关系,家族伦理秩序就是基层社会秩序。“夫家足食,为子则孝,为父则慈,为兄则友,为弟则悌。天下足食,则仁义之教可不令而行也。”[7] 1319家族成员的和谐关系直接影响着统治基层政权的稳定和巩固。血缘关系是家庭、家族群体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和联结纽带,在其延续过程中,感情教育和权利、义务传承自然地进行着。家庭、家族内人际关系秩序的核心是孝,孝的观念和行为解决了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代际沟通和交往方式,保障着家族群体共生共存和扩展壮大。战乱之后的汉帝国“以孝治天下”,蕴含着笼络社会成员感情、教化风俗礼仪的内容,“尊儒尚学,贵农贱商,此皆事业之要务也”[7]1319,如此,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基层不稳定问题,也由此发现了家庭、家族内伦理道德培育、伦理秩序维系等在国家政治统治层面的重要意义。
晋承继汉的“以孝治天下”,使得在以孝为代表的社会评价标准引领下,“孝”成为其时贤达首先要具备的品质。何曾“以高雅称,加性仁孝。……仕晋主太宰”[9] 390。司马炎刚称帝时就“拜太保、进爵为公、加置七官之职”的另一位重臣王祥,是元代郭守正编撰的《二十四孝》故事中“卧冰求鲤”的主人公,“其笃孝纯至如此”[7] 987。开国元老的羊祜,“武帝受禅,以佐命之勋,进号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改封郡公”[7] 1014,也是以“孝思过礼”闻名当时。这样一批以孝著称的天下名士担任政权中的高官要职,其言行本身就起着引领社会风尚、官场行为操守的作用。
晋武帝还以君主诏令等方式确立了儒家倡导的伦理纲常的法律地位。其在“责成二千石诏”中强调 :“士庶有好学笃道,孝悌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7] 57从而使儒家倡导的以家庭、家族伦理规范为主体的社会秩序之礼具有国家法律意义。其不仅是具体的,可以实施并给予评判,同时又具备抽象的观念性的意义,只要遵守“礼”,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10] 201,都是符合礼的要求。由此家庭、家族伦理与国家政治伦理相衔接,家庭、家族社会秩序与统治政权地方治安相并列,一并成为考核郡国守相业绩的硬性条件,“田畴辟,生业修,礼教设,禁令行,则长吏之能也;人穷匮,农事荒,奸盗起,刑狱烦,下陵上替,礼义不兴,斯长吏之否也。”[7] 57郡守一级的地方官员具体承担着“以孝治天下”的使命,将礼治的观念形态物化为社会治理的行为方式。礼“序上下,正人道也”[11] 95。源于家庭、家族伦理秩序之礼已经升华为一种统治理念,西晋统治者自如地运用到社会控制的方方面面之中。
代魏而起的西晋政权,在褒扬孝行的同时,又对违背以孝为主的礼秩序的行为严惩不贷。程树德先生所著的《九朝律考》中的《晋律考》,有一节 :不孝弃市。专门汇集了若干因不孝父老被惩以国法的刑事案例[12]251。瞿同祖先生认为 :“除秦、汉律外,历代的法典都出于儒者的手笔,并不出于法家之手,这些人虽然不再坚持反对法治,但究是奉儒家为正统的,所以儒家的思想支配了一切古代法典。”[13]320于是,以礼入法、礼法结合,儒家倡导的血缘伦理道德逐步地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表达出来,形成了封建专制主义君主集权特有的社会控制方式。
二
司马氏父子主宰的魏晋更替社会表现出许多光怪陆离、十分矛盾的现象 :一方面,从司马懿掌控政权开始,父子三代多次下令,认定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是指导建设国家秩序的基本指导思想,赞扬、表彰恪守儒家伦理道德的人物和行为,树立若干供人们仰慕和学习的榜样;另一方面,又对游走于社会生活各层面的浮华交会之徒和荒诞乖张的言行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探究其原因,最终则在于政治统治的考量。
司马氏父子掌权的曹魏末年,在以官僚士大夫为主体的名士阶层中出现了“竹林七贤”这样的社会活动性强的小团体,语言浮华,行为乖张、荒诞。阮籍、嵇康等“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即使到了东晋,“竹林七贤”的生活态度和范式仍被其时名士津津乐道。据东晋人孙盛撰写的《晋阳秋》载 :“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9]390阮籍等丧母仍饮酒食肉,看似与儒家倡导的丧礼大相径庭,却获得司马昭的赞许,称阮“毁顿如此”,是“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认为阮籍的行为是符合《礼记·曲礼》中有关居丧之礼的行为规定的。不仅没有违背礼教精神,反而恰到好处地表现出礼乐制度的细微之处。故阮籍“性至孝,居丧,虽不率常礼,而毁几灭性。然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仇疾,大将军司马昭爱其通伟,而不加害也”[9] 391。
司马氏父子对百官大臣是否遵守礼秩序有自己的认定方式和标准。司马氏代魏是一场以不流血为主要方式的政权更替方式,司马氏父子需要从旧有的曹魏统治集团中迅速培植一批对自己忠心耿耿的政治势力。故选择和忠于司马氏父子就是这个时期政治伦理秩序的核心,就是西晋重建的礼。在改换门庭、选择忠于司马氏的信念和行为走向确定后,其他即便在往朝被视为离经叛道,或者伤风败俗,甚至是鱼肉百姓和贪赃枉法的言行都是可以被忽略掉的。故辨别、评判官僚士大夫言行是否与政治统治的礼秩序要求一致,裁决标准不是以往的习惯事例,也不在于当朝百官大臣的责难和明文规定,而取决于司马氏父子的意愿和选择。
“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也。”[6] 481司马氏父子在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过程中,逐渐拼凑出自己的社会控制模式,形成了司马氏的统治风格。一方面铁腕整治,坚决从肉体上消灭胆敢挑衅其权威的任何势力,另一方面重塑礼秩序,在委以卫瓘大权时,下诏称 :“征东将军卫瓘,忠允清识,有文武之才。宜令宣风万里,为青州刺史,以统戎政。”[14]23忠诚不二是司马氏政治集团中对各级成员要求的首要品格,是礼秩序中排第一位的元素,决定着政治人物的生死去留。以放荡不拘而闻名于世的阮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即从不在公开场合对其时政治人物进行评价。“会帝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 。当不得不对司马昭的政治野心表达观点时,阮籍“沉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不仅及时交差,而且内容“辞甚清壮,为时所重” 。阮籍选择站在司马氏一边。因此,虽然阮籍放荡的言行激怒了众多高官贤达,但与司马氏的政治企图并不矛盾,“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7] 1361。阮籍所作所为虽然与传统社会中大众所接受的礼乐规范大相径庭,但留下阮籍一类的人物,既可以造成“竹林七贤”这样的知名群体的分裂,赢得贤达名流圈中异类人群的广泛支持,又在魏末以来的社会活动圈内树立起一块鲜明风向标 :认同司马氏父子夺取政权就是遵守现行的礼秩序。
司马氏在对待礼秩序观点上还采取“小疵”与“大德”的思路,诱使一大批前朝的贤达名流改弦更张,投奔到帮助自己改朝换代的大旗下。“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因与司马氏有姻亲关系显达于世。其高升时“将去选官,举(嵇)康自代”。嵇康写《绝交书》,公开自己的政治立场。虽不愿在司马氏手下做官,但也没有过激的反对言辞,司马氏仍可容忍。但当有大将诬告嵇康“欲助”叛将母丘俭谋反,“言论放荡,非毁典谟”时,司马氏“遂并害之”。可见,礼是为政治服务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礼,尽管他们都属于儒家倡导的伦理道德规范,但他们也跟随时代的步伐,满足不同时期统治政治的需要而不断充实其内涵。据载,嵇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海内之士,莫不痛之。”[7] 1374杀一儆百的效果立即呈现出来。贤达名流们只能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才有生存与进升的机会。“竹林七贤”中与嵇康情趣一致的向秀,见到嵇康被杀,立即赶到都城洛阳面见司马昭。司马昭讥讽道 :“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卑恭地回答 :“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司马昭于是“甚悦”[7] 1375。从此向秀官运亨通。魏晋以来随波逐流的社会名士们,在礼乐制度为当下政治服务的高压政策下,纷纷弃暗投明,集体性认可司马氏对礼秩序的重塑以及对伦理道德的评判方式。
晋武帝完成魏晋更替,在位二十五年,在此期间,曾先后数十次地以诏令形式训导天下、褒奖大臣,以推崇经学。称赞议郎庾纯“笃志好古,敦说诗书,有儒行,宜训导国子”[14] 37。征诏“处士朱冲,履行高挈,经学修明,其征为博士”[14] 38。与司马懿父子不同,司马炎时代不再是以刀光剑影迫使百官大臣、贤达名流选边站队,扩大统治集团;而是需要源源不断地为统治政权输送符合司马氏礼秩序的各种人才,于是,沿着汉代开辟的太学教育道路,按照司马氏的意志,全面、系统地培养统治政权需要的预备官员。儒家经典、儒学巨擘是太学中学习的内容和导师。其时,选曹尚书负责甄别人物,诏令“选曹铨管人才,宜得忠恪寡欲、抑华崇本者”[14]47。各州郡中正官荐举出来的三等九品人士以及在太学学满时限的人物,通过选曹尚书关口进入各级政权。魏晋以来的浮华交会之徒被阻挡在从政门槛以外,以忠为核心的政治道德品质被尊奉为入仕晋升的主要素质。
三
司马氏父子在魏晋更替的岁月里,建立和建设起一支效忠于自己的官僚队伍。司马氏除了武力镇压叛逆外,特别善于使用情感和物质手段,笼络人心。其仿照西汉初年的刘邦,大肆表彰、重赏政治军事集团中的各级军政官员。武帝于泰始六年专门下“优礼功臣诏”,称 :“昔汉祖以知人善任,克平宇宙,推述勋劳。……昔我祖考,遭世多难,揽授英隽,与之断金,遂济时务,克定大业。”司马氏对功臣人物除封官授爵以外,对他们的行为举止、品质操守也予以高度评价 :太傅寿光公郑冲等三人,“各尚德依仁,明允笃诚,翼亮先皇,光济帝业”;故司空博陵元公等二人,“才兼文物,忠肃居正”[7] 992。通过这些举措,司马氏政权营造出这个时期政治伦理道德的首要标准,即忠君。
司马氏政治军事集团在完成魏晋更替的同时,也着力于整肃内部政治风气,树立效忠司马氏父子的君主观、秩序观。吏部郎、参相国军事刘寔“以世多进趣,廉逊道缺”,遂著《崇让论》,倡导“以礼让为国”,“古之圣王之化天下,所以贵让者,欲以出贤才,息争竞也。……孔子曰 :能以礼让为国,则不难也。”[7] 491刘寔从评论魏晋以来官员选拔标准、官吏晋升方式、统治集团成员上下左右之间交往规则等入手,提出政治人物应该具备的道德观和新生统治政权应该建立的社会秩序[15]。刘寔一生基本上与西晋政权相始终,致力于统治集团内部礼秩序的建设, “尤精《三传》,辨证《公羊》……又撰《春秋条例》二十卷。”[7] 1197刘寔活了九十一岁,年迈时“自陈年老,固辞,不许。……诏曰 :……国之大政,将就谘于君。”[7] 1197刘寔之外,入主权力中枢的傅咸等一批高官,也因“以俗奢侈”[7]卷47《傅玄传》1324,不停上书晋帝,为建立以儒家伦理为主的道德规范、君臣秩序建言献策。
此后,官员的任命、将领提拔的标准,多以道德品质优先。山涛被任命为侍中,得以进入晋权力中枢,条件就在于“靖风淳履,思心通远,宜侍帷幄,尽规左右”[14] 27。任命羊琇为中护军,卫戍京师,其理由则是“明赡才具,乃心在公”[14] 27。放荡浮华之徒虽仍然行走在统治政权内外,但已经被边缘化,淡出政治中心。司马氏统治集团中的骨干力量从思想意识到言行举止,均与君主保持高度一致。
晋初分封二十七个诸侯王,镇守西晋腹心要隘。藩王不仅要治理一方疆土,握有率兵作战大权,而且还要常常听从皇帝调遣,入主中央辅政、出征边关。能够担当如此重任的藩王,品行情操尤为重要。武帝在任命扶风王亮为宗师诏中称 :“宗室戚属,国之枝叶,欲令奉率德义,为天下式。……扶风王亮为宗师,所当施行,皆谘之于宗师也。”[7] 67在任命下邳王晃为安西将军诏中称 :“益州险远,素号难治,宜以重将亲贤抚之。……(晃)清亮中正,体行明洁,才周政理,有文武策识。其以晃为使持节都督宁益二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益州刺史。”[14] 29武帝通过诏令的方式,为欲安身立命或继续建功立业的藩王立下诸多规矩,树起多个道德榜样。藩王飞黄腾达的同时必须遵守家族血缘伦理和君臣政治伦理,对藩王言行严厉限制,培养和具备既孝又忠的人格品质。
司马氏“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随着政权的巩固日益清晰,朝中官僚士大夫、贤达名流的观念意识、行为举止迅速出现了分野,相互之间的矛盾斗争也在晋统治的框架内越演越烈,斗而不破,体现了西晋王朝在司马氏允许下的包容性。一方面,阮籍等人“宏达不羁,不拘礼俗”[9]10。石崇杀人劫财仍官运亨通。另一方面,位高权重的在位官员又恪守儒家礼仪,遵循礼乐秩序。荆州刺史“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9] 11。侍中裴楷到阮籍家中吊其母丧,见阮籍“散发坐床,箕踞不器,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毕便去。或问裴 :‘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 :‘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9] 394裴楷等入主权力中枢的官员注重个人的政治形象,总是以遵守儒家伦理面孔出入私人或公开场合,自觉将自己的言行与浮华交会之徒所为区分开来。其言行代表着统治阶级中的主流价值取向和各级官吏的操守品行,因而也引导主流社会尊礼守法。这反映出司马氏父子在魏晋更替的每一个阶段,选择了汉代确定的治国方式,沿用汉儒改造而成的秩序观,使西晋社会与两汉统治产生了太多的貌合神离。
到晋惠帝时期,社会秩序稳定,饱学的儒术之士成为统治阶层中的主流。“时天下暂宁,(裴)頠奏修国学,刻石写经。……释奠祀孔子,饮飨射侯,甚有仪序。”儒家思想主导着社会思想意识,儒家倡导的纲常伦理规定着人们心中和现实的人际尊卑贵贱等阶级关系。一些当朝大儒,如裴頠等“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7] 1044遂下决心从理论上推本溯源,彻底清算嘲讽、责难儒家伦理的思潮。于是,裴頠著《崇有论》,从理论的高度、以思辨性的言词,驳斥“越名教而任自然”“有生于无”的“贵无”说词[7] 1396。
《崇有论》指出,世上“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凡是能意识到的存在都是有形有体的,“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任何道理之所以能够说服人,归根到底就是有真凭实据,这就是“有”。“有之所须,所谓资也。资有攸合,所谓宜也。”“有”是由具体的客观存在支持的,而这些客观存在又是有序地排列组合成的,总是最适宜当前社会生活的。表现在生活状态上,“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劳而后享”;反映在社会秩序上,“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志无盈求,事无过用,乃可济乎!”对于当朝者,“大建阙极,绥理群生,训物垂范,于是乎在,斯则圣人为政之由也。”而所谓的“无”是浮华交会之徒用来表现自己高深莫测、恫吓他人的虚幻之词,不可能用任何真凭实据来验证。《崇有论》的现实政治价值在于,从理论高度和深度阐释了“有”和“无”的关系。论证了“有”和“无”关系只能从现实中的具象来印证,实际生活是人们最直接的感悟和认识,“形器之故有征,空无之义难检,辩巧之文可悦,似象之言足惑,众听眩焉,溺其成说。”批判了空口谈“无”之徒用华丽浮躁、高深莫测的言语粉饰自己,在朝堂乃至社会所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去圣久远,异同纷纠,苟少有仿佛,可以崇济先典,扶明大业。”[7] 1046要摈弃这种歪理邪说,需从恢复宣讲儒家经典开始,兴起读圣人书、行圣人业之风,引导世风远离“口中雌黄”的浮华交会之徒,坚守儒家经典倡导的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断社会化的道路。
《崇有论》代表着西晋统治集团高层中企图正本清源、恢复儒家正统思想的观点。《崇有论》通过在思想意识领域论证“有”的真实和“无”的荒谬,对魏晋以来玄学思潮的“贵无”论系统地加以清理和反驳,其旨在于恢复汉代以来逐渐确定的儒家纲常伦理,进而维护君权至上、尊卑贵贱有序的政治秩序。其出发点虽然是“有”与“无”的抽象关系论争,落脚处却在正本清源、回到儒家安邦治国的社会秩序之中。
综上所述,汉“以孝治天下”的理念和方式,影响着汉朝灭亡以后魏晋统治的历史进程。在汉成功实践的经验里,司马氏父子亦步亦趋,完成了魏晋更替,这又一次统一了中国,实现了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有效的社会控制。又一次证明 :儒家倡导的理论学说,来源家庭、家族伦理道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充实和调整,已经成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巩固的政治指导思想,并在不同的朝代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和实践方式。
—— 兼论葬仪之议中的刘贺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