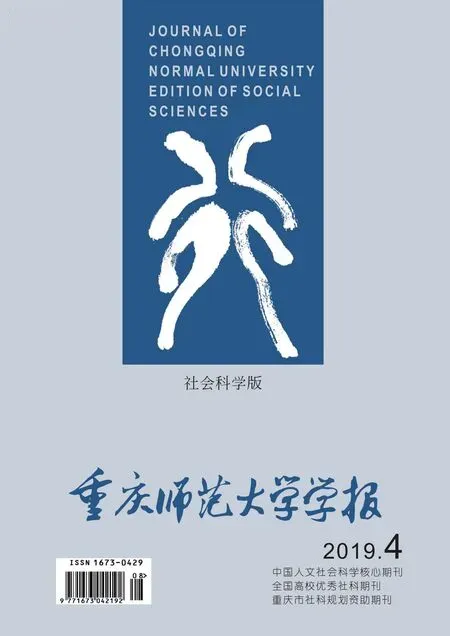新旧诗歌视阈下的杜诗学嬗变
——以吴芳吉杜诗学研究为中心
马 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102)
吴芳吉(1896—1932),号碧柳,重庆江津人,是民国时期巴蜀具有声望的学者、教育家和诗人。作为教育家的吴芳吉,从十八岁便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先后出任西北大学、东北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教授。在他的教学生涯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筹设重庆大学“以树西南风声”。吴芳吉在《重庆大学筹备会成立宣言》中探讨并解决了重庆大学筹设的人才、经费以及发展之问题[1]489,为重庆大学长期持久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诗人的吴芳吉,在民国时期表现出独特的学术立场。他对新旧文化的认识,一直是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他说:“从事文学乃终身之事,非可以定期毕业者也。吾人长愿以此嗜好文学之热忱,学习于古人,学习于今人,学习于世界,学习于冥冥,而永远为此小学生之态度。”[1]1352在新旧诗歌相互碰撞中,吴芳吉指出旧诗必须施变,但又不可“西体中用”,不能以西洋诗歌来构建中国新诗。吴芳吉论诗曰:“惟余所谓新诗,较新派之诗又有说者,吾侪感于旧诗衰老之不惬人意则同,所以各自创其诗者不同也。新派之诗在何以同化于西洋文学,使其声音笑貌,宛然西洋人之所为。余之所为新诗,在何以同化于西洋文学,略其声音笑貌,但取精神情感以凑成吾之所为。故新派多数之诗,俨若初用西文作成,然后译为本国诗者。余所理想之新诗,依然中国之人,中国之语,中国之习惯,而处处合乎新时代者。故新派之诗,与余所为之新诗,非一源而异流,乃同因而异果也。”[1]1354显然,吴芳吉的诗学观不属于保守者,从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吴芳吉就积极参与及支持,同时也发现新文化运动中的各种流弊,其中最大的流弊就是一些过分的偏激行为隔断了中国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联系。吴芳吉对古典文学的解读和研究,特别是对杜甫的热爱和对杜诗的推崇,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中国新旧文学的阻碍,使其在这一时期杜诗学研究的方法和内容上别有独到之处。
一、杜诗学研究方法
吴芳吉的作品并没有专门研究杜甫的文献,对于杜诗学的研究散见于他与朋友的信件札记、读书笔记、诗文评论,以及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中。通过对这些零散的杜诗学研究材料的整理,我们发现吴芳吉对杜诗学的研究具有内在的系统性,这主要表现在杜诗学研究方法上,吴芳吉采用传统的知人论世方法,强调研究杜诗应深刻了解杜甫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民国时期,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杜甫研究方法虽然继承了传统的知人论世方法,但又有了一定变化,从传统的考辨批判逐步发展到重视诗人生存的环境和地理特征。1922年梁启超在《情圣杜甫》中探讨了关于研究杜甫应从社会环境的角度展开,他指出:“我们研究杜工部,要把他所生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略叙梗概,看出他整个的人格。”[2]此外,1933年郑振铎在《中国文学研究者向哪里去》一文中,阐释了文学的社会因素就是时代和环境:“还该注意到这作品产生的时代与环境,换言之,必须更注意到其所产生的社会因素。”[3]312
吴芳吉很早就注意到地理环境对诗人诗歌创作的影响,他在1915年《读雨僧诗稿答书》一文中称吴宓诗风的形成与他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雨僧生长西北,关中都下,皆苦寒之地。虽时一南来,而留连不久。故其为文,朴质而少饰,此雨僧之所长,亦雨僧之所短也。以其朴质,故不免束缚于文,而不能空灵耳。……以视蜀中山水,奚啻天壤!吾不愿雨僧在文学上再下功夫,而愿与雨僧来蜀中同游,以观乎峨眉天下秀,剑阁天下雄、巫峡天下奇、滟滪天下险也。而尤愿与雨僧在嘉州少住,则西南山水可无负矣。吾知文章之精劲,当有一新境,不可测度。”[1]293同样,吴芳吉称赞杜甫在蜀中诗作具有精劲之力,主要原因是蜀中山水的影响。用时代、环境的因素去研究杜诗,自然会发现杜诗即是一部史诗。吴芳吉认为,诗是诗人建功立业之外的作品,诗人在功业之余创作的诗歌,一方面是勉励其志,一方面则是对社会史实的记载,他指出:“夫诗,功业之余也。古之诗人,不竟其功业者,而后以诗传之,其功业虽或不成,而成之以诗。使人之读其诗者,瞻望愤发,以励其志焉。此诗之为重也。子美遭安史之乱,权奸被于朝,戎马生于野,孑然一身,无以为计矣。乃寄其君国之思于诗。”[1]553吴芳吉推崇杜诗为史诗,并身体力行地学习史诗的创作,吴芳吉自言:“今后二十年间,吉所欲做之事惟二。其一史诗,其次诗史。”[1]910吴芳吉还将知人论世的杜诗学研究方法传教给他的学生,他的学生陈鸣西、杨益恒、陶嘉根、梁造今四人在1929年成都大学《文学丛刊》上分别发表了《杜甫地图十幅》《杜工部年表初稿》《杜诗地名考》《杜工部甫草堂诗年表》及与杜甫研究相关的论文,对杜诗学在民国的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
二、对杜甫思想的解读
吴芳吉之所以对杜诗推崇,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对杜甫爱国主义思想的认同。命运多舛的吴芳吉与杜甫的人生世界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是二人所处的时代背景相似。杜甫处于唐代由开元盛世经安史之乱走向衰落的转型时期,吴芳吉则经历了清朝覆灭、军阀混战的民国初期。这种动荡的社会坏境让他们比在和平盛世的诗人更多了一份敏锐的觉察感,他们对人生、社会、历史、文化有更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思考让他们的诗歌具有时代传声筒的意义;二是二人都有颠沛流离的生活遭际。杜甫自安史之乱起开始了漂泊的生活,他在成都草堂时期算是较为安定的生活时期。吴芳吉一生也因时局动荡不安经历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这种经历让吴芳吉接触到社会的最下层,所以他在诗歌创作中推崇并学习杜甫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吴芳吉有诗《曹锟烧丰都行》:
曹锟烧丰都,难为女儿及笄初。何处阿娘去,荒田闻鹧鸪。阿爷死流弹,未葬血模糊。阿兄随贼马,伏枥到边隅。阿弟独不死,伴我两无虞。离乳百余日,餐饭要娘哺。失娘怒阿姊,入怀啼呱呱。满城灰飞尽,瓦砾无人除。故居犹可识,朽木两三株。狼狈丘陇间,十日头不梳。我欲从娘去,弟幼焉所徂?我欲弃弟去,骨肉痛不舒。阿娘如已死,魂魄夜来无?阿娘如未死,念我惨何如?[1]23
曹锟于1916年奉袁世凯之命,率张敬尧等部兵入四川与护国军交战,攻陷丰都,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吴芳吉此诗描写了在丰都生活的一家人因社会的动乱而遭受亲人分离,家庭分散的痛苦。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加之地方官吏的盘剥,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吴芳吉以大量的诗篇描述了人民的深重苦难,并给予深切同情,痛斥了军阀官僚祸国殃民的罪行。他的《两父女》《儿莫哭行》《埙歌》《笼山曲》等诗篇,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勾勒出四川人民饱受战乱,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图景。在《巫山巫峡行》《北门行》《南门行》等诗篇中,他指名道姓怒斥军阀谭延闿、赵恒惕是屠杀人民的罪魁祸首。他在《长安野老行》中写道:“黄昏重国血泥糊,腿肉遭割作鲜脯。酒家人散登车去,垣头睒睒来饥乌。”[1]213一边是躺在血泊中野老的躯体,一边是豪门官吏酒终人散的场面。这种对比强烈的描绘,和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一样,既惊心动魄,又义愤填膺。他的众多书写当时人民疾苦的诗篇,多有杜甫《三吏》《三别》等名篇的风格,是他所处时代的诗史。吴芳吉说:“感情当绝对的自由,则表示感情的诗,当然绝对自由。表情的方法既不能人人相同,做诗的格调自必个个有异。……诗!不是一个学问,是一种生活的表示。依生活以表示成诗的人,叫诗人。”[1]304-309吴芳吉的诗,贯穿着他“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的写作准则,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对反动军阀的愤怒鞭挞。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杜甫忠君爱国的思想成为吴芳吉的精神食粮,读杜诗成为他的必修课,他的日记中有大量篇幅记载读杜诗之事。他将杜诗的爱国主义思想作为学习的榜样,他在《复张仕佐》一文中指出:“然学古人之诗,则必学古人为人。足下近习杜诗,当知杜公忠爱,每饭不忘君国,其人品节操,高出千古,故其诗之雄冠千古,无以加之。”[1]559他还将杜甫的爱国主义思想传授给他的学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激发他们的爱国豪情。当代学者陈光复在《白屋诗人吴芳吉与四川大学》一文中回忆了吴芳吉先生在成都大学上杜诗研究课时的情状,并指出:“他从小景仰屈原、陶渊明、杜甫、丘逢甲等爱国诗人的人品和作品,潜心学习、创作。吴芳吉担任的是六个班的古今诗歌,他选讲的首先是《离骚》和杜诗。他对杜甫生平最为熟悉,对每一首诗的背景、时间以及杜甫避乱的行踪,哪怕是一个小地方,均能详细讲述。他对杜诗研究深,记得也多。吴芳吉主张教书育人,选讲的都是富于爱国激情和民族精神的诗文。”[4]79从陈光复的记载中可以得知,在祖国危难关头,吴芳吉作为知识分子,担负起研究杜诗爱国精神的责任,并以这种精神来教育培养学生。
三、对杜诗艺术手法的阐释
首先,在诗歌创作技巧方面,吴芳吉推崇杜诗的叠字和用典。叠字运用是增强诗歌音乐效果的重要手段之一。杜甫七律中叠字运用最多且善于变化,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如:
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鱼入馔来。(《宋王十五判官扶持还黔中》)
江天漠漠鸟双去,风雨时时龙一吟。(《滟滪》)
穿化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曲江》其二)
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秋兴》其三)[5]
就这些叠字的词性而言,或形容词、或副词、或动词。就其部位而言,或句首、或句尾、或上腰、或下腰,应有尽有。明人杨慎曾认为:“诗中叠字最难下,惟少陵用之独工。”叶梦得《石林诗话》说:“诗下双字极难,需使七言、五言之间,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兴致,全见于两言,方为工妙。……老杜‘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与‘江天漠漠双飞去,风雨时时龙一吟’等,乃为超绝。”[6]
吴芳吉认为诗歌中运用叠字应学习杜诗。他在《读雨僧诗稿答书》中谈到了关于诗歌创作中叠字的运用:
律诗中喜用重叠字,亦雨僧惯性。……凡用重叠字眼,最易落俗,不可不慎。……然其运用灵活,毫不板滞,反觉用于句中,分外出色。故用之总宜自然,切勿勉强。今人作诗,往往一句不易凑合者,遂用重叠字眼,以满其数,可为大戒者也。……然如‘青山滚滚依云尽,黄叶潇潇带雨来’之句,‘滚滚’二字,能用于水,而不可形容山。皆由子美《九日登高》得来。但其‘不尽长江’亦言水也。子美《秦州杂诗》第七首,有‘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曰临关’之句,其用‘莽莽’二字,如何恰当,三四句之景,皆由‘莽莽’一句化出。下文之‘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烟尘一长望,衰飒正摧颜’,观其收局,仍与‘莽莽’一句相应,五六两句,亦由之生出。[1]294
吴宓,字雨僧,是吴芳吉一生挚友,吴芳吉曾自言:“吾,不知诗者也。吾知诗,家门雨僧兄所教也。雨僧者,吾良友而贤师也。”[1]290吴宓也曾指出吴芳吉对杜诗用心之深,吴芳吉在1921年1月19日的通信中说:“别兄五年,而杜诗批注过七部,此吉之成绩也。来湘后则多专心《楚辞》,然于杜诗仍乘闲温习之。”[1]312二人是亦师亦兄的好友,所以吴芳吉毫无避讳地指出吴宓律诗用叠字的优缺点。吴芳吉认为首先叠字的运用不可不慎,不然诗歌容易落俗,若是因为凑字数而运用叠字则是作诗的大戒。他批评《甲寅杂诗》中“滚滚”二字学杜甫《九日登高》,可惜学杜之诗只学其皮毛,没有领会杜诗的精神,“滚滚”二字能用于水,而不可形容山。他称赞杜甫《秦州杂诗》中“莽莽”二字用得恰到好处。吴芳吉对杜甫《秦州杂诗》“莽莽”二字的点评非常详细,他认为这二字贯穿于整首诗之中,是通篇的主要字眼。若不是对杜诗有深刻的研究,吴芳吉未必能够分析得如此精当。在吴芳吉诗歌创作中,他少用叠字,若用之,则尽量学习杜诗用叠字之精髓,绝不仅仅是为了诗歌的字数和形式,如“荒塚累累残劫后,征途落落篇帆开”(《夔州访古》)[1]15,利用叠字突显夔州之地的苍凉。
其次,吴芳吉认为用典不可牵强,他推崇杜诗用典,是因为杜诗用典并非将引用典故作为诗歌创作的原料,而是为了点缀诗歌。吴芳吉曰:
引用典故,为诗人通性。今人作诗,辄以典故之引用越多越为好,此亦不尽然。引用典故,宜含浑自如,不可牵强。……玉溪昌谷之诗,最喜用典。其隐僻不可探测,不似子美名贵。玉溪辈若以引典为作诗原料,子美仅以之点缀而已,且时势见地,各各不同。引用典故,最易误会。如杞人忧天之事,在我以为远虑,他人或以为愚也。总之,诗之为道,纯从天真发出,即雨僧所谓‘风雅原从至性生’也。[1]296
吴芳吉认为杜甫用典优于玉溪和昌谷,其主要原因在于杜诗用典只是将此作为诗歌创作中的一种修辞手法,不是为了用典而用典。吴芳吉在诗歌创作中也坚持将用典作为修辞手法,他说:“苟不能禁人断绝历史知识,则不能禁人不引用古事,即不能禁人不引用典故。吾人学习历史,固非寻求典故。然人情之常,见今之事有合于古人之事者,或欲援以讽喻,或以增益美趣,或使人兴乎此而悟乎彼,执其端而知其类,往往引用历史事实,或潜人语言以印证之。此典故为所用也。故此问题,非典之该用不该用,乃在典之如何去用。吾人以用典为修辞中一法。”[1]390吴芳吉认为用典不能以堆砌割裂为事,他总结出用典之要:“一曰适当,不可移动而之他也;二曰显豁,不晦涩破碎也;三曰自然,不著痕迹也;四曰普遍,不背僻也;五曰寄托,不徒逞才也。”[1]390-392这五个要点恰好能概括出杜诗用典的特点。
最后,关于杜诗中的炼句和用词,吴芳吉都高度赞同,并加以学习和模仿。吴芳吉在《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一文中,批判了胡适强行将“白话”作为评价杜诗的标准。胡适在1919年所写的日记中强调:“中国诗词常有不适(不合文法)之句,虽大家也不能免。杜甫的‘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不用说了。”[7]3关于这句诗的理解,向来说法不一,在民国以前的杜诗研究中通常将这句诗歌解释为倒装句,也有学者认为解释为倒装句有不妥之处,如唐元竑在他的杜诗注本中指出:“如鹦鹉啄馀香稻粒,可耳,凤凰栖老碧梧枝,难通矣,本应如是,非谓倒也”。民国时期,白话文运动者将“白话”规则作为评判古典诗词的标准,认为这句诗语法修辞不通。吴芳吉对杜甫的这句诗展开了深刻的讨论,他指出:“诗中之字,则以最佳之字,又有最佳之安排者也。今按此二句之字,无不安排妥善。尚译作文句,则为‘香稻啄残,无非鹦鹉之粒,碧梧棲老,皆是凤凰之枝。’鹦鹉凤凰,形容词也,非名词也。鹦鹉之粒,喻长安之富庶也。凤凰之枝,喻四海之昇平也。残,言其余也。老,言其安也。啄残,谓食之无尽也。棲老,谓居之不危也。”[1]382吴芳吉以词语活用的修辞手法来解释这句诗,接着他又找出杜诗中类似的句子:“‘思霑道暍黄梅雨,敢望宫恩玉井冰’,黄梅、玉井,以名词而状名词也。‘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风前草木兵’,关山月,虽成语,草木兵,以名词而状名词也。”[1]382他运用“以杜证杜”“以诗注诗”的互推法回应了民国期间学者对这一诗句文法的解释。吴芳吉对这句诗的解读,充分说明他对杜诗的精研细读以及对杜诗注本的掌握。吴芳吉推崇杜甫的律诗收尾有气势,他说:“诸律收尾不免太弱。凡收尾之句,其意其势其言,皆宜宏厚稳固,总勿头大尾小。子美《秋兴八首》之‘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其收结何等魄力!其与开首之‘瞿塘峡口曲江头’句,两两相应,又何等清醒。”[1]292他认为杜甫的律诗就是律诗的创作典范,无论是在表现形式和诗歌创作手法上都是值得学习的。
四、新旧诗歌下的杜诗审视
吴芳吉生活的时期正是新旧文化交替之时。1919年的“五四运动”掀起了文学革命,相继又产生了新诗运动。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强烈反对封建礼教,醉心欧美思潮在文学方面的反映。他们把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混为一谈,笼统地排斥传统,否定传统诗歌的表现手法,甚至鄙视前代的文学遗产。他们以西方现代诗歌为模式,创立一种新诗体。这种新诗体最大的特点即是自然音节,诗可以无韵,一定要用白话文创作。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传统诗歌受到冷落。胡适有论杜诗的言论,主要集中在《白话文学史》和《国语文学史》中,是以“白话文学中心论”审视杜甫诗歌,他认为:“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确是一首好诗。这诗之所以好,是因为他能用白话文写出当时高兴得很,左顾右盼,颠头拨脑,自言自语的神气。”[7]80“人们为什么爱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诸诗?因为他们是用的白话。”[7]246对于杜甫的大部分律诗则是持否定态度,认为“有点做作,不自然”[7]81。
吴芳吉的诗歌创作始于“五四”前夕,他的诗歌当然受到新文化运动影响,但他既有别于顽固派的保守者,又与胡适这样的新诗提倡者有距离,吴宓说他“于新诗旧诗作者均有褒贬,极激昂淋漓之至”[1]1331。吴芳吉深刻地感知中国诗歌要发展必须要“变”,“变之道奈何?有欲迁地另植之者,有欲修剪枝叶使勿为恶败累者。修剪之说当矣。然修剪之功,止于去秽,不足于敷荣。止于矫枉,不足于新生”[1]479。吴芳吉把植物的移栽和枝叶的修剪比作中国诗歌的变化,在他看来,中国诗歌之变应如植物枝叶的修剪,不能连根拔起,也就是说民国新诗不应抛弃中国传统诗歌之精华,而应该是在去其糟粕之后的继承性发展。吴芳吉在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最高潮之时,以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结合,他指出:“余既生于中国,凡与余之关系,以中国为最亲也。余之经验,悉中国所赋予也。余之于诗,欲以中国文章优美之工具,传述中国文化固有之精神。”[1]1042吴芳吉学习杜诗,讲授杜诗,传播杜诗,是对中国文明的传播。在他二十多年的教学过程中,杜诗是他的重要讲授和研究对象。王利器回忆在江津中学的求学经历时说:“上江津中学三年级时,吴芳吉先生来当校长。……他案头置有两部书:一是《淮南鸿烈集解》,一是《杜诗镜铨》。他每天都是要读的。我们班上和我同寝室的杜大宾同学就是从吴先生读杜诗。”[8]21吴芳吉一生最服膺杜甫,他在《赴成都杂诗》中说:“幼读少陵诗,深识少陵志。一生爱此翁,发愿为翁继。”[1]225吴芳吉用“拙”字来概括杜诗风格:“杜诗之好处在于拙,拙者忠厚之道,今人不安于拙,喜杜诗者极少矣。”[1]612他认为杜甫性情忠厚,其诗歌自然流露温柔敦厚之道,“诗之为道,发乎于性情,只求圆熟,便是上品。若过于拘拘乎声韵平仄之间,此工匠之事,反不足取”[1]292。在新文化运动中,新诗的创作受到白话文运动的影响,“诗以言情”的现象已经超越了诗教的本质,体现出肆意抒情,不加节制的倾向,这就让吴芳吉重新思考“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杜诗正是传统诗教最好的展现,所以吴芳吉专研杜诗、传播杜诗。
归根结底,吴芳吉对杜诗的推崇实际上是在新旧诗歌交替中对中国本位文化与民族文艺的传承与嬗变。吴芳吉的杜诗学研究,有“反传统”的一面,又更注重对“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吴芳吉说:“上有金碧之云天,下有锦绣之原田,中有五千余载神明华胄之少年。嗟我少年不发愤,何以对彼开辟之前贤?嗟我少年不发愤,何以措汝身手之健全?嗟我少年不发愤,何以慰此佳丽之山川?”[1]1042他以此告诫中国文化的研究不可能也不应该“照搬西方”,而应该始终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