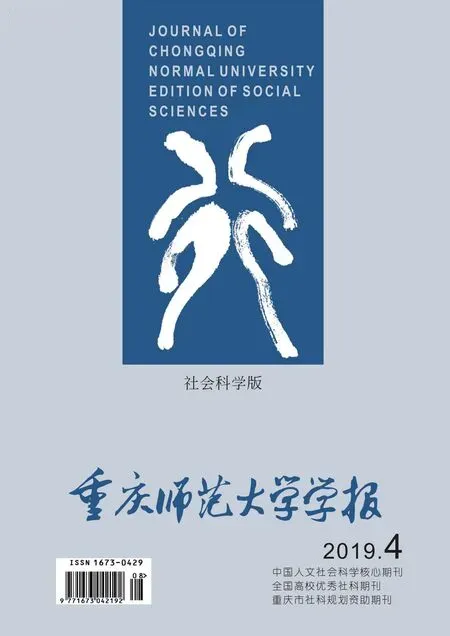为谁而写:墓志文体的书写问题考察
杨 柳
(北京联合大学 师范学院, 北京 100101)
一、为逝者而作
自汉代以来,一些墓志会在末尾处交代书写目的。如汉永平七年《马姜墓志》,“子孙惧不能章明,故刻石纪□”[1]1。北朝墓志中此类表述颇多,《魏故世宗宣武皇帝嫔墓志》云:“若功建而颂不兴,德立而辞不作,则千载之下曷闻?百代之后曷述?故简工命能,一而作是颂焉。”[1]184《郭显墓志》云:“方驰逸翰,冲天不已,霞路未央,云车遽止。清道还山,徐轩去国,寒浦邅迴,霜源眇默。石磴长芜,泉扃永塞,岸谷将迁,于焉观德。”[1]158《元祐墓志》铭曰:“吉凶不理,倚伏何常,琨峰碎璧,岱岳摧芳。星泯石户,日闇泉堂,人神同感,朝野俱伤。式述景绩,垂之无疆。”[1]108可见,墓志主要向着逝者书写,为使其道德风范不至被时光湮灭。
墓志大多采用石质材料,也正是因为金石较简帛等更坚固,更能传之久远,更契合书写者想要通过墓志书写而使志主功德传扬万代的愿望。《元郁墓志》云:“形託虚无,名寄石传”[2]2,《齐杜子达妻乙夫人墓志》:“次德金石,踰兹管弦。”[3]305《齐故东秦州田曹参军赵君墓志铭》也感慨逝者变有入无,化今成古,而“寒景不已,海岳移平”,“累累丘坟,安能长久,傥不勒石,泉门图记,遗行瞻言,万古谁得而观”。[4]可见,唯恐“遗行瞻言”会随时空转换而遗落,是作者的主要考虑。
这样,墓志书写便具有了为死者构建“公共形象”[5]的功能。曾巩在《寄欧阳舍人书》论道:“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6]为防止陵谷迁变,使死者无有所憾,墓志书写一来记事,梳理逝者一生履历,使志主的事迹能够传诸久远;二则颂美,对志主生前的嘉言懿行进行歌颂。在生命终了之时,盖棺论定,颂美其德业,给予生命最后的最大的尊重。
知其美而颂其德,是北朝墓志向着逝者而作的主要内容。如,《元熙墓志》赞美了元熙为家国大义而争战,以至捐躯逝命的崇高精神:
正光元年,奸臣擅命,离隔二宫,贼害贤辅。王投袂奋戈,志不俟旦,唱起义兵,将为晋阳之举,远近翕然,赴若响会。而天未悔祸,衅起不疑,同义爪牙,受贼重饵,翻然改图,千里同逆,变起仓卒,受制群凶。八月廿四日,与季弟司徒祭酒纂世子景献,第二子员外散骑侍郎仲献,第三子叔献同时被害。唯第四子叔仁年小得免。王临刑陶然,神色不变,援翰赋诗,与友朋告别,词义慷慨,酸动旁人。昆弟父子,俱瘗邺城之侧。孝昌元年追复王封,迎丧还洛阳,赠使持节大将军太尉公都督冀定相瀛幽五州诸军事冀州刺史,谥曰文庄王,增封一千户。二宫悲悼,亲临哀恸,行路咨嗟,莫不挥涕。孝昌元年岁次乙巳十一月壬寅朔廿日辛酉葬于旧茔。爰命史臣,勒铭泉室。其词曰:宝箓凝图,五灵代纪,金行弛御,玄符继起。维祖维宗,乃疆乃理,腾周越汉,跨虞迈似。赫赫景皇,本枝孙子,献武隆蕃,令问不已。猗欤君王,时维?哲,玉润金晖,霜明冰洁。兰芬月朗,渊鉴景彻,孤心独秀,怀贞秉节。敬让既敷,像而不设,惠结甘棠,声徽往烈。诚深体国,闻难投戈,义感君子,赴者讴歌。捐躯逝命,死也靡他,忠谟不遂,运矣如何。慷慨临危,咨嗟中圮,宿志既申,无惭昔士。赫弈宠光,名芳图史,勒铭玄宫,式彰来美。[1]170-171
于穷途末路之时,元熙又表现出极为沉稳、淡定的气象:“王临刑陶然,神色不变,援翰赋诗,与友朋告别,词义慷慨,酸动旁人。”颇为悲怆、动人,富于崇高美、悲壮美。《张彻墓志》则颂赞其“轻财重气,殉节忘躯”,志文云“按釰直驰,先登致殒”,乃是指拔陵败北魏军于五原,张彻阵亡。[2]44
有时,所纪念亡者之德行,并非关乎家国的大事,而是表现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如《处士中山甄凯墓志铭》:
凯字义矩,小字季良,司徒文穆公之第四子也。生资秀气,幼挺奇标。自有识能言,无游辞失色。尤机警,辨悟过人,纤微必察,应对如响。在儿伍之中,见者莫不敬异。文穆公特垂赏爱,以为类己。年方龆龀,业深致学,因心独悟,师佚功倍。既敦坟史,兼好词翰,芳心令质,日就月将。而遭命不幸,夙婴笃疾。降年一十有四,以正始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病遂大渐。时太夫人亦枕疴绵棘,弥留积祀。季良自识将危,不悲天命,唯以太夫人寝疾为言,因而绝气。初文穆公以其久病羸痼,忧念过甚。季良常相宽解。未图当困,一朝不救,内外摧伤。太夫人悲哀感动,寻亦薨背。公愍其短折,即其孝心,权令与太夫人同坟共殡。自云:百岁之后,终与吾儿相从。正光六年正月丙午朔二十七日壬申,良之诸兄奉安公夫人之宅兆,仰遵先旨,厝良于墓后别室。永寻二三,触情荼苦。府仰号迫,无思为铭。略陈影响,以照泉路。玄闼一扃,呜呼毕矣。正光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壬申刻。[1]161-162
志主季良年仅十四岁便因病去世,在其极为短暂的一生中,自然难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义举。但此志文尽管非常朴素,却颇为感人,一则亲情浓郁,令人感动,母子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都流露出浓厚的真情;二则写出了志主年轻如此,却能坦然面对生死,“自识将危,不悲天命”,展现出生命的从容,而“唯以太夫人寝疾为言”,又显露出相当的孝心。
《礼记·祭统》云:“铭者,论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夫铭者,壹称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观于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为之者,明足以见之,仁足以与之,知足以利之,可谓贤矣。贤而勿伐,可谓恭矣。”[7]746-747墓志铭文的书写,正是对此义的践行,虽然“铭”的形式不同,由铭于鼎而变为铭于志石,但子孙彰明其先祖之“美”,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令先祖之嘉言懿行传诸后世的动机是一脉相承的。
某些时候,不仅因为时空的变迁,还因为种种复杂的政治社会原因,一些风云人物的形象变得模糊,赫赫功绩被淹没在历史洪流中,无从追寻,这时,唯有墓志能起到记录,甚至申述和剖白的作用。如,元遥生于献文帝皇兴元年,卒于孝明帝熙平二年,作为三朝元老,元遥建立了辉煌业绩,也遭遇了诸多变故与坎坷,见证了北魏后期政局的动荡纷争。而在《魏书》《北史》中,关于元遥的记载颇为简略,其在孝文、宣武帝时的辉煌业绩被一笔带过。《魏书》本传仅载:“(元) 遥,字太原。有器望,以左卫将军从高祖南征,赐爵饶阳男。世宗初,遭所生母忧,表请解任,诏以余尊所厌,不许。肃宗初,累迁左光禄大夫,仍领护军。迁冀州刺史。”[8]445《北史》与之略同。史家甚至还张冠李戴,将宣武朝发生的事情移植到孝明朝。对此,论者以为,“不能把它简单地归结为技术问题,潜藏的政治意图才是根本”。究其根本,因为元遥是宣武帝宗室政策典型的受害者,其所遭遇的不公正对待,引来了为之鸣不平的声音,连孝明帝也“伤公巨效之未酬,慨公往而不待”,给予特别追赠以作补偿。因此,北魏史官在编撰国史时把元遥的遭遇彻底抹除,以规避政治风险;同时为防止产生强烈的对比效应,挑起读者的疑窦,连带着将其孝文朝的功业也一并掩盖。[9]唯有《元遥墓志》[1]93存录了其功绩,使其不至于被官方历史书写所遮蔽。
《元诱墓志》则对元诱、元熙兄弟的冤情进行了申述:序文云“属今上富年,权臣执政,其兄太尉虑社稷之倾危,建义节于邺城。良规密谋遥相知和,忠图不遂,欻贻滥酷。以正光元年九月三日薨于岐州,春秋卅七。捐珠之悲既切,罢市之慕逾酸,虽复冤耻寻申,而松槚方合。”铭文又云:“将隆国祉,驷马高车,忽降淫祸,归神大虚。冤申宠洽,筮令龟从,沓墙柳,铿锵鼓钟。风摇宿草,雾蔼寒松,年茂虽远,芳彩终浓。”[1]171-172元纂也因支持元熙而枉死,《元纂墓志》铭文云:“诞性冲和,渊清岳峙,仁义方远,何为衅起。衅起伊何,于国之机,高松折彩,素月沉晖。日华霜劲,兰辰雪飞,声留泉石,体与化辞。”[1]175元熙之子元晫亦见屠覆,其志载:“年十八,随父太尉镇邺。俄而权臣擅命,离隔二宫,旦奭受害,仁人将远。太尉责重忧深,任当龟玉,欲扶危定倾,清荡云雾。君忠图令德,潜相端举,有志不遂,奄见屠覆。父忠于国,子孝于家,既毙同剖心,亦哀逾黄鸟。”[1]176《元怿墓志》亦同此。元怿辅政之功同于周公,而为元乂、刘腾等奸凶所害。墓志用了不少文字来叙述这一悲剧:“而运遘时屯,恶直丑正,衅起不疑,为奸凶所劫。神龟三年岁次庚子,春秋三十有四,七月癸酉朔三日乙亥害王于位。遂隔绝二宫,矫擅威柄,四海能言,莫不悲恸。咸以哲人云亡,邦国殄悴。”为突显其冤情,志文还叙述到“自此灾旱积年,风雨愆节,岁频大饥,京师尤甚”[1]172。这都是通过墓志书写为亡者申冤,说明墓志书写有较大的自由性。公开的官方书写有所顾忌的时候,墓志起到了申述的作用。
还有一些卑微的小人物及其所属的群体,在官方书写中,自然是不可能占到只字片语的,但墓志却为我们存留了他们曾经鲜活的身影,弥足珍贵。北魏正光元年《刘阿素墓志》记:“同火人典御监秦阿女等,痛金兰之奄契,悲红颜而逃年,乃刊玄石,述像德音。”[10]“刘阿素”“秦阿女”之类极普通的名字以及“典御监”的身份,阿素因家难而入宫的身世经历,呈现出来的是一个颇为卑微的令人同情的生命。在其身后,伙伴们“痛金兰之奄契”,共同为其刊刻墓志,又显露出同是低微之人惺惺相惜的可贵情谊,令人感动。黄永年先生认为,“碑志之性质价值,大体与史传相埒,以显达身后必有行状,史传、碑志多本行状撰作。然史传止传有关系人物,碑志所述人物事迹之不见史传者何可胜计。又史传所记往往省略,而碑、墓志所记乃转见翔实。”[11]的确,从墓志书写来看,有时被书写者并非什么可以载入史册的重要人物,但在墓志书写中,他/她却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角,其名字契刻于金石之上,传之久远,千百年后,读者依然可以藉此而去感受一个个或不凡或庸常,然都有血有肉真真实实在世上生活过的生命,显现出墓志书写者对于生命本身的关怀。
二、为生者书写
《礼记·祭统》云:“古之君子论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国家如此。子孙之守宗庙社稷者,其先祖无美而称之,是诬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传,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7]748可见,铭文(包括碑志)书写不仅是向着死者书写,它也与死者的子孙有着密切关系。既是如此,书写者必然会将生者的某些心理需要纳入考虑范围。
以北朝墓志为例。墓志向着生者而书写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表达生者对于逝者的情意。虽说北朝墓志有不少程式化的写作,但其中也有不少是为着抒发真情而写。如,李德林为其生母赵兰姿所作墓志:“德林父兄早弃,夙婴荼蓼,姊妹及弟,茕然靡托,寔赖慈育,得及人伦。光景如流,瞻望日远。几筵永绝,温清无期。徒深衔索之哀,空有终身之慕。”[12]379李德林早年丧父,姊妹兄弟茕然靡托,实赖慈母含辛茹苦,方得成人。而光景如流,为人子者不及尽孝养之情,而“几筵永绝,温清无期”,作者因而充满愧悔和深深的遗憾:“徒深衔索之哀,空有终身之慕”,一个“徒”字、一个“空”字,传递出生死两隔,尽孝不能的深深无奈。据《贾瑾墓志》,志主贾瑾卒时未婚无子,兄胶州以第二息晶为嗣,而晶亦在廿一岁时去世。胶州为叔侄二人作志,悲痛不已:“痛弟息之早终,悲志业不遂,惟缘情以折中,述二亡之存意。故二柩而一坟,乃镌石而作志云尔……”[1]282隋开皇十七年蜀王杨秀为其爱妃董氏所作墓志则主要表现夫妻之间难了的情缘:
比翼孤栖,同心只寝。风卷愁漠,冰寒泪枕。悠悠长暝,杳杳无春。落鬟摧榇,故黛凝尘。昔新悲故,今故悲新。余心留想,有念无人。去岁花台,临欢陪践。今兹秋夜,思人潜泫。[13]47
作者向着亡妃倾诉衷肠,百般柔情,融化在“去岁花台,临欢陪践”的甜蜜追忆中,万分悲伤,则化为了“风卷愁漠,冰寒泪枕”凄凉意象。细节的描写,显现出感情抒泻的真实,颇为感人。这种叙述,毋宁视为一封缠绵悱恻的最后的情书。北齐《张肃俗墓志》铭词则发抒同气之深情:“白杨云聚,丹旐风生,足兴悲于行路,况同气之深情。”[12]167《王诵墓志》铭文作者抚军将军顿丘李奖,也在铭文中表达了身为同侪对志主才性的嘉赏,对其离世深感悲痛,志文“昔忝光禄,及子同官,玄冬永夜,耳语交欢。奠案不食,实忘饥寒,愿言思此,痛切心肝”[1]243,深情回顾昔日亲密交往,真情流露,哀婉动人。
在重重叠叠,几乎极致化的哀感书写中,生者的心中情意得以抒发,死亡带来的悲伤感受也得以疏泄。文学安慰、治疗的作用得以凸显。
其二,通过家族叙事,追源溯流,来加强生者的族属认同。如,《郭肇墓志》:“其先稷佐陶唐,姬文受命”,铭文曰:“履迹开原,膺符受命。瓜瓞绵连,本枝郁映”[2]94。这种家族叙事,一方面是借以确定志主的身份,另一方面,也有着向生者而书写的意味,可藉此梳理家族源流,加强族属认同。《魏故使持节安北将军恒州刺史墓志铭》追述了志主家族本为“绵枝辽右,世董番邦”的慕容氏,因时势变易“归诚改姓”的曲折经历,墓志着力叙述该家族源远流长,不管是在燕还是在北魏,都显赫隆昌:
绵枝辽右,世董番邦。埋根百刃,抽干云峰。敷仁累叶,修德遐踪。式遵两仪,氏曰慕容。为燕文明,六世大宗。膺图纳玺,受历黄龙。鸾飞幽岳,凤起山东。追尧盛轨,慕舜成功。淳风远洽,九土咸同。五运中移,宝祚迁政。符瑞有归,本枝犹盛。中山广固,再隆大命。五世始安,弼燕廓定。导以六德,华夷改听。如伊在殷,明超水镜。如旦翼周,民慕其行。入秦作辅,移魏加敬。高祖章武,道风遐映。避难密谋,归诚改姓。入列三槐,出镇作屏。恩齐冬日,威逾霜劲。唯机其神,独播斯令。[14]
至于其“归诚改姓”,也未被视为失节之举,而是堂而皇之地记录了下来。在多民族的文化背景、多战争、离乱的社会背景中,这种族属认同自然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有助于个体找到归属感,也有助于一个家族、一个民族来整合各自的力量。
其三,墓志书写极力夸赞志主及其先祖辈的丰功伟绩、道德文章,生者可藉此光耀门楣,甚至作为其出身的资本。这是北朝门阀制度对墓志书写必然产生的重大影响。
《李礼之墓志》将其先祖追溯至汉代李广、李陵,其六世祖李暠为西凉开国君主、四世祖李宝帅众归附北魏,自此家声日盛:
君讳礼之,字延州,陇西狄道人也。其在汉世,李广、李陵并为名将,著于前史,丞相蔡君之先也。及永嘉失驭,晋室迁流,六世祖暠,遂霸河右,专主征伐。四世祖仪同宣公宝以魏德广披,迁居中土。自兹已后,家声日盛,青紫相袭,轩旆成阴。汝南人物之乡,襄阳冠盖之里,不能异也。[15]
北齐河清元年《库狄回洛墓志》载:“王讳洛,字回洛,朔州部落人也。大□长公之孙,小酋长公之子。王禀资灵岳,启质悬星,随运匡朝,应时赞世。传(傅)说之翼高宗,吕望之辅太祖,年代虽殊,人何优劣。鸿源与带地均长,隆基与于天比□。石氏一门万石,杨家四世五公。物论愧其勋朱,有识多其冠冕。”[1]414志主为朔州部落人,乃北方少数民族,但如中原世族一样,也着意称颂门第,且云“石氏一门万石,杨家四世五公。物论愧其勋朱,有识多其冠冕”,颇有与中原汉族第一流高门相较高下的意思。
墓志中甚至出现伪托大族出身以自高门第的现象,可见门第观念在其时社会生活中占据何等分量。东魏天平四年《张满墓志》记载:“君讳满,字华原,南阳西鄂人也。汉相留侯之苗裔。”[1]324据史载,张满乃代郡人,且“语通书革之国,言辨刻木之乡”[16],当为临近少数民族聚居地的代郡人,甚至有可能就是出身少数民族。但在其墓志中,郡望成了“南阳西鄂”,出身为“汉相留侯之苗裔”,这样书写,当是因为南北朝之际,南阳张氏颇为显赫。而据《窦兴洛墓志》,活跃在东魏、北齐的窦氏,自称扶风郡望,但实际上应是北魏孝文帝实行改汉姓政策时鲜卑纥豆陵氏所改的代北窦氏。[17]
研究者注意到,北朝墓志中世次书写呈现出复杂的状况,世次叙述方式各有不同,有的按次序叙列,有的似乎较为随意;有的仅叙直系亲属,有的叙及姻戚或其他旁系亲属。而在经过仔细分析之后,研究者也发现,在这看似纷繁复杂的世次叙述背后,有其共性,“即墓主的家世对墓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在家世之中,世次则为首要内容;官爵和勋绩又为世次中最重要的内容”。而这种状况的出现“必与北朝特定的礼俗制度相关”[18],具体而言,即是北魏孝文帝定姓族的政治举措。(这种世次的梳理,固然如论者所云,对于确定志主的身份很重要,但不言而喻的是,对家族门第、荣耀的彰显,也可作为生者,即志主的后人出身进阶的资本,带来实际的好处。)
其四,墓志书写中,有时亦见大力显扬生者的孝行或其他的品德。
书写志主后人的哀伤,夸赞生者(多为孝子)孝行,也是北朝墓志书写中的常见内容。这种书写有一定的真实成分,但不可讳言,应也有相当的夸张。而凸显生者孝行也与北朝时期对忠孝之道,尤其是孝道的提倡,有密切关系。如,《郭定兴墓志》在对亡者盖棺论定的同时,花了不少笔墨赞美亡者的弟弟郭安兴:“弟弩将军、永宁、景明都将,名安兴,智出天然,妙感灵授,所为经建,世莫能传”,郭安兴为北魏土木大匠,设计了营造北魏大型佛寺永宁寺。正是他主持安葬其兄,铭文中又再次强调他的明敏、天授特禀,以及友于之情:“睿弟明敏,特禀天授,钦泣友于,情礼光究。敬铭榇前,千载垂籀”[12]91。
亡者的后人,既是墓志书写的操办者(或亲自捉刀,或托人代写),又是墓志的被书写者,同时,还是墓志的阅读者、鉴定者。这样一种身份,也会影响到墓志写作。书写者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孝子的心理列入阅读期待之中。如,欧阳修《与杜论祁公墓志书》云:“平生知己,先相公最深,别无报答,只有文字是本职,固不辞,虽足下不见命,亦自当作。然须慎重,要传久远,不斗速也……修文字简略,止记大节,期于久远,恐难满孝子意。”[19]1020
三、撰者的自我书写和为未来读者的书写
撰写者的自我书写,也是墓志书写中常出现的内容。墓志书写是直接面对生命、面向死亡的书写,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书写者或多或少会在其间有对于自我的书写。
一方面,发抒对于时空的感怀。站在生死的分界点上,书写者对于熟悉的时空,也会另有一种感受。日日埋首其间,岁月似乎静好,而死亡却似乎一个可调焦的镜头,可将人与当下时空的距离拉远,让人看到,沧海可以化作桑田:“罗山忽其浮海,大壑屡作犁田”[3]147。而人的生命短促如许,生死仅在一线之间。魏故处士《王基墓志》云:
哲人既徂,有识同嗟,遂使弦歌遏而无向,痛音扬而成韵。粤四年十月甲寅朔廿日癸酉窆于洛阳城北首阳之山。金门昼奄,修夜无晓,铭德黄泉,传芳世表。乃作铭曰:二仪丕绪,四像垂灵,翩翩神,降卵而生。祥应唐墟,庆震皇京,修哉今古,介祉恒明,其一堂堂盛貌,穆穆神仪,三德剋融,六艺唯熙。霜翻兰叶,风摧桂枝,丝言日远,殊章永离。其二离弦遂往,坠雨不归,逸翮未穷,遥途有期。风悲塞草,气咽寒飔,千秋万岁,往矣难追。其三白杨耸杆,崇嵑僬侥,窀穸長昏,有日无朝。玉质沉壤,蕙气陵霄,铭思泉石,流悲冀遥。其四[1]139
以上所引,是此墓志的主体部分,核心内容即在志哀。尤其是第二、三、四段铭文,把“悲感”书写到了极致。霜翻兰叶、风摧桂枝、玉质沉壤、蕙气陵霄,以喻美好的生命被死亡无情地掳去;丝言日远、殊章永离、离弦遂往,坠雨不归,逸翮未穷,遥途有期、窀穸長昏,有日无朝,以喻生死永隔。铭辞中运用了密集的意象,层层叠加,而倍增哀感。这种悲感书写,与其说是向着具体的逝者而发,莫若说是作者关于生死的自我书写。又如《隋故西胡酋长安氏墓志铭》:
君讳寿字天生,西域胡酋,安息国王之苗胄也。昔汉武之年,远修邻好,朱轩皂盖,代有其人。君天纵多能,术兼文武,风彩秀异,少拔群流,岂图势若空云,命均旋火,大业未成,奄从物化。享年卅有八,终于此土。今以大隋开皇一十五年岁次乙卯九月丙辰朔廿九日甲申,葬于紫陌河阳六百余步。泉门昼奄,户钥长閞。垅树从新,幽魂日远。乃为铭曰:
人无百年,义在临川。气随云雾,势逐风烟。府罗虚灵,仰缀啚天。日同夜后,月似中前。千龄寝庙,万岁孤坟。惭言雍子,能泣田文。阶前梦草,垅上浮云。荒□靡记,谁复知君。[20]
书写者一方面抒发对亡者的悼念,一方面又跳出来书写对生命本身的感怀。气随云雾,势逐风烟,人生显得格外短暂、缥缈、虚无,这里的时空意识显得既通达又悲观。而在序文末句和铭文大部分铺就的巨大悲剧氛围中,“谁复知君”的慨叹尤其富于悲感。此种悲感,既为逝者而发,亦可谓作者向着自己说话——墓志的书写,亦令其站在自己的对岸,来看待自己的生命。
这样一种对死亡的观审,也引人对现实人生进行反思。在墓志书写中,抒发对人生的感悟,也多有所见。隋大业十年《明云腾墓志》序文开头:“夫岷山称固,犹有塞江之崩;溟渤云深,尚致桑田之涸。况乎摄生于橐钥之间,以隙驹方其促;禀身于虚幻之中,用石火齐其短。是以宣尼上圣,无离逝水之嗟;阮子下贤,讵免途穷之苦,怆矣哉,难得而言者焉。”[13]326这样一长段文字,固然是因逝者而发,但却充满了书写者的个人感怀,若将其从墓志中抽离出来,自可成独立的人生小品。有时,书写者会在铭辞部分集中表现自身的人生感悟,甚至将其写成人生哲理诗。北魏永安元年《元诞业墓志》:“夫理归必至,去来常然,所恨秀而不实,兰芳□□。”[21]
总体而言,北朝墓志中,对死亡的认识相当理性,一般都是确认人死形灭,既不思虑死后灵魂的去处,也并不关心来世,大量的志文都在表现对死了就是死了的这样无可置疑的事实的认定与接受,或是表达对形名关系的思考。死亡,毫无疑问意味着形体的消亡,则生命的意义所在?《元郁墓志》云“形托虚无,名寄石传”[2]2,《元遥墓铭》:“形随道灭,名同岱嵩。”[1]94显然,书写者在表述自己对生命存在意义的认知:其结论是,生命之意义乃是藉声名影响而得以延续,而《闾详墓志》却又否定了死后声名的意义,认为“泉扃一奄,名识虚游”[2]100。
墓志书写中还有比较特别的自撰墓志铭,就更是作者直接的自我书写。《魏书》卷十五记载,元景自撰墓志铭曰:“洛阳男子,姓元名景,有道无时,其年不永”[8]252,表达对自己生不逢时、命短年促的无奈悲叹。《北史》记载李行之临终口授墓志:
临终,命家人薄葬,口授墓志以纪其志曰:陇西李行之,以某年某月终于某所。年将六纪,官历四朝,道协希夷,事忘可否。虽硕德高风,有倾先构;而立身行己,无愧夙心。以为气变则生,生化曰死,盖生者物之用,死者人之终,有何忧喜于其间哉!乃为铭曰:人生若寄,视死如归。茫茫大夜,何是何非。”言终而绝。[22]
墓志系亡者生前自撰,人之将终,其言也善,这种墓志颇多真情实感,可谓是积累了一辈子的人生感悟,感人至深,又发人深省。
值得注意的是,墓志书写中,有时还会出现双重叙述的现象。比如《元郁墓志》出现了书写者和被代言人的双重叙述。该志叙述口吻在铭文中间部分发生了变化:前半部分,是以他者口吻叙述志主元郁的出身及勋绩,中间换作了孝子口吻:“幼丁乾毒,长罗母辛。其辛伊何?痛骨切筋。其切伊何?兄弟早眠。天地无识,唯留罪人。棺东独立,辛形一人。岂报父母,孤孤亟亟。呜呼哀哉,痛贯苍旻”,表达幼丁乾毒,长罗母辛,又兄弟早亡的心酸,以及报恩不及的悲痛,据上下文推断,应为祠子安明的语气;紧接着,又换作了他者叙述,颂赞元郁之王妃慕容氏:“燕国休胤,遗枝茂实。成武之孙,摇华魏术。育斯淑妃,婉然令瓆……”[2]2-3
墓志书写中,时空常常是混茫、悠远,充满变易的,人事代谢,沧海桑田,是死亡书写常常出现的内容。而“坟无晓日,地有重开”之类的句子,也常常出现在墓志中,表明书写者有着对墓志未来阅读的期待。如《故魏直寝将军孟公墓志铭》,铭曰:“……寞寞长夜,杳杳深泉。谁言在后,谁在于前。掩扉今日,开更无年。痛抽心髓,叩地号天。迁移东海,可覆西山。神躯永别,叵见慈颜。(似乎不应作叵)坟无晓日,地有重开。遗风在石,刊记辞还。”[3]145魏故处士《王基墓志》铭文其四:“白杨耸杆,崇嵑僬侥,窀穸長昏,有日无朝。玉质沉壤,蕙气陵霄,铭思泉石,流悲冀遥。”[1]139《叔孙公墓志铭》:“叹九原之不归,悲仁贤之长逝,写芳尘于玄石,扬不朽于远世。”[1]366《魏故武昌王妃吐谷浑氏墓志铭》:“妃吐谷浑国主冑胤,安西将军永安王斤之孙,安北将军永安王仁之长女,太尉公三老录尚书东阳王之外孙。魏建义元年七月三日,薨于崇让里第。粤八月十一日迁期同窆王陵。实亦痛感有识,哀惊朝野,思铭德音,用贻来叶。”[1]245北魏《元郁墓志》甚至对墓葬品的未来去处,都作了安排。志盖上记着:“仰为亡妣用紫金一斤七两造花冠双钗,并扶颐,若后人得者,为亡父母减半造像,今古共福,安不慕同。”[2]2“若后人得者”,说明对墓葬的未来有过设想,葬家考虑过为亡妣用紫金一斤七两所造花冠双钗并扶颐的未来去处,嘱咐得者“为亡父母造像”,且祝福得者“今古共福”。这种对墓葬未来的设想早已有之,不过多以神秘化的预言方式(谶语)出现,而《元郁墓志》则表现得比较理性。
这种对于墓志的未来阅读的预期,无疑也会影响墓志的书写。书写者会考虑刻于志石上的文字要传于久远,必须能接受历史的检验,因而在书写时可能更为慎重。欧阳修《再与杜论祁公墓志书》谈道:“平生知己,先相公最深,别无报答,只有文字是本职,固不辞,虽足下不见命,亦自当作。然须慎重,要传久远”,又云:“或择一真楷书而字画不怪者书之,亦所以传世易晓之意也。”[19]1020-1021此即谈到,考虑到传之久远,墓志书写必须慎重,又为将来人阅读方便,书写应当明白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