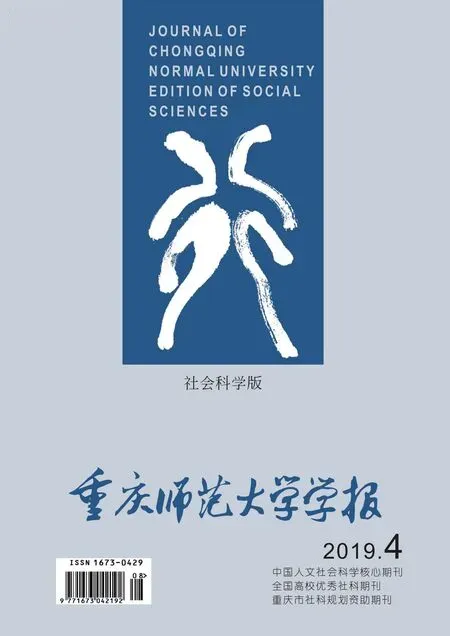重庆当代史研究的档案整理与学术研究
——以新中国成立前后为中心的回顾
龙 伟 李 琦
(重庆大学 新闻学院,重庆 401331)
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转折意义的一年,将20世纪分划成上下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1949年前后的两个时代,其政治运作、社会结构都呈现出巨大的差别。法国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赫认为,理解活生生现实的能力是历史学家最基本的素质[1]。1949年后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实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基本形态,甚至影响了当代中国的价值体系、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就历史研究而言,1949年后的当代史研究对于理解今日中国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949年11月30日,二野解放重庆,重庆这座历史古城迎来新生。建国初期,在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的领导下,新生的人民政权除旧布新,一面根除旧社会的遗留问题,一面推动重庆经济、社会建设,使得重庆社会生活发生根本性变化。如果说重庆解放是重庆历史上最值得铭记的转折时刻,那么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重庆的治理建设则奠定了当代重庆的基本格局。就此而论,重庆解放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庆史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拟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学术界、理论界对于重庆解放及建国初期重庆史的既往研究做一简要回顾,以期对重庆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重庆当代史史料整理述论
史料与档案是研究的基础,离开扎实的史料与档案,历史研究无异是沙上筑城。蔡元培曾言:“社会学术之消长,观其各种辞典之有无、多寡而知之。”[2]同样一项研究是否兴盛发达,亦可通过相关档案史料整理出版之有无、多寡略窥一斑。重庆解放及新中国成立之初重庆史的相关档案,已经整理出版的主要有以下十种:
(一)《接管重庆》,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1985年。
重庆党史研究资料丛书,《接管重庆》“文献资料”收录了接管重庆的重要报告、通知、布告等59件历史档案,整理收集了陈锡联、刘明辉、罗士高等8位当事人的“回忆录”,此外还附录了“大事记”“重庆接管时期党政军负责人名单”[3]。
(二)《重庆的解放》,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写,重庆出版社,1989年。
该书是作为纪念重庆解放40周年的献礼。全书分为文献资料、报刊资料、回忆文章和调查整理资料三个部分,并编写了大事记。是书在编撰过程中,对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人民解放军进军重庆,以及川东、重庆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统战工作,保护城市、迎接解放的资料,收录较为完整,但对于敌方资料,则相对欠缺[4]。
(三)《刘邓大军进军西南》,韦敏士、田晓光编,重庆出版社,1989年。
该书收录《第二野战军前委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等14宗重要档案文献,另收录陈赓、杨勇等回忆文章20篇[5]。
(四)《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四川卷·重庆分册)》,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
该书系《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史资料丛书的重庆分册,由重庆市委统战部、重庆市委党史工委牵头,会同重庆市工商局、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工商联共同编纂完成。是书由文献资料、典型材料、回忆录、大事记、统计表几个部分组成,收集整理了1949-1956年间重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资料,是研究新中国重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资料[6]。
(五)《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重庆卷》,钟修文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该书凡310页,内容包括综述1篇、文献42篇、回忆7篇,报刊材料11篇,并附有大事记、名录、统计表。集中收集了1949—1952年间,围绕重庆接管与社会改造的历史文件,对于研究重庆解放和城市改造具有重要价值[7]。
(六)《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编,重庆出版社,2006年。
该书共41.3万字,收入邓小平1949年9月至1952年8月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时期的文章、报告、讲话、电报、指示、书信、题词等文稿140篇,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本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邓小平在建国初期关于军事斗争、政权建设、经济恢复、社会改造、民主改革、党的建设、统战工作、民族工作、文化建设以及和平解放西藏等方面的重要思想,对于研究这一时期邓小平的业绩、思想和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具有重要的价值[8]。
(七)《解放战争战略追击:西南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
该书全面反映二野在一、四野各一部的配合协同下,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向盘踞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实施战略追击的历史。全书分为概述、文献、回忆史料、大事记、表册、图片等6个部分。其中文献档案收入229篇,回忆史料收入39篇[9]。
(八)《重庆解放》,唐润明、艾新全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
该书是为纪念重庆解放60周年,由重庆市档案馆与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共同编辑完成。其中有关重庆解放的档案史料,主要由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搜集提供,其他档案及文献资料,则主要来自重庆市档案馆馆藏。该书主要围绕“解放前重庆概况”“解放重庆”“接管重庆”“建设重庆”四篇构成,收录1948年至1951年12月间重要档案200余件[10]。
(九)《重庆解放档案文献汇编》,徐塞声主编,重庆出版社,2017年。
建军90周年之际,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重庆解放档案文献资料汇编》一书。该书主要内容包括解放重庆的有关部署、命令、作战方针、布告、电报、总结、讲话等档案,1949年报刊的相关报道文章,老同志回忆文章和部分关于区县解放的整理资料[11]。
(十)《重庆解放1949.11.30》,重庆市档案馆,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
该书与2009年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重庆解放》多有类同,被编入城市解放纪实系列丛书。与2009年出版的《重庆解放》相较,共新增档案史料14件,分别是“国民党对重庆的经营与防守”档案史料5件,“党中央、中央军委对解放西南、解放重庆的战略部署”档案史料4件,“中共川东暨重庆地下党为解放所做的努力与奋斗”档案史料3件,“建设政权”档案史料2件[12]。
不难看到,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始,重庆解放或建国初期重庆史研究相关的档案史料汇编至少已陆续出版以上十种,可谓成绩不俗。这些历史档案汇编的出版为推动重庆当代史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客观地说,这些档案史料的整理出版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难以有效满足学术界推动当代重庆史研究的急切需求。从资料整理出版的角度来看,这些档案资料的出版整理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首先,大多数史料的出版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等为代表的官方机构出版,少有研究机构独立编撰出版,反映出本土学术机构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上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因编撰主体、编撰目的之不同,现有档案整理出版多是围绕某一特定主题选编为主,史料的学术价值颇打折扣;再者,现有档案所涉及主题较为单一,空白甚多。档案史料的出版偏重于重庆解放和接管,而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历史进程却少有触及。重要的历史事件只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有单独的一册档案资料出版,其余如西南剿匪、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重大历史事件均无涉及。一些重要的机构,如西南军政委员会、重庆市委、市政府等部门的档案亦付之阙如,当然更缺乏一部系统、全面的建国以来重庆地方综合性的档案资料汇编。
二、重庆当代史相关议题的学术研究
总体而言,重庆史的研究偏重于近代,近代重庆史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当代重庆史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对薄弱,是重庆史研究中亟待加强的领域。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学术界对1949年至1956年间重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重庆解放、邓小平主政西南、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等方面。以下就这几个方面略作介绍。
(一)关于重庆解放的研究
1949年11月30日,二野在邓小平、刘伯承的指挥下解放重庆,重庆迎来历史新的篇章。重庆解放是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过程中最有标志性的事件之一。就此重大历史事件,军事类通史、文学作品等都对此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叙述。这类作品数量很多,略举数例如下:刘统《解放战争全纪录》(青岛出版社,2010年),刘统《决战:中原西南解放战争(1945-1951)》(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吴辅佐《挺进西南(二野卷)》(长征出版社,2000年),王朝柱编著《解放大西南》(重庆出版社,2009年),彭荆风《解放大西南》(云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等。这类作品侧重以通俗的笔调描述二野解放大西南的历史壮举,从性质上讲更偏向于史学通俗读物,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作品。
学术研究方面,早在1989年为纪念解放西南四十周年,成都军区政治部编研室曾出版《解放西南学术论文集》,这是较早开始以解放大西南为主题的专题研讨会。这次会议收到论文40篇,最后结集27篇。不过,因会议以整个大西南为研究视域,所述范围极为广泛,其中仅有李宗杰《党的统战工作促进重庆解放》一文具体以重庆解放为主题[13]。然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相关的研究都停滞不前。新世纪以来,相关研究的推进略有起色。论文方面,谢武申的《二野情报处与解放大西南》从历史学角度结合丰富史料讲述了在解放大西南的战争中二野司令部情报处的艰苦工作[14]。陈与《<挺进报>大揭秘——还原重庆地下党真实历史》讲述了重庆地下党组织创办的《挺进报》是如何在解放战争前夕地下党组织受到重创的情况下依然积极发动各阶层民众,与国民党斗智斗勇,最终迎来解放的曙光[15]。彭承福、刘伟的《邓小平关于解放重庆几个问题的研究》讲述了邓小平结合重庆的政治背景确定了正确的解放方式,他组建了西南服务团来解决干部问题,依靠川东地下党建立统一战线,依靠人民来建设重庆的举措[16]。蒋仁风的《重庆解放前夕我们的对敌策反工作片断》以自述的角度,讲述了解放前夕重庆地下党组织对敌人的一系列策反工作,极大地减少了人民解放军进军重庆和川东地区可能付出的代价[17]。论著方面,以重庆解放为主题的研究论著相对较少。较有代表性的如张卫、冉启虎编著的《解放重庆》,是书围绕解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重庆展开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较量,着重以军事斗争为主线,详细叙述了龚滩激战、马头山激战、黄家坝激战、彭水攻坚战、白马山追歼战、南泉激战、江防舰队起义等解放重庆过程中的重要战役,披露了众多以往关注不够的战役和史实[18]。总体而言,关于重庆解放的研究推进较为缓慢,研究多偏重于从军事史的角度做简要的勾勒,开创性的研究并不多见。
(二)邓小平主政大西南的研究
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10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西南局第一书记。二野解放重庆以后,西南局进驻重庆办公,负责对西南的重庆和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一市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实行全面领导。在建国初期重庆史的研究中,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是相关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
2000年,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率先编撰出版了《邓小平与大西南(1949-1952)》,这是对西南时期邓小平思想和实践进行全面研究的著作,在学术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19]。2004年,郎维伟主编了《邓小平与西南少族民族 在主持西南局工作的日子里》。该书以民族问题为视角,系统回顾研究了邓小平解决西南民族问题的思想与实践[20]。同年,杨耀健还主编出版了《西南局第一书记》[21]。2004年8月,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在重庆举办了“邓小平与大西南学术讨论会”。这次研讨会入选论文58篇,涉及邓小平与大西南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的议题。这是国内首次就邓小平与大西南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对于促进相关课题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同年,重庆市委宣传部还出版了《邓小平与重庆》(画册)[22]。2006年,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在会议基础上编撰出版了《邓小平主政大西南的历史经验:重庆市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文集》,该文集收录座谈会及其他相关纪念活动文稿和学术会议入选论文,共计93篇。其中庞松《邓小平与西南区的经济恢复》,周勇《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期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初步探索》,郎迎洁、季国敏《试论邓小平与西南民族工作》,魏仲云《论邓小平组建西南服务团的战略意义》等文分别从不同侧面对邓小平主政西南局的工作做了深入研究,代表了当时这一领域最高研究水准[23]。
《邓小平与大西南学术讨论会》结束后,该次会议的部分论文随后也陆续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形成了邓小平主政大西南的一波研究热潮。除上述论文外,还有一些研究论文也从不同角度对邓小平治理大西南进行研究。相关作品如蔡玉卿的《建国初期邓小平治理大西南城市失业的实践——以1949年—1952年的重庆为个案》,该文主要讲述了建国初期重庆失业现象严重,主政重庆的邓小平以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大西南的失业治理,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加强城乡联系,创造就业机会,有效地化解了失业风险[24]。谢荣忠的《邓小平与重庆解放初期劳资矛盾的化解》分析了邓小平在重庆期间化解劳资矛盾的两条经验:一是领导干部上第一线,亲自做群众工作;二是制定正确的政策,并一以贯之的执行[25]。
2010年,艾新全、林明远出版了《邓小平在西南的理论与实践:1949-1952》,从军事、政治、经济、土改、民族、统战、边防、党建等角度对邓小平主持大西南期间的施政理念和实践做系统论述,特别注意邓小平从将才到帅才的转变过程[26]。同年,中国人民大学沈波濒完成了题为《邓小平主政西南研究(1949-1952)》的博士论文。该研究以邓小平为中心,侧重就邓小平在解放大西南、政权建设、社会改造、经济发展、文教事业五个方面的实践进行了系统阐述。这两项成果代表了目前关于邓小平主政大西南研究的最新成就[27]。
三、重庆解放后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研究
受社会史研究的影响,史学界日益重视对底层社会生活的研究。在建国初重庆史的研究中,这一倾向也表现得较为明显。社会史的研究虽然面临资料的散佚繁杂,但相对于政治制度等研究而言,档案的开放程度又具有明显的优势。单从数量上看,重庆解放初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研究明显构成建国初期重庆史研究的重点,也有可能成为未来建国初期重庆史研究新的突破点。
相对而论,解放初期重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研究呈现出数量较多,领域较广、研究较细的特征。就涉及的议题来看,现有研究既包含接管改造等建政层面的问题,也涉及干部结构、离婚潮、报业改组、疫病防治、小学改造、宣传动员、公私合营、交通发展等方面的议题。特别是近年来有大量的硕博士论文围绕解放初期重庆的政治、生产与生活的相关议题展开。博士学位论文如华东师范大学程曦敏博士的《干部本地化与地方政治——以江津县领导干部构成变动为中心的考察(1949-1966)》以江津地方档案为突破,考察了建国初期江津干部的构成和基层政治[28]。硕士学位论文为数更众,相关研究如杨丽媛的《重庆市小学改造研究(1949-1953)》,康琳的《建国初期重庆地区<婚姻法>实施研究(1950-1956)——以“离婚潮”现象为中心》,李琳佳的《建国初期重庆地区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1949-1956)——以西南师范学院政治理论课建设为例》,邱艳斐的《建国初期重庆地区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1950-1953)》,李晓朋的《建国初期重庆地区突发性疫病的防治研究(1950-1953)》,任永东的《建国初期重庆禁毒法制状况刍析(1950-1952)》,曾群芳的《抗美援朝运动中重庆地区宣传动员研究(1950-1952)》等。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建国初期重庆史进行了考察,显然有助于推进相关研究的持续展开。不过也应该看到,这些研究的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有影响力的高水平论著还相对较少。
近年来关于建国初重庆史的研究成果中,显示度最高的当属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研究团队利用民国及建国后江津历史档案所作的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大约从2012年起,该团队主要围绕减租退押、统购统销展开研究,陆续在高水平刊物上发表了《江津县减租退押运动研究》《粮仓、市场与制度:统购统销的准备过程——以江津县为中心的考察》《“大户加征”:江津县1950年的征粮运动》《余粮从何而来:江津县粮食统购的数据建构(1953-1954)》等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特别关于1950年江津县“退押运动”的研究,学术界还围绕这一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和争鸣。清华大学黄柘淞在2017年于《清华大学学报》上刊文与曹树基商榷,认为退押运动的发起与1940年后押租制下佃农的经济损害直接相关,跳过这一时段去争论1940年前押租制对佃农的利弊是走向了论证偏歧。从目的看,退押运动和支持人民币信用以及增加农业税收入几无关联,并非政府为充盈财政而设计的图谋,而是中共在前土改时期打击地主、启发农民“觉悟”的决策体现[29]。随后娄敏在《中共党史研究》撰文对黄文回应,她认为双方的分歧反映出“退押运动”的研究存在两种不同路径:一是经济层面上的地权交易逻辑,二是政治意义上的革命动员逻辑。由于黄文对传统地权结构的运作机制与实践缺乏深入研究,以致对曹文论证框架的理解存在偏差,并未能有效颠覆曹文的核心论点[30]。
除上述研究外,这一时段重庆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研究中还有几个方面的研究也颇具亮点。譬如扶小兰发表了多篇关于建国初期重庆城市变迁的研究论文,系统分析了在新中国“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的号召之下,重庆对烟赌娼等社会遗留问题的治理,以及开展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造运动。杨世宁通过对西南军政委员会档案的系统挖掘,对西南军政委员会做了开拓性的研究[31]。另外杨菁对建国初期重庆行政体制的研究[32],上海交通大学华君夫、赵思渊关于重庆大新药厂公私合营的研究也都颇具特点[33]。
三、重庆当代史研究的问题与展望
综上所述,围绕重庆解放与建国初期重庆史的研究已有一定的起色,也涌现出一批有代表性的成果。不过客观地讲,该时段的研究仍然存在研究较为分散、聚焦不够明确、空白领域众多、研究深度不足、质量仍待提高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可能主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条件的制约:
一是四川、重庆档案图书系统相关史料的开放程度还相对有限,这成为当代重庆史研究的困境。以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档案为例,十余前年,四川档案馆尚对外开放相关全宗资料,但目前学者已无法再调阅。五十年代的档案开放程度有限,这无疑限制了学术界对这一时段持续深入的研究。
二是重庆历史学科在学科建设、研究方向、人材培养等方面的客观原因所决定。历史学属于人文基础学科,受历史因素的影响,重庆历史学研究队伍发展较慢,近年来虽有迅速提升,但力量还相对薄弱。历史学科在建设过程中,也因学术生产过程较为漫长,对学校量化贡献较小,因而存在重视、投入不足的问题。研究方向在设置上则多偏重于近代史、历史地理等相对成熟领域,当代史方向难以形成有效研究团队。上述种种因素同样导致重庆当代史的研究难以凝聚力量,取得重大的学术突破。
三是由于重庆1997年才成为直辖市,国内大部分对建国初期进行研究的学者重心均放在整个大西南地区或者四川地区,因此单独对重庆解放及建国初期重庆史的研究总体比较少。直到最近几年,学术界才出现少量比较规范、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当然,上述这些问题并非全然是重庆当代史研究独具的个性,当代史研究不足乃是全国性的通病。历史学分科往往以1949年为限作截然划分,党史研究则较长时期受意识形态左右,这些因素都导致对当代史的研究长期停滞不前。此外,以往的历史学研究中还存在一种“不治当代”的偏见,不少高校的研究都偏向于近现代而忽略当代,硕、博士论文也不同程度存在“不治当代”的治学传统。就当前来看,全国范围内只有当代中国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当代史研究中心等为数不多的研究机构,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较为成熟、颇具影响。
尽管重庆解放及建国初期重庆史的研究存在诸多的困难和挑战,然而历史学家应该有历史的敏锐触觉。研究者尤其应该清醒意识到,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建国初”这一前辈学人觉得尚“新”、尚“近”的时段正日益退居时代的幕后,越来越变成历史研究的成熟“对象”,当代史的研究条件正在不断地成熟,当代史研究及其崛起乃是发展之必然。重庆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建国初的重庆史研究空间巨大,大有可为。推进重庆当代史研究不但是每一位有追求、有抱负、有担当的重庆历史学者的历史责任,也当成为历史学者得预潮流、研求问题的重要学术选择。不难想见,重庆解放及建国初期重庆史的研究势必会成为将来重庆研究的潜在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