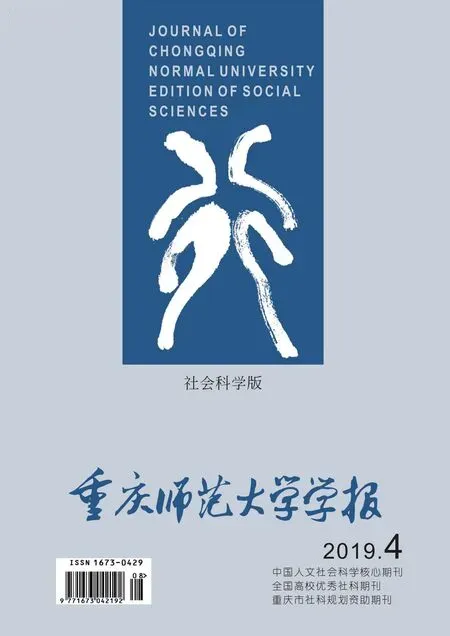历史的穿越与继承: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现代新乡绅”形象
——以《胡不归》为中心的思考
廖 斌
(福建武夷学院 人文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
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农村社会进入急剧变革的转型加速期,随着人民公社等国家基层权力的退隐、村民自治的实施和晚近“去乡村化”“乡土中国虽然有了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大得多的发展,但与之相伴而生的乡村治理危机也是史无前例的[1]。新世纪乡土文学作家,诸如陈应松、侯波、杨少衡等的作品,对此多有呈现,笔端力指乡村权力异化、人心涣散、黑恶势力横行等等。缘此,无论是上层建筑、理论界,还是社会学者、文学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积极呼吁和探索乡村治理的全新形式,以此回应“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
其中,新世纪乡土文学中的“现代新乡绅”继承传统,面向现代,穿越历史时空隧道,隐约浮出地表,活跃于乡村的现代治理空间。
一、现代新乡绅“前史”:地主、圣徒、强人形象
说到“乡绅”形象时,略知历史的读者就会列举“士族”“门阀制度”“缙绅”等特权阶层和现象,并与此联系起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们也刻画出众多貌似“乡绅”的形象:鲁四老爷(《祝福》)、吴老太爷(《子夜》)、赵守义(《霜叶红似二月花》)、赵太爷(《阿Q正传》),等等。显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反面人物。恰如学者赵园认为,“五四新文学中,乡绅基本上都是反面人物,不会有一个真正想改善民生,做点慈善事业,即使有这样的一定是伪善的。所以关于乡绅的乡村治理,也是近年来宗族史重提的一个话题,就使得原先过分意识形态化、片面化的表述受到了校正。”[2]
正是小说的“诱导”,使得新中国几代读者在很长时期内,将“乡绅”接受为“黑恶势力代表”,为他们添上了诸如:道貌岸然、男盗女娼、剥削阶级、假仁假义、心狠手辣、鱼肉乡里等标签,并通过“点天灯”“浸猪笼”“站水牢”等骇人听闻的故事,增值和固化了对“乡绅”的再认知。关于这一“诱导”,社会学者郭于华有精彩的研究,他指出,“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特别在1949年之后,‘诉苦’和‘忆苦思甜’权力技术的有意识运用,……对农民日常生活中那种较为自然状态的‘苦难’和‘苦难意识’加以凝聚和提炼,使其穿越日常生活层面,与阶级框架并进而与国家的框架建立起联系。将农民在生活世界中经历和感受的‘苦难’归结提升为‘阶级苦’……”[3]而民国时期“乡绅劣质化趋势亦日趋明显,造成此一时期乡村社会的深刻危机”[4],这一现实又进一步为文学的加工与生产输送了证据。
由上可知,通过文学教育和“诉苦”等指控,南霸天、周扒皮、黄世仁、刘文彩等被型塑为万恶不赦的“恶霸地主”形象,成为革命史教育的众矢之的和当代文学史上臭名昭著的乡绅代表。有意思的是,晚近以来,有媒体“深挖”了四川刘文彩的“轶事”,并刊载了其后人的“翻案”文章[5],将刘文彩描述成一个有仁爱之心的正派乡绅,一时聚讼纷纭,真假莫辨。在此按下不表。
进一步,在学者刘畅的新世纪乡土文学论文中,“新乡绅”依然被指认为封建宗法制度的畸形产物和阻碍现代化建设的绊脚石,他说:“(新世纪)文学作品里仍然不缺少“新乡绅”式人物,对于这场正在改变中国的伟大变革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尴尬和警醒:改革的道路依然漫长而艰辛。”[6]
根据百度百科释义:“绅”本义为中国古代服饰名。为古人用大带束腰后,垂下的带头部分,作为已婚标志的丝制腰带。后引申为旧时地方上有势力、有名望的人,一般是地主或退职官僚;在近代社会中,绅士有着特殊的地位,非官而近官,非民而近民,是高于平民的一个封建等级阶层[7]。因而,从词源学理解,“乡绅”其实是一个中性词,是日后的文学影视作品因教化取向而赋予其“负面”的蕴含,并日益建构与规训了读者的想象。魏欢认为,“地主阶级”与“乡绅”是不同概念,不能简单认定乡绅等同于地主阶级。地主阶级皆占有大量的土地,且以剥削农民为生,乡绅中虽然可能有些是富裕的地主,但也不乏贫寒之士,但其特殊的地位又高于一般地主,应关注其特殊权利及社会地位,尤其关注其是否在乡里社会具有较大的影响力。魏欢概括了“乡绅”的特点,如乡绅参与乡里公益事业、文教事业、希望自己作为乡里教化民风的榜样及领袖等,并从文学视域归纳“鲁迅等启蒙作家笔下的乡绅形象及对乡村社会的消极影响”“沈从文等京派作家对乡绅的人性光辉而非阶级属性的重铸”[8]3-6。
在共产党的权力楔入乡村后,基于继续革命的需要,并通过上述意识形态手段,将农民纳入“动员结构”,最终训唤成为深具阶级意识的“劳苦大众”,持有同一革命理想的同盟军。
综上所述,上述文学文本的“乡绅”,毋宁称之为“村霸”“地主恶霸”“财主”,更符合其在民众理解语境中的“阶级身份”,更加凸显其盘剥吸血的政治经济学本质和意识形态指向。将这几个词联系等同的理解模式和混沌表述,在那个红色年代,很具有代表性。总之,“乡绅”是有名望、有势力的聚居乡村的地主、退休官僚、士人、社会贤达等。这里的名望,应指好的口碑、才能、德行。反之,“地主”则不一定能够成为“乡绅”,而可能是俗称的“土老财”“恶霸”。
阳信生指出,乡绅专指我国封建时代居乡的退职官员和取得生员以上功名或一定职衔而未为官的居乡绅士。……扮演了朝廷、官府政令在乡村的执行者和乡村民众政治、文化代言人的角色,是乡村社会的文化发展、道德教化、公益事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防止官府力量过于消极或过度干预乡村事务、平衡地方社会国家与民众关系、维护乡村稳定的基础和重要力量。重要的是,乡绅是相对独立于正式政权之外的社会性力量[4],“在野”是其非常鲜明的属性,他们中间的优秀人物代表,有的兴办教育教化乡里,有的赈灾济民维护安全、有的设立义仓共度时艰……如《白鹿原》里的白嘉轩。他们中间的不良分子,则称为“土豪劣绅”“恶霸地主”。
新中国建立后,紧随着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等一系列农村政策的次第展开,旧地主、恶霸被彻底打倒,田地被均分,财产遭剥夺,他们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退出历史舞台。但他们的身影在当代乡土文学中随处可见。这一时期,梁生宝们成为共和国新生政权在乡村的代言人:政治精英。正是梁生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圣徒”,以其政治坚定、道德高尚、一心为民、大公无私的共产党人优秀品格,树立在乡村社会不容撼摇的新权威。
新时期文学中,高明楼、田福堂等,以及新世纪前后,众多作家塑造了呼天成(《羊的门》)、田广荣(《村子》)、荣汉俊(《天高地厚》)、旷开田(《湖光山色》)等村干部,大多是带领村民奔小康的典型、乡村改革的弄潮儿:经济能人、治村强人。这些人物形象跳脱出“圣徒”的人物模式与叙事轨迹,终结和解构了梁生宝式的“高大全”带来的“审美疲劳”,具有“祛魅”的示范性质。于是,更加符合时代特点和农村生活的“村干部”出场了,他们身上既有干部威信、经济强人的样貌,又有联姻互助、宗族首领、封建专制的潜在质素。他们有的是“农民帝国”的“老爷子”(蒋子龙《农民帝国》,村书记郭存先)、有的亦正亦邪(胡学文《逆水行舟》,村长霍品);有的恰似旧社会的恶霸地主(毕飞宇《玉米》,村长王连方),有的撂下担子逃离乡土(侯波《胡不归》),等等。但是,这些人仍然称不上“乡绅”,他们要么仅仅局限于“致富能人”,要么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是执政党在乡村的权力延伸,代表国家对乡村实行控制,是不纳入编制的“干部”。正如张连义评论,“(呼天成)作为呼家堡的当家人,呼天成建立权威正是依靠官方赋予他的政治身份。”[9]228以上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勾勒。
那么,什么是“现代新乡绅”呢?有学者研究认为,基于民国时期出现了“新乡绅阶层的再造运动”,故而将现今因农村社会重建、克服农村治理困境这一现代语境急需的“新乡绅”,命名为“现代新乡绅”“现代新乡绅主要是指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农村文化和社会精英,……他们可能有一定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但不以财富作为判断标准,特质是知识性、文化性和社会性,影响主要是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的。”[4]现代新乡绅身上寄寓了人们对乡村重建的深切期望,“他们是德高望重、具有明显的道德优势和话语权、发言权的社会精英分子,能够充当农村道德的捍卫者、农村秩序的有效维护者、农村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的有效协调者、仲裁者。”[4]
据搜索,互联网上“新乡绅”这个热词铺天盖地达到162万个网页,但意涵模糊,也遮蔽了历史不同群体:地主、乡绅、圣徒、现代新乡绅的差别。正是媒体长篇累牍地召唤“新乡绅”,进一步反衬了其在当下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性,凸显了与前现代乡村“地主”或“恶霸”、建国后迄今“圣徒”“村干部”之差异,也印证了小说《胡不归》的独特发现和历史敏感。
二、 “现代新乡绅”:从时代变化的罅隙中诞生
“现代新乡绅”的“新”在何处呢?本文认为,一是时代不同。他们诞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与发展期;二是主体不同。现代新乡绅是由返乡安居的社会贤达、致富能手、返乡企业家、知识精英、退休官员等组成的“居间”群体;三是理想不同。现代新乡绅不将自己宗族、家庭利益放在首位,而把获得的经济利润、政治资源、文化资本聚焦于村集体,有点儿公而忘私的味道,或者公私兼顾。
新世纪以来,侯波的《胡不归》等乡土小说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新乡绅”的抒写与典型塑造,具有风向标意义。这样的“乡绅”形象淡化了“十七年文学”中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厚的村干部塑造,颠覆了新时期文学“乡村权力异化”的展览式书写,敏锐地抓住当今乡村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细微变化并把握住了这一规律性认识,刻画了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新人”,充实了当代乡土小说的人物画廊,回应了社会对乡村振兴的关切。
一直以来,新世纪乡土文学之于“乡村权力”“村干部人物”的描写,大多着眼于批判和揭示,除了评论者和读者广为诟病的“苦难叙事,即不少作家不约而同热衷于展示乡村的凋敝、农民的愚昧与信仰迷失、乡村权力异化、文化荒漠化、生态恶化、伦理崩解、农民进城的命运凄惨与身份认同混乱……其作品鲜有亮色和光明的指向。只能让人空留感喟,嗟叹几句“农民的启蒙任重道远”“农村岌岌可危”的苍白之言,难以唤起人们对改造“乡土”的勇气和信心。这些书写表征乡土小说家们对乡村振兴的进展、返乡创业农民日趋增多、村容村貌建设、乡村旅游兴起、乡村内生力量崛起等“萌芽状态的事务”视而不见,以及当下乡土小说创作的软肋与短板:同质化书写与缺乏发现“真善美”的眼睛。确切地说,这多半是由于作家与“乡土”的隔膜造成的。陈平原指出:“‘乡土文学’家对故乡生活、农民痛苦的了解,多半来自间接经验。而作为直接经验的只是儿时生活的回忆和成年偶然回乡的观感。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农民生活做出精彩的描绘。”[10]198
应该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小说“陌生新人”薛文宗的闪亮登场,刷新了此类人物谱系的抒写,是具有时代封印的“独特的这一个”,也预示了乡村人物书写的一个走向。只有真正融入土地的作家,才能够从中发现乡村的嬗变,并将这一大家熟视无睹的“新质”热情地展现出来。陕西作家侯波,就是这样的土地之花。
《胡不归》是侯波发表于《当代》(2018年5期)的中篇小说。“胡不归”一词来自陶潜《归去来兮辞》之“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意即:快回家吧!田园将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回去呢?这篇小说设计了乡村教师薛文宗,一个看似老实,且又唯唯诺诺的小人物,但他知书达理、人脉广泛、见过世面。退休返乡后,因为办事能力强而被乡里定为世宁村代理村主任,随后他在世宁村主持解决了建沼气池、修公路、土地承包等一系列棘手问题,逐步获得村民认可。就在他得到村民拥戴,兴建薛家宗祠时,出事了……笔者以为,以薛文宗为代表的乡村领头人,具有“在野”和“知识性、文化性、社会性”的双重属性,是新时代乡村社会的“现代新乡绅”。
旅日学者宋青宜对中国“三农”问题有较深入研究,她认为,“新乡绅主要是指受过良好教育的,……获得一定资本的或具有创业能力的,乐善好施的,经过一定时间努力得到村民信任进而具有话语权的回乡人士。”[11]对照比较,薛文宗正是这样的回乡人士,他在恰当的时候,浮出历史地表。
宋青宜归纳了当代“新乡绅”的特点,并指出其中的关窍,诸如:讲道德,讲诚信,有爱心,有智慧;是公益事业的热心人;凭着自己高尚的人格魅力,获得了乡亲们的尊敬和爱戴。能够坚持正义并主持公道。从文本分析,薛文宗作为中学教师,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当过副校长,有一定社会地位;为举办村里的联欢晚会捐资、为了村集体利益无私奉献,敢于斗争,公道正派,有情怀爱心还带着一点小韬略……。正是这个近民而非民,似官而非官的普通百姓,乡里领导要依靠他,村民慢慢服从他。他在艰难行使“代理村长”职权的过程中,不断左右逢源,甚至无往不利,逐渐具有了“现代新乡绅”的精神气质和实际能力。小说写到后半部分,薛文宗通过工作实绩和人格魅力,慢慢积攒起人气,凝聚了人心,村里的事务有了起色,一个现代新乡绅呼之欲出。
小说刊发后,好评如潮。有评论认为,“《胡不归》的深层次内涵,作家要体现的是‘芜’,这一个‘芜’,不是指土地上的‘芜’,而是指农民的精神世界。”说到底,这篇小说烛照了一个大家习焉不察的问题:“农民的文化信仰、道德底线的精神世界的荒芜。谁来负责这些问题,谁去勇敢地承担这个拯救的义务?”[12]这个洞见是犀利清醒的,抓住了农村经济发展之后精神空虚、文化荒漠化的症候。有学者评论道:“以市场经济为后盾的改革开放虽然保证了‘文化大革命后’社会的稳定,凝聚了人心,……也导致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的涣散和虚无感的滋生,市场经济提供的物质环境,并没有为富足起来的人们提供心灵抚慰的精神资源。”[13]333-334
但是,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 “胡(为什么)不归” 的责问上滑行。关键是,面对乡土世界中农民精神荒芜、文化溃败、人心离散,要进一步追问:是谁,应该认清现实?是谁,应该肩负起这个挽颓势于既倒的重责大任?是谁,应该义无反顾地“归来”?答案当然是——现代新乡绅。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也有近似“现代新乡绅”式的人物——有文化知识、有创业资本和能力、也捐点小钱、有一定话语权。但是,两相较量,他们或者是乡土的“出走者”、抑或是最后一丝利润的“榨取者”。乡土文学作家王十月曾经有一部小说《寻根团》(《人民文学》2011年5期,获2011年人民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讲述的是在广东打工发家致富的楚州籍老板、企业家、知识精英以寻根的名义利用清明节返乡“淘金”,各取所需,最后又忙不迭出走的故事。文中的这些老板,如毕总等人衣锦还乡,得到了质朴的乡土最真诚的拥抱和欢迎。但是,他们除了走亲访友“炫富装逼”,急切地寻找合作商机在家乡再狠命捞一把外,再也没有心思为乡村做出哪怕是一丁点儿的贡献。简而言之,他们虽然头顶着“乡绅”“乡贤”的高仿帽子,实质上是乡村的索要者、榨取者,叛离者。薛文宗也返乡,他归来、留住、干好,真心实意为农民谋幸福,尽心尽力为乡村促发展。二者境界不可同日而语。
三、现代新乡绅:奉献情怀、民主协商、公心为民
所谓“治理”,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和个人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14]。新世纪以来,我们国家在各个领域不断推进现代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此应对“治理危机”。
谈及农村治理,在20世纪80、90年代的乡村社会乃至之前,由于农民缺乏主体和民主参与意识,形成由村干部“说了算”的,自上而下的“命令型”“支配性”领导(而非治理)机制。譬如,双水村的田福堂、高明楼等“威权性”村干部,牢牢把持着村里的大小事务,有专制和支配的权力。高明楼利用手中权力,排挤“乡村才子”高加林,让儿子替代他成了不用下田劳作的代课教师。
到了新世纪,农民受到现代化的影响,催生了现代民主意识和维权自觉,主体意识觉醒,参与愿望强烈,乡村事务就涉及到多主体的共同协商:基层政权、村干部、NGO组织、各级合作社、村民代表(在乡与进城)乃至宗族势力等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此时是一种“协商式”“参与性”的治理。纵观《胡不归》里的薛文宗,正是在失去“支配性”领导的有利条件下,以一种全新治理模式艰难开展村务工作,这是一个新课题。这个时候,摆在这名成长中的“现代新乡绅”面前,就急切地需要增长“新”质素来填充其内涵。
薛文宗所生活的世宁村,“这几年家家户户都有钱了,大多家户都在县城买了房子,开上了小轿车,然而在集体的事情上却越来越没人管了。村里现在连个村长都没有。”所以,薛文宗所面对的村务就十分复杂,既有苹果园的承包纠纷与上访、兴建沼气池、兴修公路、拔除钉子户等集体大事,又有邻里纠纷、用水修石碾等鸡毛蒜皮的小事。总而言之,农村无小事,中国农民在千百年时局变革中惯习陈陈相因,摆脱不了精神的“窠臼”“《胡不归》的精神世界镜像里面照出了好多农民的嘴脸,这些嘴脸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的情节有些历史上的吻合。”[12]因而,对于这个不期然卷入乡村事务提前退休的教书先生,不仅十分需要从政的智慧、管理的艺术,更需要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情怀”——这是新时代“现代新乡绅”的第一质素。薛文宗因病内退后,衣食无忧,本来可以过起乡村“寓公”的闲适生活,终日拉二胡、晒太阳。在介入村里烦恼挠心的事情后,面对老婆数落,“这村里都是些老虎豺狼黄鼠狼,个个鬼心眼,说人话不做人事,村里的事就是个火坑,别人躲哩,你却要往进跳哩。”当局长的杨同学劝说:“你又不是村长又不是支书,管这么多事干啥哩。……集体的事你干得再多也落不了好的,何苦呢?”他虽然时有后悔,却又宁折不挠,因为,他从心里认同并身体力行老支书的临终遗言,“这活人是活大家哩,活得死了也要让大家记住哩。”薛文宗还铭记返乡又出走的薛洪达的话:“老辈人常说一句话叫‘活人’哩,其实就是要活众人哩,活亲戚、活乡亲哩,否则的话,你再有钱,再有势,在村人面前也抬不起头啊。”虽然在为村里排忧解难中,他屡次受到各种内外‘阻击’,但薛文宗说:“干点事不受点委屈咋能行哩,韩信还受胯下之辱呢。”这些磨砺,反而“激起他想铺路、给村里办点好事的雄心壮志来”。
从文本解析,薛文宗居乡在野,除了有知识文化和为民服务的“情怀”,还有计划经济时代的村干部鲜有的现代因子:协商——这是现代新乡绅的第二个新质素。协商的反面是“专制”,协商是与新时代乡村民主建设同构、与村民自治制度高度耦合的元素。也就是说,直到当下,乡村才逐步迎来了它此前向村民允诺的“现代”。小说描写到,薛文宗本是一介书生,既没有过硬的政治或经济资本,也没有势力手段在民心涣散、失魂落魄的世宁村实行“一言堂”,唯一的办法就是:协商。于是,他与挂村干部协商如何完成建设沼气池的任务,与一干跳广场舞的大妈协商如何举办村级春节联欢晚会,与乡镇领导协商怎样修建村公路,与妻子协商为晚会捐资一千元人民币,与村民协商解决老大难的苹果园土地承包与流转,与秀兰协商退出乡村寺庙遗址,……正是通过他的左右斡旋、上下沟通、前后穿梭、里外安抚,渐渐重塑了世宁村的“社会生态”,解决了一个个困扰世宁村多年的积重难返的问题,积攒了村民的共识——当然,此间也离不开他农民式的“狡黠”和“韬略”,更离不开他获取认同的法宝:公心。因此,公心是“现代新乡绅”的第三重要特质。在世宁村,人心涣散是表象,根源是人性中的自私自利占了上风,小农意识抬头。中国社会改革开放40年,经过现代化的洗礼,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摩天大厦在城市随处可见,乡村触目即是一片樱红柳绿。但是,深深烙刻在农民精神世界和文化心理中的传统习气,特别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孕育出的保守、愚昧、自私等“老魂灵”,仍然有强大惯性,在乡村“空心化”“散沙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小说中,乡里的郭副书记感慨道,“这几年,村里人钱多了,可也变得极为自私了,……一些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些人等着看哈哈笑,还有一些人,不说正经话,纯粹就是捣乱。大家都没有个是非观,什么礼义廉耻,什么文明道德,全都被忘记了……这样下去可如何得了呢?”具体到村里,诸如,秀兰对圐圙的长期霸占使用,薛天成对建设薛氏家祠收取高额水费,村民们对100多亩土地承包与流转反反复复的上访、争吵乃至动手,以及修乡村公路为青苗费补偿漫天要价,等等。说到底,都是为了一己之利,这些自私行为在薛文宗的公心逼视下,榨出“小”来。且不说他积极主动为村里的活动捐款,单看他为乡村尽心尽力的无私付出:自从行将就木的老支书找他谈话后,“他心里就挂着各事”;对于举办联欢晚会,“大家都盼着他来组织活动,这些信任,让他心中暖烘烘的”;对于离乡游子薛洪达的期盼,“只有一个人记到了心里,这个人就是薛文宗,没过两天就到县里去打问铺路的事”;对于村里修路,“他就去找同学杨局长想办法,看能不能(自费)请交通局长吃顿饭,或者给人家送两条烟也行,把这事办了。”对于突破拆迁钉子户,他“咬紧牙关,下决心了。妈的,惹人就惹人,哪怕把这宗事闹完这临时村长不当了呢。”……薛文宗就是在这左支右绌中,以公心办好事、成就事,树立了威信,重新凝聚了乡村“共同体,”貌似逐渐成长为时代征召的现代新乡绅。
四、现代之子:合法与未来
总体而言,当代乡土小说之于“乡村政治”的抒写,主要继承了鲁迅的路数,着眼于启蒙和批判,表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又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缺德”倾向。无论是共和国新生政权建立的年代,还是资本全球化时期,都不乏“乡村权力”的觊觎者、滥用者。有研究者指出:“乡村权力构成中有国家权力‘安插’的成分,有新生资本力量强力介入的成分,也有社会黑恶势力渗透的成分,而很少有能代表广大弱势农民利益的成分。乡村政权中各种势力的实际权力代理者,往往是哈耶克所说的‘最坏者’。”[1]
侯波在创作《胡不归》时,倾注了对古老苦难乡村振兴的希冀与理想追求,力图与上述写作传统做一个切割,而努力写出时代前行处最新鲜的“发现”,进而把薛文宗刻画成“独特的这一个”,破除哈耶克的“魔咒”。小说塑造的现代新乡绅——薛文宗这一形象,不是凭空浮出历史地表的,正如前文分析,他的前世今生与“乡绅”“圣徒”虽有区隔,却又隐含千丝万缕、超越时空的联系。换言之,《胡不归》这一佳构,浓缩了“乡绅”的百年变迁史、文化横截面、现代史,现代新乡绅是乡绅与圣徒之子,是汲取二者精华的“现代之子”。
《胡不归》设置了一个巧妙的“隐蔽副线”叙事结构:薛文宗的祖父薛耀堂是民国时期县里赫赫有名的乡绅,在乡间广行善事,影响深远,得到乡邻的交相赞誉,被后人树碑立传载入县志。在无法开展工作时,乡里领导为了动员薛文宗参与世宁村的治理,便以薛耀堂为例百般劝导,但薛文宗对祖父死于建国后群众批斗的结局仍心有余悸,不愿“蹚浑水”时,郭副书记说:“没有人会要你的脑袋的。你看看,古时候,农村就没个村干部,都是靠乡绅治理的,乡绅也办了许多事的,像你老爷,你问问这方圆多少里大家都知道的,当初在党湾桥那儿还立有碑子呢。”“当年你祖上可就是实实在在的乡绅,给村里办过许多事哩。县志上都有记载哩。”当工作颇有进展时,又表扬说:“你放在过去,就是乡绅。……解放前农村的事都是靠乡绅来协调处理的。”当工作卡壳需要协调时,又威逼利诱:“像你这号人,在解放前,那是乡绅,村上的疑难杂症都要靠你们协调解决哩。你祖上可是响当当的,县志中都有记载的。我现在也只能指望你了,你多想想办法吧。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事你了结了,修路的事包在我身上。”
可见,薛文宗乐善好施、热心公益、关心集体是其来有自的:他身上流淌着先辈的热血,祖上的光荣与梦想构建了他的文化心理和精神底色。正基于此,现代新乡绅传承了传统乡绅的精神气质——道德教化、文化传承、热心公益等,在共和国的时空道路上,又与圣徒——老支书不期而遇。于是,乡绅、圣徒、现代新乡绅“三代”人从幽暗的历史隧道里穿越,被共时地安置在世宁村百年的兴衰荣辱中。小说写到,薛文宗得到了村里老支书的耳提面命与殷殷嘱托。因此可以说,老支书的数次教诲和黯然离世,即是一种隐喻:完成交棒,让薛文宗接续上20世纪50、60年代村干部(圣徒)的某些血脉遗传、理想信念。用老支书的土话说,就是“活人要活大家”。最终,冥冥之中恰恰是薛文宗,继承上了祖父、老支书的精神遗产,绘就了从乡绅——圣徒——现代新乡绅的人物图谱,赓续了这一人物谱系,从而具有了继往开来的意义。
然而,新生事物的成长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小说结尾峰回路转,留给读者一个大大的悬念:薛文宗顺应乡亲吁求牵头违章修建薛氏宗祠、在乡领导带队强拆中,包村干部袁芙蓉“被压在了房梁和木梯之下”。事后,薛文宗能不能顺利度过这突如其来的劫难?故事的结局溢出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呈现出间离效果和现实的复杂性。
与此同时,《胡不归》还独具匠心地悬置了一个反讽结构与发问:现代新乡绅的“合法性”问题。对于上级领导,现代新乡绅薛文宗能够走上世宁村的“政治舞台”,纯然是因为自娱自乐主办乡村联欢晚会而“被发现”的,颇具有偶然性质。他是在世宁村工作内外交困的时候,身不由己一步一步地卷入村务矛盾,被“代理村长”的。从他性格和“由民而绅”的运命来看,他是一个不断“成长中的人”。不论薛文宗后知后觉,有着怎样为村里办好事的理想雄心,“代表”党组织的郭副书记的算计,却充满了实用主义的色彩,是一种短视和卑劣的利用,更可能轻易地将这一社会新生力量推向“革命”的反面。有评论者尖锐地指出,“镇上的郭副书记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小说的故事情节里所表现的他的形象,完全是以书记的小算盘设计的。……薛文宗只不过是郭副书记眼里的一个完成他的工作作业的马前卒。比如,修道是逼迫的,给薛文宗一个代理的村主任也是逼迫的。一句话,郭副书记不是老百姓的贴心人,主心骨。”[12]如果说,郭副书记对薛文宗的“提拔使用”和前恭后倨,是出于暂时性的投机考量;假使上级领导对所谓的乡绅的态度呈现的是一种“分裂”的暧昧状态,那么,小说这样的安排是否预示现代新乡绅暗淡的前景?小说最后铺陈到,当薛文宗想丰富村里文化生活满足村民愿景,重建祠堂,并以祖父作为乡绅载入史册被纪念为例,向郭副书记据理力争时,却被狠狠训斥,“你老爷更没什么可学习的,更没什么优秀品质,他当的是国民党的官,要表彰那就应该让国民党表彰去。”薛文宗听罢,刹那间“发现郭副书记的这张脸是如此陌生”。
小说行进到此,不无揶揄地响起“画外音”:上级组织与现代新乡绅,二者由相识而熟稔,再到革命战友,最后复归陌生——是否宣告:他们的短暂“蜜月”就此终结?这不免在读者心中升起一个既是文学的,又是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应该如何安顿乡村自发出现的所谓现代新乡绅,又应该怎样将这些精英以及他们身后代表的广袤乡村,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图景?这是小说赋予的更深层次思考。
——宋恭帝赵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