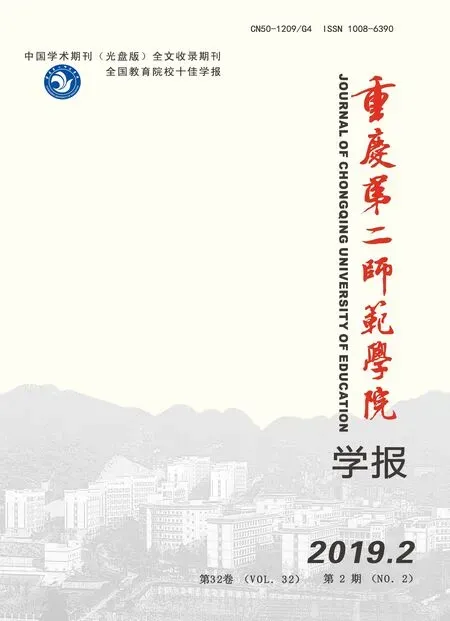繁漪与海伦悲剧命运的异同及其成因
刘春艳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 贵阳 550025)
曹禺《雷雨》中的女主人公繁漪与易卜生《群鬼》中的海伦,这两个被困在婚姻牢笼中的不幸女人,所嫁之人并非所爱之人,而作为女人的她们既然已为人妻,就得有自己作为妻子的责任和义务。她们都曾为追求自由与幸福做出过不同程度的反抗,奈何宿命就是宿命,无论怎么反抗都摆脱不了封建家庭制度与资本主义虚伪道德的束缚,越挣扎越痛苦。无论是繁漪冲破不可抑制的“蛮劲”,撕毁一切,还是阿尔文太太听从命运的安排,服务于自己的家庭,她们的命运终究是个悲剧。
一、 繁漪与海伦悲剧命运的共同之处
(一)无爱婚姻的悲苦人
周朴园娶繁漪,不过是因为他的大家庭中需要一位门当户对的女子象征性地做个女主人,替他操持家中内务。在感情上,周朴园对繁漪没有一丝丝的关爱,甚至拿男主人的威严叫妻子在孩子面前做一个服从的榜样。他经常忙于煤矿的事,很少回家,一回到家,便让繁漪看病吃药,对她没有实在的关心与爱护。周朴园心中还有着自己的前妻,他让下人将侍萍房子里家具的摆设保持原样,桌子上还放着侍萍的照片,不允许任何人将窗户打开,因为那是侍萍还在这里的时候的习惯。周朴园心里装着自己的前妻,不管是因为爱,还是因为愧疚,至少这个在他心里的人不是他现在的妻子。其次,对于繁漪来说,她也不爱这个冷酷专制的周家老爷。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向往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而周朴园是封建专制思想的维护者,他将繁漪束缚在家中,让繁漪没有半点反抗的余地,她恨透了这个剥夺她自由的专制家长。
海伦嫁给阿尔文变成阿尔文太太后,很快发现丈夫的荒淫无度,在外和女人喝酒调情,甚至与家中的女佣“闹鬼”,这表明,阿尔文心里根本没有她这个妻子。阿尔文对海伦不闻不问,在行为上没有像周朴园那样限制自己的妻子,可他的所作所为足以让海伦哀叹自己进错门嫁错郎。她看清了丈夫的虚伪,也承受不住丈夫带给她的痛苦,心灰意冷却也无可奈何。阿尔文太太对丈夫不仅没有爱,抛开夫妻关系,对阿尔文道德的卑下更是厌恶。海伦把希望寄托在曼德牧师身上,逃跑之际,希望曼德先生能收留自己,而曼徳牧师,却用宗教道德准则,将她劝留了下来,继续留在那个不爱她,她也不爱的男人身边。自阿尔文去世后到儿子欧仕华去世,海伦并没有再找情人,自始至终守在阿尔文家,孤独终老,一辈子与幸福的爱情无缘。
(二)男权社会的牺牲品
无论东西,忠贞的妇德理念对于女性来说都是无法逃避的伦理大网。在东西方传统文化中,婚姻被视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家庭被视为基本的社会细胞,其核心特征是以男性利益为中心。男性在生产中发挥了极大作用,掌管了家庭,并且制定了各种制度以确保女性贞洁得以实现,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失去了自由,被改造成符合男权意识规范要求的谦逊、温柔、隐忍的女人。繁漪和海伦就必须在这种标准与原则下生存,成了男性的附属品,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
周家的两个男人操控着繁漪的命运。一个是周朴园,另一个则是周萍。周朴园既是家长,也是丈夫,所以,繁漪对他的反抗是无效的。当繁漪拒绝喝药的时候,周朴园想尽一切办法让她服从,甚至利用孩子,让周冲、周萍请求繁漪喝下。脑科专家来到周家给繁漪看病,繁漪称自己没有病,对医生避而不见。可是她每一丝反叛的火焰,都会被周朴园浇灭。男人的意见就是法律与命令,作为女人,只有遵守与执行。不管丈夫如何凶横、自是、倔强,繁漪都只能承受。身为周萍的继母,繁漪本应该得到周萍的尊敬。但另一方面,繁漪曾经是周萍的情人,从两个人的恋爱关系出发,周萍则站在了主导地位,繁漪成了被动,面对周萍对她的“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她无可奈何。繁漪在周萍面前虽然得到过爱情,但她始终是卑微的,周萍有一千个理由抛弃她,无论自己怎么谴责、哀求周萍,周萍都无动于衷。
海伦的丈夫阿尔文没有明显干涉过她做任何事情,但他在家中的男主人地位,迫使海伦对他忠心。既然嫁给了阿尔文,就必须靠紧她选定的并且上帝叫她贴紧的这个男人。可见,在当时的社会,男人在家庭中有着支配性的特权,即使阿尔文不主动支配海伦,她也应该自觉地服从。正如曼德牧师所说:“阿尔文太太的义务是低声下气地忍受上帝在她身上安排的苦难。”[1]279上帝给了男人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与生俱来就能让女人对他们百依百顺,男权思想下,阿尔文处于权威的位置,尽管他平日放荡、不守规矩,但他的女人没有权利抱怨。男权文化教育女性要做贤妻良母,要相夫教子。海伦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为丈夫和儿子无私奉献,甘于牺牲,并因此献出了自己的整个世界,然而她得到的是满腹的辛酸与无尽的痛苦。
(三)不成熟的个性解放者
嫁到大家族中的传统女性,深入骨髓的封建意识使她们明白,她们的责任就是相夫教子,婚姻的幸与不幸都是命中注定,作为男人的附庸,不管生活过得怎么样,接受就好,内在的个性终究得不到释放。但是繁漪与海伦做到了普通女性不敢为的事情,挑战传统的封建礼教与资产阶级虚伪的旧道德,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然而她们在释放自己情绪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个性解放的思想还不够成熟。
繁漪与继子“闹鬼”,与丈夫反抗的行为都是她对命运不甘的表现。她要随心所欲,她觉得自己应该追求美好的生活,要把积藏在心中的压抑全都释放出来。然而她的反抗都是徒劳无功,甚至适得其反。她敢违背周朴园的意愿,周朴园就有办法叫她服从。她拒绝喝药,让四凤倒掉,但她在周朴园面前可不敢这么做。周朴园逼她把药喝下,繁漪虽然反抗了,但最终连缓一缓再喝的机会周朴园都不给。虽然繁漪在周萍那里找到了希望,她宁愿背负乱伦的罪名也要和继子在一起,周萍却因为害怕受到良心的谴责抛弃了她。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周萍不给她依靠,繁漪怎么争取都没有结果。这个叛逆者、追求个性解放的女人,自身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却反对儿子和四风在一起,认为四凤始终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下等人,配不上周冲和周萍。
海伦不愿和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况且这个男人是何等的虚伪罪恶。唯有离开,或许是最好的选择。海伦从来不肯忍受束缚,她要求个性解放,不愿意服从守规矩,她想冲破资本主义旧思想套在女人头上的枷锁。可惜,曼德牧师用鬼话一劝,她就乖乖地回去,并且真正做到了曼德牧师心目中的好妻子形象。从这里来看,海伦的个性解放思想还不够成熟,她的思想里也残留着旧社会虚伪的宗教道德观,如果她真的一心想反叛,曼德牧师的劝告对他来说是没有用的,她可以像娜拉一样毅然离开。
二、繁漪与海伦悲剧命运的差异
(一)反抗与妥协的斗争方式
繁漪与海伦对自己的婚姻生活都感到不满,但她们面对不幸生活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繁漪渴望自由,想要追求属于自己的真爱。她与继子周萍的爱恋,是对压抑已久的情绪的释放,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反叛,是对丈夫周朴园的报复。当周萍抛弃她,要离开周家的时候,繁漪以责任的名义谴责周萍,她不想放弃任何挽留周萍的机会。面对自己的情敌——四凤,繁漪也是想方设法让她从周萍的身边离开。在她的思想里,从来没有“听天由命”的说法,不想要的就拼命推开,想得到的就努力争取,无法拥有的东西就亲手将它毁灭。周朴园逼她喝药的时候,她执拗地拒绝,可是她执拗不过家中老爷的威严。虽然她很清楚,周朴园一句话就可以把她所有的梦打破,但她依然选择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折腾。
海伦并没有像繁漪那样与命运反抗到底,她曾尝试性地为自己创造了一次离家出走的机会,当曼德牧师拒绝支持海伦逃跑的时候,她也并没有固执地请求曼德牧师带她离开,或许是因为她在曼德牧师那里未曾得到过爱情的温暖,所以不会像繁漪那样为自己想要的爱情义无反顾。海伦回到了丈夫身边,尽到自己作为妻子的责任,在女主人的位置上做好自己的本分。为了傍晚和夜里不让阿尔文出门,海伦耐着性子陪丈夫在家里喝酒胡闹,喝醉了还要把丈夫拉去休息。海伦没有像繁漪那样反抗到底,而是选择在不幸的家庭中逆来顺受。为了孩子,她不得不忍受。海伦不仅尽了一个妻子的责任,她还掌管了丈夫的很多事,她添置了产业,做了些改革工作,采用了节省人力的新设备,在阿尔文老毛病发作,发牢骚骂人的时候,她挑着千斤担子,一个人受罪。纵使心中有百般的不情愿,她还是在那栋暗无天日的别墅里度完了余生。
(二)淡薄与浓厚的女性意识
所谓女性意识,简单说是女性对自身独立地位的觉察,拒绝接受封建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通过自身独立与努力获得人格与生存的尊严。
曹禺笔下的繁漪在反抗周朴园家长制压迫的过程中,她的女性意识正在觉醒,但她对周萍的依恋明显表现出这份女性意识依然淡薄。易卜生笔下的海伦,没有像繁漪一样处处反抗自己的丈夫,没有幸福爱情的她选择了在事业上独立。
爱情能够激发一个人的力量,却也能使人堕落。周萍就像是黑夜里的一颗星,给了繁漪希望,让她恍若重生。繁漪把一切都寄托在周萍身上。曾经在她安静等死的时候,是周萍将她救活,从此周萍成了她生活的动力。女性意识的淡薄,使繁漪没有认识到女性自身的局限,由于自己不够独立,她没有选择出走,而在作为男性的周萍面前,迷失了自我。繁漪为了自己与情人,可以不顾道德伦理,和他一起在客厅里“闹鬼”。在周萍抛弃她之后,繁漪像发了疯似的,在家中更是坐立不安,除了周萍的事,什么都不关心。周萍要离开周家,繁漪愿意丢下自己的亲生儿子周冲随着周萍一起离开,甚至愿意和四凤一起留在周萍身边。被两代人抛弃的繁漪,依旧不明白自身的力量——依附丈夫,依附周萍,不如依靠自己,自己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海伦在被曼德冰冷地拒绝之后,并没有固执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爱情。她比繁漪有自主权,也有家庭地位,所以她有条件去做一些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抛开情感问题,海伦有主见有能力,她的理性与浓厚的女性意识支撑她独立起来。她没有因为自己又回到家庭的牢笼中而沉沦,眼看荒唐的丈夫没了指望,海伦接管了家业,并做得井井有条,颇见效益。也正是因为海伦每天都忙碌着,所以她才不用随时去想那些糟糕的事情。阿尔文死后,海伦将丈夫的家产全部捐给慈善机构,完全靠自己多年经营的产业维持生活并抚养小阿尔文,在她的努力下,阿尔文还拥有了大善人的名声。在受到“道德与义务”的双重压迫下,她还能够有条不紊地操持着家中事务,证明她够独立、够强大。
(三)失责与尽责的妻母身份
中国传统强调男尊女卑,即夫为妻纲,判断女性善恶的标准是女性是否遵从“三从四德”的儒家礼仪、注重妇德、对丈夫从一而终。女性在家庭中要辅助男性,以维护男性社会的中心统治秩序,在家要相夫教子。“家庭天使”是传统西方对贤妻的定义,作为妻子与母亲所享受的权利与应尽的职责更多的是神的旨意。
周朴园虽然冷酷虚伪,在他专制家庭的治理下,家中的每个人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但是至少这个家庭是完整且有秩序的。繁漪的反抗,让周家走向了毁灭,不仅繁漪是悲剧人物,周家的每一个人都成了繁漪悲剧命运的陪葬者。一个大家庭中的男主人与女主人之间不能齐心协力,在治理家庭的过程中势必会出现难以化解的矛盾,家庭的和谐发展便会受到阻碍,繁漪一而再、再而三地与周朴园对抗,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孩子,都造成了伤害。在周家,繁漪作为母亲,没有正确教导孩子,对周冲关心得太少,连亲生儿子的年龄都记得不太清楚。在周萍面前,更是没有扮演好继母的角色,与周萍乱伦,屡次在客厅中“闹鬼”。她聚集周鲁两家,抖露两家复杂的关系,逼得四凤跑出客厅触电而死,而小儿子周冲追了出去,拉上四凤,也触电身亡,周萍在接受不了事实的情况下,也选择了自杀。繁漪本想报复压迫、背叛她的人,却万万没想到,毁灭了两个虽不和谐,但却完整的家庭。繁漪没有尽到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她的世界里只有自己和周萍。
海伦重返家中,尽管丈夫一如既往地嗜酒,寻欢作乐,作为太太的她却并没有揭穿他的真面目,而是努力替丈夫维护好人形象,为了掩盖丈夫做过的坏事,掩盖他的伪善,她甚至建立了孤儿院。在发现阿尔文与佣人私通并生下一女后,海伦没有与丈夫争吵打闹,也没有将丈夫的丑事揭发出来,为了掩盖真相,海伦给了女佣乔安娜一笔钱,让她直接离开。对丈夫与乔安娜生下的私生女——吕佳纳,海伦将她视如己出。海伦尽力地做个贤妻良母,纵使心中百般无奈与万分痛苦,她都强忍了下来,把管好家庭、照顾好丈夫当作一种使命,追求自由失败的她认为家庭和谐就是最好的结果,阿尔文所做的事,让这个家庭蒙上耻辱,而她的责任,便是努力维护这个家。海伦对儿子欧士华的爱近乎偏执,她将欧士华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毕竟在那个家中,丈夫依靠不上,欧士华则成了她唯一的寄托与希望。海伦对阿尔文的隐忍都是为了欧士华,她不想让欧士华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人。欧士华还不到七岁,海伦就将他打发出门,她觉得要是孩子呼吸家庭的肮脏空气一定会中毒。欧士华回到家中,海伦对他百般呵护,尽可能满足欧士华的一切要求。尽管对于欧士华来说,他还是缺少母爱的,整个家庭也并不和谐美满,但不管是从意识,还是行动出发,海伦一直在努力维护自己的家庭,承担着自己作为母亲与妻子的责任。
三、繁漪与海伦不同悲剧命运的成因
(一)敢爱敢恨与胆小懦弱
繁漪是一位具有新时代气息敢于反抗的资产阶级女性,向往自由、渴望爱情、蔑视一切社会禁锢、毫不掩饰自己的欲望、敢爱敢恨,像客厅外的雷雨,咆哮、疯狂,这决定了她的斗争方式是激烈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压迫,繁漪越是挣扎,越是被周朴园逼得无处可逃,她越是处处与周朴园作对,甚至对周朴园的压迫与伤害进行报复。当爱情来临,繁漪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接受,当爱情快要离她而去的时候,她也并没有听天由命,而是选择努力争取。她急切渴望自由,选择挣扎,也证明她对未来的美好生活还抱有期许,不论是被周朴园压迫还是被周萍抛弃,繁漪都没有过放弃的念头,她坚韧不拔与敢爱敢恨的性格驱使着她清除一切障碍,向着自由的方向前进。
如同繁漪一样,在海伦的骨子里,她固执任性、不服从、不守法,可是她并没有像繁漪一样在家庭中爆发出来。这个无声的叛逆者选择了在外人面前做一个端淑贤惠的妻子。海伦除了一次不成功的出走,再没有为改变自己的婚姻做任何努力。“从回到阿尔文身边的那一刻起,海伦就压抑了心中对‘阳光’的渴望而选择了对‘阴暗’的顺从与刻意的隐瞒,让外人看不出自己婚姻不幸的蛛丝马迹。”[2]249她连在家中与丈夫吵闹的勇气都没有,阿尔文与女佣乔安娜在家中暧昧,并生下一女,作为家中女主人的海伦没有为此事与他们产生纠纷,反而给了乔安娜一笔钱让她离开。阿尔文太太按照曼德牧师所说的,做一个尽职尽责的妻子,替阿尔文操持着家庭产业,使之兴旺。她是软弱的,承认自己是个胆怯的人,她对所有人隐瞒了丈夫做的荒唐事,因为她害怕破坏阿尔文在孩子心中的理想形象。由于海伦顾虑太多,唯恐后果不堪设想,她的软弱使她没有像繁漪那样不顾一切地咆哮,她所有的不幸与悲痛也只能在多年之后以倾诉的方式发泄。由于软弱,她选择了服从,也由于软弱,她选择了隐忍。
(二)“三从四德”与理性独立
中国是一个以儒家文化为主的社会,“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思想已根深蒂固。传统社会中的男尊女卑思想,造成女性对男性的依赖,女性缺乏主体意识。繁漪心中有“既嫁从夫”的观念,在家中没有权力也没有地位,因此繁漪尽管敢挑战旧制度的压迫,挣脱传统思想的禁锢,却始终不敢与周朴园彻底决裂。“三从四德”下的男女分工是“男外女内”,女性的内部空间是有限的、封闭的,没有足够的发展潜力,除了在治家上的责任与义务,她们认识不到女性独立的价值,无法通过自身独立与努力获得人格与生存的尊严。
在西方文化中,女性的思维方式多呈现理性,西方女性意识的觉醒,始终体现着她们向男权思想主动开战、她们会更加主动、更加积极地争取自由和权利的自主性,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和未来。西方女性在家庭中作为个体的人生存,在精神上有一定独立思考的空间,具有独立的人格意识。在西方,妻子和丈夫均可在外谋职,共同承担家庭的经济责任。在丈夫过世之后,女性的社会身份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她们拥有对自己财产的支配权。所以,西方女性的女性意识更为浓厚,她们具有经济上的独立性,更具有世俗生活的相对独立性。
(三)个性解放与宗教影响
繁漪不顾封建礼法而高呼:“我不是他的母亲,不是,不是,我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3]46这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表现。繁漪在追求个性解放的过程中反抗的是周朴园,破坏的却是整个家庭,当她冲破牢笼的热情爆发时,已然忘了自己作为妻子与母亲的责任。不论是在丈夫的压迫下挣扎、追求自由,还是在周萍的温暖下迷醉、追求爱情,繁漪始终是为了自己。她不甘委屈自己,成全别人。坚守在母亲与妻子的岗位上,就必须放弃个性解放,而对于这样一个有着“雷雨”般性格的女人,选择了个性解放,同时失去了一个中国传统女性在家庭中安分守己、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身份。
海伦回到家中,尽到了作为妻子与母亲的职责。这是一种顺从,这种顺从具有一定的宗教属性。曼德牧师作为虔诚的宗教徒,处处履行自己卫道的职责,灌输给海伦资产阶级的宗教意识,成功地以上帝的名义将海伦劝回家中,也因为海伦对上帝的信奉,对基督教信仰的虔诚,使她能够坚守在不幸的家庭中。上帝要求信徒之间彼此关爱,甚至是爱自己的敌人,这样的教义促使女性无条件地宽容。因此,女性的贤德是一种宗教信仰之善。《圣经·以弗所书》说:“你们做妻子的,应当服从自己的丈夫,如同服从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凡事顺服丈夫。”[4]344海伦既然选择回到丈夫身边,就必须对上帝敬畏,接受上帝赋予她的使命,执行上帝的意志,做一个“家庭天使”——尽职尽责的妻子与母亲。
作为东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繁漪与海伦的性格、思想、接受的文化不同,以致她们在悲剧命运下的抗争方式、表现出的女性意识与妻母身份的责任意识也不同。繁漪敢爱敢恨,勇于斗争,却因为传统思想的禁锢,认识不到自身的局限性,无法独立而摆脱对男性的依附。海伦的理性独立,体现了她浓厚的女性意识,然而她胆小懦弱,并且受到宗教的影响,放弃了追求自由与幸福的生活,将一生奉献给了家庭,是旧礼教的殉道者。正如黄爱华所说:“繁漪的失败,正说明了中国妇女争取解放道路的曲折性和斗争的艰巨性。”[5]91社会在发展,制度在改革,文明在传播,女性自身也要学会独立,不依附男性生存,掌握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