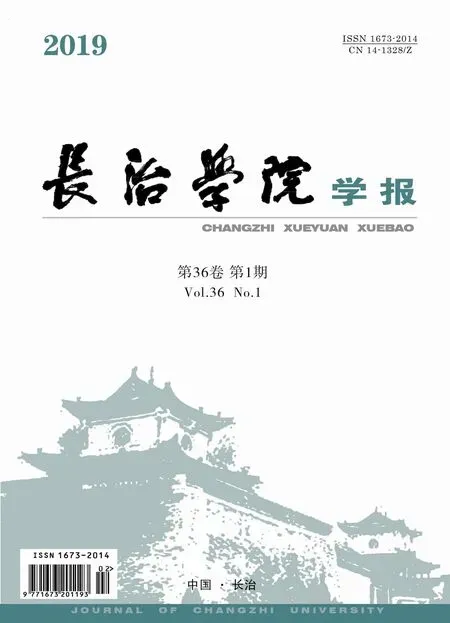山西民俗在新生代电影中的的表达与功能
——以贾樟柯电影为例
叶玮琪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生代电影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以边缘人形象出现的对于中国底层生活的高度关注,就是企图通过影像建构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历史记录。”[1]而如何在影片中更为有力地表现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就需要从他们的生活文化入手,其中独特的地域民俗文化意象发挥着重要的表达与功能。作为新生代电影导演的重要代表,贾樟柯的影片始终具有浓郁的民俗情怀。他总是将镜头对准自己的家乡,对准饱含社会多数小人物命运的辛酸苦辣的地方。无论是“故乡三部曲”还是之后著名的《三峡好人》、《山河故人》,贾樟柯的故事发生地大多都落脚在他的故乡——汾阳县,推之广及山西省,或是故事叙述不在山西,但都与山西有所勾连、密不可分。在这样大的故事背景下,山西特色民俗乃至北方民间文化便成为其影片的一大重要表现元素,也折射出他浓郁的民俗情怀。民俗外在表现为一种程式化的生活样式,并以这种外在表现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各个方面。[2]正是那些带有浓浓烟火味儿和人情味儿的民俗,或者说是一种民间文化或民间力量,助力贾樟柯在打磨他背负着理想的影片道路上不断前行,成为讲述中国故事和提升我国国家形象的优秀影视作品。
一、山西民俗意象表现人物形象
2018国庆档影片《江湖儿女》的热映将贾樟柯再次拉回到大众的视野中来。继三年前备受瞩目的《山河故人》,可以看到的是《江湖儿女》仍旧深深刻有“贾樟柯”式的烙印。从最初的《小武》开始,贾樟柯的电影始终保有着一些不变的特色:浓重的故土情怀、“粗糙”而又真实的电影风格、对底层人物的关注等等。对这类群体的刻画,只有精准把握了他们生活中的“筋骨”而不仅仅停留于“皮肉”,才能将他们的精神状态呈现出来。独具特色的生活文化,便是将电影画面引向人物内心世界的一种隐形介质。山西作为一个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省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和民风民俗。民俗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文化,贾樟柯在他的影片中大量采用了各种民俗意象,这些典型意象在电影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不仅帮助观众了解影片文化背景,更在特定情节中承载着特殊的情感和意义。
从整体上看,贾樟柯的影片大多与山西有关,几乎每部影片都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表现着山西特色。影片中的主人公大多为社会底层人物,他们的衣着简朴、单调甚至毫无特色、千篇一律,没有任何因拍摄需要而进行的矫正、修饰,在《任逍遥》中更是特意表现了山西煤矿工人的衣着。而正是因为这种真实,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饱满,也使得像《站台》中张军、崔明亮换上时髦喇叭裤这类情节更具意味。影片对县城小人物衣着外貌的原始保留蕴含着对山西朴实的生活文化的一种尊敬。山西人的主食历来以各色各样的面食为主,贾樟柯的电影中亦多处运用面食这一饮食元素来表现山西民俗文化。影片中每个涉及用餐的情节几乎都少不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站台》中张军从广州归来更是说不喜欢广州的饭,想念汾阳的“合子面”。山西的面食对山西人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承载着乡土情怀的元素,而不仅是单纯的果腹之食,对家乡“合子面”的想念传达的是山西人普遍的家乡意识。《站台》整部影片表现了汾阳县城文工团青年对更广阔天地的向往和对家乡眷恋之间的矛盾,从这个主题上讲,这一情节归于主旨,意蕴深刻。在居住方面,导演选择寻常百姓家的窑洞、土炕等作为一些内景的拍摄地点,使影片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山西特色。在交通出行方面,贾樟柯选择了驴车、老式自行车、摩托车、拖拉机、卡车等山西常见的“粗犷”的交通工具,并且多用以配合长镜头。在《小武》开头,小武的好友骑着老式自行车载着小武穿过汾阳街道,两人的对话交代了大量信息——小武的身份、故事的背景等等。小武骑着摩托车离开家远去的背影;《站台》中崔明亮等人开着卡车去看火车以及后来坐卡车四处演出;《任逍遥》开头斌斌骑着摩托叼着烟漫无目的地前行的镜头;小季骑摩托带着巧巧在公路上驰骋和反复打火上不了坡的画面等等,都配合使用了长镜头。这些情节无一不与人物内心世界和影片主旨相对应,小武内心的失落;文工团成员对更广阔天地的追寻、迷茫、回归的过程;斌斌和小季内心的迷茫与虚无。这些打有家乡烙印的交通工具载着他们前行,看似驶向远方,却总是困于现实。影片每一处看似生活化的情节和道具的使用,都反映着人物内心与现实的拉锯。
具体来说,汾阳县城的城墙、北方农村中的柴火、代表山西特色的汾酒、那个时代当红的晋剧等等民俗元素在影片中被大量使用。这些看似只是影片布景道具的事物实则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贾樟柯说:“讲故事不是我的兴趣,把我对生活的感觉、时间的感觉拍摄出来才是我的兴趣。”可以看到的是,他的影片叙事节奏沉稳而缓慢,与现代许多快节奏的叙事商业电影截然相反。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生活本身并不是一直在发生故事,大多数的时间我们都在停留,这也就是贾樟柯所说的:“电影中剪辑掉的画面,才是我们多数时候的生活状态。”因而这些民俗元素的运用,在电影中便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每一个道具都为影片叙事基调服务,每一处场景或反映人物心理状态或营造情节冲突。
二、山西民俗活动丰富影片内容
在民俗电影中,要让民俗参与塑造具有人性共通性与个性的饱满、立体的民族人物形象;要以民俗与环境氛围营造有机结合,使影片具有真切的生活质感,通过民俗来构建人物和环境的关系。[3]因而除典型的民俗意象之外,民俗活动更是贾樟柯电影中不可或缺的场景。人物的深度参与、活动的深厚意蕴,内在的文化呈现,使得民俗活动成为表现影片主旨的一大重要元素。
民俗活动因其历史惯性和社会功效深度融合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不仅丰富了电影的表现内容,激发人文思考,而且围绕影片主题突显特定区域人物的价值取向和思维范式。在贾樟柯的电影中,山西的民俗风情助力表现影片中小人物的情感、内心的坚守、社会变革下的动荡与追寻的画面俯拾皆是。
贾樟柯影片中的民俗活动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活动,另一类是寄托人们美好愿望的信仰仪式。《小武》中小武妹妹用农村珍贵的猪头肉招待城里来的二嫂,反映出中国社会中始终存在的一种阶级层次;小武曾经的好哥们小勇结婚时的排场,整箱整箱的上等烟酒、自家院子里大锅蒸煮的饭菜,在影片中暗示的是二人再也回不去的友情,唤起的是许多人关于故土的记忆;《站台》中文工团表演的山西民间歌曲《火车向着韶山跑》、《在希望的田野上》以及二胡、笛子等特色乐器展现特定时期下人们的文艺活动状况,更反映了主人公内心的热望和活力,因为怀有热血所以才会追寻,因为心中有力量所以勇于回归。《山河故人》中过年时有唱伞头秧歌的习俗,其作为一种祈福仪式在影片中不仅是一种民俗,更是贯穿全片的一个意象。影片开头巧巧是伞头秧歌的领唱,到影片结尾时她说自己“早就不唱了”,这一对比承载着人物一生心境的变化,更反映了家乡巨变给每一个人带来的冲击。
带有民俗意味的仪式在推动情节发展、表现人物情感方面有着使效果加倍的作用。《三峡好人》中韩三明到奉节的唯一的朋友小马哥在施工中意外死亡后,他默默地给小马哥点上了三支烟。在葬礼中,人们常常有给逝者点烟的习俗,在影片中这一举动更是有以烟代香的含义。面对小马哥的意外去世,韩三明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悲伤,显得平静而哀伤,他目送小马哥的尸体随船逐渐远去。影片中表现的煤矿工人这一群体每日面对生死,为了生存行走在生死边缘,他们见多了死亡,并非情感麻木而是身不由已。贾樟柯将镜头对准了这样一个群体,特殊而又没有个体主体性。正因为民俗活动意蕴复杂而又深刻,且在千百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真正深入到底层民众的生活中,因而韩三明点上三支烟这一简单的情节能胜过千言万语,成为小人物“无声的大力量”。在《江湖儿女》中,巧巧和郭斌时隔五年再次见面,郭斌牵着巧巧的手为她补了“跨火盆”这一仪式。贾樟柯在这一影片中刻画了一批“江湖”人,但他们归根结底也是有着情义和日常的小人物。在巧巧为了斌哥坐牢五年后出狱时,斌哥为了所谓尊严、金钱并没有去接她,甚至在她找寻自己的过程中处处躲避。相见无言,他让巧巧“跨火盆”去晦气。其中包含着郭斌内心的愧疚、悔恨以及对巧巧的祝福,其情感的复杂真是一言难尽。这是贾樟柯电影一贯的特质,对话不多、台词简单,善于用大量的空白、沉默和简单的行为、眼神表现人物内心世界,并抛给观众去独自揣摩。郭斌和兄弟们在迪厅里喝着“五湖四海”酒说着“五湖四海皆兄弟”、“肝胆相照”的誓言,这是一种江湖上的传统,表面光鲜豪迈却和郭斌没落的后半生形成了鲜明对比,讽刺意味不言而喻。正是导演对这些民俗行为的重视,对自身背景的正视,搭建了电影与土地之间的联系,从而使这样一个落脚于北方小县城的影片能够具有广泛的文化心理认同。
三、民俗文化氛围强化影片背景
长期以来,贾樟柯总是将镜头对准自己的家乡——山西省汾阳县,而这正是他影片独具特色的缘由。他最独特最吸引观众的地方,在于他始终直视自己的经验世界并无比相信自我的经验价值,没有任何方式能比亲身经历更为深刻地体会某种情感、了解某个社会,因而他选择拍摄自己最熟悉、最了解的地方和生活,并且将之以原始的视角呈现。他表现最真实的、不加修饰的普通生活。尽管很多观众普遍乐意去消费那些自己生活中不存在的、惊心动魄的情节,不愿花钱去审视社会中最广泛存在的生活状态,但这并不妨碍他创造出一部又一部精彩的电影。
民俗是最富于中华民族特征的本质的东西,也是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异质品。它最能深入到民族精神的根底,也最能制造民族风格的灿烂景观。[4]贾樟柯对民俗的运用并不是刻意、矫揉、生硬的,而是自然且流畅的,这源于他自身对生活的经历和体验,因而他的影片始终有民俗生活的气息。他摆脱了以往电影制作在剪辑、声光等方面的定式,而将电影作为一个个体、一个独立的生命去看待。
贾樟柯的电影全程使用方言,并没有为了迎合大众而使用全国统一的普通话。这是他的坚持,是对电影本身的尊重,对电影价值的把握。语言作为人类沟通交流的主要方式,其地位显而易见,可以看到的是,方言的使用总是为电影添色,不仅帮助调和一种“山西味道”,更在人物情感的表达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使是在《三峡好人》这样故事发生地不在山西的影片,主人公的普通话也必是带着山西口音的。他们带着一身家乡的气息而来,承载着“家”沉甸甸的分量,寻找着伴侣却都不得而归。家乡的呼唤始终萦绕在主人公周围,他们来寻自己的小家,却也始终不可能脱离故土这一“大家”。方言的存在就像连接个体与家乡的桥梁,每个人都始终生活在自我生活的文化氛围之中。
米歇尔·福柯曾说:“他们(历史中的无名者)应该属于那些注定要匆匆一世,却没有留下一丝丝痕迹的千千万万的存在者。”贾樟柯所关注的就是这些存在者,我们似乎能从影片的人物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因为我们都是众多小人物中的一员,也迷茫、也努力、也追寻、也犯错。他始终实践着这种“纪实美学”,因为这种对生活高度还原的忠实刻画,使得影片有原汁原味的“山西味道”。同为山西人,在观看贾樟柯的电影时总能找到自己生活的一点片段、一丝线索,进而产生一份认同。所谓民俗,并不仅仅是指那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习俗,从广义上来讲,更是一个地方的生活状态与生活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贾樟柯将这种状态生动还原并将之搬到荧幕上,让我们在影片中看到自己,展示有点物质却又有点可爱的大多数人。
贾樟柯曾谈到更喜欢自己的电影被称作独立电影而非第六代电影,这或许包含着一种他对自己电影的定位。他着意在影片中表现本土文化,极富中国特色,极富山西特色,他在通过自己的方式坚持着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对“独一份”的珍视和保护,是他影片最大特色。通过运用民俗的元素,尽力再现真实的生活状态,不对生活进行过度的艺术加工。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场面调度的把控,展现生活的原貌并非随意拍摄,而是改变对电影画面取舍的标准,而如何掌握这一没有标准的标准,便需要他本人对生活深切的体验和感受,这大概也是他为何总将拍摄地定在家乡的原因之一。贾樟柯说拍电影就像一个探险的过程,我们知道目的地但却不知道这一路的风景,他在拍摄过程中总是擅于捕捉“意料之外”的镜头并加以取舍运用,因此他的影片总是自然且生活化得恰到好处。
观众在他的影片中可能很难寻找到强烈的刺激,他的电影没有惊心动魄的打斗场面或波澜壮阔的情节,但观影过后总是会有一种难以消散的绵长的情绪,这可能就是生活的力量。
电影作为声画一体的艺术展现形式,是最能记录反映生活的形式,而民俗亦可以为电影创作开辟一些新的思路。民俗承载着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地区人民独特的文化,是一种凝练的语言,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我们能够通过民俗现象实现沟通。如今新民俗电影的蓬勃发展,不仅是民俗为电影注入新鲜力量的结果,也是电影帮助民俗焕发新活力的表现。随着我国电影产业进一步深度参与到全球性文化商业协作体系,创作出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能够正面讲述中国故事、正面提升我国国家形象的影视作品,是中国电影面临的机遇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