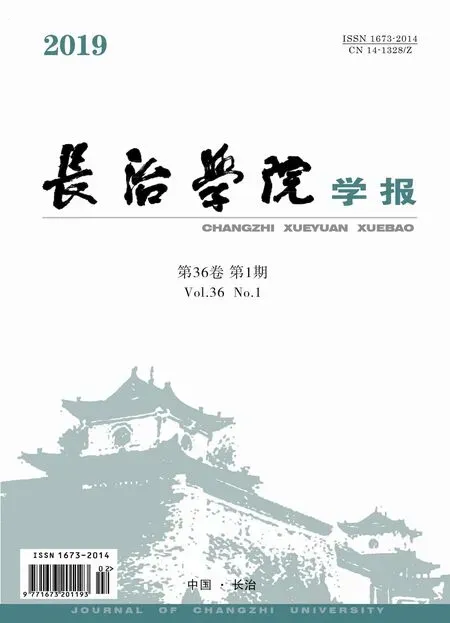传统文化视域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解读
——兼谈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
白立强
(衡水学院 董子学院,河北 衡水 053000)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归根结底体现在文化层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课程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担负着不可或缺的责任。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要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内容”方面实现中国化,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着契合点。
余秋雨认为,文化就是“由精神价值、生活方式所构成的集体人格”[2]3。“中国文化……主要在求完成一个一个的人。”[3]16或者说,“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乃在‘教人怎样做一个人’。”[4]“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5]46。同样,“马克思主义是人的解放学”[6],其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由是,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是将人的存在和发展作为基本关注点。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着眼点是人
在中国文化之中,人(修身)既是成就事业、治国安邦的起点,也是事业发展的价值取向。人、事双方在双向互动过程中,相互促进、彼此助益、不断优化、共同提高,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模式。正如《大学》所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人之为人的第一要务即修身。唯此,方得以实现齐家、治国乃至平天下之作为。如果说修身是走向事业成功的保证,那么,事业成功也同时意味着对于生命自身的进一步促进与完善(修身)。故《大学》有言:“仁者以财发身”。历史上范蠡于财用三进三出之事实就是典型例证。
《论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之作包含着丰富的人学思想,即处事做人之学[7]。如《论语·子路第十三》中,面对樊迟请教稼穑之事,孔子称之曰“小人”。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孔子轻贱稼圃,因为孔子也曾自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第九》)。孔子于樊迟所问之断言,实际上表达了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寄希望其成为“弘道济众的有位君子”[8]491。唯有诸多君子人格式人物,才具有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责任以及执行力,盖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为此意。正是基于此,《论语》中一再强调君子之气象格调,如:
君子之言行: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第四》)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第二》)
君子之气象: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第七》)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第十三》)
君子之志趣: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第四》)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第十四》)
君子之品格: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第十三》)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第十四》)
君子之操守: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第五》)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第十六》)
樊迟之关注非孔子之预期,即其属于“小道”范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第十九》)“小道,如农圃医卜之属。”“杨氏曰:‘百家众技,犹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无可观也,致远则泥矣,故君子不为也。’”[9]222稼穑纺织作为谋生技术乃不可或缺的生活手段,然而,对于君子而言,不应局限于此,而应志向高远,心怀经世济民之志,身具治国安邦之才。而不应该成为“见小暗大”“从物如流”的“庸人”。只有“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的士人,以及“仁义在身”“笃行信道,自强不息”的君子才是孔子所预期的基本人格。(《孔子家语·五仪解》)
中华传统文化着眼点是人——不是物质意义上的人(此无异于其他生命现象),而是精神意义或者说价值意义上的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看一切问题都和人联系在一起,都要思考它对人有何教益。”[5]78-79由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第八》)就是以非理性的“美学方式”发挥着“以美启真”的作用[10]182。如同“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第二》)之内涵一样,“诗三百”的人文意蕴即“无邪”,无邪乃“性之然”“真情、真性流露”[11]。总之,就是通过诗书礼乐之教化,使人成为具有真、善、美之生命品质的完美之人。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着力点是成人
《荀子·王制》有言:“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意味着,人之贵在“有义”。义者,宜也。人以内在之义实现着外在之宜,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此,人首先须自立、自达,即成人(成己),方可成他人与物。在《论语·宪问第十四》,子路问及“成人”。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第十四》)
“成人,犹言全人。”“言兼此四子之长,则知足以穷理,廉足以养心,勇足以力行,艺足以泛应。而又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使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而其为人也亦成矣。”“程子曰:‘武仲,知也;公绰,仁也;卞庄子,勇也;冉求,艺也。须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然而论其大成,则不止于此。’”[9]167以当下言之,成人就是“成就人之所以为人者”[8]537。“犹完人,谓人格完备之人。”[12]361
同样问“成人”,由于问者不同——颜渊与子路,孔子的回答也不同。如果据程子所言,于子路之问而所答为“小成”或“初成”,那么,孔子答颜渊之问则为“大成”。如:
颜渊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情性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说苑·辨物》)
“成人之行达乎情性之理,通乎物类之变”,“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等。正如《中庸》之成己、成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中庸》)
“诚虽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则自然及物,而道亦行于彼矣。仁者体之存,智者用之发,是皆吾性之固有,而无内外之殊。既得于己,则见于事者以时措之,而皆得其宜也。”[9]288-289一旦人以己之仁度物之义,则意味着人以自身之完美成就万物之性天,即“与天地参”: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
“尽其性者,德无不实,故无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细精粗,无毫发之不尽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赋形气不同而有异耳。能尽之者,谓知之无不明而处之无不当也。此自诚而明者之事也。”[9]287
《道德经》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以法天则地为圭臬,上达天道,下合地道,中为人道。从而以自身之成实现、助推与成就着天地之间万事万物达致和合共生之情状。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人
“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我所说的正面知识是指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13]如: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第二》)
“从心所欲不逾矩”即“一任己心所欲,可以纵己心之所至,不复检点管束,而自无不合于规矩法度。此乃圣人内心自由之极致,与外界所当然之一切法度规矩自然相洽。”[12]29孔子以自身的生命历程为中华文化塑造了人之价值意义上的生命,即自由与全面发展。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当知人类尽向自然科学发展,尽把自然所与的物质条件尽量改进,而人类生活仍可未能获得此一最高之自由。又若人类尽向社会科学发展,尽把社会种种关系尽量改进,而人类生活仍可未能获得此一最高之自由。”[14]98
于此,马克思主义也有类似的判断。“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15]显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自由的实现源于现实而又超脱于此,即源于物质层面而归结为精神层面。这与中国文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钱穆先生如是说:“儒家种种心性论道德论,正与近代西方思想之重视自由,寻求自由的精神,可说一致而百虑,异途而同归。”[14]98纵观整个人类社会,其发展的基本路径为由重视物质生产发展到依赖精神、信息生产;由关注外部世界到关注内在生命。其间,就是人类不断追求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这同时表明:“人类之追求自由,则只有……到达于精神我道德情状的生活,才始获得了我之人格的内在德性的真实最高的自由。”[14]96
故《中庸》有言:“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就在于外在之道德律令与君子之内在心性安守相浸相沁、优游涵泳、浃洽于中,从而达到道妙暗合之境。
就现实社会而言,“人既才性不同,则分途异趣,断难一致。”[14]61但就人之价值生命而言,“人人各就其位,各有一恰好处,故曰中庸。不偏之谓中,指其恰好。不易之谓庸,指其易地皆然。人来做我,亦只有如此做,应不能再另样做。此我所以为最杰出者,又复为最普通者。尽人皆可为尧舜,……即如尧舜处我境地,也只能如我般做,这我便与尧舜无异。”[14]61“尧舜为……人人所能到达之人格。……此种人格,为人人所能企及,故为最平等,亦为最自由。”[14]59-60
在中华文化语境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状态不仅仅期于未来,更是立足当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让文化浸润生命,让生命回归文化。体会生命之初心,方得人生之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