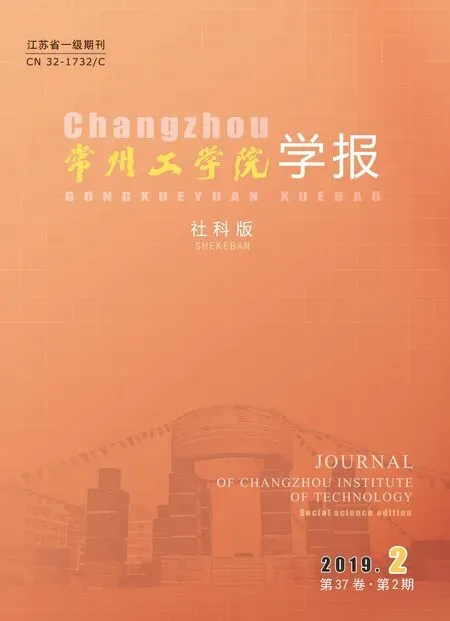太宰治小说《斜阳》中的自我认同与主体意识
李梦茹,吴雨平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二战后,日本涌现了许多文学流派。太宰治是无赖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其创作生涯分为前、中、后3个时期。后期代表作品《斜阳》《人间失格》等反映了二战后日本底层群众的生存状况,颓废是其小说的主旋律。日本战败后,社会的动荡让太宰治深感人生虚无,贵族制度的没落更将他逼入绝境。在《斜阳》中,太宰治关注在当时那种环境中,人追求自由、解放自我的过程,表达了对个体生存的意义、自我认同的思考。
一、现代语境下直治的自我认同
二战使日本民众受到巨大的伤害。太宰治在其作品中并没有直接描写战争场景,但战争的阴影却时刻笼罩在底层人民的心中。主人公直治曾经应召入伍,这场战争也成了直治一生的转折点。
(一)直治的自我定位
直治曾是一个爱好文艺的贵族青年,为了逃避周围的环境,缓解尴尬的身份带来的精神压力,他染上了毒瘾。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应征入伍,长期杳无音讯,生死未卜。直到二战结束后,和子母女二人从东京迁到静冈县伊豆半岛的山庄,直治突然回来了,但他吸毒的毛病仍未改掉。母亲病死后,直治更加放荡不羁。在把一个舞女带回家留宿的第二天早晨,他选择了自杀。
从直治的遗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自我定位。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细腻、敏感甚至纯情的贵族青年。直治对贵族身份有一种强烈的自矜心态,他一再强调自己的贵族身份,也痛恨这个颠覆传统的现代社会。“文学评论界一般认为四个主人公身上都有太宰治本人的标记。酗酒吸毒的弟弟直治叠印出中学、大学时代即早年的作者面影。”[1]80-83“出身为津岛家的公子,太宰治因为这个家庭感受了自卑与自豪的矛盾,而这双重情感的分裂无疑与太宰治一生的极度荣誉和自我欠缺感的性格基调是一脉相承的。”[2]31
直治一生都在颓废中度过,而太宰治并没有详细描写他的内心世界。直到最后,在遗书中直治才吐露出了他的心声。他厌恶世间的一切,质疑所有存在的正确性,认为一切都是虚无的。虽然他也曾努力向平民身份靠拢,但最终失败了。太宰治有一种生在名门家庭的罪恶感,这是一种近乎原罪的意识。这种原罪意识,使太宰治在塑造直治这一形象时,在他身上增添了分裂的因素。
(二)现代性的反身性与直治的自我认同困境
在传统文化中,往往存在着一些十分被人尊重的具有年代感的“符号”。直治虽然想要保存这些具有年代感的“符号”,但他也无法改变当时这些“符号”日渐没落的事实。于是他选择用自暴自弃的方式向社会妥协。最后,他发现尽管自己努力地想要融入当时的社会,却无法真正融入。
国内许多学者对现代性的定义作过阐释,较为公认的解释是:现代性是现代世界的本指依据,具体表现为一种组织模式和理念体系,诞生于17世纪的启蒙运动,由西欧波及全球,反映了近代以来人类思维、行动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性开启了个人反叛的大门,同时还与“颓废”一起加剧了个体的危机感。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拥有比传统社会更多的机会走向成功,但我们面对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各种突发的风险,同样也比传统社会多得多。归根到底还是社会中的稳定性被现代性的反身性削弱了,最直接的表现便是知识累积的主要途径从过去的归纳总结转变为对知识本身的怀疑。何为现代性的反身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反身性指的是一种敏感性,具体指社会生活的大多数面向及其与自然的物质关系对受到新信息或知识影响而产生的长时性修正之敏感性。”[3]19
这种敏感性在自我身上的投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焦虑。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认为,现代人焦虑的根源是“自由的晕眩”。即当人们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之后,人们并非像想象中那样感到自由,而是会像俯瞰深渊一般产生一种晕眩感。而这种晕眩感,正是社会的稳定性被现代性的反身性削弱的结果。个体并没有像启蒙运动的发起者所认为的那样,解放了天性之后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在追寻自由的过程中,个体明白在自由面前并不能率性而为,只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在这种自由的背后,是现代性的自我认同的困境导致的虚无感,这种虚无感使人陷入焦虑之中。现代性的自我认同在社会变迁中的变化是清晰可见的,这种变化是建立在现代性的反身性渗入自我的核心部位这一基础上的。它要求个体的自我认同的变化与社会的变迁同时进行,一旦自我认同的变化与社会的变迁脱节,个体便会陷入自我认同的困境。
自我认同是假定存在一种反身性认知的,这一点与一般的自我概念相反,自我认同是能够被个体意识感知到的。可以说,自我认同的修正与塑造和个体自身的行为或他者的定义并无直接关系。由此可见,自我身份的认同是每个人对其个人经历进行反身性理解而形成的概念。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治,他的现代性的反身性使他对社会非常敏感。战后,旧有的秩序被摧毁,贵族精神和贵族生活方式一去不返。这使直治处在一种不知如何自处的焦虑之中,这种焦虑让他陷入了现代性的自我认同困境中难以自拔。
二、现代语境下直治的主体意识
(一)联结主体的纯粹关系
直治一生和很多女性建立了密切关系。在直治堕落、反抗的一生中,他唯一想维系的就是自己内心的贵族精神。他的母亲和他所爱慕的女性——画家的妻子便是贵族精神的象征。
首先,与传统的社会不同,如今的纯粹关系是不稳定,不确定的。直治能够维持他与画家妻子这段纯粹关系的原因,便是他从画家妻子的身上得到了纯粹的爱情。
其次,吉登斯认为,男性和女性一样需要纯粹关系,也同样渴求寻找到亲密伴侣,甚至也会产生强烈的依恋之情。但纯粹关系建立后,个体也需要承受来自外界的看法和压力。一旦压力产生,较之女性,男性会更加强烈地感受到纯粹关系难以把握,他们对自身需求的表达往往也词不达意。在与画家妻子的交往过程中,直治就扮演了那个不善于沟通交流的角色。他一方面羞于表达,另一方面却又无比渴求这种亲密的两性关系。这样就导致了直治始终处于创造和维系纯粹关系的困境之中,他难以寻找到双方都满意的理想状态,在给予和接受的过程中,他显得十分被动。
再次,纯粹关系是一种以反身性方式互相作用从而形成的人际关系。这种反身性方式包括我是否安好、我是否爱他以及他是否爱我等。反身性对所有的亲密关系进行调节,而亲密关系也成为现代性的反身性的组成部分。直治在遗书中提到:“有一次我梦到了和夫人握手,而且发现夫人早就喜欢上我了,梦醒的时候,甚至感受到手掌上残存着夫人指节的余温。我以为这样自己就满足了,应该可以死心了。”[4]247反身性决定了个体会不断地思考亲密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可能性。直治的反身性促使他不断反思他与夫人之间的关系,试图维系这段关系。
最后,吉登斯认为,在现代纯粹关系中,献身精神基本上取代了前现代场景中所有亲密关系的外在支撑,当代的浪漫爱情基本上是以献身精神为基础的。献身精神的含义比较广泛,它以现代性的反身性为前提,具有献身精神的人甘愿冒着风险并承受它所带来的张力,而这种献身精神可以从纯粹关系中获得补偿。在现代社会中,爱使得纯粹关系中的献身精神变得规范化,但事实上,献身精神是个体的意愿。并不是纯粹关系要求个体成为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个体,而是个体决定要变成具有献身精神的人。献身精神和反身性有一种不确定、不稳定的联系。一方面,个体在思考有献身精神所要承受的风险,另一方面,个体却又愿意成为在纯粹关系中具有献身精神的存在。
在直治看来,具有献身精神是一种彰显自己高贵品质的方式。他的献身精神和自我反身性在互相拉扯着。在他堕落、酗酒、放纵的过程中,他的爱情是他内心的一片净土。但在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着自我认同困境,因此纯粹关系就成了难以联结的主体关系。与此同时,纯粹关系的内部也暗含着张力与矛盾。严格意义上来说,纯粹关系是一种随时都有可能被扼杀的社会关系。直治与画家妻子建立的纯粹关系是违反社会道德伦理的,在这段纯粹关系中,充斥着愤懑、抑郁以及爱而不得的苦闷。
(二)本体安全感
本体安全感依托于一种实践性意识,这种实践性意识深藏于日常的话语和行为之中。直治的本体安全感和他的纯粹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主体关系的联结源于纯粹关系,对直治来说,他的纯粹关系彰显了自身的贵族精神,因此是纯洁的,坚实的。但由于纯粹关系内部充满张力与矛盾,他的纯粹关系也是脆弱的。在这种情况下,直治对事物以及他人的真实感日渐丧失。他强烈的现代性反身性使他丧失了本体安全感。
吉登斯认为,本体安全感弱的个体表现出以下特性:“首先,个体缺乏有关其生平连贯性的前后一致感,进而无法形成一种存活于世的持久观念。其次,在充满变化的外部环境中,个体会专注于那些影响其存在的可能性风险,进而陷入行动上的瘫痪。最后,个体无法形成对自身的正直品行的信任,同时因为自尊自爱的热情而在道德上感到空虚。”[3]49
由此可见,强烈的现代性的反身性导致直治的本体处于不安全的状态中。吉登斯认为信任是建立在自我认同的精致化的基础上的。现代社会信任本身也意味着挑战与创新,它需要个体接纳新事物,敢于融入未知领域中。
但直治质疑社会中一切事物的正确性,生的虚无占据了他的内心,他表面上接受了这个社会所有的不确定事物,但内心对此不屑一顾。他在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时,内心充满焦虑。他想过逃避那些长久以来困扰着他的焦虑,也曾试着向这个社会妥协,但最终他还是选择用他的保护壳——贵族精神,来反抗这个“毫无优雅”的社会。在反抗这个社会的过程中,他无法形成和保持对自身的正直品行的信任,从而感到非常空虚。这种信任与他者的评价紧密相连,他者的评价也影响着个体的自我审查。在这样的机制下,直治的自我审查逐渐变成了一种强迫症,渐渐地他走向了死亡。
(三)主体存在性:羞耻感与负罪感
直治的主体意识中有一种羞耻感。个体的行动机制有积极和消极两面,羞耻感是消极的一面,自豪感或自尊感则是积极的一面。
个体的自尊感和自豪感,其作用远远超过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当自我身份认同的核心要素受到威胁时,外部现实的世界就会受到波及。直治对这个世界失去了信任,他也无法维持他心目中的自豪感。母亲去世后,他的精神支柱从此倒塌。这个社会本身就充满着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直接导致主体产生羞耻感。
羞耻感和负罪感极容易混淆。负罪感是束缚超我的事物被破坏时引发的焦虑,而羞耻感则源自难以实现存在于自我理想中的期待。因为真实的自我无法满足理想自我的要求,也无法维持自身的自豪感和满足感。理想自我构建了一个积极的愿望,以及实现这一愿望所诉诸的渠道。它使得自我身份得以确立,并成为自我认同的核心。羞耻感的形成与主体所设立的目标太大而无法实现有关。直治的羞耻感源于他内心有想要维系的自豪感。因自豪感而产生了羞耻感,这是值得每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个体思考的问题。
羞耻感的破坏程度比负罪感大得多。羞耻感与本体安全感有关。直治强烈的现代性的反身性使得他的本体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羞耻感之所以和本体安全感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因为羞耻感源于一种受压抑的恐惧,主体因为无法承受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所以产生恐惧感。吉登斯认为:“日常生活中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东西,与本体安全感关联十分密切,如果它不存在了——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焦虑就会扑面而来,即使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的个性,也有可能丧失。”[5]86
对于直治来说,他所熟知的贵族生活方式,随着社会的变迁渐渐湮灭。经历过二战的他,失去了对社会的统一性认知,失去了自我认同中的自尊与自豪,失去了主体存在中的信任。他努力地想要成为一个下等人,却发现自己终究还是一个“无法劝天皇陛下去开水果店的人”[4]247。
三、结语
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性虽然为我们创造了众多的机遇,但同时也将个体暴露在充满风险的环境中。危机产生后,个体若想保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找到自身存在的理由,便要付出努力走出危机,否则就会陷入无尽的焦虑中。吉登斯提出的“极盛现代性”是现代性的一种后传统秩序,其特征是建构了一种制度的反身性。当下,现代价值观念的全球化趋势对人的个体行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拜金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启蒙运动时期理想权威所构造的完美蓝图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等,使得个体的自我认同标准发生巨变。在现代性的潮流中,个体被追名逐利的价值观所驱动,多数人丧失了自我,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处于生存困境。个体在追名逐利和安贫乐道之间难以抉择,这两种价值观在人心中对抗,消解了人的自我认同的完整性,自我认同困境由此产生。
直治的一生都处于现代性的自我认同的困境之中。他的反抗是他不断地找寻真实自我、寻求外部的和内心的认同的过程。他的反抗与救赎是个体在抽象的形而上的层面上的自我救赎。身为无赖派的代表作家,太宰治用看似不甚严肃、玩笑的口吻,塑造了一个战士形象。尽管这个战士最终走向了用自我毁灭来完成自我救赎的极端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