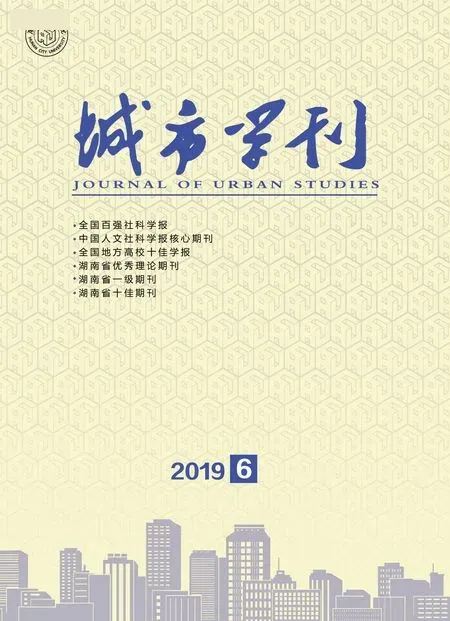新时期反腐小说创作潮的生成与流变
薛朝晖
(湖南城市学院 人文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生活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文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边缘化趋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新时期文学的沉寂,仍有一批批作家坚守着文学的阵地,他们密切关注时代社会生活并做出自己深切的人文思考和艺术探求,在市场经济大潮的背景下还能不时掀起一股股或大或小的文学创作潮。反腐题材小说的创作就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它自20世纪90年代生成后,由注目反腐英雄,书写反腐故事,高张反腐大旗,进而转入关注官场生态,表现对权力腐败的反思与忧虑,进入21世纪后则渐次滑入大众狂欢,反腐价值消隐,而在习近平新时代又随着国家对腐败的重拳出击呈现出回热与突破的趋势。对这一创作潮的生成与流变进行梳理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一、新时期反腐小说创作潮的酝酿
反腐小说创作潮的正式兴起虽然是在20世纪90年代,但并非是完全新生的小说类型,而是既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又在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中早有涉及。也就是说,这股创作潮的出现既以深厚的文学史积淀为基础,又经过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前期充分酝酿。
权力腐败是指“为了私人利益而滥用公共权力”,导致“权力职能的蜕变”。[1]这一现象并非当代中国所独有,而是具有时空的普遍性。自然也就早已为具有美刺传统的中国文学所关注。作为主要源自说书人话本的小说,往往与史传联系密切,较多关涉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政治、官场争斗、权力运行是其重要表现内容,对权力腐败自然也就颇多揭示与批判。如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在对东汉和北宋末年社会动荡的揭示中都较多地写到了政治黑暗、贪腐横行、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的内容。即使是《西游记》,虽是写神魔世界,但其实也是立足于现实世界。其中的神仙与妖怪的关系不正是官匪一家的讽喻?在这类评书式小说中还有一个特别发达的类型,那就是承载着人们清官情结的公案小说,如包公案、施公案、狄公案等。它们在写清官为民做主、伸冤查案中更是大量触及到了权力腐败。即使是在古典文人自创小说中,同样也较多对权力腐败的揭示与批判。如《红楼梦》中写的“护官符”情节,《儒林外史》中写的进学发财、相互交结等。至于晚清的“谴责小说”盛行,那更是文学反腐的一次大爆发,以致于现在人们论及反腐小说往往会联想到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等谴责小说。进入民国后,国民党治下的政治腐败、贪贿公行同样也激起了作家们的批判激情,到20世纪40年代更是形成了一股政治讽刺小说创作潮,其中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张恨水的《五子登科》、钱钟书的《围城》等作品都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官场腐败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讽刺。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配合党和国家开展的意识形态建构工作,作家们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方针指引下,主动或被动地将自己的创作融入到新中国的话语体系中。[2]而与这一话语体系相冲突的批判权力腐败的话题也就淡出了作家和读者的视野。作家们这方面的创作激情被时代社会与主流话语所规训,这一文学情境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然而即使在如此情境下,也仍然产生了诸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一批触及反腐败的作品,尽管数量较少。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作家们重又开始了对权力腐败的审视。先后兴起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创作潮中,小说家们虽然把写作重心主要放在批判和反思极左思潮,但其中不少作品都关注到了权力的失控与被滥用等权力腐败现象。如《大墙下的红玉兰》中章龙喜利用手中权力与马玉麟进行“交换”,《剪辑错了的故事》中老甘为邀功虚报粮食产量,《天云山传奇》中吴遥因害怕危及自己的政治前途压下罗群的平反申诉,《芙蓉镇》中李国香为阴暗心理而整胡玉音等等,这些无不蕴含对权力腐败的揭示与批判。如果说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中权力腐败还只是零星涉及,反腐主题还只是一种潜在的思考,那么到了“改革文学”中,权力腐败的表现就已是相当集中了,反腐主题也几乎是呼之欲出。早在1980年,著名作家王蒙就在其短篇小说《说客盈门》中,通过改革者丁一因开除县委李书记的表侄而导致说客盈门,对官场关系网及官员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作了突出表现,并借丁一之口发出了“不来真格的,会亡国”的反腐呼声。其他的如蒋子龙在《乔厂长上任记》中写的外贸局长冀申利用手中权力卡改革者乔光朴的脖子,柯云路在《新星》中写的县长顾荣的处处为难改革者李向南,陆文夫在《临街的窗》中写的汪局长导演假改革等等,虽然他们主要是在探讨社会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但在生活的叙写和主题的表达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反腐内容。它们可以说是文学反腐号角正式吹响的一个前奏,为反腐小说创作潮的生成做出了必要的酝酿。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以刘震云的《单位》《官人》《官场》《一地鸡毛》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写实小说”更是聚焦官场,以极为写实的方式揭示权力腐败。虽然从“写生存本相”“零度情感”等特点来看,它们属于新写实范畴,但实际上已开启了文学反腐的浪潮,以致于不少论者都把它们算在了反腐小说中。
二、新时期反腐小说创作潮的生成
文学创作潮的生成离不开优秀作家作品的示范引领,往往是先有一部或多部作品因其思想艺术成就和与时代社会需要的高度契合而产生较大社会反响,其题材主题或方法风格或艺术主张等为其他作家所关注、效法乃至超越,使同类作品不断涌现,于是生成为一股潮流。反腐小说的创作亦是如此。最早在此领域耕耘并取得突出成绩,起到潮流引领作用的是张平和王跃文。20世纪90年代前期,张平的《法憾汾西》《天网》和王跃文的《国画》等作品的出现,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他们一个擅写反腐斗争,一个长于官场生态。其后不少作家沿着这一叙写官场的路子,或展示官场腐败、权力滥用,或叙写反腐故事、礼赞反腐英雄,或细探官场生态、忧思人性扭曲,由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产生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如张平的《抉择》、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天下财富》等。这些作品的成功,加之政府的评奖、出版界的热推、影视的改编,进一步引发了反腐小说热。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期,反腐小说的创作更是蔚为壮观,先后涌现了张平的《十面埋伏》,陆天明的《大雪无痕》,周梅森的《中国制造》《致高利益》《国家公诉》《绝对权力》,毕四海的《财富与人性》、阎真的《沧浪之水》、李佩甫的《羊的门》等一大批作品,反腐小说创作成为了雄踞文坛的一股巨大浪潮。
反腐小说创作潮生成并成为20世纪90年代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这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既有深刻的时代社会根源也有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作用,既有读者的审美期待也有作家自我实现的需要。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时代社会生活不仅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同时它的需要与呼唤也是文学创作最直接的外在动力。反腐小说创作潮在20世纪90年代的生成就是与这一时期反腐成为时代重大主题密切相关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在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理想缺失、物欲膨胀、道德滑坡、权力滥用、公平正义遭破坏等等。当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作为社会生活核心领域的政治生态中,突出体现为权力腐败时,民怨滋生,引发社会的普遍关注与热议。而这也必然会引发作为社会良心又具生活敏感的作家们的关注、思考,并进而进行艺术呈现。也就是说,是时代社会生活向作家们发出了文学反腐的呼唤。与此同时,党和国家对腐败现象频发的高度重视,使反腐倡廉成为突显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这又为反腐小说创作潮的生成提供了可能和契机。早在1993年8月21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上就严肃指出,自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指出,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随着党和国家对反腐的重视,一系列腐败案件被查处,一大批腐败官员落马,这不仅给作家进行反腐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胆气。因为反腐小说注目官场,关涉政治,会触及不少敏感话题,要作家们完全没有创作顾忌也是不太现实的。如果没有反腐倡廉的主流意识形态,或许也能零星产生几部优秀的反腐小说作品,但形成为一股大的创作潮却是难以想象的。
文学生产影响文学消费,而文学消费也会反过来影响文学的生产,这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尤为如此。读者对反腐小说的阅读期待和文学消费无疑是影响反腐小说创作潮生成与流变的又一重要因素。反腐小说对官场生态的描绘与揭示、对权力腐败的批判与反思在很大程度上吻合了读者的阅读审美需求。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的腐败滋生使人们极度不满,热切希望能看到有人仗义执言、鞭挞批判,也希望有正义力量斩妖除魔,维护公平正义,因而乐于和期待在阅读反腐小说中获得情绪的发泄和理性的指引。另一方面,长期的官本位文化也造就了社会的权力崇拜以及人们对官场隐秘的窥探欲望。能满足大众这一欲望的反腐小说自然也就获得了市场的欢迎,甚至还有人把它们当成生活教科书,希望从中寻取职场经验的借鉴。市场消费需求的旺盛反过来又促进了反腐小说创作热潮的形成。随着几部反腐小说的巨大成功,不仅激起了一批批作家对这一社会生活领域进行更深入的艺术反映的创作欲望,同时也引发了大量的良莠不齐的市场跟风。
除了生活的呼唤、政治的指引、市场的需求这些外在动力以外,反腐小说创作潮的生成也是作家自身的内在要求。对于大多数中国文人来说,深厚的人文传统造就了他们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追求,赋予了他们感时忧国的精神气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更是他们的自我期许。改革开放以来的种种社会问题自然为敏感的当代作家所深切关注。尤其是随着权力腐败这一毒瘤越来越严重地腐蚀社会肌体,有着自觉的文化承担的作家们或愤怒或忧思,本着自己的内心要求,勇敢地切入当下社会生活,并化而为文。当这自发的创作还能契合主流意识形态需要并获得市场欢迎,反腐小说创作潮的生成也就顺理成章。
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作家来说,反腐小说的创作不仅是基于内心的要求,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同时也是在文学边缘化趋势下寻求文学突围的有力选择。也就是说,反腐小说创作潮的生成也有着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内在作用。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先锋文学陷入叙事迷宫,欲望写作和私人化写作渐渐流入下半身写作,文学日益边缘化和小众化。文学自身的发展必然要求改变这一现状,寻求突围,重回社会中心。另一方面,我国文学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文学发展面临困境寻求突围的时刻,这一强大的文化基因就会凸显其影响,引导作家们在寻求艺术突破的同时,注重关注社会生活、切合时代需要、履行文化使命。于是具有恒久魅力的现实主义重放光彩,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坛形成了一股强劲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在这种文学情境下,当反腐成为时代主题时,反腐小说创作潮也就应运而生了。
三、新时期反腐小说创作潮的流变
反腐小说创作作为一股潮流,其外在体现是大量以表现、批判、反思腐败为主要指向的小说作品既具共时性又具历时性地出现在文坛。而其内在则是体现为这类创作在规模与特质上有较清晰的发生发展脉络,以规模、角度、力度、深度等的流变历程来呈现其潮起潮落。虽然因为作家们在生活阅历、艺术个性、艺术才华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各类型、各特质的反腐小说在共时与历时两个维度上都存在共生混杂现象,因而无论是从对权力腐败反映的角度、力度、深度还是从艺术表现的成功与局限等方面,都很难做出绝对化的概括以精准描述这一流变历程。但笔者以为,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我们还是不难发现,新时期反腐小说创作潮大致经历了由对权力腐败的揭露与斗争,进而反思与忧虑,渐次滑向展示与狂欢,又在突破中走向回热的流变历程。
(一)揭露与斗争:反腐主题的凸显
从反腐小说创作的整体发展来看,初期的“反腐小说”以反腐斗争描写和清官形象塑造为主要特色。写作重点主要放在对当下普遍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的揭露上,并着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正义感、不畏强权、一心为民的反腐英雄形象。通过写反腐英雄同腐败分子的殊死斗争来展示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和尖锐性。因为重在反腐故事的叙写和反腐英雄的塑造,它们一方面使得小说的反腐主题得以凸显,回应了时代主旋律,能带给人们以神圣崇高的阅读感受。另一方面也容易流于外部矛盾冲突的渲染,妨碍了对权力腐败揭示与批判的深度与广度。它们程度不一地存在人物塑造上的理想化、类型化,情节结构上的正邪对立、正义战胜邪恶的模式化,以及清官情结中的人治思想等问题。这类作品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平的《抉择》,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和周梅森的《人间正道》等。张平、周梅森、陆天明三人也因此被称之为反腐小说“主旋律派”的“三驾马车”。
(二)反思与忧虑:反腐主题的深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因时间推移而来的反腐作小说作家自身思考的深入,加之以文艺界的评论和社会的热议,一些作家意识到了初期反腐小说思想上的局限和表现上的单一,开始思考通过对反腐败题材的深入发掘,来揭示更深层的社会和体制问题。他们从腐败的社会文化根源、政治体制根源、人性心理根源等层面来理性地思考反腐问题。他们的努力使小说的反腐主题得以深化,也使反腐小说创作潮发生了由浅层的反对腐败向深度的反思腐败的发展。这一发展既有沿着王跃文的《国画》的路子,叙写官场生态,探讨官场及社会对人物的规训的,也有沿着写反腐斗争的路子但加强对腐败反思、探讨反腐对策的。前者以阎真的《沧浪之水》、李佩甫的《羊的门》等为代表,后者以周梅森的《中国制造》《绝对权力》、陆天明的《高纬度战栗》等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由反对腐败到反思腐败,由批判腐败分子到批判腐败生态,不仅意味着文学反腐的广度与深度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创作基调的变化。随着反思的深入,作品不再是对正义战胜邪恶的浮泛乐观,而是伴随着作家对腐败的深沉忧患,忧其蔓延之猛、破坏之烈、治理之难。与忧患伴生的还有悲悯,他们的悲悯不仅投向了腐败的受害者,也投向了腐败分子,因为他们没有把腐败简单地归结为个人品质,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
(三)展示与狂欢:反腐主题的消歇
到了21世纪初,反腐小说创作潮又呈现出新的变化。一方面是随着市场经济大潮而来的文艺大众化、商品化使反腐小说写作媚俗化倾向加剧,另一方面则是随着网络阅读成为常态,网络书写与网络出版大热,这带来了反腐小说创作与发表的门槛降低。这以后虽然表现官场腐败的作品并不少见,甚至比以往更热,但整体却呈现出价值亏空状况。它们更多的是对官场腐败的展示,津津乐道的是官场争斗,争风、打脸、斗狠、比势的桥段大量出现。作品的反腐意味趋淡,甚至有些还有炫腐、赏腐的嫌疑。特别是网络写作的方式使一大批年轻的草根作者加入,生活经验、思想底蕴和艺术修炼的不够,使他们的作品更多的是对官场不切实际的想象和快感的宣泄。反腐小说创作渐次滑入到大众狂欢。代表这一发展趋势的有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老乔小树的《侯卫东官场笔记》、黄晓阳的《二号首长》等。就在这满足阅读快感的大众狂欢中,小说的反腐主题渐次消歇,反腐小说创作潮也开始走向沉寂。
(四)突破与徘徊:反腐主题的回热
在沉寂了近十年之后,随着周大新的《曲终人在》、陶纯的《一座营盘》、宋定国的《沧浪之道》、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等作品的先后出现,反腐小说的创作又出现了回热的趋势。这一回热并非是简单的反腐题材重回作家艺术视野和大众阅读视野,而是意味着反腐小说在思想与艺术上突破了原有的局限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正如文学评论家白烨所说,“现在反腐小说势头回暖,既有反腐成为社会常态的原因,更因为作品本身的质量上来了。写反腐不限于反腐,写官场又超越了官场,作品具有更丰盈的社会内容和人生内涵”。[3]从反腐的广度来看,《曲终人在》和《一座营盘》都涉足了军队反腐这一以往反腐小说没能突破的雷区。从深度来看,这些作品也探讨了诸如制度缺陷、人心变异等诸多敏感话题,正如周梅森所说“剧中(《人民的名义》)的很多对话,过去是要被剪掉播不出来的。”[4]当我们为反腐小说创作在突破中的回热而鼓舞时,我们也应看到,这种突破仍然是很有局限的。尺度的突破实际上是与现实中的反腐力度同步的,也就是说是被允许的,作家在写作上仍然是拘谨的。艺术表现上虽也努力寻求突破,但反腐小说固有的正邪对立、依靠更高层清官解决问题的叙事模式等问题却似乎难以超越,审美品格也徘徊于通俗。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