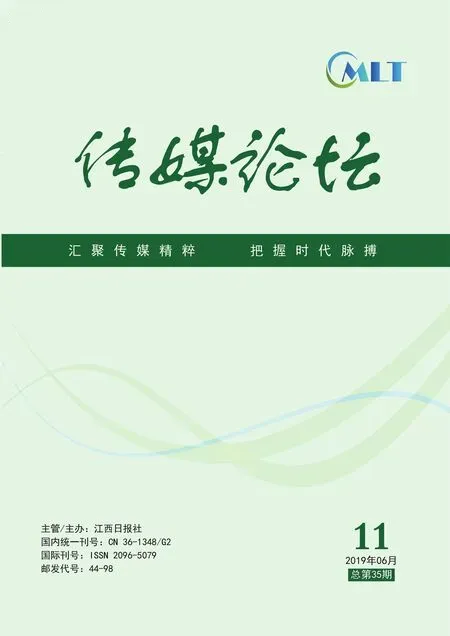电影《飞越疯人院》中的福柯理论探析
张琳悦
(大庆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大庆市戏剧工作室,黑龙江 大庆 163000)
《飞越疯人院》是美国导演米洛斯•福尔曼执导的一部隐喻美国社会的电影,该片根据美国作家肯•克西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扰乱社会、逃避苦役劳动的正常人麦克墨菲为了重获自由而多次试图逃离疯人院的故事,揭示了癫狂者远离人群、流离失所,在社会边缘艰难存活这一现象。影片反映了美国社会、制度、文明、民主、人性等方方面面,处处体现着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理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监禁
理性是文明的基础,稳定的社会公共秩序需要通过理性来建立,而疯癫作为破坏秩序的非理性的东西,是被理性排斥的对象。为了避免社会冲突、惩戒罪恶,针对非理性的监禁体制应运而生了。“监禁”隔离了疯癫,使逃避秩序的肉体变得驯顺。影片主人公麦克墨菲就是一个不服从秩序的穷人,在监狱里,他工作态度很差,没有经过许可就说话,喜欢打架闹事,又非常懒惰,为了逃避强制劳动,他甚至假装精神失常。拒绝监禁的游手好闲之人更需要加以监禁,因而麦克墨菲被送进了疯人院。
就像为了防止疾病的传播而被隔离的麻风病人一样,穷人、罪犯和疯人因其对社会和他人的危害性而被隔离在一个封闭的建筑物里。被禁闭的人如同笼中之鸟,处于一种隔绝状态。窗外的远山、土地、蓝天、大海都不属于他们,他们真正失去的不是家的温暖,不是亲人的关怀,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自由。从被幽禁的那一刻起,他们就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权利,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约束和限制,每天重复着同样的、毫无意义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仍然要持续下去,他们学会了服从,而且不得不服从,因为在这个狭小的、有限的、被割裂的空间之内,他们随时随地都会受到监视、控制和检查。
在电影中,疯人院具有完备的监督体系,结实的铁丝网用来限制病人的出入,护士室的大玻璃窗和小圆镜能够捕捉每一个病人的行踪,走廊里的窗户可以俯瞰整个操场,就连自由活动和户外运动的时间病人都受到护士或警卫的监视,但是,这个疯人院的建筑结构并不是最完美的。福柯在著作《规训与惩罚》中分析了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形象,提出了全景敞视主义理论。这种建筑的基本构造是:一个巨大的环形建筑围绕着一座中心瞭望塔,环形建筑内部被分割成许多小房间,房间的两个窗户一个向里对着瞭望塔的大窗户,以便瞭望塔中的监督者观察被囚禁者的行动,另一个窗户为了优化室内采光效果而朝向外,整个建筑就像一个巨大的笼子。全景敞视机构虽然看似十分轻便、没有那么压抑,不需要铁栅、高墙、脚镣和大锁,只需要合理建造门窗并安排一套健全的监督体制,但是权力效能却可以在里面得到更加充分地发挥,使被监禁者时刻处于紧张、孤独、恐惧的状态。全景敞视建筑就像一座动物园,按照日常表现程度或者罪行、病情的轻重,人们被划分成不同的等级,关在属于自己的区域里,这样既便于管理和安排工作,又能够避免暴力行为的发生或疾病的传染,有利于罪犯悔过和病人康复。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用于监视人群的最便捷、省力、有效的监控设备:电子眼、摄像头产生了。现在的监狱、精神病院等基本上每块区域、各个房间都安装并使用了这一装置,通过这种方式,监督者可以足不出户观察每一个人,防止他们制造混乱或企图逃走,而且可以对病人的突发病症予以及时治疗。在监控室里,监督者不用每时每刻都紧盯着屏幕,因为监控录像可以重播任何一个容易被忽视或错过的细节。在静止冻结的空间内,监控设备可以保证被囚禁者能被观看,但是不能观看,他们在失去自由的同时也丧失了自己的隐私。边沁曾经提出过一个原则: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囚徒们可以看到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就像成千上万只眼睛,镜头边上红色的光圈证明它们正在工作,这也意味着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彻底被观看,但是他们却不能确定此刻屏幕前是否坐着一位监督者,因此,囚徒们随时都在警惕着。为了不触犯规则,以免受到严厉的惩罚,他们尽量表现得驯服、安静、和顺。
二、规训
监狱和疯人院正逐渐融合为一个“暴力化”的世界,这些机构收留了流浪者、破坏秩序的人和不劳动的人,将他们的身体制伏于严格的规范中,令其具有生产性,为社会创造简单的、廉价的劳动。纪律需要封闭的空间,在一间阴冷、潮湿、拥挤、令人窒息的屋子里,身体要忍受寒冷和饥饿的煎熬,甚至还可能被殴打、虐待。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每一个禁闭的建筑物内都有一套牢房或病房守则和处罚条例,每一个被监禁者都应该了解并遵守这些规则,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必须按照工作准则来办事,就连犯人和病人的配给品也是按照规定发放的,额外的需求是不允许的。例如,电影中契士威克先生因不满自己的烟受到管制而与瑞秋护士发生争执,引发了一连串的骚动,最后,医院为了惩治闹事者,对他们采用了恐怖的“电休克疗法”。
监狱和疯人院还有一套自己的时间表,用于规定被囚禁者的生活节奏、安排活动和调节重复周期,以及最大限度地从肉体中榨取时间和力量。疯人院里的时间是没有数字概念的,取而代之的是虚妄、幻觉、记忆、梦和恐惧等东西。在那里,时间和地点都是没有意义的,人们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而是只能按照作息表的规定完成属于自己的任务并配合检查,比如工作、吃药、讨论、谈话、讯问等。影片主人公麦克墨菲为了看球赛而要求更改时间表,最终没有得到批准。可见,人们已经习惯了的时间表是不能被轻易改变的,为此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
福柯说:“为了使人群变得有用,就必须用权力控制他们。”[1]规训权力的主要功能是训练,把不顺从的人集中起来,经过操练组织成为有纪律的、合一的整体。规训的手段包括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
层级监视的网络既是自上而下的,也是自下而上的、横向的。护士和看守在负责监管被囚禁者的同时,也相互监督,例如,影片中黑人看守玩忽职守,值班护士在听到声音后及时赶来询问、查看情况。福柯认为,在一切规训系统的内部都有一个小型的处罚机制,它拥有自己的法律、自己规定的罪行和特殊的判决形式。它有权力裁决、惩罚一些偏离准则的、犯错误的人,从轻微的体罚到剥夺权利和羞辱,惩罚的方式多种多样。这种规训不仅针对身体,而且针对灵魂,人们的思想、意志、欲求、心理、行为、性格等都受到权力的控制。在纪律中,为了缩小同一个机构之内的等级差距,有时会奖惩或赏罚体制并用,以便规范、比较、区分、同化和排斥不同等级的人群,对他们进行优劣划分。
作为规训手段之一的检查不仅使人置于监视领域,而且也把个体写入文件中,作为档案永久保存下来。这种个体的建构使非正常人变成了异类、变得更加个人化,使他们成为可以与他人进行比较的个案。影片中,麦克墨菲的档案上面记录了个人工作时的表现、犯过的罪行等等,史贝菲医生借助它来寻找麦克墨菲入院的原因,麦克墨菲因此被当作了可以被具体分析和详细研究的对象,而不是一个有尊严的人。正如福柯所说的,“在一个规训制度里,个人化是一种‘下降’。”[2]
三、逃离
疯人院既是治疗机构,也是学习顺从的地方。那里面禁闭着两种人,一种是因为疯了才被关进来,另一种是因为被关进来所以才疯了。像麦克墨菲那样不服从秩序的危险家伙并不是真正的疯子,但是,在监督者看来,他们比疯子还可怕,必要的时候疯人院会采取强制手段迫使他们服从。就如2018年播出的国内网剧《疯人院》一样,疗养院里禁锢着的特殊病人到底是疯子还是天才?
疯人们丧失了思考能力,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知道什么是喜怒哀乐,也无所谓活着还是死去。当一个被幽禁在疯人院里的正常人看到眼前的疯人正上演着一出出悲剧,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现在和未来,忧伤和恐惧就会填满内心。每一个正常人都渴望自由,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像麦克墨菲那样有勇气逃走,因为他们毫无思想准备,在现实的世界里他们将什么都做不了。影片中的许多病人都自愿留在疯人院,如果他们真的出院了,也会希望自己能够回来。为了在疯人院里面安稳地存活,人们只能努力遵守规则,有些人甚至装疯卖傻,与这个压抑的环境相协调。比如,电影里的酋长装作又聋又哑又笨的傻子,却以正常人的眼光观察着疯人院里的一切,不仅瞒过了其他病人,而且愚弄了所有的警卫和医护人员。他具备飞越疯人院的能力,却迟迟下不了决心,麦克墨菲逃离疯人院的计划失败并受到惩罚后,他才醒悟到如果自己继续留在疯人院里,就只能做一辈子的囚徒,他必须逃走。最后,麦克墨菲变成了真正的傻子,酋长带着麦克墨菲的灵魂离开了疯人院。
四、结语
电影《飞越疯人院》通过典型人物、典型形象的塑造,隐喻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影片主人公麦克墨菲象征着对权威和制度的反叛。影片还隐喻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比如:“什么是疯狂” “对划一性的反抗”“性问题” “西方社会的现代性问题” “自由对抗专制” “群体力量” “道德问题——善与恶的界限” “女权主义”等,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社会政治电影的代表作。
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管理体系作为对个体进行监督、规范的机制,在科学化、程序化、规范化运作的疯人院中体现得尤为隐秘。福柯笔下的疯癫与迷狂和米洛斯•福尔曼执导的电影《飞越疯人院》中的疯狂都具有某种隐喻性。福柯通过隐喻重构了历史,把现代与古典时代联系起来,但是,他的书写却开始走向了偏执。
——从学科规训视角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