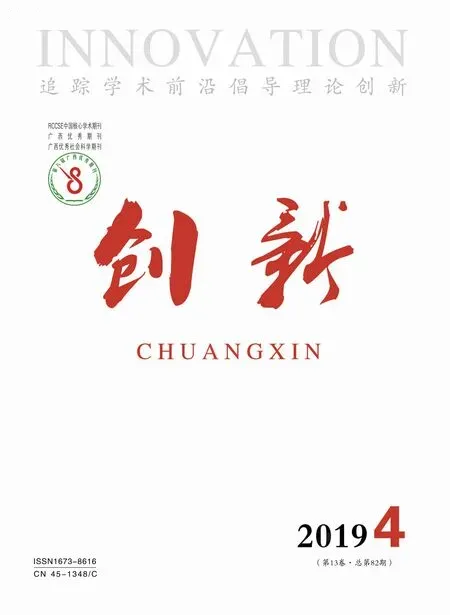欧美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景象及城乡关系述略
——基于外国文学的视窗
■ 李麦产
一、问题的提出:怎样在研究中揭示欧美城市化的真切
城市史的研究,既需要关注大趋势,梳理路径,也有必要致力很多生动、逼真的细节。前者有助于人们把握历史进程的规律、特征,从宏观上实现准确概括;后者能够让人透过细微、具体的情景或情节加深对前者的认知与理解。然而,就目前来看,对城市史的研究尚存在倚重前者、忽略后者的偏颇。在对欧美国家的城市化研究中,同样有这种情况。
(一)欧美国家城市化的内在动力与逻辑
世界上最早启动城市化并在后来率先迈进城市时代的国家与区域,是欧洲与北美洲的若干国家或地区。
得益于同步或相继开始的由工业革命所产生、释放的强大力量的推动,欧美国家那些本来商业色彩就比较浓厚的城市,日益成为经济生产基地与财富创造中心。这样,城市对包括人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所形成的凝聚力、向心力,更加无与伦比。于是,各种优质要素加速向城市聚集。由此,城市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和发展可能,而且还因为容纳与承载了各种各样的资源禀赋,发育和形成了更加丰富多样的生活内容,从而使城市结构愈益复杂化。在人类历史上,城乡对比关系中的城市,从此作为主流和最重要的人居环境空间而不断增长。欧美国家的城市化也因此成为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不宜淡忘的历史现象。
工业革命首先萌发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标志是蒸汽机代替人力或水力而成为制造业等的主要动能来源。当然,除蒸汽机外,还有其他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与生产、方法上的创新。工业革命的种子也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与地区孕育发芽、茁壮成长,如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俄国和意大利等。到了19世纪,美国亦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大幕,新大陆这驾马车在轻装上阵的优势之上,快马加鞭地前行。
然而,在欧洲与北美洲,无论是当时的工业革命的先进国家,还是紧紧跟随的跟进者或模仿者,它们的城市都由工业化的出现而获得了内生发展力量的注入,城市化步工业化之后而展开。可以说,欧美地区及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这样两类不同性质或领域里的人类社会实践,从此走入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并形成了不能截然剥离开来的密切关系。大致而言,通过对工业革命研究的切入,能够比较恰当、有效地获得相关国家与地区在城市化方面的有益信息或文化图景。
(二)记载欧美国家城市化的资料及筛选比较
虽然欧美国家的城市化获得了工业革命的支撑,但是它们的工业革命与城市化并不是从某个节点直接跳跃到更高的另一个节点,而是有其历史跨越与连接,即经历了一个时间长度,是一定时期内的动态化。借此进程,人类社会的主体变成了城市,城乡格局由乡大城小转换为城大乡小,城乡对比出现逆转。在这个似乎悄无声息,最终结果却堪称巨大的演进中,城市变得既大且强。区域与全球城市体系也出现,并不断优化或完善。由此,城市文化景观丰富多彩或瞬息万变。从城市化进程、当时的文化景观中,不仅能够总结、发现若干演进规律或教训、经验,而且有利于用历史关照当下,把现实检点与历史经验的启迪结合起来,更好用之于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中国的实践。
然而,既有的对早期、世界上领先地区的城市化的研究,是一种对历史上曾存在或发生过的宏大进程的概括与总结。这样的凝练与归纳,主要依赖于对一些历史过程中所留存下来的资料的统计、分析,是一种抛离了历史具象的后世之抽象。而实际上,在一定时段长度内所生发、变化的城市文化景象,作为城市化进程的表象,无疑更能生动折射出城市化过程中的某些规律性。
不过,对逝去的城市文化景象的记载形式、信息表达,在现代录音、录像以及其他一些电子记载手段出现前,其范围、种类及所承载信息的丰厚度或能力有很大的限制。可喜的是,在欧美国家,与工业革命齐头并进的城市化进程,也是一个文学灿烂时代,涌现了一大批了不起的作家,创作了不少直面或侧面描写城市问题,具有影响力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以其有别于历史书和其他影像资料的表达方式,从独特的角度默默记录了城市化的脉搏,以及发生在这个历史洪流中的纷繁景象、各类事件、具体纹路等。
借助彼时创作的西方文学作品,剖析、研究欧美国家与地区的城市化中的问题,提取、荟萃能够标志当时城市化的细微而具体的信息,当是一种比较新颖的城市史研究方法的尝试。
二、方法之新:从文学窗口探视早期城市化问题
(一)作为理论依据的场景主义
能够另辟蹊径地运用文学作品所提供的材料去进行客观真实的城市史研究,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是场景主义。
作为社会学家的欧文·戈夫曼,被认为是早期的场景主义理论的代表,而他的理论其实应被称为拟剧理论(social dramatic theory)。在戈夫曼的理论构建那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根据其所处的动态变化之中的场域或情景条件,在社会舞台上承担不同的角色,呈现不同的行为表现。因此,场景对于作为主体的人的行为之展示,乃至这些人所参与其中的故事铺陈与演进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场景决定了社会活动的内容。而场景即是一定的空间区域,大致可定义为受某种程度的知觉障碍限制的地方,也是具体所指的一些物理空间——如城市教堂、医院病房、咖啡馆、酒店、影剧院、法庭、车站、机场等场所与设施。作为场景的区域,既包括充分暴露在公共视野下的“前台区域”及其中的“舞台装置”,也涵盖对“前台区域”实施“工作控制”的“后台区域”——在那里收纳或蓄存着“各种舞台道具和各项个人前台”[1]。通俗地说,场景就是各种外在的物质保障,是特定社会实践与活动的前提条件、设备设施。
欧文·戈夫曼提出场景主义的梗概后,尽管后来伴随时代发展与技术进步,它又得到补充、发展与完善,但其核心要旨依旧有类于汉语中“人生大舞台、舞台小人生”一说所揭露的真谛,即以戏剧舞台及其活动要素的组成来类比人类社会的构成与活动。场景主义以其所具有的较强的解释力,超越了社会学研究的范围,获得了较广泛的接受与认可,被运用在其他一些学科与相关问题的探讨中。
当今,鉴于场景与历史实践、时代活动所具有的密切关系,为了提升特定区域空间活动的精彩度,创造同步竞争中的新优势,一些城市就遵循该理论的内在逻辑,在场景塑造上多做努力,通过创设舒适、愉悦,与特定人才相匹配的场景的方法,来吸引各类创业人士、创意人才的到来与聚集,从而让城市在后工业化时代继续获得凸显的发展优势,例如美国的波士顿、芝加哥等城市即是如此[2]。这种“栽下梧桐树,引得金凤凰”的谋划,就是用优质场景的打造而推动优秀历史剧目演出的体现,也是借助优化的城市环境与氛围而推动城市更新的新表现。
(二)场景主义的逆向运用
其实,在城市与区域的研究中,对场景主义理论还能够进行逆向的应用和操作,就是联系或斟酌场景与演剧的密不可分关系,用场景分析的方法来“铭记”历史剧目展开过程中的在场感,“侧记”当时的诸多情景特征等。这样,特定时代、特定区域的历史进程中所涌现的全部“舞台装置”“舞台道具”及作为“各项个人前台”构成部分的舞台言说、动作表达或思想活动等,都具有了标识与佐证剧情或时代特征的功能和意义。
而在小说——尤其是工业革命与城市化时代由当时的作家所创作的,以城市为背景或舞台的小说里面,那些作为底色与幕布的城市基础设施、城乡关系及人们对于城市问题的观感等,无疑可作为窥探或解读特定历史阶段的城市经验、城市面相乃至参悟城市问题的有用与有利材料。这是因为,小说家为了追求故事表达的生动逼真,以期引起读者的共鸣与同感,往往会在临摹当时的工业革命与城市化图景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秉持“真实性”这样一个尺度。这样,就把很多当时社会的特征与细节搬移到作品中来。通过剖析、汇集在这些艺术性文本中的场景描写,就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客观、真实的逝去时代的景象重建。这也为后世的人们凭借文学阅读而了解包括城市在内的诸多社会面相埋下了伏笔,创设了条件与可能。
譬如,在欧洲不同时期与国家的小说家们的集体努力下,欧洲文化史的全部内容即它的“外部和内部”各方面,俱“被放进了小说的历史和小说的智慧中”[3],包括城市在内的欧洲社会生活的很多具象与领域被艺术性地保存,因此,即使“欧洲历史全部丧失,只要小说存在,所有的历史仍然可以复原”[4],这也能够通过小说的渠道去回望、探视欧洲城市史的某些境况,并具有独特的价值甚至优势。
总之,通过对城市区域或场景的分析,能够获悉历史剧在其中展开、演出之时的特征与重大转折等。
(三)文学作品材料用于城市史研究的有效性
工业革命与城市化背景下诞生的西方文学作品的类型多种多样,如诗歌、寓言、随笔、剧本等。有一些作家还直接为特定的城市写书做传——这就属于有明确意识的书写城市故事了,有类于中国历史上自西汉时期所出现的京都赋之类的创作。有意识针对特定城市的文学性表达,固然能够替特定城市流传下来比较集中的关于该城市的历史信息,然而,在其中也一定会暗含了作家的主观感受,信息也必然经历过特定个人的偏好性选择,关于城市的更多侧面、领域、情节则可被屏蔽与遗漏。
相应地,那些并非定向、有意,却又在场景铺陈中涉及城市的书写,能够克服城市赋一类的文本的不足。通过阅读这样的外国文学作品,从资料梳理与利用的角度出发,做关于城市特征与情景的研究、分析,从文学描写与叙述中,寻找逼真的历史感、现场感,当能深化对城市史研究的生动性、丰富性,也便于加强历史研究与现实关照的联系。
其实,起始于19世纪末的世界城市规划事业,就是由文学作品对相关城市病态问题的揭露而孕育和产生的。具体来说,得益于当时的两篇著名通讯稿,一篇是安德罗·莫恩(Andrew Mearn)写于1883年的《伦敦无家可归者悲惨的哭泣》,另一篇是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发表于1890年的《另一半人如何生活》。他们的文章把人们的目光与思考引入到如何梳理城市建设、管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重大而复杂的事项上,从而促成了现代城市规划事业的正式确立或起步[5]。
为了提升在运用文学作品中的资料去研究城市化进程的准确性、客观性,下文将选择工业革命与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若干典型作家的小说,以其中的城市场景为着意关注的地方,用逼近真实的方法去剖析内中的城市文化景观,从而梳理相关的城市问题、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这些小说无论是短篇或长篇,都有故事情节,有人物、剧情,而且所展开与演绎的空间包括各种各样的城市。作家在创作这些小说时,一般皆已比较熟悉相关的城市,这样才会把人物、故事放置到这样的场域中去铺垫、舒展开完整的故事。
就此而言,作家的主要注意力虽然在于故事与人物方面,城市这样的地方仅仅是舞台或场合,甚至难免有他们的主观认识与理解在其中,但是整体上他们通常不会对城市做“故意”的剪裁,相关的城市场景也因此具有了一定的客观性。从这些作为小说得以展开的场景的城市侧面信息记载中,作家们便无心而为地遗留下不少关于他们同时代或之前城市的有价值的信息。把这些片段或凌乱的关于城市的信息剔出并串联与编织起来,就有可能获得生动、具体的工业革命与城市化时代的城市文化景观,并揭示出其他相关的信息与启示。
具体而言,本文随机选择了若干能够代表这个时期艺术水平的一些文学作品,如法国的莫泊桑与左拉、英国的狄更斯、俄国的普希金与契诃夫,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小说,通过分析其中的城市记载与信息流露,把城市当作场景,梳理场景,达到去探视当时的城市化进程等目的。
三、西方文学作品中以“场景”形式呈现的欧美城市化及相应景观之例证
欧美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延续达一两百年。在这个比较漫长的流变或过程中,既存在若干能够清晰明辨的转折点,也有一些历时性的城市生活与标识内容。这些丰富的城市信息,有不少被作家记录在西方文学作品的场景塑造中。借助于对这些作品的解读,可重新回到当时的城市化过程之洪流,再现立体而生动的诸多城市景象。
(一)处在世界工业革命漩涡中心的伦敦
英国是西方工业革命中的率先者、领先国,几乎也同时启动了自身的城市化步伐。伦敦不断发展、进步,城市影响力日益增大,当然也伴生了一些问题。这可从狄更斯等人在其作品的描写中看出端倪。
首先,作家笔下的伦敦已经具有了相对于其他城市与乡村的显著优势。大城市所提供的生存机会、发展空间,也是其他城市与乡村所缺乏的,这无疑是很多人偏爱大城市的内在原因。
如在狄更斯(1812—1870)的《雾都孤儿》中,逃离救济所与棺材铺等地方的小主人翁奥利弗,无意间选定了向伦敦奔命。当他发现指向伦敦的里程碑时,立即产生了效果:“这个地名在这孩子的脑子里引起了一连串的奇想。伦敦!——那个大而又大的城市——没有人——甚至包括班博先生——能在那里找到他!他常听习艺所的老人说,一个有出息的青年在伦敦决不会发愁吃穿;还说在那个大城市里,随时都有各种各样一个生长在农村的人想都想不到的谋生的办法。那是一个若无人帮助便将饿死街头的无家可归的孩子的最理想的地方。当他想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一跳站起身来,又向前走去。”[6]53
尽管狄更斯在该小说中纯熟地使用了英美文学中曾广受影响的哥特式风格,运用了极端、夸张、神秘等表现形式,但全文中所体现的对当时伦敦的刻画却是深刻、全面的。此时期的伦敦,得益于工业化力量的推动,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达500万,并且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和最重要的金融、贸易中心。伦敦,正处在魅力强大与容光焕发的时候。
其次,虽然此时伦敦城的规模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甚为庞大,可算是标杆与领跑者,但是它仍然处在不断的发展中。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时候的伦敦仍然获得工业革命的力量供给,城市还在继续膨胀、不断变化。
关于这一点,从狄更斯的《双城记》对人物活动环境的描写中可有所体现,例如文中提到,牛津路的南北在以前曾是通幽的静谧之处,房屋较少,树木葱茏,遍地野花,或者眼光透过墙头便可见到一片应时成熟的桃子[7]87。然而,一二十年的光阴流逝,这样浪漫的城郊也变成了城市的组成部分,当年的景色被吞噬、湮灭。
再次,伦敦作为发达的经济丛林,是舞台,也是庇护所。当时人们对伦敦所能带来的好处确信无疑,还对之进行了美好想象。故而出现了人们口耳相传的某些城市神话:伦敦被理解成是那个时代的人间天堂。如十九世纪中后期,英国著名作家兼词典编撰人塞缪尔·约翰逊曾这样评价当时的伦敦:“一个人如果厌倦伦敦,便是厌倦生活,因为在伦敦生活才丰富充实。”[8]人们认识到城市生活的便利、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等定律,开始借助伦敦这样的个案城市来表现了。
当然,城市问题也同时涌现。在整个伦敦呈现欣欣向荣良好发展态势的时候,就存在着事实不争的不良地区,大致如是:工业革命前,伦敦的东南部为人口密集、经济较繁荣的地区,而工业革命后,城市的西北部却后来居上并取而代之[9]97,原来的先进城区反而显得衰败与破落。
在狄更斯的笔下,不乏对伦敦城已出现的城市问题的揭露。各类丑恶与不法行为即主要发生在伦敦的东部:“在泰晤士河畔罗瑟海斯教堂所在的地段,因运煤船的灰尘和密集的矮房里散发出的炊烟的熏染,那些岸边建筑和水上船只显得又脏又黑。”而为了进入一个罪孽集聚的地点,还“必须穿过一片挤满最狂野、最贫穷的河边住户”,通过“行人使用的密集、狭窄和泥泞的街巷”,而两侧的“店铺里堆满了最廉价、最难以下咽的食物;最粗糙和最一般的衣物悬挂在商店的门前,飘动在屋门栏杆和窗户之外”。在这里,各种刺鼻的气味,运出大堆货物的车辆的碰撞声,以及断裂的墙壁,迟疑待倒的烟囱,被时光和脏污腐蚀殆尽的锈铁栅等难堪的景象与荒凉和荒废景象充斥着。居住者则是那些“最底下的失业劳工、搬运工、背煤工、荡妇、破衣烂衫的孩子”等[6]400。
这说明,即使是当时伦敦这样最光鲜的城市,其内部城区的发展也是不平衡,已经出现了问题频发或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
(二)法国巴黎等城市的发展概况与面相
法国是欧洲大陆较早启动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是城市现代转型、建设、规划等实施较早的国家。这场社会领域的伟大变革,对作家们(如左拉、莫泊桑等)书写城市等带来直接影响,他们从而也创作了若干不朽作品。
左拉(1840—1902)是法国力倡自然主义写作取向的非凡作家之一。他于1877年初完成的一部小说《小酒店》,讲述了一个名叫绮尔维丝的女子在巴黎20年间的命运经历(自1850年迁居巴黎到1869年悲惨去世)。从作者和主人公双重个体的视角来看,这部小说都应该是感知19世纪下半叶的巴黎的面貌、状况及变化等的有益材料。该小说在揭露巴黎所具有的吸引力与魅力,以及城市的驳杂性等方面,简直达到了纤毫毕现的程度。譬如,通过小说主人公的眼睛,每天的清早,从某个三层楼房的旅馆望出去,便能够清晰地看到从城市的外部,如蒙马特和教堂大街的方向上,有汹涌的人流、物流等涌向这个茫茫大海似的巴黎之中,而“这里面……有因一时的障碍而拥挤在道路上的人群,有去上工的络绎不绝的工人队伍,背上扛着工具……”。而在另外的时间,在背离巴黎的一座火车站的铁桥附近,却是“在空旷的天空下面有许多参差不齐的房子,或左或右,各不相连,墙壁是没有粉刷的,墙上糊着大幅的、被机器吐出的烟煤熏黄了的广告……这些广告是各种各样颜色的。其中一张很漂亮的蓝颜色的小广告是为了一只失落的小母狗悬奖”[10]。这些景象既与我们当下国内的经验、观感极相仿或接近,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复现当年巴黎情景的依据。
其实,了不起的城市总是成为不同人的观察对象。在左拉之外,还有很多作家描写、记录巴黎。从莫泊桑等人的作品中,也能够看出法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些情况。
莫泊桑(1850—1893)创作了很多短篇小说,保存了关于城市的丰富信息。如19世纪后期的法国的一些城市,其道路边沿还是一些没有掩盖起来的水沟,城市排污道尚未入地,城市卫生没有保障。《巴蒂斯特太太》中有一个叫卢班的小城市,主人公就曾目睹“不时地有一只猫轻巧地跳过阳沟,从大街穿过去。一条小狗急急匆匆地在一棵棵树根旁闻来闻去,寻找厨房倒出来的残羹剩饭”。这说明,在法国城市化的初期,由于历史条件等各方面的限制,城市基础设施不完善,城市的人居环境亟待改善与提高。
这个时候,城市功能分区尚不十分严格,或者说还存在城市空间的混合利用等情形,也能够从城市描写中表现出来。《绳子》一文就写到一个名叫戈代维尔的市镇,其广场实则也是一个市场:“戈代维尔的广场上,人和牲口混杂在一起,十分拥挤。只见牛的犄角,富裕农民的长毛绒高帽子和乡下女人的便帽在集市上攒动。尖锐刺耳的喊叫声形成一片持续不断的喧哗,在这片喧哗声上偶尔可以听见一个心情快乐的乡下汉从健壮的胸膛里发出的大笑声,或者是拴在一所房子墙根下的母牛发出的一声长鸣。”[11]众多事物混杂在一起,影像与声响交织成一团,显得光怪陆离。在城市化进程中,比较密切的城乡关系尚得以维系,小城镇在服务地方性事务上占据着有利地位、发挥着突出作用。
英国的狄更斯亦在其作品中对18世纪的巴黎进行刻画,而当时的巴黎在建设方面尚有诸多不足或缺陷。譬如,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巴黎的街道尽管已经是石头铺成的了,然而却不平坦、畅通,街上铺路的石头,粗糙、不规整,向四处支棱着,存在要绊瘸靠近它们的每一个人的安全隐患。在这些铺路的石头上且形成一个个小坑,路当中有一条顺街流的阴沟,每逢雨天便会出现泥污之水阵阵外溢,流进各家各户。更可怕的是,城市街道狭窄,没有实现人、车分流,车辆轧人等交通事故难以避免:“在没有人行道的狭窄街道上驱车横冲直撞,这种贵族的野蛮遗风,危及平民生命,也有人惨遭残害。”当然,也有一些市政类的设置,如街道旁有“粗劣的路灯,用穿过滑轮的绳子吊着;到了晚上,点灯夫把灯放下来,点上,又拉上去之后,一簇无力的暗淡的灯捻在头上病恹恹地晃动”[7]28-30,102。这其实正是当时巴黎夜间的照明情况,即1745年的时候,巴黎才用油灯取代了1667年出现的街头晚间依赖灯笼的照明[12]。
另外,文学作品场景描写下的巴黎街道狭窄,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这是因为,在19世纪的50—70年代即奥斯曼改造巴黎完成之前,巴黎街道整体上是不甚宽敞,而且也不笔直[13]。然而,经历城市规划与建设史上众所周知的奥斯曼对巴黎的现代化改造(1853—1870),现代气象的巴黎却光彩照人地出世了。在左拉的《小酒店》中即有简略的折射:“这一年本区大变了样。人们开辟了马尚达大马路和奥尔纳诺大马路,把以前的卖鱼路的界线都消灭了,而且直通到城内的大马路,这叫人都认不得了。卖鱼路一边的房子都拆除了。现在金滴路上可以望见很空旷的天空,阳光够了,空气也流畅了。以前在那方面挡住视线的破旧房屋都没有了……起造了一所六层楼的大房子……很有豪富的气象”[10]356。经此一变,巴黎城的组织结构从此得到调整与规范,空间变得开敞,卫生条件与建筑等得到改善,进步无疑重大而显著。
至于巴黎城之内的生活情景与设施,诸如街道旁有便餐店、带有镜子的店铺橱窗可供过往行人以正衣冠,以及“每个居民的姓名,必须用一定大小的字母,距地面一定的方便的高度,清楚地写在门上或门柱上”——对城市居民实行街道编码制度[7]272,320,当大体不谬。尤其是后者,最可能是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1793—1794)所推行的城市制度的组成部分[9]102。所以,狄更斯在《双城记》所述及的巴黎内部实行人户牌铭制度的情节,当是城市内人、地关系紧密结合的历史事实的艺术性再现。
(三)俄国的城市化及莫斯科
俄国是欧洲大陆工业革命较迟缓的国家,这个特点直接影响、体现在俄国的城市化进程,并渗透到文学里面的俄国城市呈现上。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均提供了例证。
1.屠格涅夫笔下的俄国城市图景
屠格涅夫(1818—1883)不仅曾就读于俄国的莫斯科大学、彼得堡大学,而且还在德国的柏林大学攻读学业,具有较好的观察不同城市的经验积累与广阔视角。在屠格涅夫的时代或之前,俄国城市的道路已经实现了人、车分离,人行道与车道两者间用小水沟进行分隔,从而避免人、车混同,减少交通事故与拥堵,提高城市道路的通行效率。这说明,人车混行、相互碰撞并酿成灾祸的现象,到了这个时候,确与狄更斯所描写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前的法国巴黎的情况迥异了。
另外,当时的俄国社会呈现明显的城、乡二元制格局,以及此两种社会发展空间对不同主体所产生的迥然有异的影响或选择偏好。如有人早年曾在首都彼得堡等地方有过任职经历,后来却重归乡居;而有人虽不排斥乡居,不过在主观上更向往大舞台,不再真正地生发对乡居的感情,因为在那儿大概会沉闷乏味,尽管当时俄国乡村贵族的家居条件并不算差——如他们有书房,有胡桃木、黑橡木做成的家具与书架等。
俄国虽然也迈上了城市化,但是城市化水平在那个时候显然不及法国与德国等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所以俄国贵族首选的国外旅游目的地也是法国的巴黎、德国的德累斯顿或海德堡这样的城市[14]。这种情景也是与历史相一致的,如18世纪早期的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就是向这些国家及其城市等学习。
2.多层面表现俄国城市化的契诃夫
俄国是一个推崇并盛产文学的国度。在俄国文学史上,除了屠格涅夫之外,还有其他很多世界著名的作家、诗人等。例如契诃夫(1860—1904)用生花妙笔从侧面记录了俄国的城市化景象及问题。
首先,俄国的城市化表现为城市扩张。契诃夫在创作于1899年的《宝贝儿》这一小说中,揭示当时俄国已经处在快速城市化的阶段:“渐渐,这座城向四面八方扩张开来。茨冈区已经叫作大街,‘季沃里’游乐场和木材场的原址已经辟了一条条巷子,造了新房子。”可见,城市扩张是城市化的普遍外在表征。
而对于莫斯科来说,则无疑更辉煌,譬如小说《万卡》(1886)就描写了一个从乡村来到这里学习工匠手艺的孩子对这个城市的观感:“莫斯科是个大城。房屋全是老爷们的。马倒是有很多,羊却没有,狗也不凶。”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首位城市最能够为人们津津乐道并满怀憧憬。
至于当时的俄国民众,尤其是农民,与莫斯科这样的大城的关系,在《农民》(1897)一文中多有生动表现:在莫科斯有着当过女仆工作经历的人说,“在莫斯科呀,房子都挺大,是用石头砌的”;而留守乡村的人则对它充满想象与羡慕,说其性质是“莫斯科那个古时候的京城,所有的城市的母亲”,肯定了莫斯科的历史悠久与崇高地位。由此,莫斯科的城市魅力也对很多农民产生了巨大吸引力。一些有能力的人早在1861年解放农奴法令颁布之前的农奴制时代便奔向那里,寻找更好的谋生机会,某些村所有的青年,只要认得字,会写字,就都送到莫斯科去,专门在旅馆或者饭馆里做仆役,或者“送到面包房里去做学徒”。而他们进城的方式即是由某一人先行,然后依赖亲友血缘关系而介绍带动,这样就逐渐地形成了被叫作下贱村或者奴才村的向外输出劳务的专业村。然而,作为大城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当在那里做工的农民因身体有了疾患而无法再立足时,只能携妻带女返乡,而因为恰在于城乡的生活境况不同、成本也不同,回村子里去,在家里不但养病便当些,生活也便宜些。另外,乡村良好、优美的生态环境是莫斯科所缺乏的,故乡的空气柔和、沉静、难以形容的纯洁,这在莫斯科是从来也没有的。不过,由于城乡关系的对立与二者发展的失衡,返乡后的农民所目睹的乡村不仅不再鲜亮,与印象中的故乡截然有别,而且呈现颓败之态,“据他小时候的记忆,故乡的那个家在他的心目中是个豁亮、舒服、方便的地方,可是现在一走进木房,他简直吓一跳,那么黑、那么窄、那么脏”等,表现出极度贫穷。
这些文学中的描写,有着深刻的历史穿透力,栩栩如生,人们自然也无法不承认其客观性、真实性。
当然,落后的土地制度、广袤的国土面积、传统文化与认识等的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制衡着俄国城市化的推进速度,对城乡关系的均衡等也有作用。
在《醋栗》(1898)一文中就表现了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对乡村的留恋。尽管城市化作为主流趋势,对人们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态度等产生了广泛影响,城市生活以其显著优势而获得深刻赞扬,“离开城市,离开斗争,离开生活的喧嚣,隐居起来,躲在自己的庄园里,这算不得生活,这是自私自利,偷懒,这是一种修道主义,可又是不见成绩的修道主义”,不过呢,当时的部分俄国人对于乡村居住生活仍然秉持着不小的留恋,其内在的原因在于乡村生活自有它舒服的地方,譬如“在阳台上一坐,喝一喝茶,自己的小鸭子在池塘里泅水,各处一片清香”,以及“只要人一辈子钓过鲈鱼,或者在秋天见过一次鸫鸟南飞,瞧着它们在晴朗而凉快的日子里怎样成群飞过村庄,那他就再也不能做一个城里人,他会一直到死都苦苦地盼望自由的生活”。因此,那有若干亩田地、连同草场、庄园、小溪、花园、磨坊和活水的池塘的农庄,也就成了即使已经在城市里面任职做事的一些人的精神故乡与向往了。这或许可以理解为是早期的逆城市化苗头。
关于城市与人口素质的密切关系问题,即城市的定位、等级与其市民之间有着直接的正相关,城市欲提升其影响和声誉,获得广泛赞美与认同,需要从养成或遴选更具有文明素养的市民开始的事实,也被文学家所关注并写入到作品中。譬如,《第六病室》中说,发生不分青红皂白把人关入精神病院的事情,“这样糟糕的东西也许只有在离铁路线两百俄里远的小城中才会出现”,与这里远离文明中心——如莫斯科等有关。相反,在“大城市里并没有智力停滞的情形,那儿挺活跃,可见那边一定有真正的人”。而从那里委派到下级城市履行职务的人却匮乏足够的才能,成为这个不幸的城形成的重要原因。在《出诊》一文中,作家再一次发问:“这些全城顶有才能的人尚且这样浅薄无聊,那么这座城还会有什么道理呢?”[15]这其实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城与人的关系之问。
(四)文学下的美国城市更新① 关于城市更新的话题,其实已超出了本文预设的论述范围,而且此时段或时期内产生了大量、足够的影像资料对城市更新进行记载、表达或再现,但考虑到检验方法论的必要性或分析理论的有效性,此处亦对美国的城市问题或城市更新给予略述、简论。
美国在迈上工业革命、城市化道路,与欧洲大陆明显不同。从整体上来看,这是由其较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发展条件所决定的。但作为一个后起却迅猛崛起的新生国家,美国也曾在其赢得独立后的19世纪等时期内经历了一个城市化进程。例如,杰克·伦敦(1876—1916)曾在《疑犯从宽》一文中塑造了一个名叫卡特尔·华特森的人物,他曾到处漂泊,研究世界各地的社会情况,但是20年后当他重返故乡的城市时,发现它已经由原来的三万人口变成了一个三十万人口的西部大城,而且到处都是日本人的商店等,这就难免让他所看到的变化真是惊人起来[16]。这其实正是美国城市以及世界移民等的真实写照,因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短短一二十年间,确实是向美国移民的高潮期,1890—1914年移民人数为1700万[17]。然而,在先期的城市化之后的城市更新,才应该是这个新大陆在世界城市发展格局里面最引人关注的地方。
所谓的美国的城市更新,是指在其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科学化、现代化主旨指导下的一个持续性的历史过程,始自20世纪的30年代,一直延续到60年代中期。而在美国的城市更新的一定时期,有一些文学作品也对之进行了集中记载、表达。这里以华人作家作品为例,简述之。
在20世纪50—70年代的美国文学中,有一支创作主体主要为台湾留学生的华文作家队伍,他们以外来与融入的视角,审视了当时美国的都市生活,集中以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城市为背景,刻画了那个时段的美国城市存在状况及未来趋势。而这个时期,恰是美国城市发展的转折、过渡期,其相关的阶段性特征,也能够从文学描写中得到生动体现。白先勇的小说《安乐乡的一日》《谪仙记》等展开故事的场景,都是在纽约外围,而那里正是成功人士的聚集区。这些作品揭示了当时美国城市正处在郊区化的进程中[18]。
在个案城市方面,关于芝加哥这个汽车城的潜伏问题或落魄端倪,当时人们已察觉,譬如对于当时芝加哥城的南部地区,各种不法现象频发:“晚上来这一带游逛的人常常会吃到闷棍,然后钱包被割去,运气坏的,把命都送了”,甚至芝加哥三十几街到四十几街一带的脏和穷,还不如台北的某些巷子,而“芝加哥的南面……所代表的贫穷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贫民”[19]。这无疑是严峻的城市问题。
有问题,就要应对和化解。作为五大湖地区最大,曾经建立在重工业基础之上的城市,芝加哥最终在后工业化时代,没有顺延传统优势而放纵机遇;相反,这个城市积极探索、寻找出路,实现了产业替代,在城市战略转型方面确立了有效应对的方法,避免了像汽车城底特律那样的全面危机与深度衰败,这不能不说是高明的城市规划与设计挽救了城市自身的成功例证。今日的芝加哥,其第一大产业是消费与娱乐业,具体涵盖旅游业、会议、餐饮、酒店等行业与业态。而芝加哥也是美国最早进行城市规划的城市,其标志是1909年伯恩汉(Burnham)的芝加哥规划方案。
当然,美国城市在更新时期的其他一些表现,诸如郊区化、白人逃离、中心城区的空心化等,在这批文学作品中也都有具体描写。
四、结语
追随工业革命的脚步而起的欧美国家与地区的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件大事。为了总结经验、发现规律、指导实践,甚至从其中的问题与病症中获得警示或启迪,均有必要对这一时间跨度较大的历史进程内的诸多知识和面相做出既深刻且全面的梳理、概括。这就不仅要进行抽象的城市发展规律的提炼,也需要对该历史洪流中的丰富现象和各类事件进行分析、研判。
大致而言,借助于既有城市史的研究成果与基础,人们对欧美国家城市化的整体演进与内在逻辑的把握和认识是较清楚的,对于他们的城市化路径等亦无大的疑问或争议。然而,由于时过境迁,当时很多的城市化景象已不能为后人所知、所触、所见,这样就会成为城市史研究中缺乏生动性、在场感的遗憾。
不过,在那个时期所涌现的一些杰出作家,他们曾依创作的需要,记载了当年城市化的时代特征,塑造了由他们转述或再加工的艺术化的城市世界,可算是对当时的城市化时代的留影存照。因此,从这些作品的场景描写、舞台背景呈现中,能够发现很多及很丰富的城市现象、城市问题等,从而为近似地理解与认知已经逝去的城市化图景提供解读文本或有用视窗。
当然,文学家于城市化时代创作的作品,初衷并不是要为后人研究城市史预设方便,其主要的注意力与观察点乃在于铺陈一个可供故事展开或上演的场景;他们对城市的描写也不完全是写真或白描,而是具有较大成分的取舍性与艺术加工在里面。因此,不能不加分析与斟酌地对这些材料全部予以采信。恰当的做法是,在使用这部分资料进行城市史研究时,尚需要参酌城市史、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等学科知识的成果,进行必要的对比分析。不过,整体上,当年文学家们的无心插柳之举,确实也能够让城市史研究鲜活、生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