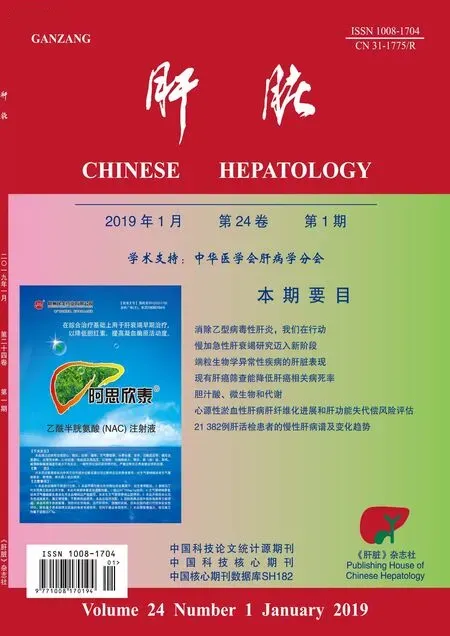肠道微生态与慢性肝病研究进展
卢峪霞 杨长青
随着近年来宏基因组学和代谢组学的进步,发现了肠道微生态在很多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最新的文献总结了肠道菌群在调节宿主生理及病理变化中的作用,并将焦点集中于肠—肝轴[1]。Marshallpo[2]于1998年正式提出了“肠-肝轴”的概念。由于肠道菌群失调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导致肝功能异常、肝脂肪变性和结缔组织重塑等慢性肝病进展,其中有炎症介质、细胞因子、氧化应激、线粒体功能紊乱等参与。肠道屏障功能被破坏时,肠道渗透性增加导致肠衍生细菌产品如脂多糖(LPS)的易位,刺激toll样受体(tlr),激活库普弗氏细胞、内皮细胞、树突细胞、胆道上皮细胞、肝星状细胞,导致肝纤维化,引起慢性肝病[3]。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失调与各种肝病有关,如酒精性肝病、非酒精性脂肪肝、肝硬化、自身免疫性肝病和肝癌等。肠道微生态与慢性肝病之间的关系,成为了新的研究热点,本文对近年来这方面最新进展作一综述。
一、 肠道微生态与慢性病毒性肝炎
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在诱导和促进乙肝病毒引起的慢性肝病进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阐明慢性乙肝早期肠道微生物的组成、功能特征,及其在疾病进展中的影响,有学者[4]入组85名低Child-Pugh scores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及20名健康对照,收集粪便样本,应用 Illumina MiSeq 测序平台进行菌群鉴定,发现与对照组比较,慢乙肝组肠道菌群有以下显著变化:5个物种操作单元(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 OTUs)增加,包括Actinomyces、Clostridium sensu stricto、unclassified Lachnospiraceae和Megamonas;27个OTUs减少,包括Alistipes、 Asaccharobacter、Bacteroides、Butyricimonas、Clostridium IV、 Escherichia/Shigella、Parabacteroides、 Ruminococcus、unclassified Bacteria、unclassified Clostridiales、Unclassified Coriobacteriaceae、 unclassified Enterobacteriaceae、unclassified Lachnospiraceae和unclassified Ruminococcaceae等。
另有研究在患有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患者中,应用定量PCR和免疫学技术,研究粪便参数,包括粪便占主导地位的细菌数量,以及从大肠杆菌、脆弱拟杆菌、梭状芽胞杆菌、产气荚膜梭菌以及一些免疫学参数[5]。数据分析表明,16 S rRNA基因拷贝数为柔嫩梭菌、粪肠球菌、肠杆菌、双歧杆菌和乳酸菌(乳酸菌属、片球菌属、明串珠菌属和魏斯氏菌属),在乙肝肝硬化患者的肠道中显示出明显的变异。双歧杆菌和肠杆菌科(B/E)比值,表明肠道菌群的定植抗力,从健康对照组(1.15±0.11)、无症状携带者(0.99±0.09),慢性乙型肝炎患者(0.76±0.08),到肝硬化失代偿患者(0.64±0.09)依次显著降低(P<0.01);表明(B/E)比值可以反映肝脏疾病进展过程中肠道微生态的失调。致病基因增加表明在肝脏疾病恶化过程中,致病因子的多样性增加。在失代偿乙肝肝硬化患者中,粪便SIgA和肿瘤坏死因子的水平高于其他组,表明机体试图通过复杂的自我调节系统达到新的肠道微生态平衡。
我国学者[6]设计了一项通过粪菌移植(FMT)治疗经过长期NA治疗后HBeAg仍未转阴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病例对照、开放标签的前瞻性研究。该研究纳入了18例经恩替卡韦或替诺福韦治疗3年以上但仍未实现HBeAg消失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患者在继续接受抗病毒治疗的同时,5例接受了FMT,13例作为对照。FMT治疗组患者接受经胃镜FMT治疗,每4周1次,直到HBeAg消失。4例患者接受了1~7次治疗,1例患者在第5次FMT治疗后退出了试验。随访结束时,FMT组患者的HBeAg滴度较基线水平有显著下降,且每次FMT治疗后逐步下降。2例患者在接受了1次FMT后即实现HBeAg清除,还有1例在2次FMT治疗后清除HBeAg。相反,对照组没有1例患者清除HBeAg。
最近研究表明[7],肠道微生物群的改变可能与丙型肝炎病毒诱发慢性肝病(CHC)的发病机制有关。HCV患者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在肝脏疾病阶段是稳定的,不同于非酒精性脂肪肝、乙型病毒性肝炎、艾滋病毒和丙肝病毒共同感染患者的肠道微生态的不稳定性。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对肠道渗透性的影响,可导致肠道菌群失调开始、进行以及促炎作用,直至发展成肝硬化和肝癌。根除HCV消除了肠道微生物群不平衡对肝脏疾病发展的影响,并可能对益生菌的使用产生影响,从而改变肝硬化进展的自然历史。
二、 肠道微生态与肝炎肝硬化
Wei等[8]招募了120名乙肝肝硬化患者和120名健康对照组患者,通过对完整的元基因组DNA和生物信息学方法的高通量测序,对20例乙肝肝硬化患者及20个健康对照组进行了比较,分析了粪便微生物群落和功能。发现儿童Child-Turcotte-Pugh 评分和拟杆菌(P<0.01)呈负相关,而和肠杆菌科及韦荣氏球菌呈正相关(P<0.01)。对另外200个粪便微生物群样本的分析表明,肠道微生物标记可能有助于区分正常人群和肝硬化患者。与对照组相比,在肝硬化患者的粪便微生物群功能多样性显著降低。肝硬化病人的粪便微生物群显示在谷胱甘肽、糖异生、支链氨基酸、氮和脂质的代谢方面增加(P<0.05),而芳香族氨基酸、胆汁酸的代谢以及与新陈代谢相关的细胞周期减少(P<0.05)。研究提示肝硬化患者粪便微生物群有广泛差异和代谢潜力,肠道微生物群落可以作为调节人体新陈代谢平衡的独立器官,并影响肝硬化患者的预后。
三、 肠道微生态与酒精性肝病
研究者[9]对在两种不同的动物设施中的ALD进行了不同的处理,以测试两种互补策略(粪便微生物群移植和益生菌治疗)的有效性,以逆转不正常生活和防止ALD的发生。在两种不同的动物设施中,老鼠被喂食酒精,并使用Lieber DeCarli的饮食(一种酒精性脂肪肝造模饲料)。用对酒精抵抗的供体老鼠的新鲜粪便移植到对酒精敏感的老鼠,每周三次。另一组老鼠在喂食酒精期间给予了果胶。结果显示:对酒精敏感的小鼠,酒精引起脂肪变性和肝脏炎症,与肠道内稳态破坏有关,对酒精抵抗的小鼠则不然。肠道菌群分析表明,在酒精敏感的小鼠中,拟杆菌属的比例显著减少(P<0.05)。分析显示,酒精敏感和抵抗小鼠的肠道菌群聚集方式不同。果胶疗法引起了对肠道菌群的重大改变,粪菌移植可以使对酒精敏感的小鼠与酒精抵抗小鼠的肠道菌群非常接近,这两种方法都防止了脂肪变性、炎症和恢复肠道内稳态。提示对酒精性肝病的敏感性是由老鼠的肠道微生物群引起的,可以用酒精抵抗的供体老鼠粪菌移植到对酒精敏感的老鼠或用益生元来治疗酒精诱发的肝损伤。
有研究证实肠道微生物群会影响个体对酒精性肝病的易感性[10]:接受严重酒精性肝炎患者粪菌移植的老鼠比接受没有酒精性肝炎的酗酒者粪菌移植的老鼠出现更严重的肝脏炎症、肝T淋巴细胞亚群和自然杀伤T淋巴细胞(NKT) 数量增加、更多的肝细胞坏死、肠道通透性增加和更多的细菌易位;同样,CD45+淋巴细胞在内脏脂肪组织中增加,在肠系膜淋巴结中CD4(+)T和NKT淋巴细胞增多;严重酒精性肝炎和无酒精性肝病的肠道菌群的细菌丰度和成分存在差异;严重酒精性肝炎的肠道菌群主要是有害细菌,而无酒精性肝病的肠道菌群主要是肠球菌属,熊去氧胆酸也更丰富。提示个体对ALD的敏感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肠道菌群驱动的,因此可以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来预防和管理ALD。
为研究益生菌(培养乳酸菌/链球菌)对酒精性肝炎治疗的影响,一项随机对照的多中心研究提示7 d口服补充乳酸菌、链球菌可以重建肠道菌群和改善患者的内毒素(LPS)水平[11]。从2010年9月到2012年4月,有117例患者(益生菌60和安慰剂57)被前瞻性随机分配,接受7 d的培养乳酸菌/链球菌(1 500 mg/d)或安慰剂。通过粪便培养,对肝功能试验、促炎细胞因子、LPS和菌落形成单位进行了研究和比较。结果显示两组中天冬氨酸转氨酶/丙氨酸转氨酶、碱性磷酸酶、谷氨酰转肽酶、胆红素、凝血酶原时间均显著改善。在益生菌组(基线和之后),白蛋白[(35±7)和(37±6) g/dL,P=0.038]和肿瘤坏死因子[(121±244)和(71±123) pg/mL,P=0.047]显示出差异。此外,大肠杆菌的菌落形成单位数量显著减少[(435±287)和(168±210),P=0.002]。在安慰剂组中,LPS的水平[(1.7±2.8)和(2.0±2.7) EU/mL]显著增加。在组间比较中,各组间观察到肿瘤坏死因子(P=0.042)和LPS(P=0.028)的显著差异。
通过白介素-22、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或法尼酯X受体激动剂、抑制细胞凋亡、早期肝移植和通过抗生素或粪便移植方法调节肠道微生物群来促进肝再生,是目前临床研究的新课题。抑制氧化应激、调节肠道菌群以及刺激祖细胞增殖和促炎途径,将是今后的研究方向[12]。
四、 肠道微生态与非酒精性肝病
非酒精性脂肪肝(NASH)的发生发展包括基因差异、脂肪堆积、胰岛素抵抗和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等多方面因素,其中肠道微生物群被认为起着重要作用,会影响肝脏疾病的肝硬化前期和肝硬化,这可能会为诊断、治疗和研究带来新的策略[13]。
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出现的进展性纤维化是肝脏死亡的最重要预测因素。在一项前瞻性研究中[14],研究者用从粪便样本中提取的DNA全基因组测序来描述肠道微生物组的组成。这项研究包括86例经过肝活检证实的NAFLD患者,其中72例有轻/中度(0~2纤维化)NAFLD,14例晚期纤维化(3级或4级纤维化),发现了一组40个特征(P<0.006),其中包括37种细菌,被用来构建一个随机的森林分类模型,以区分出轻/中度的NAFLD与晚期纤维化。该模型具有较强的诊断准确性(AUC 0.936),用于检测晚期纤维化,为通过粪便微生物宏基因组学特征来检测肝纤维化进展提供了初步的证据。
五、 肠道微生态与肝细胞癌
近年研究表明,肠道菌群作为门静脉内毒素的主要来源可能在肝硬化和肝细胞癌(HCC)的发生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5]。Grat等[16]纳入15例肝癌患者和15例非肝癌但因肝硬化及晚期肝病而行肝移植的患者,对其进行了肝移植MELD评分,对其肠道微生物概况的分析是基于从移植前阶段收集的粪便样本。结果显示有无肝细胞癌的患者在年龄(P=0.506)、性别(P=0.700)、丙型肝炎病毒(P=0.999)和乙型肝炎病毒(P=0.715)感染状况、酒精性肝病(P=0.999)和MELD评分(P=0.337)等方面相似。值得注意的是,HCC的存在与显著增加的大肠杆菌的排泄物数量有关(P=0.025)。基于大肠杆菌计数的HCC存在的预测与接受者-操作曲线下的面积为0.742(95%可信区间,0.564~0.920)相关联,最佳截点为17.728(每1克粪便的菌落形成单位的自然对数)。确定的截点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比率分别为66.7%和73.3%。由此认为,肠道微生物群与肝细胞癌的存在有关,其特点是增加粪便大肠杆菌的数量,大肠杆菌的肠道过度生长可能导致肝癌发生。
六、 肠道微生态与自身免疫性肝病
为探讨自身免疫性肝炎(AIH)患者肠道渗透、细菌易位和肠道菌群的变化、并评估这些变化与疾病分期的相关性,Lin R等[17]招募了24名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和8名健康志愿者,通过对十二指肠活检标本的免疫组织化学分析,对肠内紧密连接的完整性进行了评估,16 S rDNA定量PCR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使用ELISA通过脂多糖水平分析细菌易位,发现肠道通透性增加、微生态紊乱、细菌易位与疾病的严重程度有关,提示自身免疫性肝炎与肠道和肠道微生态失调有关,受损的肠道屏障可能在AIH的发病机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研究发现携带HLA-DR3转基因AIH小鼠的肠道菌群多样性和丰度下降,无菌鼠对刀豆蛋白A诱发的肝损伤有拮抗作用,而肠道抗原则诱导激活自然杀伤T细胞,参与到肝损伤中,提示了微生物群和AIH之间的密切关系[18]。
回顾自身免疫性肝炎的发病机制和治疗,发现了肠道微生态在先天和适应性免疫反应方面的作用,从而促进系统免疫介导性疾病的发展[19]。肠道菌群组成的改变会扰乱肠道和系统的免疫耐受。肠内的toll样受体可以识别相关的分子模式,并形成T辅助淋巴细胞的子集,这些淋巴细胞可以与宿主产生抗原交叉反应(分子模仿)。激活的肠道衍生的淋巴细胞可以迁移到淋巴结,而由肠道衍生的微生物抗原可以转移到肠道外的地方。炎症因子可以在肝细胞和肝星状细胞内形成,并且可以驱动促炎症、免疫介导性和纤维化反应。饮食、益生菌、维生素补充剂、抗生素、减少肠道渗透性的药物,以及阻断信号通路的分子干预,可能会成为补充常规免疫抑制管理的辅助疗法。
尽管许多研究表明益生菌对慢性肝病有益,但还是有争议。有国外学者研究探讨益生菌疗法在缓解慢性肝病的肠道细菌过度生长(SIBO)和通透性方面的功效[20]:53例慢性肝病患者被随机分为益生菌治疗或安慰剂,使用了6种细菌:双歧杆菌、乳酸双歧杆菌、长双歧杆菌、嗜酸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和嗜热链球菌,4周后研究粪便细菌、SIBO、肠道通透性和临床症状的变化。结果提示:益生菌治疗组(P<0.001)的粪便中增加了6种益生菌中的3种,而在安慰剂组中,粪便微生物群没有发生变化。在许多益生菌治疗组中SIBO消失了,但在安慰剂组一个都没有消失(24%比0%,P<0.05);一般的胃肠道症状在益生菌组中也有改善,肠道通透率的提高在益生菌组比安慰剂组稍微多一些(50%比31.3%,P=0.248);粪便中乳酸菌的数量与肠道通透率负相关(P为趋势<0.05);两组中肝脏生化学并没有显著改善。由此认为,慢性肝病的短期益生菌管理对缓解SIBO和临床症状有效,但对改善肠通透性和肝功能无效。
随着人们对肠-肝轴认识的深入以及系统生物学的进步,肠道微生态在慢性肝病的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已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肠道微生态纷繁复杂,慢性肝病多种多样,要进一步阐明其作用机制和管理策略,尚需深入的基础研究和大样本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