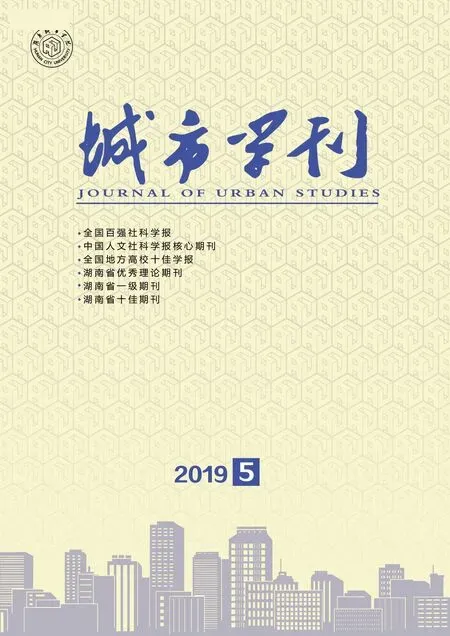日常生活审美视域中的湖南花鼓戏
刘 科,周 勇
日常生活审美视域中的湖南花鼓戏
刘 科,周 勇
(湖南城市学院 艺术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
湖南花鼓戏的产生和发展,与特定区域范围内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及其审美习性有着密切关联。花鼓戏的产生,表征着人们日常生活感性完善的追求,书写着人们的生活体验和审美体验。花鼓戏的艺术表现,则主要依托于节庆,以审美仪式的方式呈现其艺术内涵。同时,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样式,湖南花鼓戏以独特的美学追求,体现出对现实生活的升华,呈现出超越性特征。
地方戏曲;湖南花鼓戏;审美体验;日常生活;
作为地方戏曲艺术的代表,湖南花鼓戏的产生和发展,与人们日常感性生活体验的真实表现密不可分。现代社会主体感性的分裂,是花鼓戏在现代社会中遭遇尴尬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因此,从主体的感性体验及其需求满足出发,是探寻花鼓戏艺术形态生成的重要视角。作为特定区域中生产生活主体审美交流的载体,花鼓戏的传播和影响,依赖于节庆和特定的审美仪式而进行,在其中,花鼓戏实现了艺术形式与民间文化习俗及外来文化的交流与共生。
一、体验:地方戏曲的感性完善追求
(一)艺术内容:日常生活体验的间接呈现
作为民间戏种,湖南花鼓戏正式形成于清朝嘉庆年间,其后在长期的演变和创新道路上逐渐与其他泛娱乐形式的歌舞节目相分离,成为一种拥有较广泛群众基础的成熟民间戏种。这样,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来说,湖南花鼓戏都不失为一种表达日常情感体验的承载体。从艺术表现来看,湖南花鼓戏糅合了采茶调和花灯戏等歌舞类节目的文化特色和表演形式,因而具有较为浓厚的地域文化内涵和乡土气息。而从其表现的对象和内容来看,作为一种舞台表演剧目,湖南花鼓戏在剧情中都反复穿插人民勤劳生产与繁忙农事等日常情景,因而被视为是一种活泼明朗、充分反映民间现实的戏种之一。尤其是在发展初期,湖南花鼓戏通常以民间小调和生活小戏作为主要内容进行歌舞表演,来表达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内容与情感,如这一阶段的传统剧目《打鸟》《盘花》等。清末民初,湖南花鼓戏表现日常生活内容的范围进一步拓展,同时“川调”和“打锣腔”融入到一些剧目中,由此而衍生了部分以民间经典传说为题材的作品,代表性的剧目有《清风亭》《芦林会》《张光达上寿》《赶子上路》等。也基本是从这时候开始,湖南花鼓戏作为产生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以生动的表现特点,呈现日常生活感性经验的艺术形式,正式纳入到完整的戏曲艺术范畴之内了。
(二)艺术风格:日常情感的感性表达
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认为,现代社会技术的进步使社会总体和人逐步走向分裂,社会的分化,打破了和谐的日常生活整体,尤其是在商品拜物教和技术崇拜以后,所以列斐伏尔所提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对抗社会和人的感性分裂而提出的一种对抗策略。[1]但于湖南花鼓戏而言,在发展初期,其艺术的审美呈现,还是列斐伏尔所提及的感性分裂之前的一种状态,因而其艺术风格,呈现的是自然、朴实的日常情感,具有和自然、社会与主体圆融一体的素朴的审美特征。
一是朴实通俗的乡土风格追求。在选材和主题上,湖南花鼓戏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邻里乡间、各门各户的生活趣事,正如平日里乡亲之间互相唠家常时的对白,戏词平白朴实,很容易让观众沉浸到戏中人物的内心里,与其产生共鸣,进而增强角色在舞台中的戏剧张力。这种审美风格形成,就是以完善的感性主体的形成为依据的。以《打铜锣》的主人公蔡九为例,他就凭借一番出自肺腑的感人对白,在两三句话之后就迅速拉近同观众间距离,使得自身人物形象深入人心。
我一不怯台,二不打顿
要别个哭就哭,要别个笑就笑
从没踏过场
这样一种表达,是农村中农民生活的质朴表达,于主体特征的彰显之中,充满着一种素朴的自然之美。
二是民俗特征的个性风格追求。编剧在设计舞台语言时候,注重舞台语言的通俗性,依据人物性格为其量身打造生动、形象的语言风格,而且极力凸显角色的性格色彩,来烘托乡土小人物的气质。例如《小姑贤》中,姚氏就是一副厉害、刻薄的“恶婆婆”相,一番打骂媳妇的念白,表现了她尖酸刻薄的性格。
另外,花鼓戏语言风趣幽默,擅长通过唱段来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
张先生我爱看灯,怎奈我无钱打包封,关门躲债主,设法做人情,关门闭户过新春。
这一唱段将一个生活在最底层,穷且好面子的私塾先生的形象刻画得生动有趣,好面子和直白的心理描述形成强烈的反差,突出唱腔的喜剧效果和方言表达相契合的个性风格,将底层老百姓的小市民心态表达得淋漓尽致。
三是生活情感的喜剧风格追求。湖南花鼓艺人大多选择以乡土百姓的身份进入到戏曲主题和剧本创作中,对戏剧剧本进行故事情节的构思和打磨,因此许多作品均以农民真实生活的立场和视角,来挖掘其周边生活的情趣。这种创作模式使得花鼓戏许多作品相对其他戏种而言更为直白易懂,让观众看完即可在乡邻之间自发演绎和传播。如经典曲目《韩湘子化斋》里,本已修成正果的韩湘子却乔装成相貌丑陋、身体残缺的瘸子来试探妻子对自己的感情,这一闹剧最终为观众平添了许多笑料。这种故事情节的构思凸显日常生活的矛盾与冲突,挖掘其戏剧性,以一个地方老百姓的处事和思维方式来构思故事和表现人物。
四是湖南花鼓戏针对喜剧人物的性格设置大多是正面积极的,因而观众很难在花鼓戏中见到大奸大恶的坏人,主角多为性格淳朴、勤劳而善良的人,这也使得很多作品本身所宣扬的是一种多行善事的普世价值观。代表作《打鸟》《扯萝卜菜》等均为世人称颂。另外,湖南花鼓戏在表现手法上大多采用轻快而悠扬的旋律和唱腔,渲染戏中人物试图营造的喜剧气氛和情感色彩,让台下的观众情不自禁受其带动和感染,进而产生一种振奋人心、心情舒畅的观后感。所以,尽管有好人和坏人、正面和负面人物的冲突,但是这种对来源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形象的描述,都是以喜剧化的方式来呈现,对于人性的描述,也大多停留在人与人的日常冲突阶段,还尚未在主体与社会割裂的层面来探讨人的感性分裂问题。
整体而言,湖南花鼓戏在发展初期,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小农经济相适应,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未遭受现代启蒙和技术植入的冲击,因而艺术形态的日常生活化呈现,是原始和素朴的,保留着主体的感性完善和艺术形式的自然完满,因而也呈现出素朴的美感。
二、节庆和仪式:地方戏曲审美仪式化呈现
列斐伏尔认为,节庆是具有颠覆意义的,因为特定节日使人们能够摆脱感性分裂,得到暂时解脱,进而重塑人们的体验,尤其节庆往往伴随着狂欢,使人们获得一种短暂的自由。[1]213对于湖湘大地的老百姓来说,节庆是集中展现日常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舞台,也是对日常生活进行审美概括的一种重要方式。当然,对于湖南花鼓戏来说,这种“节庆”的存在,比列斐伏尔所提及的要更有意味。因为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一方面它具有了列斐伏尔所说的这种获得主体解放的特质,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与区域和乡土文化密切相关的艺术形式,它又与原始的特定仪式密切关联。在湖南花鼓戏的发生和发展中,节庆以其独特的功能和特有的仪式结合,使地方戏曲的美学形式、艺术内涵和社会价值呈现出特有的意蕴,令其发展初期既有现代意味,又有原始仪式功能的承续,从而独具魅力。
(一)节庆与湖南花鼓戏发展的密切关联
民间节日作为湖南花鼓戏初期较为关键的生态孕育环境,为其发展壮大提供了充足的发挥空间和功能展示,同时民俗节日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很好地承载了不同民族因为地域文化差异而形成的风土人情与宗教信仰。列斐伏尔所说的节庆及其审美解放意义,是在现代性语境中形成的。这种民间节日,虽然并不完全处于“现代性”的语境之中,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其作为审美解放的活动性质同样存在,而湖南花鼓戏也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中不断发展的。
可以说,只要是逢年过节,湖南各地花鼓艺人均会到乡镇进行剧目演出,表演时间多集中在春节、端午、重阳等节庆日。节日民俗活动中的歌舞演出与湖南花鼓戏之间密不可分,两者相辅相成,这种关系在湖南各地方史志中均可窥见。像嘉庆年间的《祁阳县志》就曾记载:“上元,城市自初十日至十五日,每夜张灯大门,有鱼、龙、狻猊、采茶诸戏,金鼓爆竹喧闹,午夜不禁。”[2]从这些描述里可知人们互相走访并联络亲友感情,在放松身心之余追求精神上的娱乐享受,此时花鼓戏就作为一种重要娱乐方式介入到节庆活动中,成为人们的精神消遣。花鼓戏中放鞭炮、焚香化纸、敬拜神灵,体现了观众在节日中的驱邪祈福心理,节庆活动成为曲艺发展的重要推动要素。
(二)特定审美仪式中地方戏曲的仪式化呈现
仪式化功能,使主体和审美的解放走向一种超越性。在湖南地方乡土民俗中,根据人生礼仪仪式的不同,相应也有不同的戏曲呈现。另外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湖南花鼓戏表演习俗、仪式和剧目内容等深受民俗信仰的影响。
1. 人生礼仪与戏曲呈现
1) 诞生礼。诞生礼作为人初生以来极为重要的人生礼仪,当地家长会选择在满月、周岁等日子为小孩举办大型酒宴,此时各地亲朋好友纷纷赶来祝贺,并邀请花鼓戏班进村登台演出,活跃气氛。此期间还流行为小孩子点朱红以祛病免灾,这里的花鼓戏作为家长祈愿家庭昌盛的助兴节目,主要以《麒麟送子》《五子夺魁》这类节目为主。
2) 婚礼。婚礼作为地方农村较为隆重和盛大的人生礼仪,在古代即由六礼之说,而民间各地为了简化婚礼的程序仪式,并没有严格按照“六礼”来举办,而是效仿大户人家的做法,会在婚礼当天邀请戏班举办盛大演出,以图热闹和喜庆。婚礼当天的花鼓戏演出节目多与喜庆剧目和婚娶类主题有关,在宴请宾客也可点选戏曲节目,较为流行的有《三喜临门》《牛郎织女》和《雀巢拜母》等。
3) 寿礼。寿礼作为一种重要的地方乡土仪式,从古至今都极为流行,特别是经济宽裕的人家均会选择举办戏会为家中长者祝寿,演出内容和主题多以吉祥团圆为主,如寿星爱看悲怜戏剧,戏班也会相应调整剧目来演出。在在寿礼仪式中较受欢迎的剧目主要有《三姑记》《十拜》《思凡》等等。花鼓戏在此等人生仪式中作为重要流程,目的在于为家中长者带来欢乐,也代表年轻一辈为其祝寿的心意,让整个仪式更显吉祥和美满。
4) 丧葬礼。葬礼作为一种耗资较多的哀悼仪式,一般在地方农村中为大户人家所热衷。为了聊表对死者的尊重和最后的孝心,会特别隆重地对待葬礼仪式,不但设宴招待村中往来人家和亲友,同时为了在宴席中增添哀悼思念之情,还会为顺应湖南当地“哭灵”习俗,邀请花鼓艺人表演哭腔剧目,来吊唁和慰藉逝者已逝的魂灵。可以说,湖南花鼓戏在丧葬礼的悼念仪式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一般会选择以《哭灵》《丧尸赞包封》等来演出。
2. 宗教信仰与戏曲呈现
自古以来,巫风就盛行于潇湘一带,民间信仰极为盛行,当地群众受佛道两教的影响,十分崇拜神灵。湘楚文化中巫师为了请神还愿会经常表演傩戏,并在酬谢神灵的活动中设“法堂”和请“神灵”,而“法堂”在后来的演变中也逐渐成为“师公”同戏曲表演者共同合作的舞台。像衡阳《大盘洞》中的折戏《和神》就是此类戏曲的代表作。另外,如邵阳花鼓戏也在发展和演变中与“巫教”祭祀活动有较多联系,像东路和西路花鼓戏中的很多演员多由“巫教”担任,他们在行教期间还会兼职演唱花鼓戏。由此可知花鼓戏同驱傩仪式之间是整体的关联存在,花鼓戏艺人和巫师之间根据实际教务而实现角色的自由互换。后期两者开始随着文化的演进而出现关系上的疏远,花鼓戏的宗教功能逐渐淡化,同时娱乐功能显著增强,并演化成为成熟的戏曲类型。
到了近现代,每逢神诞日会有很多庙会,湖南花鼓戏为酬神而进行的演出也是庙会的重要内容。人们拜神时可以欣赏花鼓戏,神灵信仰者成了花鼓戏的观众群,信仰活动无形中对花鼓戏的发展传播有一定促进作用,是湖南花鼓戏生存的又一载体,为湖南花鼓戏提供了传承的空间,促进了湖南花鼓戏的成熟。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湖南花鼓戏的艺术表现,由追求对现实的写照,逐渐走向对现实的超越。
(三)节庆和仪式中地方戏曲仪式化呈现的审美功能
传统的花鼓戏与生俱来一种民间力量。在形成之初就确立了与官方不一的功能,具有民间市场性与广场性,也具有狂欢节仪式表演的自由与解放功能,其一方面寄托着广大人民的生活理想,同时也渗透着大众一般意义上的审美情趣。
1. 娱乐功能
湖南花鼓戏表演艺术通俗朴实,明快活泼,但却载歌载舞、极具表现力,尤其是它幽默诙谐的艺术特征更是增加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娱乐性,使审美娱乐作为保持主体感性完善的一种重要方式而融入了花鼓戏的艺术形式之中。
湖南花鼓戏作为地方戏曲,其极为重要的审美功能在于以通俗娱乐活动的形式寓教于乐,传递正确的艺术审美理念。在进入到新时代以前,当时较为保守的社会环境使得可供人们选择的娱乐方式乏善可陈,而充满生活情趣、娱乐幽默且极富技艺的湖南花鼓戏就成为当时群众极为热衷的娱乐选择。当地居民不但爱好花鼓戏中较为生动而充满奇趣的情节和人物,而且还热衷于对不同剧目的典型形象,如“痴情书生”“负心郎君”“喊冤妇人”等进行谈论,以渲泄自己的情绪,释放自身情感。而湖南花鼓戏一向平实无华、优美婉转的唱腔也满足了其对艺术审美的需求和情感体验。
2. 教育功能
湖南花鼓戏不但娱乐大众生活,同时也富有积极的教育意义,其以戏曲表演的形式传达符合时代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宣扬社会正义,劝人弃恶从善,在生活中积极向上,努力追求真善美等道德品质。从最近几年来重新改编过的湖南花鼓戏来看,其顺应当代历史潮流,融入了现代社会文明价值观中追求自由、正义,冲破传统束缚的精神内涵,同时对社会主义以及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和政绩进行了积极宣传和正面肯定,通过轻松且通俗的形式达到强化观众爱国精神和民族团结共识的政治教育目的,提高民众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出一份力的认知,因此具有极强的教化功能。而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种教育功能,其实是在潜移默化,使人的解放和感性完善的追求成为一种自觉。
分析乾隆南巡期间排名前十的游览景观,杭州以西湖、孤山和云栖3处景观列在首位,苏州和镇江都以2处景观即寒山和灵岩山、金山和焦山并列第二,江宁、扬州和常州各以1处景观即栖霞山、大明寺、惠山位居第三。此外,苏州的虎丘是乾隆帝赋诗吟诵的重要景观,扬州的天宁寺和高旻寺、杭州的织造府行宫是乾隆帝题联赐匾的重要景观。
3. 审美功能
仪式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中始终存在的永恒文化现象和活动主题,贯穿于整个文明之中,正如上述针对民俗宗教信仰与地方戏曲呈现和发展的分析,湖南花鼓戏往往在演出时具有一定的仪式性,并配合一系列仪式活动达到某种审美目的。湖南花鼓戏在当地不但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而且极富当地民俗文化内涵,人民群众借助湖南花鼓戏所收获的不仅仅是一些历史知识,他们更借助该艺术形式形成了对各节庆活动和民俗信仰的文化解读和认知,由此来寄托自身对于家庭、社会和农事的祈愿以及心灵与精神上的依靠。
三、超越:地方戏曲的现实生活升华
(一)审美理想的实现
湖南花鼓戏作为地方民间戏曲,深受湘楚地方文化的影响和浸润。同时民俗本身由于具有一定的历史持续性,因而花鼓戏在审美意识、经济基础和语言发展中与“人”之间有了更为深层次的联系和互动。
湖南花鼓戏作为一种民间艺术,虽脱胎于民间的草台班子,但却因为丰富真实的生活选材、淳朴有趣的民间曲调以及贴近生活的表现形式,深受人们的喜爱,历经百年而愈加兴盛。从审美理想的角度而言,湖南花鼓戏正是因为力求在表现内容、主题传达以及价值导向上坚持遵从“还戏于民”的审美意识,方能使得地方文化同庙堂文化实现无缝契合,从而历久弥新,不断迸发出新的生命力。基于上述审美理想,群众在湖南花鼓戏的舞台中不但收获了民俗节庆活动所带来的情感喜悦和凝结的节日寓意,同时大大丰富了自身文娱生活,并进一步加深了同民俗节庆本身的凝聚力和精神联系。可以说,湖南花鼓戏真正做到了在发展自身之余,不仅能坚持自身审美理想,同时也为了其传承与壮大而求新求变,让地方戏曲艺术永远跟随时代的脚步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二)价值引领的实现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花鼓戏工作者受到时代的召唤,承担起“知识分子”的身份,主动意识形态化,不但改编了《刘海砍樵》《刘海戏金蟾》《打鸟》《芦林会》《阴阳扇》等传统剧目,祛除封建糟粕,使它们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还积极创作了《三里湾》《打铜锣》《补锅》《送货路上》《烘房飘香》《对象》等现代新戏,成为创作史上的一座高峰。
跨入到21世纪新时代后,抛开剧本的政治使命,经历史长河的检验,可以看到《打铜锣》《补锅》等花鼓戏历久弥新,作为湖南人民创作智慧的杰出代表,它们在戏改大潮中保持难能可贵的民间精神。这些优秀花鼓戏作品的乡土味体现在选材农村、主人公为农民和反映农民的思想愿望和审美志趣等多个方面,同时借以言老百姓之志趣,在现实生活中保持鲜明的美学色彩,保留独特的戏剧魅力,在新时代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三)未来发展的方向
花鼓戏的发展离不开创新,并且在故事内容、音乐作曲、表演范式上都需要作出大胆改革和创新,以下两个方向不可或缺。
其一是坚持地方戏曲的审美方向。花鼓戏是演给当今社会的人看的,这就意味着它必须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观念,只有与当今社会的文化融合,让新的文化渗透到里面,才不会在演出的时候与观众有隔阂。现在的中国,正处在走向富强文明的历史新时期,人们在和谐安定和政治经济文化极大繁荣的社会环境中奋斗,湖南花鼓戏的发展需要牢牢抓住固有的“俗”与“雅”,再从“新”与“合”上下功夫,结合现代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创新,争取让湖南花鼓戏也像黄梅戏、二人转一样,成为能被大多数电视观众所熟知与喜爱的民间艺术形式。
其二是坚持剧目内容的时代方向。对于戏曲现实题材创作而言,时代性和人民性决定着戏曲现实题材创作应该始终追随着时代发展的需要,用属于这个时代的思想和情感标准来尊重并引领观众的审美。[3]湖南花鼓戏剧本的创作需要关注当今社会具体环境下,不同生活环境的人群以及他们对生活的体会,关注时事热点,挖掘生活内涵,提升哲理品味,弘扬主旋律,内容力求故事性和艺术性结合,用现代意识刻画鲜明的人物性格,如此方能紧跟时代的步伐,在大众娱乐生活中占得一席之地。
[1] 本·海默尔. 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M]. 王志宏,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203.
[2] 谭真明. 湖南花鼓戏研究[D]. 曲阜: 曲阜师范大学, 2007.
[3] 王馗. 聚焦现实题材戏曲创作[N]. 中国文化报, 2018-08-08(02).
Hunan Flower-drum Opera in the Aesthetic Standards of Daily Life
LIU Ke, ZHOU Yong
( Art Literature College, Hunan City University, Yiyang, Hunan 413000, China )
The birth and growing-up of Hunan Flower-drum Opera and its progress is close link to the household daily life and the aesthetic customs. The birth of the Hunan Flower-drum opera shows the local people’s hope in their daily life. It is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the local people daily life. Its art form exists in the local custom and in the local festivals. It shows the contents in the style of aesthetic and also as the sole art form, as the sole art form Hunan Huagou (flower-drum) opera is sole art style that is showing the sole beauty in the colorful life in the local people in Hunan.
local opera; Hunan Flower-drum opera; aesthetic experience; daily life
(责任编校:贺常颖)
2018-11-2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BB015)
刘科(1978-),女,湖南邵阳人,副教授,主要从事音乐理论研究;周勇(1966-),男,湖南益阳人,教授,主要从事高等音乐教育与地方戏曲研究
J 802.1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9.05.015
2096-059X(2019)05–008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