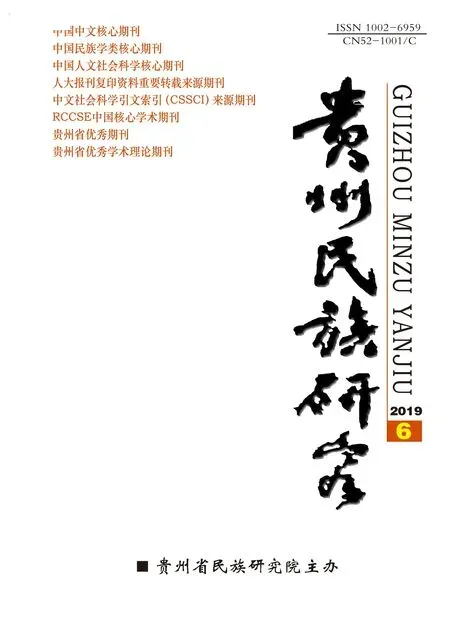“音乐”与“功能”视域下的民族音乐探析
刘清明
(长春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吉林·长春 130032)
民族音乐相对于汉族音乐体系,是少数民族群众在社会生活和生产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形成的同音乐关联的艺术体系。民族音乐基本上同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音乐发展并驾齐驱,但同中原汉族音乐注重音乐旋律与奢靡所不同的是,民族音乐早期基本上以“乐中非乐”与“仪中生乐”的特色发展。“仪中生乐”是民族音乐发展中不可忽略的界令,换句话说:民族音乐的艺术性发展基本上以民族传统仪式为依托,或镶嵌于个体生命的始末,以婚丧嫁娶中民族音乐的蕴意为主。比如:土家族群众的《哭嫁女》和《跳丧舞》分别从土家族群众喜闻乐见的婚葬仪式中分化而成。或依托于宗教仪式逐渐演变为以宗教为题材的宗教音乐,比如:西域匈奴等少数民族宗教音乐《于阗乐》等。总之,基于“音乐”与“功能”视域下的民族音乐探析就是要抛开现代音乐学流派中以音乐元素为标准的音乐学发展研究,探究“音乐”与“功能”双重属性下民族音乐的别样发展。
一、“音乐”与“功能”视域下的民族音乐发展
(一)基于“乐”的民族音乐囊括
“乐”是世界音乐所遵循的唯一标杆和价值尺度,是音乐最为本源的存在。少数民族音乐之所以同汉族宫廷音乐的历史追溯一脉相承,关键在于民族传统音乐的最终归宿以“乐”的艺术表达和审美形式为主,或喜中生乐、情感万千,比如:在蒙古族婚嫁音乐中《鲤鱼猋滩》等曲调平缓,喜乐欢快,而《哭嫁女》却阴阳顿挫、曲调低沉。或悲中生乐,比如:哈尼族等少数民族群众在丧葬仪式中反而以欢快愉悦的《跳丧舞》折射晚辈对逝者的孝道之心。纵观少数民族音乐,基于“乐”的民族音乐主要包括:民族歌乐、说唱音乐等声乐和种类万千的民族舞蹈音乐及器乐。基于音乐属性的民族音乐是许多现代音乐创作的源泉。
民族歌乐是民族音乐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骨架,以战国时期南越号子为主的泛音乐存在不断活跃于山野乡间,同中原宫廷乐的奢靡享乐对比鲜明,而后两汉时期少数民族逐渐汉化,民族歌乐自下而上的发展被民族群体的上层社会所接纳。民族音乐中民歌的多元化表现是繁荣民族音乐的核心,民族群体中上层群体对愉悦身心曲调的接纳,扩大了民族音乐的艺术性。比如:《龟兹乐》中对匈奴奴隶主贵族音乐以旋律和伴奏的形式包裹,这是民族歌乐最为显著的特征。
少数民族说唱音乐是少数民族群众在社会生产中不断沿袭而成的音乐符号,比如:积石山东乡族“花儿”早期基本上说唱结合,而蒙古族群众的《格斯尔传》是游牧民族典型说唱音乐之一。舞蹈音乐也是民族音乐范畴的重要存在,民族舞蹈音乐以其独特表演形式逐渐被类化,特别是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受音乐文化的影响,舞蹈音乐本身以习俗祭祀舞蹈和娱乐性舞蹈为主分类,比如:基洛族舞蹈音乐通常分为习俗祭祀舞蹈和娱乐性舞蹈,前者以祭祖舞、大鼓舞等为主,后者主要以儿童舞蹈“佐交交麦”为主[1]。
民族乐器是民族音乐的精髓,民族乐器在民族音乐发展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特别是民族乐器的工具化衍生,使得民族乐器从发端之际具有双重属性,而音乐属性的后天性使得民族乐器的工具性不断延续至今。比如:基洛族民间乐器“塞土”本是祭祀用具,在音乐艺术的发展中逐渐演变为鼓。当代民族器乐的创作作品也常常表现出对于民族音乐的吸纳与传承,常表现以传统民族器乐存在形式为材料,加以现代作曲技术的丰润,形成富于民族特色的当代创作。比如:朱广庆创作的编鼓与乐队合奏作品《跑火池》,是以满族祭祀仪式“跑火池”作为音乐与文化的双重素材创作而成,成为民族音乐多元化现代性艺术表达的代表作之一[2]。
(二)典型民族音乐形态的历史追溯
典型民族音乐形态的历史追溯是探析少数民族群众传统音乐类型,还原少数民族音乐原生态、洞悉民族音乐潜在人文精神的关键。我国民族音乐的历史追溯务必要与中原音乐相对立,兼顾民族群众社会人文元素的诸多领域。我国少数民族音乐“乐”的双重属性广泛波及和大众接纳是少数民族音乐发展的转折点。纵观我国民族音乐基本以三个阶段的类型为主。一是少数民族兴起“乐中非乐”类音乐的发展[3]。一方面民族音乐在形成发展中并非以音乐的属性延续,而是通过音乐艺术表达特定的民族文化或者传统习俗。比如:哈尼族《跳丧舞》在沉痛欲绝的氛围中揭示着民族群众攀比文化和孝道文化。另一方面在音乐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民族音乐的发展不是以娱乐身心为重心,而是无形中逐渐被艺术化。比如:藏族《砌墙歌》、蒙古族《挤奶歌》等民族音乐都是在音乐发展中逐渐被规范化的艺术体现。二是民族音乐在发展中受宗教习俗等传统文化的影响,传统习俗对表演形式的需求,促进了彼此之间的共同发展,即“仪中生乐”。比如:白族群众流传至今的庙会祭祀音乐《叠断桥》是民族仪式音乐中的典范,在早期基本上作为祭祀神灵的重要环节并不是音乐艺术,而后在庙会祭祀活动中逐渐转化成为白族群众家喻户晓的民族乐曲。三是民族音乐艺术的扩张性阶段,此时民族音乐的本源性逐渐被妇孺皆知,音乐的主题和思想逐渐鲜明。比如:白族群众“山花体”歌曲旋律的重叠基本同现代音乐格局一致。另外,民族音乐的时代性主题也逐渐鲜明。此外,同一民族音乐形态的历史追溯也是映射民族音乐发展轨迹的重要依托。比如:水族群众能歌善舞是民族秉性外,其音乐发展轨迹也印证着民族音乐的发展历史。在氏族社会时期水族群众敬畏自然,以追溯人类起源为主的“旭济”成为其传统音乐的雏形[4]。在奴隶社会时期水族群众除创造了特色鲜明的民族乐器外,还创造了生产歌、情歌等民族乐曲。新中国成立以后水族歌曲中出现了产生了反映向往美好生活、感谢党的新民歌。
(三)民族融合中民族音乐元素的移植
民族音乐元素的移植与嫁接是推动民族音乐艺术发展的催化剂,民族音乐在发展中也得益于其他民族音乐元素的补充。比如:西凉音乐发展中既吸收了匈奴音乐中的粗犷又纳入了吐蕃人宗教音乐曲调反复、节拍平缓的艺术特色,在民族器乐方面,西凉音乐综合了西域游牧民族乐器的整体特色,逐渐形成了以打击乐为主的伴奏形式。民族融合为民族音乐元素的移植提供了必要的环境基础和保障。首先,民族融合中民族音乐“音乐”同“功能”混同与分离的趋势加强[5]。少数民族群众在融合过程中音乐文化的交流成为必然,一方面在民族融合交流中音乐的共同属性逐渐被跨民族认同并接纳,民族音乐在融合中突破了自我,民族音乐的共性成为彼此音乐发展秉持的必然趋势。比如:景颇族的民间曲调《西塞》同德昂族等西南少数民族的“隔山调”如出一辙,都表示亲热之意。另一方面民族音乐在民族融合中功能性逐渐突出,民族音乐的类化也逐渐完善。其次,民族融合中民族音乐娱乐性逐渐鲜明[6]。一是少数民族音乐逐渐流入宫廷,赋予了民族音乐更多的娱乐性,比如《南诏奉圣曲》唐代被列入宫廷乐,极大地提高了白族“吹腔”大本曲的娱乐性。二是民族融合中民族音乐自下而上的音乐属性构建。换言之,民间音乐在民族群体上流社会的接纳直接推动了民族音乐本源的发展。再者,民族融合中民族音乐元素的移植促进了民族音乐地域性风格的形成。游牧民族高音粗犷的音乐表现形式同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群众的婉约、平缓乐曲形成了鲜明对比[7]。此外,民族融合中民族音乐类化趋势日益突出,在民族融合中民族音乐的功能性逐渐自然地吻合,比如:婚嫁音乐、祭祀音乐等在各少数民族当中普遍流行。
(四)民族音乐发展的历史重心转移
民族音乐发展的历史重心转移是认知民族音乐不可忽略的主题[8]。民族音乐艺术非娱乐性的群体性构建以同中原音乐截然相反的轨迹演绎着民族音乐的魅力,究其轨迹,第一阶段是从音到乐的转移。民族音乐从乐曲、舞蹈到器乐,基本上是由音到乐的转移。一方面民族音乐在发展中源自于大自然的模仿和劳动行为的转化,比如:藏族舞蹈音乐《砌墙歌》本身对劳动行为的模仿,而后成为风靡一时的舞蹈音乐。另一方面民族音乐在发展中注重音的音乐性演绎,比如:普米族群众依托推磨的声音,根据特有呀哈巴拉的曲调将推磨声转化为《推磨歌》,从而增强了民族音乐的娱乐性。第二阶段是民族音乐从“仪中生乐”到仪式音乐的转移[9]。“仪中生乐”是“音乐”与“功能”混同状态下民族音乐表达的主要形式之一,民族音乐在传统仪式中逐渐分离,审美价值逐渐树立,形成民族音乐属性的重要趋势之一。“仪式音乐”是民族音乐功能性逐渐凸显的结果,同时也是民族音乐逐渐形成独具特色音乐文化和倾注人文精神的重要阶段。比如:佤族音乐起初都是从祭祀自然万物中的民歌中散落而成,而后在宗教祭祀中也逐渐采纳舞蹈音乐,从而为佤族信仰万物有灵的文化习俗注入了艺术点缀。第三阶段是仪式音乐向大众音乐转移。仪式音乐释放了民族音乐的娱乐属性,仪式音乐的特定性突破成为民族音乐发展的主体,因此,以民族劳动音乐、情歌、婚嫁音乐为主要形态的大众音乐逐渐传播[10]。比如:水族群众类似念唱形式的生活调歌,将民族音乐推向了大众化、生活化。第四阶段是规范化主导下民族音乐重塑的阶段。一是对民族音乐曲调、旋律的规范化整合。二是对民族音乐时代性主题的塑造,使民族音乐逐渐摆脱随意性的即兴表演而成为蕴涵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的艺术表达形式。
二、民族音乐的音乐性与社会性探析
(一)“音乐”主导下民族音乐的多元化发展
民族音乐的音乐性是音乐本源和自身属性的概括。换言之,音乐性是音乐特有的属性,无外乎节奏、旋律、声乐同器乐的结构性调整等[11]。首先,基于“音乐”与“功能”视域下的音乐性探析无可厚非,一方面民族音乐的音乐性基本上同民族文化密切关联,比如:畲族“果”(山歌)在表演中基本上毫无章法可寻,但一般依据歌词起字的读音来确定各段曲调的起音,而后在多元民族音乐交汇中逐渐形成了同一调式调性,在五声音阶宫调式内做旋律的变化。另一方面民族音乐的音乐性通过歌词押韵和语句重叠来折射。比如:畲族条歌中“谜语歌”八度音的转换外主要通过词曲彰显音乐的旋律。其次,“音乐”主导下民族音乐的多元化发展也是民族音乐音乐性呈现的基本趋势,一方面民族音乐在旋律、节奏演变中逐渐突破民族性和地域性,以大众接受程度高的形态不断发展。比如:“杂尼斯闹开”作为阿昌族山歌在历史演变中逐渐成为旋律鲜明、节奏欢快的民族乐曲之一[12]。再者,民族音乐规范化过程中的艺术性扩张是民族音乐在社会发展中审美价值不断提升的过程。最后,“音乐”属性下民族音乐的时代性认知是民族音乐音乐性向社会性延伸的关键,也是民族音乐人文元素的折射。比如:赫哲族群众受萨满教的影响,在歌曲衬词“啊郎”开头中阐述着赫哲族群众是非善恶鲜明的价值取向[13]。此外,民族音乐发展中通过民歌民调等独特的形式,反映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生活的题材也举不胜举。
(二)“功能”主导下的民族音乐社会性透析
“功能”主导下的民族音乐社会性透析是民族音乐发展不可规避的主题,换言之,“仪中生乐”的音乐特色是民族音乐社会性彰显的关键[14]。一是民族音乐艺术的功能性凝聚与分离,民族音乐在发展中辅助于传统民族仪式,在音乐发展中逐渐被独立,比如:哈尼族《跳丧舞》本是丧葬习俗的必要环节,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演变成为独具特色的民族音乐,音乐同丧葬文化逐渐分离。二是民族音乐艺术“音乐”功能的分化,在民族融合中民族音乐的汉化造成民族原生态音乐形式的流失,民族音乐表达形式和艺术手法逐渐向世界主流音乐靠拢,比如:赫哲族群众《乌苏里船歌》以流行音乐的符号彰显着民族音乐的魅力。三是功能主导下民族音乐艺术的类化,“仪中生乐”的民族音乐特色使得民族音乐在兴起之际就彰显着民族音乐的功能性,比如:祭祀音乐、婚葬音乐、表演音乐、宗教音乐、劳动音乐、情歌、谜语歌、现代音乐等,在民族群众的生活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以特有的功能性折射着民族音乐的社会性。
民族音乐与生俱来的非娱乐性和大众性使得民族音乐在发展中往往以自下而上的“音乐革命”为民族音乐井喷式发展的导火索,不断推动着民族音乐的规范化、多元化发展[15]。就民族音乐的整体而言:“音乐”是所有音乐艺术存在的基本属性,旋律、节奏、音色等要素是音乐的生命所在。“功能”是民族音乐对音乐发展的延伸,是民族音乐经久不衰的源泉。“音乐”与“功能”视域下民族音乐的探析,是以民族音乐的社会功能为出发点,审视民族音乐的艺术表达,在掀开民族音乐原生态面纱的同时感悟功能主导下民族音乐魅力与人文精神的艺术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