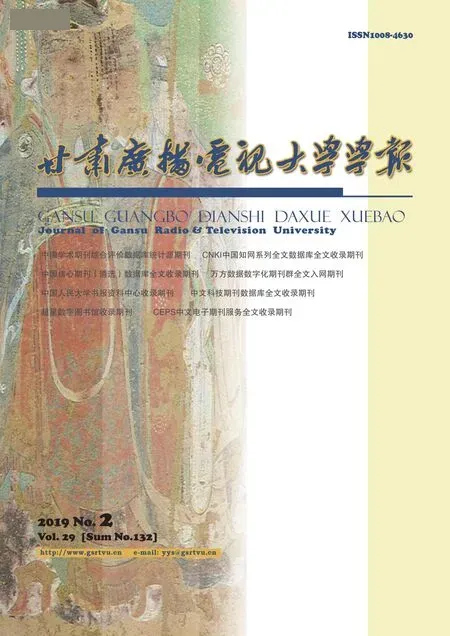先锋性的自我颠覆与超越
——对余华转型之作《活着》的再解读
王 茜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余华在一次答记者问时曾说道:“我认为我现在还是先锋作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还是走在中国文学的最前面,这个最前面是指,我们这些作家始终能够发现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需要前进的方向又在什么地方,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先锋派作家。事实上,现代也好,先锋也好,都是传统的一部分,并不是和传统对立的。”[1]
《活着》自1993年首版以来,这部带有温情和悲悯的作品被视为余华由先锋向现实主义转型的标志。对《活着》的研究也多从论证其转型以及探究“活着”哲学两方面展开,很少有学者挖掘《活着》文本中先锋性的一面,也有学者对其后悲剧特质、现代主义、极简主义、戏剧诗学等特点进行研究论述,但数量极少。
时至今日,对先锋的定义已不仅仅停留于20世纪80年代的“形式实验”,先锋作为一种观念和态度,已成为每一个有所抱负的作家始终的坚守。在余华的创作中,他不停地寻求自我突破,思考着 “小说从何处来,该往何处去”,于是在被学界认为是转型之作的小说《活着》中,余华用自己前卫的眼光,老辣的笔触,写下了十分具有五四启蒙气质的故事。《活着》中所具有的平民性及其出版后无论是在读者还是学术界中所引起的持久不衰的关注,都体现了启蒙文学重视人、启蒙人、主客统一、平民性等特点。而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以五四文学为起点的文学对人的探索一度被割裂,余华对五四精神的重拾,是他作为一个作家对“人的文学”的反思与回归。但这种回归不是单纯的“返回”,而是尝试提出一种全新的生命哲学研究。这种“野心”与他在小说中的摸索正体现着余华这位“老先锋”由繁入简式的自我革新,以及在这种革新中对自我先锋性的颠覆和超越。研究试从《活着》对人个体主体性的关注、双层叙事语言、双重叙事视角、“重复”的隐喻和开放性主旨几方面来探讨余华的写作策略,试论余华怎样在不动声色中以一个极为普通的故事演化出了“伟大”。
一、《活着》中对人个体主体性的关注
“主体性是指人在一切对象性关系中作为主体所具有的地位、作用和特性的概括。”[2]而主体性观念作为近代历史和近代哲学发展的产物,是寻求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启蒙运动的精神核心。
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处于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个体开发自身理性能力,以期建立个体主体性的过程”,但由于“这场文化革命通过反对家庭、家族、地方来追寻人类中‘真我’却没有摆脱新的‘国家主义’权威的束缚”,“新文化运动解放个体的任务远没有完成”[3]。20世纪末,余华的小说《活着》以自己冷静的叙述纳入到这场未完成的对个体主体性的探讨之中。
小说中,福贵在进城给母亲抓药时被国民党抓了壮丁, 有一段身处战火的经历。在进行战争描写时,余华用细腻的笔触呈现出一个极尽荒诞与恐怖的战场。当部队被包围时,“连长都不知道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只是躲在坑道里赌钱;国军开始空投大米,为了烧火煮饭,人们迅速地去伐木甚至拆房子,“才半天工夫,眼睛望得到的房屋树木全没了”;子弹却没有人用,铺得到处都是,“咯得身子疼”,大炮也一弹未发便被流弹打成了废铁。“天越来越冷,晚上几分钟就冻醒一次”;在坑道里的人常常被炮弹炸得弹起来,“国军每天都在拼命死人”,伤号越来越多;“起先是一堆一堆,没多久就连成一片,在那里疼得嗷嗷叫”;抬伤员的人只是喊“一二三”,担架一翻就把重病的伤员倒在地上。在这种“拼命”死人的特定战争场景里,每一个个体如同蝼蚁一般渺小,失去掌控自我生命和生活的权利。这种目睹了人的群体性死亡的体验对个体心灵所造成的震裂性伤害是无法缝合的,福贵没有杀人,如若他也拿起炮火来,戕害到同类的性命,他的心灵将蒙受永远的不可逆的阴影。
夜晚的大雪为战争填上了白茫茫的死亡的颜色,躺在坑道外的几千个没死的伤员呜呜地叫着,“像是在哭,又像是在笑”,福贵“这辈子再没听过这么怕人的声音”,“一大片一大片像潮水一样从我们身上涌过去,只是觉得身体又冷又湿,手上软绵绵一片,慢慢地化了”。天亮时,什么声音也没有了,一夜之间几千伤员在哀曲一般如同鬼魂的声音里全死了,“一动不动,上面盖了一层薄薄的雪花”,他们的衣服被还活着的人扒下来御寒,只有这薄薄的一层雪花成为他们永眠的丧衣。在俄罗斯的经典战争小说《红笑》中,战争对个人的戕害被抽象成“红笑”的意象,而《活着》中下着大雪的夜晚鬼魂般的呜咽声同样也让人感受到一种“白笑”的恐怖、诡异和悲哀。
这种种荒诞的场景,细节性的惊心动魄,完全是一种个人化的战争体验,是个体在被抛出到集体性灾难时的某种特定记忆。余华在这里从纯粹的个体出发,展现了战争中人的主体性被践踏、被摧残的血腥过程,彻底消解了战争在以往文学作品中的宏大叙事。尽管关注战争中个人遭遇的小说在世界文学中并不少见,但在我国现当代的文学史中,正如陈思和所说,“个体的悲剧性遭遇总是能够溶化到历史的喜剧性结论中去”,摆脱“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而关注战争所带来的“人的命运、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命意识的哲学思考”[4]仍然是比较新鲜的视角。
在这场极端饥饿与死亡的战争体验中,福贵是一个完全的小人物;在《活着》所讲述的从土改到人民公社到文革到新时期的整个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福贵亦是一个地道的小人物。余华不去写圣人,而选择了用农民的形象来表现“人如何可以解脱”的命题。在《活着》中,一个朴实无华的小人物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活着”的智慧。正如佛教讲“人人都是佛”,余华的《活着》也有一个“佛眼”。福贵由“阔少爷”变成了“贫农”,小说对“贫穷”的面目模糊却又无处不在的呈现使福贵的精神受难更为纯粹,剥离了物质对人的奴化。而村长对小米的寻味而来,分地瓜的丑剧,都因为极度的贫困反而显出一种天真,于是“道德审判”的不在场自然而然地发生。余华无意去审判道德,更无意审判历史,他写下了善恶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即人与命运的和解。
二、《活着》的双层叙事语言和双重叙事视角
在对“人”的精神世界解放探索的向度上,余华的《活着》体现出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的启蒙精神。五四以来,对“人”究竟是谁,“人”应该怎样活着,知识分子已做过太多的讨论。然而,从娜拉的出走,到围城的困境,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战火的烽烟使人们放下了对个人的思考,转而关注国家存在;新中国的成立后对集体主义的拥护也使得人们无暇思考个人命运。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精神渐渐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迷。《活着》是对个人该往何处去的一种回答,也是对人应当如何与生活、与命运、与宇宙和解的回答。
福贵生活的时代跨度非常之大,经历了新中国建国前后的历件大事。他的人生轨迹在时代的动荡中被改写着,可余华在叙事语言上的双层情感向度却使这些时代背景虚化成了模糊的幕景,使福贵的苦难和精神向度在这幕景之前愈发清晰起来。
福贵生活在一个个人命运与政治息息相关的时代。福贵的儿子有庆去世时才七岁,他所在学校的校长是“县长的女人”,生孩子时大出血。有庆跑得快,立功心切,血型又匹配,兴高采烈地给校长输血,却因血被抽干而死在了医院里。到大炼钢铁时,贫穷的福贵把自家的锅砸掉,有庆的羊被宰了。后来食堂不再提供伙食了,又要自己做饭吃。“当初砸锅是队长一句话,买锅了也是凭队长一句话。” 城里闹大革命,春生被打,在地上被拖着“像一块死肉”。尽管如此,晚年福贵讲述自己的一生时,叙述时代记忆的语调却是波澜不惊的,不见太多热情,也不见埋怨;当他叙述自己,叙述亲人的时候,却饱含着相依为命的温情和遭受离别的痛苦之情。两种不同的态度使得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被虚化,于是在这种实情和叙述的鲜明色差中,福贵的人生哲学和个人魅力清晰地被推到读者面前,一种动人心魄的“和解”的力量得以产生。
这种“和解”力量的体现,同样有赖于小说的双重叙事视角。《活着》这个故事是由牵着老牛耕田的福贵在黄昏的乡间田地里讲给一位采集民谣的年轻人的。在福贵的叙事视角中,我们可以看到家珍的温柔贤惠任劳任怨,凤霞的天真纯洁、勤劳可爱,有庆的活泼、勇敢、友爱、善良。可是,我们很难看到福贵的性格,福贵的模样。福贵这个打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形象的魅力是通过小说的另一个叙事视角——民谣采集人流露出的。在民谣采集人的叙事视角中,我们才得以看到晚年福贵的幽默、豁达、充满智慧,才得以看到福贵的讲述本身所呈现出的力与美。
民谣采集者的叙事视角在《活着》中一共出现了六次。这位年轻人遇到福贵时,福贵正在开导老牛:“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人织布,哪头牛不耕田?这可是自古就有的道理,走呀,走呀。”而疲倦的老牛竟也“知错般地抬起了头,拉着犁往前走去”。不一会儿,老牛放慢了脚步,福贵又吆喝道:“二喜、有庆不要偷懒,家珍、凤霞耕得好,苦根也行啊。”他向年轻人解释道,老牛听到有别的牛也在耕田,就不会不高兴,就耕得起劲了。福贵或许也和老牛一样,他劝导老牛的话就像劝导自己,他知道只要他还在这世上活着,死去的亲人的生命就还在这世间留有温度。想到他们,他也就活得不那么孤单,也就活得起劲起来。
在那个满是阳光的午后,福贵向年轻人讲了自己的故事,年轻人想:“我再也没遇到一个像福贵这样令我难忘的人了,对自己的经历如此清楚,又能如此精彩地讲述自己。”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年轻时远近闻名的阔少爷福贵还没有消失,他仍是自信的,谈吐风生的,这一生的贫穷和死亡都没能打倒他。
第三次,福贵跟年轻人开玩笑说:“我全身都是越来越硬,只有一个地方越来越软。”第四次,福贵对旁边田地里吵起架来的年轻人说: “做人不能忘记四条,话不要说错,床不要睡错,门槛不要踏错,口袋不要摸错。”这种“自黑”式的幽默和随口对年轻人的叮嘱都让我们看到一种历经沧桑后的从容和豁达。在走到生命的末段时,时间和命运的际遇已然使那个当年吃喝嫖赌的纨绔子弟变成了充满智慧的老者,而他所有经历的悲惨和温情也就在这里沉淀出生命的力与美感。
“每个时空发生联系的时候都会产生意义”。在福贵的回忆时空与晚年现实时空的交错之中,双重的叙事视角调和出一种“复调”的音乐感。这种节奏感和余华清澈舒缓的语言交叠相生,小说本身好像也似那个充满阳光的午后,波光粼粼。福贵这位经历了太多灾难的老人,牵着老牛,耕着几亩薄田,不时唱起民谣——“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桀骜不羁的少年和满是沉痛的中年在这个午后被忆起,而主人公已然是在生命的尾端。于是这个充满死亡却温情如水的故事在可视范围中最终成为一个闭合的圆形,它仿若在阳光中飘动轻摇的纱缦,若隐若现的是人类永恒的封闭感和宿命感。
三、重复的宿命性隐喻及开放的主旨
福贵看似普通,但他是一个连接宗法、现代革命以及未来的人物。他是地主出身,本身代表了一种封建宗法的血缘,这种出身虽然在情节的演进中被龙二所置换,但其根本性的隐喻却始终存在。当福贵把家产输给龙二时,福贵的老父亲对他说:“从前,我们徐家的老祖宗不过是养了一只小鸡,鸡养大了变成了鹅,鹅养大了变成了羊,再把羊养大,羊就变成了牛。我们徐家就是这样发起来的到了我手里,徐家的牛变成了羊,羊变成了鹅。传到你这里,鹅变成了鸡,现在连鸡也没啦。”慢慢的,福贵有过两只羊,给了公社,后来又有了一只羊,饥荒时卖给了宰羊的换了袋小米。福贵晚年时,二喜也死了,苦根便跟着福贵过日子。福贵在家里养了两只母鸡,他对苦根说:“这两只鸡养大了养成鹅,鹅养大了变成羊,羊养大了变成牛,我们啊,也就越来越有钱啦。”后来,苦根死了,福贵买了一头和自己一样老的老牛。苦根的死切断了福贵家的传承,于是从鸡到牛,从牛到鸡,再从鸡到牛的链条并不是无限展开的,而成为一种封闭的循环。这种封闭和年迈的牵着老牛的福贵互相映照,呈现出一种轮回性质的宿命隐喻。
在小说中有许多“重复”。有庆和凤霞都因生产而死,新生命的降临置换了旧生命,也可以说是脆弱的力量置换掉了强壮的力量。春生曾经和福贵在战场上相依为命,代表的是“生”的向往,此刻却又间接造成了有庆的死亡,成为“死”的符号。
有庆出事时,福贵跑到医院,看到有庆“一个人躺在一间小屋子里,那张床是用砖头搭成的”。凤霞去世时也是在那间小屋子里,福贵去看她时“一见到那间屋子就走不进去了”,他跟二喜说:“我们回家吧,这家医院和我们前世有仇,有庆死在这里,凤霞也死在这里。”到苦根四岁时,二喜也死了,是被两排水泥板夹死的,又停在了那个医院的那间停尸房。“去领二喜时,我一见那屋子,就摔到在地上。” 二喜、凤霞、有庆都死于同一间医院的同一间小屋,都是非自然死亡,“小屋子”的冰冷成为了福贵生命里的一个梦魇之地,正如同余华儿时父亲医院里的停尸间。这种生命中特别却又黑暗的记忆不是作为个体的人去主动选择的,却成为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恐惧体验。由记忆叠加而造成的“重复”使得生命在时间的线性展开中不定时被抛回到某一个原点,进入某种闭合的宿命性圈套,而这个具有“生”与“死”的意味的原点也正是“人”的“原点”,即偶在。其中所裹挟着的压迫感和复杂的命运隐喻即是福贵所承受的命运的重量。
到故事的最后,福贵买了一头老牛,给它取名“福贵”,他们同样的年迈,并分享着同样的名字。《活着》对福贵和老牛的相处着墨甚多,福贵常常对老牛是体谅的,“牛老了也和人老了一样,饿了还得歇一下,才吃得下去东西”,这种“推己及人”的理解是一种对宇宙规律的内在体悟,背后隐含着福贵对自己遭遇的理解,这位普通的老人也由此具有了“天人合一”的精神气质。正是这种“一”,成为了余华解锁轮回性宿命的钥匙所在,成为余华给出的最终和解,人性的“宽广”与“高尚”,以及人的尊严。于是时代和命运一虚一实的呈现、悲剧和豁达合奏而成的人与宿命的和解、源于宗法土地而向着中国传统精神的旨归,都使得《活着》具有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阐释空间。
余华将生活从事无巨细的琐碎里抽离出来,让生活只是沿着一条由重大事件构成的直线前行。他冷静克制的书写淡化了个人的七情六欲。在这部长篇中,每一个小人物都已经不是现实中的普通人,他们不必承受生活的琐碎与无聊,不必负担人性的自私与邪恶,在不停地承受过生与死的戕害后,仍是像最初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样单纯地生活着。他们的灵魂是不受难的,于是余华展示出的是人的一种可能性。而这种“宽广与高尚”究竟应该如何在生活的千锤百炼中抵达,这种可能性的道路何在,余华在《活着》中没有给出回答。尽管如此,“活着”这粒启蒙主义的种子,却一如余华不动声色的书写,已经悄然埋在了每一个读者的心中。在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际遇中,它将发芽,它将生长。“除掉杂草最好的方式就是种上庄稼”,《活着》对人们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活着》看似书写现实,却充满了浪漫的精神,而其具有人类学内涵的启蒙气质也正体现了余华对“先锋性”的不懈追求与重新理解。与其说《活着》放弃了“先锋”而转型现实,倒不如说是余华对“先锋”概念的再理解和自我诠释。余华这位“老先锋”及其《活着》也应纳入当下“重述先锋”的语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