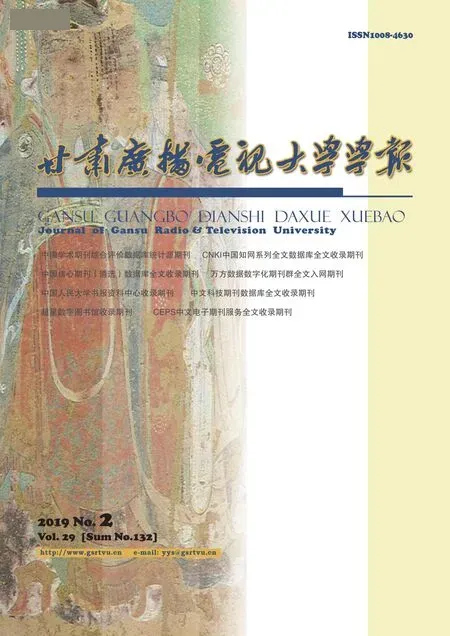论阿来长篇小说《格萨尔王》的英雄叙事形态
何城禁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藏族口头史诗《格萨尔王传》是青藏高原上藏族历史记忆的当代遗存,是关于民族神话英雄格萨尔斩妖除魔、安定四方,实现民族统一的英雄叙事。《格萨尔王传》先后于2006年和2009年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藏族文学中影响深远的民间文学代表作。藏族作家阿来立足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对史诗《格萨尔》的宏大叙事加以重述,实现了对口头史诗书面化的一大创举。他采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在对格萨尔英雄故事进行复写的同时,也利用格萨尔民间说唱艺人的认知视角对英雄史诗加以现实主义的寻根性考察,在诗性与理性的并置中重新塑造格萨尔这一民族神话英雄形象,并在民族英雄叙事背后寄予了民族的隐忧。
一、角色功能的线性复颂
阿来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延续了史诗的基本故事形态。他将整个叙事分为神子降生、赛马称王、雄狮归天三个部分。阿来采用小说文体,以复颂的形式将远古牧业文明时期的英雄人物格萨尔呈现出来,将藏族人民耳熟能详的格萨尔口传神话史诗加以具象化的表达。
普罗普认为功能指的是从行动过程意义角度定义的角色行为。角色功能充当了故事中稳定不变的因素,构成故事中的基本组成成分[1]22。阿来在小说的第一部“神子降生”中引入初始情境:青藏高原上家马与野马刚刚分开,藏族人民进入后蒙昧时代,岭噶人、神、魔大战的序幕即将拉开。岭噶百姓饱受苦难,佛教高僧寂护大师和莲花生大师先后来到这片草原,又都无奈地离去。初始情境后小说引入主人公格萨尔,神子崔巴噶瓦不忍人间众生的悲苦,发愿降生岭噶降妖除魔。神子发愿便是格萨尔的第一个角色功能。神子选中岭噶穆氏家族幼系出身的森伦为生父,出身龙族的梅朵娜泽为生母,下界岭噶成为幼年时期的格萨尔——觉如。神子下界便是格萨尔的第二个角色功能。觉如以其不平凡的出生,五岁的年纪就已经有了二十岁的身量和非凡的神通。他遭到叔叔晁通的敌对,还被处于智识蒙昧阶段的岭人的放逐。年幼被放逐便是格萨尔的第三个角色功能。觉如母子被逐,岭噶遭遇雪灾,岭噶百姓复又投奔觉如开辟的新领地,觉如带领岭噶百姓走出困境。解除岭噶百姓的雪灾困境是格萨尔的第四个角色功能。
小说的第二部为“赛马称王”,讲述格萨尔十二岁称王岭噶,消除四大魔王的故事。天母朗曼达姆在梦中告知格萨尔尽快称王完成使命,格萨尔幻化为对头晁通崇拜的神灵马头明王,诱其发动赛马大会,并以王位、美女、财宝为彩注。珠牡姑娘迎回格萨尔参加比赛,格萨尔不负众望赢得王位,实现了赛马称王。阿来用大量笔墨叙述赛马称王这一角色功能,这也成为神性主人公下界后的一大转折点,同时格萨尔也迎娶了珠牡等十二王妃。随着王妃梅萨被北方魔王鲁赞掳走,格萨尔开始了降妖除魔的伟大业绩。他先后剪除岭国周围的魔国魔王鲁赞、东北霍尔国白帐王、南方姜国萨丹王、西南门域国辛赤王,实现了封疆扩土,也给百姓带来了更多的安宁。战胜四大魔王成为格萨尔的第六项角色功能。
小说第三部为“雄狮归天”。赛马称王后的格萨尔一方面剪除了威胁岭国的妖魔,另一方面他也发现妖魔难以除尽。他在使命的指引下又消灭了罗刹转世的卡契国国王赤丹、木雅国法王玉泽顿巴、作恶多端的叔叔晁通,又前往伽国收复了妖后,并在地狱解救和超度了王妃阿达娜姆以及代己受过的生母梅朵娜泽。格萨尔一生南征北战,降妖除魔,平定一方,扩大疆土,在他下界八十一年时,他感到“自己在人间的功业已经完成,该是自己回归天界的时候了”[2]351。雄狮大王格萨尔返回天界,将岭国交到侄儿扎拉手里,晁通之子东赞辅佐朝政。
小说《格萨尔王》的叙事形态遵从了史诗故事对主人公英雄格萨尔的线性复颂,是对史诗主体情节的重述,是将作为口头史诗巨著《格萨尔》的文本化。著名《格萨尔》史诗研究学者诺布旺丹认为回忆或记忆的延续是在历时和共时、时间和空间方面得以实现的[3],阿来作为小说文本的叙述者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史诗魔幻现实主义的叙述,将史诗格萨尔故事进行小说文体的重述。小说《格萨尔王》在“故事”层面的结构形态并未违背格萨尔作为史诗英雄的叙事结构,这也体现出对格萨尔这一英雄角色功能的整体文化认同。
二、第二声部行动圈的空间补写
小说《格萨尔王》采用了双声部的叙述,将作为“故事”的格萨尔英雄史诗加以复颂,并将作为“说唱人”晋美的行动圈纳入小说叙事的另一核心功能圈。现代视域下的格萨尔说唱艺人分为掘藏、神授、圆光、顿悟、智态化、闻知和吟诵艺人等类型,至今仍有160多位不同类型的民间说唱艺人活跃在青藏高原上[4]。神授艺人认为自己头脑里的关于格萨尔的东西不是自己学来的,不是听别人说的,而是神把格萨尔的故事降到他的梦里,注入头脑心腹,然后他就开始说唱了[5]。作为小说另一声部的主要功能角色晋美,他属于英雄史诗说唱神授艺人。
行动圈是指从逻辑上按照一定的范围联结起来的功能项,并在整体上与核心功能相对应的范围[1]61。例如英雄主人公格萨尔的行动圈包括神子下界、赛马称王、拯救王妃梅萨、降伏妖魔、迎娶魔国公主阿达娜姆、地狱救妻、地狱救母、雄狮归天等,这些行动圈与英雄人物格萨尔准确对应。而阿来设计的又一主人公“说唱人”晋美的行动圈是与英雄主人公互为补充的,一古一今,一虚一实,分别在时空维度上实现了对格萨尔故事的“故事新编”。格萨尔故事历来被作为活形态的民间口传文学,不断被注入新的时代声音和叙述话语。
牧羊人晋美在梦中得到演唱格萨尔故事的神力,又在梦中和英雄格萨尔展开对话。梦作为叙事的一大空间,让双线叙事中的格萨尔和神授艺人晋美有了对话的空间媒介。梦开启了他说唱格萨尔英雄事迹的大门,使活形态的《格萨尔》史诗创作有了新的生机,晋美也成为草原上能够演唱段落最多的仲肯(格萨尔艺人)。不同于格萨尔英雄故事中草原人民的智识未开,晋美是在现代语境中生存的人,他已经意识到梦中的格萨尔是一个下界到人间的凡人,他对未来的一切一无所知并且极端好奇,格萨尔也被凡人身份周遭的世俗所扰,人性与神性的冲突让他困惑和苦恼。在梦中,远古神话中的格萨尔有了和未来世界的晋美交流的桥梁,带着现代理性思维的晋美也更加能够理解蒙昧时代的英雄格萨尔精神世界的困顿。
晋美从草原牧民变成格萨尔说唱艺人,他也成为了阿来小说中的一个隐含作者。从“每个岭国百姓口中都有一部《格萨尔》”到如今需要特定的说唱艺人进行演唱,格萨尔已经从民族集体记忆逐步转化为个体的文化专利。格萨尔故事存在的真实性也遭到质疑,晋美一路演唱神授的故事,一路寻找着答案。晋美寻找史诗中姜国魔王萨丹想要抢夺的岭国的盐湖,他来到康巴草原南部的几个盐湖,发现有的干涸有的搁置,随着国家盐业的统一管理配置,中国大地上的百姓已经很容易购置食盐,不再需要用古老的方式淘取不干净的湖盐。故地的遗民不再记得姜国,也已经不愿追究英雄格萨尔故事的真实性,“故事就是故事,从来没有人想这是故事里的什么地方”[2]224。晋美“盐之路”的寻根吊古实际是文化地理空间的失语,投射出的是现代性的脚步正在消解或者已经消解了古老民族英雄的业绩。
说唱艺人晋美在现代空间场域中展现了格萨尔英雄叙事的当代境遇,他用自己作为格萨尔故事传承人的切身遭遇诠释了英雄格萨尔在当代文化空间中的尴尬处境。在康巴赛马会上的格萨尔艺人说唱比赛以及樱桃节上的说唱活动中晋美已经感受到格萨尔故事的文化空间已经被商业经济逻辑所裹挟。晋美在省藏语广播台说唱格萨尔时被女主持人阿桑姑娘暧昧的声音所迷惑,在影像店和流浪途中,他聆听CD中传出的自己演唱的格萨尔故事时,却发现周围的人对此是麻木的,对他这个演唱者是无视的。晋美带着英雄格萨尔的故事从古老的草原经验中走出来,在现代性的空间中难以修复格萨尔的英雄原型。这种难以言说的尴尬处境让晋美和他代言的格萨尔英雄叙事不得不在社会的发展潮流中从集体走向个体、从主体文化走向边缘话语。
三、诗性与理性并置的英雄重塑
古希腊时期就把人类的思维分为两种,即Mythos(米索斯)和Logos(逻各斯),Mythos代表神话或诗性思维,Logos代表理性思维。“诗性智慧”是人类原初的智慧,它适应了尚处在远古集体记忆时代的藏族牧区那种质朴性的思维方式,是在人类自我意识完全独立出来之前,原始人类的思维方式,是一种集体表象[6]。史诗《格萨尔》汇集了人与神、魔幻与现实、人类与自然、神话与历史等叙述的民族集体记忆宝库,给予神授艺人晋美和作家阿来以传承和演绎的宝贵资源。小说以民族史诗《格萨尔》为叙述原型,在基本故事形态上复颂神话英雄格萨尔的角色功能,让小说不失传统民族文化的底色。在英雄叙事的诗性叙述中,阿来在英雄格萨尔身上注入了神性和人性的冲突,人性化的具象书写让格萨尔的英雄形象更加饱满,更具张力。在多个回合的叙述中,“妃子争宠让他进退失据血缘的亲疏以致赏罚不能分明”[2]178,作为天神之子的格萨尔也有困顿迷惑甚至残忍的一面。当格萨尔从魔国六年的酒色淫靡生活中醒悟过来去寻找被白帐王掳走的王妃珠牡时,面对珠牡与白帐王的孩子,格萨尔手起刀落将一个无辜的婴儿杀死而没有流露出半点悲悯之心。在小说《格萨尔王》中,不乏类似负向功能的叙述,展现出英雄的无聊倦怠以及神性被消磨的一面。普罗普指出,在某种原因影响下,功能会出现负向的结果(Negative Result)[7]。在藏族社会经验中是不接受将英雄形象和宗教代名词污名化或者妖魔化的,阿来在他的英雄叙事中重塑了英雄格萨尔,让这个人物更具多面性,成为一个圆形人物。
作为“故事”的格萨尔英雄叙事采用的是一种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即零聚焦叙事,叙述者掌握一切,而故事展开又是以口头史诗为原型的复颂。这在认知层面上与人类早期认识世界的诗性思维遗存有关,是属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对格萨尔英雄的深刻透视和认同。小说的另一叙事线索“说唱人”则采用了固定内聚焦的叙事视角,通过格萨尔神授艺人晋美一路流浪说唱逐渐成为著名的仲肯,格萨尔英雄叙事的当代形态也逐渐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在诗性智慧高度发展后出现的理性智慧,是对神性故事原型的消解,是作为活形态的《格萨尔》史诗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又一“真相”。
阿来将“故事”中的格萨尔成就英雄业绩和“说唱人”晋美演唱格萨尔英雄事迹作为两条交织进行的叙事链条,将线性的英雄叙事和格萨尔在当代的空间形态进行相互参照。阿来的“神话重述”赋予了英雄这个命题更多的思考,他更多地挖掘与突出格萨尔王作为人而不是作为神的一面[8]。一千多年来,格萨尔的英雄业绩一直在青藏高原上被岭国百姓集体记忆,并有了职业化的格萨尔故事说唱艺人。然而格萨尔并没有真正地解决草原百姓的苦难,无休止的征战带来无尽的流血,魔性依然在人心中滋生,发愿建立的正义与慈爱之国也并未得以真正建立乃至传世。阿来借助晋美这一格萨尔神授艺人的角色行为,阐发出对格萨尔英雄叙事的理性思考。他以敏锐的社会洞察力感知到民族史诗《格萨尔》正在社会变迁中不断被重述和改写,并创造性地将传统格萨尔的英雄叙事形态和格萨尔的当代境遇转向结合起来。小说《格萨尔王》将蕴含在格萨尔宏大英雄叙事背后的诗性叙事和在现代性文化语境中的理性书写并置,客观地还原了线性历史中格萨尔的故事形态,同时呈现出时代对英雄格萨尔的疏离。33万字的小说《格萨尔王》是阿来跟随一批《格萨尔》史诗研究学者一起进行田野考察后的成果,在呈现出人类理性的光芒和文化认同的失落,也折射出现代性对民间文化传统的消解和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