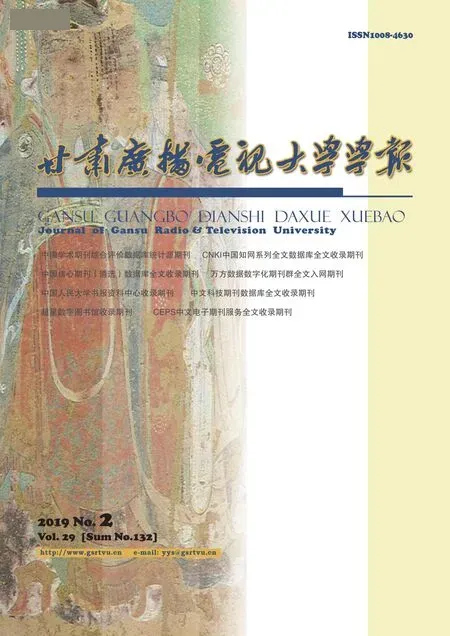也论经古今与汉代阶级关系
陈颖聪
(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专上学院 语文及传意学部,香港 999077)
一
周谷城先生根据廖平《今古学考》中区分经古今文歧异的十五条标准,归纳为三项九条[1]61-62。其文大意谓经古今文两派的主要区分,可以简单地归结为:经古文学派代表的是贵族的势力,经今文学派则代表平民中的工商势力,而这两种势力都是属于奴隶主阶级。
贵族奴隶主以他们自己的公有土地为剥削手段,眼睛往后看,重封国的分立,重既得利益,重传统形式,重保守。工商奴隶主以新兴的工商业为剥削手段,眼睛往前看,重统一,重生产致富,重当时的现实,重进取。[1]61-62
周先生认为,这些区别,其焦点在于代表工商奴隶主的经今文学重统一,而代表贵族奴隶主的经古文学则重封国分立。如果笔者的归纳不违反周先生原意的话,那么,所谓贵族奴隶主实指当时的地方王侯和武断乡曲的豪右势力。所谓工商奴隶主则是指被汉中央政权“重农贱商”政策打击下的“工商业者”。因为周先生自己也说:
汉承秦制,据说是“重农贱商”的。然而“商人已富贵矣”。换句话说,就是工商奴隶主已得势了。工商奴隶主既已得势,凡是附和他们的要求的人,便一律尊显起来。经今文派正是附和他们的要求的人,当然要尊显。果然,汉代所立十四博士,无一例外,都是今文派。[1]63
基于周先生上述论点,笔者有三不可解之处。
第一,史称汉代的工商业者,他们正如周先生所指出,是受汉中央政权“重农贱商”政策所打击的,他们得到富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交通王侯”。即与“封国分立”的王侯相勾结,从而与中央对抗。那么,“封国分立”的王侯势力的存在,正好是工商业者抗拒或逃避中央贱商政策打击的凭借,为什么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又主张“统一”,而与地方王侯的“封国分立”相抵触呢?此不可解者一。
第二,周文认为,经今文学派的代表者“是代表平民中的工商势力”,经古文学派的代表者“是代表贵族中的等级势力”,“这两种势力都属剥削阶级,即奴隶主阶级。其盛、衰、消、长,可从历史的变化看出来”[1]59-60。从这段话看来,周先生似乎是说,自春秋战国以迄于汉的整个朝代,剥削阶级内部只有两个主要的阶级,即贵族奴隶主与工商奴隶主,他们在对抗着,斗争着,消长着。如果这样去理解,那么,汉中央统治集团,这一牢牢掌握着国家统治大权的诺大阶层,又将置于何地呢?这个阶层既打击地方王侯、豪右,也打击工商业者。显然既不能把三者合而为一,或者混而为二。汉中央统治集团这一阶层在当时历史上起什么作用?他们在经今古文斗争中处于什么地位?周先生对这么一个重大的问题则避而不谈。此不可解者二。
第三,经今文学的提倡、宣传,设立博士官,以至于以经今文来设科取士,都是由汉中央统治集团中的汉武帝、董仲舒等肇其源,而历来帝王演其流。这是载于史册,众所周知的史实,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而周文竟谓:
古代历史的变化,可以拿春秋战国之交作一个分水岭。在这以前,贵族的等级制度有支配作用;在这以后,工商的自由竞争有支配作用。[1]60
古文派的主张,与贵族奴隶主的要求,颇相接近,甚至完全一致。今文派的主张,与工商奴隶主的要求颇相接近,甚至完全一致。[1]61
这样说来,仿佛自汉武帝以来,历代所立经今文博士学官,都是仰承工商奴隶主的意旨而设立的。汉中央统治集团这一阶层,自汉武帝后,斗争的结果是彻底地失败了。自此以后,不但汉政权完全被工商奴隶主这一阶层掌握了,甚至自战国以后,中国政坛均在工商势力的掌控之中。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此不可解者三。
二
我们试回顾一番历史:汉代的政策,正如周先生所说,是“重农贱商”的,但制定此政策及具体执行者不是“封国分立”的贵族奴隶主,而是汉中央统治集团。汉高祖不但颁布“贾人不得衣丝乘车”的法令,而且对商人乃“重租税以困辱之”[2]1418。汉惠帝、高后时虽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即允许商贾之家衣丝乘车,减其租税,但仍然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2]1418,商贾之家是不能进入国家的统治机构的。禁止商人衣丝乘车,困辱工商业者的法令,汉武帝以后循而不改。武帝时,因外事四夷,财贿衰而不赡,而采取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等权宜之策,因而“选举陵夷,廉耻相冒”,而“兴利之臣自此始”[2]1421。从此,一些富商大贾,如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之流都走上了政治舞台,且得到武帝重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汉中央统治集团重农贱商政策的改变。至于所谓“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情况[3]1133,只能说明汉政权打击工商的政策出现相对的、暂时的失败,却不能从而得出工商奴隶主与汉中央统治集团在根本利益上已取得一致,或者工商奴隶主已能左右汉中央政权的结论。因为这个建议的创始者晁错明确地指出,“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3]1134。以通过封赠并无实权的爵位获取豪商巨贾的粟物,这是对国家有利而无害的经济政策。汉中央统治集团并没有拱手把政权让给豪商巨贾,豪商巨贾更没有得到实际的权力,他们的地位与中央集团内的官员相差甚远,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仍然掌控在中央统治集团手中,商人的地位仍然决定于中央政权。不错,武帝的确是任用、提拔桑弘羊等富商巨贾,但这绝不说明这些原来的富商大贾左右了汉政权的政治、经济;相反,却是汉统治者武帝利用了少数可以利用的富商大贾为他出谋献策,发展中央统治集团的经济,从而打击地方经济,打击更多的富商大贾,其本质亦是一项巩固并发展中央经济的措施。
史称,武帝时,外事四夷,府库不给,加以山东大水灾,民多饥乏,县官大空。武帝面临的形势是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焉。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3]1162-1163。这是武帝时面临的严竣形势。可见,武帝时中央与工商业者一直是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这种状态发展到任用桑弘羊等管榷盐铁,实行政策专利,达到高潮。而这些措施,实际上就是维护中央的财政利益,打击和控制地方商贾的势力。在实施管榷盐铁之后,史载:“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矣!”[3]1166这时较多的“贾人”当了政府的官吏,似乎是工商业者在斗争中获得胜利了。其实不然,那些当了官吏的贾人,尽管他们可以利用职权去牟取个人的更多暴利,但总的来说,他们已被中央统治集团用名利之缰紧紧地羁络住了。他们既为政府官吏,就要为中央的经济政策服务,而这些政策是有利于中央,不利于广大工商业者阶层的。正是由于桑弘羊等都出身于工商业者阶层,所谓: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而桑弘羊贵幸;咸阳,齐之大鬻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产累千金,故三人言利析秋毫。[3]1164
所以武帝才设法利用他们在工商界中的经验与号召力为中央规划经济政策,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央获得了大批财富。武帝的政策成功了,所以班固说:“及孝武时,国用饶给,而民不益赋。”[3]1186特别是武帝在此基础上又采用了杨可告缗的方法,向工商业者征收所得税,加大了对工商业者的打击和控制,无论有无市籍,一律估价征收。
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得民(笔者按:指告缗对象,即大小工商业者)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3]1170
结果,武帝解决了富商巨贾对中央经济的威胁,而由朝廷直接管榷盐铁之事,控制着当时的经济主脉。延至昭帝时的盐铁会议,中央与地方工商业者的矛盾又发展到另一高潮,结果只是罢酒酤,而盐铁管榷如故,而盐铁的专买,“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变改。元帝时尝罢盐铁官,三年而复之”[3]1176,这说明中央已牢牢掌握了经济的主动权。
从上述史实来看,汉中央统治集团与富商巨贾的矛盾,终汉之世一直没有停止过,情况是复杂的,其中虽有一些反复,但总的来说,中央势力一直占据上风。
基此,可以认为,经今文学,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偏重于“微言大义”,能为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构造汉大一统的统治理论提供方便,因此,经今文学很快便为武帝接受,确立了“一尊”的地位。经今文学本来就一直是中央的官方哲学,它反映了汉中央统治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工商阶层的哲学,不完全代表工商阶层的利益。经今文的学者,更不是由于工商业主得了势而去附和他们,相反,大量的经今文学者却是沿着武帝所开辟的利禄之路跑进了中央。史称: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3]3620
这是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的历史。其实,学术与经济虽有联系,但不是等同的,工商业者注意的是赚钱,是名利富贵,他们很少注意到学术,在历史上也找不到哪个经今文学者去附和哪个得了势的富商巨贾,更找不到哪一个工商业者是经今文派学者。同时,武帝时一些工商业者虽然当了官,甚至当了大官,已经富且贵,但并不等于工商业者这个阶层已得势,更不等于这些人已能掌握政权,并取代中央统治集团既有的势力,取代了中央的官方学术思想,或另提倡某种学术思想,从而使当时的经今文学家都去依附他们。
三
汉至武帝时,汉初一些比较跋扈的功臣和大部分王室封国,都被中央镇服了,但当时内部的主要危险是一些尚存的王侯和地方豪右与工商业者相勾结,而形成的一股潜在的势力。那些王侯、豪右既有一定的“地望”和文化,也拥有相当的经济势力,他们往往在地方多行不义,严重影响甚至破坏社会的安定,史载“延年乃选用良吏,捕击豪强,郡中清静”[3]2666。武帝对付他们的方法,一方面是用酷吏镇压他们,所谓“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3]2641,就成为了当时国家的一项重大工作。另一方面尊儒术,提倡董仲舒的今文经学,设科考试,立五经博士,给以利禄。这些措施,对化解当时的社会矛盾,稳定中央的统治,是有深刻意义的。以武帝为首的中央统治集团,一方面广泛吸收庶族地主中的知识分子,加强本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笔者认为,汉中央统治集团是属于新兴的地主阶级,与周先生所说的贵族奴隶主和工商奴隶主不同。因非本文讨论范围,兹不赘);另一方面,也笼络各方面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可用之材,为中央政权效力。建元五年(前136)初置五经博士,又相继“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3]3620,乃至“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3]3593。这样,不但广泛地维系和吸引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也使一些工商业者,只要他们有能力,甚至纳款出谷,也可通过卖官鬻爵的手段,为中央朝廷效力,使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出路。武帝的这些政策,相对来说是成功的。
汉武帝开设五经博士,设科取士,提倡经今文学以维护中央的统治,不仅壮大了新兴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而且分化了原来的旧贵族,使他们为中央朝廷效力,这就是汉统治者提倡善于阐发微言大义,与当下的政治需要相贴近的经今文学,压制以训诂、考据等为主要研究内容,与当下政治时有距离的经古文学的目的,也是经今文学一向成为汉代官方哲学的社会政治根源和历史根源。至于武帝提倡盐铁专卖,吸收一部分工商业者进朝廷当官,从而打击更多的工商业者,也可以作如是观。
四
至于上文所举的周先生归纳的经古今文学的分歧点,笔者不能完全同意。比如说,经古文学重“封国分立”,经今文学重“统一”的说法,有点绝对化,且与事实不尽相符。其实,经古文学同样是重统一的。例如,《左传》是经古文学派的经典,而且是经古文学派与经今文学派论争中的极关重要的经典。但《左传》对于“尊王攘夷”“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这一类有关“一统”思想的“春秋大义[4],是非常坚持的。同时,如果说经古文学派一向是代表贵族奴隶主的思想,似乎也不尽然。如《左传》就充分肯定了像郑国商人弦高一样的人物[5]495-496,而指责了像晋灵公一样的贵族奴隶主[5]655。《周礼》是另一部重要的经古文学派的经典。王莽即根据《周礼》“王为诸侯缌缞,弁而加环绖,同姓则麻,异姓则葛”的礼制[3]4091,在为汉平帝举行丧礼时,力压各地王侯,凌驾于孺子婴之上,确立了自己摄政的地位和权力。获取政权后,王莽又根据《周礼》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制,如《周礼》有“膳羞百有二十品”的说法,于是王莽“令诸侯各食其同、国、则;辟、任、附城食其邑;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3]4142,改革了过去王侯的俸禄制度。又认为“《周礼·司马》则无徐、梁”,而改革行政区域的划分[3]4128。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巩固王莽中央集权的需要,而经古文的典籍,则在其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不仅王莽利用《周礼》等经古文来托古改制,纂取汉朝政权,巩固新政;还有宋代的王安石也利用它去抨击一些社会弊病,构建自己的理论。例如,北宋时,朝廷经常滥杀耕牛以佐膳,王安石即引《周礼·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的制度,指出这个制度一直为后来开明的君主奉行,如唐代“九庙时享有摄事共用一犊。国朝开宝初,冬至亲郊,诏有司宗庙共用犊一,郊坛用犊三。又诏其常祀惟昊天上帝用犊,自余大祀悉以羊豕代之”,至于宋仁宗更是“三年亲祀,八室共用一犊。有司摄事,惟以羊豕”[6]。于是主张改革祭礼,保护耕牛,大力提倡节俭之风气。可见,无论在自身理论研究的取向,还是在社会的实践中,经今古文的分野并不是在于主张“统一”,还是主张“分封”。其要点应是两个系统对经书的不同理解和诠释,在实践中提供给应用者的不同需求而产生的不同遭遇和不同的社会地位。
周予同先生曾指出:
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莽。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7]
经古今文学各有偏重,各有特色,但经古文学重训诂、考据,比较实事求是,较少沾染谶纬迷信的不正之风。在汉朝中央政权的压迫下,它散见在民间,除新莽时期立过一些古文经学官,及东汉光武时偶立《左传》,旋又废止外,一直受到官方排斥。但它当时在民间势力却很大,它的学术地位实际上远远超过经今文学派。而经今文学派则往往发挥微言大义,关切政治得失,为读经者尤其是政策的制定者,留下很多可以利用的空间,故往往得到当权者的偏爱。所以,对经古文学派不能一概以“眼睛往后看”“重保守”等斥之;同样对经今文学派,亦不能一概以“眼睛往前看”“重统一”而褒扬之。 总之,经今古文的斗争是一个牵涉面极广,极其复杂的问题,要说清楚,实不容易,只能就学习周文的过程中提出一些疑难之点,就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