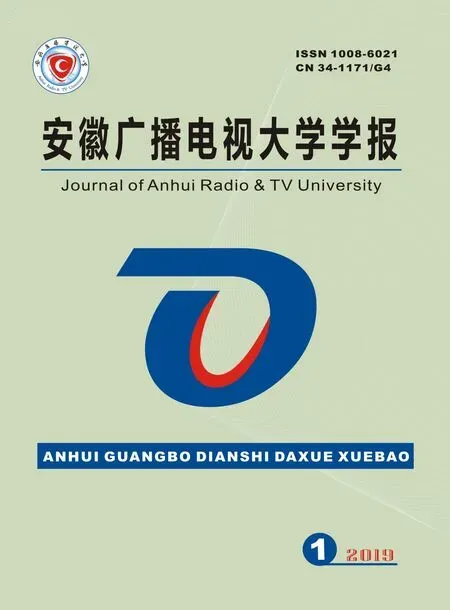晚清启蒙知识分子的觉醒之困与身份焦虑
——以吴汝纶为中心的考察
潇 潇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合肥 230026;2.合肥学院,合肥 230601)
一、引言
19世纪中叶以来,国门洞开、西潮涌动,中国传统社会的稳态格局不断受到冲击,以晚清启蒙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这种“世纪之变”又与民族文化本位色彩的社会认同与典型儒家精英知识分子情怀的身份定位交织在一起,具有典型的时代性与复杂性。在经由传统士绅社会向近代知识人社会过渡中,这种精神、情感上与西方现代知识方凿圆枘的思想隔膜、觉醒困境与身份焦虑,使“开明”与“守旧”、“传统”与“近代”的矛盾构成了近代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的艰难抉择和复杂心理,预示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转型之艰。
在近代思想史上,吴汝纶思想复杂而备受关注,他“注定与‘旧时代’、‘旧人物’天然地联系在一起。他面对新的社会思潮所跨出的步伐,虽也有惊人之处,但最终没有完成质的跨越。”[1]这种未跨越的遗憾与晚清以来中国知识群体追求精神主权的时代困境和主体建构下的认同焦虑密不可分,同时这种渴求“自主权”的民族文化本位观与“去民族性”的普遍西化思想间的矛盾也呈现出代际知识转型的典型意义和深远影响。
二、追求精神自主权的民族觉醒之困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指出,晚清中国属于官方民族主义的典范,这种民族主义是民族与王朝制帝国的刻意融合,内含着民族性与爱国心。在这一民族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情况又具有特殊性,一是近代民族主义运动与半殖民主义抗争同时出现,二是在中国历史中“既内在于王朝又超越于具体王朝的‘中国’认同远早于近代民族运动”[2]。因此,“亚洲和非洲民族主义想象的最有力也最具创造性的部分不是对西方推销的民族共同体模式的认同,而是对于这一模式的差异的探求。”[3]
长期以来,晚清启蒙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对民族精神自主权、控制权的不断追求,便是上述认同差异的时代性标志,必然导致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在古今中西张力中的觉醒之困。清末民初,特别是1895—1905年间,启蒙还停留在“开绅智”与“开官智”阶段,儒家学说中的“修身”“经世”思想依然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西学诸说虽不再被视为无父无君的洪水猛兽,但“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问题却始终占据了民族国家认同观念的制高点。
晚清启蒙知识分子通过交流工具(翻译、出版)、普及教育和内政构造等多种形式传播西学,开启民智,试图推进国家由上而下的文化和政治统一,但在这种社会与文化启蒙过程中,制度与道德、科学与文化之间的扞格不通与疏离现象始终存在,以至于中国近代启蒙运动中长期存在着两股暗潮相互颉颃,即对西方物质的模仿(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的现实诉求和在精神上寻求自主、独立、区别于西方模式的民族认同,而后者的目标恰恰是为了挣脱前者的约束,确定一个非西方的特殊性精神领域。因此,无论是洋务派、维新派还是宪政派,他们在接纳西方事物方面或许存在保守、温和或激进的不同做派,但都脱离不了为民族精神(民族历史中特有的文化宗教传统)寻找外在保护物的认同模式。在这种复杂的民族主义情感基调下,“即便我的国家会犯错,但在情感上,不论国家对错,她依旧是我的国家”[2]6。对于一个民族共同体来说,随着对西方的物质、制度模仿越深入,就会越发需要在精神上获取并保持某种主权性。
究其原因,这一群体虽然经历了某种知识觉醒,但依旧身处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受制于高度组织化的等级体系。从社会历史情境来看,他们无法改变自身也是作为历史存在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文化和结构性因素(社会建构)。许纪霖曾指出,伴随着传统的中华文明帝国的瓦解,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无疑是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但“这一民族国家究竟是一政治共同体,还是历史文化共同体?”是困扰中国人的一个社会乃至族群认同难题[4]。甲午战争之后,国人普遍意识到西方知识的重要性,儒家文化亦有日益式微之迹,但此时以西学所代表的现代知识远未真正取代传统国学,获得建制化的垄断地位,“士大夫的精英意识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在新的国民观念中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强化”[5]。
面对时局困顿与民族危亡,这一群体虽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角色立场定位与民族情感诉求,“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6],但这种探索归根结底还是基于其儒家精英主义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他们有着“开拓并延续民族文化的使命”“有担负国家政治的责任和问过政治的兴趣”“有谋致全民幸福乐利的抱负”和“有悲天悯人之情怀,淑世之热肠”[7]。但当他们试图用西方社会文化思想来诊断和引导中国的政治命运、社会命运和文化命运时,又“发现自己处在某种由前人遗留下来的情境之中,这种情境也包含着一切适合于它本身的思想方式”[8],难以割舍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自觉,更无法对儒家伦理进行有效的理智性控制和彻底的自我批评。例如,传统中国的德性思想借助近代“公德”问题,再度获得历史正当性,成为建立民族国家的关键节点,梁启超就曾大举阳明学说,以反对西方的破坏主义和功利之说。吴汝纶也借日本友人之口提出“宜以孔道为学生道德之基”[9],认为“英国大学修德之法,依宗教也,欧美诸大学多采此制。”而中国与日本一样,信教观念淡薄,因此“固宜以孔教为养德之基。然若不研究孔道之真谛,则道德之观念未固,而独立之确心已消。”[9]134-137
中体西用的民族文化立场在吴汝纶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他忧心西学流行必然导致国学失语,“西学畅行,谁复留心经史旧业,立见吾周孔遗教,与希腊、巴比伦文学等量而同归澌灭,尤可痛也。独善教之君子,先以中国文字浸灌生徒,乃后使涉西学藩篱,庶不致有所甚有所亡耳。”[10]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东游归国之后,他对民族文化乃至民族精神存亡的忧患意识不减反增,曾以日本学制中西洋公学与本国古学的不能两存为引,忧心“国种两绝”,继而“思之至困!执事乃欲兼存古昔至深极奥之文学,则尤非学堂课程之浅书之可比,则尤无术以并营之,又众口之所交攻者也。西学未兴,吾学先亡,奈之何哉!奈之何哉!”[10]407
为了解决东西文化、古今文化割裂对峙的问题,吴汝纶提出取新未必要全盘革旧的部分改良、渐进改良的思想融合方案,并在这种方案中潜移默化地赋予儒学以精神主权意识和独特文化价值。儒学乃立国之本,即吴汝纶所言,“法不可尽变。凡国必有以立。吾,儒也,彼外国者,工若商也。”“夫法不可尽变,又不可一守吾故而不变,则莫若权乎可变不可变之间,因其宜而施之。”[11]他认为中学、孔教乃国之根本,经史百家则是新学根本,进而他认为儒家精神可以支撑西学诸说的实现,“今欧美诸国,皆自诩文明,明则有之,文则未感轻许。仆尝以谓周孔之教,独以文胜……今世富强之具,不可不取之欧美。得欧美富强之具,而以吾圣哲之精神驱使之,此为最上之治法。”[10]385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这种基于儒家精英主义立场的精神主权追求一直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道路选择和价值判断,导致了民族文化本位主义的精神需求与寻求邦国发展的现实选择之间的矛盾。对此种现象,杜维明曾有生动论述:“他们在情感上执着于自家的历史,在理智上又献身于外来的价值。换言之,他们在情感上认同儒家的人文主义,是对过去一种徒劳的、乡愁的祈向而已;他们在理智上认同西方的科学价值,只是了解到其为当今的必然之势,他们对过去的认同缺乏知性的理据,而他们对当今的认同,则缺乏情感的强度。”[12]
在民族危机日益突出的晚清十年,民族属性逐渐成为近代中国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合法性的价值之一。在吴汝纶的日记中,不乏对“邦国”“主权”“国体”“自强保种”诸思考,民族主权追求与民族文化认同被筑成一块,“内圣外王”的道统思想自然成了其保存民族精神核心、发扬本土文化合法性价值之标的物。在中国长期以来“政统”与“道统”双重权威影响下,即便1905年科举废除以后,由学及政的仕进之途被切断,公共政治与知识权力紧密勾连的社会认同模式的影响依旧长久而深远。这种认识的固有结构导致了晚清思想界觉醒的双面性与矛盾性,并最终造成了这种一只脚踏在“旧时代”,另一只脚踏在“新世界”的觉醒困境。
三、主体建构中的身份焦虑
清末十年间,启蒙知识分子的内群体认同焦虑是其追求民族精神主权现象的深层心理结构。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内群体为群体成员提供了情感和价值意义,群体成员将群体身份内化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通过认同内群体来获得身份满足感和尊严,个体的重要身份来源于社会阶层和民族的群体身份。由于晚清知识阶层群体权力的源头是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秩序观,他们信奉的是一种天下主义的文化理想,是一种“不是国家至上,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13]的超国家主义。因此,晚清启蒙知识分子的“群体身份”依旧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历史文化共同体。这种延续性的群体身份认同和民族危亡之际的社会认同具有同构性,导致了以吴汝纶为代表的一批有着传统功名,又接受了西方新知的启蒙知识分子无处安放的身份焦虑。
内群体身份的形成受制于特殊的时空条件,从一个纵向的大时段来看,晚清启蒙知识分子属于典型的“知识界”,他们隶属于传统中国的知识阶层——“士绅”。由于“这些群体的专门任务就是为这个社会提供某种对世界的解释”[10]11,因此他们身具社会权威、文化规范的角色和稳定、延续传统文化秩序的使命。如果以张朋园的“启蒙—疏离—革命”三段论来概括这一群体,即以魏源(1794—1856)至黄遵宪(1848—1905)为近代知识分子第一代,梁启超到孙中山(1866—1925)为第二代,胡适(1891—1962)为第三代[14]。那么,以吴汝纶(1840—1903)生卒时间与学说思想来看,他不仅早年入曾、李幕府,历官直隶深州、冀州知州、直隶天津知府,思想观念倾向“洋务”一派,后弃官从教致力于教育改革,基本可以将其归于近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一代。新旧嬗替之际,传统士绅和近代知识阶层的界限尚未清晰,尽管接受了新思潮、新学理的洗礼,萌生了某种关于存亡、人格、知识的自觉意识,但基于内群体的情感需求和价值实现,他们在规范伦理与德行伦理领域有着重叠的共识,依然认同于传统知识阶层中的“士”形象,并以士类自谓、四民之首自居。其启蒙学说与实践常被论证为一种受到西方启示所产生的“防范”策略,目的是“阻挠部分或完全源于本土的更为根本的、更具威胁力的变革”,因此造成“与西方有关的变化在特定环境下亦能与中国社会中本质上较为保守的力量联合”的特殊现象[15]。
群体身份不仅是个时空概念,更是个主体建构的过程,取决于个体主观性和特殊性的经验的影响。启蒙知识分子的觉醒与反思常常带有一种急迫的功利色彩,希望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放置于一种“长与短”视角加以审视,然后取长补短,发挥西学在天行人治方面的补充性、修复性效用。吴汝纶虽广览西书,醉心西学,曾访日调研新学制,为《天演论》作序,倡议废科举、重学校、兴人才,其言行具备一定程度上的近代启蒙思想价值;但又一直秉持着中体西用的观念,曾撰文讥讽维新派,政治立场与维新变法相悖。吴汝纶认同于高岛张辅关于“中国之教育,有益于心,西国教育,有益于身。不可舍己从人,当取长补短”的观点,称之“所言甚扼要。”[9]64他赴日考察教育后提出了中国教育改革救急之策、培养急需人才的诸多设想。这种“致用”思维的延续注定其无法对母体思想进行根本性质疑,只能徘徊于某种敏感与迟钝交织的悖论之中,进而导致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与政治变革的不彻底性。
作为桐城派的末代宗师,吴汝纶天资高隽,少习举业,“好文出天性,早著文名”[11]428。他向以“士”自居,入幕多年,为官数任,其心性、志趣却不在仕宦,入曾幕后,“亦师事国藩,而所诣尤为精邃”[11]435,越发深信文事辞章乃士大夫“坚车行远”之基础,古文之学可以成为“谈论军国、臧否政治、慷慨论天下事的利器,成为开启蒙昧、昌言建策,道问学与新新民的坚车。”[11]5因此,他试图打通桐城文章形式与含西方政治学说之间的融通之路,赋予新思想以合法化的形式,以此解决中西学交融的问题,即只要以桐城文去表现西学“名理”,即可“合为大海东西奇绝之文”[16]。
如何在以学习西方知识为主导的近代教育改革中接轨新旧学说,发挥本国古文并功、德、言于一途的重要作用,成为吴汝纶晚年主体建构的某种镜像折射。自清末兴学堂、派游学以来,举国崇尚欧文渐成学界风潮。在《东游丛录》中,吴汝纶试图调和新旧、中西冲突,寻找群体与个体文化身份的安身之所。首先,通过对日本近代教育改革的利弊梳理,极力塑造汉文、汉学的本源性、正统性。他在《东游丛录》中认为日本的汉文教习讲《左传》,“所讲皆粗浅,此国汉文,不复措意矣。”[9]58当得知日本维新以前学堂课本多为“四书五经史记汉书”时,吴汝纶又写道:“吾国自八股盛行,无人能读史汉,鄙论尝谓六经四史不可废。近日议兴学者,亦绝不议及四史,盖所谓史学者记事迹而已,仆私心病之。……恐吾所勤勤谋改革者,适得日本德川幕府时之旧迹也。”[9]61其次,在中西教育与文化比较中割裂两者各自的完整性,找到中国之教育、中国之文明、中国之风俗存续的合理性。他认为“本国原有之文明,皆精神上事,西国之文明,皆制度上事。以吾精神,用彼制度,是用彼之长而不为彼所用”[9]67,“古城谓,移易风俗,圣贤犹难,五方交通学有长短,如废贵国之文学。则三千年之风俗,无复存者,人则悉死,政则悉败矣。是故英国有保守党,以制西人制轻浮狂简也。”[9]64
诚然,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知识分子的“群体觉醒”可谓一种共同的征候,但群体身份的焦虑使他们无法脱离那些构成其判断基础的个体经验,离不开情绪性冲动与生命冲动所具有的诸种心理根源,吴汝纶等一批清末赴日考察官绅在面对西学教育理念时的犹豫、矛盾正是这一群体心理的派生物。进而,这种身份焦虑和内在冲突造成了近代改良诸学最终脱离其中产生以及试图加以解决的现实情境,成了一种精神性的内在观察。无论是将中西文化之差异视为“精神”与“制度”不同类型,“益于心”与“益于身”不同作用,还是将传统文化视为制约“轻浮狂简”的手段,始终离不开吴汝纶对其个体和群体身份的一种认同与维持。
四、并喻文化的过渡性历史价值
在1840年之前,中国传统社会因国门封闭、思想阻滞而停滞不前、发展缓慢,恰如梁启超笔下“世界中濡滞不进之国”[17],这种处在社会发展迟缓状态下的代际传承文化类似玛格丽特·米德所说的“前喻文化”[18],而鸦片战争打破这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中国被强行纳入世界体系,人们赖以依存的象征性价值体系受到破坏和怀疑,呈现出“并喻文化”诸种特征。出生于1840年的吴汝纶,在某种意义上,当属于中国“前喻文化”的末代与“并喻文化”的初代人群,这一代经历了相同的社会变革并形成独特的“历史社会意识”或集体认同,影响着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区别于先前的几代人。
虽然并喻文化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化类型,其在同一社会中一般不会持续几代人以上,但并喻文化对后代的影响和辐射确是长远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下的中国式并喻文化更具有某种“史无前例”之开创性和独特性。正如“每一代都有产生自己的新人,但从一代到下一代的更新程度却可能极不相同。人类从得到火车到拥有飞机的时间并不太长,但为了得到火车却费了几千年之久。”[15]8从这个意义角度来说,这批一只脚还站在革命前中国社会的知识群体,他们理解世界方式的巨大变化导致的不仅是跨时代的文化觉醒,而且正是这种过渡性的思想准备使得中国之后的革命性巨变成为可能,其革新程度和变化容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革命后的群体更具时代意义。张灏先生亦曾指出晚清知识阶层与五四新文化之间的不可分割,且“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最初十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19]
19世纪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出于自我抉择和完全的自我欣赏而孤立于世的儒教中国”[15]7,绝大多数中国知识阶层的精神世界被千百年恒定的儒学理念锁定,这种情况直到鸦片战争时期,依旧变化甚微。在接连战败的连锁性激荡和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下,晚清启蒙知识分子逐渐开眼看世界,从“盛清”的骄傲与舒适中觉醒,意识到中国社会融入世界潮流之迫切,开始关注西方学说的富国智民之策,进而批判那些长期置于思想价值顶层中的陈腐观念。作为近代中国向西方探寻真理的初代启蒙知识分子,吴汝纶早年深受传统思想的侵染,但中年以后以新学倡天下,更以63岁高龄东渡日本考察学制,其“治学的闳博视野和融通思维显然迥异侪辈”[20],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并喻文化阶段代际思想渐变的可贵意义。
从时间上看,吴汝纶接触近代西方新事物的时间并不早,直到1866年应邀入曾国藩幕府操办洋务,才有机会开眼看世界,涉猎西方事物,接触西方人物。短短的十几年间,他以超乎常人的求知欲饱览各类西学报刊书籍,汲取西学知识,不但“自译行海外之奇书,新出之政闻,与其人士之居于是或过而与相接者,无不广览而周咨也。”[11]435而且通过广泛交友,“于西人新学新理尤兢兢,尝欲取彼长技,化裁损挹,以大行于天下”[11]459。在他的日记中,多涉西学理论和西方工业革命成果译介,大量介绍西方的宇宙、地球、生物演化之进化论思想,全集中见诸文字西书书目约有六十余部,所包西方实业成果译介亦甚广,内容涉及化学、声学、植物学、测量学,被世人评价为“喜以西学引掖时贤”[10]122,“固尝以新学倡天下矣”[11]450。在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十二年间(1889—1901),他还创办了英文、日文学堂,“专力以兴教化,并中西为一冶,日以精神灌澼而铸熔之,风气旷然大变”[11]433;“欧美名流皆喜与过从;推为东方一人。日本人尤信慕,学者或航海西来,执弟子礼受业。”[11]451
在兴办新式教育过程中,吴汝纶对应用科学、自然科学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得到进一步提升,进而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批判了那些“仍欲以中学为重,又欲以宋贤义理为宗,皆谬见也”[10]284的社会积习,不仅认为“天算、格致等学,本非邪道,何谓不悖正道!西学乃西人所独擅,中国自古圣人所未言,非中国旧法流传彼土,何谓礼失求野!”[10]130而且极力推崇它们的功用,即“此时国力极弱,由于上下无人。人才之兴,必由学校。我国以时文为教,万不能保其种类,非各立学堂,认真讲求声光电化之学,不能自存。”[10]82
由此可见,吴汝纶虽有“夷夏之辨”,但随着时局发展以及西学浸染,其晚年思想发生明显转向,“体用”“夷夏”已经不再是他恪守的文化“雷池”,其关于废除科举、兴办新学、培育新民诸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晚清以来冯桂芬、王韬、张之洞等倡议的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体用”思想局限,大有走出传统、迈向近代的发展趋势。吴汝纶有感于学术衰微、人才不兴,认为“吾国士人,但自守其旧学,独善其身则可矣,于国尚恐无分毫补益也。”[10]143,进一步认为“居今日而不知外交,不通西学,不得谓之人才”[10]386“目前西学未兴,人才不出,正人,憸士,同归于无用。”[10]94继而,他强烈呼吁废除科举,“改废科举一事,诚当务之急”[10]337“吾谓非废科举,兴学校,人才不兴”[10]365,“窃谓废去时文,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字取士。举世大兴西学,专用西人为师,即由学校考取高才,举而用之,庶不致鱼龙混杂。”[10]194而且意识到“盖非广立学堂,遍开学会,使西学大行,不能保此黄种。”[10]311继而,吴汝纶认为中小学教育是开民智,兴民权的基础,“小学养成德性,扩充知识,使后有国民选举之权”[9]11,“小学教育,国民之教育也,无论士农工商皆须先入小学。一国之文明分野,全自此分。中学校则教育中等以上之人,一国之文明势力,全系中等以上之人之智能。”[9]42此种培养在德力、智力、体力诸方面皆强的“新民”的思想直到五四时期依然是占据着中国文化启蒙的主流。晚年,他还应严复之邀,相继审阅《天演论》和《原富》译稿,并为两部译著撰写过序言,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社会进化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五、结语
戊戌之后,“新学”“旧学”之区分渐显,但晚清最后十年间中国思想界的变革并未如新旧称谓变更那般决绝与彻底,“西学”与“中学”依旧并行不悖。在传播西学过程中,以吴汝纶为代表的启蒙知识分子们通过著书立说、创设报馆、译书局、兴办学校,凝聚和吸引了大批改革新生力量,承担着促使新学合法化、建制化的重要角色,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传播做出了可贵探索。与此同时,受制于其自身价值观、历史观、伦理道德等方面的认知局限,晚清启蒙知识分子一方面冀望于新学以济世应变、自强保国;另一方面又在如何处理“醒华”与“兴华”的问题上受到晚清以来追求民族精神自主权这一现实诉求的影响。这种矛盾复杂的文化心理既深刻地影响了晚清社会变迁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也开启了日后延续几十年的关于中国文化价值以及中国文化之近代适应问题等诸多讨论的先河。
——吴汝纶辞官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