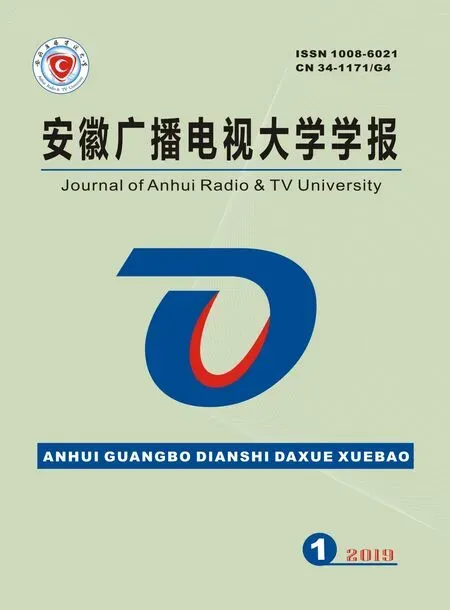曹植诗歌的悲剧意蕴
张军强
(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安徽 阜阳 236015)
曹植(公元192—232)为曹操与卞氏所生第三子,曹丕同母弟,建安文学代表人物。曹操认为曹植在诸子之中可堪重任,但曹植却“任性而为,不自雕励,饮酒不节”[1],这种个性直率、扬才露己而不加以自控的性格弱点,成为曹植政治失败的主要原因。从后来曹操“自临淄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1]337的评价可窥一斑。因司马门事件,曹植引起曹操的猜忌和反感,转而立曹丕为太子。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病逝,曹丕继承王位,旋即称帝,曹植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从此,他被迫远离了优游宴乐的贵公子生活,变成一个被限制和被打击的对象。曹丕病逝后,曹睿继位,碍于叔侄间的人伦礼仪,表面上曹睿对曹植的态度稍有好转,实质上却秉承其父之志,继续对曹植采取高压手段。公元232年腊月,曹植抑郁而死,卒谥“思”,后人称之为“陈思王”。
卢那查尔斯基在评价高尔基的文学成就时指出:“伟大的文学现象和重要的作家个人多半是、也许纯粹是社会大变动或社会大灾难的结果。文学杰作就标志着这些变动和灾难。”[2]曹植政治的失败,促成了文学的升腾。特殊的人生经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敏感丰富的精神世界,加之他笔耕不辍、“精意著作”,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使他成为屈原之后、陶渊明之前最杰出的诗人。据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统计,今存曹植比较完整的诗歌75首、赋42篇、文123篇,是建安时期作品最多的作家。其中抒发遭受迫害而忧伤、愤慨的作品,成为区别于建安时期其他作家的显著特征,是他对时代命运的慨叹,更是他对个人命运的深沉体会,彰显了文学作品的悲剧色彩。
一、“君门以九重,道远无河津”:政治理想的步步失落
曹植既是一个杰出的诗人,又是一个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人。鲁迅先生认为曹植孜孜以求于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理想的破灭,导致他否定了文学的作用。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勠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3]其上魏明帝《求自试表》又说:“窃不自量,志在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奉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3]289可见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为国家建功立业,从而名垂青史,是曹植终生的理想和追求。
曹植生活的时代社会动乱不堪。黄巾起义,董卓之祸,群雄割据,灾荒频仍,瘟疫流行,这些因素的合力,致使国家出现了曹操所说的“白骨露丁野,千里无鸡鸣”极其悲惨的状况。由于曹植深受儒家积极用世思想的影响,他极力想去改变这种悲惨的状况,加之曹操通过文治武力,统一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初步改变了国家的现状,使曹植看到了政治理想实现的希望,激发了他的建功立业的热情。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去世,曹丕继位为王,并转而称帝自立。从此,曹植的政治厄运真正来临。争储斗争的失败,对曹植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实质的影响,但曹植此时仍然抱有强烈的政治追求。
实际上,曹植越是想在政治上大所作为,其建功立业的愿望越是强烈,也就预示着他所面临的各种迫害越深重。作为一位在长期政治斗争中历练而成长起来的政治家,曹丕当然知道,以曹植的特殊身份,一旦给他建功立业的机会,将会再一次威胁到自己的政治地位。曹丕即位后,很快找理由杀害了丁仪、丁廙二兄弟,不准曹植滞留京城,不仅铲除了曹植的政治帮手,又剥夺了曹植继续参与朝政的权利,把曹植逼上了政治的绝境。
曹丕的高压手段并没有让曹植死心,即使在曹丕死后、曹睿为帝时,曹植对政治的高昂热情也没有减退,他对建功立业的追求之心仍旧坚定。《杂诗》其五说:
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3]261。
这首作于明帝太和二年的诗,抒发了曹植的忧国报国之志。开篇即点明了其报国的理想。即使“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两句有悲伤、愤慨和不满的情绪,但诗人并没有沉溺于这些伤感之中。“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慷慨激昂地抒发了诗人为国自效、建功立业的情怀。
同样写于明帝太和二年的《求自试表》,曹植的报国之志,仍然表现得十分强烈。在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情况下,他依然不想“虚荷上位”,认为自己应当效命于朝廷,立功于社稷。但是曹睿对他实施了更为严重的迫害和摧残。不但没有起用他,而且把他一贬再贬。《五游咏》描述了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抛弃后的凄凉心境:
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逍遥八紘外,游目历遐荒。披我丹霞衣,袭我素霓裳。华盖芳晻蔼,六龙仰天骧。曜灵未移景, 倏忽造昊苍。阊阖启丹扉,双阙曜朱光。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棂,群后集东厢。带我琼瑶佩,漱我沆瀣浆。踟蹰玩灵芝,徙倚弄华芳。王子奉仙药,羡门进奇方。服食享遐纪,延寿保无疆[3]263。
这首诗表达了曹植的生命意识,他以游仙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对生而无用的悲伤,抒发了不能见用的人生感慨。可见,此时曹植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同他建功立业的抱负仍是分不开的。曹丕父子给予曹植的政治迫害乃至生命的摧残,使他忧伤难堪,备感压抑和愤慨。这首诗深切地表达了曹植在屡遭迫害、忧愤郁结于胸后的心态,并以幻想的形式,表达他绝望中残存的些许企望。他的另外两首诗《远游篇》《当欲高墙行》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亦与此相近。
曹植后半生都是在频繁的迁徙和严密的监禁中挨过,他诗歌的悲剧色彩,主要表现在对其后期悲惨命运的哀吟。长期的迁徙和严密的监禁,使曹植的生活异常艰辛。《吁嗟篇》就反映了他对骨肉分离、形影相吊,羁鸟般生存状况的痛切感伤:
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终天路,忽然沉下泉。惊飙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存。飘周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3]268
这首诗全篇写的都是转蓬。写转蓬,当为自喻也。诗人以“转蓬”暗指自己漂泊如浮萍一样的生活,并以强烈的情感予以表现。“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诗人对自己没有自由、任人摆布的被动的生存方式表达出强烈的、难以承受的悲痛之情。
如果说,曹植对离京居藩、迁徙不定的生活还可以忍受的话,那么,画地为牢、处处监禁的囚笼禁锢,尤其使他难以承受。
曹丕父子政权对各诸侯王采取了事事限制、处处监视的控制方式。“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4]而曹植又是所有诸侯中被限制、监视得最为严厉的。钱钟书把曹植这种心情与李陵《答苏武书》中描写异城孤寂心情的文字做类比:“殊可断章,借申众裏身单之感。与人为群,在己无偶,吾国词章中写此情者,以曹、李两文为最古。”[5]钱先生认为曹植描写的这种孤独无依的心情非常成功。曹植的许多诗文都表达了他对这种牢笼般生存状况的悲痛:《磐石篇》中的“常恐沉黄垆,下与鼋鳖同”“仰天长太息,思想怀故邦”,《杂诗》(高台多悲风)中的“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等,都是他孤独惶恐心态的写照。
二、“不惜万里道,但恐天网张”:全身远害的悲凉心境
曹植在他的封地受到监国使者严密的监视,日常行为、交游和言语都在被监视的范围之内,他过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生活。即使如此,在黄初二年,监国使者奏曹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曹丕欲以此治曹植之罪,后因卞太后的极力阻挠,曹植才幸免于难。面对身心遭到的双重摧残,曹植无可奈何,只能在愤懑中默默承受。即使在诗歌中,曹植也变得更加小心。透过《当墙欲高行》 中的“众口可以铄金,谗言三至,慈母不亲”、《乐府歌》中的“耀漆至坚,浸之则离,皎皎素丝,随染色移。君不我弃,谗人所为”、《怨歌行》中的“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等诗句,可以看出曹植对曹丕、曹睿父子的用心,有了明确的认识,使他对传统的叔侄、兄弟之间应该持有的孝悌伦理关系产生了怀疑。对自己所处的无比危险的处境,曹植必须如履薄冰、谨慎面对,否则定会招致祸患。
这种杀机无处不在的罗网般的迫害,在他的《无题》诗中表现得非常充分:
双鹤俱遨游,相失东海傍。雄飞窜北朔,雌惊赴南湘。弃我交颈欢,离别各异方。不惜万里道,但恐天网张[3]265。
但凡无题之诗,多旨意遥深。此诗以双鹤喻人事,所喻的人事,难以作出比较准确的解释。结合曹植的经历,该诗当是写曹植和曹彪离别之时,曹植对唯恐兄弟二人再受迫害的担心,从其《赠白马王彪》一诗的序言亦可窥此意。文帝黄初四年,曹植和曹彪朝京拜谒后返回藩国,二人本想携伴而行,但曹丕派遣的监国者不准,二人被迫分道而行。曹植在《赠白马王彪》里表达了对兄弟间骨肉分离、永难聚首的悲伤和愤慨。但这首诗传递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与早期的《野田黄雀行》中的“罗网”等诗句中透露出的担忧相比,表明曹植对曹丕的阴险用心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不惜万里道,但恐天网张”,蕴藏着曹植对随时可来的迫害的忧惧,警觉的心态更为凝重和复杂,也促使他不得不用智以远祸。
曹植在其《写灌均上事令》中说“孤前令写灌均所上孤章,三台九府所奏事,及诏书一通,置之坐隅,孤欲朝夕讽咏,以自警戒也”。又,《赠白马王彪》中“苍蝇间黑白,谗巧令亲疏”,这显然是针对监国使者等人的谗言毁谤而发,尽管内心充满愤慨之情,但曹植只是把责备的矛头指向监国使者等进谗之人,而没有指向曹丕,可谓不失中正之旨。这种做法,曾经使曹丕对他的防备和迫害有所减轻。黄初六年,曹丕曾到雍丘与曹植聚饮。所以,这种做法应该不是曹植懦弱的表现。刘克庄《后村诗话》说“黄初之世,数有贬削,方且作诗责躬。上表求自试,兄不见察,而不敢废恭顺之义,卒以此自全,可谓仁且智矣。”[6]反观曹植诗歌中的那些不满和难以盛言的悲痛之语,约略可以理解其奏章中的明显阿谀之词,显然是曹植全身远祸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是建立在他对自己所处的现实境遇的深刻认知的基础之上。
三、“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稀”:人生不永的忧生之嗟
忧患意识有着深广的文化背景和非常丰富的内涵,尽管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里,面对不同的事物不同的时机,人们表现出的忧患意识各不相同,忧患意识的深刻程度存有差别,但它们却有着一个大致相同的指归,那就是对个体生命无常的忧患。各种因素对生命的损伤与人类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形成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于是,追求延长生命的长度,增加生命的密度,就成为人类孜孜以求的梦想。
曹植生活的建安时代,连年的战争和不断的瘟疫,造成人口的大量减员。徐干、陈琳、应场、刘祯等著名的文士也难逃英年早逝的厄运。曹操《秋胡行》“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 徐干《室思》“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蔡琰《悲愤诗》“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等,无不表现出对生死存亡的关注。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7]
曹植也深具此种忧患意识。由于曹植前期涉世不太深入,对生命意识的体验就显得不够深刻。这时他的“忧生”主要来自行乐游宴之后的副产品,大多是对生命无常的感伤和喟叹,就如《箜篌引》中的“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西山”。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言“平原侯植,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6]95,当针对曹植前期创作而言。到了后期,曹植受到曹丕父子猜忌和迫害不断加深,过着“名为藩王、实则囚徒”的生活。前期他慷慨豪壮的进取心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内心深处慢慢滋生了退避三舍的心理,转而向道家求助,以浇灭内心熊熊燃烧的激情和愤怒。《闲居赋》“阳春之发节,聊轻驾之远翔。登高丘以延企,时薄暮而其雨。仰归云以载奔。遇兰蕙之长圃”,《九愁赋》“愁戚戚其无为,游绿林而逍遥。临白水以悲啸,猿惊听而失条”,无不显示出曹植寻找宁静、回归自然的挣扎和努力。这正是他“勠力上国,流惠下民”的政治理想在濒临破产时,以牺牲自我久存在心的远大志向为代价与老庄无为思想合流的辛酸和无奈。在无奈之后,曹植并没有彻底的沉沦,他仍然矢志不移,其《杂诗》(仆夫早严驾)有云:“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可见,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他依然心怀忧国之心和报国之志,“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的理想之火仍然没有熄灭。
随着政治环境不断恶化和生存状况急剧变化,曹植的忧生之磋也逐渐深刻。政治同僚的被杀,自身境遇的步步跌落,使他的内心变得忧惧不安起来。惶恐不安之态在其诗文中逐渐显现。《赠白马王彪》“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曹彰的意外死亡,对曹植的心灵造成不小的打击,使曹植平时那种忧生之嗟变得深沉起来。而他的《蝉赋》则通过对蝉所处的危险环境的形象描绘,表达了自己对谗言流语的畏惧。这些忧思和恐惧,大多来源于诗人对生命意识的关切。
四、结语
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和贵公子,身处乱世的曹植,更以匡扶社稷,救天下于危难为己任。但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重重敲击着曹植的心灵,浇灭了曹植报国的梦想,使得他不得不游离于进取和退让之间,时常面临进而无路、退而不甘的尴尬处境。曹植就这样进退于儒道之间,没有儒家“舍身取义”的无畏,也没有达到屈原“向死而生”的悲壮。这种思想上的儒道互补,以及行为上的进退两难,对他的诗歌创作,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诗歌,时时表现出建功立业理想的幻灭与人生如朝露的悲凉。他的忧生之嗟从前期单纯地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转向后期对人生社会的深沉关切和深沉的忧世之思,形成强烈的忧世意识,奠定了其诗歌悲沉的色调,蕴含着巨大的悲剧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