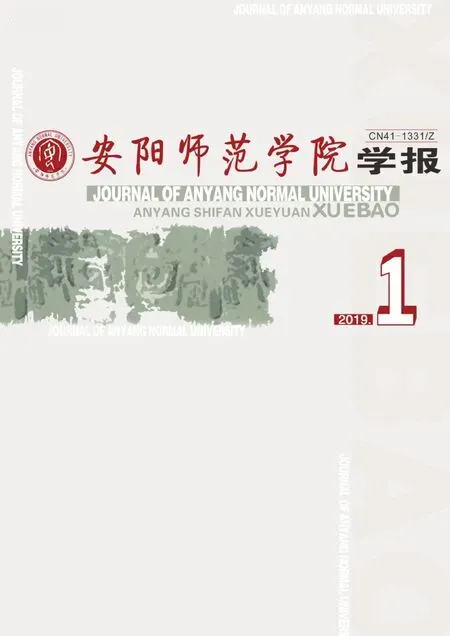五花爨弄与宋杂剧演出体制的形成
马小涵,徐博一
(1.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 2.河南博物院, 河南 郑州 450000)
关于宋杂剧的演出体制,学者有不少研究,多认为包括“一场两段”注黄竹三、延保全《中国戏曲文物通论》认为宋杂剧的演出是“三段式”,即:“‘勾杂剧入场,一场两段’,有时加杂扮,构成三段”。(见黄竹三、延保全《中国戏曲文物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第222页。)“三段说”是不少学者坚持的观点。日本学者青木正二坚持“四段说”,其引《都城纪胜》“杂剧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一段后云:“则杂剧先有艳段,次有正杂剧,而杂扮一段。如从《梦梁录》‘杂剧之后散段’语,则当为散演于正杂剧之后者。若然,则杂剧由‘艳段(一段)——正杂剧(两段)——杂扮(一段)’之四段而成,其后元杂剧之以四折为定形之体例,已萌芽于此。惟其各段所演之内容并不互相连络耳。”(见青木正二《中国近世戏曲史》,王古鲁译著,蔡毅校订,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2页。)与“一场四人或五人”。黎国韬在《古剧考原》一书中专辟 “两宋杂剧演出形态转变考略” 一章进行了探讨。并认为“杂剧一场两段的出现最有可能就是从徽宗朝开始的”;[1](P205)“一场四人或五人颇有可能是徽宗时期宫廷乐人对杂剧形式进行创新的结果”。[1](P207)但这种体制是怎么来的,是本土长期的发展,还是有其他外来因素,大多语焉不详。本文试作考证。
一、宋杂剧体制的演变
关于宋杂剧体制的分析,耐得翁《都城纪胜》中有关于宋杂剧的演出状况:
杂剧中,末泥色为长,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为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吩咐,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又或添一人装孤。其吹曲破断者,谓之把色。大抵全以故事事务为滑稽,本是鉴戒,或隐为谏诤也,故从便跣漏,谓之无过虫。”[2](P113)
耐得翁系别号,姓赵,余无可考。《都城纪胜》是介绍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于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写成该书,已是南宋晚期。其记录的也应该是南宋杂剧的情景。
这里说到“一场两段” 问题。这里的两段,一是艳段,二是正杂剧。其是否一个有机的整体呢?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多次记载北宋杂剧“一场两段”,但大多语焉不详,不知道“两段”到底是什么样。其中在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里的一段还算清晰:
复有一装田舍儿者入场,念诵、言语。讫。有一装村妇者入场,与村夫相值,各持捧杖互相击触,如相驱态,其村夫者以杖背村妇出场。毕。后部乐作,诸军缴队杂剧一段,继而露台弟子杂剧一段。是时,弟子萧住儿、丁都赛、薛子大、薛子小、杨总惜、崔上寿之辈、后来者不足数。合曲、舞旋。[3](P195)
所谓“诸军”似指“钧容直”,“为军中乐,乐人籍属军队编制,主要为皇家仪仗服务,但有时也为皇家娱乐服务”。[4](P208)当然,也有可能指“东西班乐”。
从上面杂剧主体看,“诸军缴队”先作一段杂剧;“露台弟子”则指民间剧团的艺人,接着再作一段。但从上述引用的整体一段资料看,倒也像是耐得翁《都城纪胜》中有关宋杂剧的演出状况。其间,有念诵、言语,有引戏,有两段杂剧,有杂扮,甚至还有最后的合曲、舞旋。“杂扮”在北宋时是独立的技艺品种,到南宋可能就合在杂剧的后面。可见,北宋末期,杂剧体制已经成熟。
二、五花爨弄与宋杂剧体制
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辍耕录》卷二十五“院本名目”云:
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公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国朝院本、杂剧始厘而二之。院本则五人:一曰副净,古谓之参军;一曰副末,古谓之苍鹘,鹘能击禽鸟,末可打副净,故云;一曰引戏;一曰未泥;一曰孤装;又谓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见爨国人来朝,衣装、鞵履、巾裹、傅粉墨,举动如此,使优人效之以为戏。[5](P371)
陶宗仪把院本体制的“五花爨弄”起源于北宋徽宗时期的爨人备为一说。关于爨国人在宋徽宗时期献“五花爨弄”,当今学者仁智互见,认同者认为确有其事,认为“就表演体制而言,五花爨弄的出现,实际上是我国舞台艺术发展途程中的一个转抉点”[6];对于引戏、末泥、孤装角色的出现到了决定作用并对中国戏剧具有重大影响”[7];不认同者则多纠结因为爨国在唐代已经灭亡的问题。但既然有此一说,我们就不能置若罔闻。黎国韬显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指出“虽然有学者曾指出爨人来朝的说法不可信,但五角出现的时间却未必有错”。这个论断是中肯的。事实也正如此,检索史书,我们可以得到不少佐证:
首先是宋徽宗是否见到爨国人的问题。
《云南通志》载:徽宗大观二年,(段正淳)避位,子正严嗣立。[8]
清人冯苏《滇考·段氏大理国始末》云:
徽宗大观二年,子正严嗣,改元日新文治永嘉保天广运。正严勤于政事,爱民用贤,与国主髙量成谋遣使入广南求内附,观察使黄璘奏闻许之。政和六年,遣进奉使天驷爽、彦贵、李紫琮,副使坦绰、李伯祥,贡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细毡、碧圩山诸物;又有乐人善幻戏,即大秦牦轩之遗,名“五花爨弄”。徽宗爱之,使梨园优人学之,以供欢宴,赏赐不赀。[9]
这里的“牦轩”,即犛靬。《汉书·张骞传》:“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犛靬、条支、身毒国 。”颜师古注:“自安息以下五国皆西域胡也。犛靬,即大秦国也。”
徽宗大观二年,大理国主段正严嗣位,主动内附,令宋徽宗兴奋,也颇符合其“万国来朝”的梦想。
明谢肇淛《滇略》“南诏”亦载段氏父子在宋徽宗朝的交往,云:
徽宗崇宁二年,正淳遣高泰运入朝求经籍,得六十九家以归(按乾道中,南诏使者见广南人言其国有《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张孟押韵集》《圣历》诸书)。
(徽宗)政和五年,广州观察使黄璘奏大理求欵附。七年,南诏遣进奉使天驷爽、彦贲、李紫琮,副使坦绰、李伯祥来朝,贡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细毡、碧圩山诸物。诏册其主和誉为大理国王(按《宋史》作段和誉;《南诏通纪》作段正严)。[10]
这在《宋史·徽宗纪》《宋会要·大理国》都有记载。这里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宋徽宗确实召见过爨人;第二,爨人确实曾给宋徽宗进贡过乐人,并且这些乐人擅长的是一种幻戏。
元陶宗仪说是宋徽宗因为对爨人的服饰、举动感兴趣而让宫廷优伶效法。谢肇淛则明说是宋徽宗喜欢他们的表演。那么,宋徽宗有没有可能对爨人服饰感兴趣而以之为戏呢?这也有可能。我们以唐朝的一个例子作为参考:
(唐太宗)贞观三年,其酋元深入朝,冠乌熊皮,若注旄,以金银络额,被毛皮韦,行縢著履。中书侍郎颜师古因是上言:“昔周武王时,远国入朝,太史次为《王会篇》。今蛮夷入朝如元深,冠服不同,可写为王会图。诏可。”[11]
意思是,唐太宗贞观三年时,东谢蛮酋长入朝,穿着奇特的衣服。颜师古就给唐太宗建议,周武王时远国来朝,写了《王会篇》的文章;现在蛮夷入朝,可以把他们画下来,叫做《王会图》。那么,到了宋朝时,宫廷戏剧兴盛,完全可以用表演的方式来纪念。
史书对爨人的服饰有简要描述。唐樊绰《蛮书》说,东爨乌蛮“男则发髻,女则散发,……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12]《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褁结。”[13]张增祺解释说,所谓“曲头”是指头上佩戴铜制的“弯曲形装饰”;“木耳”即系在耳上所佩的大耳环,因“原为木制,故名之”;“环铁”乃指铁镯;“裹结”大概是指其发型或发髻上多用包裹而言。[14]
谢肇淛也形容其服饰说:
男子椎髻,去须髯,佩双刀,喜斗轻死。妇女披发,衣皁。贵者锦绣饰,贱者披羊皮。乘马,则并足横坐。室女耳穿大环,翦发齐眉,裙不掩膝。男子无贵贱,皆披毡,跣足。[10]
“翦”,《说文》解释为:“翦,羽初生也。一曰矢羽。”王筠注:“翦者谓新生之羽,整齐之状也。”“睂”,古语同“眉”。
谢肇淛又记载:
广西有黒爨、土獠、沙蛮等种杂居,各据其俗。得犬方祭。有争辨,诣鬼神盟诅,直者敢前,曲者缩朒。妇人以布为袍,圆领大袖。土獠则以黒线绣布裹头,缠腰已上,皆爨种也。[10]
上述记载中可看出爨人衣着服饰颇有特点,但却未见其爱“傅粉墨”之说,则“傅粉墨”的爨人一定是爨人的优伶,用于表演节目。
爨人有“鬼主”文化。所谓“鬼主”《新唐书·南蛮传》说:“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唐樊绰《蛮书》卷一也说:“(夷人)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据此,“鬼主”的本质是“主祭者”巫师,同时又是大小部落的军事和行政首领。另外,还有“大都鬼主”“都鬼主”“大鬼主”“小鬼主”“次鬼主”之分,其中“大都鬼主”地位最高,由众部落推长而产生。由此可知,“鬼主”是一种政教合一的社会组织制度。[15]
其俗喜耍霸王鞭和刀叉舞。《白族简史》“科学文化”目说:还表演霸王鞭、龙灯、狮子等舞蹈。陆良县古名同乐县,南诏灭爨,20余万户西爨白蛮贵族被迫胁迁滇西,留滞于西爨区的平民融入彝族形成今白彝。每逢过春节,同乐白彝吹着大长号到县城舞霸王鞭和刀叉舞。[16]
爨人信奉佛教,多灵异故事。如谢肇淛记载:
夷人中有号为仆食者,不论男女,年至老辄夜变异形,若犬,或彘,或驴,于人坟前拜之,其尸即出,为彼所食。盖出白夷一种焉。杨慎《滇程记》云:百夷家畜一拨,厮鬼无形,而善噬人魂。中者越宿死,死则百夷取其尸为醢。鬼畏犬,闻犬声则逺遯不返,殆谓是耶?[10]
年老就变成异形,或者变成狗、或者变成猪、或者变成驴,从现在的科学知识来看是不可能的,大概也是一种乔装或者幻术吧。
谢肇淛又记载唐朝南诏的幻术:
唐南诏永贞间,有鸡足僧小沈者,与二僧同住一庵。小沈入城乞食,诏问:“识何法门?”小沈答云:“我能使死者生极乐世界。”诏令国中但有死者,请小沈起棺,如此十余年。有谗于诏曰:“小沈妄人也,云能超度死魂,何所证验?臣愿入棺试之。”诏如言,请小沈起棺。将至化骨之所,启棺视之,诚死矣。恳小沈求生,沈又作法,遂苏。死者悔曰:“我已生在七宝宫殿中,如何复来此?”小沈遂还旧庵,见二僧问食,二僧曰:“汝从城中来,乃不裹粮,却至此欲食耶?”小沈遂走,叩迦叶石门,门訇然中开。二僧追呼,至则石门闭矣。二僧悔恨,焚身门外。焚处生柏二株,或谓小沈迦叶化迹也。[10]
《蛮书》《华阳国志》《滇考》《滇略》记载爨人灵异故事颇多,与其佛教文化、祭祀文化、鬼文化有关。从上述对爨人文化的简单描述我们似乎可以进一步说,“五花爨弄”来自爨人,而爨人学之大秦,并且肯定也融入了爨人的文化,比如服饰文化、鬼文化等,是一种结合鬼文化分角色表演的幻戏;并且宋徽宗也让宫中的伶人学着爨人的模样表演。如果考虑到宋徽宗时期浓厚的道家文化氛围及其道教表演爱好,这种学习是顺理成章的。
所谓“弄”是耍;玩弄。早在唐代就有。史载:
杨慎诗:“逡廵乌爨弄,噭咷白狼章。”注“乌爨”,滇蛮名,唐世取入乐府,名“乌爨弄”。[17]
根据这个说法,“乌爨弄”在唐代就已入乐府。清人田雯《碧峣书院歌吊杨升庵》也提及此诗,所谓“天教老噉红槟榔,吴粉傅面两丫髻。簪花拥伎何徜徉,都卢倒吹泼醉墨。僰儿观者如堵墙,白狼噭跳乌爨弄。百斛文鼎非寻常,雷硠光焰留南诏”[18]。此中“白狼噭跳乌爨弄”出自杨慎《雨夕梦安公石张习之觉而有述因寄》一诗,原文为“逡巡乌爨弄,噭咷白狼章”[19]。文中有注“乌爨,古之乌蛮,今之猡人也。其乐谓之爨弄,唐世取乐府以为笑云”。可见爨人确实有“爨弄”之乐。如果上述资料确实,那么,即使是唐代的“弄”戏也是来自爨人。
那么为什么叫“五花爨弄”呢?
谢肇淛《滇略》记载爨人北宋时的国王段氏喜爱种花:
段氏素兴,以宋庆历中嗣位。性好狎游,广营宫室。于春登堤上多种黄花,名“绕道”“金棱”;云津桥上多种白花,名“萦城”“银棱”,今二棱河名由此也。每春月必挟妓幸,载酒,自玉案三泉遡为九曲流觞。男女列坐,斗草,簪花,以花盘髻上为饰。今花中有“素馨”者,以素兴最爱,故后人名之也。又有花遇歌则开,有草遇舞则动,素兴令妓歌者傍花,舞者对草。[10]
可以猜想,“五花爨弄”这种幻戏的特色主要是歌、舞以及幻术表演。至于“五花”,疑即“绕道”“金棱”“萦城”“银棱”“素馨”五花或者黄、白、青、红(蓝)、黑等色;其中“花遇歌则开,有草遇舞则动”本身就十分奇异。当然在表演时可能是五个人,五种角色,画五种颜色,进行歌、舞、幻术百戏、音乐、宾白的配合表演。学者认为“花”是化妆,那也是对的,就是化妆成五种花样,即五种脸谱的样子。
大秦幻术输入中国,早在汉代已经开始,到北宋时,大秦幻术应该有了更高的技术和发展。前述“又有乐人善幻戏,即大秦牦轩之遗,名‘五花爨弄’”中的“即大秦牦轩之遗”可以理解为仅仅是说幻戏是大秦余风。那么,有没有可能北宋时爨人到大秦即罗马帝国学得当地的戏剧,融入自己的文化,又转献给宋徽宗呢?按当时的情况,是有这个可能的。
其传入中国的道路也是畅通的。谢肇淛载:
僰夷之地,西南际海。海行五月至佛大国、阿育国、大秦国、伽卢国。[10]
在《滇略》里还记载爨人到达这些地方的各种见闻。当然,这说的是明代的事情。
当时,喜剧和滑稽剧作为戏剧体裁,在希腊、罗马时代早已成熟,这已被众多作品与研究所证明。爨人在北宋时期从大秦国学得幻戏的表演体制,并在宋徽宗时期进贡到朝廷是可能的,这与中国戏剧体制形成的时间也十分契合。但目前我们没有更多证据,因此,也只能推测:爨人从大秦学得戏剧角色体制并根据地域特色进行了改变,进而献给了宋徽宗,从而又在糅合了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完善了北宋的杂剧体制。
波耳的《支那事物》说:“中国剧的理想完全是希腊的,其面具、歌曲、音乐、科白、齣头、动作,都是希腊的。……中国剧的思想是外国的,只有情节和语言是中国的而已。”[20]这有点过分了,但说中国的戏剧角色体制引自希腊(或者说东罗马帝国)倒是可能的。
三、小结
宋徽宗时期,杂剧已经为社会所承认,有些已经综合了歌唱、音乐、舞蹈、故事等艺术形式,以演唱曲子来叙事表情,甚至成为“百艺之首”;进一步说,其特点就是“将人物妆演、故事叙说、谐谑科诨融合一体”,并且角色上已经有了明确的分工。这从河南的考古资料中也可以看出来,杂剧表演体制已经形成。其四人五人分角色化妆表演的形式并非来自前代表演形式的自然发展,而很可能是受到南方爨人表演的直接影响和希腊戏剧表演形式的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