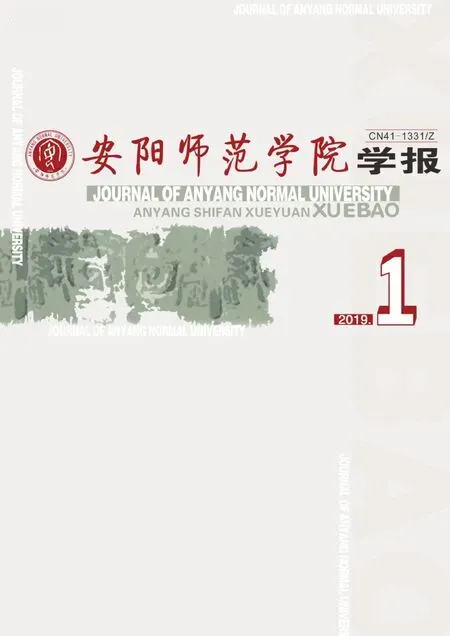希利斯·米勒的解构主义语言观研究
陈 聪,王 玫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
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学理论家,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著作等身,其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不断地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开拓新的思路。纵观米勒的学术生涯,从新批评时期的起步,到意识批评时期的崭露头角,再到解构主义时期的理论的成熟,进而进入述行理论阶段的深入探讨,其学术纵深式的发展历程彰显了他学术思路的灵活与研究视阈的广阔。目前国内对于米勒的研究多聚焦于其解构主义阶段的文学理论,主要采取历史梳理和再阐释相结合的方式。此种研究模式一方面确实完整呈现了米勒解构主义阶段的研究思路的完整性,并且在一定深度上呈现了米勒文学理论的学术价值;然而,从另一个侧面观之,也出现了米勒学术研究的众声喧哗的局面,客观上造成了米勒学术研究过于发散的事实,使米勒的解构主义阶段的研究成果缺乏一个统一的原点,在追求研究深刻性的同时又解构了米勒研究的整体性。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任何文学理论都不可避免地要处理语言和其他诸多构成要素的关系,语言作为文学的组成部分在米勒的批评实践中具有提纲挈领的价值。从米勒的研究初始到后期的成熟和深入,米勒一直将文本置于研究的首位,将对文本的细致阅读作为其研究的主导性策略,在其研究的过程中,一直在探讨那种“把文学作品看做对依据的质疑,建立在语言之外、自然之外以及人的心智之外的一种永久的形而上学基础的基础之上”[1]的做法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本文试图探讨米勒解构主义时期的文学语言观,在对米勒解构主义阶段的文学理论进行梳理和探讨的基础上,呈现其隐于其后的逻辑之线,实现米勒文学理论研究的系统化和清晰化。
一、米勒解构主义语言观的内涵——异质性
在西方的传统语言观中,语言与现实的关系被认为是所指与能指所构成的稳定关系,即语言总是指向一个稳定的外部现实。这种语言观的实质是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映。该语言观认为,语言由三种要素共同组成,即逻辑、语法和修辞,修辞受制于语法,语法受制于逻辑。语言在指涉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了语法意义与修辞意义,因为逻辑是最终的统摄性力量,所以修辞意义是语法意义的派生,从属于语法意义,换言之,后者压制前者。语法意义/修辞意义之间产生了一种二元对立。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一个比喻性结构中,出现了喻旨和喻体的关系,而二者最终服务于一个明确的意义的传达,即逻辑的清晰性和有效性。在这种语言观的影响之下,艾布拉姆斯等传统的文学理论家认为不同的作家之间尽管存在着差异,但却最终统摄于一个共同的源头,即文学无论如何发展,批评家总能在其所谓的源头上找到其发展的动因。寻求某种连续性和一致性是文学批评工作的旨归。米勒认为,语言不应该被看成是思维和自然之间的一种直接的镜像式的反映,它所传达的并非是先于它所存在的、在本质上不依赖于它的某种外在的现实。换言之,米勒与解构主义的观念相同:语言以及由语言所构成的文学作品不是反映了或摹仿了什么超出语言之外的现实,而是建构了现实。这是一种反形而上学的语言观,即异质的语言观。语言不再是充当工具去被动地呈现某种超语言之物,相反,语言是人类生活的构成性要素,在本质和源头上是隐喻的。具体地说,在语言的内部,语法意义和修辞意义不再是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相反,由修辞所产生的修辞意义总是在不断的颠覆和解构由逻辑和语法所产生的语法意义。 “对文学或哲学文本中的修辞作用的重视是必需的,但不是因为修辞语言提供了从‘字面语言’向‘虚构语言’的一种轻松的过渡。修辞是模仿的根本性手段,比如用在确定实体性的同一性或者通过隐喻来类比上。对修辞作用的重视是必需的,这是因为任何文本的一致性(heterogeneity)在修辞的回荡(fluctuation)中表达了自身。修辞就是指涉与对指涉的解构之间的战场。”[2](P158)相较于传统的同质语言观来说,米勒的异质的语言观在对语言的本质的认识上走得更远,前者虽然看到了语言的隐喻性的冰山的一角,但最终将语法意义和修辞意义归为一种辩证的统一,并以前者压制了后者,周全了逻各斯的中心地位,从而将文本的意义引向了文本之外的现实,而后者则坚定地认为修辞意义对语法意义的颠覆和解构使语言指向一个超于自身之外的稳定的现实成为了一个神话,米勒认为这种对语言的指涉与对指涉的解构并存在语言之中的现象构成了语言的异质性本质。语言的形而上学使用只不过是对这种语言异质性本质的遗忘。
二、语言异质性的四个层面
纵观米勒的论著,他主要从四个层面分析了语言的这种异质性:词语的层面,语句的层面,文本的层面和作品与其源头的关系层面。
从微观的语言层面到宏观的作品层面的路径彰显了米勒解构主义批评策略的思维惯性。首先,米勒认为对词语的追根溯源会发现词语的源头的差异性。任何一个词语都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源头。词语的单义现象源自于人们在对词语日常使用中源头的遗忘。事实上,所有的词语都是自我分裂的。以“寄生物”(parasite)这个词为例。米勒认为: para-是一个双重对立的前缀,同时能指附近和远处,相似和差异,外部和内部。某种家庭组织内部的同时又是其外部的事物,某种同时既是一种分界线、阈限或边缘的此侧又是超出这些范围的事物,在身份地位上既平等又从属或依附,驯顺,如关于宾主、奴隶与主子的关系。而且,以para-表示的事物不仅同处于内部与外部分界线的两侧,而且它就是界限本身,亦即一种联系着内部与外部的具有渗透性薄膜的屏帘。它使内部与外部彼此混淆,让外部得以入内,让内部得以外出,使其一分为二又使其合二为一。[3]词语这种自我分裂的性质导致了词语只能在不停的交换关系中获得自身的意义,而这种意义的获得也是一种不稳定状态,因为词语从本质上说永远处在一种矛盾运动之中,没有片刻的停留,这意味着,词语稳定的指涉只能是人们暂时得到的一个幻像。
第二,异质性存在句子的层面存在。既然每一个词都包含着分裂的源头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源头,那么由词构成的句子、由句子构成的作品必然是分裂的,而不是统一的,必然是复义的,而不是单义的。在句子的层面上,异质性表现为一个句子的意义从来不是由自身所决定的,而是在与其他句子的关系中得到呈现。换言之,一个句子是寄生在其他的句子之上,是不断地在各种新的关系中得到呈现的,所以,一个句子的意义也是不确定。德里达曾经分析过著名作家马拉美的《模仿》中的一个句子:“不到一千行,那角色,那读的人,会立刻理解那些规则……”
德里达阐释了这个句子的意义的不稳定性,其实也就是句子自身所具有的异质性。德里达认为,句子找那个的“那读的人”可以视为“一般的读者”,也可以理解为“那个角色”。如果按照第一种理解,这个句子可以解释为:“不到一千行,读者对角色进行阅读,可以立刻领会那些规则”。如果按照第二种解释,则可以产生这样的解释:“不到一千行,那角色,也是那阅读的人,可以立刻理解那些规则”。由此可见,这个句子本身并没有稳定的所指,句子的意思是在具体的阅读语境中,在一定的阅读关系中发生的,而不是一个武断的、决定性的阐释所能敷衍了事的。不论在在语言的内部还是语言的外部都不存在任何可以使它自我统一的基础或中心。语言的语法意义和修辞意义无论是在词语的内部还是在句子的内部都处于一种对抗式的关系之中。米勒在《语言的时刻》中认为:“对立的一方玷染了另一方,越过了双方的界限而进入了对方的领域中,阻止清晰的理解或者清晰的选择。”[4]
第三,异质性存在于作品的文本层面。文本是由语言组成的,语言从词语到句子都是异质的,那么,文本当然是异质的。对于一部叙事作品来说,米勒认为,从作品的结构到人物形象再到作品中种种意象的运用,都是异质的。
首先,米勒在细读结构主义经典叙事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反叙事学”(ananarratology)。结构主义叙事学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理论基础,集中探讨了叙事如何得可能以及解读叙事如何进行的问题,其中心要旨是力图在研究叙事文本诸多组成因素的基础上,呈现叙事文本的稳定的结构,并探索其内部诸要素运行的规律。结构主义叙事学把叙事文本内部诸要素的运行以线条的形象加以总结和概括,认为叙事文本内部诸多要素的协调运作最终指向一个稳定的所指,而沿着这些叙事要素的运作和探讨最终所形成的线条意象必将成功展示文本的意义,到达那个所指。所以,对于结构主义叙事学来说,叙事的意义在于以一定的叙事形式重现某种“不在场”。米勒认为,结构主义叙事学对叙事诸多要素进行的研究是全面的、敏锐的,但是,其通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暗示对于叙事特征的详尽描述可以解开叙事线条的复杂症结,并可以在灿烂的逻辑阳光之下,将组成该线条的所有线股都条理分明地展示出来。”[5](P48)米勒认为,长久以来叙事学所认为的叙事的线条型结构不过是一个幻像而已,对叙事的所谓的科学性探索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叙事本就是对不可叙述之事的叙述;传统的叙事所认为的叙事线条是建立在重复的基础上的,但是,每次叙事都是建立在对原有线条的扭曲的基础上的,都只是“大致相同而非完全相同”[5](P77),包含着潜在的模糊性和非确定性。同时,由于语言是异质的,处于异质的双方互相颠覆,这导致任何话语都是“尼采式的重复”,是在与其他话语的交缠而不是重合中得以显现自身的,所以,任何一个叙事都是从一个大的叙事中切割出来的一个部分,倘若按照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线条形象进行追溯,叙事将会永无止境地回溯下去,难以穷尽其源头。这样,叙事就从一个有开端、中部和结尾的线性结构变成了一个多重、开放、断裂的结构,从而使叙事的逻各斯不再可能。沿着叙事的线性结构解读叙事文本,获得作品意义的行为也随之成为一场镜花水月。
在《小说与重复》中,米勒以康拉德的小说《吉姆爷》为例探讨了叙事文本结构上的异质性。小说主要写的是吉姆从在远洋商船队上接受训练开始,后来到帕特纳号上担任大副,期间因为沉船事件而弃船逃跑,来到太平洋地区工作,进入到帕图森地区,最后牺牲的故事。总的来说,整个故事是以时间为顺序安排的。情节之间的发展形成线性的结构。但是,这部小说所采用的是多视角叙述。有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第一人称人物叙述,其中包括了马洛的叙述、吉姆的叙述、船长布莱尔利、切斯特、斯坦因、船长布莱尔利等等。多人称叙述本身就是一种不统一的叙述,因为每一个人物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进行叙述故事的,因为视角不同,有时对同一故事的叙事甚至是截然不同的。“故事的许多部分出自吉姆对马洛的叙述。在这些叙述中,读者可以发现吉姆力图用明确的语言来解释他的体验,马洛对这一自我解释重新加以解释,然后马洛的听众有暗暗对此加以解释。”[5](P36)“在马洛的叙述中,有许多次要的角色……他们在故事中叙述了个人的想法,他们作为对吉姆不可替代的观察视角存在于马洛的视角中,他们是吉姆部分故事的源泉,并提供了对它种种不同的评价方式”[5](P37)同时,每一个人物都会有自己安排故事的顺序,这意味着,每一个故事的叙述其实是被重新安排的,相对于整个故事而言,这是异质的、矛盾的、不统一的。“同样确实是事件的线性发展顺序,当它有众多的叙述者显现在读者面前时,它已从根本上重新组合,偏离了事件实际发生时的实际顺序。”[5](P39)由此可见,整个故事其实充满了不统一性。作者着意以看似矛盾、多元的方式安排故事,正是为了让故事显得众声喧哗,从而营造一种空间立体感。
其次,米勒认为在一部小说中,人物的形象也是异质的。在《小说与重复》中具体分析了康拉德的小说《吉姆爷》中的异质性。米勒认为,这部小说是由各种不同的因素所过程的,而每一个因素都是矛盾自反、互相解构的。从人物形象来说,主人公吉姆的形象就是多元异质的。一方面,吉姆崇尚荣誉,渴望出人头地。他从心底里钦佩勇敢者,渴望成为英雄。在帕图森岛上他与当地的恶势力与海盗进行斗争,保护了岛上的土著人,赢得了当地居民的尊重和爱戴,这是他被尊称为“爷”的原因。在帕特纳号上当大副时,他对船长和水手面对危险不顾乘客的安危弃船而逃的行为表示不齿。这些都表明他的正义感和优秀品质。但同时,他身上还有另一种完全相反的因素。在帕特纳号即将沉船时,吉姆虽然对船长和船员弃船的行为感到不齿,但是他自己也抛弃了乘客,独自上了救生艇。对他来说,这是卑鄙的、不能容忍的、与自己恪守的英雄主义截然相反行为。这说明,在吉姆的内心深处盘桓着某种阴暗的东西。这是吉姆性格中截然相反却又真实存在的两种相互抵抗、彼此矛盾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米勒认为吉姆的形象是异质的,多元的,二重的。
再次,在小说中充满着各种意象,这些意象也是内在矛盾的、二重的。在作者对这些意象的异质性的处理中蕴藏着《康拉德》这部小说的意义。“这种隐喻(或者说‘象征性’)的模式从整体上看,意义同样显得模糊不清。”[5](P42-43)“它们中没有一个堪称初始因,能成为其他段落赖以解释的基础。《吉姆爷》正像一本词典,一个词条将读者引向另一个词条,后者又将他引向另一个词,然后又回到第一个词,构成了一个无限的循环圈。”[5](P44)在小说中,白与黑、白天与夜晚、可见与不可见等充满矛盾的意象互相纠缠在一起,成为小说异质性的一个特征。
第四,在作品与其源头的关系问题上,米勒一反传统的文学观,认为作品不是在重复其源头,相反,一部作品是在颠覆其传统和源头的基础上得以存在的,这样文学史不再是线条型的结构,相反,是断裂的、多元的,简言之,异质的。词语的内部的开裂意味着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不是自在自足的,而是与其他的事物相伴而生、依附于别的事物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寄生的,都是寄生物。一个句子是寄生在其他的句子之上的,一个文本是寄生在其他的文本上的。既然一种话语文本是寄生性的,是在吸收以前的文本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旧话语文本和新话语文本的合成体,是由多种话语成分构成的,自然就不是统一的、明晰的,而是矛盾的、模糊的。“任何一个‘单一的因素’,都远非是明确的它所是,而是它内在自我分化,重新回到寄生者和寄主的关系中,在那里它是其中的这一端或那一端。”[6]在语言的“异质性”的基础上,米勒不仅注意到了文本内部的不一致,而且注意到了文本和文本只之间的既相似又相异的矛盾、多元的关系,从而打破了以艾布拉姆斯为代表的传统批评家所认为的文本的意义必将指向一个统一的源头的观念。米勒认为,无论在语言之内还是语言之外,人们都无法找到一个完全是自我统一的意义源头。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并不是如传统批评所言是建立在一个永恒固定的基础上,相反这些作品“保持着顽固的异质性,它们很难被同化,抵制着被辩证的综合。”[7]从一个作家与其传统之间的关系看来,作家也不是在维护、重复其传统,而是在不断的修改、颠覆、破坏这个传统。比如,一旦小说经由作家创作完毕,进入读者的阅读过程,那么就会出现不同的阐释和解读,所以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时,一部小说也不会与作者的其他小说在风格、主题、结构等方面完全一致,尽管有时在作家的创作过程中会使用相同或相似的词语,类似的情节,但这些相似之处绝不能互相替代。再将一位作者投入进文学传统进行分析。文学史编纂一个惯用的方法就就是将一位作家归入某一个传统或流派,其基础就是被归入一类的作家之间都分享了某种相似性:或是是主题,或者是语言,或者是题材等等不一而同。但是,被归入该流派的每一位作家其实都是各异的、不同的,都在不同程度上瓦解了该流派的存在。所以,文学史上有很多关于同一位作家被归入不同流派的公案。这意味着“背景关系并不能完全决定写于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的作品中重复活动的方式。”[5](P25)文学在对其父辈传统的扼杀中实现了自身的繁衍和发展。
三、米勒的解构主义的独特理论思路
今天的学者在探讨解构主义以及与其相关的诸多问题时,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是一个不能淡描的关键人物。对于米勒来说,与德里达的共事成为其解构主义的渊源和背景。然而,正是大多数学者对于“渊源”、“背景”等词汇的过分强调,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过分解读米勒解构主义和误读“异质性”的事实,学者们在单一强调解构主义反传统、反逻各斯等的同时,使米勒的解构主义变成了德里达解构主义在美国的“分支”。实际上,米勒的解构主义从提出之始就已经蕴含了他所一贯秉持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正是相对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而言的,换言之,米勒的解构主义具有自身的特点。
首先,米勒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有着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对语言及其本质属性“异质性”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米勒的解构主义是一种彻底的解构主义,是一种区别了西方传统文学观的解构主义的文学观。如前文所述,在语言的异质性基础上,米勒从词语、语句、文本和作品与其源头的关系层面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文学观进行了全面的批判。米勒的解构主义的彻底性主要是表现在与文学理论家瑞德和哲学家海德格尔所主张的语言观的对比中。米勒认为二者的语言观相较于传统的语言观有很大的进步,他们明确地阐释了语言与其存在的关系的断裂。但是,从根本上说,二者的语言观未能完全脱出西方形而上学的困境,因为二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深信“存在”这个源头的真实存在,从而保留了语言复现这个存在的可能性。瑞德在其著作《被颠倒的钟》(The Inverted Bell)中认为:“每一首诗歌回忆起与其源头的分离,并且它参与了对‘原初命名’(inaugural naming)的越界行为。”[2]米勒认为,瑞德对诗歌源头的分离的承认事实上是预设了其源头的存在,这与德里达运用散播、游戏、延异、踪迹等关键词阐述源头的虚无不可等量齐观。瑞德的语言观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很相似,二者虽然都认为人们无法直接到其源头,但通过词语的比喻性运用可以进行指涉,在瑞德那里表现为“对原初命名的越界行为”,在海德格尔看来则是“解开存在之谜”。这实际上是对语言的工具性运用,并没有克服形而上学的概念模式,都预设了某种超越于语言之外的、独立于语言的存在。而在米勒看来,并不存在所谓的“源头”和任何超越语言之外的存在,人们的一切阅读行为都是依靠语言进行的,所有的“源头”都存在于语言之中,而语言是异质的,不指向稳定的所指,所以一切“源头”都是语言的幻像。
第二,米勒的解构主义在解构其本源和逻各斯,消解了文本的稳定的所指的同时,又并非如人们简单地设想的那样,将文本变成了一堆毫无意义的符号。事实上,长期以来,随着米勒和他的解构主义的传播,很多学者对于解构主义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解的。这主要表现为,国内外的学者在阐释米勒的解构主义时,过分地强调了解构主义对于原有的文本和文化破坏的一面。他们或者忽视了米勒的解构主义所强调的文本的“自我拆解”,即由于文本语言的“异质性”,所有的文本都具有一种潜在的“自我解构”的性质,这意味着,由语言所构成的文本一旦形成,就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中,由此观之,“解构”一词在米勒那里其实是指文本本身的状态,而非一种由外力所施加给文本的暴力行为。对文本的“自我拆解”的性质的界定可以通过米勒在意识批评时期和解构主义时期使用“布匹”这一意象的不同阐述中得以呈现。在意识批评时期的论著《托马斯·哈代:距离与欲望》中,米勒认为文本是词语的肌理结构,文学研究者从文本外部将其结构打开,呈现出文本的内在的“佩内罗蒲之布”的线条,或者重新编织它;而在解构主义批评的论著《小说与重复:六部英国小说》之中,米勒再一次使用了“佩内罗蒲之布”这个比喻来指代文本,不同的是,米勒不再认为像布匹一样的文本是依靠批评家的外在力量的介入而被拆解的,他认为文本的解构不是由读者的主观性的阐释而形成的,而是由文本自身控制的。这种对同一比喻的不同运用恰如其分地说明米勒对于文本意义不确定性的看法是从文本的内在构成要素出发,是建立在对文本性质和语言本质属性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国内外学者对米勒的解构主义的另一个误读是关于解构的与建构的关系问题。很多学者倾向于将解构视为一种反传统的、颠覆的力量,导致一些学者诘难解构主义批评是“语言的狂欢”或者“语言的游戏”。而事实上,在米勒看来,“解构”与“建构”应该是一对互为表里的概念。米勒在与中国学者张江教授的通信中澄清了对于“解构”(Deconstruction)一词的看法。米勒认为,“解构”一词是德里达在海德格尔的“Destrcktion”之上创立的,兼有“否定”(de)和“肯定”(con)两种含义。所以,“解构”作为一种思维的方式,其目的是要打破西方固有的二元对立传统,在表明文本已经自我拆解的前提下,重新构建起文本的意义和结构。换言之,“解构”是重建,而非破坏。较之于前者,后者仅仅是一种手段和方式。这一点可以从米勒的批评实践中管中窥豹。他一直强调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应该“回到文本”,即通过细致的阅读,回到文本中的语言的
“异质性”上,循着语言的“自我拆解”之路为文本构建新的意义。
四、 结论
作为美国解构主义的旗手级人物,米勒教授正是以语言的“异质性”为根基,构建自己的解构主义文学观念的。可以说,“异质性”是米勒解构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也是其进行文学批评实践的最终理论归宿。米勒通过对经典作品的“解构主义”式的阐释,不但更新了人们对于经典作品内涵的认识,同时也进一步夯实了语言“异质性”的观念,对西方二元对立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拆解。米勒的文学批评实践之路不仅仅是一条反传统的道路,更是一条富于创造性的道路,是一条充满了严密的理性思考的文学批评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