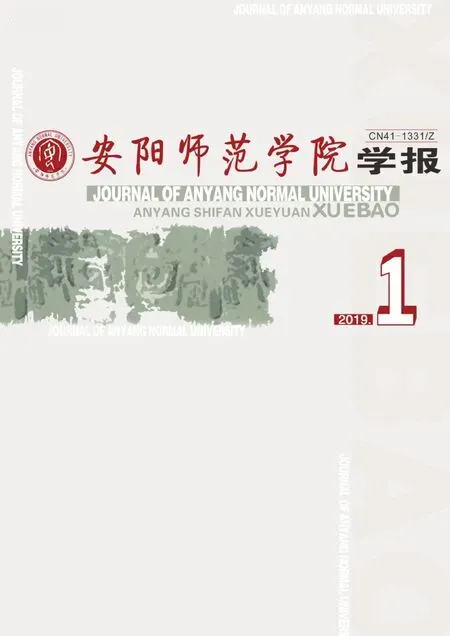闻一多的艺术思想探赜
马晓君
(云南师范大学 中文系,云南 昆明 650500)
一、闻一多关于艺术的目的、价值的观点
(一)闻一多对于艺术的目的的观点
关于艺术的本质、定义到底是什么,闻一多先生未曾做过专门的探讨,我想非要给一多先生关于艺术的本质、定义做一个解释也过于牵强。不过他强调的是艺术的非营业的目的。闻一多先生对于艺术的目的的观点主要是通过分析电影因为以营业为目的而非艺术来说明艺术的非营业目的的。他说:“他们除了激起你的一种剧烈的惊骇,或挑动你的一种无谓的,浪漫的兴趣,还能引起什么美感吗?哎!这些无非是骗钱的手段罢了。艺术假若是可以做买卖的,艺术也太没价值了。”[1](P118)闻一多认为电影不能归为艺术,根本原因就在于电影的生产者们无不怀着营业的目的性,而“营业的人只有求利的欲望,哪能顾到什么理想?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迎合心理。”[1](P118)他们的目的就是采用各种各样的电影表现手法让观众心生刺激、引发笑点和泪点或者是制造一种虚幻的、理想的世界,让人们暂时陶醉其中无法自拔。既然电影所做的一切努力是为了更大限度地增加营业收入,以达成盈利的目的,那么它就不是艺术。由此可以得出真正的艺术是不以盈业为目的的。正所谓:“艺术是一项人文事业,它不是降格以求来适应社会趣味和赶潮追风,也不在于舍本逐末地参展、获奖、入会,攀附炒作更是南辕北辙。”[2]
(二)闻一多关于艺术的价值的观点
在闻一多看来,艺术的核心价值在于能给人以心灵最崇高的快乐。他说:“艺术的快乐虽以耳目为作用,但是心灵的快乐,是最高的快乐,人类独有的快乐。”[1](P117)正如欧阳修所言:“有暇即学书,非以求艺之精,直胜劳心于他事尔……学书不能不劳,独不害情性耳。要得静中之乐,惟此耳。”[3](P286)闻一多还认为快乐应该是有所区分的,有普通的快乐、高尚的快乐、灵魂的快乐、自由的快乐和有束缚的快乐等。他并非反对个人追求快乐,相反,他觉得快乐是生活唯一的、真正的目的。他关注的是人们追求快乐的方式,他说:“禽兽的快乐同人的快乐不一样,野蛮人或原始人的快乐同开化的人的快乐不一样。”[1](P117)正是因为对快乐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闻一多才特别强调艺术给人带来的快乐才是最高尚的快乐。因为艺术的快乐是心灵的快乐、灵魂的快乐。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快乐的原则是应该建立在不妨碍别人快乐的基础上。为此他举例说:“盗贼奸淫,未尝不是做者本人的快乐,但同时又是别人的痛苦,……今日盗贼奸淫之快感预为明日刑法制裁之苦感所打消矣,所以就没有快乐了。”[1](P117)而艺术给人的快乐是不会妨碍他人的快乐,精神的快乐诚乃真正的快乐。闻一多先生谈论艺术的价值时,不惜花费大量精力对快乐的类别、人们追求快乐的方法、各种方法所追求到的快乐的区别以及追求快乐的原则做了面面俱到地分析,正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只有艺术给人带来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的观点。
二、闻一多关于艺术的灵魂的观点
(一)艺术的灵魂——内涵的思想和精神
关于艺术的灵魂,他如是说:“内涵的思想和精神便是艺术的灵魂。”[1](P119)所谓内涵的思想就是指一件艺术作品要能传达或者是象征着一种深厚的、崇高的、能给人以精神营养的力量。灵魂对于艺术正如水对于鱼儿,翅膀对于鸟儿、氧气对于人类一样重要,没有了灵魂,艺术便成了“零余者”。 要知道“艺术不是仅仅迎合和愉悦人的感官,它更要触及人的内心,要启蒙和启迪,要提升和塑造,这才是艺术的真正使命。”[2]艺术的这种精神力量不是别的,它正是一种春风化雨般的、潜移默化的、能慰藉我们平庸的心灵的、使我们忘却世俗的烦恼的力量。你看不到也摸不着它,然而它就在那里召唤着一颗颗心灵,这就是艺术的灵魂。闻一多非常强调内涵的精神的重要作用,其实是注重艺术对人的心灵的塑造作用。正如叔本华所说:“任何小说,要成为一部高雅的作品,往往对人物心灵世界的描述不惜花费大量笔墨,而人物的世俗生活则显得不那么重要;二者间的这种比例,为人们提供一种判断任何小说属于哪类作品的方法。”[4]叔本华把是否对心灵进行深刻的刻画、揭示作为判断艺术作品好坏的一个参照标准,也是为了强调艺术应该具有内涵的思想和精神。总之,艺术的灵魂就是通过表现那些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的事物以唤醒那些处于沉睡、黑暗、堕落状态的人们,给人以取之不尽的精神营养的一种内涵的精神。
(二)艺术的灵魂的实质
闻一多认为:“艺术品的灵魂实在便是艺术作者的灵魂。作者的灵魂留着污点,他所发表的艺术亦然不能免相当的表现。”[1](P119)也就是说,任何艺术的灵魂一定是反映了作者的灵魂。所谓 “音之起,由人心生也。”[5]、“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6]如果艺术家没有优美的灵魂,那么反映他内心的艺术如何能幸免于难。闻一多所强调的艺术的灵魂正是这种艺术家的灵魂。
艺术家的灵魂既然如此重要,那么艺术家要如何才能获得这样的灵魂呢?闻一多认为:“艺术作者若是没有正当的人生观念,以培养他的灵魂,自然他所发表的或是红男绿女的小说,或是牛鬼蛇神的笔记……再也够不上什么高洁的内容了。”[1](P119)艺术家应该时刻保持正确的、高尚的人生观、价值观,才能为灵魂的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纯正的、高尚的养料。正如清代书论家朱和羹说的那样:“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故以道德、事功、文章、风节著者,代不乏人,论世者慕其人,益重其书。书人遂并,不朽于千古。”[3](P309)闻一多先生正是强调这种由内心逐渐积累而产生的、而不是由外界强行输入的艺术家品性对于艺术灵魂的决定性作用。
三、闻一多关于艺术的表现方式的观点
(一)重象征、轻写实
关于艺术的表现方式,闻一多曾直言不讳地说:“写实主义正是现代的艺术所唾弃的,现代的艺术的精神在提示,在象征。”[1](P118)为了很好地说明这个观点,闻一多先生用电影和戏剧艺术作比较。他认为电影之所以不是艺术,是因为电影的表现手法太过于写实,电影总是不厌其烦地力求在一个有限的场景内融入各种各样的元素。比如电影总是乐于表现由数万人马组成的一次次大规模的、惊心动魄的、叹为观止的战争场面,这样的电影似乎自以为找到了自己的“艺术真谛”,其实它们恰好失去了艺术性,因为它无时无刻不在用它自己的写实性的语言代替观众的想象,这些应接不暇的荧幕形象挤占了我们的大脑,根本用不着观众发挥想象的翅膀,这就是电影过分写实而使它与艺术失之交臂的缘由。然而,戏剧之所以能成为艺术殿堂的一员,就是因为:“理想的戏剧的妙处就是那借提示所引起的感情的幻想。”[1](P118)戏剧的表现方式更注重象征性,所以能给以读者最大限度的暗示性、启发性和联想性,一部经典的戏剧能呈现一个多维的、深广的艺术世界。这也就是闻一多先生强调艺术象征性而轻视写实性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而,闻一多本人在艺术实践中也确实身体力行地应用象征手法。首先,他在各种文艺评论中反复强调象征、提示的重要性。在《论<悔与回>》中,他说:“明澈则可,赤裸却要不得。这理由又极明显。赤裸了便无暗示之可言,而诗的文字哪能丢掉暗示性呢?”[1](P165)认为诗歌应“有不可捉摸之神韵”[1](P156);其次,在新诗创作中认真贯彻象征之法。据统计,他的多首新诗中,应用了象征的表现手法的诗占比大于三分之一。其中代表作《死水》、《红烛》更是象征手法的成功应用之典范,前者用“死水”这一自然景物象征军阀统治下腐败不堪的社会,后者之“红烛”则象征着他的人生之追求。他大力提倡并应用于创作中的象征手法不仅使它的创作大大成功,而且还为中国新诗发展做了很好的表率。
(二)艺术表现一定要注重形式
在闻一多关于艺术表现方式的思想中,注重形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认为:“美的灵魂若不附丽于美的形体,便失去他的美了。”[1](P125)从他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好的艺术应该具有灵魂;艺术的灵魂、内涵必须借助好的形式才能更大限度地体现出来。据此,他曾大胆地批判泰戈尔在艺术方面不足以引人入胜,原因就在于泰戈尔的诗歌不讲究形式,所以他认为泰戈尔只能算个诗人而不能称之为艺术家。或者只能算是个哲学家,“他的艺术实在平庸的很”。他反复强调形式的重要性,“但是我不能相信没有形式的东西怎能存在,我更不能明白了若没有形式艺术怎能存在!”[1](P160)。他不仅仅认为形式是艺术得以存在的载体,更是万事万物得以存在的载体。闻一多先生对于形式在艺术中的重要地位的看法恰好可以用西方文论家桑克蒂斯关于艺术形式的观点来阐释:“如果要在艺术的长廊中置一雕像,就在那里放上形式,盯住它,研究它吧,原理会从那里产生出来的。在形式的前面,存在着创造之前的那个东西:‘混乱’。当形式出现的时候,美学才出现。”[7]闻一多也确实践行着这一原则,形式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得很是明显,尤其是他在新诗创作中追求的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更是体现他的艺术形式的典型代表。形式是闻一多十分强调的一种艺术表现方式,他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也努力践行着这一原则。
闻一多关于艺术的思想没有进行系统的理论探讨,但是通过分析研究他的相关的文艺评论,我们不难发现他对艺术的目的、价值和功用、灵魂以及艺术的表现方式等多方面都有精妙独到的见解,了解闻一多的艺术思想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他的文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