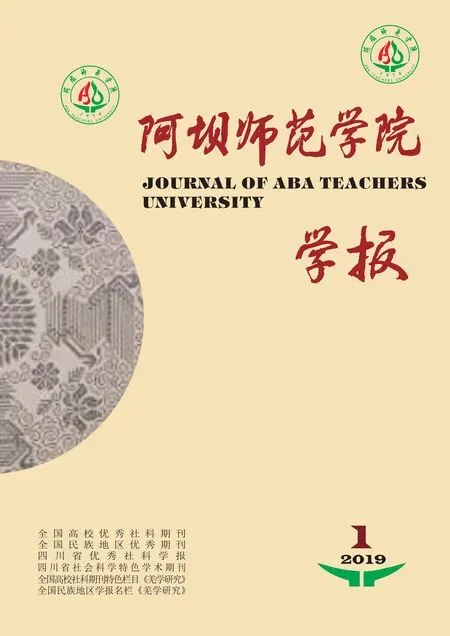明代《左传》学研究综述
王子初
以往研究对“《左传》学”虽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界定,但综合来看,包括《左传》源流和《左传》解经两大部分,具体包括:《左传》的作者、《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左传》的性质、《左传》的授受以及《左传》的解经体系等内容。《左传》学史的奠基性著作,沈玉成的《春秋左传学史》把包括对《春秋》大义解释的经传学著作,也视作春秋左传学史的重要部分[1]。明代《左传》学是《春秋》学史的重要环节,也是理学和朴学两种学风衔接的载体。明遗民和四库馆臣的消极评价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使得这一领域前人研究稍显不足。近20年来相关论著逐渐增多,主要包括整体研究和个案研究两方面。具体来说,可以分为对明代《左传》学是否空疏的研究、对明代《左传》学考证和义理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左传》经学以外价值的发掘的研究。
一、 对明代《左传》学定性的研究
传统对明代《左传》学的研究是从属于对明代经学空疏的反思基础上的,以明遗民学者的反思以及《四库总目》的评价为先导和价值规范,如顾炎武说:“秦以焚书而五经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经亡”[2]9。“明人之说《春秋》,大抵范围於胡传。其为科举之计者,庸滥固不足言。其好持议论者,又因仍苛说,弥用推求,巧诋深文,争为刻酷,尤失笔削之微旨。”[3]231大体从空言宋学义理和为附庸八股取士需求而把经学实际含义弄得支离破碎两个角度进行批判。这样的认识在今天的明代《左传》学研究中具有很大影响。代表性的通论著作中,沈玉成把元明单设一节,认为明代的《春秋》学成绩远不如宋代和清代,核心是围绕胡传的注疏阐述或者以朱熹为宗的辨疑考误。简要评述了赵汸、《春秋大全》、张以宁、陆粲和傅逊,以为部分著作在研究方法上或对清代考据学有开拓,也有破除穿凿平易解释的风格,但如赵汸区分经史细目的努力是“无效劳动”,“《经义考》所列明人关于《春秋》经传的著作,今存者大约不足五分之一,值得参考的更为数寥寥,事实本身已经充分说明了问题”[1]246-256,把明代《左传》学的成果基本归因为“官学束缚思想的直接后果”。赵伯雄也把这一时期界定为“《春秋》学的衰落”,以为官学《春秋大全》使得士子趋于制艺而不钻研经典,“故有明一朝,经学最为衰废”,“《春秋》学从此起几乎没有发展”[4]590,404。宏观介绍了赵汸、汪克宽及《春秋大全》,而未深入分析赵汸的笔削体系,以及《春秋大全》对汪书的改动。戴维以为,“明朝则完全是空疏的时期”[5]388。也认为官学限制了思想自由,又补充了经学空疏的心学因素。同样认为明代以对胡传的阐发和批评为话题[5]403-404。简要介绍了多位学者,指出赵汸上升到自觉阶段,认识到分辨史法与笔削的意义,且形成系统的研究方法,以《左传》为主要事实依据,反对虚辞,“在经学的发展过程中却是一次前进的举动,使《春秋》学中凡例学进一步细密化、深入化”[5]402。指出张以宁对胡传“夏时冠周月”的批评“是最有系统、最有力量的反击,自此以后,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指出陆粲开始用钟鼎铭文考证经文,有先进的方法论观念[5]407,409。指出高攀龙墨守经文,对经有传无者不敢疑,经无传有者不敢信[5]412。童品多从《左传》的角度驳公榖,但左氏多辞藻而义劣。傅逊将《左传》改编成本末体的形式,且加以评论以厘正杜解及《左传》有失经义处,注意古字奇音的训诂与音读,以及地名、人名和古器物的考辨。冯时可于训诂议论较为简明扼要,不牵扯枝蔓,其实这正是明人的作风,也反映了明人于经学空疏的现象[5]417-418。三部通史性专著观察到明代《左传》学者的某些关键特征,可惜的是,评价多借助四库馆臣所云以及序言做结论,没有考察明代《左传》学外延的独特性,没有从国家和社会层面考察《左传》学的普及状况和思维体系的成因。罗军凤[6]12认为,八股文使得“经史之学成为绝学”,“阳明之学,渐入空虚之境”,“宋明学者……不理会前代传注在经解中的作用,而凭一己私意臆解经义”[6]55,把明代学者和宋儒的研究作为清代《左传》研究风格的对立面,是舍弃参考、臆解经义的。
伴随更多的明人著作的梳理进程,对明代《左传》学肯定的观点越来越多。这些学者认为,明代研究显示的更是一种博杂和多样性,确实在具体经学问题以及经世致用方面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不能以后世标准化、规范化的学术方法和学术路径来衡量其价值的高下。
近年有两篇博士论文对明代《春秋》学和《左传》学有了比较深刻的揭示。林颖政在文献上将明代存佚的《春秋》类著作基本都搜集出来,并制成《明代春秋存轶录》,将自序和他序放入。该文侧重于回应顾炎武以来对明代经学的贬低或忽视,从《四库总目》的评价与理由、科举和学术上胡传与《左传》的消长、训诂考究、文史子等领域的发展四个方面,论述明代《春秋》学具有思想丰富且影响深远的价值。作者归纳《四库总目》著录和存目对历代《春秋》著作的评价,以及《四库总目》编纂的宗旨,得出贬低评价的原因在于馆臣的政治立场和重朴学的学术倾向。在考察士子备考的参考书时,作者指出,《左传》节文等讲章有着普及知识的功效,而未必完全负面[7]116。《左传》由于亦经亦史的特征,没有被胡传完全压制,明代学者不同程度地把左氏当作《春秋》需要参考的材料[7]149-150。明代学者在关于《春秋》的名物典制、制度沿革和文字音义的考证上也为朴学做出了前导之功。在经学以外,左氏多元丰富的内容显示出来,不再执着于经学的神圣性。“《春秋》学的微观中还有《左传》与胡传的竞争,这里面所隐藏的讯息,可以解读为崇尚征实史事的《左传》学者与漫谈义理微言的胡传系统,两者之间也产生了矛盾,进而发展出竞争的态势。”[7]151作者多借助凡例和序言来介绍考证学者的旨趣,可惜有嫌疏略。周翔宇认为,在学术发展方向上,明代《春秋》学是在汉宋基础上的继承和超越,既不像汉唐学者恪守注疏的文辞诠释体系,也不像宋儒一样抛弃文辞,纯以义理诠释,而是根据经文字词的具体情况,采舍三传事义,较彻底地抛弃了前人对书法文例的拘泥[8]64。在学术传承上,明儒经历了以胡传为代表的以义解经和朱学为代表的以事解经的两种流派的势力消长,以及王学带来的解经新变化,上述的变化与科举和治学的崇尚取向又密切相关。在研究领域上,明代在经义研究之外的文史改编领域有空前规模的发展[8]48-52。周翔宇把明代《春秋》学的著作数量、版本、内容和学者信息,进行时代、地域统计分析,其中以《左传》标目的著作仅次于通解类著作,而远多于以胡传和公榖二传为名的著作。据此得出明代《春秋》学发展成熟的三个阶段和地区差异,以及在清代影响的衰退。王子初关注从经传相互构建义理的角度,以及从《春秋》经传资政的现实关怀的角度对明代《左传》学进行研究[9-10]。
此外,有学者针对《左传》学在与科举的互动关系、针砭权威注解以及史学改编等方面的贡献,论争明代《左传》学的积极价值。张德建以为,《春秋大全》虽宗胡传义,但因为《左传》的史事特征使得士人必须参考左氏,“故其学术指向便由假经以明传,变为因传以明经,以补救胡传之失。欲因传以明经,便须由《左传》入手。《左传》开始引领学术风尚的变化” 。通过考据事实以求《春秋》笔削之旨,故而明代《春秋》学者多强调《左传》的重要性[11]。李卫军以为,“与前代及其后的清朝相比,明人的《左传》研究,精诣或有不及,而博杂则远逸前人,不让清儒”[12]。归纳了《左传》作者及与孔子之关系、《左传》与《春秋》之关系、义例说、各种史材和兵书改编,以为,明人精湛见解不多,但部分作品还是对清人有很大参考作用的。作者指出黄泽、赵汸在左氏经史源流和文风比照上,回应了前人对左氏身份的质疑,多为明人接受。以为明人受宋儒影响,多从尊经之说,而赞左氏史实翼经之功。明儒多从朱熹,反对例解《春秋》之说。邢猛研究了明儒对杜注的批评后指出,陆粲、傅逊、凌稚隆、刘绩等学者指出杜注在训诂和义理解释上都有错误和不充分的地方,或予以修正,或提出新解,体现了严谨的训诂态度,“援引经史古训、采录诸家之说,比较古书异文、利用注疏自身矛盾、联系《传》文语境”[13]。
二、对明代《左传》义理、义例问题的研究
一是对明初朴实学风的研究,如对赵汸和汪克宽的研究;二是对明中叶心学倾向在经学研究中渗透的研究。就前者而言,周翔宇指出,明初,官学基本上保持古注疏和胡传并用的局面,《春秋大全》正式把胡传作为科举的功令,古注疏的地位下降。而在野学术一直不废汉学,注重以事解经的朱学对胡传穿凿义理的批判。明中晚期,就科举参考书也不再泥于专尊胡传,转向吸纳其他传注,出现了要求修改《春秋大全》的呼声和考官重视会通四传的风向[8]150-151。作者指出此时期以事解经存在自由解说和据传解说的两种倾向,“由于纯粹的据经论事存在着臆测、杜撰等等弊端,所以在熊过、季本等人极端追求思想自由发挥的同时,也有一部分明代中期学者更加关注经说的合理性,坚持以传文补充经文载事之略。所以当他们论及经传关系时,就特别强调《左传》记事的优异,极力主张它在解经中的作用” 。在确立以事解经的研究方法时,明儒尤其注意辨析《左传》的叙事记载,对经传记载差异之处做出选择[8]212,208。周文的特点是揭示了明代《春秋》学的时代、地域分布趋势,以之为划分明代《春秋》学的依据。揭示了宗胡和宗朱两种思潮竞争的实质,在于以事解经和以义例解经的冲突,这个线索贯串明代。关于赵汸的研究,多数学者都指出了,赵汸师承黄泽,重视凭借《左传》来作为区分《春秋》中经文和史文的依据。赵汸的贡献是提出了系统的史文书法原则,并且指出以前的代表性左氏学者的特点:杜预推阐史例有功,但曲从左氏,把本应是史文的内容看成经文;陈傅良试着把三传结合起来解释,但把左氏完全当成鲁史,用公榖义释有经无传之处,混淆师法[4]586-589[5]398-403。洪飞指出,赵汸总结的史法主要来自《左传》,其中,总结的十五条策书之例和笔削之义中的存策书之大体是不同的,“此策书十五例与笔削八义中的存策书之大体虽然在内容上是一样的,但是使用者不同,存策书之大体是孔子要保存国史之貌,而策书十五例则是赵汸通过《左氏传》等史书归纳出来的史例” 。赵汸吸取了杜预变文的说法并将范围扩大,包括名实之辩、中外之辨、用辞特异[14]。胡闵凯认为,赵汸在从《春秋集传》到《春秋属辞》的写定期间,对左氏的评价是有降低的,体现在“在求《春秋》‘经学’大义的场域里,代表‘史学’的左氏,事实上仅能作为辅佐、补充的资料”[15]。作者有夸大《春秋集传》和《春秋属辞》文字差异的倾向,并把这种差异看成赵汸的思想转变。实际上赵汸可能没有这么剧烈的转进思想。黄开国认为,“赵汸《春秋》学的主要成分是《左传》的以史说经。但是,赵汸只是讲到《春秋》存策书之大体,而并没有把《春秋》视为鲁史,并且把存策书之大体、辞从主人等与鲁史联系的方面,都说成是孔子笔削之义,他认为《春秋》之成为经典并不在于文与事,而在于义。这又与《左传》的以史解经绝异……又接近于《公羊传》、《榖梁传》” 。指出赵汸有综合历史上《春秋》各派的特点[16]。李建认为,赵汸在左氏和杜注的基础上,分辨出如何区分经史的系统原则,“哪些是孔子因鲁史旧文、有笔无削、述而不作的,哪些是孔子损益笔削、有述有作的,以及孔子是如何因循、制作的,其制作多寡、轻重程度又如何,等等……正可以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地排比区分鲁史旧文与笔削制作,使之各有归属,体统分明,繁而不乱”[17]。对赵汸经史区分的义例体系业已论述很多,而在衔接这种理论和应用的对应关系方面的研究尚较薄弱。
关于汪克宽的研究,戴维指出其归纳分析法的四方面:记事及名爵、各家经文同异、广采众说、综合分析[5]392。张学智以为《春秋胡传附录纂疏》视《春秋》为理学著作,虽宗胡传,但翔实考证其观点来源,体例上详注各传同异,名物兼采杜注与宋儒之说,书法上间附己意[18]642-644。甄洪永认为,汪氏春秋学特点:一是宗胡而不废古注疏;二是博采前人成果择善而从[19]。
就后者而言,集中于对心学中王学与湛学分歧的研究。关于湛若水的研究,张学智等认为,湛若水《春秋正传》体现其心学思想,认为“圣人”之心通过所论之事表现,《春秋》全是鲁史旧文据事直书,反对后儒穿凿义例而不原“圣人”之心的研究[18]648-649。刘德明分析了湛若水的以事解经倾向,一方面,这种路径是《左传》叙事为主特征的延续,“从学术的源流与发展来看,其似乎可以视为《左传》学在‘以事解经’这种经解方法更进一步深化的发展,但就现今关于《左传》学的研究成果来看,似乎对于湛若水的《春秋》学的成就过于忽视,并未将其纳入《左传》学的范围之内”[20]133-159;另一方面,以事解经的办法在遇到有经无传的情况时,往往不得不借助贯通全经的大义说解。由于作为客观存在的事件往往有复杂性,其中的意义并非如“直书其事,善恶自见”般单纯,故而湛若水的议论往往又成了自己对于义理的执著,走向了所树立的大义必须建立在事的基础上的宗旨的反面。
关于郝敬的研究,张学智以为,郝敬的《春秋直解》反对义例、褒贬、特笔说,断言《左传》为周秦间伪作,不是左丘明所做之鲁史,《左传》的叙事作为是三晋辞人之见,贻误后世,反对褒贬和书法以及夷狄之说,以为《春秋》直书其事[18]656-660。张晓生以为,郝敬倾向于把左氏记事当做鲁史旧文,但史事义理不可依赖于左氏或四传,而是自己体会孔子简明直接的态度,“不再依靠‘例’及‘褒贬’的框架来范限人们对《春秋》的理解” 。左氏由于有很多与《春秋》不合之处,所以很可能不是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所做,而且左氏导致公榖、胡传益发附会义例。这可能与郝敬对佛学的研究和从鲍观白接受的心学有关。作者以为,宋明“诸新出传说对于《三传》旧说,只是选择性的或依或违,并没有发展出更有意义的解释系统……上焉者犹博采众说而折衷之,下焉者则一空依傍而自抒胸臆……(郝敬)对《春秋》义理的掌握,并没有比他所反对的《三传》更高明”[21]65-93。张晓生在另一文中[22]377-400认为,郝敬把左氏看成一切穿凿之说的鼻祖,以为传中参杂后世语且偏袒晋国,不是左丘明所作,左氏的凡例和书例解释不了《春秋》,只有用心摒弃义例,直观地体会孔子之意才是出路。“郝敬却代表了‘舍传求经’一系极致发展的弊端—经义的浅薄化,这样的弊病也让《春秋》学‘经传一体’的起点值得重新被思考”。张晓生指出了郝敬分离经传、各自为书的一面,不过忽视了郝敬对《左传》保存鲁史的肯定。
三、对明代《左传》学经学外改编的研究
近人指出,明代《左传》学在史学、文学、子学方面也获得了重大突破,使得《左传》著作有独立于经学自立门户之势力。周翔宇指出,明代《左传》在制艺文上的改编所起到的事实根据意义,冯梦龙的《春秋衡库》、穆文熙的《左传评苑》采撷相关的叙事、文辞以便考生作文揣摩。应试程文出现从依附胡传,逐步转向将四传等量齐观的趋势,甚至出现如颜鲸、杨时秀明确以《左传》为主,将胡传还原成宋儒一家之言[8]299,157-158。《左传》在“以事解经诠释体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李卫军详细介绍了万历以后,《左传》评点迅速发展的表现:第一,依托于古文选本的评点著作继续发展,有将《左传》视为古文正宗之意,选本的篇目有趋同倾向。从内容上,更为充实丰富,有重史事评价者,有重文法分析者,有二者兼顾者。旁批、眉批多揭示文章脉络,尾批多总论事义。从形式上,多有凡例,正文眉批、旁批、尾批多种形式,圈点更繁复。第二,《左传》评点专书大量出现。在内容上,广涉经史文。第三,科举导向增强,托名现象多。第四,多局部阐发,少全文总括;多感悟品评,少细致分析。第五,为寻求通畅,多有删改原文。数量较多,但质量不高[23]20,23。穆文熙的作品以分国记事的形式,采录前人评价,于《左传》大义发明无多,对初学揣摩文意还有帮助。凌稚隆的作品侧重经学集评的形式,与坊本之泛然采录者不同。孙鑛、钟惺侧重指摘左氏行文句法意境。这些论文开始从演进脉络或者某些侧面观察明代《左传》学的传承与影响。林颖政分析冯梦龙的《新列国志》有忠君忘身、公私义利、孝慈友恭、守信弃贪、善恶终报、戒淫贞节等主旨[7]298-304。龚鹏程注意到,冯梦龙把科举制艺和《春秋》研究关联起来,讨论经世的主张,是一个新颖的角度。冯氏总结了比合题的类型,主张围绕书法确立答卷文意。与其他玩赏《左传》文辞的评点著作不同,重视推求事迹的所以然“义理”,即“圣人”善心与经世大法。既重词气文章,从文例书法文势上寻找大义,“玩辞见义”,又便于读者揣摩作文之法,以便考试[24]236-269。也有对陆粲、孙鑛、钟惺的考证或评点研究,如邢猛[25]、张盼盼[26]、郑艳玲[27]等。
林颖政指出,在明中晚期边防压力日增的背景下,经典经世致用的需求唤醒了对左氏军事论述的研究兴趣,左氏被奉为兵学之祖。作者按照儒将和儒生的著述分别举例讨论,重点介绍了陈禹谟的《左氏兵略》、宋徵璧《左氏兵法测要》的主旨与体例,魏禧的《左氏兵谋》、《左氏兵法》。《四库总目》的负面评价并不合乎改编兵法的学者本意,“《四库总目》对明人的恶评劣价亦绝非仅仅是馆臣私人的意见,它所代表的是清廷的官方看法,再宣称清朝取代明朝是理所当然,明亡非清朝所为,乃自亡耳,以此证明清朝在中原地区的正统与道统上的合法性”[7]260。林文介绍了明中叶以降评点走出了私人领域,在印刷业发达的情况下,评点范围波及经典。作者详细介绍了评点的起源、符号和功能,讨论了明清士人对待《左传》等经典被评点和小说选入的褒贬看法,“跨越了经典神圣的鸿沟,进入到通俗浅显的领域,从经学研究者的书架推广至一般文人学士,甚至进入到普罗大众的生活中,这一剧烈的变动虽被传统经学家目之为‘经典沦丧’,倾覆经典的行为,明人则将此视之为‘典范再造’,调适雅俗的过程”[7]306。捍卫经学地位的势力最终战胜这种企图改变经典本质的潮流,故而明代经学被定性为经学既衰。林颖政的研究提供了最全面的明代《左传》学目录,对具体著作的研究有按图索骥之功,且是较早的系统详尽地批评主流贬低明代《春秋左传》学意见的著作。
四、关于顾炎武和王夫之的研究
关于顾炎武。罗军凤指出,顾氏强调要考辩学术源流,故而重视汉宋前儒的传注搜集,以求经解,还重视以《左传》的史实为解经依据,反对穿凿生义[6]52-54。金永健认为,顾氏重视左氏以史解经的特征,并指出顾氏寄托矫正世风的深意于义例分析和史事褒贬上,又指出顾氏多重考据经传的方法开启朴学方法先河[28]。蔡妙真讨论了顾炎武《日知录》中的《左传》学,举例论述了顾氏的训诂成果和义理关怀,与左氏是否是独立的史著持中立意见,以为左氏作者非一人。指出顾氏《左传》学的特色在于用历史的发展眼光考察古词古义,利用金石文献与后世文献互证、因声求义不限形体、运用异文对勘、数量统计等多种手段夷夏之辨、辨别礼制[29]。古伟瀛以为,顾氏将夷夏之防融入对《左传》的注解中,并谓《春秋》书例所谓“文势使然”的部分是顾炎武为孔子辩护。作者结合诠释学的理论以为,顾炎武作为诠释者“本身之色彩都深深烙在所诠释的对象上”[30]。
关于王夫之。招祥麒以笺注的方式,将王氏《春秋稗疏》逐条分析,将前人具体意见分类,比较王夫之的超脱之处。对《春秋》地理和杜注补苴,有很多创见[31]。
五、不足与展望
关于明代《左传》学的研究无疑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尤其是在文献统计,以及作者的身份、时代、地域、与社会的关系和学术发展的特色方面,相较四库馆臣以来的忽视评价有了较大的突破,不过仍有一些需要深入探讨之处,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认识论和方法论有待丰富。明代《左传》学固然是学术史和文献学的重要组成,而根本地,它是《春秋》学的一部分。以往研究多从社会史的层面分析作者的身份、时代和地域的分布规律,结合国家的科举政策和教育政策,分析明代《春秋》学的兴盛程度和普及程度。如林颖政和周翔宇的论著。周文还探讨了学术师承和《春秋》学者学派的关系。这些都是重要的研究路径。不过,在经传对应关系、传传选择关系以及《春秋》经传基本问题这些方面,明代学者有着怎样的统筹体系,在众多学者指出的以事解经的共同取向背后,有着怎样“理一分殊”的逻辑推论,目前仍是比较薄弱。
二是文献解读有待细化。目前的研究成果固然努力矫正以及反对以四库馆臣为主的贬低评价,不过在以明代学人的著作阐释观点时,难免主要引用作者的序言和他人的评价,以及四库馆臣的评价。序言当然是把握一家宗旨的重要门径,不过也会使研究者忽视作品实际内容与序言的差异,尤其时常以四库馆臣之言为结论,反而与突显明代学术特征的初衷相违背。经解著作以及史学、评点和兵学著作的代表性作品的解读还比较欠缺,尤其是经学以外的作品,由于基本都是按《左传》史料分类,作者编纂篇次的用心并不直观,评点的语句经常只是几个字做一意境描绘而不铺陈,难以概括出体系性的理论。这些作品还缺少推敲和比较。
三是研究领域有待扩展。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著作学理的阶段性演进的探讨,其他向度的考量还比较薄弱,比如《春秋》经传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诗歌中的经典典故、史学著作中的经典引用和科举制艺中的经典调试等等。突破作品名称的限制,在其他类型作品中寻找某种经典的运用目前尚显不足。
针对以上情况,笔者以为未来明代《左传》学的研究展望应当有几个方面:
第一,从经传关系的角度研究。传统《春秋》学者都是在经传体系的高度研究经传关系的。除了训诂内容以外,《左传》的解经部分是连接经传的关键媒介。在《春秋》通论性质的作品中,作者如何以《左传》的义例和叙事来建构经义,又如何站在经高于传的高度审视《左传》的“不足”,《左传》的若干重要原则如赴告、阙文,以及杜注的演绎等与学者的以事解经脉络是什么关系。此外,《左传》的基本问题虽然有一些如作者时代问题在明代论述得不多,但有一些还可以继续讨论,如明人认为的《春秋》内外传的关系,《春秋世学》这样的伪书对《左传》的改动、利用等等。把《春秋》通论的著作纳入《左传》学研究中,对于明代《春秋》学也是内容的扩展。
第二,从著作的具体内容入手。与上点对应,学者的《左传》学思想往往是要从经解和传例的比较中概括而成的,就不能满足于序言和评价。在经学著作中,要条列左氏传义,比照作者经解,以及公、榖、胡传义,观察作者是倾向选择旧说,还是另辟新解。在史学改编著作中,要考察作者对《左传》材料的去取和搭配,在作品之间作比较,以见优劣。在兵学改编著作中,要考察不同历史环境下策略运用的可操作性,且结合近现代军事理论进行比较。在小说改编作品中,除了要概括小说的内容旨趣,还要比照《左传》的史料经历了怎样的文学处理,《左传》的解经特征在文学作品中的保留状况。
第三,从更多的视角研究。既要考虑共时性的平面展开,也要考虑历时性的传承变迁。《左传》学在明人日常生活、为人处世中是怎样体现出来的。有时,像大礼议这种政治斗争的指导思想往往把《左传》等多种经典综合运用,那么《左传》在引用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怎样的,断章取义的实践和原典有哪些差异,为什么产生这种差异。此外,如宗教与《左传》学、理学与《左传》学、诗歌中的《左传》学、史学著作中的《左传》学,都是这种横向展开。就历时性上,《左传》的基本原则在元明清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关注点有哪些变动,为什么产生这种变化,是纵向的展开。突破题材的限制,会有更多的认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