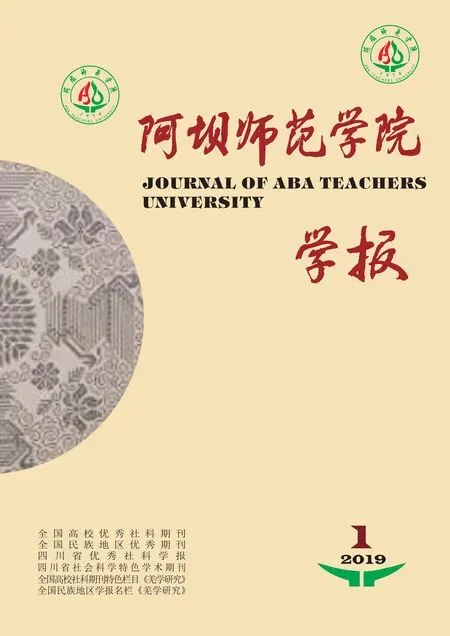清代瓦寺土司与羌人的关系
曾晓梅,吴明冉
清初岷涪江上游尚有二十五处管束羌人的土司[1]342-246,至道光一百多年的时间,羌族地区的土司,除瓦寺土司外,有的改土归流,有的名存实亡,如静州、岳希、陇木、牟托等土司,仅辖三、五个寨子,势力衰弱。瓦寺土司身为嘉绒藏族,属民有藏羌汉,以羌人居多。藏羌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瓦寺土司的兴衰成败。本文以此为线索,探析瓦寺土司与羌人的关系,敬请方家指正。
一、因羌乱而设的瓦寺土司
瓦寺土司是嘉绒藏族十八土司之一。明正统、成化年间奉调出藏镇压汶川一带羌乱,移驻汶川涂禹山。所辖之地聚居的藏羌民族,分散在山谷,以寨各居,互不相率,加之明代所在1400-1600年正值中国气候寒冷鼎盛期[2]35,干旱、洪涝灾害频发,为争夺资源,常有滋衅。明廷便采用以番治番、以夷治夷策略加以镇压。《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川》:“加渴瓦寺,亦董卜韩胡支派。正统中,调征草坡。……成化间孟董、梁黄之乱,调发协征,遂就汶川涂里山巅居焉。”[3]676《清史稿·四川土司》:“正统六年,威茂、孟董、九子、黑虎等寨诸番跳梁,雍中罗洛思、桑郎纳思坝奉调出藏,带兵出力,即留住汶川县涂禹山,给宣慰司印信号纸。”[4]14234(卷513)《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成都府部》进一步记载,正统“十一年,威保西沟诸番跳梁,汶川草坡野蛮作乱,……雍中罗洛斯征剿,平服事宁。十二年颁勅印为董卜韩胡宣慰使司,即令住守威汶适中之涂禹山。控制远近番彝,防御威汶灌河西一带地方。”[5]30(卷593)虽然在第一代瓦寺土司移驻涂禹山时间上,各书存在分歧,且正统六年、十一年的军事行动亦不属于同一历史事件,但所述“诸番”一致,皆为藏羌,并以羌人为主。也就是说瓦寺土司的设立与羌乱有直接关系,旨在“以控西沟北路羌民”[6]99。
瓦寺土司辖境最广时有数千平方公里,包括今汶川县大部分地区、茂县、理县、都江堰的一部分,多是羌族核心聚居区,古冉駹人居地。但最初的辖地并不大,只有涂禹山三寨和四山三寨,后因功和政治原因朝廷多次增封领地。其中最重要的两次一次在明,一次在清初。明隆庆二年(1568),草坡羌乱,杀寒水土巡检高茂林及居民七十余人,第十一代瓦寺土司南吉二朋讨定。万历中,草坡十二寨头领复乱,互相屯兵吞并,争杀不休。第十二代土司舍躬进剿,自此草坡十二寨由官府划归舍躬[7]456(卷2)。汶川县三江乡照壁村存嘉庆八年(1803)《刘氏百代兴隆碑》,碑文简述远祖刘什魁于隆庆四年(1570)从茂州文镇迁徙至三江,“世受头人之职”[8]1362。刘氏羌人的迁徙,应与两年前草坡羌乱有密切关系。
历代统治者除以夷治夷镇压羌人,亦征调汉族势力镇压羌人,甚至调用羌人镇压本民族人民。如牟托、陇木两土司,调征羌区,遂住牧当地,成为羌人土司,融入羌族。牟托土司,其先陕西宝鸡人。《牟托巡检司土规碑》载隋文帝时温光耀“调征川夷,留戍无忧”[8]1269。据《隋书》之《本纪二》《崔仲方传》,隋初其统治势力就已达岷江上游。开皇八年(588)、十四年(594)姜须达、崔仲方曾任会州总管。隋会州,即汶山郡,辖境颇广,约今汶川、理县、茂县、黑水及松潘县南部一带。其时,诸羌犹未宾附,温光耀确有可能此时调征至会州。但所言“无忧”,即无忧城,位于今理县杂谷脑镇杂谷河北岸,乃唐李德裕筑,吐蕃号曰无忧城。故碑文在记述温氏祖先事迹的时间上有误。陇木土司,自称其先唐山西太原人杨氏,调征播州,子孙世有其地。宋时杨文贵随剿罗打鼓,留居茂州。《道光茂州志·土司》载,明嘉靖间“土司杨翱随总兵何卿征白草生番著有劳绩,命改何姓”[9] 384(卷3),即《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成都府部》陇木土司坤儿卜协剿核桃沟、五寨三沟白草等处羌,因“战功居多,赏赉甚厚。卿命从何姓”,其孙何敬国[5]30(卷593)。可见,陇木土司至迟在嘉靖间已改羌名。又如清杂谷五屯参加大小金川平乱,战后抽调九子、上孟、下孟兵营中勇武精悍的羌藏兵驻守当地。瓦寺土司所率藏羌兵更是参加了明清,特别是清代许多重要战争,诸如征讨大小金川、杂谷土司、草坡生番、贵州苗族等。调用羌人镇压本民族最典型的一例便是正德间静州长官司节贵与子节孝,约同羌番“攻茂城,断水道七日”[10]8023(卷311),官军渴甚,幸获节孝弟车勺引水入城,缓解危急,擒斩贵孝父子,车勺袭职。勺故,子法宝袭职,调征三沟五寨;孙法从调征白草坡。基于以上认识,以及岷涪江上游羌人反抗明王朝统治的斗争贯穿明代两百多年的史实,笔者认为草坡羌在隆庆二年(1568)至万历间仍有小规模的反抗斗争,史乘失载。《刘氏百代兴隆碑》有“颁旨”之语,从侧面反映了隆庆四年(1570)草坡羌人的反抗,以及明廷遣调茂州羌人镇压一事。
清初瓦寺第十五代土司曲翊伸率先投诚,辖境进一步扩大,东至威州,南至三江口,西至斑烂山,北至沙派沟[7]587(卷6)。有学者进一步研究其境东抵威州保子关,南至三江和老塞坝(今都江堰市境内),西临日龙、斑烂山,界沃日土司,北至沙派沟,与杂谷脑相交界[11]121。耿达、卧龙、三江等乡和十一寨,都在其辖境。嘉庆《四川通志·武备·土司》载,“其地东至汶川县、理番属蒲溪木兰交界,南至汶川县中滩堡、灌县鱼子溪水磨沟、崇庆州山交界,西至沃日土司巴郎山及水坪土司大邑县属雪山山梁交界,北至三杂谷壁峰山、理番厅杂谷丹札山岭交界”[12]3068(卷96),成为岷江上游势力最大的土司。至第十七、十八代土司,野心不断膨胀,有了觊觎灌县、平原之心,立于水磨连山坡村碑杠岭的乾隆五十六年(1791)《灌瓦界碑》就是当时边界之争的缩影。瓦寺土司与灌县以碑所立鹞子山为界,“内归灌县,外属土司”[8]1321。清代后期,领地缩小,只余岷江西岸二十八寨,见咸丰三年(1853)《瓦寺土司差役碑》,约占汶川县三分之二。
从明代至清代,历代瓦寺土司参与中央王朝的军事行动,“凡遇调遣,悉能统率所属,奋勇向前,著有劳绩”[13]710(卷40),维护了地区安定、国家利益,被朝廷视为“敬恭职守”的典范[14]57(卷4),累受褒奖,这是瓦寺土司长久不衰、延续至民国的重要原因。如康熙二年(1663),第十五代土司曲翊伸征剿杂谷阿朋。五十九年(1720),第十七代桑朗温恺随征西藏、郭罗克地,因功加宣慰使。乾隆十七年(1752)、三十二年(1767),第十八代土司桑朗容忠奉征杂谷土司苍旺、大小金川,赏戴花翎。五十五年(1790),乾隆赐第十九代土司桑朗荣宗姓索诺木,瓦寺土司自此定姓索。同年,“遣土弁领二百人从大军进讨”廓尔喀[14]55(卷4)。廓尔喀,今尼泊尔。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七年(1791-1792),廓尔喀再次侵犯西藏,清政府调集各族大军入藏,七战七捷,收复失地,并深入廓境迫其求和。嘉庆八年(1803)《刘氏百代兴隆碑》中刘氏第七代刘正祥,即嘉庆十五年(1810)《刘正祥墓碑》碑主。据刘正祥享寿四十三岁,知碑主生卒年误倒。正祥生于乾隆十五(1750),卒于五十七年(1792)。碑称正祥在“西藏出师廓[尔喀]”[8]1387。乾隆五十七年(1792)七月初三一役,将士死伤惨重。加之军粮不继,疾疫流行,减员日多。清军总督福康安等密奏前线窘况,请求准许廓降。七月十九日奏:“前调川兵,原拟五月中赶到,今总兵彭承尧带领头起瓦寺等处土兵五百名,于本日始行到营。”[15]754-757正祥身为千总,应率领了不少羌兵,此时已是战争末期,几天后即“廿二日阵亡”[8]1387。八月,福康安准许廓降。嘉庆元年(1796),瓦寺土司受命随剿达州教匪,封宣慰司。道光二十年(1841)十月,鸦片战争,第二十代土司索衍传遣土舍索文茂领兵出征浙江宁波,士卒英勇杀敌,死伤过半。阵亡将士们的辫子和腰牌被剪下,葬于故地,是为“辫子坟”。今汶川县三江乡、理县甘堡藏寨等地都有“辫子坟”。上文刘正祥墓亦是辫子坟无疑。可见,瓦寺土司参与中央王朝的军事行动,都有羌藏并肩作战的身影。
汶川位于岷江上游,与都江堰灌口毗邻,是川西北高原通往成都平原的要道。瓦寺土司奉命扼守保子关、三江两处关隘。保子关位于杂谷脑河与岷江交汇处,是茂州与理县必经之道,可谓蜀西门户,明在此设保子关巡检司。乾隆《四川通志》卷四下《关隘·直隶茂州》:“保子关,在保县新并威州西北一里湔(岷江)沱(杂谷脑河)二水之中设索桥,以通金川杂谷沃日及威保二处,羌汉往来要冲。”[16]186(卷4下)为了防止藏羌造反,清政府将前明松潘卫迁于此,设立维州协,由瓦寺土司管领镇守。嘉庆《四川通志·武备》:“杂谷厅维州协左营属瓦寺宣慰司索诺木荣宗”[12]3067(卷96)三江,地处汶川南端,是灌县与邛崃等地间的重要关隘。瓦寺官寨就设在今三江乡。同时,瓦寺土司在此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钳制明以来董卜韩胡宣慰司势力向东、向北的扩张。威州之西有嘉绒藏族董卜韩胡宣慰司与杂谷安抚司。早在永乐间,杂谷土司“与董卜构兵。维州诸地俱为侵夺”[10]8595(卷331),迫使威州沿杂谷脑河、岷江,自西向东三迁。明威州州治本在理县薛城镇,即古维州[14]5(卷1),洪武间被迫徙威州治于霸州,宣德间再徙治汶川县,后又迁治于寒水驿北[17]306(卷1),这些地方都是交通要道和军事隘口。清廷令瓦寺土司扼守保子关、三江两处关隘,足见其对瓦寺土司的信任。
二、瓦寺土司对羌人的管理
土司制源自秦汉因俗而治的羁縻制,统治者通过分封地方首领并准其世袭官职,以达到统治当地民众的目的,成熟于元代。明清时期在岷涪江上游设置了二十五处管束羌人的土司。土司制上下等级森严,民国《汶川县志·艺文志》曾作细致研究,并列瓦寺土司组织系统表,依次为:土司、土舍、头人、寨首、乡约、土民等[7]629(卷7),各级各司其职,不能僭越。土舍,一般由土司的兄弟或近亲担任,辅佐土司管理,解决继承、战争等重大事件,地位较高。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军陷浦,据吴淞,逼金陵,瓦寺土司第二十代索衍传就派遣土舍索文茂率领土兵千余人往征,至宁波抗英军,功加一等,赏戴花翎[7]579(卷2)。寨首,负责执行土司政令、处理村寨日常纠纷等。头人,分大小头人,是土司制下管理者,一般由土司自己设置,代理土司处理内外事务。王仲典先生认为瓦寺土司头人又分大头人、正头人、副头人、空衔头人[18]41。《刘氏百代兴隆碑》所载刘氏远祖什魁于隆庆四年(1570)从茂州文镇迁徙至三江,是在瓦寺土司设立百年之后。茂州,古冉駹地,直到北宋仍“居群蛮之中,地不过数十里,宋初无城隍”[5]30(卷593),熙宁八年(1075)始筑城。文镇,今文镇乡。道光《茂州志·里甲》仍旧名,与“绵族、斗族”等羌村相连[9]348(卷2)。什魁本茂州文镇羌人,据上文知刘氏在隆庆间镇压草坡羌,因而留住汶川,再迁徙至三江,世受头人之职,但属哪一级头人,详情不可知。从头人一般有自己的寨子、土地看,多数头人是部落头领,推刘氏羌人应率领了部族人征战、迁徙。
土司是其辖境最高行政统治者,也是土地、森林、水利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19]81。土地全归土司所有,大小头人由土司分给部分土地,百姓租佃土司土地耕种。土司管理羌人使用自定的法律,也称“土规”“土律”。这是土司管理辖境事务的法律依据,也是羌族习惯法内容之一,涉及社会治安、纳税、债务、生产、土地、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如康熙四十年(1701)《牟托巡检司土规碑》有土规八条[8]1270,碑石原刻立于茂县南新乡牟托村温土司衙署内,现存茂县南新镇牟托村温耀萍家门前。还有道光二十三年(1843)《岳希土司碑》、道光二十五年(1845)《静州土司碑》,茂县羌族博物馆藏;咸丰三年(1853)《瓦寺土司差役碑》,汶川文博馆藏。历代瓦寺土司听从朝廷调遣,特别是清代,瓦寺土司参与了中央政府的许多重大军事行动,并且非常尽职,势必造成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加之,羌人承担差粮过重,无法生活而逃亡等原因,户口锐减。光绪十九年(1893)《竹石达川主庙碑》,刻于汶川县克枯乡周达村竹石达,就记载了乾隆间平定金川,竹石达一带的羌人“夫马甚重。每月垫夫马银六两,又男女上路咏兵粮,口食夫马,先辈受此艰难,故花户逃走在外甚多”的史实[8]1604。“咏”,方言“运”,读音相同而误写。光绪四年(1878)《铁邑告示碑》,刻立于汶川县威州镇铁邑村,亦记载平定金川,夫差、兵差过境,“催修路道”[8]1508。而“川省有夫马费,豫派之民间,自征大小金川暨咸同军兴,相沿已久”[8]1618。军兴,谓朝廷征集财物供军用。周达、铁邑,清属理番厅,但碑铭反映差役、战争为民众带来的沉重负担是相同的。据嘉庆《四川通志·户口》载,嘉庆年间瓦寺土司“管寨落大小共二十八寨,户口共八百。”[12]3068(卷96)魏煜《谕九寨羌民》:道光时,汶邑“现查户口甚少,未减差徭。”[7]605(卷7)咸丰时,《瓦寺土司差役碑》载“烟户只有四五百家”[8]1470,迫于辖区内藏、羌民大规模反抗斗争,土司重新制订经四川总督批准的、作出了种种让步的差役条规共十四条。差役条规除规定“土民”应服兵役、差役等外,还对土司作出了种种规定,如分赏部分粮食给租种土司官田的土民,秋收归还籽种;让减药材;裁毁土司所设油房;革除土司所设烧房等。对土舍、会首的权利也作了相应限制,如“每土舍一人,准用跟役二名。……愿缴退跟役一名,只用跟役一名,……土舍之子孙,不得滥用家役,不得私增”。“三江口官寨会首,每年让免三名”[8]1470-1471。值得关注的是此土规由瓦寺二十八寨土民,会同汶城绅士、保甲公立,刻两碑,分别立于涂禹山瓦寺土司公署和汶川城北外禹王宫(绵虒镇),反映出清政府在羌区推行的改土归流和对羌区最大土司——瓦寺土司特权的限制。
三、瓦寺土司面临的形势
自秦朝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来,历朝历代不断完善、加强,发展到明清已极大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空前加强,在县以下基层民间推行保甲制,并在实行土司制的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土司制逐渐衰落。
瓦寺土司在设立后,对于稳定羌区政治、遏制本地区劫掠、配合王朝军事行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过积极作用[19]83,但建立在封建农奴制上的土司制是残酷、黑暗的,羌人不仅要累服繁重的兵役、差役,参与繁多的军事行动,还要承受土司间为了扩充势力互相吞并以及土司对属民的武装镇压所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其经济、生产、生活受到了重大消极影响。据《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载,清代瓦寺土司在羌区,甚至自己辖区多次镇压羌人反抗。顺治十八年(1661),第十五代土司曲翊伸督剿威州境内隆山、蒲凹、竹达等诸寨生番,迫其认纳麦粮。康熙元年(1662),镇压西沟星上、水田、木公、三岔、曾头、牛罗等十五寨生番。康熙二十四年(1685),茂州北路巴猪、力角、双马、猫兄山、梁黄、六定、力力、小力等寨生番叛,第十六代土司坦朋吉卜率兵至石大关,协助官兵平定诸寨。同年,围攻汶属通山五寨羌人。民国《汶川县志》以为此乃第十五代土司曲翊伸之功[7]578(卷6)。康熙三十七年(1698),镇压龙溪、布纳、纠股、牛脑等寨生番[6]101-102。乾隆十七年(1752),第十八代土司桑朗容忠奉征杂谷土司苍旺。随后清政府即在杂谷土司旧地置理番直隶厅,境内九枯、十寨为羌人聚居地,五屯为汉羌藏族杂居地。当然,这些军事行动都是瓦寺土司在履行对朝廷的“听调”“助征”“随征”等义务,但武装镇压本身势必激化矛盾,引发更加强烈的反抗。瓦寺土司在三齐对羌人多次实施残酷镇压,并遭到羌人坚决反抗就是最典型的事例。
三齐三十六寨,今属茂县曲谷和三龙乡的一部分,雍正至乾隆间遭受瓦寺第十八代土司桑朗容忠肆意敲诈勒索、无端残杀。雍正十三年(1735),容忠残杀羌人80余人。乾隆元年(1736)三齐地区受灾严重,羌人未交麦粮本色,用银折交上纳,土司不满,率土兵300余人,联合三齐寨后的杂谷土司夹攻,毁房无数,又杀80余人,激起羌人反抗。在麻黄寨王特的率领下, 三齐羌人堆石为盟,要求脱离土司管束,归隶茂州流官管理,派代表到成都等处控告,坚持斗争,直至乾隆九年(1744)八月摆脱土司统治。三齐共设三里,三里共设保长一人,正式归隶茂州。面对容忠的残暴,羌人没有以暴制暴,而是采用和平的方式——投递诉状多次具控,一是羌人释比文化的“非战祀和”宗教心结[20]57;二是羌村社会投明、议话、公断的习惯法,及习惯法所体现的公众共同参与、秉公执法的民主意识和执法程序;三是羌人冬季经常到内地汉区谋生,熟悉封建法规。清代岷江上游羌村社会已能非常熟练地将羌族习惯法与国家法规结合,积极有效地处理问题。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灌瓦界碑》记载了瓦寺土司境连汶川、灌县,因汉夷争界诉讼,从查短投明,到控至衙门,盐茶、成绵道共同督办,就所争之处,详加核勘裁断边界,汶灌“照原定界址,各管各业”,汉羌不得“越境滋端,……越界生非,……倘有故违,一经告发,或[被]访挐,律法森严”[8]1321,瓦寺土司第十九代桑朗荣宗遵勒界碑。
羌族释比文化经典《羌戈大战》《泽基格布》以及咸丰元年(1851)《河西议话碑》都表达着羌人崇尚和平、和谐、不战的思想,并深深浸透在羌人心里,成为民族思想,融入到日常生活。三齐羌人没有以暴抗暴,就是这种思想的外化。由此笔者联想到同为唐代调征播州的杨氏后裔——陇木土司和播州土司的不同命运,或许就是最好的说明。一支融入羌人,在茂县繁衍生息。从宋至清,其家族墓葬数十座,原存光明刀溪村南凤凰山。而在播州的一支,传二十九世八百余年,至万历三十一年(1603)杨应龙反,播州杨氏亡。杨应龙曾在万历十四年(1586)率七千播州兵征喇麻,“渡歪地”,击破诸羌[21]316-317(卷5)。今黑水县洛多乡沃河村西沃河山顶,存万历十九年(1591)《播州营题记》。其势力强大不可小嘘。
如果说《灌瓦界碑》反映了清廷阻挡瓦寺土司向灌县、向成都平原推进的决心,那么三齐羌人反抗瓦寺土司斗争的胜利,就是清廷阻遏瓦寺土司向松潘、黑水的发展,减小瓦寺土司对威州、茂州的威胁,将其势力限制在原地的重要举措。
四、藏羌的共融与共容
岷江上游羌藏汉小聚居大杂居,共同的政治、经济、生产、生活,必然出现民族融合,带来风俗习惯的相互影响和变化。特别是明末清初改土归流,对藏羌推行与汉族相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如征收赋税、编查户口、兴办学校、实行科举等,有助于消除民族歧视,促进各民族团结和融合。民国《汶川县志·风土》所称“合番夷为一家,联中外为一体”[7]554(卷5),既是社会理想,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藏羌毗邻“儒家文化圈”,长期浸染,其文化明显带有双重性[22]1413-1418,嘉绒地区的文化兼具藏传佛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特征,羌区的文化兼具释比文化和儒家文化的特征。学界对此多有论述,此不赘述。
嘉绒地区原信黑教,金川事件后,清廷令各嘉绒土司改信黄教,但瓦寺土司草坡官寨仍有木刻黑教经版百余块。自明崇祯年间,瓦寺土司在今汶川县草坡乡金波村北修建了辖区内最大的喇嘛寺,又称“金波寺”“金坡寺”。后世重修、维修,瓦寺土司及家人都是主要捐资者。清《金波寺庙碑》载,瓦寺土司祖母捐地捐钱作为庙产[23]41。惜已亡佚。现存光绪二十年(1894)《索杨氏金波寺给发碑》、宣统二年(1910)《培修金波寺佛庙内外完字碑》。前碑索杨氏,瓦寺第十九代土司荣宗子索衍传之生母。后碑题土司家族四人。其中,大老爷代兴,字怀仁,瓦寺第二十二代土司。父索世蕃。至于“索大老爷即代杨”[8]1661,根据旧志记载代兴卒、弟代赓嗣的史实,知代杨应与二人同辈。这些碑刻,以及境内遗存的《灌瓦界碑》、《瓦寺土司差役碑》、嘉庆十四年(1809)《四圣寺碑》、咸丰六年(1856)《重修跃龙桥碑》,无一例外均是汉文碑。《四圣寺碑》述瓦寺第二十代土司索衍传等捐资培修四圣庙;《重修跃龙桥碑》述土司索衍传、土舍索文茂等捐资修建桥梁。瓦寺土司虽为嘉绒藏族,但能写藏文的人少。据载,1947年涂禹山官寨能写藏文的仅有杨喇嘛一人[23]39,瓦寺土司辖地通用汉文。历代土司以“桑朗”“索”置于名前,已从汉俗先姓后名。瓦寺第十九代土司荣宗年幼,母麦氏训育有方。民国《汶川县志·孝义》赞誉麦氏“笃志守贞,满三十年……题名旌表,崇祀节孝祠”[7]571-572(卷4)。可见,瓦寺土司深受汉文化影响。
汶川羌人受汉文化影响,最早可追溯到唐代,汉官在境内修建学宫、文昌祠等,大兴礼仪之风。近现代羌人家里一般供有“天地君亲师”神位,左右上角则分别写始祖神、山神、寨神、祖先名讳,并有释比作法。羌寨里既有羌族释比,也有道士、喇嘛。靠近藏族的羌区,如小黑水、小姓沟地区的羌族信奉喇嘛教,有“龙潭寺”。而信奉喇嘛教的嘉绒藏族,也如羌人一样普遍敬奉白石神,供白石于屋顶小塔上、敬奉山神[23]42。羌族民间至今流传着端公和道士、端公和喇嘛斗法的传说,其实就是道教、喇嘛教传入羌区后与羌族原始宗教信仰之间曾发生过激烈的摩擦、碰撞的事实,以及藏羌汉多元文化共融和谐的现实,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从瓦寺土司与羌人婚姻关系上看,藏羌又是共容的,即互相包容,但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嘉庆八年(1803)《刘氏百代兴隆碑》题刘氏羌人九代,从明隆庆四年(1570)至清嘉庆八年(1803)两百多年间,存90余人题名,除倪氏、杨氏、李氏、徐氏等可能是汉人外,余皆为羌人题名。明清时期,岷江上游羌族仍以房名为主,记录在碑铭上的题名为汉字译音。《刘氏百代兴隆碑》既有羌人特有的父子连名,亦有父与女、孙女连名,以及兄弟连名、姐妹连名,也就是说羌人不论男女,都有连名之俗[24]158。而在同一碑铭中连名形式之多,实属罕见。题名还采用羌人取名常用字,如“木”“保”“子”“勺”等,亦有刘姓“正”“保”字辈题名,人数不多,但已有字辈的意识。该时期羌人仍然以族内婚制为主。瓦寺土司上下等级制森严,可与土舍联姻,也是以族内婚制为主。如瓦寺第二十代土司时有土舍索文茂。藏羌上层,也就是说瓦寺土司或土舍与羌人头人很难通婚。过去我们认为刘氏作为头人与瓦寺上层可能有联姻,是不正确的[8]1368。当然,瓦寺移驻羌区后,其属下必然与羌汉通婚。嘉庆以后,随着改土归流的深入,刘氏羌人与瓦寺土司辖区内驻防的藏族屯兵或头人互有婚姻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或许是今天的三江刘姓人自称藏族的原因。
瓦寺土司辖区的羌人,乾隆时期已逐渐改汉姓,但主流仍是羌名。如绵虒白土坎村存乾隆五十九年(1794)《大埃咪张氏家谱碑》,十代,除始祖姓张,连续七代都是羌名。其中五代用羌名常用字“保”,第九代用汉姓汉名。如汪家保、□□保、仙山保、磊比、楼保、赤止、田保等,都是典型的羌名。碑称张氏“原籍湖广麻城县孝感乡……故而改名张生,后世改姓张”[8]1328,可能是汉人张氏融入羌人,也有可能是白土坎村大埃咪羌人改汉姓编纂出来的故事。《刘氏百代兴隆碑》除第二代外,其余各代都有刘姓者,但直到第六代才开始比较多地用汉姓,而真正具有字辈意识是在第八代刘正祥时。从《刘正祥墓碑》题名看,刘正祥二子、两女、两婿,仅有祀男姓刘,余为羌名。刘氏羌人一族,到嘉庆十四年(1809)已有了儒生刘正元、刘润元,见《四圣寺碑》[8]1384。而直到咸丰六年(1856),刘氏羌人仍有任三江口头人之职的。如《重修跃龙桥碑》题三江口副目领袖刘福寿、三江口寨目领袖刘珍、会首刘永福[8]1478,与《刘氏百代兴隆碑》所称刘氏世受头人之职的记载是吻合的。
总体而言,清代改土归流促进了羌区进步,瓦寺土司与羌人的关系亦由碰撞、冲突到和谐共容与共融。
——李良品《中国土司学导论》读书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