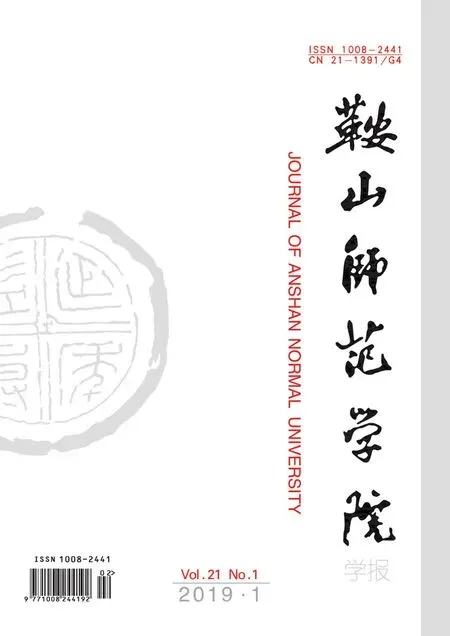论《紫色》中的隐形母亲和“病态”父亲
童杨柳
(安徽外国语学院 西方语言学院,安徽 合肥 231201)
一、引言
《紫色》是美国黑人作家艾丽丝·沃克的一部重要代表作品,也是美国文学史和黑人文学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自1982年出版以来,就在学术界和评论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女性权利、姐妹情谊以及男权压迫等主题被多次讨论,而往往忽视了小说中父母身份和言行对子女的深刻影响。如小说女主人公茜莉从未从母亲那里得到过任何关爱和体贴,母亲对待她像是对待敌人,尤其是知道女儿受到继父的侮辱后,不但对女儿没有任何安抚和宽慰,反而言辞疯狂冷酷,让人唏嘘心痛;阿尔伯特因为父亲对其恋人冷嘲热讽而又无法反抗,即使和恋人相互爱慕,也最终错过;他的儿子哈珀也在他的“要想使妻子听话就揍她”思想灌输下,和妻子的关系越走越远……因此,笔者认为从母亲的隐形身份和父亲的“病态”行为出发,分析父母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以及他们的言行对孩子的消极影响,对揭露白人霸权文化下黑人的悲惨遭遇,推动黑人女性团结互助、自尊自爱,黑人男性摆脱传统观念,认清自我,和女性和平共处,意义深远。
二、母亲的隐形身份
俗话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启蒙老师。父母的言行举止对孩子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众多文学作品中,对母亲的描写大抵是温柔、贤良、独立、坚强,所以,母亲可以看作是孩子最孤单无助时的温暖依靠。而在《紫色》中,母亲的形象却是虚无的、苍白的;没有任何话语,没有任何力量。母亲的隐形身份其实就是女性意识的完全沦丧,她们看不到自我,也看不到将来。而这种消极影响不仅给她的孩子们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同时也让孩子们看清了现实,了解了自身的需求和力量。
(一)女性意识的缺失——无语、无我
女性意识是一种自觉意识,是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具体体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指以女性认识自我、认可自身价值,肯定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对男性权力的质疑和颠覆;二是指关注女性生存状态、审视女性心理情感以及表达女性生命特色。[1]而女性意识的缺失就是指女性还没有认识自己,认清自己的价值,一味屈服于男性的权力,在男性具有话语权的社会中完全丧失表达的权力,简言之,就是无语、无我。
《紫色》中女主人公茜莉的妈妈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个勤快人,开的店也经营得很好。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却在一夕之间被彻底摧毁。仅仅是因为他的生意威胁到了白人的利益,所以就被白人们悄悄地拖出去吊死了。自此之后,茜莉的妈妈精神失常,疯疯癫癫,后来嫁给了阿尔方索先生,开始年复一年地为他生孩子,彻底沦为生育机器。而阿尔方索先生是一个自私贪婪而又道德败坏的恶棍。当茜莉的妈妈再也不能尽到做妻子的义务时,他竟然把魔爪伸向了茜莉和她的妹妹耐蒂。茜莉十四岁时遭到了继父的强暴,之后继父对她说:“除了上帝,你最好决不要对谁说,否则,你妈妈会给气死了。”[2]而她的母亲在知道这件事后,既没有站出来为她申诉,也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去保护她,而是“老对我唠唠叨叨的,眼睛盯着我。她快活了,因为,他现在对她挺好,可她病得太重,活不了多久啦[2]。” 母亲甚至在临死的时候还对茜莉又叫又骂。由此可见,作为母亲,她根本不知道要保护和爱护自己的孩子,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温暖,反而由于自己在家里一直隐忍退让,所以总把不满和怒火发泄给孩子。母亲的这种行为表明她的女性意识的缺失,她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母亲,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在家庭中应该享有和丈夫同等的地位和权力,应该和丈夫一起保护并爱护自己的孩子。母亲在家庭生活中的无语地位体现了其丈夫的专制和霸权,而孩子们也在父权制的压迫下忽略母亲,从而忘记自我。这也是造成茜莉和阿尔伯特结婚后,同样过着麻木、卑微的生活的原因。当她被阿尔伯特狠揍的时候,她对自己说:“茜莉,你是棵树。这就是我终于懂得树怕人的原因。”[2]她不仅要负责照顾家里,照顾孩子们,还要操持田地里的一切事情,阿尔伯特从不干活。而且她也很少说话,因为阿尔伯特总是让她闭嘴,其凶狠的眼神让她退避三舍。阿尔伯特就是一个自以为是、行径恶劣的男人。当茜莉最后离他而去的时候,他才开始反省,转而从事家务劳动。但是,茜莉在这一阶段受到母亲的影响,完全没有人格尊严,同样缺少女性意识。她和阿尔伯特结婚是因为她的继父要摆脱她,阿尔伯特也要找个人照顾自己的孩子们。所以,茜莉不爱阿尔伯特,她也不知要爱自己。她在家庭生活中完全处于没有话语权的最底层,也没有萌发任何反抗意识,一切都是逆来顺受。
(二)女性意识的觉醒——有语、有我
女性意识的觉醒,即女性从个体的自尊和自立走向群体的自强和自大。主要表现为女性要做到自尊、自信,而非自卑、自弱;能正确评价两性关系,坚持男女平等,而非男尊女卑。
小说《紫色》中,苏菲亚就是一个这样敢爱敢恨的女性形象,她第一次亮相的时候就给茜莉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她是一个身材高大、性格直爽的姑娘;当她和哈珀一起去拜访哈珀的父亲阿尔伯特,请求他同意他们的婚事时,就一直昂首挺胸,步伐坚定;在阿尔伯特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并认为她是一个很随意的姑娘的时候,她仍然昂首挺胸地离去,并告诉哈珀等他有空时再去看她,她和孩子会等着他;在她和她的兄弟们抬着母亲的棺柩进教堂时也是“步伐稳健,震得教堂咚咚响”。这样一个意志力坚定的姑娘却在生活中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困境。当她冒犯白人州长夫人不愿到她家当女仆的时候,她被关进了监狱并干了很多重活,但她毫不妥协,咬牙坚持;当哈珀企图像他的父亲一样控制并奴役她时,她就再也没有享受到丈夫的关爱和家庭的温暖了,但她也没有放弃,仍然在不停地抗争;当她得知是茜莉告诉她的丈夫要打她的时候,她感到非常伤心并告诉茜莉:“我一生都得打架,跟我爹爹打,跟我兄弟打,跟我堂兄弟和叔叔伯伯打。一个女孩在一个男人统治的家里是不安全的。可我从没想到在自己家里也得打一架。”[2]所以,女性要想在男权社会中保护自己就得不断地进行斗争和反抗,但是苏菲亚在和哈珀的长期打斗中,她一直孤军奋战,以致最后身心俱疲,被迫离开。苏菲亚的家庭遭遇也是缺乏母爱的结果。结婚前,没人关爱,处处小心;结婚后,没人理解,婚姻不幸。所以,在成长道路中,苏菲亚一直是被动的,孤单的。在小说中,苏菲亚的母亲形象并没有正面提及,只是一带而过她的葬礼。这说明人物本身可有可无,地位低下。因此,苏菲亚母亲的隐形身份让她在生活中受尽羞辱,但也让她看清了现实,只有不停地抗争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成为不附属男性的独立女性。这些也为茜莉女性意识的觉醒埋下了种子。真正让这个种子生根发芽的是莎格,阿尔伯特的情人。莎格是一个独立自信的女人,她是一位蓝调歌手,靠自己的能力生活在这个男权社会中。尽管她和阿尔伯特曾经相恋,但没有得到阿尔伯特父亲的同意。不仅如此,还受尽他父亲的鄙视和嘲笑,最终她也没有妥协,离开了阿尔伯特并过着自己独立的生活。后来在她生病期间,阿尔伯特把她带回了家,茜莉对她细心照顾。两个人共同的悲哀让她们变得非常亲密,茜莉也慢慢变得开朗,她不仅对莎格有了特殊的感情,也开始欣赏自己的笑容,关注自己的需求。所以,莎格的鼓励是茜莉改变自我的关键因素,她开始了有语并认识了自己。
(三)女性意识的形成——爱己、爱人
在小说中,茜莉没有得到过母亲的任何关爱和照顾,而索菲亚母亲的描述也是寥寥数语,最特殊的是莎格的母亲,她的形象几乎没有提到,仅阿尔伯特父亲说过一句话——她和她母亲一样下贱。但是,从这些女性的生活中我们可以得知,她们的母亲在家庭中的角色是微不足道、可有可无的,否则索菲亚不可能会说她的一生都在抗争,在家里她需要和任何一个男性作斗争。莎格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莎格虽在小说中是一个有职业的女性,不依赖男性独立生活,但她和男性的关系一直暧昧复杂,家庭观念也很淡薄。这些都是缺乏母亲的正确引导造成的。也正是由于这些女性的共同生活经历,所以她们才能紧紧联系在一起,并知道只有互帮互助才能真正过上独立自主的生活。茜莉本是一个胆小懦弱、麻木自卑的女孩子,但在索菲亚和莎格的帮助下慢慢地发现了自我并知道了女性并不比男性卑微低下。在她发现阿尔伯特藏着她妹妹写给她的信时,她愤怒地想杀了阿尔伯特。最终在莎格的游说下,她决定离开阿尔伯特并和莎格一起去孟菲斯市。茜莉的决定激起了阿尔伯特的强烈反对。他对茜莉恶意中伤,但茜莉并未妥协,而是说:“你是个卑鄙地家伙,这就不好!我说,是离开你,走出去创造新天地的时候了。你去死,我正好求之不得!”[2]最后还是坚决地离开了。到了孟菲斯市后,她学会了缝纫技术并开了一家做裤子的工厂。后来,工厂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她还招收了一批黑人女性帮忙。她感到非常快乐。裤子工厂是茜莉真正成长的表现。因为在西方传统观念文化中,女性是穿裙子的,裤子是男性的标志。茜莉裤子工厂的创办说明在她的思想意识中,男性和女性是平等的,女性再也不是男性的附属物,再也不比男性卑微低下。小说最后,茜莉还继承了生父遗留下来的房子,她开心地等着妹妹和孩子们的回归,等待家庭的团圆。自此,茜莉已彻底完成了她的华丽转变。尽管经历了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但在众多黑人女性的帮助下,茜莉彻底摆脱了父权制和夫权制的双重压迫,认识了自我身份,实现了自我解放;苏菲亚最终也在茜莉和其他女性姐妹的帮助下,原谅了丈夫的错误行为,和他重归于好;哈珀也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狭隘和不足,改过自新和苏菲亚一起共建自己的小家园。自此,母亲的隐形身份在她们孩子身上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小,孩子们最终都有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三、父亲的“病态”行为
传统观念中的父亲形象总是离不开高大、伟岸和安全感。只要有父亲在,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没有跨不去的鸿沟。父亲这一光辉形象在很多文学作品中也有具体体现。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新历史小说中,对人物的塑造不强调其“高大的形象,豪壮的语言,高妙的思想和超越历史迷误的眼光。相反,重点描写他们的日常生活,如吃喝拉撒、愚蠢呆憨和狭隘胸襟,使得传统的政治色彩消失殆尽。”[3]在《紫色》中,对父辈的描述就印证了这种观点。首先是茜莉的继父阿尔方索,一个行径无耻令人唾弃的家伙,整日算计着自己的继女,对她们图谋不轨;另一个是阿尔伯特的父亲老某某先生,对待自己的同胞从不伸出友好之手,反而恶语中伤,使出全身解数教他的儿子们怎样使用暴力让他们的妻子屈服顺从。这些黑人父辈的丑陋形象及其影响下孩子所过的扭曲而又痛苦的生活,究其缘由,都是白人霸权文化压迫和黑人自身文化缺失带来的结果。
(一)白人霸权文化压迫
文化霸权是指帝国主义国家借助传播媒介对后殖民国家进行文化和思想控制的一种意识形态的侵略。《圣经》指出白人是上帝的“选民”,而黑人则是他们的奴隶。法国人布弗恩伯爵也在《自然史》中明确表示白人是所有种族中最优越的种族,黑人之所以低劣是因为他们长期受到赤道阳光的照射而产生了世代遗传的丑陋“基因”。因此,黑人作为最低等的种族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4]。这些看似“科学”的论证为白人奴役黑人找到了最完美的借口。而黑人也在白色种族的剥削和压制下,精神一直处于无知、恐惧和依附的状态,除了被动接受这些奴役之外似乎别无选择。
在《紫色》中,沃克也从历史的角度解构了种族主义剥削,即“白人中心而黑人边缘,白人强大而黑人低下”[5]。小说中的老某某先生并非一个纯正的黑人,他有一半的血统是白人。沃克曾评论道:“老X先生憎恨自己黑人那一部分,于是他一辈子都在批判、诋毁和试图去控制比自己黑的人,不幸的是,这个人却是他自己的儿子。”[6]老某某先生对莎格的辱骂就是典型表现,因为她“太黑了”。老某某先生蔑视莎格,重点并不是因为她长得丑或是她行为不检,未婚生子,而是因为“她黑得象柏油”。在老某某先生看来,黑就是丑,就是卑微低下的同义词。尽管他有一半白人的血统,自恃比纯正黑人更加高级,然而他自始至终都不被白人承认,不得不生活在黑人聚集区,从事和黑人同等的工作。这种自我种族特征的迷失是白人霸权文化侵蚀的必然结果。白人文化和黑人文化就是典型的不平等的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这种文化不平等状态不仅会严重影响黑人文化的发展,还会在精神上贬低和蔑视黑人来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7]。此黑人男性既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也是加剧这一问题的元凶。茜莉的继父阿尔方索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生前不仅虐待茜莉的妈妈,让她最后疯癫致死;而且百般讨好白人,为了发达不择手段,对自己的同胞残暴欺辱。但就是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人,在他死后,他墓碑上的悼词却是:“当地商界要人和农场主、正直的丈夫和父亲,对穷人仁慈但无能为力啦。”[2]甚至在他死后两个星期,他的坟地仍然开着鲜艳的鲜花。这些讽刺的字眼表明黑人男性在现实生活中已经习惯了白人的奴役,知道自己不能和他们抗争,所以只好把愤懑转移到比他们更弱小的黑人女性身上,以此证明自己的“优越”。他们对黑人女性施加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侮辱从而展现自己的尊严,巩固自己的权威,充分说明了黑人男性盲目扮演着“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双重角色。在这种“白人至上”的观念腐蚀下,他们逐渐迷失自我,迷失种族特性,从而彻底沦为白人欺压黑人的走卒。
(二)黑人自身文化的缺失
美国黑人作为美国殖民地时期由其他地区掠夺而来的劳动力,其在长期的弱势地位上受白人文化压迫,跟本源文化隔绝,从而导致“固有特性”的弱化,甚至丧失,以至于他们对自身黑人文化的构建意识不强,对征得社会的认同也不足[8]。以阿尔伯特的婚姻经历为例,他和莎格彼此相爱,但却受到父亲老某某先生的百般阻挠,最后只能痛苦分手。莎格是一个独立自强的女性,有才华有能力,但在老某某先生看来,她未婚生子,是个贱货,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莎格的妈妈也是贱货,甚至怀疑莎格的孩子不是阿尔伯特的。这些都给阿尔伯特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最后草草娶了茜莉。这说明在白人主流文化影响下,黑人的彷徨和痛苦不仅仅来源于种族歧视,更多来源于黑人自身文化的丧失,而这种文化的丧失更多地体现在父权制和夫权制的压迫和剥削上。
在《性别和性质》一书中,奥地利作家奥托·威宁格尔说:“女性从来都不真挚的,因为她们既没有存在也没有本质。”除了被当作“男性表达和凸显他的性能力的工具”外,就一无是处了[9]。在《紫色》中,十四岁的茜莉在被继父第一次强奸后,继父对她的疼痛和流血视而不见,还命令她给他修剪头发。继而日复一日的折磨和殴打让她对男人只有害怕和恐惧。后来,继父对她厌烦,转而把她嫁给阿尔伯特。阿尔伯特第一次见她时骑在马上,而茜莉则顺着继父的要求转着身子,任由他上下地打量。这种自上而下俯视的目光揭示父权社会中男性至上的地位。茜莉和阿尔伯特结婚后还是逃脱不了他的暴力虐待。她在信中写道:“他打我,象打孩子们一样。”[2]他甚至把茜莉妹妹写给她的信藏起来,让两姐妹失去联系数十年。阿尔伯特对茜莉的种种做法都代表了黑人男性对女性的霸权行径。甚至当他的儿子哈珀带着怀孕的索菲亚来到他的面前时,他不仅嘲讽了索菲亚,还问了和他父亲相同的问题:“我们怎么会知道(孩子是他的)?[2]”这些都反映了他们父权思想的一脉相承。而哈珀对于父亲对索菲亚的侮辱与蔑视与阿尔伯特在面对他父亲对莎格的侮辱时的反映竟然一模一样,他们都是低下头去,沉默不语。当哈珀企图欺压并奴役索菲亚去问阿尔伯特方法时,得到的答案是“你打过她吗?老婆象孩子,你得让她知道谁厉害。除了狠狠揍她一顿,没别的办法[2]。” 这些都反映了父权制对男性身心的压制和戕害。
姓名缺失也是文化丧失的一种重要表现,是造成文化身份危机的重要标志。因为姓名是一个人的特殊身份符号,往往与民族文化和血脉传承息息相关。茜莉在被继父强暴后,被威胁不准告诉任何人,所以她只能不停地给上帝写信来倾诉痛苦。在信中,她一直用的都是“He”这样的字眼,因为一想到继父的名字就让她全身紧张和颤抖。而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从一开始也是没有名字的,在茜莉的信中一直以某某先生来称呼,因为这时候的阿尔伯特对她非打即骂,仅仅把她看成是干活和泄欲的工具,没有人的道德和情感,只有动物的野性和兽性。后来,在茜莉的不断反抗中阿尔伯特才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改过自新,从而获得了自己的名字。
种族主义的内化导致了黑人的自恨,并把这种自恨投射到其他黑人身上,其结果必然是整个黑人种族的自恨、自嘲和自灭,进而放弃自己的民族之根[10]。
四、结语
《紫色》中母亲的隐形身份一直是孩子们生活和情感上的伤痕,母亲自我意识的缺失是夫权制剥削和压迫的必然结果,而父亲的“病态”行为则是他们在强权文化中迷失自我、寻求自我的手段。随着孩子们身心遭受的折磨和反省,父辈的病态和扭曲心理在他们身上正逐渐变弱消失,父权制和夫权制对他们的影响也慢慢淡化;而黑人女性在相似的生活经历和情感遭遇中变得更加亲密,更加独立自强,彻底摆脱了母亲对她们的负面影响,开始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和经济权。这也正验证了沃克的妇女主义思想:黑人男女只有和谐共处,才能共同致力于全民族的生存和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