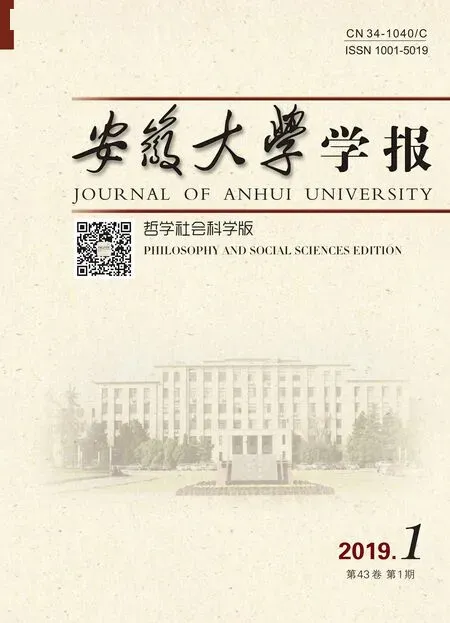我们为什么需要权利?
——论权利的独立性和必要性
吴 然
乔尔·范伯格(Joel Feinberg)在《权利的性质与价值》一文中描述了一个没有权利的社会。有趣的是,这不是一个人们遭受极权统治的社会,也不是一个你争我夺的无序社会。相反,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的合理利益都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各种价值都得到尊重,因为人们非常清楚彼此负有什么义务,而且这些义务得到了最为系统周全的规定。可以说,凡是其他社会通过权利来保护和促进的价值在这个社会中都得到了保护,甚至因为人们的美德能得到更为细致的保护[注]Joel Feinberg, The Nature and Value of Rights, 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vol.4, no.4, 1970, pp. 243-249.。这样一个设想的社会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义务和美德足够充分,我们是否还需要权利来促进价值实践?
这个问题其实是在问权利的独立性和必要性,问权利在价值实践中扮演什么不可或缺的角色且这些角色不能由义务或美德扮演。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我们需要权利的原因,正是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不尽然是美德,义务规定也并不详尽全面,各种价值不能得到全面的尊重。然而,这样的回答误解了权利独立性与必要性问题的重点。这一问题不是在考虑是否有必要由权利来补足义务或美德在现实中的未尽之责,而是问是否有必要由权利来补足义务或美德在概念上的未尽之责。如果我们不能给出可靠的回答,权利在概念上就很可能是冗余的。
这一问题在权利话语泛滥的今天,尤其值得重视。因为对权利独立性和必要性的判断会影响我们讨论和运用权利的方式。如果权利没有独立性和必要性,很多用权利作为基础提倡修改某种法律的主张就令人怀疑。相反,如果权利具有独立性和必要性,我们论证每一项具体权利时都应该将使权利独立且必要的因素纳入考虑,而且我们对某项具体权利的行使就不能违背我们拥有权利的理由。
已有的权利理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可以被归为两类,一类是从权利对于义务的基础地位出发,另一类是从权利与作为权利基础的价值之间的关系出发。本文将对这两种思路做出检讨,指出它们无法说明权利在价值实践中的独特且必要的意义。本文认为讨论权利的独立性和必要性需要我们尤其关注权利与指向性义务的关联。权利是从权利人视角回应义务的指向性,它的独立性和必要性就在于权利使得权利人以主动的地位参与价值实践。
一、基于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论证
(一)权利控制他人义务
H.L.A.哈特(H.L.A.Hart)的权利选择理论指出,权利意味着权利人可以自主控制他人的义务。权利人可以选择是否要求义务人履行义务,在义务人违背义务时选择是否诉诸法院以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以及选择是否豁免事后赔偿义务[注]H. L. A. Hart, Legal Rights, in Essays on Bentham: Studies in Jurisprudence and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83-184.。权利人不是他人履行义务的被动受益人,而是可以主动控制他人义务的人。我们在义务之外需要权利的必要性在于权利使得权利人可以控制他人的义务。相反,如果仅仅存在义务,权利人无法决定如何处置他人的义务。
然而,我们的权利并不总是赋予我们自主选择如何处置他人相应义务的能力。比如,我们不能豁免他人不得虐待我们的义务;在他人严重伤害我们的身体健康时,我们也不能豁免侵犯者受到相应的惩罚。哈特的权利选择理论只适用于可以让渡和放弃的权利(alienable rights),不适用于不可让渡或放弃的权利(inalienable rights)。换言之,对于我们生存和发展来说重要到不可让渡或放弃的权利并没有哈特所说的控制他人义务意义上的独立性。我们需要一个关于权利独立性的一般理论,既能解释可以让渡或放弃的权利,也可以解释不可让渡或放弃的权利。这一理论对这两种权利独立性的具体解释或许是不同的,但是必须能够同时解释,而不能只解释其中一种权利。
也许有人试图补强权利选择理论对于权利独立性和必要性的解释力,他们指出,这些不可让渡或放弃的权利提供我们拥有可让渡权利的前提条件,如生命安全、人身自由等。只有确实拥有这些事关我们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权利,我们才可能去谈论和实行对他人其他义务的自主控制。但是问题在于,这些权利发挥的前提性作用完全可以由与其对应的他人义务来完成。我们甚至可以将“不得豁免这些义务”规定为一种义务来确保人们生命安全或人身自由不受伤害。因此,该补充解释只是再次强调了这些权利和相应义务的重要性,却没有说明不可让渡不可放弃的权利如何不会被义务替代。
(二)权利证成义务
权利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思路是权利利益理论。最早由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的权利利益理论,将权利视为法律义务旨在增进的利益,极易导致权利附属于义务而变得冗余。但是在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发展权利利益理论提出权利充分理由命题后,将权利视为利益也可以保持权利独立于义务的重要性。该命题指出,权利是可以给出充分理由向他人施加义务的利益[注]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66.更多解释可参见吴然《基于角色责任的利益理论——权利概念分析新解》,《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1期。。
当然,这不是说义务总是对应权利,也不是说义务的来源总是权利,而是说对于某些义务来说,构成权利的那些利益因为具有某种价值而向他人施加这些义务。权利因此在实践推理中有了更为基础的地位,是相应义务的逻辑基础[注]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80.,也因此不会被义务取代。权利充分理由命题并不反对可让渡可放弃权利的权利人可以控制他人义务,只是指出这类权利使权利人可以控制他人义务之外,还有一个特征是构成这些权利基础的利益是他人义务的逻辑基础。这项特征使得可让渡可放弃的权利在概念上有了独立于对应义务的重要性。同时,权利充分理由命题同样适用于不可让渡不可放弃的权利,它们都是他人义务的逻辑前提,因此无法被义务替代。
然而,权利的充分理由命题只是让权利独立于与其对应的义务,却没能让权利独立于作为权利基础的利益的价值。因为在该命题中,可以向他人施加义务的并不是权利(或构成权利的那些利益)本身,而是这些利益对于人类福祉的价值。这些利益或者具有内在于权利人福祉的价值,或者对于他人福祉或公共福祉有不可或缺的工具性价值[注]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pp. 178-179; Joseph Raz, Rights and Individual Well-Being, in 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 revise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50-55.。简言之,权利人利益对于人类福祉的价值才是义务的逻辑前提。但是,既然价值才是证成义务的基础,那我们似乎只需要价值,未必需要权利。我们要阐释清楚权利的必要性和独立性,不仅要说明权利如何相对于义务有独立性,还要说明权利如何相对于价值有必要性。
(三)权利作为价值到义务的中间结论
拉兹进一步解释说,权利的必要性在于作为从终极价值到义务的中间结论。中间结论有着不可缺少的重要性:当人们对于终极价值充满争议时,只要人们赞成存在某些权利,就会直接使用这一中间结论,而不必总是去问终极价值是什么才决定是否采取某些行动。这意味着,作为中间结论的权利可以“节约时间和避免繁琐”,还可以“使人们围绕中间结论形成一种公共文化”,进而使社会生活变得可能[注]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p.181.。比如大多数人认为作为婚姻权基础的是人们与心仪伴侣共同生活的利益对婚姻当事人福祉的价值,但也有人认为婚姻权是在回应人类繁衍生生不息的利益对于家族或者人类整体的价值。尽管如此,大家普遍接受“人有婚姻权”这个中间结论,因此承认“不阻止情侣结婚”这一义务和“国家保护合法婚姻”这一义务。在引导他人应该如何行动的过程中,婚姻权作为中间结论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也在社会中促进形成一种尊重婚姻的公共文化。
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直接把作为中间结论的权利本身当作理由来用,而不管它们背后的终极理由是什么,“就好像它们本身就是完整的理由一样”[注]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p.181. 不过,拉兹并不认为只有权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当中间结论,义务、规则等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充当中间结论。。比如,人们可能对作为隐私权的基础价值意见不同,但是这不妨碍我们将隐私权本身视为一项理由,来反对他人侵犯自己的隐私。因此,虽然价值优先于权利,权利只是价值到义务的中间结论,但是由于中间结论能节约时间和促成公共文化进而成就社会生活,权利对于价值实践而言有其必要性。
然而,这种诉诸权利作为中间结论的工具性意义论证权利独立性和必要性的思路存在一个问题,中间结论并不总是能发挥这样的工具性作用。其一,如果我们不能明确一项权利的基础价值,我们可能不仅无法达成中间结论,甚至还直接否认存在这项权利。其二,某项权利能向谁施加什么义务,某项行动究竟是否侵犯了某项权利,也常常充满争议,解决这项争议往往需要诉诸权利的基础价值。比如,受教育权能向国家施加多大程度的免费教育义务?再比如,未经他人允许私自拍摄他人在公共场合的行为,是否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犯?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诉诸受教育权和隐私权的基础价值。权利作为中间结论,并不总是能节省时间和精力,反而可能引起关于权利本身的更大争议。我们关于权利独立性和必要性的判断应该是更可靠的更稳固的,而诉诸权利作为中间结论的工具性意义不能实现这一目标。
二、基于权利与价值关系的论证
(一)权利与价值选择
我们确实常常对一项权利允许我们做什么或他人有义务容忍我们做什么意见不一,也常常就一项权利的基础价值持不同看法。杰里米·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认为,权利的独立性和必要性正在于保护我们在面对这些争议时做出自己的价值选择。具体地说,在诸如职业选择、宗教信仰、婚姻伴侣的选择、私有财产等领域中,个人自主作为基础价值证成了相应的一般权利,如职业选择权、宗教信仰自由权和婚姻自主权等[注]Jeremy Waldron, A Right to Do Wrong, Ethics, vol. 92, no. 1, 1981, pp. 34-35.。这些权利保护我们在这些领域内依据自己对价值的理解或偏好等做出任意选择,无论这些选择是否明智或缺乏品味,也无论这些选择是否道德错误[注]Jeremy Waldron, A Right to Do Wrong, Ethics, vol. 92, no. 1, 1981, p.37.。
上述观点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权利保护我们在这些领域做出的道德错误选择。虽然道德会对我们在这些领域如何做选择提出要求,告诉我们什么是道德允许的和什么不为道德允许,但是权利不在意选择的道德正误。凡是权利人自主选择的选项,权利都施加保护,保护方式是权利人在自主选择行动时可以排除他人的强制干涉[注]Jeremy Waldron, A Right to Do Wrong, Ethics, vol. 92, no. 1, 1981, pp. 29-30.。比如尽管购买奢侈品相较于从事公益事业来说显然没有什么道德上的吸引力,但是财产权保护我们购买奢侈品。这使得权利区别于道德和道德上重要的各种价值:道德和价值引导我们做出选择,并为我们的各种选择提供正当化说明;权利则是保护我们的选择,帮助我们排除他人的强制干涉。
然而,如果权利确实如拉兹所说可以塑造某种公共文化,而权利确实保护道德错误选择,那么它塑造的公共文化(如奢侈品消费)可能并不值得追求。这是沃尔德伦解释权利独立性方式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找到的权利独立性和必要性可能将我们带到道德上糟糕的境地,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这种独立性和必要性?此外,我们不难注意到,沃尔德伦语境中的权利共享一个基础价值——自主,它们的差异只在于促进不同领域的自主。这个共享的基础价值提示我们这些权利无法区分于“自主”这种价值。与其说是财产权、宗教信仰自由权等权利在保护我们的各项选择,不如说是自主在保护我们的各项选择。沃尔德伦思路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做道德错事时未必可以正当排除他人的适当干涉。比如当一个人在做道德极其邪恶之事时,即使是他的个人自主也没法帮助他排除他人的适当干涉[注]Ori J. Herstein, Defending a Right to Do Wrong, Law and Philosophy, vol.31, no.3, 2012, p.347, p.359.。做错事的权利本身是需要单独证成的,但我们未必能够证成这项权利。
范立波提出权利的内在道德命题,对沃尔德伦的价值选择观点做了修正补充。根据这一命题,权利的内在道德之一是尊重“以自主为核心的个人福祉”。一个选择要得到权利的保护,首先要尊重以自主为核心的个人福祉。同时这个选择还必须符合一项权利的基础价值,才能得到该项权利的保护[注]参见范立波《权利的内在道德与做错事的权利》,《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范立波在文中指出,权利的构成性规则是“X因为I而对Y拥有权利”,这里的“I”便是指该项权利的基础利益。。这意味着,权利并不保护所有道德上错误的选择。如果一项选择不仅道德上错误且违背权利的内在道德,那么权利不保护该项选择。
我们不妨以医生开具药方的权利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作为这项权利基础的价值是病人的身体健康对于病人的个人福祉的内在价值以及医生出具专业化医治建议对于履行职业角色责任的构成性价值。按照沃尔德伦的观点,医生为了实践这些价值,似乎可以随意选择药品,其选择似乎不受病人身体健康和医生职业角色责任的限制。显然,这样的结论让我们感到担忧。当然这也可能不是沃尔德伦的本义,但是他的前述观点确实容易将我们误导至此。内在道德命题可以减少我们的这些担忧。医生开具药方的权利既允许医生做出选择,也要求医生根据病人身体健康价值的引导对症下药,还要求医生以尽可能最佳的方式履行自己的角色责任。这也就排除了医生开具价格更贵而药效并无不同的药品的可能。
从解释权利的独立性和必要性来看,与沃尔德伦的思路相比,内在道德命题对受到保护的错误选项做了限缩,强调每项权利的基础价值对于选择的筛选意义。更重要的是,内在道德命题将自主从外在于权利的价值转变成权利的内在价值。这样一来,只要自主价值是必需的,权利就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内在道德命题仍没有成功地说明权利相对于价值的独立性和必要性。首先,每项权利的基础价值是每项权利的构成性内容,进一步说明权利无法独立于基础价值而存在,不能说明权利对于这些价值而言的必要性。其次,虽然自主是内在于权利的价值,但是权利并不内在于自主。换言之,如果自主的实现不一定要求权利,权利并不因为我们无法缺少自主而获得必要性和独立性。
(二)价值实践依赖权利
沃尔德伦的观点和内在道德命题与其说论证了权利对于价值和价值实践的必要意义,不如说进一步承认了权利在概念上依赖价值。即使是引入自主,也只是丰富了权利的价值基础,而且还使得权利与价值之间的必然关联更加密切。不过,这也提醒我们,我们论证权利独立性和必要性的有效思路不是否认权利依赖价值,而可能是论证价值同样依赖权利。阿朗·哈雷尔(Alon Harel)做出了这一转向,提出权利与价值的“互惠命题”[注]Alon Harel, Why Law Matt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3.哈雷尔提出的互惠命题主要是在说法律权利与价值的相互作用。但是,本文认为,其关于法律权利的描述也可适用于道德权利等。因为道德权利等其他权利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价值实践对于特定行动的需要,并且有助于人们理解价值和形成有效实践某些价值的公共文化。不过,我们也需要承认法律权利在促进价值实践方面有独特于道德权利的地方,比如法律诉讼转变人们关于价值的理解的效率远高于道德权利。但是这些差异并不影响我们将互惠命题(如果成立)一般地适用于道德权利等其他权利。。该命题承认权利对于构成权利基础的价值的依赖性,证成一项权利的基础在于价值;但同时坚持价值也依赖于权利,权利不是“促进价值实现的简单规范”,而是通过做出一定的限制使得价值实现变得可能[注]Alon Harel, Why Law Matters, p.13.。权利在促进和实现这些价值方面发挥着价值自己无法发挥的作用。
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价值的实现依赖于特定行动。特定价值(未必是所有价值)和特定行动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特定行动对于特定价值的依赖,表现为特定行动因为可以促进该项价值而值得保护;另一方面是特定价值对于特定行动的依赖,表现为这项行动能促进该价值的前提是,行动者是出于对该价值的尊重而采取该行动[注]Alon Harel, Why Law Matters, p.15, pp. 39-41.。总之,有效实践价值要求我们对行动做出筛选并且将促进价值作为采取该行动的基础理由。此外,认可特定行动对于该价值的重要意义,以及普遍知晓行动者应该出于何种理由采取该特定行动的公共文化更有利于人们采取该行动并进而促进实现该项价值[注]Alon Harel, Why Law Matters, pp. 41-42.。比如现代社会认可自主选择婚姻对于个人自主的重要意义,这种公共文化更有助于促进婚姻自主。
权利在实践其基础价值时恰恰满足上述要求。首先,我们可能有多种理由要求保护某个行动,但是权利不认可所有行动理由,而只认可其中一些行动理由,那些促进该权利基础价值的理由。比如,获得收入是保护个人职业选择的一个理由,但是职业选择权只认可“自由职业选择可以促进个人自主”这一项理由[注]Alon Harel, Why Law Matters, pp. 14-15, pp. 18-25, p. 27.。其次,权利对行动有筛选。对于看上去可以促进某种价值的诸多行动,权利并不都给予保护,而只是保护其中一些行动。比如财产权不保护人体器官交易,言论自由权不保护人们发表诽谤性言论等。这就意味着,权利对实践价值的具体方式做出了筛选,而且这个筛选不是基于有多少分量的理由支持某种可以促进某种价值的行动[注]Alon Harel, Why Law Matters, p.15, p. 18, p. 27.。这样的筛选既对人们实践相关价值时持有的理由做出了要求,也对人们实践某种价值的具体方式做出了限制。
人们可能质疑权利事实上无法限制人们出于什么理由实践某种价值。因为只要其实践方式在该权利保护的行动范围内,权利就不能拒绝给予这些行动保护。比如婚姻自由权以在建立亲密关系方面的个人自主为价值基础,但是当一个人出于对方家庭资源丰厚接受父母关于自己婚姻的安排时,权利无法拒绝给予该选择保护。但是,互惠命题不是说权利可以事实上确保人们确实出于内在于相关价值的理由采取行动实践该价值,而是说权利明确告知人们在相关领域内应该如何理解这种价值,告诉人们促进某种价值的典型情形和应该出于何种考虑来采取某种行动,进而塑造一种尊重和促进该价值的公共文化和惯例[注]Alon Harel, Why Law Matters, p. 17, pp. 41-48.。比如当有人基于财富和地位选择婚姻伴侣,社会中的其他人可能会指出他这样做不是对婚姻领域个人自主的恰当实践方式。再比如,当一项权利进入法律层面并且出现相关诉讼,诉讼会更为清晰地说明这项权利的基础价值和实践该种价值的正确方式,传播关于该项价值的信息,引起公众实践该价值的兴趣,甚至唤起公众参与完善实践该价值的社会惯例[注]Alon Harel, Why Law Matters, p.17, p.44.。因此,权利有助于行动者理解这些价值和采取适当行动,也有助于构建认可特定行动重要意义的公共文化。
然而,即使价值实践依赖于人们出于以特定价值为基础的理由采取特定行动,而权利可以使这些行动成为可能,价值对权利的必然依赖命题也未必成立。首先,正如哈雷尔自己承认的,互惠命题并不适用于所有权利[注]Alon Harel, Why Law Matters, p.14.。其次,互惠命题似乎默认人们对所讨论权利的基础价值意见一致。当我们对一项权利的基础价值充满争议时,我们无法确认一项权利在引导我们实践何种价值。再者,虽然价值实践确实依赖于人们出于以特定价值为基础的理由采取特定行动,但并不只有权利可以使其成为可能,其他概念也可以使价值实践成为可能。比如,规定每个人有义务尊重某种价值并出于以该价值为基础的理由实践该种价值,也可以形成上述公共文化。甚至使用各种传播手段的道德教育、围绕某些价值的文艺活动等也有利于这些公共文化的出现。权利有助于构建上述公共文化,但不是构建上述公共文化必不可少的方式。
但是,我们需要承认哈雷尔思路的合理之处在于其从权利在构建上述公共文化方面的作用说明权利的独立性和必要性是可行的,至少可以突出权利相对于价值的必要性。哈雷尔的可惜之处在于,他没有沿此思路成功说明权利在构建上述公共文化上如何不同于其他道德或法律规范,如义务或美德。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权利在构建尊重某种价值的公共文化和引导人们实践价值方面究竟发挥了哪些无法由义务或者美德等其他道德或法律规范发挥而又是价值实践所必需的功能?
三、可能的新思路:基于义务指向性的论证
通过上文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事实上权利离不开价值,因为权利由价值证成。本文认为,权利以价值为基础而无法独立于价值,这一事实本身并不导致权利变得冗余。这就好像义务,义务也以价值为基础,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认为义务是冗余的。我们讨论权利的独立性和必要性,不是说权利一定要独立于价值,也不是一定要指出权利在价值到义务的证成过程中扮演什么独特的角色,以至于一旦离开权利,价值到义务的证成过程就无法顺利完成。权利和义务都是由价值证成的概念,也都是被精心设计来实践价值。我们要找到权利的独立性和必要性,只要能说明权利在价值实践过程中发挥着与义务或美德不同且必要的作用就可以说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
本文认为一个可能的思路是回到权利的概念结构。权利是一个与义务指向性有关的概念。“义务的指向性”指义务人向某个特定的个人或整个共同体负有该项义务[注]“义务的指向性”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例如,Michael Thompson, What is it to Wrong Someone? A Puzzle about Justice, in R. Jay Wallace, Philip Pettit, Samuel Scheffler, and Micheal Smith(eds.), Reason and Value: Themes from the Moral Philosophy of Joseph Raz,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33-384; Gopal Sreenivasan, Duties and Their Direction, Ethics, vol. 120, no. 3, 2010, pp. 465-494; Stephen Darwall, Bipolar Obligation,in Morality, Authority, and Law: Essays in Second-Personal Ethics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0-39.如何判断一项义务指向谁,是另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本文暂时不处理这个问题。。义务的指向性有特殊的实践意涵:(1)当义务人违反指向性义务,他不仅是在犯一个简单的错误,而且是在对义务指向对象犯错。(2)在义务人违反义务之前,义务指向对象可以要求义务人为其利益履行义务,有时候还可以选择是否豁免义务人的义务(这主要指可让渡可放弃权利的情形)。(3)在义务人违反指向性义务之后,义务的指向对象可以谴责义务人,要求义务人向自己道歉或赔偿,还可以选择原谅义务人。义务的指向对象就是权利人,与指向性义务对应的概念正是权利。
首先,主张权是与他人指向性义务直接关联的权利。当X有一项指向Y的义务,Y拥有要求X履行相应义务的主张权[注]See Wesley Newcomb Hohfeld, 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 23, no. 1, 1913, pp. 30-32.。当然,不是所有义务都对应主张权。比如慈善和慷慨的义务,即使我们认为道德上存在这些义务,我们也不认为谁有要求人们给予慈善和慷慨待人的主张权。从本质上说,这是因为这些义务没有明确的指向对象而不是指向性义务,因此没有与其对应的主张权和主张权人。但是,当义务有明确指向对象(如特定个人或特定社团或整个社会共同体),就有一项对应的主张权。比如国家提供义务教育的义务明确指向每个适龄儿童,每个适龄儿童都有一项要求获得义务教育的主张权。
其次,自由权也是与义务指向性有关的概念。自由权是对义务的否定,当Y没有不做某事的义务,Y就有一项做某事的自由权。尤其是,当某人要求Y停止做某事,Y可以否定自己对干涉者有不做这件事的指向性义务。换言之,自由权也意味着干涉者没有要求Y为相反行动的主张权[注]See Wesley Newcomb Hohfeld, 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 23, no. 1, 1913, pp. 32-33, pp. 38-39.。当然,这不是说自由权只否定指向性义务,而是说当Y对X说自己有做某事的自由权时,至少表明了Y对X没有不做这件事的义务。X可能是所有人,也可能只是部分人或特定人。比如婚姻自由权人可以自主决定是否结婚和选择结婚对象,这项自由权意味着权利人对任何人都没有接受他们婚姻安排的义务。而在A同意B可以自由使用A的电脑的情况下,B使用他人财产的自由权限于A,而不能扩展至其他人。因此,对干涉者主张自己有一项自由权,是在否认自己对干涉者有一项相关的指向性义务,即否认干涉者有一项主张权。
主张权表明他人对自己有一项指向性义务,自由权则表明自己对某个或所有他人没有指向性义务。在这个意义上说,权利在概念上与指向性义务必然关联。但是,人们可能怀疑,这还不足以说明权利的独立性和必要性。因为一旦我们区分指向性义务与非指向性义务,并且从义务人角度区分履行指向性义务与非指向性义务的方式,就可以满足义务指向性的实践意涵并能够促进价值实践。因此,想要说明权利拥有价值或义务等不可替代的独立性和必要性,我们可以从这一概念关联出发,但必须进一步说明这种概念关联有何无法被替代的实践重要性。即如果没有权利来关联指向性义务,指向性义务的实践意涵无法实现,也无法有效促进指向性义务想要促进的价值。因此,我们的问题具体化为“权利”这个概念相较于“指向性义务”究竟多了些什么? 为什么我们必然需要“权利”来回应“义务的指向性”?
本文认为,权利与指向性义务最大的区别在于“权利”将权利人引入了价值实践,而且赋予权利人主体地位。如果只谈义务,我们关注的只是义务人有义务做什么,而不关心权利人与这些义务有什么关系。那么,事前对义务人的要求和事后对义务人的谴责或惩罚也都可以由国家或政府来提出和执行,不需要任何真正拥有该价值的个人(也就是权利人)参与。而引入指向性义务之后,义务指向对象进入我们的视野,义务人会意识到自己的义务是指向谁的,也会意识到违反指向性义务不是在简单地犯错,而是在对义务指向对象犯错。甚至,义务人也会被告知义务指向对象事先可以要求义务人履行义务或者豁免义务人的义务,而且可以在事后谴责义务人并要求义务人承担责任。然而,只提及指向性义务不足以解释义务指向对象提出上述这些要求的立场和身份,也不足以给义务指向对象具体的方式和媒介提出这些要求。只谈义务或只谈指向性义务还会造成这样一种误解——价值实践似乎只是义务人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义务人的义务首先促进的是义务指向对象的某种利益,是对义务指向对象个人福祉有利的价值,我们就更能认识到只谈指向性义务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将视角转至义务指向对象。
“权利”正是从义务指向对象的视角回应义务的指向性。主张权使得权利人以主动的地位参与价值的实践,而不是被动地因他人的某项义务指向才出现在价值实践中。而且主张权表明,权利人参与价值实践的方式是作为价值拥有者主动采取行动促进某种价值(如婚姻领域的自主、人格尊严等),或在价值受到伤害时主动寻求救济,而不是被动地依靠他人履行指向性义务来保护和促进对自己有价值之物。自由权也使权利人得以主动参与价值实践。自由权人不是被动地躲开他人对自己的要求,而是可以主动拒绝他人对自己提出的要求而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
总之,权利从义务指向对象的视角回应义务的指向性,使得权利人与义务人一起主动参与价值实践。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作为主张权基础的价值(也是指向性义务想要促进的价值)不仅从根本上证成了他人的指向性义务,而且证成了价值主体的主张权;作为自由权基础的价值不仅证成了价值主体不对他人负有一项指向性义务,而且也证成了价值主体遵循自己意愿行动的自由权。指向性义务告诉义务人为价值主体和为价值主体的何种价值履行义务,权利则确认价值主体主动参与价值实践的地位。这种主体地位表现为前文提到的要求义务人履行义务和在义务人侵犯权利后要求义务人承担事后责任。
权利人的这种主体地位不仅是由于权利人是义务人通过履行义务想要促进的价值的拥有者,更是源于权利人的尊严。与此同时,权利也给了权利人彰显自己尊严的一种有效途径。范伯格认为,权利使得权利人能够提出要求[注]Joel Feinberg, The Nature and Value of Rights, 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vol.4, no.4, 1970, p.252.。更确切地说,是权利人的尊严和权利人拥有的价值使人们拥有权利和提出要求的地位和资格,但是权利提供了相对具体的方式和媒介使人们“提出要求”成为可能,使权利人提出的要求产生实际效果,并且在要求未产生实际效果时继续对义务人提出要求。在道德权利的情形中,这种事后主张表现为权利人的谴责和抱怨。在法律权利的情形中,权利人的这种主体地位表现得更为明显,权利人可以诉诸国家机关来确保自己的要求产生实际效果。
从权利回应指向性义务来讨论权利的独立性和必要性问题与前文提到的权利与价值的互惠命题并不冲突,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强该命题,说明价值如何依赖权利。价值的实践分为基本和高级层面。高级层面的价值实践由美德、分外之责等来完成。基本层面的价值实践则由义务和权利来完成。其中一些义务是指向性义务,权利就是在回应义务的指向性,进而使得权利人主动参与价值实践。与美德、分外之责等相比,权利促进价值实践的独特性在于给予价值主体提出要求的方式和媒介,并保证其要求可以产生实践效果。与(指向性)义务相比,权利关注不同的价值实践者并给予该实践者主体地位,权利关注的是义务指向对象,也即权利人。我们有必要区分价值的实践者,这会影响我们参与价值实践的态度。权利人在实践价值的过程中同时作为价值的参与者和受益人出现,而义务人在参与价值实践的过程中主要扮演参与者和牺牲者的角色。前者在价值的实践中更容易有积极的态度和动机,而后者则需要被强调和灌输一种理念:为了权利人参与价值实践。这种区分也会对权利人如何行使权利提出要求。权利人是为了参与价值实践而拥有这些权利的,因此行使权利的方式不能违背作为权利基础的价值的要求。价值实践不仅依赖于他人采取促进价值的行动,而且依赖于价值主体主动为自己的价值参与价值实践,向他人主动提出要求或者主动拒绝他人的要求。价值主体参与实践的立场和方式只能由权利来确认和提供,因此价值实践也依赖权利。
四、结 论
本文主要讨论权利的独立性和必要性。要成功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说明权利在价值实践中发挥义务或美德等无法发挥的作用,而且同时必须说明这对于价值实践来说不可或缺。哈特和拉兹都是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角度论证权利的独立性,指出权利有优先于义务的意义。然而哈特忽视了那些不能控制他人义务的权利,拉兹把权利看作终极价值到义务的中间结论的观点则有可能将权利的独立性建立在偶然的工具意义上。沃尔德伦、范立波和哈雷尔从权利与价值的关系角度论证权利的独立性。他们都承认权利是对价值的实践。沃尔德伦与范立波强调权利保护我们关于价值的自主选择,突出权利区别于其基础价值的地方在于它包含了对自主价值的实践。然而,既然权利是对权利基础价值以及自主价值的实践,我们只要直接实践这两种价值即可,并不必然需要权利。哈雷尔则试图说明价值实践依赖权利。对价值的实践是需要精心设计的,需要人们理解价值并出于以特定价值为基础的理由采取特定的行动而非任意行动,同时还需要尊重该价值和承认特定行动可促进该价值的共同文化。权利标示着如此实践的社会惯例,是连接价值与行动的桥梁。可惜,义务和美德也能满足价值与行动之间的相互需要,哈雷尔还是没能说明权利在价值实践层面的独立性和必要性。
本文从义务的指向性出发论证权利的独立性和必要性。这一思路并不否认已有路径对权利与义务、价值关系的判断,承认主张权人能够控制他人对其负有的某些义务,也承认我们在行使权利时不能违背作为权利基础的价值,并且可以在权利允许的范围内自主选择行使权利的具体方式。从义务的指向性看权利的独立性和必要性也不否认确认权利有助于我们理解其背后的价值和原理,明确应该出于何种理由行使这些权利,塑造一种促进某种价值的公共文化。本文只是认为这些都不足以说明权利在实现价值方面的必然内在意义。我们需要从义务的指向性看待权利的独立性和必要性。在回应义务指向性的过程中,权利将“权利人”这个主体带回我们的视野,为价值主体主动参与价值实践确认立场和提供方式,满足价值实践的必然需要,而且无法为义务和美德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