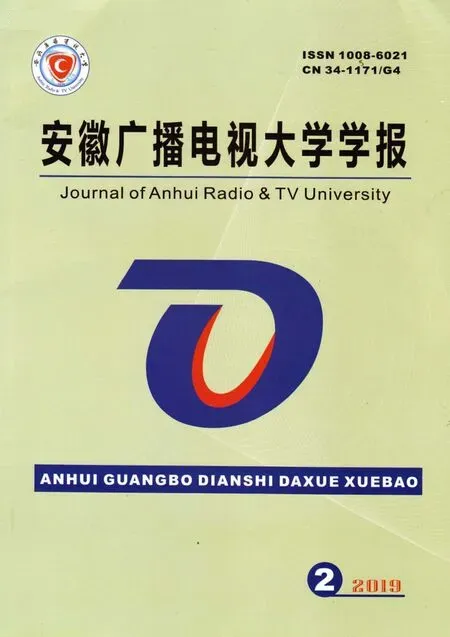论乔叟中世纪宗教文化叙事
——以《坎特伯雷故事集》修女院长故事为例
陶丽丽,高艳丽
(山东科技大学 外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590)
巴尔扎克说过,“宗教永远是政治的必需品。”在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呈现的欧洲中世纪晚期,基督教发展鼎盛,是主要的宗教信仰,但由于教会内部黑暗,教廷腐败,道德沦丧,开始慢慢走向衰落。费尔巴哈认为,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已不同于自然宗教,是统治者作为政治实体占有、决定、统治、支配也是政治实体的人的精神宗教[1]。乔叟的女修道士故事以赞颂基督信仰为目的,成为当时宗教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代表,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她的宗教叙事,是身份政治与种族政治的历史缩影,体现了中世纪宗教文化的政治霸权本质。
一、叙事语言中的宗教偏见潜意识
《坎特伯雷故事集》主要以第一人称叙事展开,并以故事中人物的口吻讲述故事。女修士作为叙述者表现出宗教优越感,首先表现在语言上赞颂“我者”信仰和贬斥“他者”的对比鲜明的词汇运用方面。对于圣母的描述是“洁白似百合花的”(ofthewhytelylyeflour)、“荣誉的”(honour)、“贞洁的”(maydealways)、“仁慈的”(rooteofbountee,magnificencevertu,benyngnytee)、“谦卑的”(humnlesse,gretehumylitee)、“明慧的”(sapience)、“伟大神圣的”(goost,blisful,greteworthyness) ,是“美德”和“圣洁”的代名词,是博爱世间万民的慈善者。讲故事是为赞颂圣母玛利亚,并“向圣母致敬”(totellitinthyreverence)。相反,犹太教徒的形象被刻画为“卑劣”(vileynye)、“邪恶”(foule)、“可憎”(hateful)的,犹太人“污秽的钱财,是通过放高利贷获得的”(Forfouleusureandlucreofvileynye39[注]本文的引文摘自网址http://www.librarius.com/cantales.htm 中《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古英语原文,引文后的数字为其在书中的行数,译文为笔者自译。),“该死的犹太人”(cursedJews233)是 “恶毒的(cursednesse179)”,是“毒蛇般的撒旦,我们的天敌,他们的心灵是黄蜂的巢窝”(Ourefirstefoo,theserpentSathanas,/ThathathinJeweshertehiswaspesnest106-107),他们“对基督徒充满了深仇大恨”(HatefultoChristandtohiscompaignye40)。这种对自身信仰产生的优越感和对异己信仰产生的贬伐态度,泾渭分明,具有排他性。赞扬我者,排斥他者,用二分法去评价人,丧失了公允的判断,是典型的宗教逻格斯中心主义。除了有意识的词汇褒贬,语言的无意识也体现了这一点。叙事中使用主动语态描述基督徒的积极主动,而使用消极被动的语态对犹太教徒做补充说明,体现了以“我者”为尊的潜意识,正如伊格尔顿认为,从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角度来看,历史对语言具有“生产性”,“譬如作为原材料的语言,不再是清白的中性工具”[2],而是“布满了政治历史的灾变留下的疤痕和裂隙,到处散落着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以及阶级搏斗的遗墟废址”[3]。叙事语言的使用揭示了中世纪基督教对异教文化的偏见潜意识,特别常把犹太人“看成在种族和宗教上均属特殊类型的”异类,进行丑化和污秽化,体现出不接受、不平等、不自由的宗教态度。否认异质文化的差异性,排除其他一切异质宗教文化的一神教,是黑格尔历史目的论的虚无主义表征,是一种“狭隘的”宗教中心主义。
二、叙事结构布局的宗教霸权隐喻
除了叙述者的叙事语言运用,叙事结构框架中内容比例失衡,侧重了圣母与基督徒的救赎与颂圣,犹太人部分不仅比重小,而且没有正面叙述。他们集体“无声”,完全丧失“话语权”,在主流文化之外被他者化、边缘化和异类化。叙事之初,案件缘起,儿童每天在犹太聚居区吟唱圣母赞歌,犹太人愤而杀童,犯下了罪恶行为,并遭到残酷刑罚。然而,犯罪动机并不明晰。犹太人为什么会因孩童的一首歌曲反映如此强烈?对于犹太人因为感到自己的宗教信仰受到羞辱,而产生复仇或反抗的行为,在整个叙事中被遮蔽,只是强调了他们的残暴与罪行。很明显,叙事的话语权在女修士手中,在叙述者的偏见下,犹太人及犹太思想没有表达的机会。存在主义理论家萨特,曾主张文学要“能在审美命令的深处觉察道德命令”,即作家要弘扬正义,揭露一切非正义的行为。在其“自由的选择”理念影响下,他把文学的自由和政治的自由联系在一起,主张用文学反对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人奴役人的社会制度。他认为,“任何时候也没有人会假设人们可以写出一部颂扬反犹太主义的好小说。”[4]经典作品《坎特伯雷故事集》并不会和故事的叙述者持同样的反犹主义思想,那么,女修士的故事恰恰是通过“狂欢化”叙事对反犹主义思想进行了反讽和质疑。
这样失衡的叙事结构,却并不能掩盖一神教的政治霸权目的。反犹主义的历史背景证明了这一点。故事中把杀童的凶手认定为犹太人,正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对持不同宗教思想的异教徒的一种主观迫害和贬低。1240年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对犹太人进行诬告的事件开始不断出现。血祭诽谤就是这类指控中常用的一种。在这一诽谤中,犹太人被指控无端杀害基督徒,特别是基督男童,用他们的血祭犹太人的神。”“尽管根据犹太教的教义,明文禁止犹太人食用任何血液,人们还是相信此类谣传。”[5]那么,本文故事中的杀童凶手被指定是犹太人,就可能也是基督教对犹太教徒的又一次莫须有罪名的诬告和诽谤。并且,叙事过程中没有任何作案过程的描述,和犹太人有关的证据只有一条,那就是孩子的尸体是在犹太人居住区的臭坑里找到的。这条证据能直接证明凶手就是犹太人吗?不能。有人可能会反驳说,肯定犹太人为罪犯是因为只有他们有作案动机,那就是受辱后的愤怒。七岁学童的确唱了一首颂扬圣母玛利亚的赞歌,然而,所涉赞歌“慈悲圣母(Almaredemptoris)”是一首具“安全性”的赞歌。它不似其他圣母赞歌,如“我爱玛丽亚(AveMarie)”那样包含了辱犹措辞,具有煽动性。这一点“暗示了到1380年代,犹太人因孩子所唱歌曲而愤怒的合理解释已经不再必要”[6]。然而,在案件疑点重重之时,基督徒的市长未经调查,马上“就下令把犹太人都捆绑起来(Andafterthat,theJewesleethebynde168)”。然后,犹太嫌犯也没有发声或辩护,而是直接被下令集体处以酷刑。审判过程的不合理与不公正是以主流宗教为中心的反犹主义思想在作祟。
由此可见,“杀害基督徒,特别是基督男童”的罪魁祸首不管是不是犹太人,修女的政治叙事必然要求对持“异见”的犹太教徒进行贬斥和镇压,这与查尔斯·金斯莱的《希帕提娅》中,一位优秀的希腊女子因宣讲新柏拉图思想,而被基督徒杀害一样,都是特定时期对“异见”身份者的迫害。正如福柯所言,“权力总是要在知识和意识形态上打上自己的烙印,使其为自己服务。”[7]因此,叙事结构的不均衡是意识形态霸权思想主导下对“异见”身份者进行排斥与镇压的结果,是宗教争斗中排他性的政治体现。
三、叙事伦理的宗教教化目的性书写
作品的伦理价值观在叙事的结局部分体现得淋漓尽致,具有鲜明的文化教化目的性。虐杀儿童的案件在最后惩治了凶犯,伸张了“正义”。然而,处罚场景很夸张,“市长把每个预闻这件凶案的犹太人都处以酷刑”(Withtormentandwithshamefuldeethechon/ThisprovostdooththeJewesfortosterve,/Thatofthismordrewiste,andthatanon176-178),“用野马拖拽他们,然后依法吊死”(Andtherefore,withwildhorses,didhedraw,/Andafterhang,theirbodies,allbylaw.181-182),让人触目惊心。真正的凶犯必须严厉惩治,可是把每个预闻凶案的犹太人都处以酷刑和极刑,似乎量刑过重,具有统治阶级权力统治的暴力性特征。首先,这种“依法”公开处决,是展示性的,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律的胜利,更是当权者的胜利,是基督教对抗犹太教的政治胜利。福柯认为,公开处决,“是一种恐怖政策,即用罪犯的肉体来使所有人意识到君主的无限存在。公开处决并不重建正义,而是重振权力”[8]。由此可见,所有预闻此事的犹太人,无论有辜无辜都被处决,具有武断性,是权力威严的展示,而不再仅是伸张正义。超出维护正义目的的统治阶级通过此次展示,进行了一次思想大清洗,是杀鸡儆猴,是对“他者”种族与身份的震慑与警告,是对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保护行为。也可以说,以“地方官(provost)”为代表的宗教上层阶级,在国家机器的帮助下,积累了威信资本。而这种资本的本质意义就是要与宗教资本结合在一起,从而兑换某种象征资本(即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根据布尔迪埃的学说,象征资本是一种建构的权力,一种通过社会动员造成新群体的力量,换言之,象征资本是社会群体权威代言。它作为“赤裸裸”的经济资本的象征性调解,起到了掩盖统治阶级经济统治的作用,并通过表明社会地位的本质,使社会等级制度合法化,政治统治合法化。然而,象征资本最终还将转变为经济资本,以稳固统治阶级的经济与政治统治地位。
这样的权力政治叙事通常具有教化目的性。虽然宗教文化的传播不是战争,却胜似战争,其过程具有文化侵略性、威胁性和隐秘性的特点。并且,故事中提到,孩子在学校学唱赞歌时,和同学们一样,并不懂得其中拉丁歌词的含义和文法,而是一种“鹦鹉学舌”的学唱。这种在政治教化手段之外的文化扩张途径,通过宗教文化渗透,对异教民众进行基督教中心主义的统治阶级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粗暴植入,以达到文化教化的目的性。
四、叙事主题的宗教荒诞文化书写
修女叙事通过无辜儿童被虐杀展开了“恐怖”与“救赎”的宗教主题,并在现实叙事中糅合了神奇和怪诞的情节,具有强烈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孩子在喉咙已割穿到颈骨而死去的情况下,继续唱歌,以引导人们发现自己的尸体。这与现实逻辑不符,是夸张变形的荒诞主义写法,是对主流宗教思想外在服从而内在抗议的态度的隐晦反讽,是看似合作实则不合作的悖论情境。这种“过犹不及”的宗教信奉,体现了乔叟一种对黑暗社会存在绝望背后的价值关怀,是在基督教中心主义的“大他者”环境影响下,对个体信众“小我者”的体谅与同情,其本质是隐形的、无声的政治反抗。正如加缪所说,“荒诞运动,反叛运动,凡此种种……其目的是同情……即是说,归根到底,是爱。所以,我们在荒诞作品一团漆黑的世界背后,总能看到一个反抗绝望的英雄,或者一个痛苦挣扎的灵魂。”
除了这种悖论逻辑的主题揭露,作家还通过荒诞化叙事映射了一场政治合谋与欺诈。当这个七岁文盲孩子躺在圣坛上举行葬礼时,开口说了一些不合常态的话语,比如,“从书上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要他的光荣继续在人间(But Jesu Crist,as ye in bookes fynde,wil that his glorie laste and be in mynde)(200-201)”“怜恕之源,耶稣的慈母,是我罪衷心最虔爱的(Thiswelleofmercy,Cristesmooderswete,Ilovedalweyasaftermykonnynge)(204~205)”等,这些话语理智而老道,与前文提到孩童对文法和歌词大意一无所知的学识情况自相矛盾。除此之外,孩子后来还解释了死后说话奇迹出现的原因,说是圣母放了一粒谷子在自己割破的喉咙上,才导致了自己死后仍能唱歌说话,取出谷子后,孩子才渐渐死去。这一场充满神秘“奇迹”的葬礼,令人匪夷所思,但是当时葬礼在场的见证人分别是“地方官”(provost)、“修道院院长”(abbot)和“教士们”(monkes)(190~191),都是基督教中心主义政治统治的代表,解释了这些超出常理和超现实的“奇迹”事件出现的可能性,那就是基督教的内部人员共同策划了这一场以宣传为目的的合谋行为。借用经济学家拉丰(Laffont)等人的研究范式[9],为了追逐最大利益,当监管人和代理人之间不存在剩余的不对称信息时,根本不存在有价值的监管,合谋必将产生。如果把这个欧洲中世纪的一神教社会比喻为一个经济实体单位,孩子葬礼就是场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利”就是政治话语权与信仰归化,那么在场的市长和教士们就可以看作既是葬礼活动的监管者又是代理人,双重身份使得合谋的产生顺理成章。在没有任何异教徒的有效监管和见证下,孩子葬礼上的离奇表现,极有可能被进行富有浪漫主义的荒诞化演绎,篡改情节内容,产生 “令人震撼”的宣传效果,来达到对异教徒思想教化与文化侵略的政治目的。
五、结语
伊格尔顿认为,“一切批评都是政治的”。女修士的故事不仅仅是供朝圣途中香客们调侃的娱乐故事,更是一个欧洲中世纪晚期时代背景下充满隐喻色彩的政治文化叙事。赛义德说,“回顾过去是解释现在的最常见的策略”[10],重读经典,并试图政治解读经典对我们仍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