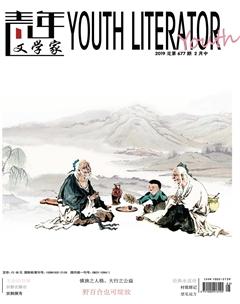《文心雕龙》“通变”篇之探微
摘 要:讲述《文心雕龙》通变篇“本色”论提出的原因及其内涵;分析刘勰在论变通时列举的五个例子;阐释了《文心雕龙》“通变”篇与其他创作论诸篇间的关系,彰显“通变”篇的独特意义。
关键词:通变;“本色”论;继承;革新
作者简介:郑重,湖北民族学院文艺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化与文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5--02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1]说的就是事情在穷尽的时候应当有所变动,变动之后就能够通达,通达之后就可以运行长久。王国维也说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2]他要表明的是每个时代最主要的文学创造体裁都是不同的,强调的是一个“变”字。《文心雕龙》“通变”一篇与《周易》说的变通有类似之处。但其内涵与《周易》之变通其实大不相同。前者主要是强调一个“通”字,在“通”的基础上对文章的创作手法有所革新。后者的“通”是因为变化才能通达,而变化的根源是事物已经处于穷尽或者说穷尽的边缘。为此,两者发展的逻辑其实是大相径庭的。
“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3]千百年来,人们把这句话概括为“青出于蓝胜于蓝”来表扬有为的后辈。刘勰却一反常人的思维,说“虽踰本色,不能复化”。意思是虽然这两种颜色都超过了本身的那两种颜色,但是却不能再作变化。读到这里,让人很难不想起那段著名的对话。“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所谓“绘事后素”,说的就是有良好的质地,才能进行锦上添花的加工。孔子和刘勰关于“本色”的理解虽然有内涵上的相通之处,但两者的侧重点还是有很大不同。孔子强调的是要在好的、无污染底子上进行艺术加工,从而是可以超越原始底子的。而刘勰虽然并不否认“青”、“绛”在颜色上是胜过“蓝”和“蒨”的,但他的着力点还是“蓝”、“蒨”具备某种超过“青”、“绛”的特性,也就是能够变化,具有可塑性。但刘勰为什么发现这点,而且要不遗余力的反复强调呢?回到“通变”原文,作者说:“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而大概的说明了各个时代诗文创作的特点。关键是,刘勰接下来又说“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这句话有大可玩味之处。从前面八个字可以看出作者认为现在的诗文越来越没有味道了,具体表现就是诗文从质朴流向于诡诞。后面的九个字,便点明了原因,那就是时人“厚今薄古”,从而导致文风黯淡。提炼一下,无非也就是“质”、“讹”、“今”、“古”四个字在作怪。再来把次序排列一下,“古质”、“今讹”。单从这里来看,刘勰显然推举“古质”要远胜于“今讹”。按这个逻辑,不就成了越古老的朝代创造的诗文就越好,越有味道了么?这个显然不符合文学史的发展轨迹。比方说楚辞对比诗经,其形式更加富有变化,不再局限于《诗经》四字为主的创造法式。内容上,楚辞中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也不是《诗经》所能桎梏的。由此可见,说时代越远诗歌越好就站不住脚。那刘勰是不知道这些呢,还是没有注意到这些呢?其实两者都不是,答案只有一个,这个答案不仅是在“通变”里面,更是贯穿整部《文心雕龙》。那便是刘勰经常有的放矢地针砭时弊,虽然不免矫枉过正,但重病需要重药来医治,如果刘勰患得患失要求事事都要密不透风,反而不能体现出他的独到观点。
再来看刘勰在“通变”中对汉朝五个赋家的描述。刘勰列举了两个西汉的作家,枚乘和司马相如,东汉的作家有三个,分别是马融、扬雄和张衡。刘勰说“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自兹厥后;虽軒翥出辙,而终入笼内。”[4]最关键的是后面十个字,意为对声音形貌的夸张想要跳出旧套,但最后还是在那个圈子里。颇有一点类似孙行者想尽办法逃出如来佛祖五指山的感觉。先看时间最早的枚乘,他说道“通望兮东海,虹洞兮苍天。”里面最核心的语素就是“海”和“天”,“东”是表方位,“苍”表示颜色。它们搭配到一起,就组成了最为核心的词语“东海”和“苍天”。“兮”是语气词,“通望”、“虹洞”分别就修饰“东海”和“苍天”,所以整合在一起就是“远望啊东海,广阔无边啊连着苍天”的意思。下面四个赋家说的确实也和这个差不多,只不过多了“日月的出入”这个意思。再来回到前文所说的“本色”论,这五个赋家表现的无非就是“天”、“海”、“日”、“月”四个意象,这就好比“蓝”和“蒨”。然后各个作家都用一些修饰词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比如司马相如的“日出东沼”、马融的“大明出东”、扬雄的“出入日月”、张衡的“日月于是乎出入”等意思都是大同小异。然而已经和最初的“日月”已经不同,在已经修饰的基础上再来进行文字加工用来变化,难度就更大了。这也就是前文说的“不能复化”。可十分诡异的就是刘勰他又说到“此并广寓极状,而五家如一。诸如此类,莫不相循,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似乎他举的五个例子都是既有沿袭又有革新的典范,达到了刘勰所说的通变。诡异之处在哪里?第一,从这大段文字的开头来看,这五个例子明明就应该被看做是“终入笼内”的例子,与这大段文字最后所说的“通变革新”完全是相反的。第二,抛开刘勰的主观因素,这五个赋家所描述的内容与语言形式,相同之处实在是远大于相异之处,也就是说“诸如此类……通变之数也”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
创作论的前五篇分别是“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按照王运熙的分法,[5]“神思”论的是创作的构思和条件,中间三篇是风格形成的主观因素,“定势”是风格形成的客观因素。整部《文心雕龙》的每一篇目与之前后篇目都有很大关系,“通变”作为三大风格形成的主观因素之末,又下启“定势”这风格形成的客观因素,处于一个结合点的位置,所以对“风骨”与“定势”的分析也很重要。“风骨”到底有什么用,刘勰开门见山说道“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意思就是有了风骨才能使形体既有骨架,又有生气。在其后又曰“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虽然都是被批评的对象,但有了“风骨”,至少有了一种气势,比一群野鸡到处乱跑还是要强得多的。“定势”篇提出的背景是当时的文风不正,具体来说就是“体性”篇里面的“新奇”和“轻靡”。前一种是“危侧趋诡”,后一种是“浮文弱植”。要纠正的话,那就是要定势,也就是“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神思”一篇的重要性早就已经达成共识。为的是它主要讲的就是创作的构思和条件,而《文心雕龙》本来就是一部兼具实践性和理论性的著作,是一部指导写作的书,但不是就事论事谈写作,而是有意识地赋予理论意义。“积学”、“酌理”、“研阅”、“驯致”是作者进行创作的先决条件,用最通俗的话来讲,其实也就是要打好基础,然后顺着自己的思路自然而然的写好文章。说到这里,又不得不提到范文澜先生在“神思”篇目的第一个注释里说到的那个表。老先生说道:“兹将下篇二十篇,列表于次,可以知其组织之靡密。”“神思”向下指向“体性”的“性”,“性”又朝左横着指向“体性”的“体”,“性”向下又指向“风骨”之“风”,而“风”又朝左横着指向“风骨”之“骨”,这里要注意的是“体”与“骨”之间只是用横线连着的,没有箭头作为指向关系。然后“风”与“骨”又同时向中央指着本文主要讲的“通变”,通变居中往下也是只用一条没有箭头的横线而连着“定势”。可范先生为什么没有对该图表进行解释呢?第一种可能就是认为没必要写,因为他可能觉得他说的已经够清楚了。第二种可能就是他故意不写,为的就是不让他自己的理解来束缚读者的见解,倘或范先生在注釋下写了几千上百字注释,现在也轮不到我辈在此论述。前文已经说了,范先生治学严谨,在《文心雕龙注》的绝大多数注释里,都生怕读者不理解而进行详细的说明,创作论的体系了解很有必要,而他在这里确实没有说明白。如果真是这第一种原因,那么就真如韩愈说的“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所以只剩下第二种可能,我私下认为,其实在第二点原因后还可以补充一下,那就是范先生一方面不想束缚读者的思维,另一方面也就是让读者真正了解研读《文心雕龙》后,再来对着他的表来看。不然范先生说什么,读者就做什么,那实在是了无趣味。还是用《文心雕龙》里面的话来解释最好,“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
简单来说,“神思”篇目已经说明在有一定的基础(“积学以储宝”)上,应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说的就是不要凭空苦想,而是要体会外物的美好。在“神思”篇中,刘勰举的12个例子只是说了下创作的快慢,并没有指出快慢的根源。即便后面又提到了“骏发之士”和“覃思之人”,也只是隔靴抓痒。而到了“体性”篇,刘勰提到了“才气学习”,也就是所谓的“性”。并说道其形成的原因是“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分为“庸?”、“刚柔”、“浅深”、“雅郑”,正是有了这些“性”,才会有对应的八位体(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庸”、“浅”、“郑”明显是不太好的“性”,所以“新奇”、“轻靡”这两种“体”也自然是刘勰所贬低的。接下来还是要说“风骨”,可从“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这一句看出其端倪。后半句意思是深刻通文风的,表达的感情一定明显,为什么明显?因为这个是人“才气学习”之“性”所传达出来的,如果知道自己的特性,当然就可以顺畅的表达自己的感情,所以“性”的箭头才会指向“风”。前半句的意思是能够锻炼文骨的,辨析文辞一定精当,加之首段所说“如体之树骸”,可以说明这个“骨”字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为框架结构的。这与先前的“体”是对等关系,不是继承发展关系,所以不用箭头。而“风”之所以能箭头指向“骨”,则是因为“骨”的这一结构只能用“风”来充实才会变得有意义。“风”与“骨”都同时箭头指向位居中央的“通变”,说明“通变”是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体,而“通变”拆开可以为“通”和“变”,这两个字的关系与“体性”、“风骨”拆开后两字的关系是大不一样的。“风”、“性”大体可以看做是情感内容,“体”、“骨”可看做是框架结构。“通”与“变”不存在那种决定关系,也不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因通则变,因变而通,两者在一起才能包含整个创作过程,所以“通变”在一起位居中央。“定势”作为风格形成的客观因素与“通变”这个“集大成的”主观因素在一起,就在中央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创作体系,所以它们之间也只是用横线连着的。
说一道万(“洞晓情变,曲昭问题,然后能……”),刘勰几乎在每一篇都要大談学习前人文章制体的重要性,有时甚至会感到他是拿着创新的旗号来宣扬复古观点的。但从根本上来讲,刘勰还是有很强的创新意识的,只不过时人创作太过轻浮,他也就不能不更加强调继承的重要性了。
注释:
[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3]王先谦著.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周振甫著.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