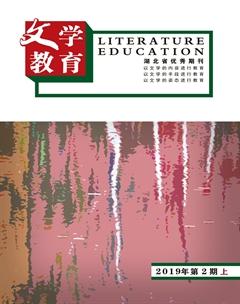孤独个体的欲望追寻:细读张执浩《什么意思》
内容摘要:《什么意思》是湖北诗人张执浩的诗作。这首诗将过去与现在、独自睡觉与同床共枕进行对比,描绘了你从独处到渴求爱情再到爱情消亡后再次寻求独处的全过程。通过这场对欲望的追寻之旅,诗歌揭露了个体的孤独本质,同时也反映出欲望只会无休止地延宕,它永远不可能被满足。
关键词:张执浩 诗歌 新批评 文本细读
什么意思
一个人睡觉有什么意思?两个呢
年轻时你梦想
同床共枕
年轻时好像没有现在冷
现在,一张床上有两条被子
像两垄地,分别
种着孤寂,和孤寂
你半夜溜上床,拧亮台灯
读几页书
内心里翻涌着小偷的情欲
这首诗看似容易理解,实则没那么简单。首先标题就令读者陷入了一个窘境:“什么意思”究竟是什么意思?作为疑问句,它对“意思”的内容表示了关切,但同时又有些反诘的意味。如果说前者还限于中立的立场,那么在第二种情况下,语气便微妙起来,产生了某种质问与否认的倾向。诗歌的指向与哪种语气有关,目前还不得而知,暂且将其搁置一旁。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弄明白的是,不管是疑问还是反诘,这个问题是谁提出的?又是提给谁的?毋庸置疑,这自然是作者之问,他抛出一个暧昧不清的问题,或用以自问,或用以对读者的盘问,但这也不妨看作读者的问题,或者说——这当然是读者的问题了,毕竟我们确实满腹狐疑,对作者所说的“意思”一无所知。于是,被提问者的身份也就随之揭晓:他是包括作者在内的所有人,以及诗歌本身。
现在进入正文。首句以提问的方式切入,对标题作出补充,基于上文的叙述,我们很快便能厘清“一个人睡觉有什么意思”的两种语义指向。第一,这可能只是一个单纯的疑问,第二,这可能出于反问,而诗歌的精妙之处恰恰在于制造含混,也就是说,诗句的指向并非两者取其一,而是兼而有之,诗人真诚地发问,同时又隐含着反讽语气。“睡觉”作为人类日常作息的一环,即睡眠、休息,事实上,睡眠是生命体最接近于原初的一种状态,仿佛婴儿回到了幽暗而温暖的子宫。对于未出生的个体而言,其一切生理需要都能在母体中得到自然满足,而一旦个体出世,就意味着通过脐带传输的自然需要被割断了,与母体的分离也就形成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决定性缺失。由此看来,个体是在母体中呈现出一生中最完整、最满足的状态的,在出生后,尤其是进入语言领域之后,人们就会在发现主体的过程中走向南辕北辙,毕竟言说本身就已经意味着主体的消亡,语言领域中的每个人都无法摆脱被异化和阉割的命运,而惟有睡眠才能使个体短暂地体验到重返母体的无上享受。因此,“一个人睡觉”不妨理解为个体自身对原初欲望的追寻,而“有什么意思”则暗示着这一过程失败了,当个体认识到自己存在决定性的缺失后,他总是试图通过与另一个体的相互指认来趋于完整。于是诗歌进而转到“两个呢”,即“两个人睡觉有什么意思呢”,可惜的是,延续前一句的反讽语气,答案不言而喻:两个人睡觉也没什么意思。至于为何如此,我们需要继续往下看才能弄明白。
年轻时你梦想/同床共枕/年轻时好像没有现在冷:“年轻时”本就表明了一个回溯视角,即“你”已年轻不再。另外,“年轻”除了指年龄较小外,还带有幻想、幼稚、不切实际的情感特征,似乎在說“你”曾梦想的一切都是一个笑柄,于是,“年轻”这个表面中性但语义极为混杂的词语就为后文的叙述埋下了一个天然的转折。“同床共枕”与上文“两个呢”相呼应,如果说“两个呢”的表达还有些许隐晦,那么“同床共枕”对爱情的指涉就很直白了,也就是说,这两句是在写年轻时的“你”渴望着爱情。
接下来的一句中,“年轻”与“现在”两个阶段形成了时间上的对照,值得一提的是,“好像”这个词很有意思。“好像”即不确定、难辨明,之所以要用模糊的表述,第一种可能性是,年轻时与现在间隔的时间太长,以至于说话者真的已经记不清楚当时是不是比现在冷了;第二种可能性是,“好像”是诗人有意设置的副词,意在昭示一种语义上的动摇,它并不醒目地夹在一句话中间,暗自发出了警醒:这句话作出的结论可能是虚伪的。年轻时真的没有现在冷吗?或者说,该说法仅仅是一个借口,倘若如此,这又是对什么的借口呢?回溯上文,我们不难找到端倪。前面提到过“年轻时”一词带有天然的转折,也就是说,可以推知现在的“你”已经不再渴望“同床共枕”了,“你”发现一段亲密关系的展开并不能使人达到预想中的满足,于是对过去的幻想进行了嘲讽,而“年轻时好像没有现在冷”便是用于掩饰失败、宽慰自我的借口。
现在再集中到“冷”这个字上。冷与热相对,指温度低,那么问题就来了:一般情况下,人只有感到寒冷才会想要相拥取暖,“年轻时你梦想/同床共枕/年轻时好像没有现在冷”,意思是年轻时比现在更热,既然更热,为什么还要互相依偎,挤作一团呢?显然,这里的“冷”就不是体感上的,而是心理上的了,例如“冷清”指寂静、不热闹;“冷淡”指疏离、不热情;“冷门”指不受欢迎、没人过问,我想,这些涵义均适用于此处的语境。这个“冷”字就是对爱情现状的描摹,即随着岁月的流逝,爱情降温了,曾经的梦想也走向终结。
至此,行文总算转入了下一个部分:现在,一张床上有两条被子/像两垄地,分别/种着孤寂,和孤寂。年轻时,爱人之间可能是共用一条被子的,那是相互包容、彼此合一的象征,但是现在一条被子变成了“两条被子”,被子的包裹是排他性的表现,这意味着两个曾紧紧相依的个体又退回了各自的领域,这怎能不“冷”?细细读来,我们还会发现一个更为可怖的事实,即在“同床共枕”到“一张床上有两条被子”的转变中,“人”不见了!前者所隐含的主语自然是两个人,但后者的描述却彻彻底底抹煞了人的痕迹。曾与“你”共眠的那个人或许还真切地躺在身旁,但于“你”而言,床上仅仅是多了一条被子。“分别”这个含混的词在明义上指分头、各自(respectively),在暗义上则有两种指向,一是指分开、离别(leave each other),二是指不同、差异(difference)。往日的爱情再炽烈,如今也消散如烟了,“你”终于明白,原来人与人之间是那么地不同,即使相拥也无法完满。
“种着孤寂,和孤寂”不免令人想到鲁迅《秋夜》中的著名句子:“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毋庸赘言,这绝非无意义的重复,先看到一株枣树,目光移动,再看到另一株枣树,表达的冗余实则是内心的无味。既然先说了一株是枣树,人们往往会预设另一株是其他的树,当读者心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疑虑和期待,欲知另一株是什么树时,我们无趣地发现,哦,原来还是枣树,生活并无惊喜。不说两株,而把它们看作一株和另一株这样两个彼此分离的个体,想必看树人的内心也是相当寥落的吧。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种着孤寂,和孤寂”的写法了,何况诗人已经直白地将“孤寂”二字点出来了。
诗歌至此,我们遗憾地发现,“一个人睡觉”没什么意思,“两个呢”同样如此,为何会如此?这种孤寂仅仅是由于爱情的消亡吗?
诗歌的最后三句给出了提示:你半夜溜上床,拧亮台灯/读几页书/内心里翻涌着小偷的情欲。“床”本是一个充满安全感的私密场所,而“你”却要“溜”上去,“溜”含有偷偷地、悄悄地、不希望被人察觉的意味,“你”提防的这个人显然是自己“同床共枕”的另一半。再来看,溜上床的时间是在“半夜”,这是一个众人熟睡的时刻,我们可以再现情境:深夜时分,床上的人已经入睡,灯关着,夜色沉沉,一片黑暗,这个时候“你”才轻手轻脚地溜上床,悄悄旋开台灯看书。这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你”与另一半并没有一起睡觉;第二,“你”不希望有人打扰,连爱人也不行。再往下看,如此神秘,竟是为了“读几页书”。在这里,“读书”与获取知识无关,而是一种放松身心的方式。读书不过是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一项活动,但诗中的“你”却偏要在爱人睡着时偷偷进行,这可能意味着“你”在白天并没有这种闲暇或兴致,两个人的相处令“你”身心俱疲,只有置身于無人叨扰的深夜,才能愉快地做几样自己喜欢的事,因此“读几页书”反倒成了一种奢侈。
最后一句将这种心态具化为“小偷的情欲”,这里的隐喻相当有趣。“半夜”是“你”读书的时间,通常情况下也是小偷作案的时间;“溜”是“你”爬上床的动作,也是对小偷蹑手蹑脚、小心翼翼姿态的生动描摹;“拧亮台灯”是你读书前的准备,而入室盗窃的小偷往往也需要打开手电进行小范围的照明,如此一来,“你”不就是那个小偷吗?激起“情欲”的不是“读几页书”,而是做贼的感觉,“你”的内心一面波涛汹涌,担心被爱人发现,一面又沉溺其中,无比享受。
诗歌在这里呈现出一种回归。最开始是“一个人睡觉”,接着又渴求“同床共枕”,而当爱情变得庸常无趣,“你”则将“梦想”与“情欲”重新转向了自身的独处。诗歌以爱情为载体,但应该注意到的是,这首诗从头到尾都没有明确地提到过所谓的爱人,而是使用诸如“两个”、“同床共枕”、“两条被子”、“两垄地”这些笼统的描述,与其说是含蓄,不如说诗歌原本就无关具体的另一半。令人倍感孤寂的,是爱情的消亡,但从根本上来说,是欲望无休止的转移,这也是诗歌呈现出回归的原因。
具体来说,“小偷的情欲”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你”已经不再“一个人睡觉”了。倘若现在仍是独处的状态,“你”大可随心所欲,不必等到深更半夜才溜上床,“读几页书”也就不构成“小偷的情欲”了。独处时希望有人共眠,有人陪伴身侧后又贪恋独处,人永远对现状不满,永远向着与当下相反的方向逃离,欲望也永远在能指链上滑移。
回过头来想,“什么意思”究竟是什么意思?如同文章开头所述,它首先是抛出疑问,其次又是一种反诘,意在表明无论是“一个人睡觉”还是“两个呢”都没什么意思。在指出诗歌的回归趋向后,可以提出第三种解读:“什么意思”即什么都是意思、无限种意思。“意思”是无法穷尽的,它从一个不断地指向另一个,永不停歇。
由此可以作出最终阐释:从根本上来说,《什么意思》是一场对“情欲”的追寻,它揭示了个体的孤独本质,同时也揭露了欲望即对缺失的欲望。诗歌向人们展示了两点:第一,人生而匮乏,个体出生所带来的决定性缺失非但无法弥补,反而是人存在的方式,爱情中的两个人事实上也不过是“孤寂,和孤寂”;第二,欲望本身永远也不能被充分表达,它只能不断地从一个要求转移到另一个要求上去,无休止地延宕。现在的“你”已实现了“年轻时”所梦想的“同床共枕”,于是“情欲”便不在此处了,它会转移到“读几页书”上。不妨假设,当有一天“你”终于得以解除爱情关系,到那时还会在半夜溜上床去读书吗?还会体验到“小偷的情欲”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这个时候,欲望早已滑移到别处去了,而“你”也不会就此停下,“你”还会被它继续牵着鼻子走,不断地走,“你”一生都渴望原初的完满,却一生都要跋涉在永无止境的欲望旅途上,但孤独就是孤独,缺失就是缺失,那是人生的常态,也是人存在的证明。
(作者介绍:马玉聪,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