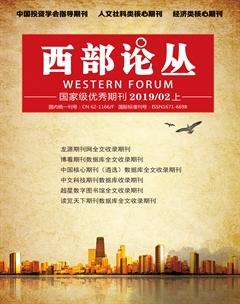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老人社会参与适应性研究
摘 要:在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农村社会公共空间呈现萎缩,挤压了农村老人的社会参与空间。在农村老人具体社会参与实践中,其社会参与意愿与社会参与能力和社会参与机会存在不匹配,这些都限制了农村老人的社会适应性实践,针对其存在的社会参与困境,政府与社会可以采取提高他们参与空间、适应能力和健康支持等多方面综合措施,切实为当下的乡村振兴注入内生性力量。
关键词:社会适应性;社会参与;公共空间;农村老人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设计
近年来,在“积极老龄化”理念的推动下,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于老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价值有了新的认知,老人不再被看做是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被动参与者,而是被赋予了积极自主的角色。同时有学者认为对于老年人口的关注,确保老人的健康权、参与权和保障权应该是应对当下老龄化的主要三大举措,并明确这三位一体不仅是老年人的需要,而是一种权利,强调应努力创造条件让老年人回归社会,重返社会,这种重返不仅仅是体力活动和劳动,更包括社会参与、乡村社会治理、乡村社会文明建设社会价值传承等各个实践领域,充分发挥其独特劳动技能、经验和智慧,从而使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压力转化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积极推动力量。
社会参与适应性是指农村老人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如何依据变迁的农村社会日常生活,去参与村落的日常生活体系,这样的参与对于农村老人而言,其主动性适应的程度高低直接影响其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
本文作者和研究团队分别于2017年10月份和2018年7月份在A省两个县市对于农村老人的社会适应性实践进行了问卷调研和深度访谈,总计发放320份问卷,有效回收302份,深度访谈了15位老人,笔者本人在2018年9月份又对一个村庄进行了细致调研,深度访谈了10个老人,以期对他们社会参与进行细致考察,并试图了解他们背后逻辑。
二、农村老人参与社会村落事务意愿较高
对于很多老人而言,为了帮助子代生活,主动承担了代际责任转移,支持子代外出务工,自己主动留守在家,承担家务劳动对于他们而言,他们很多人都集中在65岁左右,而在当下乡村社会中,65岁已经不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是老年的标准了,他们在自我评价和社会认知中,65岁都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年龄,只要身体健康,65岁的老人完全可以胜任除了重体力之外的很多劳动,其中自然也包括乡村公共事务参与。很多老人不仅仅满足与在家庭中仅仅承担一个留守的角色,更多的人想去参与自己所在村落的日常生活,在采访中有约70%的老人表示愿意参加自己所在村的公共实务,他们明确表示,只要村委会找他们,他们就会去干。在参与意愿上,农村老人都保持这较高的适应性,他们愿意去主动适应变迁的乡村公共生活事务,保持积极意愿。
访谈对象4:男,L,67岁,身体健康
我们虽然在家呆着,也不是废人对不对,我自己买了一辆小三轮车,赶集方便,地里粮食也都能弄来家,你说我们不比那些年轻人差,他们干活我看不上呢。在家里面呆着也无聊,尤其是寒天时候,又没有活干,我想着要是村里能报我们这些老人都组织起来干事情,我们都能干的,谁不想多出去走走,谁愿意天天在家窝着啊。
三、农村老人参与场域空间狭小,社会参与受限
村落作为一个公共舞台和公共生活空间,每个体不能脱离这些场域,尤其是老人生于斯、长于斯并终于斯,在一个熟人社会中,每一个老人对于村落内部的事情都了然于胸。对于每一个村民而言,村落的公共生活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点和空间上简单的聚集,而“是他们生存的空间,是他们本土道德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权力、地位威望物质资源社会秩序等等生存的基本要素都得到了确实的体现”[[2]],哈贝马斯(1964)认为公共领域是开放社会生活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形成如舆论和自由的场合。在原则上讲,公共领域对所有公民都是开放的,人们在这里面可以不受到任何的外在压力,保持有高度的独立性来进行他们相应的活动,这种活动不会因为其性质和个体特征而受到外在的制约和影响。
农村老人社会参与主要体现在社会场域参与上,要有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场域空间以供农村老人社会参与。依据上文所述,在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农村老人的社会参与空间逐步收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村落的公共空间日渐萎缩,很多原先用于村落公共休闲的实体性空间全部被改造作为他用,村民缺乏具体空间聚拢,老人亦缺乏了具体场域和空间展示其社会参与的独特价值空间;其二,在村落事务的精英化模式下,农村老人社会参与场域日渐縮小,诚如前文所言,现存农村社会推行精英治村和资本下乡,这些都在无形中消解了农村老人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机会和途径,精英与资本相结合,对于农村老人的社会参与形成了共同排斥。
四、参与村落事务的个体类别差异较大
伴随着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变迁,农村人口的流动单向度,农村社会日益过疏化[[3]],农村公共生活空间日渐萎缩,伴随着农村公共空间的变迁,是农村公共生活的减少,阎云翔认为在中国家庭化的大规模推进,加强了私人生活空间的拓展,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村庄公共生活[[4]]。这种抑制主要体现在农村老人社会参与的个体性差异上。
虽然在调研区域,老人都表示愿意参与村落的公共实务,包括正式组织体系内的事务,但是对于部分老人而言,他们在实际参与村落公共实务中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由于农村老人存在较大的异质性,老人在经济方面、健康和知识能力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总体而言,健康条件成为制约农村老人社会参与的主要障碍。在调研中发现有70%的老人有参与意愿,但是真正能参与村落日常生活的仅有30%,另外经济条件也成为制约农村老人社会参与重要因素,有40%的老人认为自身条件差是影响自己社会参与的主要因素,他们认为自己经济差,日子过得穷,在村庄里面都不能抬头,自己日子过的不好,没脸到处去跑,有32%的老人认为老人说话没有用,说了也没意思。30%的老人认为自己不懂,不太知道要去做什么,没有办法去参与。农村老人社会参与中个体差异还体现在性别差异上,总体上而言,男性社会参与意愿与能力均高于女性,女性更愿意在家庭中承担角色,80%的老年女性坦言不喜欢在村庄里面正式场合说话,只愿意在闲谈和非正式场合说话。
访谈对象6:男,S,68岁
我们是想出去帮村里面干点事,可是我们也不懂要干什么,现在什么都是新的,我们老了,好像都没有用了,跟不上人家步子,你干什么别人还看不顺眼,说你过时了,你说怎么出去,还能干啥呢。
五、宗教信仰——农村老人社会参与的另一中途径
在当前社会生活原子化的阶段,农村社会生活中公共生活空间的萎缩,尤其是经历过火热的集体生活的农村老年人对于现在这样凋落的生活境遇心理会有极强的失落感,由于公共空间萎缩和社会参与的限制,很多老人在内心压抑着自己的精神和参与的社会需求。从情感社会学的角度讲,“情绪感染是一个社会生理学事实。……人类像其他动物一样,在神经上要求相互响应;而且体验产生这些反应的社会情境是十分有益的。[]”宗教中的祷告和讲经满足了当前农村居民集体生活缺失的精神需求。而宗教的班集体化和小型的集体化的生活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的集体生活的需求,他们相互之间容易接纳和形成非正式的组织群体,从而使这些老年人获得身份认同、安全感与归属感,满足了他们精神慰藉需要,群体交往的需要,情感渲泄的需要,成为农民社会支持网络的有益补充。同时宗教宣扬的向善和互助的理念在情感上与当前农村老人的价值需求相切入。农村老人几乎都是传统的坚守者,他们看不惯当前农村社会中中青年经济利益主导下的经济人的自利性行为和农村道德下滑的倾向,而他们却无力来阻止或者改变。但是在宗教活动中,他们能寻求到对这些现象的解释之道,要靠主的感化,主教人们行善,他们对于这些教义有了天然的契合,很快便完全投入到宗教活动中,成为虔诚的信徒。
农村老人在全身心投入宗教的过程中,在日常生活的宗教化中,宗教高度嵌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支柱,也成为他们人际、社会关系网络的核心实践。因此对于宗教的日常生活的皈依实现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和价值归宿。伴随着宗教与日常生活的高度契合,很多老人自此开始走出家庭,开始向宗教来寻求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实现了他们人生价值的外展寄托,他们的晚年也开始在向外拓展的过程中实现自己人生追求。
访谈对象9,L,女,72岁,“以前不信教时候,不知道这里是什么样子呢,看着那些人大忙天的地里面活都不干,跑去信教,做礼拜。当时就想要是我家的人非打他一顿不可,太懒了,明显是躲懒的,哪有把小麦丢一地自己跑去玩的,不正经啊,不归过日子路的。自从我女儿生病也看不好进去之后,才知道那里和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呢。到里面和姊妹们一说主的事情啊,就浑身是劲,家里面、外面的烦心事都忘记了,人浑身都轻松啊。我老头原先说我偷懒去信教,后来他也去信教了,比我还虔诚呢。”
六、拓展农村老人社会参与适应性路径建议
(一)加强农村社会的公共空间建设,拓展农村老年社会参与空间
乡村振兴,首先要振兴乡村日常生活的内生力量,而乡村内生力量之中,农村老人无疑是极为重要的群体,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拓展他们社会参与空间应是当下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之一。针对农村社会公共空间日渐萎缩,农村老人缺乏社会参与的社会空间现实情境,乡村基层组织应有意识培育农村社会公共空间,使得该空间重新成为农民日常互动的重要载体和实践场域。公共空间的重建不仅仅是硬件设施的建设,更应注重聚拢性和日常互动性,引导村民在该空间内形成良好的价值体系和村落日常生活的约束机制。而这些,对于农村老人而言,具有价值最大化优势,他们的个体价值和传统习俗都可以在在这个空间内得以发挥,从而起到引领村落日常价值、重塑乡村传统的独特作用。
(二)提高农村老人的社会适应性能力,加强其社会参与技能
农村老人的社会参与性即受到社会空间制约,还有农村老人自身个体制约,很多老人有较高参与意愿,但是确缺乏参与能力和参与勇气。因此针对农村老人个体而言主要是提高其社会适应性能力,增强社会参与技能。其一,在理念上,针对农村老年个体,可以大力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尤其是针对农村老人开展优势视角取向下的老年社会工作,放大他们优势能力,并且培育他们自信和优势视角,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积极参与社会日常事务。其二,在具体技能上,培训农村老人日常生活具体技能,使其有获得感,祛除其社会参与无力感。这些技能包括对待社会变迁的态度,积极接纳新生事物,并尝试去了解和使用新媒体,增强其社会沟通能力。
(三)加强乡村老年医疗系统支持,增强其社会参与可行性能力
在前文論述中,农村老人社会参与最大障碍来自于其身体健康问题,虽然中国农村人口寿命较之于以前有了较大提高,生活质量也有了较大改善。但是对于农村老人而言,很多老人都是带病生存状态。在调研中,发现困扰农村老人的疾病多是基础性疾病,如高血压、脑血栓、筋骨痛疼等,这些疾病对于农村老人就像定时炸弹,随时可以发作。故而,很多老人由于健康顾虑不敢过多参与社会事务。农村老人没有日常的例行体检,他们对于自身疾病状况经常忽视。继续加大在农村退推行具有针对性的农村老年普遍性疾病的筛查和治疗体系,为农村老人晚年生活和社会参与提供健康保障。
参考文献:
[2][]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p34
[3][]田毅鹏:村落过疏化与乡土公共性的重建[J]社会科学战线·2014(6):8-17
[4][]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
[4][]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24页?
作者简介:仇凤仙(1979-)女,安徽宿州人,社会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社会保障理论与实务?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农村老人社会适应性实践研究---基于日常生活实践研究视角》(AHSKY2015D62)阶段性成果?
本项研究的部分资料和数据来源于我指导的团队《安徽省农村老人社会适应性研究》团队的同学相关调研资料,并经过他们的同意?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其余文责本人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