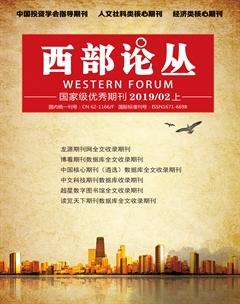信访治理中政府的“元治”角色及其行动指向
查荣林
摘 要:基于信访研究的学术检视,发现信访治理主体责任的相关研究甚少,政府在信访治理中“应然角色”难以彰显。立足信访治理的语境分析,认为信访治理的理论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信访治理的目标问题;二是信访治理的协调问题;三是信访治理的责任问题。通过“元治理”理论阐述及其适用性探讨,进一步廓清信访治理中政府的“元治”角色,进而提出政府在信访治理中的行动逻辑与指向,认为:在制度上,利用立法契机推行“扩权”改革;在战略上,动员社会力量实施“减压”安排;在机制上,通过顶层设计谋求“增效”实质。
关键词:治理;元治理;政府;信访治理
Abstract:Based on the academic review, we find that there are few researches on the governance responsibility of public complaints and proposals. Consequently,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government to manifest its deserved role.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ual analysis, the governance failure of public complaints and proposal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namely the objective problem, the coordination trouble and the liability issue. By expounding the theory and applicability of meta-governance, this paper further clarifies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s meta-governance and puts forward the action logic and direction for government in the governance of public complaints and proposals. It is essential to take advantage of legislative opportunity to implement some reformational policies institutionally, mobilize social forces to implement the arrangement of reducing pressure strategically and seek the essence of increasing efficiency through the top-level design mechanically.
Key words:Governance; Meta-governance; Government; The governance of public complaints and proposals
一、研究缘起及学术检视
“治理”一词的争论由来已久,并且伴随着治理理论的发展未曾休止,然而概念的争议和要素的讨论并未削减治理理论的推广与应用。信访治理既是治理的理念、工具在信访领域的应用,也是信访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冲突化解和矛盾疏导功能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信访”与“治理”是可以兼容的:一方面,信访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制度安排和重要技术手段,国家通过信访渠道掌握社会治理的实际情况,统摄社会秩序,从而达到治理社会之目的;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治理的手段整合分散化的信访资源,推进信访的制度化和理性化。治理是指官方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圍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需要(俞可平,2006)。信访治理内含着治理的价值理念和行动策略,“大体可以理解为有多个主体参与协商、合作解决信访问题的过程,即government(包括政府机关在内的主体)通过governance 的方式,实现governaning(过程)”(朱涛,2014)。可见,信访治理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各种社会组织、公民等力量;信访治理手段既包括正式制度、规则和政策,也包括非制度化的参与和认同。信访治理的困境有哪些?政府在信访工作中的价值考量和行动逻辑是怎样的?只有发挥信访多元治理的组合优势,找准信访部门的价值定位和行动指向,才能进一步明确信访治理的责任。学界相关研究要点如下:
一是信访法治改革的论述。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在社会各个层面都有所体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增长,而“相对剥夺感”在短期内难以明显削减。因此,信访在新时期的功能作用显得更加重要。尽管有学者认为“国家层面的‘信访立法,于国家治理未必有利,理应谨慎”(肖唐镖等,2016),但从实践看,国信发〔2016〕9号文件已将“深入开展信访立法研究论证和宣传”列入“2016-2020年全国信访系统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规划”的内容;国信办发〔2016〕4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信访立法步伐”。在此背景下,近年学界已逐步摈弃信访制度存废之争,转向信访法治改革的学理论证,主要围绕“可行性与必要性”、“权责配置”、“困境与实践路径”等问题展开。可见,信访工作的法规制度体系正逐步完善,信访制度正从法治的“边缘”走向“重心”。
二是信访功能定位的讨论。
信访制度的功能研究是准确把握信访制度属性的重要切入点。民众之所以选择信访,是因为对政府的需求或期待。民众可以借信访表达对政府政策的意见,从而满足某种“当家作主”的心理需求(Minzner, Carl F., 2006)。从公民的视角看,信访功能表现为诉求表达、权利救济、政治参与等;从国家视角看,表现为信息收集、协调权力机关之间的冲突、解决纠纷并化解社会矛盾、提供决策咨询(王凯, 2013)。Laura M. Luehrmann通过对中国公民诉求的研究,发现力求解决民怨的公民个体与试图发现社会问题的政府官员之间的互动状态强化了上级政权对下级政权的控制,如果处理好这一(互动)过程就可以增加政府统治的合法性(Laura M. Luehrmann, 2003)。Liebman B L认为在包括信访制度、调解、仲裁和行政复议等争议解决机构的改革中,党和国家的重点是需要解决争端和不满,从而维护社会稳定(Liebman B L, 2007)。
三是信访存在问题的研究。
综观学界相关著述,信访难题表现为:依法治访政策“落地难”(白慧玲, 2017)、信访部门“责重权轻”(朱维究等,2016)、信访制度的功能异化(张海波, 2016)、无理信访不断出现(林辉煌, 2017),等等。国外学者也较为关心民意表达和群体性抗争行为。Tilly等从政治过程理论的框架下解释抗议事件的缘起和变迁方向(Tilly. C., 2008),这为我们分析群体性信访事件提供了参照。Paik W.分析中国各省的信访活动,发现尽管经济总量高速增长,民众仍广泛遭受着过度发展伴随的高度腐败和不平等问题(Paik W, 2012)。Matthew Bruckner指出信访制度不能有效地实现公民在纠纷解决方面的预期要求,在解决纠纷方面的普遍低效和无力成为民众对政府丧失信心的又一因素(Bruckner M,2008)。
四是信访治理对策的探索。
国内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改革方案,主张采用“包容性治理”(尹利民等, 2017)、“大数据治理”(张海波,2017)、“分类治理”(田先红等, 2017)等方式进行改革和完善信访制度。从国外看,国外学者较为重视网络民意,认为“电子参与渠道可以帮助政治冷漠的人向积极参与社会问题和民主决策过程转变(Cruickshank P, esc., 2010)”,并且一定程度上,“有效的网络申诉可以提高公民民主参与的程度(Alathur S, esc., 2012)”。
国内外关于社会矛盾与民意表达问题的研究,为信访问题研究提供了宏大的理论背景和宽阔的学术视野,但学界相关研究较多局限于信访功能、制度定位等价值、体制层面问题,鲜有从主体责任这一角度进行分析。转型期的信访工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信访改革离不开主体责任的落实。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并不能抹杀政府在处理信访与社会矛盾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如何克服信访治理的困境?如何廓清信访治理中的政府责任?“元治理”理论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价值依据。
二、信访治理的理论困境
信访治理作为治理理论在信访领域的现实应用,仍然无法回避“治理”本身的局限。信访工作实务中,跨域型、涉众型等信访事项仅仅依靠信访部门难以有效解决,这就需要其他信访治理主体的引入,而多元治理往往囿于理论设想之美,实务中主要存在以下困境:
一是信访治理的目标问题。
在信访治理中,鉴于法律地位、行动能力、价值偏好等多方面的缘由,信访治理的目标导向难以准确表达和实施。在法律地位方面,信访人通过与属地政府多次“谈判”,可能更加了解政府的规章制度和办事流程,利用政策导向提升谈判资本,从谈判的“相对方”转变为“强势者”,进而主张更多的权利。在行动能力方面,信访人的多元化诉求可能伴随着“过激行为”,部分信访人带有“以闹求解决、以访谋私利”的心理,难以在政策范围内解决。在价值偏好方面,信访人的“维权”目的与政府部门的“维稳”目标也存在着失衡,这可能产生“过渡维权”或“片面维稳”的现象,无益于诉求解决。
二是信访治理的协调问题。
信访问题作为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涉及方方面面,问题较为复杂,处理难度较大。特别是涉众型利益诉求,属地信访部门的资源和能力有限,甚至经过多轮协调也难以促成各方达成一致意见。部分成因复杂的信访问题甚至涉及规划、国土、财政、环保、公安、房管、建设、文保等多个部门,需要各方协调联动,协同负责。信访问题的跨界性、联动性特征客觀上使得信访部门从“业务权威”转向“协调中介”,这显然偏颇于《信访条例》赋予信访部门的工作责任。
三是信访治理的责任问题。
信访治理在信访部门主体之外,发现了信访工作的多中心秩序,但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理念和实践追求,它缺乏有效的责任监督和控制机制,利益分歧和治理目标的分化很可能导致“有组织的无序”,导致多元治理的僵局。由于缺乏明确的责任控制机制,责任边界的模糊使得治理实践往往流于形式。部门间责任划分和统筹协调存在一定难度,可能引发各部门的推诿、敷衍和拖延,加剧协调会办的难度,造成“法难为据、理难服人、情难感人”的困局,难以发挥整体效益。此外,在强调社会力量参与信访治理时,政府的责任也容易被“误解”或“虚化”。
传统的信访治理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表现为:政府内部缺乏权力与资源的有效整合,尤其是分散化的管理规范、属地化的管理原则以及部门化的行动逻辑,缺乏总体性的制度设计和战略统筹。信访治理面临的一系列难题有赖于进一步厘定政府在信访治理中的角色与地位,从而把握政府在信访治理中的行动逻辑和具体安排。
三、“元治理”理论引介及其在信访治理中的应用
(一)理论阐述及其适用性探讨
从词源语境看,“Meta”一词含有“在…之后”“超出、超越”等意思。“Meta”意指较晚出现的更为综合的事物,这一前缀通常旨在“完善或强化后者”。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元治理(Meta-governance)作为治理的组织准备(条件),是对“治理方式”的“再治理”, 即通过多种治理形式的理性选择与运用,弥补治理的内在缺陷。从逻辑角度看,元治理旨在实现“更完善、更完美”的治理,这意味着元治理既是对单一治理的修缮与完善,也是对多元治理的优化与超越。
承认政府治理范式演变的总体趋势和一般规律,并不否认政府在现实治理中的制度性选择。作为一种制度愿景,信访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制度,借助元治理理论的指导,有助于建构和实现具有中国意蕴的宏观制度,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施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元治理的制度设计适应了转型期中国独特的历史语境,在强政府的社会治理框架下建构元治理的实践模式可以避免政府干预不足的窘境。作为一种价值工具,元治理的理性表达更有利于我们在治理洪流中,坚定治理本身所有蕴含的主体性选择和价值性建构等一系列治理要点。
(二)信访治理中政府的“元治”角色分析
作为对政府治理失灵的矫正,元治理旨在重新定义政府的角色,即将政府定义为“制度和规则的设计者、目标和利益的协调者、冲突和矛盾的调和者”。在社会建构意义上,“元治”的制度安排为实现“善治”愿景提供了主体设计。作为一种混合策略安排,“元治理”在信访多元治理体系中重新发现和认识政府在治理力量中的重要作用,即政府处于“统摄”和“整合”的战略地位,而非简单的“统治”和“管理”,从而有利于协同其他治理主体,减少政府治理的阻力。
1.制度和规则的设计者
从信访制度的发展趋势看,20世纪50年代之后,信访制度的法制化、规范化体系逐步形成。信访法治化是依法行政的重要推动力,也是信访制度自我完善的必然路径。依法行政作为一种价值理念,需要具体的机制保障其运行和实现,信访则是这种机制之一。当然,信访仍离不开法治的约束。依法治访即指信访活动依据法律进行,保障信访秩序,以实现民主、公正的价值追求。在信访治理中,一方面强调政府本身应依法行政,保障民众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另一方面在民众利益受损的情况下,政府应依法维护民众的利益,通过部门间的协调,发挥“权利救济”的作用。因此,依法行政是依法治访的基本前提和基础,而依法治访是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和动力,两者统一于服务型政府和法治型政府建构的实践之中。
信访问题既是治理问题,也是法治问题,两者统一于信访治理法治化的进程。信访制度改革应坚持“治理”和“法治”两条主线,治理是从技术、工具层面对信访法治提出的要求,而法治则是从制度、价值层面对信访治理提出的规制。信访法治化是信访制度自我完善的重要路径,应整合现有的信访法律制度体系,发挥和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同时,积极推进信访立法,完善配套法规和立法解释,提升信访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2.目标和利益的协调者
由于信访事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日益增强,政府自身的资源、知识和能力有限,这就需要引入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来共同建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机制,并重视政府在其中所具有的“元治理”的特殊角色和作用。在元治理中,政府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统筹各方力量,牵头相关组织机构联合会诊,动员其他力量参与,既达到“元治”,又不破坏“自治”。
信访工作牵涉部门繁多,有效的跨部门协同治理体制,有利于提高信访治理的“内聚力”,有利于提高信访事项办理质量。在内部,从权责配置、协同机制、常态考核等维度,理顺政府组织内部各个部门领导体制及决策体制。在外部,引入多元主体力量的制度化参与,建构高度专业化、合理化的信访治理体系和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网络,推进信访治理的制度化、法律化。监管的复杂性和网络社会的多元性需要元治理,政府可以通过使用元治理工具行使权力,同时与其他行动者共担公共治理的责任(Kari Hakari, esc., 2013)。政府应整合多元社会主体及其资源,构建网络化的治理结构,通过政府的“有限参与”让渡一部分“社会权力和资源”,提升信访治理绩效和能力。
3.冲突和矛盾的调和者
元治理有利于政府在信访治理角色调整中实现量与度的统一。从“量”看,通过多元治理的混合安排,发挥政府在信访工作中的统摄作用,这有利于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良性互动中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从“度”看,元治理范式克服了多中心治理模式下政府治理的“碎片化”问题,通过公共理性和公共价值的建构,协调和疏导社会矛盾。元治理理论是对治理主体的积极回应,采用更加灵活、更具弹性的治理形式,从而调和冲突、化解矛盾,推动多元治理的责任共担。
多元治理力量的重新布局和优化组合,促使行动一致,有利于实现最优效益。推动社会矛盾的多元调解模式,分流和疏导社会矛盾,防止信访矛盾引致较大规模的群体冲突。建立和完善利益平衡体系,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制度性的利益表达渠道,以合理、有序的疏导方式,将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传达到地方政府的决策体制中,促进公民的有效参与,谋求政府与社会的制度化合作。
四、“元治理”视域下政府信访治理的行动指向
元治理并非主张“全能型政府”,而是致力于通过制度整合和战略安排,实现主体结构优化和利益联结。鉴于此,信访部门可以在制度、战略和机制等层面进行改革。
(一)制度上,利用立法契机推行“扩权”改革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运作逻辑表明多元主体共存时代,国家仍在治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不管这种作用是实质性的还是象征性的,国家的“治理化”倾表现的尤为明显。国家治理体系建立在治理能力现代化基础之上,强调对政府及其治理方式的“治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元治理打破了政府与治理对立的僵局,通过混合制度安排将科层制置于治理的首要位置。
信访制度的改革应与社会制度变革相联系,以法治建设为核心,完善信访治理体系。一是建立法律体系。将信访制度纳入法律的轨道,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明确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权责范围和运行机制等;推进信访的法治化、规范化和科学化,进一步实现依法治访。二是完善协调机制。信访制度所遭遇的困境,远非单纯的信访制度本身的改革,而应将信访制度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通过国家制度体系的整合,探寻信访制度与行政诉讼、行政复议、中央巡视制度的有效对接。三强化监督体系。由于中国共产党具有较高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权威统治能力,应充分发挥党的监督。同时,强化人大的法律监督地位,通过问责机制,追究政府及行政人员应承担的责任,以达到权力与责任的平衡。四是改革考评体系,将信访问题解决的成效和民众满意度相结合,纳入公务员考核体系。
(二)战略上,动员社会力量实施“减压”策略
元治理在治理“去中心化”的浪潮中,完善了多元治理的规则和机制,将政府及其治理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元治理既坚持“协同、合作”的理念,又强调“权威、协调”的价值,从而保证了“共治、共享”格局的稳定性。认为元治理是“政府强势回归”的观点是对元治理理论的误读,实质上元治理并非是要塑造绝对统治或过分干预的“强政府”,而顶多是想要构建科层制影响下的“大政府”。信访治理的战略框架应涵盖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这些主体依据特定的法律、规则和制度安排,采用网络化的组织体系,在信访事项的各个阶段,共同配合,协作完成信访矛盾缩减、预备、反应和恢复的全過程。其中,政府居于“元治”地位,制定行动依据,统一调度资源,协调多元治理主体的目标分歧与利益矛盾。尽管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治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在政府主导型社会下,元治理理论在信访领域推行和应用的阻力相对较小,并且政府仍是信访治理的“第一责任人”,其主体责任并未削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