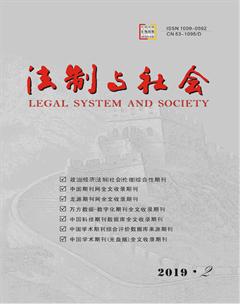论归因之于归责的区分性意义
杨加宇 钟凯
摘 要 刑法上的归因与归责分属不同层面,司法实践中,通过因果关系明确归因这一事实性问题尚不能解决行为定性的全部疑难,从位阶关系来看,归因仅是归责的前置性条件,而欲完清归责这一评价问题,还需通过客观归责理论进行判断。本文通过对张某涉嫌滥用职权一案司法定性问题的评析,指明在行为不具备刑法上的实行行为性时,不应将该行为作为危害结果之原因。而在因果关系获得确证后的归责过程中,若行为人尽到了法律上的注意义务,没有制造不被允许的危险、没有实现不被允许的危险,亦不能将责任归咎于行为人。
关键词 滥用职权罪 归因 归责 因果关系 客观归责
作者简介:杨加宇,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助教;钟凯,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2.024
一、案情概述
张某系四川省某市某县规划管理局副局长,分管该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审查等工作。2009年,张某多次接受“XX大厦”开发商王某等人的宴请,并收受了其提供的红包现金人民币5000元。2009年6月22日,在“XX大厦”规划报建时,张某予以了审批,在审批过程中,张某发现方案总平图上标注该宗用地上尚有一处应当拆除的已建建筑,遂提醒王某,应在项目竣工验收之前拆除该建筑,并要求其写下了一份书面承诺,该宗土地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也就该情况出具了证明文书。随后,张某对该项目颁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XX大厦”顺利建设完毕,并预出售给158户业主,业主共支付购房款共计人民币4000余万元。但在该项目规划核实阶段,张某发现该应拆建筑仍未予以拆除(事实上,由于王某报建时提供的“XX大厦”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明系通过贿赂国土部门,以空白的国土证书变造,故该宗用地事实上无法整合,该应拆建筑亦无法拆除),故不同意通过该项目的规划验收,由此导致150余户业主无法办理房屋产权证,并引发群众多次到县委、县政府上访。
庭审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意见:
控方认为,根据《某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08年)》(以下简称“08规范”)附录五某市建设工程方案设计总平面图编制规定第7条之规定,建设用地范围内要保留的现状建筑应明确,同时总图中应正确表达用地周边现状建筑。总平面图审查时对用地范围内未标注的现状建筑视为将被拆除,不纳入指标计算,并在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必须现予拆除。故张某在审批“XX大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时,属于违规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造成了群众上访的恶劣社会影响,应当构成滥用职权罪。
辩方认为,张某在审批“XX大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的审批依据应为《某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07年)》(以下简称“07规范”)第9.0.6条,即城市规划要求应当拆除的建筑物,必须拆除后方可办理规划验收的规定。按该规定之意旨,只要“XX大厦”在规划验收阶段拆除了应拆建筑的,均不影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核发。故即便出现了群众上访的结果,亦不可归因于张某的审批行为,而应归因于王某伪造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行为,其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
二、法理评析
笔者认为,归因与归责是不同层面的两个问题:在归因的层面上,张某核发“XX大厦”规划许可证的行为,涉及两个层面的判断,其一,其行为是否属于具有造成法益侵害结果危险性的类型化的实行行为,若其行为本身不具有法益侵害的危险,就应该排除其行为的实行行为性,换言之,其核发规划许可证的行为就不应成为导致150余户业主无法办理房屋产权证,并引发群众多次到县委、县政府上访结果的原因;若其行为可以被类型化的解释为滥用职权罪的实行行为,则存在从刑法上进行归因的理由。其二,就滥用职权罪的结果这一客观的超过要素而言,若张某核发规划许可证的行为虽与结果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但通过从客观归责的条件进行审查,能够形成行为没有制造不被允许的危险,或该危险不是在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中实现的,则不能将该结果归责于张某。若对该两个层面的问题都得出了否定性的判断,就只能形成张某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解释结论。就此,笔者拟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张某不具备滥用职权罪的实行行为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所要解决的是,是否以及以何种标准将某个构成要件结果归属于行为的问题。因此,实行行为的确定成为因果关系判断的前提。 从规范形式上来说,构成要件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的类型,因此,判断张某的行为是否属于滥用职权,首要的工作是对行为进行定型。理论上认为,滥用职权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为存在不法行使职务上的权限的行为,也即就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般职权权限的事项,以行使职权的外观,实施实质的、具体的违法、不当的行为。
结合本案之案情分析,笔者认为张某核发规划许可证以及不通过“XX大厦”规划核实的行为并不能充分滥用职权罪关于实行行为类型的描述,不属于法律上的滥用职权行为类型。经审理查明,作为某市规划部门行政审批主要依据的《某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修订较为频繁,相关技术规定在不同版本中也有所调整。“XX大厦”项目系于2008年7月2日经某县规划局核定了规划条件,并于2008年7月22日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而“08规范”的生效时间为2008年9月1日,该情况说明,即便“08规范”的文本在在“XX大厦”项目规划许可阶段前已然公布,但由于尚未生效,相关法定义务就不能构成对张某行政审批的约束,其在核发规划许可证时亦只能适用“07规范”,而该规范也就必然构成“XX大厦”项目行政审批的基本依据。同时,根据“08规范”之规定,其虽要求在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需拆除应当拆除的建筑物,但该规范亦专门在其第9章第9.0.1条对该规定所可能导致的前后两项规范适用冲突的情况进行了释明,并以授权性规范的形式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即2008年9月1日前),已取得《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并经核定规划条件,或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工程,可按原有关规定,即《某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07年)》执行。”按该条之规定,“XX大厦”项目具备规划条件取得规划许可的时间为2008年9月1日之前,故即便是依照“08规范”之意旨,张某仍可以继续沿用“07规范”的相关规定,适用该规范第9.0.6条。由此观之,王某所经营之单位,在项目施工阶段未拆除应拆建筑的,只会对项目规划核准阶段的规划验收造成影响,而不会影响规划许可证的审批与颁发。故而,张某核发规划许可证的行为并不属于不法行使职务上的权限,无法类型化为上述任何一种滥用职权的行为类型,不具备实行行为性。与此同时,张某在“XX大厦”竣工验收过程中,查明该项目尚有应拆而未拆除的建筑,不符合通过规划核实的条件后,拒绝该项目通过规划核实,亦是符合“07規范”之限定性要求的,是依法履职之结果,而在欠缺了“不法”之前提后,无论是运用何种解释方法,都不可能将该合法行为类型化为滥用职权的实行行为的。
(二)张某的行为不能从刑法上进行归责
笔者亦拟按客观归责理论的诸条件对其行为的归责问题做进一步分析:
第一,张某没有制造不被允许的危险。被允许的危险理论表明,法所禁止的仅仅是不被允许的风险,当行为人在遵守既定的规则、规程与注意义务的前提下,发生了法益侵害的结果时,这一结果不应在客观上归咎于行为人的行为。关于制造法所不允许的风险之客观归责的规则,理论上存在降低风险、没有制造风险以及假定的因果过程三种类型,张某的行为符合没有制造风险的类型性要求。本案中,由于王某提交审批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明系其伪造,其客观上并不具备拆除该应拆建筑之条件,由此必然导致项目无法通过竣工验收并获得房屋产权证的结果。如后所述,张某在不具备对国土证的真实性进行实质性审查的法律义务的前提下开展行政审批活动,对 “XX大厦”项目变造国土证并必然导致无法通过竣工验收的结果不可能具备预见可能性,故其只能在自己的责任领域范围内,根据王某提交的形式上合法的报建材料,依照《行政许可法》和“07规范”之要求,在完成形式审查后核发规划许可证,至于国土证是否系变造抑或是是否是通过合法方式取得,张某既无法律上的义务也不具备实质审查之权限。故应该说,张某核发规划许可证的行为虽然没有降低风险,但也没有以在法律上值得关注的方式提高风险,属于没有制造不被允许的危险的情形。
第二,张某没有实现不被允许的危险。在客观归责的认定中,不仅要关注是否制造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还应当进一步考察法所不容许的风险是否实现。关于实现法所不容许的风险之客观归责的规则,又包括未實现风险、未实现不被允许的风险、结果不在注意规范保护范围之内以及合法的替代行为和风险提高理论四种类型,张某的行为符合结果不在注意规范保护范围之内的类型性要求。该规则认为,行为没有引起和足以规范的保护目的所包含的结果时,排除客观归责。易言之,行为虽然违反了注意规范,但所造成的结果并不是违反注意规范所造成的结果时,排除客观归责。 就张某的注意义务而言,按照《行政许可法》第31条之规定与该法第34条第2款规定,根据该法之意旨,张某作为行政审批机关的主管人员,对王某提交的行政审批申请,仅具有形式上的审查义务,相关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应由王某负责。也即是说,只要王某提交审批的申请材料在形式上符合行政审批之要求,张某即无理由驳回其行政审批申请,否则即构成行政上的不作为。然而,由于王某提交审批的关键材料国土证系由国土部门颁发的空白国土证变造而来,张某通过正常的审批程序如核查印章、编号等对该证件进行形式判断并无可能发现该情况,而张某在完成了形式审查之后,就已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若是在法律之外对其科加实质上的审查义务,实属强人所难。
(三)张某履行了职务上的注意义务
风险如何分配,本质上涉及的是注意义务如何分配的问题。它往往与风险是否容许的判断联系在一起。 在对张某的行为进行归责的过程中,判断其是否制造了不被允许的危险的依据之一就在于其是否在核发规划许可证时履行了职务上的注意义务。
笔者认为,张某在核发“XX大厦”项目规划许可证时,已按《行政许可法》之要求,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也即依法按程序进行了形式审查。从前文所做之论述可知,由于规划部门不具备辨别国土证系变造之客观条件,故张某对“XX大厦”建成后无法通过规划验收是不具备预见可能性的,当然,对于业主无法办理房屋产权证以及群众多次到县委、县政府上访的客观超过要素所描述的结果,规范上也不可能对张某科处该项注意义务。
从认识因素上看,张某在审批“XX大厦”的项目总平图时,获取的是由王某提供的底图,该底图在功能上只能用于反映客观存在,只要在其中未标注为保留建筑的,均应作为应拆建筑进行审核,故是否在总平图中标注了该建筑,并不影响规划许可证的颁发,换言之,即便张某知晓项目总平图中标注了应拆建筑,也不能据此形成不应核发规划许可证的结论。从意志因素上看,一个简单的司法推定即可证明,张某对于可能出现的不能通过规划核准的结果是排斥的、否定的,否则其亦无必要在核发规划许可证时“节外生枝”的要求作为建设方的王某在规划许可阶段提交承诺书,承诺在规划验收前拆除应拆建筑。显然,该项举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规避可能出现的应拆而不拆违规建筑并导致无法通过规划核准的结果。故而,可以说,就职务上所设定的注意义务而言,张某已经做到了履职尽责。
注释:
张健一.解构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
[日]山口厚.刑法各论(第2版).有斐阁.2010年版.第607页.
张明楷.刑法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页.
劳东燕.风险分配与刑法归责:因果关系理论的反思.政法论坛.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