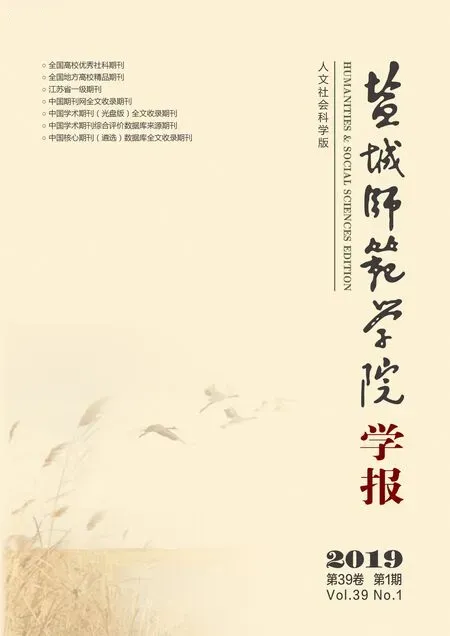传统节庆中的兰草应用及其文化意义
张晓蕾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兰草与兰花的历史区分与演变大概以宋代为界,即宋代之前的“兰”主要指兰草,宋代及其以后的“兰”则主要指兰花。兰草外形朴素,是一类枝叶皆香的香草,其中以佩兰、泽兰、蕙草(即零陵香)三种为主,具有广泛的社会应用价值。兰花即今天常见的兰花,是一种花香叶不香、形态优美的观花植物,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我们这里主要探讨的是兰草在传统节庆中的应用,并对其中所蕴含的精神文化意义予以揭示。兰草是一种具有独特香气的香草,具有驱除蚊虫、防止瘟疫、净化空气等多种功效,而其香则令人感到心情愉悦,故古人认为兰草十分神秘,从而赋予了其通感神灵的功能意义,在古人心目中,兰草是一种十分美好、神圣的香草,从而被应用到各种民俗节庆之中,其中尤以在上巳节、浴兰节和浴佛节中的应用最为突出,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意义。
一、上巳节----秉执兰草,拂除不祥
上巳节是我国的一项传统节日,历史悠久,今多认为起源于春秋时期,两汉时期经过官方大力推广,魏晋时期普遍流行开来,至唐代已成为全年的三大节日之一,但宋代以后渐趋衰落,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仅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尚有保留。魏以前上巳节的时间是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并不固定,魏以后才被固定为农历三月初三,如沈约《宋书》云:“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巳也。”[1]386早期上巳节的主要活动为祓禊,是一种在水边举行的祓除邪恶的祭礼,目的是为了消灾除病。先秦时期这一活动名为衅浴,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其目的是为了消灾除病。郑玄注曰:“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2]816这里的“衅浴”就是在水边举行的祓除祭礼。东汉时期,这种临水洗濯、祓除邪恶的祭礼仪式才正式称作“禊”。需要注意的是,古人袚禊并不一定是真的在水中沐浴,朱熹曰:“古人上巳祓禊,只是盥濯手足,不是解衣浴也。”[3]另外,上巳节还是一个青年男女相会的节日,这一活动起源于仲春会男女的风习,《周礼·地官·媒氏》记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奔者不禁。”[2]733迟至春秋时期,随着上巳节的兴起,男女相会这一风习活动逐渐移入了上巳节,成为上巳节的一项重要活动,并在唐代发展成为踏青、游春的全民活动。因此袚禊和男女相会可谓是上巳节最传统和最重要的两项活动。
兰草与上巳节之间的关联见于《诗经·溱洧》一诗,诗曰:“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毛传曰:“蕑,兰也。”[2]346沈约《宋书》引《韩诗》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1]386可知《溱洧》诗中描绘的场景应是郑国上巳节的盛况,郑人聚集在溱水、洧水岸边,举行袚禊活动,同时青年男女也趁此节日自由约会。诗中的青年男女为了互表情意赠送芍药,而“秉蕑”则是为了拂除不祥。人们普遍认为,兰草的香气可以祛除邪恶、带来好运,如《神农本草经》记载:“兰草,味辛平,主利水道,杀蛊毒,辟不祥,久服益气、轻身,不老,通神明。”[4]《神农本草经》相传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约在秦汉时期被整理集结成书,可见人们很早就认为兰草具有“辟不祥”“通神明”的功能,所以郑人在上巳节之时秉执兰草以拂除不祥。
郑人上巳节秉兰拂除不祥,主要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是拂除病灾的不祥。春秋时期,医学尚不发达,而郑国又处于晋国、楚国、卫国、宋国等国的包围之中,战争频繁,死伤较多,因此人们需要这样一个日子来为亡者招魂续魄,同时也为生人拂除不祥,上巳节就承担了这样一种使命。兰草是一种香草,也是一种药草,因此古人认为兰草的神性和药效可以为他们消除病灾的磨难,而郑人上巳节秉兰就是希望芬芳的兰草可以消除疾病和灾难的不祥。其次则是拂除无子的不祥。古人十分重视家族的传承、子嗣的繁衍,周代就有仲春祭高禖的习俗,高禖即掌管人间子嗣繁衍的神,《礼记·月令·仲春》中即有记载。另外,《周礼·地官·媒氏》也记载了仲春时男女相会、自由婚配的习俗。毛忠贤先生认为祭祀高禖和男女相会“是性质相关相近的两件事,且同在仲春,因此是统属于高氏高禖节的,它源于人类的生殖神崇拜”[5]。上古时期,人们生育率低,又渴求子孙繁衍、家族长盛不衰,故有祭祀高禖的礼仪和男女相会的习俗。郑国青年男女在上巳节相会可以说是对这一古老习俗的一种继承,人们认为兰草具有生子的吉祥寓意,因此秉执兰草也含有祈求子嗣的意愿。关于兰草的生子寓意,主要源于郑国燕姞梦兰生子之事,据《左传·宣公三年》记载,郑文公的妾燕姞梦见祖先伯鯈赐兰,并言“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2]1868,后燕姞生得一子,并登上王位,即后来的郑穆公,可见在郑人心中,兰草与子嗣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郑人上巳节秉兰既是希望消除病灾,同时也寄寓了人们对子嗣的祈求。
需要注意的是,兰草在郑国被称为“国香”,有着崇高的地位,除了兰草自身独特的应用价值外,也与郑国的国情有关。郑国处于中原之中,北有晋国,南有楚国,而晋楚争霸,战场常在郑国,这使得郑国境内人口大量减少,疾病流行,而兰草正好具有防止瘟疫和治疗疾病的功效,是一种常用药草,同时人们还认为兰草可以“辟不祥”“通神明”,所以郑人上巳节秉兰希望可以拂除不祥,为他们带来好运。“上巳节民俗活动的表象是带有祭祀和狂欢性质的岁时节日,其内涵是中国古代民众对于延续后代和避免灾祸的需要”[6],兰草在上巳节中的应用实际上就紧紧贯穿了这一内涵。然而遗憾的是,上巳节秉兰这一美好的古老习俗并没有得到很好地继承,尤其是随着上巳节这一节日的衰落,后人对这一习俗已经十分陌生。
二、浴兰节----沐浴兰汤,辟邪祛病
“浴兰节”一名最早见于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荆楚人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形,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7]44-45《荆楚岁时记》是我国现存最早专门记载荆楚地区时令风俗的著作,作者宗懔(约公元502-565年),祖籍南阳涅阳(今属河南南阳市),其八世祖宗承,曾任宜都(今湖北宜都市)郡守,后子孙皆定居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宗懔生长于荆州,自然十分了解荆楚一带的时令风俗,因此撰写了《荆楚岁时记》一书,其所记浴兰节就是当时荆楚地区盛行的一个节日。至隋代,杜公瞻引用八十余种文献为其作注,杜氏所用材料并不限于荆楚地区的文献,而是多用北方文献,故从杜注可看出,当时荆楚的许多习俗也流行于广大的北方地区,其中浴兰节就是扩展到了北方地区的一项节日。另外,杜公瞻注曰:“今谓之浴兰节,又谓之端午。”[7]45可知至隋代时,浴兰节又称作端午节。宗懔所记五月五日为浴兰节,并未言及“端午”,但所记节日的活动内容却与端午节一致,这就表明宗懔时期,荆楚地区五月五日还未有“端午节”之称,后来随着“端午节”名称的普及,“浴兰节”之名渐废,故今多认为浴兰节是端午节的一个别称。
所谓浴兰,即以兰草煮汤沐浴,兰草是香草,具有浓郁的香气,用来煮汤沐浴可以洁身除垢。宗懔之前虽并未见有“浴兰节”一说,但浴兰习俗却是由来已久。《夏小正》中就记载了浴兰这一习俗,其曰:“五月……煮梅,为豆实也。蓄兰,为沐浴也。”[8]豆实是盛放在木豆中的祭品,五月煮梅用作祭品,而蓄兰则是为了沐浴,沐浴与斋戒是祭祀前的必要准备。先秦之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1911,祭祀是和平时期国家最重大的事情,而以兰汤沐浴洁身,则显示出古人对祭祀的虔诚。战国时期的楚国就沿袭了这一浴兰习俗,巫师在祭祀之前会以兰汤浴身,如屈原《九歌·云中君》云“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9]57-58,巫师以兰汤浴身,以香草沐发,然后穿上华美的衣服去侍奉神灵,这是巫师为迎神而做的一系列准备。其实楚国浴兰习俗带有浓厚的地域文化和宗教巫术色彩。一方面,兰草带有浓厚的楚地文化色彩。屈原辞赋开创了香草比德的传统,其辞赋中言及大量香草,如江离、杜衡、揭车、留夷、木兰、芷、兰、蕙、椒、桂、荪等,其中尤以兰蕙数量最多。屈原不仅通过佩带兰蕙来表达自己的芳洁之志,还以兰蕙来比拟贤才、忠臣,因此后世咏兰文学中多有“楚兰”“屈兰”之称。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有一篇《兰赋》,该赋是早于或者与屈原所处时期相近的楚辞类作品,作者不详,题目是由其整理者曹锦炎先生据其内容而定。从内容上来看,这篇《兰赋》是作者以兰比德、托物咏志之作,作者笔下的兰草虽然生存环境恶劣,遭受蝼蚁虫蛇的损害,但仍然保持自身的美好品德,这与屈原作品中的兰草比德相似。可见兰草在楚地绝非凡草,而是带有楚人情感认同的一种独特香草,具有重要的精神文化意义,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印记。另一方面,浴兰习俗带有浓厚的楚国巫术色彩。战国时期,楚国巫术活动十分盛行,班固《汉书·地理志》云楚人“信巫鬼,重淫祀”[10],楚人信巫,对鬼神深信不疑,故祭祀活动十分隆重。他们在祭祀前用兰汤沐浴洁身,除了表示对神灵的尊敬外,还有着十分重要的目的,他们认为兰香可以沟通神灵,因此通过浴兰可以使身体沾染兰草的芳香,从而实现人神沟通,得到神灵的庇护,这实际上是巫师取悦神灵的一种娱神行为,带有浓厚的楚国巫术色彩。
南北朝时期,荆楚地区浴兰习俗十分流行,但此时的浴兰习俗已经摆脱了早期的宗教巫术色彩,成为了一项全民性的节庆活动。人们在五月五日浴兰主要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辟邪,二是祛病。五月俗称恶月,自古就多禁忌,《礼记·月令》记载:“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齐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勿致和。节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毋刑,以定晏阴之所成。”[2]1370人们对五月心有畏惧,从而制定多种禁忌,希望能够避免灾祸。民间甚至还有五月五日生子不利父母之说,司马迁《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田文生于五月五日,其父田婴认为:“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11]可见五月在人们心中是一个十分不祥的月份,因此端午节的许多习俗内容都与辟邪祛恶相关,如在门口悬挂艾草、佩带香囊、饮雄黄酒等。而兰草自古就被认为具有辟不祥的功能,因此浴兰也是人们五月辟邪的一项习俗。另外,五月初始,天气变热,五毒孽生,是瘟疫易于流行的时期,人们容易感染各种疾病,尤其是皮肤等方面的疾病,所以人们会在此日采集艾草等诸种草药,用以祛除毒气,《荆楚岁时记》云此日“采杂药”,杜公瞻注引《夏小正》云“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8]48,而兰草作为一种使用广泛的药草,自然也属人们采集之列。兰草煮汤沐浴不仅可以洁身除垢,还能起到预防疾病的效果,因此人们在五月五日蓄兰沐浴具有祛除疾病的实用意义。
至后世,五月忌讳之说已渐渐消亡,如明谢肇淛《五杂俎》曰:“五月五日子,唐以前忌之,今不尔也。”[12]36但唐代时期浴兰习俗仍存,如唐韩鄂《岁华纪丽》曰:“浴兰之月。朱索,赤符,祭屈,祠陈,长命缕……时当采艾节及浴兰。”[13]367表明浴兰仍是唐代端午节的一项习俗。宋代欧阳修《端午帖子·皇帝閤六首》其四曰:“岁时令节多休宴,风俗灵辰重祓禳。肃穆皇居百神卫,涤邪宁待浴兰汤。”[14]表明宋人端午节也仍有浴兰活动。至明代浴兰已不再专用兰草一种药草,《五杂俎》云“兰汤不可得,则以午时,取五色草拂而浴之”[12]35,也有用菖蒲、艾草等煮汤沐浴的,后来“浴兰”“兰汤”逐渐成为沐浴、浴汤的一种美称,其辟邪祛病的民俗文化意义则逐渐为人所淡忘。
三、浴佛节----煮兰浴佛,敬佛祈福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十分流行,伴随着佛教的流传,与佛教相关的节日也随之盛行,纪念佛祖释迦诞生的佛诞节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项节日,又因佛诞日要以香汤灌洗释迦佛像,故又称作浴佛节。浴佛节一般在每年的四月八日举行,相传佛祖诞生之时,九龙吐水为其浴身,故人们此日灌洗佛像以为“弥勒下生之征也”[13]365。浴佛节自汉代开始出现并流行,晋陈寿《三国志》记载:“(笮融)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15]笮融是东汉末人,早年巧取豪夺,发家之后大兴佛事,修建佛寺、佛塔,吸引僧侣前来。每到浴佛节的时候,笮融就在道路上摆设宴席,数万民众都前来观望并就食,所费钱财要以亿为单位来计算,其盛况可想而知。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更加兴盛,僧人和寺庙的数量都不断增加,浴佛节作为佛教的重要节日,也随之盛行。关于浴佛节的意义,有学者认为其主要有两重含义:“一是象征性地再现佛祖诞生时的九龙吐水;二是表达对佛祖的怀念之情感。”[16]其实除此之外,浴佛节还含有人们希望子孙兴旺的祈福意愿,一方面人们趁浴佛节之际拜佛乞子,如《荆楚岁时记》记载:“四月八日,长沙寺阁下有九子母神。是日,市肆之人无子者,供养薄饼以乞子,往往有验。”[7]70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浴佛来为子孙祈福,如《高僧传》记载:“(石)勒诸稚子,多在佛寺中养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诣寺灌佛,为儿发愿。”[17]
“浴佛”即灌洗佛像,但所用之水并非普通之水,而是以各种香草制成的香水,据西秦释圣坚翻译的《佛说灌洗佛经》记载:“四月八日浴佛法,都梁、藿香、艾纳合三种草香,挼而渍之,此则青色水,若香少可以绀黛秦皮权代之矣。郁金香手挼而渍之于水中,挼之以作赤水,若香少若乏无者,可以面色权代之。丘隆香捣而后渍之,以作白色水,香少可以胡粉足之,若乏无者,可以白粉权代之。白附子捣而后渍之,以作黄色水,若乏无白附子者,可以栀子权代之。玄水为黑色。最后为清净。”[18]可知都梁香是制作浴佛香水的原料之一。都梁香即兰草,宋洪刍《香谱》引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曰:“都梁县有山,山上有水,其中生兰草,因名都梁香,形如藿香。”[19]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亦记载:“(都梁县)县西有小山,山上有渟水,既清且浅,其中悉生兰草,绿叶紫茎,芳风藻川,兰馨远馥,俗谓兰为都梁,山因以号,县受名焉。”[20]可知都梁香是兰草的俗称,是荆州都梁县地区兰草的特定称谓,圣坚虽是西秦人,但精通华、胡语文,曾译出《罗摩伽》等15部佛经,他一生云游四海,见多识广,因此知道都梁香草并不稀奇。关于制作香汤浴佛,宗懔《荆楚岁时记》中也有相关记载,其曰:“四月八日,诸寺设斋,以五色香水浴佛,共作龙华会。”杜公瞻注曰:“按《高僧传》:‘四月八日浴佛,以都梁香为青色水,郁金香为赤色水,丘隆香为白色水,附子香为黄色水,安息香为黑色水,以灌佛顶。’”[7]39这与《佛说灌洗佛经》记载有所不同,当时我国佛教僧徒浴佛所用香水已经衍变为由五种香草制作而成,但其中依然包括都梁香,也就是兰草这种香草。
兰草气味芳香,其自然属性适合制作香水,而以之灌洗佛像主要蕴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人们希望借助兰草的芳香向佛祖传达崇敬之情,另一方面则希望取悦佛祖、赐福于己。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认为兰草这种独特的香草,具有辟不祥、通神明的功用,从而被应用于各种祭神活动之中,在人们心目中兰草是一种能够建立人与神之间联系的“神草”。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加上当时战争频繁,赋税较重,疾病流行,朝不保夕的人们渴望和平安定、无病无灾、多子多福的生活,因现实的不可得,人们希冀借助宗教的力量来实现安定的愿望,而佛教徒为了宣传自己的教义也尽量迎合民众的心理需求,兰草沟通神灵的功能,正好投合了当时人们祈求佛祖庇佑的普遍愿望,所以僧人以兰草来制作浴佛香水,正是基于对传统与现实的深入思考。僧人除了用兰草浴佛外,还用兰草沐浴,是一种洁身净心的方式。《幽明录》记载:“庙方四丈,不作墉,道广五尺,夹树兰香。斋者煮以沐浴,然后亲祭,所谓兰汤。”[22]关于兰香,据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引《唐本注》云:“陶云都梁香乃兰草尔。俗名兰香,煮以洗浴,亦生泽畔,人家种之。”[22]可知兰香即兰草。僧人在寺庙路边的树下种植兰草供斋戒之人沐浴,以洁身除垢、净化身心。可见兰草是僧人常用的一种香草,无论是以之沐浴,还是以之浴佛,实际上都是对当时普遍流行的浴兰习俗的一种反映。
风俗具有时代性,随着时代的变迁,浴佛习俗也在不断变化,到了宋代,浴佛节增加了饮用浴佛香水的习俗,金盈之《醉翁谈录》记载:“既而揭去紫幙,则见九龙,饰以金宝,间以五彩,从高噀水,水入盘中,香气袭人。须臾,盘盈水止。大德僧以次举长柄金杓挹水,灌浴佛子。浴佛既毕,观者并求浴佛水饮漱也。”[23]为了满足人们饮用需求,浴佛所用香水也逐渐开始发生了变化,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四月八日,佛生日,十大禅院各有浴佛斋会,煎香药糖水相遗,名曰浴佛水。”[24]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四月八日为佛诞日,诸寺院各有浴佛会。僧尼辈竞以小盆贮铜像,浸以糖水,覆以花棚,铙钹交迎,遍往邸第富室,以小杓浇灌,以求施利。”[25]浴佛香水不再使用兰草等各种香草或香料,而是改用更加适合人们饮用的糖水,更加贴合民众,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
四、结语
兰草在传统节庆中的应用始于先秦时期郑国的上巳节,这并非偶然。首先,郑国溱、洧流域地处中原腹心,土壤肥沃、水源充足,十分适宜兰草的生长。其次,郑人称兰草“国香”,燕姞梦兰生子,都足以说明兰草在郑国具有崇高的地位,是深受国人崇拜的一种“神草”,因此郑人上巳节秉兰希望能够借助兰草的力量拂除不祥、带来好运。而至南北朝时期的浴兰节,人们以兰草煮汤沐浴希望可以辟邪祛病,这实际上与上巳节秉兰殊途同归,都是希望借助兰草的力量来达到禳灾的目的,但浴兰显然比秉兰的方式更能体现人与兰草之间的密切联系,似乎也更加贴合人们实现洁身除垢、消除病灾的愿望。如果说上巳节和浴兰节是人和兰草之间通过接触的方式来实现禳灾的目的,那么浴佛节则是通过建立佛祖和兰草之间的联系来传达人们的祈福意愿,以兰草制作香水灌洗佛像取悦佛祖、传达己愿,从而达到祈福目的。虽然浴佛仪式是从印度传入我国的一种佛教活动,但是以兰草制作浴佛香水,却是我国佛教徒的一种自觉选择,这显然是受当时流行的浴兰节及浴兰习俗的影响。其实兰草在这些节庆习俗中的应用,都是建立在兰草自身的实用价值以及人们对兰草的崇拜情感之上的。一方面,兰草香气可以驱蚊杀虫、预防瘟疫等,古人认为兰草具有“辟不祥”的禳灾意义;另一方面,兰草香气令人感到愉悦,但又无色无形,古人感其美好、神秘而认为兰草具有“通神明”的祈福意义。所以古人上巳节秉执兰草拂除不祥、浴兰节沐浴兰汤辟邪祛病、浴佛节以兰草制香水浴佛祈福,实际上都源于人们对兰草或“禳”或“祈”功能的认知,寄寓了人们辟邪趋吉的心态以及对生活的美好祈愿,蕴含着丰富而深厚的精神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