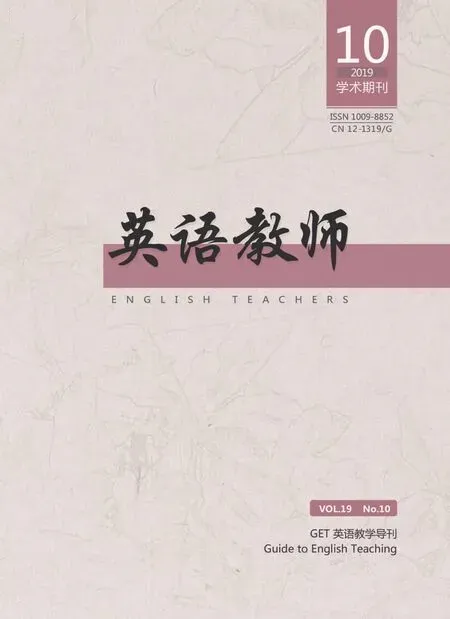二语对我国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的影响因素分析
李冬萍 邓东元
引言
在研究语言能力的发展过程中,国外学者发现二语对三语习得产生了影响,三语习得有别于二语习得,因为习得者可以对二语习得过程中使用的策略进行有意识反思并将其应用到三语习得(Jessner 1999)。克拉申(Krashen,1985)输入假说(The Input Hypothesis)的核心概念是“可理解性输入”,在语言习得过程中,为习得而输入的语言信息应略高于习得者现有水平,即:若习得者的现有语言水平为“i”,那么语言习得时的输入水平应为“i+1”。在语言习得过程中,二语的输入会对三语习得产生影响。我国少数民族学生的二语(汉语)是在民族语(母语)之后学习的一门新语言。研究发现,随着二语水平的提高,我国少数民族学生的二语(汉语)水平与三语(英语)学习效果呈正相关(孟娜佳、敖玉文2012)。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重视学生三语的习得问题,为学生的英语有效学习提供了良好环境,通过重视语言输入来促进其学习效率的提高。
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三语教学现状
(一)教学模式多样化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教学模式和其他方面相对滞后,不同民族聚集地区的教学现状也有所不同。现代教育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翻转课堂和微信平台等不仅推动了语言教学的有效输入,而且推动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三语教学模式的多样化发展。有研究发现,翻转课堂在我国少数民族学生构建学习模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运用语言能力方面具有显著效果(赵冰、何高大2015)。由微信平台支持的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及英语教学的量化分析发现:通过微信平台的英语学习能使少数民族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得到较大提升(凌茜、秦润山,等2016)。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和三语教学模式已在现代信息技术影响下呈现形式多样化趋势,学生的学习效能得到了较大提升。
(二)师资力量不均衡
不同语种的相互交错与融合为三语教学的师资力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队伍不仅要有扎实的语言基础和丰富的教学经验,还应有足够支撑办学规模的数量。通过对我国西北民族地区外语基础教育现状的调查研究发现:师资数量和质量不足的情况成为限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外语教学发展的主要因素(姜秋霞、刘全国,等2006)。甘肃民族地区的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队伍仍存在师资力量比例失衡的问题,如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及中高级职称比例等(邱梦琪2017)不均衡。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外语师资力量不均衡,不仅阻碍了学生语言输入质量和水平的提高,而且限制了该地区的三语教学发展。优质而均衡的师资力量不仅能有效推动我国少数民族学生的二语习得,而且能改善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三语教学状况。
二、我国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一)多语言变化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语则属于印欧语系,是日耳曼语族。我国一些民族语属于汉藏语系或印欧语系,如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彝语。我国少数民族学生习得的语言多种多样,在语音、词汇、语法和文化知识等方面也产生了较大差异。处于不同语系环境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面临的语系变化更为复杂。在语音方面,多语之间若有重音,学生能较快且准确地掌握语音;在语序方面,汉语和英语的基本语序结构具有相似性,如主—谓—宾结构,这类相似性能帮助学生加快学习进程。在多语言变化的影响下,语言转换的熟练度也是语言习得的有效输入。
(二)多文化理解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体现。我国少数民族学生受地理位置、生活条件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自身文化内涵特色多样。有学者在研究三语教学时指出:通过将英语教学和文化适当结合,可有效发挥文化价值在语言中的作用(梁春霞2010)。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文化理解差异是英语学习的难点。当少数民族学生长时间处于汉语的文化环境时,其英语习得会受到汉语文化的影响。随着汉语文化的输入不断增大,学生的汉语语言学习水平会逐步提高,而作为中介语的汉语会对英语学习产生显著效果,从而加深学生对英语文化的理解。
(三)多频次使用
周锦国(2018)通过对云南省民族地区的学生语言使用情况调查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学生在校园里使用普通话的频率较高。二语在三语习得中的使用频率和语言距离密切相关,二语在语言类型上越接近于三语,习得者使用二语的可能性越高。语块习得问题在外语教学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应该把重心放在输入与输出不同类型频率的效用上。语言的使用频率在学习过程中具有积极作用(周正钟2018)。我国少数民族学生有充足的汉语输入,对习得与运用汉语并提高英语具有推动作用。对汉语的高频使用提高了我国少数民族学生汉语的熟练水平,同时提高了英语学习的效能。
三、二语(汉语)对我国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的影响
(一)思维认知转换模式
二语习得不仅推动个体认知控制能力的发展,而且在认知控制能力方面,二语个体比单语个体更有优势(Costa&Sebastián-Gallés 2014)。二语的有效输入对我国少数民族学生的认知水平、语言能力及非语言能力都会产生影响。如果对二语的思维认知较弱、学习策略不恰当、理解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不强,那么在三语习得过程中会有更多的语言信息损耗,从而加大三语学习难度。因此,在我国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的过程中,二语的思维认知能力至关重要。因为提升二语的思维认知能力能进一步掌握三语的学习规律和方法并扩大输入量,从而更好地习得三语。
(二)语言水平表现差异
语言水平是影响语用能力的首要因素(Ellis 2008)。习得者二语的语言水平影响其语言能力,从而对其三语及三语习得产生影响。我国少数民族学生的二语作为学习三语的中介语,不仅表现出跨语言影响的一种复杂性,而且影响其语言能力的发展。二语水平对三语习得有显著影响,在新疆学生样本中体现出汉语水平高则英语水平高;汉语水平低则英语水平低的情况(蔡凤珍、杨忠2010)。较高水平的语言习得能较好地提高语言有效信息的输入量,从而推动更高效的语言习得。在二语习得过程中,习得者只有达到一定的语言水平高度,才能有一个更好的语言认知,从而在基于这一语言认知优势上达到更佳的学习效果。
(三)语境文化意识特征
根据输入假说表明,基于“i+1”水平的输入语料时,通过语境文化的辅助理解,习得者能以更好的语言能力来消化语言。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教师在英语教学中不能离开语境,应该注意对特定语境的理解,以锻炼学生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使用能力(李育卫、王琼2018)。在汉语的大环境中难免会有英语输入较少、标准性不达标等问题,从而影响英语语境文化的意识培养。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英语教师普遍使用汉语进行教学且教学方法与汉族学生相同,于是少数民族学生在以汉语理解英语的过程中易出现输入偏差等问题。这种偏差不止表现在少数民族学生从民族语到汉语的意识理解,也表现在从汉语到英语的内涵认识,导致他们对英语的语境文化接受程度有差异,从而存在对三语的理解困难等问题。
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三语教学建议
(一)制订符合我国少数民族区域特色的外语教育政策
制订符合少数民族区域特色的外语教育政策,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交流和语境特征,有助于因地制宜地设置外语课程。目前专门为我国少数民族双语学生编写的外语教材较少,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主管部门没有制定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学大纲或要求(曹艳春、徐世昌2014)。因此,应充分考虑我国少数民族的认知思维模式,从听、说、读、写、译等方面促进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汉语的有效输入能提高英语学习的效率。所以,有关部门应根据学生的具体掌握情况制定外语教育政策,增强教学政策支持,同时加大教学设施的投入。
(二)加大适宜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师资队伍建设力度
在我国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中,学生学习英语的中介语是汉语,大多数英语教师只会用汉语教学,没有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经历,英语教学方法和所用教材也与汉族学生相似(崔占玲2011)。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应加大师资队伍的建设力度,加强本民族外语教师的培养,通过信息与通信技术培训,提升教师的创新教学能力;同时培养具备使用民族语、汉语、外语(英语)等多语能力的教师;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来丰富教学模式,因地制宜,培养能满足我国少数民族区域特色的英语师资队伍。
(三)提高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认知和身份认同感
语言与身份认同在语言学习中起着重要作用。我国少数民族学生在生活、学习中对三种语言的认知和理解都会强化自身的民族认同,进而推动自身学习语言文化的动力。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语(母语)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优势会成为强化学生民族认同的因素,英语(三语)使学生注意反思本族的文化与语言(阿斯罕2015)。我国少数民族学生需要提高自身的认知和反思能力,积极锻炼语言的转换模式,以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英语。因此,在语言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重视我国少数民族学生的身份认同感的培养。
结语
通过分析二语对我国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的影响因素,发现三语习得与二语习得有较大差异,所涉及的教学情况和跨语言影响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我国少数民族学生在三语习得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通过克拉申的输入假说分析二语对少数民族学生三语习得的影响,对英语教育提出参考性建议。三语习得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具有更高的探索价值,能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外语教学提供更为丰富的参考并对语言习得的研究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