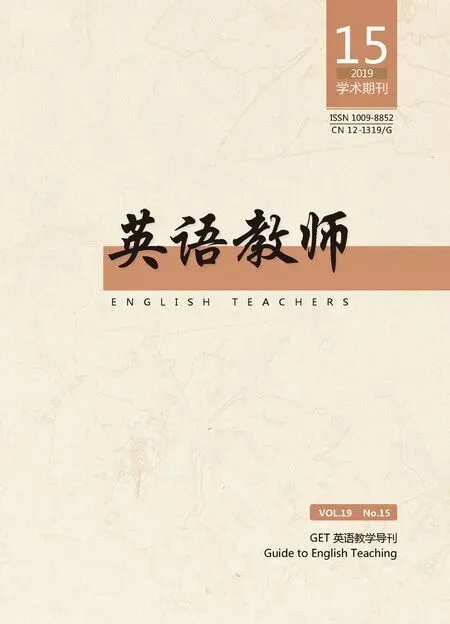汉译英中“雅”的境界
——以葛浩文英文译著《米》为例
张仲德 李雅萍
引言
译者必须是原著的忠实读者。葛浩文说过:“翻译的一切过程都由阅读开始。翻译是阅读过程,阅读也是翻译过程。因为在阅读的时候脑子里也是做翻译的。”(闫怡恂、葛浩文2014:194)葛浩文在谈翻译观时认为严复的“信、达、雅”的次序应该是“雅、达、信”或者“雅、信、达”。他认为“雅”是最重要的。这实际上是以美学的观点看待翻译,认为“信”和“达”是翻译的必备素质,而“雅”是翻译者的再创造。“雅”首先是一种内在的气质,这种气质来自译者对原著的深刻理解和自己翻译旅程的积淀。在语言上,葛浩文的翻译细致入微,深刻地体现了中文所携带的浓厚的文化信息,同时注重逻辑,以明了的事实袒护着读者的欣赏角度。然而,任何译语与源语的转换是不可能一一对等的,特别是小说翻译。戴乃迭认为葛浩文的翻译为中国文学披上了英美的外衣。鲜艳的外衣不但会吸引读者的眼球,而且会指引读者进入小说情景。葛浩文钟情于翻译,也钟情于中文;翻译是他一辈子的事业,中文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母语为英语的人,在逾越了中文的鸿沟之后,品尝阅读所带来的喜悦直至产出。母语是中文的读者,品读原著和译著,亦会有不同的感受和发现。本文在细细品读葛浩文英译著作《米》的基础上,探究葛浩文的翻译视角,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一、词语选择的“雅”境
无论中西方小说有多大的差异,它们都以文字所携带的信息表达过去的、当下的、未来的、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时间、事件、人物等因素。在事物描写上,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思维方式在语言中展现出独特的魅力。《米》的故事发生在20 世纪30 年代,其中的人物带有很深的农业和商业的色彩,这一点可以从人物名字见微知著。以下是葛浩文英文译著《米》中的重要人物名字:丝云—Cloud Silk;织云—Cloud Weave,抱玉—Jade Embrace,五龙—Five Dragons,六爷—Sixth Master,柴生—Kindling Boy,米生—Rice Boy,吕否基—Lu Piji。
从中文角度讲,除了最后一个是全名外,其他人物都有名(given name)无姓,但在翻译过程中,葛浩文把这些名字(汉语中的小名)用实词翻译。在翻译“丝云”“织云”“抱玉”时,依照英文先名后姓的顺序翻译;在翻译“五龙”“六爷”时,没有转换顺序;在翻译“柴生”“米生”时,将后面的“生”以“孩”或者“娃”的意思代替;在翻译吕否基(lu 应该为lv)时,则完全采用了现代的拼音译法。
中国人的名字含义丰富,有时与时代紧密相连。葛浩文在翻译时突出了这一特点,同时灵活变通,总体上表现了中国姓名与文化相关联的特点。通过姓名,母语非汉语的读者也可以理解小说的中国社会背景。葛浩文的翻译既重视了原文,又带有一种灵性和文雅。柴、米、油、盐,丝织、玉翠是农业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将这些表现在人物姓名中就会让读者明白,它是一部中国小说。对于“五龙”的翻译,葛浩文采取了直译法,龙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寓意吉祥、灵异和威严,但在西方社会中有邪恶之意。小说中的“五龙”性格乖戾,充满了邪意。葛浩文在翻译时借用了“龙”这个词语,拉近了与英语读者的距离;同时,以实意名词作为名字翻译是对中国文化深刻的理解和尊重,这对想了解中国的西方读者而言,是一种惊奇的发现;即使对中国英语学习者来说,这些姓名的翻译也颇有难度。笔者在英语课堂上曾让学生翻译“六爷”,很多学生将“六爷”译为six grandfather。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对中文太过熟悉而忽视了其内在的含义,在英译汉时出现了文不对题的错译。因此,在英汉翻译中要全面统筹,在理解过程中“除了把握原文的词义、句法之外,还应该掌握原文文化、时代、文体、作者的个人语言风格及作者或文中人物的情感、语气、观点、立场等方面的信息”(门冬梅、王一龙2015:82-96)。
葛浩文曾经说“自己阅读小说是以语言为主的,也喜欢人物描写”。然而,中英两种不同语系文字巨大的差异对于它的译者来讲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作为葛浩文的英译读者,有时会对他的翻译充满期待,有时会对他的翻译提出质疑。葛浩文的翻译以准确的理解为基础,让读者把握原意,如把“八抬大轿”翻译为“a sedan chair with eight bearers”,把“狼心狗肺的东西”翻译为“someone with the heart of a wolf and the lungs of a dog”。葛浩文在词语的翻译上先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再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将原著小说的形象以最贴切的方式表达,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集诗人、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德莱顿(转引自廖七一,2000:10)指出:“译者必须考虑译文的读者和对象,翻译方言时应以译作读者能否接受和理解为准绳,并适当借用一些外来词,但对这些词要适当斟酌,适可而止。”葛浩文对原著的斟酌是基于自己对中英两种语言及其文化深刻的理解,他对词语的翻译力求达到与原著同等的效果,将意义与形式完美结合,达到“雅”的境界。
二、句子翻译的“雅”气
从词到句,葛浩文的翻译都经过了精雕细琢。译者一方面要融入作品的语境;另一方面要切实感悟读者的理解能力。葛浩文曾经说:“我的翻译并不要‘雅’压到‘信’。如果‘雅’压到‘信’,那就不好了。”葛浩文翻译中对“美”的要求其实正如他所说的,抓住了中英文之间的创造性,将原著忠实地用英语漂亮地表达出来。下面是《米》一书中典型句子的中英文对比:
原文:织云还小呀,她才十五岁,那畜生到底安的什么心?
译文:Barely fifteen.How can that old bastard sleep at night?
这是妹妹织云沦为他人情妇之时自己父亲发出的咒骂声。用barely,fifteen 两个词为一句话代替了“织云还小呀,她才十五岁”的全意,干脆利落。在这里葛浩文紧扣原文,化解了“畜生到底安的什么心”所带来的语义冲突。因为“畜生”一词在中国语言中带有浓厚的贬义色彩。葛浩文采用非常简洁的直译法将意思表明:“仅仅十五岁,那个老混蛋晚上也能睡得安心?”副词barely 表明了父亲对女儿深深的爱,也表达出对吕否基的痛恨之情。在翻译时,译者要尽量以最贴切的西方人的语言表达习惯来传达作者的本意。再如:
原文:你是姐姐,你怎么不狠狠治她一顿呢?
译文:You’re her older sister,why not show her who’s boss?
原文:……可我们哪像一对姐妹,倒像是仇人。
译文:But instead of being sisters,we fight like cats and dogs.
在前一句中,由于姐姐丝云鄙视织云背后向她的衣服吐唾沫,五龙唆使她教训妹妹一下。译者在这里没有用teach her a lesson,而用show sb.who’s boss。如果就具体行为而言,这里用前者(teach her a lesson)比较合适,但从上下文来看,实际上姐姐丝云是主事人,是她的理智与聪慧在支撑着大鸿米店。因此这里用后者(show sb.who’s boss)更能显示出姐姐的权威性,也很适合西方人的表达习惯。后一句说两姐妹在米店内的恩恩怨怨,但毕竟是一家人而不是传统意义上不共戴天的仇人(enemy),用俚语(like cats and dogs)翻译更加贴近原文。
翻译是以一种语言符号代替另外一种语言符号,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转换表达,从而引起目的语读者的共鸣。同时,对于小说的欣赏,“用视觉符号的方法去洞察生活、再现思想时,便成为一种思维创造的操作方法,创造文字的符号和符号的文字,创造文字的图形和图形的文字(葛艳梅2015:70-76)”。在中英两种语言中徘徊,不仅仅追求的是词语的语义对等,更是对文学作品中一种灵性的追寻。很明显,在英译著作《米》中,葛浩文远远逾越了译者是作家仆人的界限,他大胆地以自己的尺度试图超越原著。他考虑的是语言的能量,创造的不仅仅是意向,更是一种能够吸引读者的优雅之美。汉语中浓厚的文化色彩如“畜牲”“仇人”“放荡”等无法被英语国家的人所理解,即使理解,也会在译文中显得差强人意。然而,葛浩文走进了中文的世界,又在中文中摄取了她的精华,用英语将其表达出来。他无意冒犯作者,也没有随意取悦目的语读者,而是以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手法使译语显得温文尔雅又不失威严。
三、段落逻辑之“雅”
葛浩文在翻译《米》时,很注重翻译的逻辑性。作为译者,葛浩文一遍又一遍地体会原著的意思。因为对于译者而言,有读不通顺原作的地方,这有可能是作家的问题,也有可能是译者自身语言理解的问题。例如:
原文:午后的阳光从两侧的屋檐上倾泻下来,柔软的丝绸像水一样地波动,静心捕捉甚至能听见一种细微的令人心醉的噼啪声。
译文:Rays of afternoon sunlight poured down past the eaves;soft silks fluttered gracefully,like waves,calming her mind...
从翻译的角度来讲,这段话处理得非常简洁,语言具体、生动。但是从小说的整个布局来看,这句话在所在章节甚至整个小说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鸿米店老板的姑娘丝云和织云在瓦匠街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但她们的厄运都在此章降临。丝云与阿宝的偷情,五龙告密,阿宝被杀,丝云失宠,都在这一章内发生。小说中“能听见一种细微的令人心醉的噼啪声”有意地点明了这一悲剧的发生,然而葛浩文在翻译中将它省略,当再进行转译时就会理解为“午后的阳光从两侧的屋檐上倾泻而下,柔软的丝绸如涟漪般粼粼波动,使她的思绪安静下来”。从具体段落来看,起笔就是“织云的心情像天空一样明朗……”,这时的织云是高兴的、自满的,与“令人心醉”毫无关系。葛浩文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把握翻译的逻辑性,这时如果突然来个“令人心碎”,则会显得逻辑不通。但从小说来看,织云的命运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平静是暂时的,因为她摆脱不了乱世安排给她的人生布局。对于译者而言,他直面的是原著,考虑的是译作的读者,同时也在审视他所译作品的合理性。这样的省译处理同样出现在英译著作《米》的第一段,原著一开始就将五龙这个主人公展示给了读者,但在译著中一个年轻的异乡人取代了五龙。在不触及原著表意的准确性后,葛浩文灵活地处理了原著中对目的语读者来说不可理解的地方,使文章更具逻辑之美。
四、解析“雅”的根源
秉承着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热爱,葛浩文成为现当代中国文学英译的先锋,“雅”也成为葛浩文在翻译时所追求的标准。葛浩文曾经说:“有一段时间我很想当个中国人,二三十岁的时候,觉得中国话美,中国姑娘美,什么都美,在家里穿个长袍什么,多好。”(转引自季进,2009:45-56)葛浩文在20世纪60 年代规避了中国传统文化饱受颠簸的时代,在中国台湾与中文结缘;回美国后在读硕士期间涉猎了中国古典文学、戏曲和元杂剧,在读博士期间研究作家萧红及其作品。葛浩文的《萧红评传》使他在中国小说评论方面占有一席之地,但他更爱中国小说的英译。作为中文小说的译者,葛浩文从事的是异域和边沿文字的翻译,选择的是彳亍独行的“苦行僧”之道。有评论家认为葛浩文的译文之所以美,正是因为他熟谙英语读者审美趣味,并借助自身高超的英语写作能力,使作品之表现形式和作品内容具有了审美意味,从而获得艺术性和可读性的完美统一(季进2009:45-56)。这也正是葛浩文翻译“雅”的表现。葛浩文的“雅”不仅来自横跨两种语言的障碍,还来自钟情于作者、读者和语言内在美的张力,更来自浸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精神和执着。
葛浩文在阅读苏童的著作《米》时认为小说中的一切都在黑暗之中,苏童将人的恶的一面(bad side)展现得淋漓尽致(转引自张艳,2013:79-82)。在某次评论中,葛浩文(2014:188-192)认为“苏童的这部长篇小说和多部短篇小说把中国近几年的历史——又借助暗指,旁及当下——写得一片漆黑”。译者在翻译时自然地将自己的阅读体验展现出来。葛浩文从语言、情节和人物的性格及逻辑方面审视原著。葛浩文的译著在“信”和“达”上没有过多的障碍,但在“雅”上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追求。意大利美学家、文学评论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在其美学名著《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翻译必须靠再创造,就是要求译者读到一篇原文并把它放回熔炉即思维中,让它和译者个人的思想、性格融为一体,然后创造出新的表达形式”(转引自李文革,2004:35)。葛浩文要完成尽善尽美的表达方式,让读者在阅读中找到一种节奏和美感。文学翻译应使读者感到他所读的是艺术作品,能从中获得智慧、知识,从中得到美的享受,感到与原作相应的艺术感染力(葛艳梅2015:70-76)。葛浩文之所以不断地提到《米》的翻译,其内在的原因是《米》这部小说将人性的恶以一种震撼的力量传达出来,引起了共鸣。从这一点来讲,葛浩文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文化的,更是心灵的、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