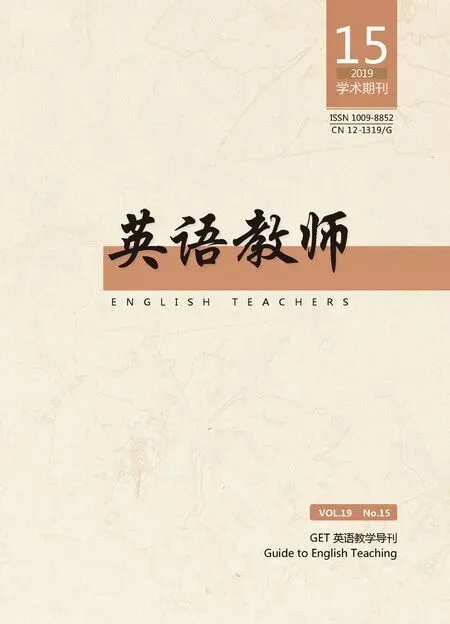二语习得者的文化身份特点对英语教学改革的启示
王秋菊
近二十年来,语言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关系研究是国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在外语教学过程中,应更加注意语言学习者身份认同的变化对于语言能力提升所发挥的作用(张浩2015)。语言是文化身份的外在表征和重要表现手段,而二语习得者的文化身份变化发展则是语言学习变化发展的内在体现。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二语学习是使用新的中介工具进行“自我建构”的认同转换过程,在社会交往中二语学习者积极参与意义建构,将目的语文化内化,构建一种新的文化身份,并通过该过程习得第二语言。这个内化过程不是简单地全盘吸收,而是一个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通过语言活动同外部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学习者认同和接受第二语言的文化规范,同时把言语行为和语言表述协调到合乎目的语文化规范的状态,在文化融合中努力寻求平衡点。二语学习者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文化身份的发展过程就是其语言能力发展提高的过程。
一、二语习得者的文化身份发展
学习者在习得二语的过程中,其母语文化身份和目的语文化身份之间具有差异,呈现分裂与统一的特点。在学习外语、了解异文化的过程中,文化的多样性和变动性决定了文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二语习得者的母语文化身份就会发生某种变化,表现为文化身份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出现文化身份的变化与分裂问题。但人类共同的生活决定了不同文化之间会有交融相通的地方,这种共性即二语习得研究中所谓的“共有知识”,是人类认知上的相似之处。人类思维的共性特征在二语习得者身上表现为母语文化身份与目的语文化身份在某种程度上的统一特征。而正是由于这些共性才使跨文化交际成为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些共性为认知的基础,差异才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渐渐缩小。
(一)二语习得者文化身份的动态曲折发展
文化身份并非直线式发展,而是一个长期曲折的逻辑过程,是一个循环往复、逐步升级的动态状态。正如斯图亚特·霍尔(2000)所言,“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文化身份“既是一种‘存在’,又是一种‘变化’,它在连续性中有着差异,而在差异中又伴随着连续性持续的存在”(阎嘉2007)。在冲突过程中,人们加深了对异文化的认知,强化了对异文化的认同,更明确了文化的差异,进一步扩大了文化身份的认同范围。这种随着时间的积淀形成的语言文化,又会促使新的身份认同标准的产生,差异出现,排斥现象又随之产生,身份处于新的分裂状态。所以,文化身份认同的出现并不能看作是终点,而应视为文化身份变化新的起点。
学生在利用已有文化知识试图理解新的文化信息的同时,其内化的母语文化系统也在发生分裂与变化。在冲突过程中,二语习得者表现出不同的文化身份认同模式。有的坚持原有的文化身份定位,以自己的母文化为交流与合作的基础和前提;或者逐渐接纳异文化,改变自己的原有文化身份;有的表现出双重文化身份,但表现出对其中一种身份更强烈的认同感;还有的在保持原有文化完整性的同时,不断与异文化比较,对原有文化内容进行文化整合,试图将两种文化不分主次地融合为一。不管是哪种文化身份,不论是“削减性文化认同”(母语及其文化观念被目的语及其文化观念所取代的趋势或程度)、“附加性文化认同”(学习者并用两种语言、行为模式及观念的程度),抑或是“生产性文化认同”(母语与目的语水平及对两者文化理解力的相互促进的程度)(高一虹、周燕2008),在其形成、发展中,学习者的母语和目的语文化身份在交流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经历母语和目的语文化身份的裂变、融合过程,从而在身份的冲突与统一中习得二语。
(二)语言发展与文化身份发展的不平衡性
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生理、心理及社会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对所学语言的态度、动机、社会环境等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些都影响着二语习得者文化身份的发展、变化过程。随着二语学习时间的增多及外语文化输入的增加,学习者的二语文化身份认同度也随之增长(胡旭辉2008),学生的二语水平越高,越倾向于认同二语文化(高一虹、周燕2008;冯卉、安守荣,等2015)。
但语言的变化和文化身份发展并非是亦步亦趋的,语言与身份并不总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随着环境、情境的改变随时发生着变化(Norton 1997)。有研究发现,英语水平高低与学习者对英美文化的认同的高低不一致(任小华2011),或是文化能力远远落后于语言能力(钟华、樊威威,等2001)。尤其对于工具型动机的学习者来说,这种英语水平与文化认同不同步的现象很是常见。边永卫、高一虹(2006)提出双语认同的一般发展模式:先由工具性双语认同发展为削减性双语认同或附加性双语认同,最后发展到生产性双语认同,但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只有略微过半(52%)的学习者呈现出这一模式。有的研究发现学习者的自我认同在生产性变化出现后削减性变化依然持续(刘璐、高一虹2012);有的则发现文化身份的附加性变化与生产性变化出现之后,又出现了削减性的变化(熊淑慧2009)。由此可见,二语习得者的语言发展与文化身份发展并不总是一致的,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这同样也说明,二语习得者的文化身份现象并不稳定,不是、也不必是一个衡定的状态,会在两种文化认同中来回摇摆。
(三)二语习得者文化身份的全球化趋向性
不同的文化在相互碰撞的过程中既有冲突的一面,又有融合的一面。文化间的差异是可以被认识、理解并能从无意识过程到有意识过程得以超越(高一虹2000)。而且,文化具有适应性、外向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因而,在全球化语境下,世界上各种文化必然可以形成一种具有内在精神的统一发展趋势。
人类社会经历了和正在经历从“异”到“同”的发展变化。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文化传播中,语言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语言的全球化和被全球化(Fairclough,N.、田海龙2010)。语言在交际与思维两个层次上的全球化特征,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张杰2002)。当前越来越多的学生生活方式西化,崇尚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不能不说部分是因为全民学英语过程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影响的。尤其是思维的语言全球化,更快速、便捷地为不同文化提供相互交流、相互吸取和整合对方的文化成分,他们之间的文化共性会进一步增大,在更多的问题上会达成共识,必然推动一种反映人类共同利益、共同要求的文化形式的出现。互联网时代全球性的文化交往更促使文化边界消失,呈现出一种全球互动的态势。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的同质化及趋同现象,形成某种或者某些共同的文化特质。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二语习得者的文化身份在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差异、冲突中从分裂逐步走向统一。
但这种统一呈现出以往所不具有的新特征和新趋势,具有新的时代意义。它是一种多元文化共存、和谐共处的跨越国家、民族疆界的状态,具有文化身份的多重的、不断构建的、随时变化的特点,处于一种不断混杂变化的过程之中。尤其是以“和”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复兴思想的提出,特别是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建立,与外语文化融合的步履加快。在“东学西渐”的进程中,汉语文化走向世界,从而推动文化全球化中主导地位的形成,为人类文化多元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文化的传播必然会影响世界文化,从而对全球化语境下的二语文化身份建构产生影响。
二、二语习得者文化身份发展对英语教学改革的启示
英语学习者应是“对话性交流者”,在尊重与反思中通过中西对话交流达到个性和人类共性的整合(高一虹2014)。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学习者深切地感受到中西方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客观、公正地进行中西文化比较,从而促进其文化身份与语言能力发展变化,逐步培养出通晓中西文化,具有国际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这也是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对英语教育提出的要求。由此,均衡、合理的中西文化输入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英语教学中西方文化输入“一边倒”的情况严重妨碍了英语教学目标的落实,导致当代英语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冷漠和疏离,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致使其民族文化身份弱化甚至缺失,出现中国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冯卉、安守荣,等2015)。英语习得者文化身份发展的不和谐现象在语言能力上则直接表现为学生的中国文化知识匮乏,难以用英语正确地表达中国文化,尚不具备向外输出、宣传、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良好英语表达能力。而母语水平是外语学习的天花板,外语的真正水平是以母语能力为前提的(潘文国2013),因而,英语教学亟需改革,保证教学中输入合理、充分、有效的中西文化,促进语言学习者构建理想的身份认同,以利于英语语言技能的提高。
首先,在课程设置中提高中国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比重,增加中西方文化对比内容的学习。外语文化的学习与母语文化学习密不可分,多元文化环境更能使学习者比较不同的文化,更能培养他们的文化反思能力(周岐晖、陈刚2015)。课程设置要明确设定中国文化教学的目标、内容和要求,体现中国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合理定位,反映英语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统一。在保留传统的综合英语课程及英美文化课程的同时,增加中国文化英语课程并开设相关的文化比较课程、跨文化交际英语课程。通过中西方文化对比,实现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让学生领悟到中西方文化的关联性与差异性,加深学生对中西方文化的认知与理解。
其次,在课程体系上应循序渐进,保持课程设置的连贯性和承续性、统一性与多样性。二语习得者文化身份与语言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需要在英语教育的长期目标中得到增强。正是考虑到外语学习的规律,新制订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提出“要充分考虑语言学习的渐进性和持续性,在大学本科学习的不同阶段开设相应的英语课程”。各个学校在校本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学生的实际水平、专业及兴趣等,充分考虑差异性,开设英语必修课与选修课,摒弃只在大学低年级开设,以学习语言为目的的基础英语教学,增加“专门用途英语”等个性发展课程,保障后续个性化学习和专业英语学习的需求。
第三,改革教学模式,实施实践英语教学。语言的切身实践有助于语言学习者发展自我反思能力,以开放、理性、包容的态度看待世界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增强多元文化意识(高一虹2014)。课堂上,文化内容教学要以学生的体验代替教师的讲解,通过视听资源、图片或实物展示、角色扮演,互动交流、文化案例与讨论等方式认识中西不同文化的本质和内涵。另外,大力增加跨文化交流活动,坚持“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学校既可以为中外学生搭建有效的沟通平台,组织多种跨文化活动,又可以定期邀请外国留学生进入英语课堂。例如,中国高校的国际留学生日益增多,他们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教育背景、语言与生活习性不同,如果有计划地让他们参与大学英语教学,不失为一个让学生了解多元文化的机会。让学生走出课堂,参与有关跨文化的英语辩论赛、专题讲座、社团等,或参加海外交流互访项目、出国交流学习。中外学生的沟通和融合更能促进学生的国际化意识及国际交流能力的提升。
第四,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审慎选择文化资源。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课程、各类交流工具和平台、电子图书与期刊等,给学生提供大量的信息资源,引导学生主动、积极地阅读,促进其知识更新和自主学习。特别是让学生参加慕课、全球理解课程等具有很强的交际实践性的课程,使他们在学习语言的同时,理解世界的多元性、全球社会存在的重大共同问题、国际发展现状与国际准则,学会共处,学会合作,最终形成国际责任感、民族自豪感和全球意识。但文化资源广博浩瀚,这就要求教师及有关人员对庞杂的信息进行组织、筛选和整理。针对学生的学习规律、学习兴趣和专业需求,优化网络资源,确保资源内容的丰富性、准确性、实用性,减少学生资源利用的盲目性,充分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除此之外,还要提升英语教师的文化自觉,提高其文化教学意识与能力。英语教师不仅要在教学中重视文化输入,还要适时调整教学内容、改变教学设计,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更要及时更新知识、转变观念,从而提高文化选择能力。同时,重视考试的反拨效应,对高校英语的考核内容、评价方式、评价主体等方面进行改革,采用多元化的考评方式等。
结语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展开和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持续提升,中国的外语学习者担负的弘扬、传播中国文化,增进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沟通、了解,树立中国国际形象的重任进一步加强。二语学习者的学习背景是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快速转型的社会,不论是语言,还是社会文化均具有多样、变动、复杂而微妙的特点。二语学习者要掌握不同民族的共同文化知识来理解语言,深入考察文化与语言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关注文化差异,将语言学习与文化个性有机融合。在保持其母语文化身份的前提下,二语学习者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目的语文化身份意识,确立恰当的全球化语境所要求的多样化的文化身份,从而提升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